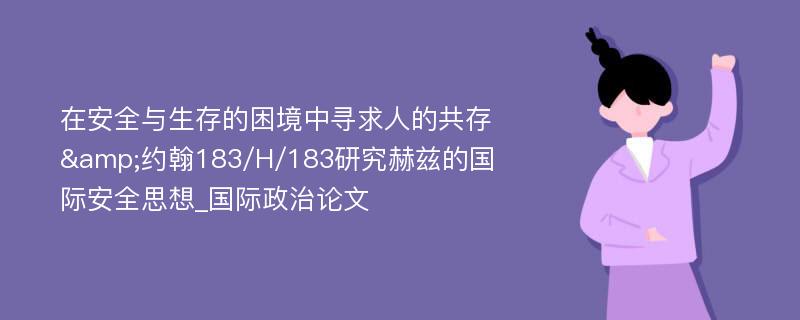
在安全与生存困境中寻求人类的共存——约翰#183;H#183;赫兹的国际安全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困境论文,人类论文,思想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安全和生存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政治学科重点关注的课题。“国际政治研究不能是脱离实际的‘纯’研究,它必须同时致力于揭示所面临的致命的危险并为必要的行动指明方向。”①这是20世纪著名德裔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翰·H·赫兹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所设定的目标,他的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堪称典范,在安全与生存困境中寻求人类的共存是他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这份执著和追求不断地催生了他一系列睿智的思想和原创性理念,从“安全困境”到“生存困境”,从“普世主义”到“生存伦理”,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于今天的人类应对21世纪各种全球性安全与生存危机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安全困境:赫兹国际安全思想的核心概念
1908年9月23日,赫兹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先后就学于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1931年获得科隆大学的博士学位。1933年希特勒掌权后被迫移居海外,1935年进入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所,在这里,赫兹撰写了他的国际政治研究处女作——《国家社会党的国际法学说》(The National Socialist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Law),正是希特勒纳粹政权的政治迫害唤醒了赫兹的国际政治权力意识,但该书在德、奥相继被禁。②1938年赫兹移民美国,从此开始了在美国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历程。
赫兹曾自述其安全困境概念在移民美国后不久就已经接近成形,③赫兹是这样描述“安全困境”的: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民族国家(或地区)间的相互不信任和相互惧怕导致了安全成为各自的首要目标。为获得安全,各国竭力增加军费,力图获得军事上的优势,改善自身的安全状况。但由于军备竞赛是互动的、无休止的,一国的军事优势很快被其他国家同样的扩军努力所打破,因此使得绝对的安全变得不可能,各国陷入了一种无从解脱的困境之中。④
与赫兹提出“安全困境”说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国际关系学者都是从人性角度来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他们大致又可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个学派。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人性本恶,人生来就是自私的,正是这种自私的人性驱使着人及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彼此相互竞争,不断追逐更多的权力是他们永恒的目标,这样,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在大部分现实主义学者看来,战争更多地是由人及国家自私的本性决定的,是不可避免的。与之相反,理想主义建立在人本善的人性论基础之上,它坚信战争可以通过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和国际法等来加以避免。而赫兹的“安全困境”说则第一次从社会结构层面对国际关系进行诠释,从而为人们思考有关避免战争和维护安全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思路。“安全困境”说很快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为结构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⑤结构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著名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指出:“上溯至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和古印度学者考蒂尔亚(Kautilya),武力的使用以及控制武力的可能性始终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首要关注。约翰·赫兹创造了‘安全困境’这一术语,用以描述这样的一种环境。这一困境无法得到解决,只能加以或难或易的应对。”⑥正是以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这样的结构性因素而非人性论为基石,结构现实主义才成为迄今为止最为简约、最富有科学性的国际政治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明确指出:“‘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文献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它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⑦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基欧汉也非常强调安全困境这样的体系和结构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体系理论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理解行动本身之前,必须理解行动的环境;结构理论是重要的,因为它为透彻地分析世界政治中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动,提供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工具。⑧当今美国国际政治领域三大主流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几乎都接受了安全困境的前提假说,只不过他们对安全困境的根源或成因以及解决途径的思考不同而已。安全困境说还催生了许多不同视角的相关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安全困境的不同前提假设进行研究⑨;有的涉及安全困境概念的进一步界定⑩;有的致力于不同类型的安全困境研究,如把安全困境分为“体系诱发型的安全困境”(system-induced security dilemma)和“国家诱导型安全困境”(state-induced security dilemma);有的研究了同盟国的安全困境问题(11)。冷战结束后,随着美苏两极对抗的终结,许多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或文化冲突加剧,一批国际关系学者开始把赫兹的安全困境理论用来分析国家内部的冲突和民族纷争等问题;近来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有关安全困境的缓解和逃逸研究(12),另一些学者则主张建立安全机制以对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13);还有学者强调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信息交流和观念建构对于缓解安全困境的决定性作用,如建构主义学派等。这些对于安全困境的进一步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赫兹“安全困境”理论的洞察力、影响力和持久力。
赫兹的安全困境概念对国际关系实践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50年代的“日内瓦精神”(通过外交而非武力解决争端的思想之再现)的形成和60-70年代美苏之间有关核武器部分禁试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签订都与安全困境说的传播和影响不无关系——它们正是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和超级大国的领导人逐渐意识到国家间所存在的安全困境的背景下才得以产生的。
今天的世界仍然深受赫兹揭示的“安全困境”问题所困扰,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安全困境”思维仍然主宰着当今的国家间政治,它突出地表现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军备竞赛上。尽管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经济已陷入寒冬,但与全球经济整体衰退相比,全球军费反而大幅攀升。(14)其次,“安全困境”思维在当今的一些大国关系中和热点地区表现得尤为突显。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些经济因素也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龃龉摩擦,但是造成它们战略关系恶化的最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安全困境”因素。
二、生存困境:赫兹国际安全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冷战期间,两大对立的集团在军事上的激烈竞争与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科技发展给人类所造成的生存困境。随着冷战的结束,人类对于自己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99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21世纪科学与文化:生存计划”国际讨论会上,与会各国科学家签署的《关于21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明确指出,“造成我们今天这些(生存)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科学上的进步。”(15)其实,早在此之前,赫兹就敏锐地洞察到了科技发展是造成人类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核武器发明之后,赫兹较早地意识到了核武器对国际政治以及人类安全与生存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他指出,在核时代,核武器使领土国家丧失了其传统的“不可穿透性”(impenetrability)和“可保护性”(defensibility),传统的国际安全体系和战争体系都失去了可控性。核战争的爆发无异于人类的集体自杀。由于每个人的安全和生存都时刻处于不确定中,它使人类第一次有了一个共同的生存目标:阻止核战争的爆发。(16)20世纪中叶以原子技术诞生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开始之后,赫兹就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更早地意识到了科技发展有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1960年代之后,他开始关注科技发展进程与人口爆炸、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即今天有些学者所称的“3P”问题(population explosion,preservation of nature,pollution of environment)及整个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17)这些都体现了赫兹在此领域研究上的前瞻性。
赫兹还及时地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缓解或摆脱生存困境的方法。针对核武器的出现所造成的生存困境,赫兹提出了“护持”(holding operation)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两步走战略。“护持战略”是赫兹针对1950年代末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提出的一种务实战略思想。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和平与共存。其主要手段是双方互相界定和认可彼此的势力范围,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理性,以避免矛盾的激化和战争的爆发。赫兹提出的“护持战略”有两大贡献:其一,它充分认识到全面核战争的爆发意味着“集体自杀”的严峻后果,对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的认识是辩证和合理的,既避免了“核威慑可以带来核和平”之类的盲目乐观,也抛弃了那些对原子时代的核威胁和核恐怖的过分悲观绝望。其二,“护持战略”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实践来说,特别是对于大国的决策者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沿着“护持战略”的思路,冷战才一直没有发展为热战。
赫兹指出,核战争爆发的集体自杀性特征使人类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避免核战争爆发以确保整个人类生存已成为人类追求的普世利益和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人类有时不得不牺牲短期的、局部的利益。这就是赫兹提倡的“普世主义”战略。赫兹明确指出,“普世主义”战略是人类的长期目标,在很多国家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会信奉“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国际政治现实中,期待它在短期内能得以实现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不应放弃这一追求。
针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3P”问题,赫兹指出,既然“生存困境”缘于技术的飞速发展,那么人类必须改变有关技术发展的理念,在现代社会里人类应该反对技术服从主义,提倡技术反叛主义,要提倡人类控制机器,而不是相反,否则人类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为此赫兹呼吁开展“技术反叛”运动(a campaign of "technological disobedience")。(18)为了最终摆脱核武器和“3P”问题所造成的全球性“生存困境”,1974年12月赫兹在以色列海法市举行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最小生存伦理”(a minimum ethic of survival)概念。生存伦理指的是:为了整个人类的生存,所有的国际行为体都必须遵守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或准则。赫兹的“生存伦理”是一种广义层面的国际伦理,一种“全球性”或“普遍性”的伦理,即所谓“普世伦理”。
三、普世主义与生存伦理:赫兹国际安全思想的现实意义
由“安全困境”到“生存伦理”,赫兹的国际安全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和升华的过程。在人类步入了一个新的千年时,全球化进程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进一步加快,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两者的迅猛发展给21世纪人类社会造成了一系列深刻复杂的全球性问题,而其中最为严峻的仍然是“安全困境”和“生存困境”问题,赫兹的“普世主义”与“生存伦理”思想对于人类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普世主义:一种日益明显的历史趋势
与赫兹提出普世主义思想的20世纪中叶相比,今天的世界正面临着更多的全球性挑战。除了核问题外,其他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如贫富悬殊、生态恶化、资源短缺、气候变暖、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毒品走私、拐卖妇女儿童、全球性疾病、国际金融危机等等。与诸多全球性危机日益加剧的背景相背离的是,现实主义的逻辑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指导或制约着国际关系实践。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理性国家只能按照自助的原则争得利益和求得安全;国际政治是不同国家相互竞争、追逐更多权力的“游戏”,是一种典型的“权力政治”,“强权即真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对抗性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人类共同利益不仅不具备合理性,而且似乎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的逻辑当然有其现实的基础,但它反映的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关系,该时期的社会发展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人类根本上还没有形成“命运共同体”,人们的社会关系只存在于个体安身立命的特定阶级、民族和国家,因此人们不可能具有人类共同利益的意识和观念。但是,今天人类生活的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的利益存在和实现条件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全球化发展大大加强了人类整体性联系,人类在经济、政治等诸方面利益上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人类利益的整体性不但业已形成,而且日益加强。另外,不论在面临全球性危机还是在民族国家发展等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闭关自守,独自为战,完全局限于本民族或国家的视野和利益。由此,人类整体利益及其实现要求人类必须形成一种合作与共存的社会关系,而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急切地呼唤人类形成一种新的思维观念,因为现实主义的逻辑已经与当代现实的要求越来越相背离。普世主义是一种与时代发展要求相契合的新的意识和观念,它所蕴含的全球意识和合作意识是人类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前提条件。普世主义的核心就是要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和共同性,强调人类和平、安全与生存的不可分割性,强调在应对危机时各国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强调在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普世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要给予长远利益和普世利益更多的考虑和重视。因此,与现实主义的逻辑相比,普世主义的理念更加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当前,尽管民族国家仍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民族与国家利益仍是当下人们所认同的最基本的共同利益,(19)但是,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业已形成的事实使普世主义成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历史趋势,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2.普世伦理:必要性与可能性
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普世伦理”(universal ethics)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显然,赫兹的“生存伦理”属于一种典型的“普世伦理”。在今天的世界里,是否需要建立“普世伦理”?有没有可能建立“普世伦理”?有些学者,特别是诸多的现实主义者,对此问题一直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中既不存在“普世利益”,也没有建立“普世伦理”的必要。笔者认为,在今天世界里,建立普世伦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它是人类必须努力共同完成的一项十分紧迫和艰巨的任务。建立普世伦理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普世伦理的建立是实现世界“和而不同”的有效手段。全球化并不等同于经济、文化同质化,而是多元化的互渗。它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和伦理方面的“碎裂化”甚至相互冲突要求不同文明之间经常进行对话和沟通,寻求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认同,建立得到各方认可的普世性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目标。
其次,普世伦理的建立有助于摆脱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危机,确保人类文明的存续。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全球性的危机和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物”的世界。现代社会和现代人已经陷入深刻的“文化危机”、“意义危机”和“道德危机”。其危机之深已使得普世伦理成为人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时代性课题,而现有的各种伦理观念,都已无法单独满足现时代的道德文化需要。这些都是提出普世伦理所基于的最基本的事实判断。(20)
再次,建立普世伦理是“人之为人”的必然要求。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行为的一切都以人的利益作为唯一尺度,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取向具有至上和绝对性,这种伦理价值观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当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层次,即当满足自身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已经不再困惑人类时,人类就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是人之为人的要义。
建立普世伦理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普世伦理的建立具有现实的生活基础,特别是利益基础。全球性“普世伦理”的建立或人类在伦理上共识的达成,在根本上决定于人类的“共同生活实践”。(21)当前,包括经济全球化趋势、网络和信息传播的同步化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全球安全问题、全球文化的互渗等,这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需要并且会导致全人类形成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
第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和科技的加速发展使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交往、交流和沟通进一步增多,为人类取得对共同利益和价值目标上的认同以及建立普世伦理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普世伦理的建立依赖于一定的人性基础。构成普世伦理的人性基础,是人类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社会理性。社会理性使人们能够意识“共同生活”的需要和共同的利益,同时也使他们有可能进行思想的交流和对话,从而对“共同生活”的伦理基础形成一定的共识。
第四,历史和现实让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以及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建立普世伦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是建立普世伦理最重要的推动力。
尽管在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的今天,建立“普世伦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当今世界建立普世伦理仍然面临许多障碍。其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一些经济大国依然操纵世界主要事务,强国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仍然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其二,群体主体与个体主体之间的矛盾仍然很突出。现代性的核心是以人为绝对主体和最高目的的主体主义,它导致了人对自身狭隘利益的极端关注,而无视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存在价值,具体表现为个人全球责任意识的缺失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三,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工具理性逐渐压制了价值理性,并开始在各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物质利益的重视仍然胜于对自由、平等和人权价值的追求。只有人类扭转了工具理性的支配地位,恢复价值理性的合理地位,“普世伦理”的建立才有可能;其四,一些西方大国利用宣扬“普世价值”的机会,实则推行本国或某些利益集团的伦理和价值,这种文化霸权主义无疑会使其他国家人民建立真正的“普世伦理”的信心和努力受到极大的影响,严重妨碍真正的“普世伦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因此,建立“普世伦理”必将是人类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John H.Herz,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D.McKay,1976,p.6.
②参见John H.Herz,"An Internationalist's Journey through the Century," Joseph Kruzel and James N.Rosenau (eds.),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Thirty-four Academic Travelers,Lexington:D.C.Heath and Company,1989,p.248.
③John H.Herz,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the World Politics,p.8.
④John H.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1.
⑤参见叶江:《“安全困境”析论》,《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
⑥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250-251页。
⑦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48页。
⑧罗伯特·O·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⑨参见Nicholas Wheeler and Ken Booth,"The Security Dilemma," in John Baylis and N.S.Rengger(eds.),Dilemmas of Word Politics: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
⑩Alan Collins,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Edinbrugh:Keele University Press,1997.
(11)Glenn H.Snyder,"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36,No.4 (Jul.,1984 ) ,pp.461-495.
(12)参见Barry Buzan,People,State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2nd ed.,1991,p.177.
(13)Robert Jervis,"The Security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36(2) ,1982,p.178.
(14)《世界银行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将下滑1.7%》,http://finance.people.com.cn/GB/9059385.html.
(15)余谋昌:《生态文化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73页。
(16)参见John H.Herz,"Political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25,No.2 (Jun.1981 ),p.188.
(17)参见John H.Herz,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the World Politics,pp.22-23.
(18)参见John H.Herz,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the World Politics,p.194.
(19)梁守德、李义虎主编:《全球化与和谐世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20)万俊人:《普遍伦理及其方法问题》,《哲学研究》1998年第10期。
(21)高扬先:《关于建立普遍伦理的思考》,《求索》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