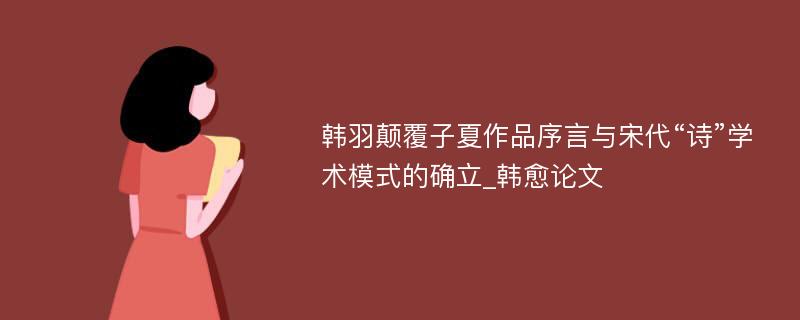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格局论文,韩愈论文,子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诗序》,四库馆臣谓之“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以《诗序》的作者为例,即大致有十六种、十七种、三十种等说法,去其重复,“异说恐不下二十余种”①,实千古聚讼之端。学者们如此热衷于《诗序》研究,原因就在于《诗序》总括“一篇之义”②,决定了《诗》的经学性质;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系统化的诗学理论,为后世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故但凡说《诗》,则欲一究《诗序》之根本。其中,关于《诗序》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作者”,它关系到《诗序》产生的时间、内容的权威性以及《诗》学传承谱系等。因此,古今以来争论大多聚焦这一问题上。中唐之前,学者们对此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子夏作”、“子夏、毛公合作”与“卫宏作”,其实后两种说法都是从“子夏作”衍伸而来,所以中唐前关于《诗序》作者的主流意见就是“子夏作”。而韩愈一出,便要挑战“子夏作”的权威,将汉唐以来围绕《诗序》的结论全部推翻,这是《诗》学历史上意义重大的变奏动向,也是《诗》学发展最突出的转折点。 一、“子夏作《序》”说 最早提出“子夏作《序》”的,是汉代经学家郑玄。此观点,汉唐以来,主流《诗》学研究皆从之,如王肃云:“子夏叙《诗》义,今之《毛诗序》是”③;陆德明云:“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④;孔颖达提及子夏作《序》达十次之多;魏征认为子夏作《序》,毛公、卫宏有所润益而已⑤;司马贞云子夏序《诗》⑥,等等。“子夏作《序》”,是汉唐《诗》学研究的共识,确立了《诗序》在《诗》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孔子距离《诗》产生的时代最近,且是《诗经》的第三次编辑者⑦,子夏“亲受圣人”,《诗序》由他所作,则能较贴切地反映《诗》的创作初衷,如此一来,《诗序》所传达的关乎人伦道德的政教意义,就都是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汉唐经学家尊奉“子夏作《序》”,皆据《序》说《诗》,可以说《诗序》决定了汉唐《诗》学恪守“政教”的特征。 第二种观点“子夏、毛公合作”,也是郑玄提出。此说不见于今之《诗谱》。关于大、小《序》,陆德明引旧说云:“起此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迄末名为《大序》。”⑧此处郑玄区分大、小《序》,一则表明《诗序》是逐步完善而成;二则将《大序》从《关雎序》中抽离出来,凸出了《大序》的重要性,是谓“宜引以冠经首,使学者得以考焉”⑨;三则为后世的《诗序》研究提供了新门径,宋代学者谈及《诗序》多以大、小《序》分别论之,如程子以为《小序》乃国史之旧文、《大序》为孔子作⑩,等。针对《诗序》,郑玄本人就前后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则在东汉时已不能确知《诗序》的作者。但无论哪种说法,郑玄对“子夏作《序》”深信不疑。 第三种观点“卫宏作”,最早是由陆玑提出。陆玑认为子夏所作的《序》,并非今之《毛诗序》,其后东汉卫宏乃作《毛诗序》。这是《诗》学史上首次将子夏《序》与《毛诗序》视为两家;也是首次提出卫宏作《序》,后世主张卫宏作《序》者皆从此说,如范晔云:“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11)姚际恒云:“大抵《序》之首一语为卫宏讲师传授(即谢曼卿之属),而其下则宏所自为也。”(12)夏炘云:“《序》为卫宏作无疑矣”(13)等。陆玑主张子夏作《序》、卫宏作《毛诗序》,言下之意,子夏的《序》是最原始的《诗序》,之后“四家诗”兴起,各自有《序》,《毛诗序》是卫宏因师说而成。四库馆臣云:“案《礼记》曰:‘《驺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蘋》者,乐循法也。’是足见古人言诗率以一语括其旨意,《小序》之体实肇于斯。王应麟《韩诗考》所载,如《关雎》,刺诗也;《芣苢》,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离》,伯封作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又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所作《独断》载《周颂序》三十一章,大致皆与《毛诗》同而但有首句,是《鲁诗序》亦括以一语也。”(14)《韩诗序》、《鲁诗序》与《毛诗序》大同小异,但惟有首句,故陆玑认为先有子夏《序》,后有卫宏《毛诗序》。这种说法,其实仍在维护“子夏作《序》”的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在韩愈之前,主张“卫宏作《序》”者并不否认“子夏作《序》”说;而韩愈之后,主张“卫宏作《序》”的往往是从反驳“子夏作《序》”开始,“意毛公既托之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15)又如,夏炘言:“先儒以《诗序》为子夏作,非也”(16)等,说明在《诗》学史上,韩愈提出的观点即如峰回路转,其首次挑战“子夏作《序》”,并引领了之后《诗序》研究的发展方向。 二、韩愈对“子夏作《序》”的颠覆 韩愈之前,《诗序》研究将“子夏作”奉为圭皋,直至韩愈提出“子夏不序《诗》”,将此前的观点一并推翻,《诗序》研究才真正意义上地翻开新的篇章。韩愈论《诗序》,首见晁说之所引: 善夫,韩愈之议曰:“子夏不序《诗》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17) 此说不见于今之《韩昌黎文集校注》,《全唐文》亦有目无词。晁氏之后,李樗也引此说,云: 韩退之作《诗之序议》则谓:“《诗》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辞不讳君上,显暴丑乱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经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诗序》,其汉之学者欲自显立其传,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国详、小国略,斯可见矣。”(18) 内容与晁氏所引不同,意思即晁氏所引的第二、第三两点。明代杨慎也引到韩愈论《诗序》,其云: 余见古本韩文,有《议诗序》一篇,其言曰:“子夏不序诗,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扬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三也。汉之学者欲显其传,因籍之子夏。”(19) 文中“知不及”与晁氏所引的“不智”稍有出入。宋代范处义反驳韩愈之《议诗序》,即引作“知不及”(20),则在宋代开始就已经有“知不及”和“不智”两个不同的版本。历代对此的理解也不同,大致有两大类:(1)时代相隔久远,无法得知。范处义云:“子夏犹知不及,汉去诗益远,何自而知之?”(2)学力、领悟尚未达到。程子云:“《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21)学者多从此说,如王得臣、晁说之、员兴宗、杨慎等。但结合二、三点,韩愈明显是在反驳、推倒《诗序》,历代学者的解释却是以尊崇《诗序》为前提,这与韩愈要表达的意思并不一致。私以为“不智”应是最接近原貌的版本,一是,“不智”与“不道”、“不敢”在语言表达上前后一致;二是,韩愈认为《诗序》暴扬私闱、不讳君王,如此荒诞不经,必定不是子夏这样“可与言诗”者写出的;故从整个语境和前后文意,及韩愈对《诗序》的历史态度来说,“不智”都应该是指“不明智”的意思。 第二点“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所谓“暴中冓之私”,《诗序》中有很多讽刺统治者荒淫的内容,如齐襄公与其妹文姜通淫之事,《南山序》云:“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敝笱序》云:“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载驱序》云:“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这些都是直接讽刺襄公与文姜的鸟兽之行。又如《墙有茨序》、《君子偕老序》、《鹑之奔奔序》等,讽刺卫宣姜与公子顽淫乱宫闱;《株林序》、《泽陂序》讥讽陈灵公与夏姬淫乱,等等。韩愈认为此乃“《春秋》所不明”,《诗序》也不应暴扬在光天化日之下。如齐襄公与文姜淫乱,桓公三年《春秋》载:“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公会齐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齐。”《左传》云:“齐侯送姜氏于讙,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春秋》乃以“送”字刺襄公无礼。《春秋》以礼定褒贬,往往微言大义,对于齐襄公与文姜的鸟兽之行,仅云“送”“会”“至自”而已(22)。又公子顽与宣姜之事,《春秋》并无记载。范处义云:“大抵《春秋》虽严,而其辞深而婉;《诗序》虽通,而其辞直以著。”(23)《诗序》的表达方式与《春秋》迥异,前者直刺淫乱,后者隐晦深微,故韩愈认为《诗序》不合于“六经之志”。孔子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24)“六经”以“礼乐”为核心,今《诗序》斥言君王乃与“温柔敦厚”不合,故韩愈云“子夏不序《诗》”。 第三点“诸侯犹世,不敢以云”,也就是避讳君王的问题。子夏生活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此时《诗》中最后一位诸侯陈灵公也早已离世,故韩愈所谓“诸侯犹世”应是指诸侯后代尚且在世。要知道,《诗序》讽刺某君王往往直接点明,如“《雄雉》,刺卫宣公也”“《考槃》,刺庄公也”“《蟋蟀》,刺晋僖公也”等。于公子大夫之类更直呼其名,如“《有女同车》,刺忽也”,忽乃郑庄公世子;“《车邻》,美秦仲也”,秦仲乃周宣王大夫;“《墓门》,刺陈佗也”,陈佗乃文公之子,等。《诗序》毫无忌惮地斥言君王权贵,韩愈认为在诸侯犹活跃于历史舞台之际,公然刺其先祖,或不被诸侯所容,故云“不敢”(25)。韩愈自身即有“不敢”之事,谈到排斥释、老,其云: 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书出焉,其所以虑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至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辅相,吾岂敢昌言排之哉?(26) 此时贞元十二年,该年四月德宗命徐岱等与沙门鉴虚、道士万参成等讲论三教(27)。鉴虚云:“元元皇帝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陛下是南瞻部洲之圣人。”(28)德宗大悦。足见,三教合流之风盛行。韩愈提到王公贵族、公卿辅相皆事佛、老,若此时公然著书以排之,岂不是自掘坟墓?此韩愈之不敢为之事,以此揣度《诗序》之斥言美刺,认为子夏必“不敢以云”。 上述“不智”“不道”“不敢”三点,韩愈明确提出“子夏不序《诗》”。在韩愈之前,《诗》学研究皆认为“子夏作《序》”,这种说法确立了《诗序》的权威地位,也决定了汉唐经学家关涉政教的说《诗》趋向;而韩愈一出,大刀阔斧地就要颠覆“子夏作《序》”,公然挑战《诗》学权威、怀疑经典,这在《诗》学研究史上简直是划时代的声音。从汉唐以来,学者一直视为金科玉律的“子夏作《序》”之说,被韩愈一下子拉下神坛,而韩愈敢于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其原因及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种观念,对之后《诗》学发展又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在计较韩愈之说有多少合理性外,更应该探讨的问题。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其实是与重建儒学密切相关。韩愈对“子夏作《序》”的否定,是顺应了大历后所形成的对传统学术的怀疑大趋势。大历学风务求标新立异、以己意说经,多反驳传注旧文;发展到贞元、元和之后,这种反驳之风上升为对经典本身的质疑,并开始出现肆意增补、删改经文的动向,如白居易补《汤征》;陈黯补《语诰》;林慎思著《续孟子》;沈朗新添尧、舜、禹诗并《文王》诗四篇,置之《关雎》之前(29);柳宗元著《非国语》(30),等等。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韩愈也展开了对经典的系统性思考,否定“子夏作《序》”只是其中之一。此外,韩愈还否定《孟子》乃孟轲自著(31),否定《论语》旧注(32),并因此构建起新的经典系统。《原道》篇云: 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33) 此处确立了以《诗》、《书》、《易》、《春秋》四经为主的新经典系统,将原来孔子纳入“六经”的礼、乐划入法制体系中。表面上看来,这只是典籍归类的细微变化,很容易就被忽略了,而仔细考究便会发现,这一变化其实是对文化传承系统的重新调整,它将改变世人对“礼乐”的既定接受,“礼乐”不是作为修身养德的一部分,而是作为硬性规定的、必要遵守的法规。在德治与法治的天平上,韩愈是有一定偏颇的。韩愈对文化系统的建树,还有首次阐扬《大学》之义,《原道》篇将《大学》也列为经典。《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汉唐以来,并没有特别称道者。韩愈特意将《大学》的“修齐治平”“正心诚意”单独拿出来,与先王之教相关联,“提供了一个沟通心灵道德培养与国家秩序治理的思路”(34),使《大学》从个人修养的准则变为治国安邦的经典,是其意义所在。除此,韩愈又倍崇孟子。周秦之际,儒家中孟荀二派并峙。西汉时荀学为盛,仅扬雄对孟子有相当之推崇;此后直至韩愈一倡,孟说方大行,“《孟子》一书,遂成为宋明道学家所根据之重要典籍焉”(35)。《昌黎文集》中提到孟子达24次之多,其云:“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36)《孟子》也被韩愈划入经典系统中。则经韩愈之手,孔子的“六经”系统转变为“四经”与《大学》、《孟子》。尔后,朱子就是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四书”,承载着一套以“理”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世人言“四书”系统对宋以后的中国文化影响之大,往往将朱子奉为神明,殊不知韩愈的开创之功,实在可惜。 从否定“子夏作《序》”到确立新的经典系统,韩愈的本质目的是为了重建儒学。其实,韩愈曾明表心迹:“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故《诗》、《书》、《春秋》无疵,余欲削荀氏至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亦孔子之志与?”(37)孔子确立“六经”,构建的是一个传承文化的经典系统,人君循之则国治,士人修之则大吉,“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38);韩愈要继孔子删述之志,所以他整理典籍、确立新的经典系统,其目的就在于要重新激活民族文化的传承系统,要重建儒学,以维系世道人心。而韩愈颠覆“子夏作《序》”,就是重建儒学中隶属于整理典籍的一部分。韩愈重建儒学的举措又见诸所著《原道》、《原性》、《原鬼》等,从理性思辨的角度架构儒家关于性、命的学说,以夺回儒学在思想领域的霸权;更有,韩愈为阐明儒学的正统地位,以排斥佛、老,建构了历史第一个传道谱系,首次发表了“道统”思想,之后遂成为宋明道学家“致君行道”的思想武器。李翱谈及韩愈,云:“六经之风,绝而复兴。”(39)皇甫湜云:“(先生)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觝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40)欧阳修云:“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别以朴,划伪为真。”(41)韩愈的功劳不仅在于复兴儒学、抵触佛老,使文化正脉回到儒家的经典系统;也在于启发了宋代新的儒学思想及学术格局的形成。颠覆“子夏作《序》”,就对宋代的《诗》学研究有深远的影响。 三、韩愈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 韩愈之后,宋代《诗》学研究不再提“子夏作《序》”,范家相云:“疑《序》者始于韩昌黎,发于成伯玙,而宋儒从而力排之、舍《序》言诗者,始于苏颕滨,甚于郑夹潦、王雪山,而朱子因句诋而字驳之,嗣是以后或信或否,又分道扬镳,不可胜纪矣。”受韩愈影响,宋代《诗》学明显分为尊《序》与反《序》两大派,叶德良先生有一段概述:“治《诗》者,约可分为守《序》、反《序》二派。反《序》一派,大抵以为《诗序》晚出于卫宏(或卫宏以后人),不足采信。守《序》一派,则或推崇过当,有以为诗人自作者,如王安石是也;有以为《小序》乃孔子作者,如王得臣是也;有以为大、小《序》皆是国史作而杂孔子之言者,如范处义是也。唯反《序》一派,说诗每并《首序》、《后序》,俱不採信,直据本文为说。而守《序》一派,则或不信《后序》,以为杂有说诗者之言。”(42)无论守《序》,或是反《序》,皆无主张“子夏作《序》”者,现分别论之。 守《序》派,主要集中在北宋,如欧阳修云:“《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43)程颐云:“《诗小序》便是当时国史作,如当时不作虽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则非圣人不能作。”“《诗大序》孔子所为,其文似《系辞》,其义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国史所为,非后世所能知也。”(44)王得臣云:“予以为《序》非出于子夏,且圣人删次《风》、《雅》、《颂》,其所题曰美、曰刺、曰闵、曰恶、曰规、曰诲、曰诱、曰惧之类,盖出于孔子,非门弟子之所能与也。若‘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题,其下乃毛公发明之言耳。”(45)欧阳修所谓“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与韩愈所云“不智”是出于相同的逻辑;程子与王得臣认为首句非子夏所能,则是“知不及”之义。韩愈开了“子夏不序《诗》”的先河,守《序》派据此多以子夏“不智”“知不及”为由,否定“子夏作”,或以为国史自作,或以为孔子所为,务在尊崇《诗序》,维护《诗序》的权威地位。 反《序》派,以郑樵为首,云:“设如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46)又云:“卫宏之《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至数句者;有杂取诸家之说,而辞不坚决者;有委曲婉转附经,以成其义者。”(47)郑樵认为《诗序》乃卫宏所作,掺杂了经书、各家之言,并不可信。从此说者,主要活跃于南宋,如曹粹中云:“《序》若出于毛,亦安得自相违戾如此?要知《毛传》初行之时,犹未有《序》也,意毛公既托于子夏,其后门人互相传授,各记其师说,至宏而遂著之。后人又复增加,殆非成于一人之手。”(48)朱熹云:“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于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后。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于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后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后而超冠篇端,不为注文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后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49)章如愚云:“圣人删诗不为之序,非不能为之也,正使学者深维其义,而后可以自得。不幸汉儒之陋,一冠之以《序》,《诗》始无传焉。且彼又乌有据哉?不过多据《左氏》之说尔。《左氏》亦自诬妄,不足信,以妄传妄,反可信乎?”(50)朱熹等人延续韩愈观点,认为《诗序》出于汉儒臆度之私,主张“信《诗》不必信《序》”(51),说《诗》全凭己意断之,由此,反《序》派在否定《诗序》的同时走向了《诗》学研究的另一个极端,即去《序》说《诗》。之后,元、明两代针对“《诗序》废存”形成不同的《诗》学阵营,而朱子在《诗》学史上的权威地位也在此时确立下来。 可见,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乃造就了宋代的《诗》学格局——以守《序》与反《序》两大派别为主。一方面,守《序》派虽推崇《诗序》,但并不盲从,如欧阳修云:“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随而正之”(52);程子直言“《序》之误也”(53);王安石明辨《诗序》未允(54)等,这些意见都是从情理出发,着眼于《诗》本身。另一方面,反《序》派以朱子为代表,否定《诗序》,“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故主张去《序》说《诗》。朱子著《诗序辨说》专论《诗序》之失,又云:“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55)这段阐释中,所提到的“天道”、“理”、“情性”、“言行”及修齐治平,都是属于理学讨论的范畴,朱子已完全是从理学的角度来定义《诗》。朱子反《序》、探求《诗》理,便形成了与《诗经》汉学相抗衡的《诗》学新系统,更成为了元、明两代奉为圭皋的《诗》学新权威。 所以,由韩愈所引发的关于《诗序》的争辩,其实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鼎故革新。在宋代脱离《诗序》、全凭己意解《诗》的过程中,整个《诗》学系统经历了一次大换血,其本质原因是,宋代以“义理”为核心的新意识形态系统,替换了汉唐以来以“礼乐”为重的旧意识形态系统。汉唐《诗》学总是从政治教化的方面来阐释;而宋代《诗》学是从“天理人欲”的角度来阐释。因此,在宋人抛却《诗序》的背后,本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新阳改故阴”的大革命。正是“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56),中唐是唐、宋变革的过渡阶段,韩愈则是启发宋学的关键人物。 ①刘毓庆:《历代诗经著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15页。 ②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校勘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9页。 ③王肃:《孔子家语》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6页。 ④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2册,第366页。 ⑤《隋书·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18页。 ⑥《史记索隐》云:“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见《史记》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0页。 ⑦刘毓庆、郭万金:《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24页。 ⑧孔颖达:《毛诗正义》,第263页。关于大、小《序》之分大致有四种观点,除陆德明所引外,第二种是成伯玙认为,《关雎序》乃《大序》,其余众篇之前为《小序》(《毛诗指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174页);第三种观点是朱熹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乃为《大序》,其余为《小序》(《诗序辨说》,《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6册,第262页)。第四种是程大昌认为,“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谓大序者,宏语也。”(《考古编》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第10页)。文中郑玄所谓的大、小序是指陆德明提及的分法。 ⑨王鸿绪:《诗经传说汇纂》卷首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册,第1页。 ⑩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6页。 (11)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九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75页。 (12)姚际恒:《诗经通论·诗经论旨》,《姚际恒著作集》第一册,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3页。 (13)夏炘:《诗序》,《读诗劄记》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70册,第617页。 (1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集传》,第121页。 (15)朱彝尊:《经义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9年,第699页。 (16)《读诗劄记》卷一,第617页。 (17)晁说之:《景迂生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8册,第222页。 (18)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册,第3页。 (19)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第296页。 (20)范处义:《诗补传·篇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22页。 (21)《二程遗书》卷二十四,第312页。 (2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97、99页。 (23)《诗补传·篇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23页。 (24)《礼记正义·经解》卷五十,《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第1069页。 (25)对于《诗序》斥言美刺的问题,孔颖达却有另外一种观点,《齐谱疏》云:“子夏亲承圣旨,齐之君世号谥未亡,若有别责余君,作叙无容不悉,何得阙其所刺,不斥言乎?”认为子夏作《序》本就应斥言,君世之谥号本当详细道明(第455页)。韩愈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这是韩愈反对旧说、挑战权威的又一证明。 (26)韩愈:《重答张籍书》,《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页。 (27)《韦渠牟传》,《旧唐书·德宗纪》卷一百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28页),亦见《唐语林》卷六(第519页)。 (28)王谠:《唐语林》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9页。 (29)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年,第139—140页。 (3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441页。 (31)《答张籍书》云:“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30页)早在三国时,姚信即疑非孟子自著,但并未形成较大影响,在韩愈之后才引起了广泛注意。 (32)《答侯生问论语书》云:“愈昔注解其书,而不敢过求其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则足以信后生辈耳。”《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83页。 (33)《韩昌黎文集校注》,第18页。 (3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3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36)《送王埙秀才序》,《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62页。 (37)《读荀》,《韩昌黎文集校注》,第36页。 (38)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6页。 (39)《祭吏部韩侍郎文》,《全唐文》,第2864页。 (40)《韩文公墓志铭》,《全唐文》,第3119页。 (41)《新唐书·韩愈列传》,第5269页。 (42)《宋人疑经改经考》,第75页。 (43)欧阳修:《诗本义·序问》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93页。 (44)《二程遗书》,第312页。 (45)《麈史》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2册,第619页。 (46)郑樵:《诗辨妄·诗序辨》,《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6册,第227页。 (47)郑樵:《六经奥论·诗序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68页。 (48)朱彝尊:《经义考》,第699页。 (49)朱熹:《诗序辩说》,《续修四库全书》经都第56册,第261页。 (50)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诗序之辨》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8册,第86页。 (51)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1页。 (52)欧阳修:《诗本义·序问》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第214页。 (53)《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三》,第1049、1051、1059页。 (54)程元敏:《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二)》上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5、68页。 (55)《诗辨妄》,《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56册,第227页。 (5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页。标签:韩愈论文; 文渊阁四库全书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国风·周南·关雎论文; 国学论文; 原道论文; 文渊阁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