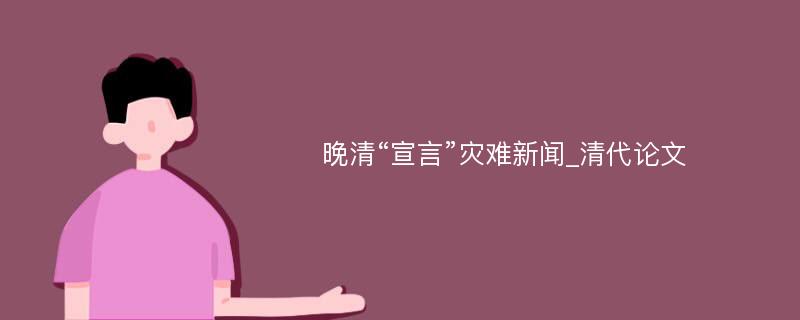
晚清《申报》的灾害新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灾害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3-0133-05 中国虽然从唐代就产生了报纸,但统治者对灾害消息的传播控制极严,导致古代报纸上的灾害消息极少。晚清以降,随着国门被打开,近代报刊在租界诞生。这些报刊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清政府的控制,开始大量报道各种社会新闻,真正意义上的灾害新闻终于产生。对于近代灾害新闻,目前学界尚无系统的研究。据笔者考察,作为晚清第一大报,《申报》报道灾害新闻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具有代表性。故本文以《申报》为中心,对晚清灾害新闻略作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近代灾害新闻的兴起 《申报》自1872年4月30日创刊后,大量报道社会新闻以吸引读者,其中就包括灾害新闻。初期的灾害新闻主要是转载《京报》上有关灾情和赈灾的奏折,《申报》自己采写的新闻很少。虽然这些采写的新闻比较简单,但已具备了灾害新闻的基本要素。如5月4日、26日,《申报》两次报道了法国牛瘟传到上海后的情况,既涉及灾情的发展,也关注救灾情况,内容完整,层次清晰。 1876-1879年,国内发生持续四年的旱灾——“丁戊奇荒”。面对这场大灾,《申报》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报道,标志着近代灾害新闻的兴起。这次报道的信息量很大,除转载《京报》消息、转译外报(主要是英文的《北华捷报》)消息外,《申报》还派出记者,进行跟踪采访。这一时期,《申报》的灾害报道逐渐变得丰富。 一些新闻史著作认为,1878年6月27日《申报》刊登的《豫行日记》是近代最早的通讯。《豫行日记》是义赈善士潘少安给《申报》发回的信件,记叙了他在河南归德府赈灾的情况。此信经《申报》转载而成为新闻。然而据笔者所见,在《豫行日记》之前,已有不少义赈善士给《申报》发回信函,报告赈灾的情况。笔者所见最早的是1877年5月3日《申报》刊登的《散赈情形》,该文源自义赈善士靳文泰、严佑之、尹德坤给《申报》发回的信件,记述了三人赴山东放赈的经过:“弟等由扬动身,十七日(3月31日)至清江,廿日开车,廿八日(4月11日)抵济南,一路均托庇平安。廿九日至都城隍庙拈香求签,仍拈得先到临朐县……三十日(4月13日)即见藩抚宪,欣喜非常,情文备至,并派员拨兵护送票号银两、□米,又可先在藩库拨款借用,种种顺手,且委员人亦好善,听弟等自行查办……弟等定于初三日(4月17日)到临(按:临朐)。”[1]此后,这种信件逐渐增多,成为重要的灾区新闻报道。 在报道“丁戊奇荒”的过程中,《申报》与国内义赈组织开始建立联系,刊登他们从灾区发回的信件,报道灾区的情况,并通过《申报》进行募捐,募捐后则刊登征信广告,成为中国近代慈善募捐活动的开端。随着灾害报道的增多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申报》处理灾害新闻、刊登募捐和征信广告都越来越熟练,并逐渐融入到义赈活动中。1890年,申报馆成立了自己的协赈所,专门办理慈善和义赈事务。此时的《申报》,已经可以在救灾中发挥领导作用,不仅能报道灾害新闻,而且能发起募捐活动、参与赈灾事务,这在当时国内媒体中是首屈一指的。 从版面情况看,《申报》创刊时为两开八版,没有明显的栏目标志,新闻标题和正文的字号一样大小。第一版通常是评论和“恭录上谕”,与灾害和赈灾相关的重要上谕,通常会放在“恭录上谕”中。第二版通常为重要省份(如北京、天津、直隶等)的新闻。募捐、义赈的新闻通常在第三版,捐款清单则放在第四版。1878年,这种版面划分成为一种惯例。“京报全录”通常在新闻后的第五版,如果新闻较少,则从第四版甚至第三版开始刊登。“京报全录”里都是官员的奏折,大多是报告灾情和赈灾的情况,尤以后者为主。 1905年《申报》改版后,版面扩充到四张16版,新闻量大大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记者的采访。与此同时,《申报》转载的《京报》消息越来越少,到1910年,《申报》就完全不转载《京报》消息了。这对灾害新闻最大的影响,是关于各省官员办理赈务的消息少了,而被《申报》自己采访的新闻所代替。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当时的报道集中在江浙一带,主要关注江浙一带的赈务。 整个晚清时期,《申报》报道的主要灾害是:1876-1879年“丁戊奇荒”、1887年黄河决口、1894年港粤鼠疫、1905年崇宝川南风灾、1906年旧金山地震、江苏水灾、1910年长江水灾、1911年东北鼠疫。 在《申报》的带动下,其他报刊也开始报道灾害。1893年《新闻报》在上海创刊,该报风格与《申报》相似,对普通大众很有吸引力。《新闻报》在创刊后也开始报道灾难新闻,并刊登募捐广告,但总体上看,它的新闻量较为有限,在慈善组织中的影响力也无法与《申报》相比。1898年改名的《中外日报》、1904年创办的《时报》,情况也类似。这种情况到清末得到改变。1902年为江西水灾募捐时,《新闻报》加入到《申报》募捐的行列。1904年为日俄战争难民募捐时,《中外日报》加入。1906年为旧金山华侨募捐时,《时报》加入。随着它们的加入,《申报》的领导作用更加突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此外,《大公报》1902年创刊后,也开始报道天津瘟疫的情况,积极宣传防疫知识。但初期多关注北方新闻。随着该报的不断发展,1906年江苏水灾发生后,该报也掀起募捐活动,逐渐和上海的几大报刊形成联合之势。这些都促进了该报的迅速发展,数年间《大公报》已成为北方第一大报。 二、近代慈善广告的发展 据笔者所见,最早的慈善广告是1876年12月15日刊登在《申报》二版上的一则《乐善可风》的广告。该广告没有署名,内容是为山东灾区募捐:“救灾恤邻,士夫难得之事,不图于闺阁中见之也。今年山东旱荒较广,灾黎待哺嗷嗷,各处量力捐输以济涸泽。兹有法界美国晏副领事宅中寄寓之前次出洋局翻译官曾阑生眷属女公子二位,约同闺友数人,均精于西国之女工者,各将一应女工针线耍货等物,约期于本日遍请西国女眷来家茶叙,并将一切女工发卖,所得价值尽数寄往山东,以助赈济,真难得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知当仁不让,必有闻风继起者矣。噫!巾帼且然,须眉丈夫岂不更当慷慨乐施耶?”[2] 随后,1877年3月10日,烟台英领事哲美森在《申报》二版刊登广告,为灾情最严重的青州府募捐。启事指出:“近有英国传教牧师李先生(按:李提摩太)心存利济,代赈饥民若干口,其中或一家多人仅存一二者,或奄奄垂毙、赖以复生者。然而,博施济众,自古为难。日者,本领事等悯此灾民,会同西国官商共襄善举,捐成数百元,汇付青州典铺内交李牧师散赈。灾民尚恐日久不能继,难以克终,望各省仁人君子慷慨乐输,救难济急,定是功归实济,惠泽均沾。”[3] 4月3日,李提摩太又在《申报》二版刊登广告,为青州募捐。该广告除叙述了青州的灾情和官方的赈济措施外,并指出:“办理虽善,然灾难宽阔,不免有老幼无依靠者,专恃一麦之粥,日有饿殍,多少不定。弟明知上帝扑其所爱,聊以示儆,吾侪人力何能补救?而乐善者宜尽人事,以听天命,尤愿有力者解衣推食,挽回天心,丰年可待。弟传道青郡,岂忍坐视?除自行力量已劝各海口外国士商捐助,在益临二县境内设立五处收养实无父母亲族依靠之幼孩,现有四百名……”[4] 国内慈善组织最早刊登的广告是1877年5月5日果育堂在《申报》三版刊登的《果育堂劝捐山东赈荒启》。广告云:“下民造孽,上天降灾,去年水旱频臻,饥寒荐告,最苦者江北之淮徐、山东之青济,几至易子析骸,饿殍载道,闻者惨伤。业蒙各大宪奏请赈恤,所虑灾黎散处、遍逮为难。敝堂曾醵银千两,专派司事附入招商局唐、徐二君,速赴淮徐,相机接赈,而于东省则阙如也。适法华玉樵李君交来佛吉十三枚,嘱即附寄东省云云。同人额手称庆,以为首倡者李君而相与成此善功者,我邑中当有同志也。爰用布告绅商善信,务希踊跃玉成,自千百以及十数,无拘多寡,乞亲交果育堂账房,掣付收票为凭,不再另立捐簿。一俟集有成数,迅附轮船,汇至青济,拯此鸿哀,不胜雀跃。总乞多多益善,赶速为贵。呜呼!万间广厦,原非寸木可成;九仞为山,端赖一篑所始。至于为善获福,理有必然,兹姑勿赘。果育堂同人公启。”[5] 该广告刊出后,很快得到响应。4天后(5月9日),果育堂又在《申报》二版刊登《东赈续启》。在广告中,果育堂首先表示:“蒙申地各大报馆主人玉成人美,慨列报章,普告同诚,广成善举。”这说明5日的广告是免费刊登在上海各大报纸上的。广告报告了收到的捐款情况:“适有闽帮振隆行主林君闻斯善举,归而谋诸同志,登高一呼,众山皆应,共得鹰蚨四百余元,而林君独捐其半。报章既出,随有北市隐名氏番银五十元,躬亲送到敝堂。收此巨宗,立即置备规元五百两,□招商局唐徐二君速附便轮北上。于昨续有濠北草堂洋钿三十元、粤东冯君五元、归安顾善姓英佛一百元,本日同元诚庄规银一百两,踊跃解囊,实乃可钦可感。未逾三日,陆续已来六百余元,行见先声所树,众善同归,后此之源源而至者,不知几十百人、几千百金,俾能迅速汇东……他时赈务告圆,自当汇刊征信,以昭核实。此外,并不立簿劝捐,杜绝假冒。”[6]可见,这是一则征信广告。这则征信广告比西人的要早大半个月。西人的征信广告始于6月1日传教士慕维廉在《申报》四版刊登的《捐款续登》。[7] 此后,《申报》刊登慈善广告逐渐频繁。在“丁戊奇荒”中,广告的刊登位置固定下来,一般是要闻版后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同时,广告内容逐渐丰富,不仅有各种募捐广告和征信广告,还有了彩票广告、赈捐广告。但目前尚无法确定后二者是否免费刊登。 1895年2月7日,为了给甲午战争中的中方伤员募捐,《申报》首次在评论前面刊登募捐广告:“奉省诸军现与倭兵奋力交战,计受伤者不计其数,忠义之气殊属可嘉,本由西国善士及兵船上医生陆续舁归医治,兹以医药资不敷,行将中止,特函请沪上大牧师慕威廉先生出为劝募,其情形已录入今日本报内。惟此款自应多多益善,是以本馆愿效微劳,帮同办理,务祈远近诸君共切同仇敌忾之心、溥施起死回生之力,克日佽款,多寡不拘,本馆当立掣收条,一俟集有成数,即交慕威廉先生汇解奉省。此非寻常善举可比,切勿迟延观望,盼甚!祷甚!”[8]而且,该广告在第一版连续刊登了三天,引人注目。 此后,连续刊登募捐广告成为一种常用的宣传手法,不仅常见于《申报》,也为清末各报所仿效。而且连续刊登的时间越来越长。1897年,为四川旱灾、湖北水灾募捐的《劝输川鄂急赈启》,在半个月内刊登了4次。[9]1905年《申报》改版后,募捐广告刊登的频率更高。如1906年旧金山地震发生后,4月26日,《申报》刊登《筹赈旧金山被灾华侨公启》,到5月9日,约半个月内刊登了12次。[10]同年江苏水灾发生后,11月23日,《申报》刊登《江宁七属急赈募捐启》,到12月21日,在约一个月时间里刊登了21次。[11]由于这些广告刊登在第一版显著位置,随着广告频率的增加,宣传效果也增强了。 三、近代灾害报道伦理的演进 伦理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新闻伦理解决的是媒体和外界的关系。在灾害报道中,必然要报道灾民,要报道死难者,这就涉及到灾害报道伦理的问题。换言之,灾害报道伦理解决的是媒体与灾民、死难者之间的关系。灾害报道伦理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直到近代,灾害报道伦理才真正出现,并且迅速发展。 早期《申报》在灾害报道伦理方面,意识很弱。灾害对于《申报》而言,仅仅是新闻,越是吸引人的东西,越要下大气力报道。例如在对“丁戊奇荒”的报道中,大量出现对于灾区惨状的描述,十分骇人。1878年初,天津粥厂发生火灾后,1月25日,《申报》对火灾过程进行了详细叙述:“西北各棚,已成灰烬,焦头烂额,死尸枕藉……至午,则该厂一百余棚烧毁净尽,以后火尚不息,或炙人肉,或毁人骨,或熬人油,或烧棉衣棉裤,故至酉刻仍有余焰。”[12]虽然叙述极其详细,但读之令人作呕。 再如学者们常常引用的、刊登在1878年4月11日《申报》上的《山西饥民单》,全篇1780字,全部都是骇人听闻的死亡数字:“灵石县三家村九十二家,(饿死)三百人,全家饿死七十二家。圪老村七十家,全家饿死者六十多家。郑家庄五十家全绝了……阎庄村符小顺将自己亲生的儿子六岁活杀吃了。巴公镇亲眼见数人分吃五六岁死小孩子,用柴火烧熟……屯留县城外七村内饿死一万一千八百人,全家饿死六百二十六家。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人见之,将他拉到社内,口袋中查出死人两手,他说已经吃了八个人,活杀吃了一个,有一女年十二岁活杀吃了。又有一家常卖人肉火烧。有一子将他父亲活杀吃了。有一家父子两人将一女人活杀吃了,这就是一宗真事……太原县所管地界大小村庄饿死者大约有三分多。太原府省内大约饿死者有一半。太原府城内饿死者两万有余。”[13] 这条新闻把吃人的场景细加描述并加以强调,极具震撼力,但让人毛骨悚然。而且,从《山西饥民单》前后几天的报道来看,这则报道显得非常突兀,没有来由,仅是为了强调灾情的惨烈,吸引眼球。所以,虽然这则报道屡被引用,具有史料价值,但从灾害报道伦理的角度看,它并非一则好新闻。 当时灾区发生不少惨剧,《申报》都一一报道,不乏猎奇的意思。这样的报道,语言方面即使没有渲染,直白的表述仍然极不合适。还有些报道,看似“趣闻”,却经不起推敲。例如天津粥厂火灾后,当地政府施粥赈济灾民,由于粥少灾民多,街头发生了一起抢粥事件。《申报》是这样报道的:“二十一日(按:4月23日),有垂迈老妪手挂面斗,领粥而回,过东浮桥时,值开关,行人拥挤。老妪行桥头,徒被乞丐伸手从其篮内捧粥而走,妪拄有拐杖,遇抢情急,举杖便打,中丐肩背。丐以人多路挤,止不得行,复被击破头颅,血出而跛,该处正系桥旁,当颠跛时,上重下轻,几乎落水。幸有桥旁摆卖柳木杆者将其拖住,否则为一捧粥,直有性命之忧矣。”[14]言语之间,不乏“幽默”,但没有顾及到乞丐的可怜,因此整篇报道显得浅薄。 以上例子都说明,在《申报》灾害报道的前期,灾害报道伦理还没有发展起来。这也导致当时的灾情报道显得非常多,内容无所不有。 到清末时期,这种状况明显改善。例如,1906年湖南发生大水后,虽然淹死者最终高达万人以上,但《申报》的报道非常克制。如5月12日伤亡信息刚刚到达时,《申报》报道云:“连日大雨如注,永州一日三电,报称到处发蛟,江水陡涨三四丈,沿江居民漂没无算。有一百五六十里,从前人烟稠密,今竟片瓦寸椽俱已不见云云。省垣低处亦水深数尺,城外一片汪洋,不堪寓目,据闻为本朝三百年来所未有。上台派船往救,日有千人从水中遇援得活。现各处遍设粥厂,待办振捐……”[15]当伤亡信息逐渐增多时,《申报》报道:“省河上游之易家湾,核至十五日(5月8日)止,经救生船捞起浮尸六七千具,下游回水湾捞起二三千具。该两处苦无棺木,一时无从购办。”[16]相比从前,此时的报道已经大不相同,并未一味渲染伤亡情况,而是从救灾的角度进行叙述,给读者以慰藉,也更有现实意义。 与救灾报道结合起来,是清末灾情报道的一大特色。还是以湖南水灾为例。5月16日,《申报》刊发《湖北水灾三志》的报道,云:“湖南水灾情形迭志前报。兹闻此次大水,各处圩田坍决至数百处,十一日善化县属观音港圩堤冲决时,毁民房数百户,居民溺毙者以四五千计,已经禀报到县。省城房屋倒塌亦多。十二日,有北城外警务总查某大令随带护勇两名督同施粥,该处铺屋忽然倾塌,大令适罹其害,护勇两名亦同时压毙。此外压溺至毙者亦时有所闻……省河下游之回水湾一处,自十一日止,经救生船捞出浮尸已多至九百六十一具,中有女尸尚抱一小孩不释,情尤可惨。湘潭县属之易家湾一处,亦经救生船捞出浮尸二千余具。此外各处捞起者尚不计其数。惟前报所纪湘潭县出蛟并火灾一节,系属讹传,然水势则有不可言状者,现在虽已渐就销退,而势尤迟缓,三日内仅止退去二尺上下云。”[17] 这是一则非常完整的报道。受灾情况非常具体,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很清楚,但并不让人感到恐惧。相反,灾情已禀报给官府让人感到踏实,因公殉职的大令的形象让人由衷地感动,水势开始消退的消息则让人看到了希望。这些细节,真实地体现出清末灾害报道伦理的巨大进步。这无疑是晚清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反映。 四、灾害新闻中的清政府形象 在灾害尤其是大灾面前,政府扮演了主要角色。早期的《申报》大量转载《京报》新闻,报道了很多清政府赈灾的情况。加上及时刊登在第一版的大量上谕,当时清政府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在《申报》的视野内。同样重要的是,《申报》的救灾报道是多层面的。既有清廷的政策,也有各省的赈务,还有大量《申报》自己的评论。这在“丁戊奇荒”报道中非常明显。这种多层面的报道,把清廷围绕在中间,体现了清廷的领导地位,也反映出了以清廷为中心的救灾活动正在稳步有序地进行。在这样的灾害报道中,虽然不时有对清政府的批评言论,但总的来看,经常出现在读者眼中的清政府形象是正面的、积极的、有领导能力的。这对赈灾工作的顺利开展无疑非常有利,对清政府的政治稳定也间接起到了作用。 然而,到了清末时期,随着清政府和《京报》的衰落,清政府方面的消息减少了。而且随着清末商业报刊的发达,官报在竞争中地位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因此灾害发生后,清廷方面的消息比重很小。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之前清政府拨款赈灾,可以说是重要新闻,一般都放在“恭录上谕”栏内,非常醒目。而清末时期,清政府拨款赈灾的消息一般都在广告内提及,不再单独列出。而和言辞丰富的广告语言相比,类似“皇太后关怀民瘼,已降恩旨命户部拨银四万两”、“仰蒙圣慈发帑四万两”的简短消息已经丧失了吸引力。在众多的募捐广告和新闻报道中,清政府的形象已经渐渐模糊。 取代清政府形象的,是地方督抚的形象。随着地方权力的增长,包括《申报》在内的各地媒体,都大量报道地方新闻和地方官员。如在1906年江苏水灾中,《申报》对两江总督端方非常关注,相关报道很多,大量新闻标题直接突出端方个人,如:《江督批斥请弛七濠口米禁》、《江督治理两江之政策》、《江督端午帅会同苏抚、江北提台电奏海州匪乱情形》、《江督对于赈米免厘之判断》、《江督奏请截漕展捐》、《江督电饬截留饥民》、《江督严禁米粮出口》、《江督皖抚会奏皖北赈务》等。而且这些新闻往往被放在比较突出的版面位置。 再来看看具体的报道。1907年1月8日,《申报》刊登了一则《江督尝饼之慨念》的新闻。新闻如下:“两淮赵渭卿都转奉江督谕办淮北赈务,都转以米粮稀少,爰购豆饼以饷灾黎,日前将饼色呈验。午帅甫中餐,变色而作,取其饼而饱之,谓僚属曰:‘昊天不惠,降此鞠凶,我辈忝为民表,应如何设身处地、同际(济)时艰?’于是各僚属亦感发奋起、争尝其味云。”[18]端方心系民生的形象跃然纸上。 与此同时,更多的揭露官员腐败无能的报道出现了。如1907年3月1日,《申报》刊登了一则《误认饥民为钦差》的新闻。新闻云:“十二日(按:2月24日)夜,有南京及镇江遣散饥民之船五艘,用小轮拖带路经扬州。其时各官正在徐凝门外候接钦差,远闻放汽声即认为钦差,随即整肃衣冠,排齐队伍,前往迎迓。继见小轮并未停泊,乃知饥民过境,各官均有惭色,当将仆隶以探报不实大加申饬云。”[19] 在清末十年的灾害新闻中,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这反映出到清末时期,清政府统治能力的下降。正如笔者在对清末旧金山地震报道的考察中提到的,清政府虽然很早就对旧金山华侨给予了赈济,但国内报刊对此报道很少,而且有误报现象,明显反映出在清末十年的动荡局势中,国内报刊对清廷的不关注。而这样的报道显然对清政府的统治不利。[20] 此外,出于革命动员的目的,革命派报刊对清末灾害进行了大量渲染性的报道,借以打击清政府。如《民呼日报》1909年5月17日报道河南旱灾,18日报道广州水灾病民,19日大骂盛宣怀、汪大燮,20日刊登《民不聊生》,23日报道万县旱灾,24日报道安东水灾……6月10日开始大量报道甘肃旱灾。该报后因抨击陕甘总督升允而被清政府查封。此后,革命派又办《民吁日报》,继续报道灾情严重和赈灾不力,再次被清政府查封。之后,《民立报》继起,继续报道灾情,辛亥革命前夕日销已达两万余份,超过了日销一万份的《申报》和《新闻报》,成为当时的舆论骄子。在清政府逐步灭亡的过程中,起了舆论助推器的作用。标签:清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