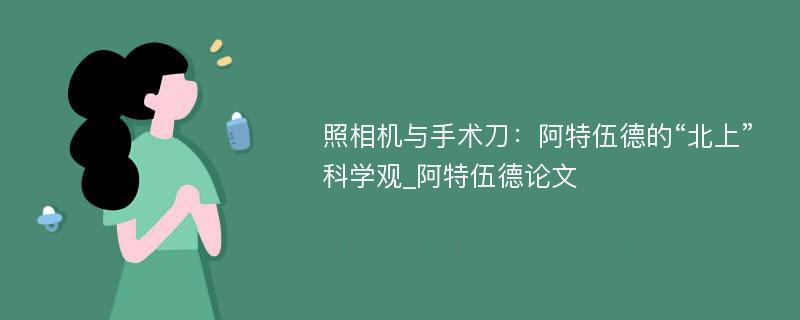
摄影机与手术刀:阿特伍德的加拿大式“向北”科学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术刀论文,加拿大论文,摄影机论文,向北论文,伍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5)03-0101-07 一、引言 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文学家们就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哀叹科学技术的滚滚车轮辗碎了农业文明时代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与浪漫。科学的理性与文学的温情似乎总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从在信仰与科学间痛苦徘徊的丁尼生,到视机器为洪水猛兽的哈代,再到当代美国向科技文明发出愤怒“嚎叫”的金斯堡……科学更多地以负面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而在当今加拿大文坛,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皇”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也在自己的作品中阐释了带有加拿大特质的科学观。 作为一位昆虫学家的女儿和一位神经生理学家的妹妹,阿特伍德与一般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本人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①,而且不止一次地在访谈中声称科学只是一个工具,其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综观阿特伍德50年的创作生涯,从1969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an)到80年代中期《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再到本世纪发表的《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和《水淹之年》(The Year of Flood),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地展现出科学对人性的异化、对环境的破坏,乃至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摧毁。既然科学仅仅是一个工具,为什么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科学总是那么“不友好”,那么具有破坏性与毁灭性?正如阿特伍德自己所说,关键在于掌握和使用科学的人。那么,在阿特伍德的笔下,科学的使用者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阿特伍德的科学观与其加拿大民族主义有何关系?下文将分别从“摄影机”与“手术刀”这两个意象出发来分析这些问题。 二、摄影机:“凝视”权的现代化升级 上世纪60至70年代,摄影机、摄像机和望远镜等在当时看来是先进的科技工具频频出现于阿特伍德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这是一首发表于1964年的短诗《相机》(“Camera”): 你想要这个瞬间: 临近春天,我们俩都在散步, 微风吹拂…… 你想要这个画面,于是 你安排我们 在教堂前面,为了取景, 你让我们停步 替我在草坪上摆好姿势; 你要求 云不再移动 风不再摇着教堂 在它的沼泽地基上 太阳在天上静止不动 为了你设计的瞬间。 相机男人 我如何爱你的玻璃眼?② 不可否认这首小诗的女性主义倾向:一个手持摄影机的男性为了拍摄他想要的画面,安排与操纵面前的女性摆出特定的姿势与神情。诗中的相机无疑象征了男性对女性凝视和操控的权力:前者借助这一科技工具将女性与景物一起进行物化与他者化处理。国内加拿大文学研究学者丁林棚认为:“摄影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利手段而非纯粹的审美,摄影首先体现了拍摄和被拍摄者的不对称权利结构。”③所以此处的“照相机”其实就是男性肉眼的延伸,是男性对女性“看”的权力的隐喻,是传统男女两性“看与被看”模式在现代高科技辅助下的升级。诗的最后两行,“相机男人”这一称谓实际上就是将男性与科技工具置于女性的对立面;而“玻璃眼”的意象更是把男性的眼与摄像机的镜头幻化成了一个整体,说明科技与男性在本质上相通或统一的,但对于女性来说却是异质与敌对的。 在阿特伍德的早期作品中,摄影机、摄像机和望远镜等器材的使用者无一例外地都是男性:《可以吃的女人》中的彼得熟练掌握摄影机的各项功能;《浮现》(Surfacing)中的大卫随身带着他的摄像机;《肉体伤害》(Bodily Harm)的男主人公保罗拥有一架高倍望远镜。相对于照相机,望远镜使男性置身于更为有利的“看”的地位:在观察别人的同时将自己隐匿于暗处。而女性却似乎天生对这些器材具有排斥性,如《浮现》中的无名女主人公说:“我害怕有一架机器,也会这样让人们消失,走向虚无,就像照相机,它不仅盗走你的灵魂,还偷走你肉体。”④《肉体伤害》的女主人公雷妮是阿特伍德作品中少数拥有摄影机的女性,但她的相机不但没能用上,反而成为她后来逃跑时的累赘。阿特伍德研究专家瑞格尼(Barbara Rigney)断言雷妮的相机是“看的失败的象征”⑤。 在阿特伍德早期的创作理念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一场事关生死的战争,因此摄影机所代表的“凝视”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欣赏与操控上,而是进一步发展为对其的掠夺与谋害,这在她的第一部小说《可以吃的女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小说讲述的是女主人公玛丽安与男友彼得由恋爱到订婚后又逃跑的故事。小说的主旨非常明确:在当代西方消费主义社会中,甚至连女性也沦落为男性的消费对象,而男性成为消费者的关键就在于他拥有先进的现代化科技工具。男主人公彼得就是这样一个率先掌握了以摄影机为代表的各类高端科技设备的人。在一次晚会上,彼得先后再次用摄影机对准玛丽安,后者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恐惧: 他举起相机……她只觉得身子发僵,冷冰冰的。她没法动弹,就那么站在那里,瞪着照相机的圆镜头发呆,甚至脸上的肌肉也不能动。她想对他说别按快门,可是她没动……⑥ ……彼得站在那里,穿着他的黑色豪华冬季西装。他手里拿着照相机,但她现在能看清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了。再没有别的门了,她的身体贴到后面的门把门,眼睛却不敢从他身上离开。他举起相机,将她锁定为目标;他嘴巴露出一排尖牙。有一道炫目的亮光。⑦ 当是时,彼得身着黑色西装,玛丽安则一袭耀眼的红衣,而红色是最容易成为射杀目标的。而且,在英文中,“拍照”与“射杀”两个词都是“shoot”。综合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拍照行为,俨然是一个躲在暗处的猎人在捕杀他的猎物,而彼得手里的这架高性能的摄影机就相当于捕猎的手枪。 将摄影机、望远镜等比作武器,这种象征手法在阿特伍德早期小说中并不罕见,比如《浮现》的女主人公说:“双筒望远镜对准了我,我能感觉到那种目光,如手枪瞄准器射向我额头。”⑧乔拍摄安娜时,手中的摄像机“像一架火箭筒或奇怪的刑具对准了,按下按钮,上抬,邪恶的嗡嗡声”⑨。这正如《可以吃的女人》的题名所暗示的,女性与动物一样,都是男性捕杀的对象和餐盘中的食物。男性借由以摄影机为代表的先进科技,实现了对女性的权力施加。科技沦为强者手中对付弱者的武器。于是,原本中性的科学技术演变成了一种极具破坏性的异己力量。 为什么科技总是与男性联系在一起呢?这源于阿特伍德早期一个独特的创作理念:女性与动物的受害认同。由于加拿大的地理与历史特点,动物主题的作品在并不长的加拿大文学史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阿特伍德在《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以下简称《生存》)一书里说:“加拿大动物故事的类型与主题演绎有着自身的特点。”⑩她将加拿大的动物文学与英国和美国的动物故事进行了对比,认为英国文学中的动物实际上是“穿着毛皮的人”,动物王国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翻版;美国小说中的动物常常是人类征服和捕猎的对象;而在加拿大文学中: ……动物永远都是受害者,无论它们是多么勇敢、灵巧和强壮,最终都会被杀死,不是被同类就是被人杀死……如果文学中的动物永远是象征,在加拿大的动物故事中它们经常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那么这些动物受害者象征着我们民族心理的什么特征呢?(11) 阿特伍德认为,加拿大的动物文学之所以总是呈现出一种悲悯、无助与伤感的基调,是因为受害动物的身上体现了加拿大人的弱者心理。加拿大的民族心理中潜藏着一种强烈的受害认同感,即总是倾向于将自己摆放在被受者的位置,而女性由于其所处的不平等的地位,尤其容易与受害的动物产生认同。综观阿特伍德的早期作品,女性与动物的受害认同主题频频出现,基本形成了男性为施害者、女性为被害者的二元对立模式。 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掌握科技手段的施害者呢?答案是否定的。阿特伍德表示,她既反对作为施害者的男性,也不赞成作为被害者的女性,在这个二元对立之外,应该还有“第三种人”的存在:“理想的情况应该是某个人他既不是杀人者,也不是被杀者。”(12)事实上,阿特伍德在早期的几部小说中塑造了不少所谓“无害的第三种人”,即虽然是男性,但并不是施害者。比如《可以吃的女人》中游离于男女两性权利战争之外的邓肯;《浮现》里还没有完全被“文明化”的乔。既然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施害者,那么什么样的男性才是真正代表了科学杀伤力的人呢?答案是“美国人”。但阿特伍德所谓的“美国人”概念并不完全是国籍上的。还是以《浮现》为例:女主人公将那些残杀动物、破坏环境,在加拿大湖区乘摩托艇呼啸而过的人定位为美国人,即使在得知这些人其实是加拿大人之后,她依然坚称:“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并不重要,他们依然是美国人”(13)。关于“美国人”一词,阿特伍德在《生存》中作了更为明确的定义:“美国人就是猎人。”(14)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是猎人、战士和富有侵略性的金融家。”(15)在阿特伍德笔下,“美国”一词总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而“美国人”就是真正掌握科学技术的人。简言之,“美国人”代表了现代科技文明对人类异化的势力。 阿特伍德研究专家C.A.豪威尔斯(C.A.Howells)在分析《浮现》时说的“就像男人摧毁女人,有些团体和国家也会摧毁另一个团体和国家”(16)点明了这一理念:美国与加拿大、男性与女性在本质上都是受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阿特伍德在《生存》中说得更为直接:“美国(侵略国)是杀人者,加拿大是被杀戮者。”(17)阿特伍德的这种观点在加拿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济与科技更为强大的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更多的是负面的。不少加拿大人认为自己的国家“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美国是加拿大创建自身民族特色最大的障碍。阿特伍德长期以来作为“加拿大文学的代言人”,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你试图像一个美国人或英国人那样写作,而实际上你并不是,那你只能制造出一片塑料。”(18)言下之意是加拿大人作家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家。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大卫·斯坦尼斯(David Staines)说阿特伍德:“世界成为她的中心,而她关注的显然是加拿大人。”(19)C.A.豪威尔斯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加拿大和加拿大性生成于阿特伍德小说的文本空间里。作家植根于某个地方,而阿特伍德的地方是加拿大。”(20)由此可见,阿特伍德的科学观实际上是与她的民族主义立场联系在一起的:就像男性借由摄影机成为两性关系中的施害者,美国也通过科学技术成为加拿大的强者。 三、手术刀:现代医学的“肉体伤害” 正如小说《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中格雷斯所说:“哪里有医生,哪里就有坏兆头。”(21)“医学恐惧症”几乎是阿特伍德笔下主人公们的通病。与科技的使用者相同,阿特伍德笔下的医生也无一例外地都是男性,而男性医生的形象又总是和手术刀联系在一起。格雷斯说医生“把他像猪一样割成小块,就像是腌肉似的”(22),似乎医生与屠夫是同一个职业。“刀”的意象说明现代医学在治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有所破坏,而再高明的医术也不过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高科技手段而已。阿特伍德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浮现》与《肉体伤害》从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表达了对现代医学手段与理念的质疑。 《肉体伤害》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小说围绕着女主人公雷妮的乳房疾病和手术展开,讲述了她因乳房切除而遭男友离弃后,以旅游记者的身份来到加勒比岛国,不料卷进当地的政治纷争而入狱,后经加拿大政府出面调停才得以返回多伦多。正如题名所暗示的,雷妮的身体创伤作为女性受害处境的隐喻是贯穿于全书的中心意象。在这部小说中,阿特伍德将现代医学放置于女性与自然的对立面:现代西方医学对身体的救治是在各类现代器械和工具的操作下,借助于各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药品,并将身体极端物化的前提下达成的。因此雷妮“一想到再次遭受医院无用的折磨、疼痛、难忍的恶心、细胞的粒子辐射、皮肤消毒、头发脱落,她就无法忍受”(23)。而这些治疗手段显然也无法根治她的疾病。对于雷妮来说,直接用冰冷的手术刀将病变的地方切除而留给她一具残缺的身体并不是真正的治愈。小说是这样描写雷妮的乳房切除手术的: 现在她浮在天花板下,在一间白色房间的角落里……她的身体在下面的桌子上,盖着绿布,有几个人围着她,戴着面具,他们正在进行一个操作,一个程序,一个切割手术,不是表皮手术,他们要找的是心脏,在那里的什么地方,把它挤出来,一个拳头在一个血球周围打开、合上。也许她的性命得救了,但谁说得清他们在干什么,她不相信他们。她想重新回到她的身体,但是下不来。(24) 这个手术过程完全如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苏(Hélène Cixous)所描述的:“女性被驱离了自己的身体”(25),人的身体被极端物化了。现代医学使得人丧失了对身体的自主性,将人与自我剥离开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雷妮在监狱中用自己的双手救助女狱友洛拉: 她将洛拉的左手握在她自己的双手之间,一动不动,一切都静止不动,但她在遏尽所能地拉住这只手。空气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洛拉在洞的那一端,她必须把她拉过来……她握着她的手,一动不动,用尽全力。(26) 冰冷的刀与温暖的手,医学的理性与身体的感性,男性的技术与女性的情感,阿特伍德有意造设了一系列鲜明的对比。最后雷妮仅凭一手之力将奄奄一息的洛拉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事实,无疑证明了后者对前者的胜利。 事实上,阿特伍德不止一次地在作品中描写女性双手的治愈能力。《肉体伤害》还讲述了一个加勒比老妪用徒手治愈一个德国女人伤脚的插曲;另一部长篇小说《强盗新娘》(The Robber Bride)里女主人公的外婆也是用手成功地为受伤的邻居止血。这种医治方式多少带有点反科学的巫术意味。实际上,用手的温度来对抗刀的冰冷,以古老的巫术来对抗现代医学,是响应了这一时期(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流行的女性主义思潮中“回归身体、回归自我”的口号。 如果说《肉体伤害》是用手来对抗手术刀,那么《浮现》则是以自然力来抵制医学手段。《浮现》讲述的是在书中没有出现姓名的女主人公回到家乡加拿大北部原始林区寻找失踪父亲的过程。小说以女主人公的心理发展为线索,把寻找父亲、重返自然与找回自我三个过程统一了起来。女主人公年少时曾被自己的老师诱奸并致怀孕,又在后者的安排下在医院进行了人工流产:“把我绑起来塞进死亡机器、空空的机器里,双腿架在金属架上,秘密的刀子。”(27)这个流产手术给她留下了永久的心理阴影:“我被掏空、被切除了;我身上散发着盐水和消毒剂的臭味,他们把死亡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在了我体内。”(28)盐水、抗菌剂、金属架和刀子等意象构成了一个残酷而冰冷的手术氛围。这一次,被摆放在女性身体对立面的是医学。 为了治愈流产事件对她的伤害,多年以后女主人公重返林区时,不管是受孕还是生产,都极具“反医学”色彩。受孕时,她与情人在野外湖边的湿地里:“躺了下来,让我的左手握住月亮,右手握住消失的太阳。”(29)而她为自己设想的生产过程也完全是返回自然式的: 这一次,我要自己来,独自蹲在角落的旧报纸上面,或者树叶上——干树叶,有一堆,这反而更卫生。婴儿会像一个蛋似的轻松滑出来,或是像一只猫崽,我要把它舔下来,咬断脐带,让鲜血流回它应属的大地。那时候月亮会是圆月,充满拉力。(30) 树叶代替了清洁剂,鲜血流向大地而不是金属架,靠月亮的引力而不是药物催产剂的力量使胎儿脱离母体。用自然来对抗医学,也是当时生态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 根据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女性身体与大自然是同质同源的,而女性受孕与繁殖过程与大地孕育万物的性质是一样的。女性的生育能力是男性所不具备的自然力,这对男性的绝对强者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成为男性试图完全征服女性的一个障碍。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说,在整个人类社会,“对女性生殖和养育力量的恶梦般的幻想贯穿了整个时代”。(31)而所谓“女阴恐惧症”(gynophobic)的实质就是对女性生育能力的恐惧和厌恶:“当时人们实际上是无法摆脱女性生殖性那不被驯服的力量,并不遗余力地要将其置于强有力的文化控制之下。”(32)于是,医学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展开了一场子宫争夺战。博尔多认为,17世纪席卷西方的女巫迫害运动,其真正动因就是男性试图将掌控着女性生育力量的“女巫”驱逐出这个领域。这场战争最终以男性的胜利结束。在女巫被逐出的同时,男性进入和控制了女性的生殖领域。 男妇科医生的出现标志着医学正式进驻女性生育领域:“男性逐渐掌管分娩和一般的医疗……在助产术上的这种变化使得妇女在分娩过程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境地,终于使得人们相信分娩是一种生理上的潜在紊乱,需要男性的有力控制。”(33)博尔多还说:“强迫孕妇接受医学治疗,为进一步侵犯一个女人的隐私和身体完整性提供了一个苦涩的先例。”(34)所以妇产科是以健康与科学的名义,借助医学技术和医疗器械对原本隐秘和自然的女性生育过程进行无节制的干预与操控。“与‘主体的’身体所依据的神圣理由所受到的特殊待遇相反,医学和法律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干涉女性的生育生活时所用的方式是随意和专横的”。(35)简言之,医学剥夺了女性对身体的自主权。 根据生态主义的观点,现代妇产科把孕妇看成是“胎儿孵化器”,是对女性神秘性和自然力的野蛮解构。以男性为主宰的人类文明化进程,其中一部分就是对女性生育的技术化和文明化改造,而改造的方式即是医学。女性怀孕的母体就像大地蕴藏着各类矿藏,而与男性大肆开采土地的矿藏一样,他们也随意地取出和扼杀女性体内的婴儿。人工流产就是男性野蛮破坏女性身体的自然力和自主性的极端体现。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浮现》一书从某种角度看就是对这一生态女性主义观点的文学阐释。 在笛卡尔把“人”定义为具有思想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的同时,身体被贬为这个高贵“主体”的载体。于是,人就是如吉尔伯特·赖尔(Gibert Ryle)所言的“机器里的幽灵”(36),身体便成了一具没有灵性的、必须由“主体”加以控制和操纵的机器。理性主义将精神与身体看成是两个独立的领域,认为身体是没有丝毫灵性的、纯粹的物质的混沌,而精神代表了人类(其实是男性)文明和智慧的成就,所以身体只能是精神处理的对象。“身体的‘去神秘化’或者‘去魅’主要表现为身体被机械地看待。”(37)理性主义宣告了精神对身体的绝对性胜利。然而,当代西方哲学对这种“崇心抑身”的传统哲学进行了反思和清算,认为身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物化“它者”,它可以反作用于精神,而且精神与身体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线,于是出现了身体的灵性化和精神的物性化。西方哲学在提高身体地位的同时,也将精神拉下了理性主义至高无上的神坛,于是整个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思想界都普遍呈现出“精神的式微和身体的反抗”。 在阿特伍德的早期作品中,与精神∕身体、男性∕女性、文明∕自然这些二元对立相应的,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对立关系。《浮现》的地点设在加拿大北部魁北克的原始湖区。在加拿大面临被“南方传来的病毒”(暗指美国的强大影响)感染的危险时,北方的荒原地区尚处于相对纯净的状态。阿特伍德认为,“南方”代表了以美国为标志的喧嚣的现代科技文明,“北方”则是加拿大民族归属与心理的自留地。因此,苍茫而渺无人烟的加拿大北部荒原既是加拿大的地理特征,也是加拿大人回归本土与自然的心理象征。《浮现》的后面部分,女主人公选择独自留在北部荒原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暗含了加拿大文化界中“向北”的精神诉求与姿态。所以说,阿特伍德“反对医学,返回自然”主题的实质就是回归加拿大自我。反对科技文明、回归自我与回归加拿大,这三者是统一的。远离科技文明,就是回归自然,而回归自然即是回归自我及自我的加拿大属性。 四、结语 必须承认,在阿特伍德早期的创作中,科学与人性对立的理念是与生态女性主义交织在一起的。但是细究之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阿特伍德的科学观中,生态女性主义只是出发点,她最终还是倡导人们回归加拿大式的自我与自然。同时也必须注意到,阿特伍德的创作对于科学的解构呈现阶段性特征,早期的作品多是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将科学放置于女性的对立面进行批判,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使女的故事》乃至于本世纪初的《羚羊与秧鸡》,则更多地从环境意识和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角度来审视科技滥用所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羚羊与秧鸡》中,作为科技时代“失败者”的吉米所就读的玛莎·格雷厄姆学院与“秧鸡”考入的沃森-克里克学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象征着已然没落的艺术文化,后者代表了发展到极限的科学技术。阿特伍德在批判对科学的滥用的同时,也为被其摧毁的旧时代唱了一曲挽歌。 也许,每一位当代作家内心深处都会有这样一种隐隐的担忧:科学的极度发展和过度膨胀将会挤掉文学的一席之地,而最终导致文学的灭亡。换言之,文学家这个群体天然具有一种集体“反科学”的倾向。 注释: ①Atwood,M.:"Dissecting the Way a Writer Works",in Ingersoll,G.Earl(ed.)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s,Princeton:Ontario Review Press,1990,p.176. ②Atwood,M.:"Camera",in M.Atwood,The Circle Game,Toronto:Cranbrook Academy of Art,1964,pp.45-46. ③丁林棚:《视觉、摄影和叙事:阿特伍德小说中的照相机意象》,《外国文学》2010年第4期,第125页。 ④Atwood,M:Surfacing,New York:Fawcett Books,1987,p.138. ⑤Rigney,B.H.:Margaret Atwood,Houndmills: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7,p.108. ⑥⑦Atwood,M.:The Edible Woman,Toronto,Ontari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73,pp.232、pp.243-244. ⑧⑨Atwood,M.:Surfacing,New York:Fawcett Books,1987,p.138、p.159. ⑩(11)Atwood,M.: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House of Anansi Press,1972,p.72、p.75. (12)Hengen,S.:Margaret Atwood's Power:Mirrors,Reflections and Images in Select Fiction and Poetry,Toronto:Second Story,1993,p.46. (13)Atwood,M.:Surfacing,New York:Fawcett Books,1987,p.151. (14)(15)(17)Atwood,M.: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Toronto:House of Anansi Press,1972,p.70、p75、p.77. (16)Howells,C.A.:Margaret Atwood,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96,p.20. (18)Atwood,M.:"Dissecting the Way a Writer Works",in Eeal G.Ingersoll,(ed.)Margaret Atwood Conversations,Princeton:Ontario Review Press,1990,p.9. (19)Staines,D.:"Margaret Atwood in Her Canadian Context",C.A.Howells,(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2. (20)Howells,C.A.:Private and Fictional Words,London:Palgrave Methuen,1987,p.48. (21)(22)Atwood,M.:Alias Grace,New York:NAN A.TALESE,Doubleday,1996,p.27、p28.. (23)(24)(26)Atwood,M.:Bodily Harm,New York:Bantam Books,1982,p.60、p.173、p.298. (25)Cixous,Hélène."The Laugh of the Medusa." in R.Warhol & D.Herndl(eds)Feminisms: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p.347. (27)(28)(29)Atwood,M.:Surfacing,New York:Fawcett Books,1987,pp.193-194、p.169、p.192. (30)Atwood,M.:Surfacing,New York:Fawcett Books,1987,p.193. (31)苏珊·博尔多:《笛卡尔的思维男性化和17世纪从女性特质的逃逸》,见汪民安等编:《现代性基本读本》,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6页。 (32)(33)Bordo,S.:The Flight to Objectivity:Essays on Cartesianism and Culture,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7,p.108、p.109. (34)(35)Bordo,S.:Unbearable Weight,Berkeley/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83、p.73. (36)Ryle,G.:The Concept of Mind,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49,p.92. (37)杨大春:《从法国哲学看身体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见杨大春、尚杰:《当代法国哲学诸论题——法国哲学研究(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