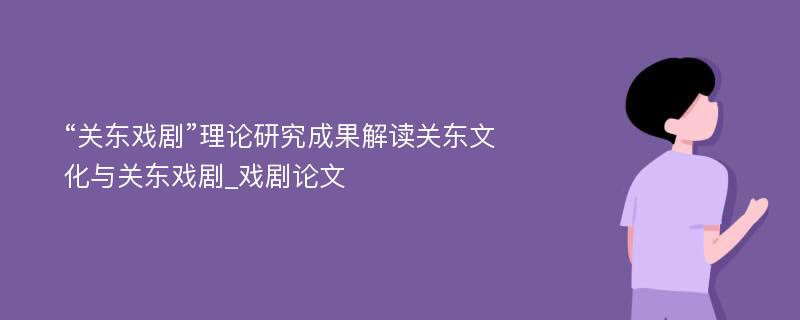
“关东戏剧”理论研究的成果——读《关东文化与关东戏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东论文,戏剧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文化与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东文化与关东戏剧》是赵文翰同志的一本论文集。这本专集,集中反映了赵文翰“关东戏剧”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他以戏剧理论家的敏锐,对“关东戏剧”这一社会历史现象,进行了多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的潜心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成为“关东戏剧”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家。本文拟将我阅读《关东文化与关东戏剧》一书后的几点看法写在这里,或许也可以说是对本省戏剧理论家研究的一个尝试吧。
“关东戏剧”的理论界说
赵文翰发表于1986年9月的《“关东戏剧”刍议》一文,在我省戏剧理论界,第一次提出了“关东戏剧”这一概念,并对“关东戏剧”做出了理论界说。
所谓“关东戏剧”,是一个地域文化学的概念或定义。文化区划并不等同于行政或地理区划。文化地域,以人类某一群体特定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大体相同或近似为划分原则。“东北”是行政区划,明确指的是辽、吉、黑三省所辖的地域;“关东”则盖指山海关外,不仅包括东北三省所辖区域,还包括内蒙、河北等与辽、吉、黑三省接壤的某些部分。因此,“关东戏剧”是专指这一文化区域内的戏剧文化现象而言的。但是,并非说“关东的戏剧”就是“关东戏剧”,它有自己的内涵:
第一、这一戏剧现象的出现,有它自己的社会历史背景,它是在“危机”、“不景气”的时候,“与新时期同步”产生的,是与关东文化意识的觉醒直接相关的;第二、这一戏剧现象,存在于“白山黑水之间”、“从辽河之滨到黑龙江畔”的“关东”文化区域之中;第三、这一戏剧现象不是个别的,它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戏剧流派,它是“刻意追求关东(山海关外)人民历史文化的意蕴和审美需求”、“致力于发掘关东文化的作家群”精心创造的表现关东“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和命运”的“一批新作”,它的共性艺术特征是:“表现关东人、关东事儿,具有关东情、关东趣儿、关东风格、关东味儿”;第四、它已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以叠起的轰动效应在关东剧坛、京华舞台掀起一股股颇为悍烈的‘东北风’,流波所及,全国戏剧界为之瞩目,称之为‘关东戏剧’。”(引文参见赵文翰:《关东文化与关东戏剧》一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以下引文多出此书,恕不加注。)
赵文翰总括说:“关东戏剧是特定地域或空间和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改革开放年代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产物;归根结蒂是古老的关东文化在时代风雨催生下结出的一颗灿烂的果实。没有关东文化,就没有关东戏剧。地域性文化特征是关东戏剧的生命所在。”
很明显,他是运用文艺社会学的地域文化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关东戏剧”这一感性存在的戏剧现象,做出的理性判断或理论界说。将“关东戏剧”这种社会现象,置于关东地域文化的总体系统之中进行考察研究。“关东戏剧”研究引起戏剧理论界的重视和赞同,不少人随之投身其中,一篇篇文章不断在《戏剧文学》“关东戏剧论坛”问世,似乎已形成了一个“关东戏剧”理论学派,愈来愈引人注目。
“关东戏剧”理论研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建设既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又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关东戏剧,使其带着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色彩,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关东戏剧”文化特征的理论阐述
赵文翰的《“关东戏剧”刍议》,可以说是他的“关东戏剧”理论研究的纲领性篇章。此文提出了四个命题:①“关东戏剧”的出现是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②“关东戏剧”的审美意向;③寻找“关东戏剧”的“根”;④强化“关东戏剧”的现代意识。这就首先确立了他的“关东戏剧”理论研究的框架。他把“关东戏剧”的产生,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把它与关东地域文化联系起来,从“关东戏剧”(小文化)与关东文化(大文化)的相互关系中进行考察分析,认定了“关东戏剧”的出现是地域文化发展的必然,是在关东传统民族文化、地域性文化积淀中孕育、形成,在时代风雨的催生下诞生的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东地域戏剧流派。因此,采用文艺社会学的地域文化学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关东戏剧”,无疑是最适当的。由此我们看到:对于关东地域文化特征的考察研究,成为他的“关东戏剧”理论研究的重点,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一、从哲学、社会学视角,揭示“关东戏”作为一种社会的精神现象,它的最根本性质,就在于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关东戏剧”的这种意识形态性,说明了它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意识中反映的产物。作为观念形态的“关东戏剧”,只能是关东“父老乡亲们的生命和命运”在关东作家群“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们的生存状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对它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深入地认识“关东戏剧”的特点和规律,考察关东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人的意识,是受着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以及人们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它不可能超越一定社会、时代人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这即是说,关东作家群关东文化意识的觉醒,对地域文化特征的自觉追求,也只能“与新时期同步”形成。“关东戏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有意识地按照关东人民的愿望和需要来创造的,体现着关东人的审美理想和精神追求。因此,“关东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关东戏剧”的意识形态性,规定了它既是一种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戏剧,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戏剧。赵文翰说:“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特征是关东戏剧的生命。但必须置于时代精神的辉映下,经由当代人类文明的观照和审度,生命才能焕发出新的光芒。”这是他面对着一批“关东戏剧”的优秀作品,作出的一种理论概括。
第二、从美学、心理学的视角,深入研究“关东戏剧”。对“关东戏剧”的哲学、社会学研究,揭示出它的意识形态特性,这属于一般性层面即最高层面的研究,它着重于关东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也即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对“关东戏剧”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但是,这种关系是相当复杂、曲折的。在“关东戏剧”与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许多的中间环节或中介因素。无论是社会经济结构对文艺的支配、决定作用,还是文艺对经济结构的反作用,都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机械的,而必须通过中间环节的联结即中介作用才能实现。赵文翰的“关东戏剧”研究,没有停留在一般性层面上,而是深入到特殊性即中间层面的研究,并相互紧密联系起来,全面认识“关东戏剧”。于是,我们看到:赵文翰对“关东戏剧”又进行了美学、心理学的研究,而且是与哲学、社会学研究有机结合的。他采用了“中介论”方法,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地域文化心理结构这个中介环节之上。因为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直接支配着作家们的创作,并决定着他们的作品的独特个性与风貌。
赵文翰在这方面的研究,概括起来,大约有这样一些成果:
他探讨了关东地域性生存环境如何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关东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和人格特征。既做了纵向考察又做了横向比较,寻“根”探源,资料丰富,分析细致,论证翔实。
首先,是自然环境的影响。他以吉林省为例,来谈他对“关东戏剧”与东北山川风物之间关系的认识。他写道:东部的高山密林、中部的平畴千里、西部的苍茫辽阔,真是要多险有多险,要多宽有多宽,要多平有多平,天高地广、浩瀚无边,因而从人的心胸、气度到艺术风格上,都不大倾心于纤丽、小巧和过分的琢饰,所以江南园林式的建筑极少见到;而崇尚豪壮、雄浑和阳刚之气,要唱就敞开喉咙高唱(如东北民歌),要跳就跳个昏天黑地(如萨满舞)。又由于处地偏僻,历史上长期远离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势必养成一定的封闭感和内化倾向。历史上名人少,争强好胜者少,步履滞重,敏感度低,开拓意识弱,生活态度偏于守成和隐忍,艺术上缺乏创建和胆识。
其次,是民族构成的影响。人文环境(社会环境)是一个复杂系统。包含诸如经济、政治、历史沿革、民族构成、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民俗民风等许多分支,交叉重合,对当代人的心理、气质、事业等等,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拿民族构成来说:东北地区历来是多民族聚居,有汉、满(历史上又称肃慎、靺鞨、女真等)、蒙古……历史上虽盛衰交迭、局面复杂,但总的趋向是逐渐亲近和融合。以致少数民族中有些如乌桓、鲜卑、契丹已不复存在,有的特点也正在消失;即如汉族,许多传统意识如壁垒森严的宗法观念也薄弱了。各民族之间彼此尊重、安然相处。这与西北、西南的情况很不相同,与关内一些地方相比,东北人最少自视优异的排他情绪。当然也不受别人的欺侮,故有“东北虎”的雅号。反映在艺术创造上,也是取长补短,互相融容的。各自家乡的俚词小调等口头文艺也极易与当地原有的东西接近和杂交,从而获得旺盛的生命力。通俗、质朴、清新、刚健的关东民族艺术的强烈感染和熏陶是深远的。它形成了关东人的审美定势,如艺术上追求的“大喜大悲,大楞大角,大红大绿,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等,依然没有脱离这种一脉相承的美学传统。
在关东的礼俗世风上,这里始终不曾出现如关内那样的世家望族和显赫门第,没有等级森严的家法族规,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繁文缛节。宗教上释、道并存,人们供奉观世音菩萨,也供奉财神爷和胡黄二仙,和尚、道士、神汉一律受欢迎。老百姓什么都信,又都不过分执着,表现出明显的泛神论味道。一些地区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宗教纠纷在这里很少见到。齐鲁余韵、燕赵遗风,钟白山黑水之秀。铸就了豪迈、旷达、古朴、厚重的关东气度和关东风采。反映在艺术上的又一方面的特点,是不大为条框所拘,比较宽容、大胆、火爆、泼辣,敢恨敢爱,敢打敢骂,敢哭敢笑,敢于痛快淋漓地表露感情。
第三、不仅寻找了“关东戏剧”的“根”,还注意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关东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个因子。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上的种种缘故,关东人同苏联、俄罗斯文化和日本文化,在文化心理上的距离似乎较其他地区要小一些。东北的老、中年一代的剧作家们,几乎无人不曾是苏联、俄罗斯文学的崇拜者,受其影响,他们的作品常常要透露出一股俄罗斯式的冷峻和深邃。对艺术创作来说,借鉴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十分必要的。
同时,文翰同志还注意到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包括戏剧运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股汹涌澎湃的浪潮,不是山海关能够挡得住的。萧红、萧军等乡土作家群应运而生,戏剧也不能不改变自己的面貌。剧作家对一个社会时代的潮流和氛围的心理感应,是构成艺术家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内容。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在中国兴起,掀起了一个时代浪潮。正是在这种浪潮中,人们认识到:若想让戏剧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下根子,进而打出山海关,走向全国、全世界,离开对地域文化的呼唤和追求,都将事倍而功半。他认为“京派”、“海派”、“西部戏剧”、乃至“浙派”、“闽派”戏剧的开台亮相,“这是渊远流长、多元构成的中国戏剧在时代风雨的催化下所发生的历史必然,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戏剧走向繁荣的可喜征兆。”他在另一处热情地写道:只有当“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成为响彻云天的口号,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澎湃而来,人们迫切需要审视历史和昨天的自我时,这才扳动了文化的闸门,使之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关东戏剧出现了。
总之,生活在关东地域生存环境中的关东人的先天秉赋和后天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素质和人格特征;地域性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时代潮流和文化氛围的感应;地域性审美心理定势等诸多因素融汇整合,就构成了关东作家群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从整体上对“关东戏剧”的创作起着重大作用。正是关东地域文化意识的觉醒,对地域文化特征的认知、把握和自我追求,使“关东戏剧”在发展中,愈益显现出其鲜明的文化品格。对此,赵文翰在《意识·意象·意蕴——“关东戏剧”的文化品格》一文中,做了专题论述。
他认为:关东文化意识的苏醒,决定了“关东戏剧”的文化品格;而“关东戏剧”文化品格的确立,又为研讨和振兴关东文化,特别是戏剧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文翰认为“舞台意象”是地域审美特征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关东戏剧”文化品格的一个构成因素。他说:“意象的捕捉、凝聚和呈现,标志着‘关东戏剧’的某些作家已超越直观的、浅表的摹写和再现,而跨入为理性所烛照的文化深层。”他把呈现在关东剧坛上的舞台意象,归纳为四类意象系统,即:自然景观系统、民风民俗系统、人文实物系统、语音符号系统。
赵文翰在这里所说的“舞台意象”,不是指美学、心理学所说的“审美意象”,或“心象”,而是指作为艺术传达的物质载体或艺术媒介而言的。所以他说:作为地域审美特征的重要载体之一——舞台意象,它是戏剧艺术的一种舞台表现手段、一种形式。就如同戏剧艺术语言(台词)一样,与其他艺术形态如小说不同。这说明,他的“关东戏剧”研究,从一般性、特殊性的研究,又进入了个别性的研究,即从高层、中层到了底层。这已属于语言学、形态学视角的研究了。我觉得,对“关东戏剧”的个别性的研究,是特别重要的。不进入这一层面的研究,就不可能使“关东戏剧”理论研究,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专门学科,从关东戏剧文化学到关东戏剧学。目前,他对“关东戏剧”的研究,给人的感觉,主要还是一种对关东文化特征的研究,对戏剧自身形态的特征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因此,我认为“舞台意象”的研究,在“关东戏剧”研究中,正如文翰所说:“具有着不容忽视的特殊位置。”因为说到底,戏剧作为一种综合性整体艺术,它的主体应当是“舞台艺术”。戏剧文学只是戏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舞台演出服务的。它终归是要“演”给人看的。不管你的“审美意象”、“审美意蕴”多么有价值,多么有意义,如果不能鲜明、具体地呈现到舞台上去,其审美价值、社会效益,都不可能得到现实性的社会实现。一般性、特殊性,都应寓于个别性之中,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只有从一般性、特殊性进入到个别性的研究,才能使“关东戏剧”研究,更有血肉,而不显得抽象、空泛。
戏剧是综合艺术,它是由戏剧文学、舞台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因素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戏剧的舞台艺术形象,实质上是一个由诸多种“舞台意象”系统构成的一个大的舞台意象系统。文翰说:“它是物质的实体,又确乎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
赵文翰无论是对自然景观系统,民风民俗系统,还是对人文实物系统、语音符号系统的研究,认为它们“都与人物、动作、主题组成了一个严整而和谐的结构体系,从整体上提高了全剧的品位。”这是正确的。
如果说“舞台意象”是审美特征的载体,一种舞台表现手段、形式,那么“关东戏剧”的又一文化品格:“深邃、鲜活、丰沛的意蕴”则是指剧作家执着追求的艺术内容。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构成“关东戏剧”的文化品格。
对于“关东戏剧”的“意蕴”,赵文翰又划分为三个层面,即:历史意蕴、人格(性)意蕴、哲理意蕴。从三个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对“关东戏剧”的“意蕴”作出了总体性的分析、研究。他强调指出:无论是从历史的视角切入、从人格(性)的视角切入,还是从哲学的视角切入,归根结蒂,首先都必须是艺术,是属于审美的。
关东地域的文化意识、舞台意象、意蕴,三者共同构成了“关东戏剧”的文化品格。应当说,这是一切地域的或流派的戏剧都应具备的品格和追求的目标。文翰所以予以强调,是因为:“关东戏剧”作为一个已为世所公认的、具有独特的美学理想和美学特性的、较为成熟的戏剧现象,表现得尤为坚实、尤为自觉、尤为突出。因此,“关东戏剧”应“更加努力地锻造自己的文化品格。”加强“关东戏剧”的个别性的研究,发现其与众不同之处,是“关东戏剧”理论研究的重点课题。
赵文翰还对关东文化精神,做了较充分的研究,也很有理论价值。但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作具体评述了。他对关东文化精神,从四个方面做了研究、探讨。这四个方面是:①日神文化意识;②黑土文化意识;③多元文化意识;④塞垣文化意识。
他对关东文化精神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关东文化精神的审美体现,就是关东神韵;而关东神韵,则是关东戏剧的“灵魂”。
戏剧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是戏剧文学与剧场艺术的统一。从“关东戏剧”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大多数理论文章,可以说基本上还是侧重于戏剧文学的分析、研究,而对“关东戏剧”的“剧场艺术”研究,相对说来还很薄弱。如果“剧场艺术”研究不够、不深入,“关东戏剧”理论研究,就是不全面的。赵文翰的“关东戏剧”理论研究,也存在这个缺欠。
我觉得,“关东戏剧”理论研究,急需对“关东戏剧”的舞台艺术各方面的独特个性作出深入研究。希望这样的理论文章多多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