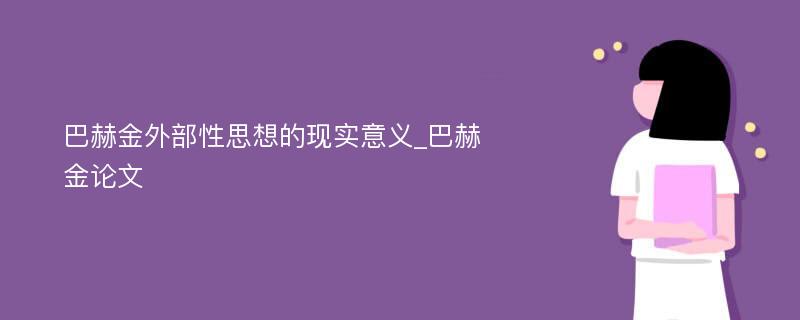
巴赫金外位性思想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思想论文,金外位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的不少外国文学研究者,无论作文还是发言,心头总会先浮上一个念头:人家外国学者说过吗?这种谨慎自然可免去不着边际的胡说,但有多少学者由此而走上了一条满足于引入疏理、“述而不作”的路子,自称“二道贩子”,实以代言人自傲,以至从虚心到心虚,落到食洋不化,邯郸学步的“忘我”地步:过去是听老大哥的——在老大哥面前怎敢有所言说!待到苏联解体,一下子从宗经于苏变为征圣于美,而实际的路数还是没变。看来,改革开放虽然冲击了以往极“左”的精神桎梏,但是在大开眼界、解放思想的风光底下,不少人还是有一点潜藏的旧意识未肯割舍,这就是长期形成的对洋文化的病态“谦虚”。比如一些评论文章,往往把个活生生的文本放到新趸来的某个洋理论之床上拉短截长,却鲜有解读本土问题的感悟之谈。于是发现——失语了。实际上,他们又何曾想过言说自己的话语呢?
又如,一些人把文学批评的探索和创新变为追赶和变换舶来的时髦方法,今天学了结构主义,则结构主义就成了他奉为至上的批评武器;明天学了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又成了他悉心皈依的批评宗旨。所以如此,恰恰正是当下自我文化立场缺失的缘故。这种人好像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没有自己思想的“宝贝儿”(契诃夫语)。
我们通常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即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因此,长期以来在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就潜在着一种追求,这就是竭力想把我们变为别人的“自己”。这其实正是一种巴赫金早就指出的“错误观念”,即“为了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文化,似乎应该融于其间,忘却自己的文化而用别人的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1]。
实际上,真有可能“忘却自己的文化”、变为“别人的自己”吗?巴赫金用学理证明了不成,百年来中国现代历史也证明了不成。那些不加辩证、历史地分析扬弃,一味地“砸烂和扫荡”之举,只会使自己的文化传统支离破碎,险些失去自我更新发展的机制,而如玻璃渣一般潜藏在我们脏腑之中,伺机就要作痛。
而想“用别人的文化的眼睛来看世界”最多只能是一种永不可及的求似的追求,正如巴赫金所说的,这只能是一种“简单的重复,不会含有任何新意”。更多时候是成为自作聪明的东施效颦,乃至是邯郸学步似的“失语”。这种试图完全融人别人之中的虚心的好学生,必然是永远出不了师的学生。因为你怎么能比洋人还洋呢?只有别人自己才最像他“自己”。我们永远也变不成别人的“自己”。这倒应了圣经上的老话,学生永远不会高于老师。抱了这种信念,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不仅“别人”是这样看我们这些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而且这些外国文学研究者自己在潜意识里,或者干脆在嘴上也是这么大言不惭地自认的。
难道这就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的宿命吗!
二
于是,我们发现了巴赫金的外位性思想。我们看到,巴赫金曾一度苦苦思索过这样一个困境,即作为一个主体,它难于反观自身。其原因或许正如巴赫金所说的,“我没有从外部观看自己的视点,我没有办法接近自己内心的形象”[2]。这其实就是我们俗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各自的文化圈子里研究自己的文学,自有它清楚明白的一面,却也有它自视不见的一面。它的许多“涵义潜能”(巴赫金语)在自己当时的文化视野中是被遮蔽着的。它不仅需要历史——时间的外位性,也需要空间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外位性来揭开遮蔽。
所以,巴赫金一再强调,“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强大动力”,“外位性对于理解是了不起的事”[3],因为这种外位性恰恰可以使人看到因身在此山而不能看到的潜在涵义。巴赫金说,要知道,一个人甚至对自己的外表也不能真正地看清楚,不能整体地加以思考,任何镜子和照片都帮不了忙,只有他人才能看清和理解他那真正的外表。这是因为他们是他人,而非自己。
三
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正是要珍惜这一“外位性”的优越位势。既然如巴赫金说的,“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的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的揭示自己”,那么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不正理应有所言说,而且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吗?岂有失语的道理!质而言之,外国文学研究要求于我们的恰恰不是鹦鹉学舌式的人云亦云,而是要有意识地超越别人的文化视角和思路;从我们的文化视角上,正可能重构新的阐释体系,揭蔽潜在涵义。这样,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就能以自身的外位性文化立场,做到他们本国人不可替代的工作。
当然,重视自己的文化立场决非固守传统的文化立场。在世界愈来愈小的今天,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封闭的民族文化,任何文化都需要在不断地融合各种文化的过程中得到吐故纳新的发展。怕的只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砸烂和牵强机械的灌输。因为文化的扭曲和畸变只会导致文化的癌症。
举例说,中国现今的汉学热——关注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正说明我们本来就了解外位性视角的功能。实际上,20世纪的中国正是在多方面通过对“某某国洋人看中国”的考察,更加了解自己的形象,理解自己的长短,乃至有自惭形秽、痛心疾首改革自己的世纪革命。那么,何以一到研究人家外国文学的时候,就显得含糊起来,以为只有永世为徒的份儿呢?
有了对外位性的理解而意识到自己文化立场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才真正有了不失语的可能性,才不会总去拾人余唾,才能真正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在大家交口呼喊“全球化”的当今时代,自我文化立场的缺失,必然导致自我边缘化,而成为霸权话语的应声虫。其实,嘴就长在自己的脸上,但你非不说自己的话语,这“失语”又怪得了谁呢。正如巴赫金指出的,在相互外位性的对话中,“我们给别人的文化提出他们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的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的文化给我们以答案,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新的层面,新的深层涵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能创造性的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4]
相互外位性的对话一定会产生文化涵义的新拓展,一定会使对话各方的文化立场和视角不断充实和发展。对话的结果不会是视角和观点的融一,它总是“和而不同”,总是更充分地证明不同文化立场和视角存在的合理性和珍贵性,正所谓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讲对话,讲多元阐释,就意味着不但重视自己的文化立场的言说,以为唯我看到了真谛,而是也重视别人的言说,看到自己仅仅是多元互补的诸多文化立场中的一个,对话中的一个。正是在这种诸多文化立场间的对话中,巴赫金所谓的“涵义潜能”才得以最充分的释放。
当然,在意识到外位性不可替代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外位性不可避免的局限。相对于“本位”文化立场来说,对象内部的许多“个中消息”又是对它遮蔽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外国文学研究者首先要把老老实实倾听“别人自己”的声音,视为一个极重要的视角。只不过既要能走得进去,又要能跳得出来才好。这样才能打破在任何一种文化视域中所必然存在的封闭性和片面性。由此,我们外国文学研究则可能形成面向各种文化视角,吸取各种理论方法、容纳百川而自成一体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