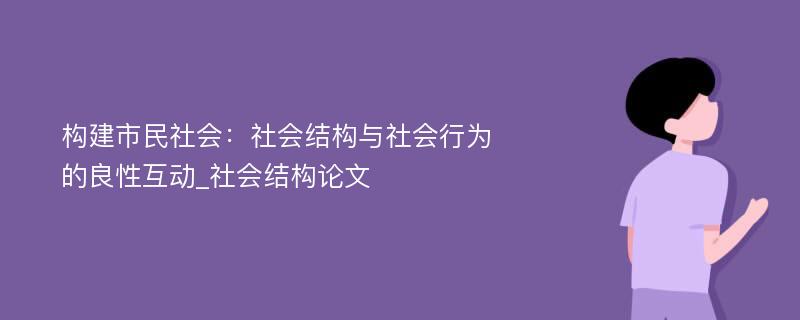
构建公民社会: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良性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互动论文,公民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管理涉及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个维度。要创新社会管理,就需要对社会管理的这两个维度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历史地看,社会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社会的自我管理,另一种是社会的“被”管理。在任何社会,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中国,大家比较不重视的是前一种,即社会的自我管理。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家长式社会,这种传统根植于封建社会的“父母官”意识,也受到计划经济时期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不仅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反而在政府的人力、财力不断强势之后更加强化。一般说来,一提到社会管理,各级政府官员很自然地把它理解成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市民也更多想到的是政府应该提供何种社会服务和完善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社会各阶层对于社会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都较为淡漠。但是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一个国家发展中不可回避的议题。经济发展之后,为避免社会政治制度不被资本控制,同时避免权贵资本对社会造成的割裂,需要保证公民对于社会政策、重大政治决策平等参与的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在社会政策制定中,都有公平获取信息、发表意见的机会,以及参与政策拟定过程的机制,不仅是社会公平发展的要求,也是回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保证社会公平发展的基础。要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首先要塑造社会公民的权益意识,建设责权利相符的公民社会。没有自我服务意识的市民不是公民,他们如果要求保证自身的公民权益,可能会走向偏颇的“私民权益”,对于社会的公平有序发展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提高公民权益,必须首先厘清公民的社会责任。虽然中国目前有很多情况表明公民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但是客观而言,现代中国社会的市民中,其公民自我服务的意识更差。要真正提高公民权益保障的合法性,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还要有可获得的法律服务保障,以及公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意识的提高。简言之,中国需要动员全部社会行动力量,不仅是政府,也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构建中国的公民社会结构,使社会学理论对社会分析的两个主要内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未来将是我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时期。公民社会简言之,就是“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其着力点就在于“公民身份”(citizenship)上。“公民”首先区别于“私民”(Natural Man)。“公民”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存在形态,是专指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归属,是社会人(Social Man)的角色展现;私民也就是个别存在的自然人,是对人的存在的自然属性的揭示,私民只具有自然性、动物性特征,还没有获得“人”的本质属性。故私民只有个人的“权利”,没有对他人、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其次,“公民”与“人民”(People)、“国民”(Nation Man)之间也有不同的内涵与范围。公民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强调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平等性。而人民则是政治性概念,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态度、立场及其阶级属性。“国民”表明一个人的国籍,而“公民”除了表明国籍外,还内含着此人与该国内其他公民之间地位相互平等,并拥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公民社会的本质体现在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上,而公民身份的现代性意义,不仅在于公民与私民、人民和国民的差异,而更主要的是通过它与臣民”(Subject Man)身份的比照衬托出来的。换言之,公民在其本质规定上,是与臣民对应的,公民与臣民是关系状态的两极。臣民(子民)是君主专制制度下人的无主体性、不自由、不平等的社会存在状态。它所衬托的是依附型人格、身份差别、人群对立、政治歧视、消极盲从权威等前现代性特征。与臣民在人格上的依附性、人身的不自由性和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恰恰相反,公民身份正是在这些维度上走向它相反的端点,这就是公民身份在人格上的独立、自由与平等以及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对等性。换言之,公民社会就是以社会成员主体上的独立性、人格上的自由平等性、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为主轴的社会。这是公民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当然,正如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明显地区别于西方,而具有“中国特色”,是一种“政府引导的公民社会”。
政府应对社会风险的责任源自社会公民权的需要,社会学理论关于社会公民权的研究是值得称道的。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这一概念对于我国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19世纪末期之后,社会权开始正式嵌入到公民权的结构之中。1949年,英国著名社会学家T.H.马歇尔《公民权与社会阶级》这一著作的问世,开创了公民权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公民权是给予一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的一种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成员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权从民事权发展到政治权、再到社会权,进而指出公民应享有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社会权是指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介入而保障的某种权利,包括劳动保障权、休息权、生存权、受教育权等,是享受少量经济和安全的福利、充分分享社会遗产和按照社会中通行的标准而生活的权利,对应的实现制度是教育系统和社会服务。在马歇尔看来,社会权是一种要求获得实际收入的普遍权利,而实际收入并不按人们的市场价值来衡量。这对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不平等有深远影响。
反观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是一场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引进、强化市场机制的过程,但市场机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其在社会公平发展中力量将有限。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使得福利水平、福利提供的性质,以及保障对象都有了重大改变。政策上对于市场的过度信任和依赖导致了经济转型中的问题。此外,脆弱的市民社会组织和传统社会支持体系所遭受的压力也意味着福利覆盖水平开始下降,而且很多服务的获取比以前更多地依赖于收入水平。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不平等加剧了,财政分权又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服务获得上的不平等。现在,我国开始重视研究并着手建立或重建组织机构来解决社会服务递送中的问题。这些社会服务的提供与递送,都是社会政策中重要的内容和组成,而社会政策也是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政府主导设计和组织实施。自从俾斯麦创立世界上第一套福利结构和社会福利项目以来,社会政策就被认为是国家建设、政治统治、社会控制,维持社会秩序、效率和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在社会政策的制定,或说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充分借鉴和参考。目前至少可以确定的方向是,在未来社会管理政策的设计中,我们必须摆脱社会经济精英的偏好,而更多地关注普罗大众的现实需要。只有充分关注了社会政策受惠阶层的需求,社会政策的执行才能克服经济至上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不平等,使社会在关注经济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关注公平的问题,获得良好的效果,提升社会政策的可持续性,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公平发展。
当前追求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发展中,我们有必要引进社会公民权的概念,改革行政体制的同时完善中国的社会模式。具体到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条件的种种特征,也要考虑社会资源的各种特征,在提升公民意识的同时,鼓励公民自我服务,引导公民自我管理,以社区资源的启动,配合政府政策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适度投入,稳步提高公民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权益。
(http://www.wenming.cn/ll_pd/sh/201304/t20130401_1152134.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