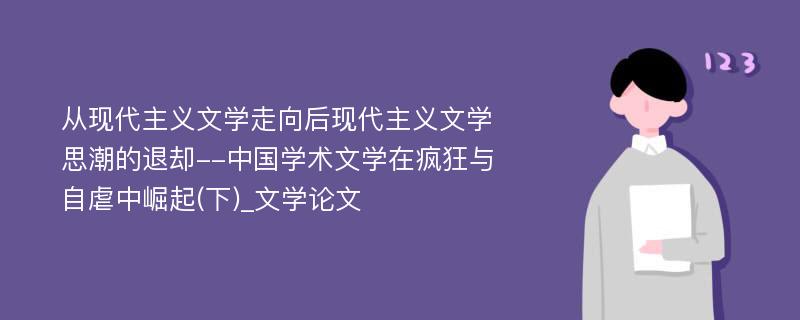
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思潮论文,文学论文,学院派论文,疯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在人类文化史上,在每一次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崛起的表象背后都脉动着哲学的生命冲动。严格地讲,如果没有一遁入哲学的思考就贪婪而忘我地扑向诗思之疯狂的天赋,如果没有良好而敏锐的哲学意识,就无法带着一种生存的体验走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空间。值得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注意的是,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拒斥是从两个走向完成的:即张扬生命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哲学和玩弄词语、概念、能指、所指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如果我们把学院派文学界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发展阶段,那么,在理论上支撑前期学院派文学创作的哲学思潮是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正因为前期学院派文学是浸淫于非理性的生命体验中的,在思潮上则张显为现代主义文学。那么在后期,在理论上支撑学院派文学创作的哲学思潮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哲学关注的主要是从对宇宙本体的理性沉思转向对生命本体的非理性体验,从而导致西方文学艺术思潮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从词语、概念、符号、逻辑、结构和意义等方面去冷静地沉思西方的古典形而上学,把西方的古典形而上学推延到海德格尔这里,企图在一种解构中颠覆一统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后期学院派文学正是受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一种表象的平面感上自虐着自己。
还是让我们的思考驻足于前期学院派文学崛起的文化景观下。在哲学上,从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向西方现代派非理性生命哲学本体论的转向,实际上暗示了人从对宇宙本体的理性沉思向对生命本体的非理性体验的转向,也暗示了人的思考从对宇宙的终极关怀向对人自我生命的终极关怀的回归;这也是个体生命为俘获思想自由,逃避形而上学的规范以执求自我生存自由的渴望。在缪斯空间,这种回归和渴望则表现为古典艺术的终结和现代派艺术的崛起。康德在设定人逼向终极永恒时,认为人类道德在信仰的抚爱下不可逃避地导向宗教,人在本体的终极关怀中永远以宗教的膜拜方式生存。理性和非理性追溯终极的本质决定,人无法在迷失终极偶像的信仰惶惑中生存片刻;人的灵魂必须依附在一个终极本体上,哪怕它仅仅是道德和信仰上的假设,这也足可以慰藉人苟延求存一生。可见,理性和非理性在宗教的信仰膜拜方式上必然把人导入两种生存方式。理性把人导向对宇宙本体膜拜,而非理性则把人导向对生命本体的膜拜。也正是在这个理论意义的层面上,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迷失了思想膜拜的偶像惶惑中,借助非理性哲学的生命冲动在信仰的终极膜拜中找到了精神依附的奇点,那就是在生命本体上鼓噪的自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江在《青春》中把黑格尔、康德等冷冰冰的名字打入冷哲学的另册,这的确昭示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反理性和反文化上的理论自觉。
历史太残酷了,当这些“浅薄者”在逃避学术文化的苦闷中自觉地接受了西方非理性生命哲学时,在某种程度上,却不自觉地承受起以第二次启蒙拯救一个时代文化命运的重任。冰马曾在《纯洁》中描述他们所经历的这样一种文化启蒙感受:“我们有幸受到的思想启蒙运动,与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有点相似。”(注:《纯洁》冰马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60页。)如果说,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启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那么,在20世纪的80年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精神启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启蒙运动。
这,正是他们的浅薄,也正是他们的深刻。
在历史上,文学的诗意体式是文人特有的文化反抗方式。80年代的第二次启蒙运动的文化肇事方法还是借助于文学的勃兴,文学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它自身存在的意义,文学的价值在于它无言地承受了历史上人类的一切欣悦和苦难,因此,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总是贪婪地把自己弥漫在诗的空间中:“一个陈腐的世界是抵制诗的。在艰难沉重的时日里,诗舒展了我们被庸常生活揉皱了的灵魂。”(注:《生命的出口》伊村著,见于《90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膜拜的年龄——最新中国校园随笔选萃》同上,第180页。)在这里, 文学也承受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一代人以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反理性、反传统、反文化而张扬的疯狂和自虐。这就是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的最主要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就在于:其颠狂于张扬的势态中以非理性的疯狂和自虐对秩序井然的道德世界进行最大的亵渎和破坏。检视学院派文学的全部文本,创作于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集中地展览了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这些作品把骇人听闻的“丑”作为审美对象来肆无忌惮地拥抱和讴歌,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张扬的疯狂和自虐中以裸露人性的原始天真去摧毁传统人道主义附加给他们的文化律令。在他们看来审美就是疯狂地亵读“美”,审美就是疯狂地拥抱“丑”。
现代派文学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它对传统与文明的反抗和破坏都是一样的。传统和文明曾摆出卫道士的姿态,绅士般地质问现代派文学的肇事者:“你们的文学将是不美的!我们将失去缓慢起伏、调子平稳的语言交响乐。”(注:《未来主义文学技巧宣言》马里内蒂撰,见于《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开掘精英——马里内蒂是这样带着极端地蔑视回敬了传统和文明的质问:“我们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把一切粗野的声音、一切从我们周围激烈的生活中发出的呼喊声都利用起来。我们大胆地在文学中表现‘丑’,以此杀灭文学的尊严。算了吧!你们不要在听我讲话时,摆出这种伟大的卫道士的姿态!必须每天朝文学的圣坛上吐唾沫!我们进入了自由直觉的无限统治时期。在自由的诗歌之后,自由的语言终于到来!”(注:《未来主义文学技巧宣言》马里内蒂撰,见于《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这是一种疯狂而诱人的现代主义“黑色情绪”。东方大陆的学院派文学圣徒们也带着这种疯狂而诱人的现代主义“黑色情绪”,把笔触直指文化灵魂中最阴暗的部分,回敬了传统和文明的质问。倘若,我们不能从学院派文学的非理性疯狂表象下透视其骨子里的理性沉思;那么,我们对学院派文学的理解永远在最浅薄的层面上进行。在灵魂和精神上,我们也永远无法与他们达到默契和沟通。
理性地张扬非理性是学院派文学的审美特征之一。真理和思想就是这样在他们张扬的疯狂和偏激中闪光。他们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并且也知道他们将到哪里去。“佯狂”是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掩饰自己活得“糙”的一种文化假象,一切正如周榕在《故人琐忆》中所言:他们“身不由己地遭遇一场时代的悲剧,除了用粗糙来掩饰伤口,又能怎样生存呢”?(注:《故人所忆》周榕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76页。)实际上,这种在活得“糙”中,张扬的疯狂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清高。因此,他们不是垮掉的一代,而是崛起的一代。这种“佯狂”的偏激使他们的反叛精神理性地超越了马里内蒂,马里内蒂只不过号召文化的反叛者“必须每天朝文学的圣坛上吐唾沫!”而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则接受了尼采的要超越生命就必须站在生命之上的训诫,他们疯狂地号召栖息于校园的芸芸众生要推倒威严而高雅的神殿。《超越世纪》一书所集入了的40家诗歌作品,正如这部诗集的代序所言:在藏棣、王寅、伊沙、戈麦、孟浪、于坚、西川、海子、骆一禾、韩东等四十家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诗中,“他们把高雅的神殿推倒,就像尼采推翻了上帝。”(注:《“玩”文学·纯艺术·及其闲话(序)》黄祖民撰,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超越世纪——当代先锋派诗人四十家》同上,第3页。 )当我们翻开《海星星——大学生抒情诗集》、(注:《海星星——大学生抒情诗集》复旦诗社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注:按:《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为马朝阳编选,北京师范大学五四文学社1987年版。谢冕在本诗集序《多梦时节的心律》中指出:“校园诗一般指作者为大专院校学生时创作的诗,此类诗,有的称学院诗,有的称大学生诗。名目殊异,所指则一。”(见于该诗集的第1页。))《走出荒原》、(注:《校园文化系列丛书之二·走出荒原》马朝阳编选,北京师范大学五四文学社1988年内部印刷。按:据马朝阳在该诗集的《后记》说:《走出荒原》是北京师范大学自1977-1987年学生诗歌创作优秀成果的总结。)《当代大学生诗选》、(注:《当代大学生诗选》韦云翔、岑玉珍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按:蓝棣之在本书诗集《序》这样评价学院派诗歌:“在当代大学生诗歌中,我认可那些有荒诞,有调侃,超现实,反传统,甚至反理性,反崇高,反优美,反文化,反诗的作品,然而我喜爱的是它们骨子里的纯情和理想主义,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对人生和艺术的价值肯定。”(见于该诗集的第4页。))《中国当代校园诗歌选萃》、( 注:《中国当代校园诗歌选萃》马朝阳编选,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按:此书收入了全国各高校从77级到86级学院派诗人的精英作品。马朝阳在此诗集的《编后记》中强调:“值得指出的是,入选在这本集子里的作者是纯粹意义上的大学生。函授生、夜大生、电大生、作家班学员,插班生等都不在入选之列。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与我一向所持的‘纯粹意义的校园诗歌’这一主张相符合的;其次是为了纠正目前一些大学生诗歌选本对大学生这一概念的故意宽泛和模糊的理解。”( 见于该诗集的第457页。))《学院诗选》、(注:《学院诗选》于水、张翼、刘建良、王红主编,中国人民大学诗丛编委会1986年出版。按:该诗集的副标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诗丛。获帆在该诗集之序《紫色的星星》中写道:“学院诗正在崛起和成长之中,需要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不断地探索开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世界,愿学院诗作者们写出没有任何模式、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好诗。”(见于该诗集的第4页))《 再见·20世纪一一当代中国大陆学院诗选(1979-1988)》,(注:《再见·20世纪——当代中国大陆学院诗选(1979-1988)》为老愚、马朝阳编,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按:此书是《二十一世纪人丛书》中的一本,这套丛书是学院派文学的典范丛书,其中还包括《夏天的审美触角——当代大学生文学意识》、《青春的抗争——当代中国大陆学院探索散文选》、《世纪末的流浪——中国大学生自白》、《一位现代女性的灵魂独白》、《颤粟》、《权力的祭坛》、《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7部。 老愚在该诗集序《眼睛望着上帝》中说:“二十岁,谁都是诗人。身处学院,我们都有亲临梦境的体验。……我们是诗,诗是我们。”(见于该诗集的第1页。))众多的学院派诗人和着一种青春的脉律在歌唱着。 无论如何,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中所张扬的疯狂和反抗溢出了校园,走向了社会,又干预了社会。也正是在对社会的干预中,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拯救了文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低下地位。2500年前,孔子就把《诗经》读解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论语注疏》见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下册,第2461页。)在中国文学史的源头上,文学创生的原初身份仅是苟延于先王礼乐制度之下为主子媚艳而生存的小妾。千年来,多少华夏墨客和中国文人为了摆脱文学媚艳的小妾身份,付出了生命被文化暴力毁灭的代价。实际上,在第一次启蒙文化运动后,被理性支撑的现实主义文学及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在其自治理论体系的界说中,文学还是话语权力的小妾。而在非理性生命哲学张扬的疯狂和偏激中,学院派文学摆脱了以往文学作为话语权力伟丈夫之小妾的奴婢地位,拥有了高洁的品质。
历史太残酷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拥抱现代主义文学中所张扬的非理性精神亢奋,兑现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一种张扬式的疯狂和自虐。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必然要遭到来自于社会道德律令的拒绝和抨击。他们只是故作百无聊赖态,以颓废的自我放纵耽于声色之乐,在非和谐的晕弦感中稀释痛苦。他们自觉到为了他们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他们必须放弃传统道德所衡量的正常生存状态,甚至以毁灭自我生命为代价,才可能兑现他们所期待的收获。在张扬的疯狂中以毁灭生命来祭奠失落的信念、理想或一首诗,在张扬的疯狂中以毁灭生命来警示这个社会和苟延者,这已成为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所渴求的自虐方式。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接受了非理性生命哲学的死亡意识,把生存视作痛苦,又把拥抱文学视为一种逃避痛苦的路径;因此,当他们失落了诗,失落了文学,无法借助于诗和文学的路径逃避生存的痛苦时,他们只有选择自杀,拥抱死亡,毁灭生命。海子就是如此疯狂且自虐般地为殉情于缪斯而贪恋死亡和自杀。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无论是生存着的,还是死了的,他们均为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的崛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于80年代中期在张扬的疯狂中崛起,于80年代末期被这些偏激的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张扬的自虐中“玩”到了辉煌的极致。
四
东方大陆的80年代末是“玩”文学走向鼎盛的一年,也是历史为它敲响丧钟的一年。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正是在这一年“玩”到了辉煌的极致,并开始了它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退却的必然历程。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的历史交汇点上,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出人意料之外地出现了巨大的转向。80年代末期,东方大陆又沉沦在建国以来几乎每隔10年就轮回一次的社会转型中,这一切都使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浅薄和偏激,那种陶醉在现代主义文化的非理性疯狂中,张扬参与社会的精英意识遭到了来自于外部世界道德律令的拒斥和惩罚。干预生活、社会的失败使他们产生了无尽的幻灭感。因此,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必然从张扬的疯狂跌入了苦闷的困惑和焦虑中,“生活失去目标的焦虑感困惑着相当一部分北大人,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以方式的失败而告终,青年人的热情四散流失,空虚开始了它所向披靡的征服”。(注:《穿越冰山》橡子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挽歌与幻像——大学校园生活实录》同上,第13页。)如果说,80年代是人文主义精神高扬的年代;那么,90年代则是拜金主义精神泛滥的时期。
在八、九十年交汇期掀起的拜金狂潮在历史的瞬间席卷了整个东方大陆,一切在劫难逃,任何一位中国公民都无法拒绝接受这场拜金狂潮对其灵与肉的血腥洗礼。这场拜金狂潮在推动国家经济过热发展的同时,吞噬了从80年代一贯而下的人文主义精神,使栖息于高校校园的这些知识分子们在执求人文精神的圣洁中迅速走向了相对贫困化。社会拜金欲的膨胀又迅速导致知识的贬值,“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古老寓言在这里被颠倒为“有钱能使磨推鬼”,这一颠倒的古老寓言在当下作为绝对命令被拜金主义者遵奉为现代宗教般的信条。拜金狂潮冲击着高校校园这个天堂般的阳光地带,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拜金狂潮的冲击下,他们失落了一切优越感,成为“一无所有”的绝对拥有者。
他们被历史交会期文化和经济的转向彻底击败了。
历史总是如此惊人地相似,“读书无用论”在90年代的拜金狂潮中如此准确地拷贝了其在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存在价值。当下东方大陆在后工业文明还没有到来的前题下,都市文化却畸形地违背了经济基础,超前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孕育期。实际上,在西方欧美文化语境下,后现代主义究竟是现代主义的延续还是断裂,这本身就存在着争议,麦当·萨拉普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导论》一书曾质疑:“后现代性使人想到在现代性之后所来到的一切,它涉及了与现代性所维系的那些社会形式的初步或具体的瓦解。一些思者假设后现代性是伴随后工业时代的一场运动,但是,关于这一点来看还存在着意义的含糊,我们应该把后现代看视为现代的一个部分吗?后现代是一种延续,还是一种彻底的断裂?后现代是一种物质的改变?还是暗示一种模式或一种意识形态?”(注:Madan Sarup: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New York 1993.P.130.按: 麦当·萨拉普认为“关于后现代的条件,利奥塔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内,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已经逐渐地影响了语言:各种语言学理论、通讯的各种问题、神经机械学、计算机及其各种语言、转换的各种问题、信息储存与各种数据库。技术的转化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冲击着知识。各种机器的小型复制和商业化已经改变了知识获得、分类、利用和开发的方式。利奥塔相信在代际转型的语境下,知识的本质不可能在一成不变中生存着。知识的身份在后现代时期众所周知的社会内部被改变了。”(见于此书P.133.)就利奥塔描述的后现代社会条件来看,东方大陆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们认为大陆的后现代文化仅是一种脱离经济基础的抽象思潮,其与大陆的社会经济状态是断裂的。关于这一问题,本人另有文章专述。)但有趣的是,在东方大陆学界由于教科书的传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被奇妙地理解为两者之间的传递、承接与延续,后现代主义文化似乎在东方大陆学人之思中没有质疑就开始孕育着。一种文化的孕育就意味着一种文化行为的崛起。实际上,这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大陆学人理解中的一种畸形孕育,它昭示了大陆知识分子在90年代的拜金狂潮中,以击败的过客身份表现出对经济狂潮的冷漠和麻木。这种畸形的大陆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态,也是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现代主义的疯狂和自虐中,被碰得头破血流后不得不再度退却和再度逃避的另一方文化空间。学院派文学从现代主义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退却,是学院派现代主义者的生存哲学和体验美学在张扬凌厉中遭到外部世界的拒绝后,所寻拣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方式。因此,从“逃避”到“再逃避”,这就是学院派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从“逃避”到“再逃避”的轮回则是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沉默在骨子里的再次精神反抗,是对流血的伤口的再一次撕裂。
如果说,前者的“逃避”,是作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张扬的疯狂和喧哗的自虐中奋起的反抗;那么,后者的“逃避”,则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在沉默的疯狂和无言的自虐中奋起的反抗。
无论那些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家是怎样不承认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大陆拜金狂潮中的崛起,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由对社会及文化的嘲弄退却进作品的文本空间中,通过沉默的疯狂和无言的自虐在制造着经久不息的话语喧哗。学院派文学创作于90年代之后的作品无论在审美特色和价值取向上都直涉、切入后现代主义文化深处的冷漠感和神秘感:“祝福从那片灰色中带来的/祝福丛林中的蹄痕以及随之失去的/在我荒凉的城市/你是穿平底鞋的人/祝福你的执著、自怜、兽般的孤独。”(注:《下雪天的祝福》侯马著,见于《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哀歌·金别针》徐江、侯马著,同上,第166页。 )我们只要走进这一时期学院派文学作品的文本空间,诉诸我们感觉的就是,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对任何文化价值都丧失了判断的兴趣,他们的生存仅仅是为了合力体验那个原初世界的冷漠和神秘,因此,他们本身就生活得相当“后现代”。所以,不要说我们从他们作品文本的语义世界中还原出的仅是一个破碎而无法修补的“原真”世界,从他们所生存的现实世界中还原出的也是一个破碎而无法修补的“原真”世界。
一切在张扬的疯狂之后归向了破碎的寂寞:“朋友像秋天的树叶飘落/都市的黄昏/我孓然一人/倾听旧日/青苔爬满脸颊/石板走在脚上/探问寂寞的深度”,(注:《在没有朋友的地方》海童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超越世纪——当代先锋诗人的四十家》同上,第30页。)90年代的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彻底放弃了80年代的疯狂,他们也只有瑟缩在自解自嘲的虚假卑琐中呻吟着、乞求着另一种生存的态度:“我孤独的心因你的远离更加孤独,我冰封的心因你的远离而更加寒冷,我在它面前都要发抖、打颤了。”(注:《冲突》叶兰著,见于《90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你好,青岛——大学生情侣两地书》同上,第282页。)这种生活态度, 实际上是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幻灭之后以虚假卑琐的生存方式恶意嘲讽当下这个拜金社会,企望在一个充满铜臭的死海中打捞久已失落的纯洁。80年代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审美视点和价值视点在此移位了,他们用后现代生存方式的冷漠性、散漫性、多重性、偶然性、放浪性、荒诞性、卑琐性、零散性、无我性、泯灭性、非确定性、非原则性、无深度性消解着这个世界对他们施加的一切话语权力。这种后现代生存方式进入他们作品的文本空间后,则表现为在价值、规范失重状态下的沉默疯狂和无言自虐。他们再也不张扬地为信仰和理想而反抗什么了,他们只是以后现代的生存方式无言地自虐自己。
一切都在默默地流血。
90年代之后学院派文学作品大都以后现代式的“元叙述”话语冷漠地拷贝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后现代生存方式。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徜徉在校园生活的边缘地带,以游戏人生的琐屑来瓦解自己,进而颠覆这个拜金社会的整一性。从作品文本中我们看视到,他们以错位的生活方式,把被传统中心主义压制的意识形态进行重新组接,使现实生活中传统中心主义设置的权力秩序在错位的重新组接中颠覆、失效。伽达默尔把大于句子的语言组合体指涉为作品的文本,德里达进而把整个生存文化形态扩展为一个更大的此在文本。无论在学院派文学圣徒们作品的文本空间中,还是在他们生存文化形态的文本空间中,这无疑是一种疯狂的自虐生存行为;他们像落入黑夜的羔羊,在真诚的丑陋和虚假的文明中毁灭着自己的青春韶华。如果我们仅把校园学子们的这种无言的自虐生存行为认同为是一种拉康式的后现代精神分裂症,而没有洞视这种后现代精神分裂症在无言和沉默的自虐中所反抗的什么,那是对学院派后现代主义者最浅薄的理解和最大限度的不尊重。
的确,当学院生活被涂抹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底色后,学院派文学圣徒们以解构的生存方式在生活的边缘地带颠覆着当下文化的中心主题。学院派后现代主义在这里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思潮,也更表现为一种游离于文化中心之外而带有支离破碎感的行为生存方式。从学院派文学作品摄入的素材、题材、主题与写作的文本体式来看,其包括了诗歌、小说、散文、随笔、杂文、情爱日记、情侣两地书、校园生活实录、大学生热点现象纪实等等这些校园后现代文化的特写镜头。因此,学院派文学在作品的形式本体上表现为一种典型的种类杂混的后现代主义“副文学”。并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学院派文本所集入的作品种类杂混,在文本体式上,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副文学”用各种文本体式所拼凑成的典型面貌似浅薄的审美风格。
从理论上透视,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崛起是对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承续,支撑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背景理论更主要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一反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沉入文化深层的非理性式的生命反抗,其冷漠地退入作品“文本”的世界和作品的“话语”空间中,以玩弄语言的解构“游戏”去拆解历史和文化,其中心指涉结构的整体性、同一性和权威性。因此,学院派文学圣徒在建构其破碎的文本世界所运用的语言是一种撕裂传统与阻断逻辑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无序性和非定向化以无言和沉默的话语表述方式反抗着文化中心主义。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圣徒们就是这样逃遁在支离破碎的语义世界中,把负载人类绝对精神的权力话语拆解为一连串暂时性的空洞符号,恒定的语义世界消解了,终极真理和权威话语被放逐了。而这种文学上冷漠的文本解构方式作为一种对文化渗透的解码,也把学院派文学从现代主义的意义深渊推向了后现代主义的平面感和浅表感,的确,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那种缺乏深度的虚假浅薄削平了学院派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度性。学院派文学90年之后的作品几乎都以这种杂乱、破碎的艺术形式展览了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圣徒们冷漠而破碎的内心世界:“生活时不时出现巨大的苦难/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园倾刻破碎瓦解/心灵又要作漫长黑暗的远行……”(注:《苦难》冰马著,见于《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铁玫瑰》冰马著,同上,第45页。)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学院派文学在“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上无论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是怎样的重复,而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脱胎于东方大陆拜金狂潮中的文化产物;严格地讲,大陆的这种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态不是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简单的复制和拷贝,而是学院派后现代主义者在拜金狂潮中失落了一切后,无可奈何的求生方式。因此,我们无法、也不应该把它们生硬地直接拷贝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中去验明正身。
五
透视90年代大陆拜金狂潮,从理论上剖解,推动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孕育而崛起的文化动力还是来自于高校校园。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肇事主体主要是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所隶属的社会阶层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中产阶级。在当下欧美国家的经济体制下,中产阶级往往是社会和文化的主要决策者。西方欧美中产阶级的生活是富足的,但正是这种富足降解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后现代时期高科技异化人性所进行反抗的内在动力。他们在生存的信仰上不愿意承受反抗必遭毁灭的悲剧,但是,他们又不满足文化中心主义的压制;因此,他们则以一种后现代的生存方式逃避于虚无主义的政治承诺中,以自我分崩离析的自虐消极地抵御着现实。这种“自虐”也正是他们温文尔雅地以玩弄语言以解构话语权力的游戏法则,他们就是企图以此颠覆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
而大陆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肇事主体,主要来自栖息于高校校园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东方当下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中产阶级,他们被拜金狂潮推向社会边缘,在经济上已沦落为相对贫困的现代无产阶级。因此,仅这一点已证明大陆后现代主义文化不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复制。欧美的中产阶级希望以自己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方式去创造适应自己生存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这一点如同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认同的欧美之所以出现这种文化状况,主要是欧美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对现代文化的侵袭和改造。在90年代当下的大陆拜金社会经济结构中,大陆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从当下的发展势态来检视,那些逐步挤进东方大陆社会中产阶层的中产阶级们,大都是在拜金狂潮中“陶冶”出的“大款”和拜金暴发户。他们都是来自于社会的底层,仅仅拥有金钱而绝无文化、知识和思想。从一个悖立的逻辑视角来看视,他们在文化与知识上富得一无所有,穷得也只剩下钱了。他们有的人以其瞬间发迹的经济实力挤进中产阶层后,而在文化与知识结构方面还带着在社会底层熏染的痞气和流氓精神,他们的生存逻辑直线就是一个从骗人到赚钱的旅程。东方大陆的中产阶级绝没有西方欧美中产阶级所拥有的那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也没有西方欧美中产阶级在富足后玩赏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自觉意识及雅兴。
东方大陆90年代的拜金狂潮把这些拜金暴发户推向当下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实际上,这一经济阶层的形成不自觉地在理论上和文化上张扬了一种愚民政策。你要想进入中产阶级,你就必须放弃对文化和知识的执求,“下海”是你达向中产阶级的唯一通道。拜金狂潮就是要你在经济的富有中成为无知识、无灵魂、无精神的思想贫困户和文化贫困户,这样你才可能以“大款”或拜金暴发户身份进入中产阶层。所以,东方大陆的中产阶级在文化和思想上表现出先天性不足,因为他们在骨子里不需要文化和思想,他们只需要金钱。因此,大陆目前所形成的现代中产阶级在精神和思想上是破落的毫无希望的阶级。
东方大陆知识分子作为当代相对贫困的现代无产阶级,他们也正是在大陆现代中产阶级信仰和思想的先天性贫困中,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大陆后现代主义文化倡导者的历史角色。90年代的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正是以这种倡导者的角色,把大陆后现代主义文化从校园推向了社会。当然,大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倡导者还包括那些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因此,东方大陆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它艰难地孕育在校园文化的母体中。由于孕育它的母体没有接受过后工业文明给予它自然而正常的受孕,它仅是在教科书上接受了人工受孕;所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必然表现出先天性不足。但是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大学无疑是各种理论思潮实验的空间,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曾讨论了大学在后工业化社会景观下的人文职能:“因为大学是整理和检验理论知识的场地,它已经逐渐地成为社会的一种基本组织……大学已经更多地承负起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承负过的重任。”(注:Daniel
Bell: TheCultural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Basic Books,Inc,Publishers NewYork.P137.\P.198.)我们可以预言:大陆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脆弱的,它的崛起本然地存在于早产或流产的二元选择之间。尽管如此,当下东方大陆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在母胎的孕育中就已经表现出一种沉默而无言的反抗精神。如果我们不在比较中理解东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价值差距,我们就无法理解东方大陆后现代主义者在沉默的疯狂和无言的自虐中所张扬的这种反抗精神。
西方欧美的后现代主义者作为一群自虐徒,他们在疯狂的解构中击败“自我”,最终默认了现存社会秩序及其权力关系。而东方大陆学院派后现代主义者却把击败“自我”默认为一种反抗,所以,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一次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拜金狂潮中以毁灭自我、自虐自我而掀起的无言启蒙运动。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绝对没有以“媚俗”来填充自己苦涩的心灵,从而不给自己留下反思的空间,他们把现代主义的精神超越性转换为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沉沦性,让自我在灵与肉的颤栗中重新接受考验。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在作品的文本世界中颠覆着自我,让自我的灵魂撕成碎片在信仰危机中散落得遍地都是。没有信仰危机的人永远不会成为思想者,也正是如此,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奔命于拜金狂潮冲击的精神荒原上,他们以诗意的文体营构向人们的灵魂深处垂下一枚枚尺度的法码,来测量这个社会灵魂的深度。
大陆学院派文学在90年代转向后现代主义之后,昭示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以写作的方式逃避于诗意的文本空间中去抗争,这也是一种对当下社会问题回避的路径。回避社会本身就呈现为一种干预社会的态度。因此,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潜在社会性的文学解构游戏和文化解构游戏。从作品的语言代码上检视,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无虚构性的零度写作中表现为一种媚俗性,好像是一群有文化的人在主体精英意识的缺失和想哭但又找不到痛苦中写没文化的事,实际上,他们是在无言的疯狂和沉默的自虐中捍卫着自我的尊严;学院派文学圣徒们就是这样在逃避拜金狂潮的若闷中自觉而不自觉地承受起拯救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命运。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在沉默的疯狂和无言的自虐中“玩”到了前所未有的深沉。一种文化的孕育就意味着一种文化在历史地平线上的崛起,太阳在跃出地平线的一瞬间是最辉煌的,学院派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孕育和崛起的瞬间更拥有了这一切辉煌。
东方大陆学院派文学在80年代崛起后,在疯狂和自虐中完成了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退却的艰难历程。这个历程昭示了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心灵始终在思想的回旋之路上追溯着自己,最终企图回溯到自我生命的最根本的存在形式,做一个本然的人。也正是在这种执求生命本然生存的价值意义上,学院派文学的建构者在心理上都以彻底的精神自杀者扮演着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悲剧性角色。回眸学院派文学圣徒们跋涉过的踪迹,无论是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无论是张扬在疯狂和自虐中,还是沉默在疯狂和自虐中,他们都是彻底地把自我毁灭给他者看视的精神自杀者。我们只要走进学院派文学的文本空间,就可以随意睹视到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精神自杀意识在作品的文本中闪光:“告诉我:那个我一直找寻和恐惧的/是不是叫做‘死亡’?我莫非生来就是为了写它/崇拜它/然后跪去/与它相会。”(注:《为什么我曾书写死亡》徐江著,见于《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哀歌·金别针》同上,第96页。)“梦一向是使者/但由于死亡/伟大的音讯只能被暗自猜想”,(注:《风雪夜》藏棣著,见于《阳光地带的梦丛书·超越世纪——当代先锋诗人四十家》同上,第10页。)为什么迎接我的总是死亡/栖鸟归林,万物憩息/唯有我仍在江边捕捞残月”,(注:《为什么迎接我的总是死亡》冰马著,见于《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铁玫瑰》同上,第46页。)“一个人的死是一颗石头打破了水面的平静/脆弱的波纹之网/向远方笼罩”,(注:《一个人的死亡》橡子著,见于《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致命的独唱》同上, 第151页。)“一个生命的熄灭/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鹦鹉们都在探讨你死亡的秘密/只有我知道人死了永不能复生/我不相信你死得很惨/真的/你是诗人”,(注:《诗人之死》海童著,见于《中国当代先锋诗人丛书·阴影里的倾诉》海童著,同上,第59页。)“雪下得太少,这孤独的/征兆已持续多年,默默地/像一种神秘的仇恨/所以一旦大雪突降/死就要被祭奠”,(注:《詹姆斯·鲍德温死了》藏力著,见于《再见·20世纪——当代中国大陆学院诗选(1979-1988)》同上,第518页。)“暮色四沉/我渴望一次突然的死去/渴望你来,姗姗而来/拎回我的骨头,”(注:《男人在外》叶舟著,见于《90年代校园文化新潮丛书·开放的天空——最新中国校园诗歌选萃》同上,第65页。)……太多了,强烈的精神自杀意识浸灌于这些学院派文学圣徒们的心田,最终酿成为一种和缓的思想之流,它诱惑着这些文学圣徒们在阳光地带做着精神死亡的白日梦。
爱米尔·杜尔凯姆在《自杀论》中沉思了人把生命肉体自我毁灭的哲学意义:“长时间地沉浸在空虚的思考里就不可避免要落入空虚之中。”(注:《自杀论》爱米尔·杜尔凯姆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而他忽视了人在生存中把生命的精神自我毁灭给他者看视的这种精神自杀的哲学内涵,从哲学上沉思,生命的肉体自杀者在毁灭生命后所产生的价值毁灭感及巨大的悲剧感,只能转移给生存着的旁观者去体验、承受,死亡了的自杀者去永恒地规避于生命毁灭的悲剧之外宁静地沉睡,无法享受他以自我生命的毁灭而施加给他者的威压。而那种以生存着的方式毁灭自我的精神自杀,使旁观者和精神自杀行为的实施者双方都必须承揽精神生命价值毁灭的痛感及悲剧感。所以,对学院派文学圣徒们来说,这种生命的精神自杀比生命的肉体自杀更具有诱惑性,因为,生命的精神自杀者可以充分地体验和享受到自我精神生命被自我毁灭后所升华出的崇高感。人在生存的压抑状态下以生存的方式自觉地体验和领略一种精神人格死亡的痛苦,这是一种以疯狂的自虐方式在反抗和宣泄中对施暴者的警示。在这种反抗和宣泄中,精神的自杀者能够体验到一种以自我精神毁灭的痛感压到施暴者的精神胜利、精神享受和精神宣泄。也正是在这种伴有痛感的精神胜利、精神享受和精神宣泄中,精神的自杀者以这种疯狂的自虐行为逼迫施暴者放弃他的话语权力,也正是在这种自杀的美学意义上,学院派文学圣徒们自虐成瘾,同时,他们也为这种成瘾的自虐行为负出了沉重的代价。
标签:文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学院派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艺术流派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