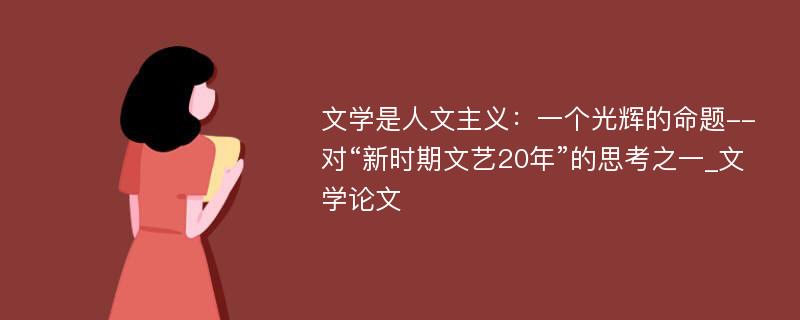
文学是人学:一个辉煌的命题——“新时期文艺学20年”的反思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新时期论文,命题论文,人学论文,辉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及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带来主体精神的全面高涨。主体的伸张冲击了反映论文艺学的板块结构,文艺学的哲学支撑开始由客体论向主体论倾斜。“文学是人学”再度张扬,成为新时期文艺学的一个响亮辉煌的口号;文学主体性问题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并繁衍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潮流;文艺心理学向文艺主体的内在视野大幅度开拓,成为新时期文艺学中的一门显学;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批评,标志着文艺学的主体意识又一次深化和拓展。总之,80年代是新的历史时期人的主体精神全面高涨,文艺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成绩显赫的一个时期。
禁区的打破
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人性根柢开放出来的精神花朵,它的生成和发展必然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心灵的滋润和制约。作为对文学本质进行理性思考的文艺学,也不能不从“人”的角度入手开始自己的理论探求。因此,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是一个既无可回避也封禁不住的论题。然而,“人”的到来在当代中国文艺史上却经历了一段坎坷的历程。50年代,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人都曾著文讨论文学的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并以此论证文学的本质特征,因而招致一系列残酷讨伐。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将学术问题强行拉入阶级斗争的轨道,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等罪名,处以“极刑”。谈人性、人情、人道的人,遭到了非人性、无人情、不人道的摧残。老作家老学者巴人身心倍受折磨,沉冤九泉。钱谷融后来慨叹:“……在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对我的批判,却大都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上的反动罪行来批的,并且是不由分说的。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一段时期的历史,似乎有许多现象之居然能够发生与存在,都会使人感到无限惊诧,甚至简直不可思议。”(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而这确实是历史的真实而荒唐的一幕。
然而,历史终究结束了那一幕。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理论禁区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的到来而被打破。
新时期文学起步于十年浩劫留下的累累“伤痕”之中,作为对“文革”践踏人的严酷现实的反抗,“我是人”(注:北岛《结局与开始》,见《朦胧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的呐喊,必然成为这一特定时期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进行历史反思的出发点。正如何西来所说:“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界中和艺术家创作中消失以后,又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课题。”(注:何西来《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红岩》1980年第3期。)
在新时期文论重建之初,“人”的意识的觉醒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体系的触发性思考,它一方面依托于原体系,一方面又在其中寻找和发现新理论的生长点。“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注: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0页。)的提出即标志着学术思想界在原体系基础上的新思考。朱光潜立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论述,强调马克思这部书的整体论述“都是从人性出发”:“马克思正是从人性出发去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消除私有制。”(注: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性美和共同美的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朱光潜的观点得到了汝信等人的赞同。汝信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内在的联系,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道精神。他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处境和地位的深刻分析,以及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中,发现了贯穿于其中的“把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的人道精神”,又从人道主义“要求人的充分的自由发展”的基本内涵入手,探讨它与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最高目标的一致性,确认了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的不可或缺(注: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3年8月15日。)。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马克思自己就明确表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致性。在这期间,胡乔木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将人道主义的含义区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应当批判剔除”,而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则可以批判的继承,“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的一项内容,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任务”(注: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红旗》1984年第2期。)。但也有人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其基本原则是“人的价值是第一位的”,它不仅是一些道德规范而且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人们需要以唯物主义对世界作出科学的评价,同时也需要以人道主义对世界作出适当的价值判断(注#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1~253页。)。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理论探讨,尽管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它无疑在新时期哲学和文艺学学术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它不但打破了以往的理论禁区,而且使我们对“人”、“人性”、“人道主义”的认识水平大大深入了一步,理论思想大大提高了一步。人们普遍肯定了人道主义的积极价值,确认了人性的客观存在的独立内涵。这场讨论,逻辑地呈现了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内在联系,为中国文学走出“神化”的天国返回“人”的家园,标示出方向和路径;为中国文艺学以人为出发点的文学观念的重新确立,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再度张扬,提供了理论依据,奠定了哲学基础。
历史的回顾
“文学是人学”,这本是一个老命题。在论述它的现状之前,需要首先对这个理论命题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含义进行辨析。这个命题最早是由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提出来的。1928年,高尔基被选为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成员,他在庆祝大会上致答词中解释自己毕生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时说,我毕生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高尔基还曾指出:“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一样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和多变的趣味和情绪。”(注: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16页。)而且,高尔基整个一生都在强调,文学应该始终高扬人道主义精神,高唱人的赞歌;文学要塑造、歌颂、赞美“大写的人”,要把普通人提高到“大写的人”的境界。总之,文学须以人为中心,不但以人为表现和描写的对象,而且目的也是为了人。这也就是他的“人学”的基本含义。联系到高尔基的全部创作实践,他毕生所从事的的确是这样一种“人学”的工作。文学是“人学”,这是作为一个作家的高尔基从自己毕生的切身体验中所得出来的结论。作为伟大“文学”家的高尔基,也可以称为伟大的“人学”家。然而,在前苏联的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理论界,并不是都对文学有这样清醒的符合它的本性的认识。有的人从“唯物认识论”原理出发,在说明文学与现实之间“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强调文学是现实的反映的时候,往往见“物”不见“人”。例如,有一位理论家布里克指责高尔基是“偷换唯心主义”,说什么“应该给文学提出的任务是:不是反映人,而是反映事业;不是写人,而是写事业;不是对人感兴趣,而是对事业感兴趣。我们不是根据人的感受来评价人,而是根据他在我们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事业的兴趣于我们来说是主要的,而对人的兴趣是派生的……高尔基的公式:‘人——这个字听起来多么令人自豪!’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适宜的”(注:苏联《新列夫》1927年第10期。)。直到40~50年代,仍然有人把所谓“现实”摆在文学的中心位置上,而“人”在文学中只被看作是反映“现实”的工具,只是从属性的手段。例如在前苏联虽算不上第一流文艺理论著作却作为文艺学教科书出现在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就有这样的话:“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注: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页。)这虽不是权威的说法,却是流行的观点。恰恰是这种流行的观点,随着前苏联文艺思想(包括季摩菲耶夫之类并不高明的甚至是将#
克思主义美学庸俗化了的二流文艺思想)向中国大量移植,也流行到中国来,并且与中国某些人的文艺思想一拍即合,成为5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中很有市场的观念。翻翻当时的文艺理论教材、著作和文章,几乎随处可见对文学反映和认识“外在现实”的强调,似乎文学的根本任务就是真实地反映和认识“外在现实”,而写“人”不过是为了写“现实”,“人”比起“现实”来反而成为次要的东西。这种观念把“唯物认识论”庸俗化了,当它在文艺学中贯彻所谓“唯物认识论”时,认为“物”就是“现实”,而“人”似乎可以和“现实”分开;“人”,特别是“人性”、“人情”,总是和“心”连在一起,倘若重在写“人情”、“人性”,就有点“唯心”的嫌疑;因而须“唯物”(“唯现实”)而不“唯心”(“唯人”)。这样,“唯物”固然是“唯物”了,也“唯”到家了,但却把“人”“唯”掉了,把“人情”、“人性”“唯”掉了,把“人道主义”“唯”掉了,把文学中最根本的东西“唯”掉了。这种观念也影响到创作,表现在某些作家那里,就是创作些“见物不见人”的作品,他们不是着重刻画人物,不是在描绘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性格特点上下功夫,而只是着重描写生产过程、战斗场面,从而严重地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钱谷融的贡献
正是针对当时文学理论中这种糊涂观念和文学创作中这种糊涂倾向,钱谷融在1957年写了一篇很著名的、也是长期受批判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着重批评了当时已经介绍到中国来并且在中国已经流行的前述季摩菲耶夫的观点:“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他说:“这样,人在作品中,就只居于从属的地位,作家对人本身并无兴趣,他的笔下在描画着人,但心目中所想的,所注意的,却是所谓‘整体现实’,那么这个人又怎么能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自己的真正个性的人呢?”他发挥高尔基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反复强调:“文学的对象,文学的题材,应该是人,应该是时时在行动中的人,应该是处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任务是在于揭示生活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然要扼杀文学的生命。”在文学创作中,“一切都是以人来对待人,以心来接触心”。总之,人,才是文学的中心、核心。而且钱谷融还特别强调“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中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我们之所以对那些伟大作家“永远怀着深深的敬仰和感激的心情,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作品里赞美了人,润饰了人,使得人的形象在地球上站得更高大了”(注:《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钱谷融的这篇文章虽然不可避免地有着当时那个时代的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但却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理论水平。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第一,当某些人只注意“现实”而忽视“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人”的作用时,他突出了“人”,突出了“人”在文学中的中心位置,并且响亮地提出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有的人说他曲解了高尔基的原意,或者说,对高尔基进行了“误读”。然而我认为,他并不是歪曲了高尔基,而是发展了高尔基,弘扬了高尔基,把高尔基那里还不那么鲜明的命题变得十分鲜明,把高尔基那里还没有直接连在一起的那几个字直截了当地连在了一起:“文学是人学”,使文学理论中这条千古不灭的真理更加显豁,从而也使高尔基更加光辉、伟大、可爱。
第二,当有的人糊里糊涂地把文学中的人和现实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并且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弄颠倒(“现实”为“主”、“人”为“从”)时,钱谷融指出,在文学中,“现实”就是人的现实,即“人的生活”,并且把颠倒的关系又颠倒过来:“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但是,这中间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反过来,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本质,作为你创作的目标,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不完整的;而所谓生活本质,也很难揭示出来了。”(注:《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第三,钱谷融突出强调了“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灵魂: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他对中国和外国优秀文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继承,特别是对“五四”以来倡导“人的觉醒”、“人的解放”,提倡“人的文学”的优秀传统的继承。当然,那时他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和诠释亦非尽善尽美,但他强调“尊重人同情人”、“把人当作人”等观点,绝对比后来(特别是“文革”中)某些人“把人当作兽”或“把人当作神”要进步,要正确。
第四,钱谷融注意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注意文学自身的特性。当人们只看到文学的“认识”性质、“反映”性质,把文学的任务只局限于“揭示”“本质、“反映”“规律”时,他提醒人们要注意“文学作品本来主要就是表现人的悲欢离合的感情,表现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对于不幸的遭遇的悲叹、不平的”(注:《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当人们观察文学的眼睛只盯着“外在现实”、“客观生活”时,他提醒人们要注意人的内在精神、情感世界——不但要注意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人,还要注意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人(作家)和作为文学批评主体的人(读者与批评家)的内在世界、世界观、思维和情感方式:“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注:《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这潜伏着后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新时期)人们摆脱文艺学中单一模式,从多种角度观察和阐释文学的萌芽;也成为后来“主体性”文学思想的先声。
然而,也仅仅是潜伏的“萌芽”和微弱的“先声”而已。如前所述,无情的现实是,钱谷融的这些文学思想一直处境悲惨,被加上各种罪名予以批判。这种偏颇直到1978年结束了“左”的思想路线之后才逐渐得到纠正。于是,有了80年代“文学是人学”的再度张扬。
“人学”的再度张扬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这篇长期受到批判的论文作为一本理论著作出版发行。这等于把它郑重其事地重新发表了一次,一是表示理论界对这篇文章基本观点的认同和赞扬,二是为它平反。在这前后,一些报刊杂志发表了钱谷融的与此文有关的文章,如1980年第3期《文艺研究》发表了他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这是《论“文学是人学”》受到批判后,作者于1957年10月26日写的一篇检讨性文章,而其内容,则是对自己观点的进一步阐释和辩护。他再次强调“人是社会现实的焦点,是生活的主人,所以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现实,抓住了生活”;在文学领域内,“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都决定于作家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文学既然以人为对象,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应该是其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注: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1983年第3期《书林》又发表了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说明该文写作、发表和受批判的一些情况,提供了一些背景材料。这些著作和文章的发表,说明当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与此同时,许多作家有意识地以“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指导自己的创作,并且总结创作经验,将它提高到理性水平上来。例如,高晓声在总结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验时说,文学创作是一项关于人的灵魂的巨大工程,如果说文学要“干预”什么“反映”什么,那么“文学应该干预或反映的是人的精神生活、人的灵魂”(注:高晓声《创作思想随谈》,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刘心武说:“按文学眼光来观察、分析生活,就是要更多地着重去观察、分析人的命运、人的心灵。”(注:见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冯骥才提出:“是不是应当注重写人生?”(注:冯骥才《下一步踏向何处?》,见《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许多批评家也总结新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如,俞建章详细分析了从刘心武《班主任》、谌容《人到中年》、宗璞《三生石》、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蝴蝶》到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中对人的描写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总结说,“文学是人学。作家对于人道主义社会理想的追求和歌颂,最终是要通过塑造理想人物表现出来”,“这股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从它的兴起,到艺术上形成比较鲜明的特征,都是时代造就的。是历史变革的产物。对于这个变革的规模和趋势,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中华民族即将面临一个由变革而振兴的时代。报晓这个时代来临的,将是20世纪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注:俞建章《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面对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和“文学是人学”审美实践的显著成绩,批评家和整个文学界都充满着自豪和信心。以创作实践为基础,许多理论家和学者著文,进一步阐发和深化“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例如吴元迈和李辉凡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高尔基当年有关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及提出这个命题的文化思想背景情况之后,对文学是“人学”的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解。吴元迈说:“文学是人学。更正确地说,文学是艺术领域的人学。因为在世界上除了文学以外,还有心理学、生理学、解剖学……也是研究人的,它们都属于人学的范围。我们只有把文学看成艺术领域的人学,才能够深刻地揭示出它的特殊本质和特殊意义。”(注:见吴元迈《关于艺术领域的人学的思考》,《女生报》1982年第4期。)包忠文在《试论艺术规律和“人学”》一文中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
文学是人学’这个一般的结论,应当在此基础上向前跨进一步。这就是说应当进一步研究作为‘人学’的文学和各种研究人的科学的不同点,研究文学意义上的人和各种科学意义上的人的不同点”。他进一步阐释说:“作为文学意义上的人,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立体的、社会的心理结构,而非简单的、单线条的、机械的平面结构。我们承认文学意义上的人的灵魂的复杂性,同样也应当承认在这个复杂的整体中,有其主导的方面,正是它构成了人的全灵魂的核心。正是这个主导方面,使人的灵魂中的各种因素,得到有机的融合,并构成活生生的艺术上的‘这一个’。”(注:包忠文《试论艺术规律和“人学”》,《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杜书瀛在《文学原理——创作论》中还列出一个专门的题目,论述作为人学的文学中“人”的特殊性:文学中的人,既不同于物质实践部门(如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等)中的人,也不同于精神认识部门(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人,又不同于精神实践部门中其他学科(如道德、宗教等)中的人。这是作为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的人。这是作为“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现象与本质相统一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整体”的人。这是显示着“人的灵魂、内心世界,人的感觉、感受、情感、情绪、思维,人的无意识……以及这整个像海洋一样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瞬息万变的形态,有形无形的运动轨迹”的人(注: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5页。)。这就把文学中的人更具体化了。
显然,“文学是人学”在80年代,比起30年代(高尔基)和50年代(钱谷融),其理论内涵有了更新和更深的发展。
“人学”命题的局限及对它的超越
新时期之初,“文学是人学”的巨大功绩就是使文学回归到“写人”、“写人的全部生命需求”,把人作为文学的中心和目的,并在批判林彪、“四人帮”专制政治对人的异化的同时肯定人的价值。它使文学创作充满了人的气息,人的主体意味。这对于刚刚结束的“文革”文学的“人的匮乏”,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当时代发展给予了人的尊严与价值以充分肯定,“把人当作人”的人道主义要求已经成为文学中一个不争的事实的时候,这一命题却反而显得有些苍白和空泛了。新时期中国社会为文论家们提供了一个拥有巨大包容性的历史语境,改革现实的急剧变化和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派生出多重复杂的时代需求和人文话语。这个时代既需要对专制政治“造神运动”的批判,树立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又需要在经济关系的改革中确立竞争意识,强调利益原则。于是,人们刚刚还沉浸于从神道主义、兽道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亢奋当中,却又很快面对无可抗拒的经济原则的残酷挤压而丧失自信与激情,走向怀疑与虚无。多元现实促使文论家重新思考文学的“人学”意义,超越这一命题的政治学阐释,转入对它的文化哲学思考。
当新时期的人们在经济观念驱动下走向新的异化形式——“物化”、又一次丧失人的尊严之时,文论家发现:“文学是人学”命题的人道主义解释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首先是它建立在实践美学基础上的单向度思维方式,即认为只要人类战胜外部世界,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就会产生美。显然,它的思考中缺少了一个向度,即人类的历史生成的双重性和循环性,人类在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同时,又在遭受来自对象对人自身的种种扭曲,而人又是在被异化过程中不断抗拒异化回归自然本真的,这是一个永恒的循环过程。由于人类总要不断地改造自然推进文明,所以人类也不可能消除其改造成果对自己的异化。而异化的这种持久性,又使人类永远处在不断地走向自我的过程中。因此人类历史不是单向度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而是自然向人生成与人向自然生成的双向同构过程。美在此分别从互相背反的形态中产生出来,人类不仅在自然的人化中,通过物质劳动创造美;而且在人的自然化中,通过艺术活动创造美的心灵世界。于是,美便显示为两种形态:改造自然的成果形态和审美活动的过程形态。而人道主义话语对美的本质的解释却仅仅局限于人类历史生成的单向度上,局限于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作为改造自然的成果出现的美的形态。
“文学是人学”话语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把重点放在了表现内容的“人学”特征上,忽略文学形式上的发现和创造。因此,当人性、人情、人欲大量出现于文学作品中时,文学作品的艺术创造却未见起色。“于是,在人道主义意义上大写的‘人’走到前台时,文学反倒退隐到幕后去了。或者说,文学在摆脱为政治服务时,又蹈入为‘人’服务的工具性窠臼,其结果,受损的依然还是文学自身”,“通过对人的呼唤,作家行使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但也失去了把这种呼唤转换为文学上创造的权利”(注:吴炫《中国当代文学观局限分析》,《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正是在这种政治话语暴露出局限性的地方,反异化的文化话语显示了它的超越性,李劼的《文学是人学新论》站在人类的自我生成的高度,对“文学是人学”作出了新的反异化、反规范的解释。他认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是文学向人的生成,一是人向文学的生成。前者具有文学的人本性,后者具有文学的文本性,它们构成文学与人的双向性,即人在文学创造活动中创造了自身,而文学又在人的自我创造过程中获得了存在。相对于人的存在,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显示了它的规定性,而相对于文学的规定性,人作为文学的创造主体在一个非人化的世界面前得以确立了自身。文学与人之间这种相应的创造性构成了彼此的同构性,即人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创造而创造自身,语言艺术通过人的自我创造而体现自身的文学性。前者构成文学的审美性质,后者构成文学的审美样式”(注:李劼《文学是人学新论》,见《艺术广角》1987年第1~2期。)。在他看来,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文学,总是在异化给人类历史带来退步的时候显示自己的抗争,把每一个文学创作主体推向其作为人类的存在的自由境界。而文学在这样的抗争中自我生成着,生成为具有人性意识的审美主体。由于异化现象是一种与文明发展相应的共有物,只要人类文明不停止发展,异化现象就不会在人类历史上消失,异化的这种持久性决定了人类审美活动的永恒性。在人向自我生成的过程中,文学也向自我生成着。
在“人向自我的递归”中,李劼将实践美学作为传统人道主义自负心理的理论复制,分析了它的局限性,认为:“自然向人生成的每一步,都充满着生成的自然的人的异己化”,所以人类不可能像实践美学描述的那样“通过实践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完成审美”,人类的生成史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向人的生成史,即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还是一种抗争异化实现的人向自身生成的历史。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正是以抗拒异化的方式,在人向自身生成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生成。文学拥有一个与人类的自我异化与反异化的过程同构的过程,它是一个规范与反规范的向自我递归的过程。规范是文学确立自身的界定,又是文学丧失自身的异化。文学在不断地界定自己的过程中不断丧失自己,又在不断的反抗异化中寻找自己。
总而言之,“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作为一个颇富政治色彩的文学观念被重新提出,到对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反封建意义的强调,再到文学的人类本体论哲理内涵的揭示,这一命题逐步展现出深广的涵盖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同时它也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以及审美本体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标签:文学论文; 高尔基论文; 人性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艺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艺术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