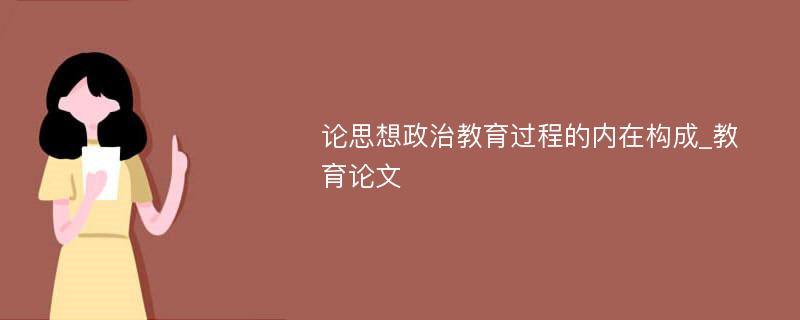
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在构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政治教育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建设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运作体系的建构,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
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包括教育者的认识活动和情感活动。
(一)认识活动
这种认识活动主要表现为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是认识主体,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是认识客体。在任何主客体关系中,客体都以自己的本性、以自己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部规律规定着、制约着主体的活动。把握和运用客体的本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主体有效地开展自己的主体性活动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在实践中要想富有成效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克服客体的外在的必然性。教育者要想富有成效地推进自己的教育实践活动,就必须首先深刻地认识外在于己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克服教育对象、教育内容等的外在必然性。在教育者的认识活动中,对教育对象的认识,是教育者编制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的基础。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认识关系的确立及相应认识活动的开展,为其间实践关系及相应实践活动即教育活动的开展创造着前提条件。
对于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认识活动在整个教育活动中的意义,历代思想家多有关注。中国古代学者将教化的实施与对人性的讨论置于不可分割的同一论域,正是看到了对人性的认识与教化的有效进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少学者还跳出性善、性恶、性无善恶、性混善恶等探讨层面,更为具体地分析现实的教化对象的各种性情特征,以此作为教化展开的依据。正是基于对教化对象有效教化的展开中所具作用的深切体认,与中国丰富的教化论同时成长起来的,还有丰富的“知人”论,无论是《吕氏春秋》的“八观六验”之说,还是董仲舒的“故知其气矣,然后能食其志”之论,无不是“知人”论的具体表现。在西方,人们同样将对教育对象的认识视作教育开展的前提。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代表人物杜威强调“心理学的方面”是教育过程有效展开的基础,所谓教育过程中的“心理学的方面”,即教育过程中对教育对象的内在心理结构的认识和掌握。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对人格内部结构的研究是理解人能传递给世界什么和世界能传递给人什么的必要基础”[1];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也指出:“作为人类行为、生理心理机能、发展顺序和变态科学的心理学,应成为教育计划和决策的基础,因此教育机构也变成了心理学的场所。”[2]如此之类的描绘,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对教育对象的认识在有效教育开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当然,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这些论述尽管多有精辟、深刻之处,但在整体上,并没有为教育者全面认识作为人的教育对象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思想意识产生、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为教育者正确认识教育对象提供了基本的科学指针。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认识,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深入地分析处于现实、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之中、作为教育对象出现的人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实际状况、思想意识接受能力、接受倾向等,从而为其制定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方案创造首要的、必备的条件。
教育者的认识活动除了包括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之外,还包括对教育内容的认识。此外,教育者的认识活动,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进行,还增加着对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影响下相关反应的认识,亦即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反馈信息的认识。这种认识,构成了教育者由其实践活动进入到对教育对象、教育内容重新认识、重新制定其教育方案阶段的必经中间环节。
(二)情感活动
教育者的情感活动主要表现为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所展示、所蕴含的理想和信念、对教育对象所产生的积极的情感体验。如果说认识活动的有效进行为教育者教育实践活动的定向及方式方法的选择提供着理性指导,那么,教育者情感活动的有效进行则为教育者的认识活动、实践活动,为教育对象的意识、实践活动提供着驱动力量、感染力量、催化力量。
首先,教育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由此而迸发出的教育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执著、奉献精神,是教育者自觉以端正的态度认识、对待教育对象,积极进行教育实践活动的推动力量。
其次,教育者对于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所展示、所蕴含的理想、信念和积极情感体验,以及由此而迸发出的教育者对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所蕴含、所展示的理想和信念的矢志不渝的追求精神及坚定不移的信奉态度,既是一种示范力量,以身教的巨大感染力构成为有利于教育对象接受教育内容的强大“感染场”,推动教育对象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展开和良性运作;又对教育者实践活动的喻含意义具有意义充实及意义放大作用,从而使教育者的教育行为声情并茂、有血有肉,使教育者的教育行为成为其真情的流露,真实自我的表达,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照本宣科和口头信息递送。
再者,教育者对于教育对象的积极的情感体验以及由此而迸发出的对教育对象的爱护、尊重、同志式的友好态度,是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确立的前提条件,也是教育对象接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内容的必需的催化力量。
作为意识活动过程的重要方面,教育者的情感活动同样表现出动态发展性。它以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既有情感为基点,随着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意义体味的逐步加深,对教育目的、内容理解的愈益全面、深刻以及对教育对象认识的愈益全面、深刻而不断发展。
教育者的认识活动与情感活动构成了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发展进程这一角度而言,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担负着推动思想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转换,即由社会对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素质要求与教育对象既有思想政治素质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向具体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对象既有思想政治素质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转换的任务。教育者的意识活动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这一形态转换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其为教育者实践活动即教育目的的制定、教育内容的编制、传递等活动提供认识前提和驱动力量而得以实现。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实践活动过程
教育者的实践活动即在意识活动的基础上,教育者所进行的编定教育内容,创设教育情境,择用相应的教育方法,向教育对象传递教育内容的实践活动。对于这一活动,我们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这一活动以教育者为主体,以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为客体,通过教育者阐发教育内容,引导教育对象思想、行为的变化等形式进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教育者理解为主体,将教育对象理解为客体,主体以其对教育内容的阐发等活动为中介,作用于客体,以引起客体的相应反应,如引起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认识、情感,引起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践行等。但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理解教育者的教育实践活动过程,我们都必须肯定教育者教育实践活动过程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核心性意义。
如前所述,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的转换提供了必备的认识前提和驱动力量。而教育者实践活动过程则具体担负着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转换的任务。在这一活动中,教育者所进行的教育目的制定、教育内容编制、教育情境创设等活动,就是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要求,依据自己对教育对象既有思想状况、思想信息接受基础等的把握,力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转换的活动。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一形态向第二形态转换的同时,教育者的实践活动还担负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二形态向第三形态转换,即由教育者所确立的教育目的与教育对象思想政治素质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向教育对象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自我期望与教育对象既有的思想政治素质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转换的任务。教育者所进行的教育内容的展示等实践活动,所应实现的正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二形态向第三形态转换的推进。
总之,教育者的实践活动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确立趋向于解决的整个过程中必经的一环。这一过程的有效进行,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一般层面、抽象层面向具体层面的转换,将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由外在于教育对象的存在形态向内在于教育对象的存在形态的转换,为以教育对象为主体的意识与实践活动过程的展开创造着必备的条件。
三、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意识活动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教育者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但是,也只有教育者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真正促成了以教育对象为主体的意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过程的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才可能获得其运行程序上的完整性,才可能会有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现,“一切有效果的教育工作,都应以受教育者本人的德育活动为其内在条件……形成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的工作是否卓有成效,就取决于这种德育工作,取决于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并指导这种德育活动。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此。[3]我们之所以强调是否能有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二形态向第三形态的转换是判别教育者实践活动过程是否有效的重要依据之一,关键也正于此。
教育对象的意识活动包括认识活动与情感活动。
(一)认识活动
这一活动,是以教育对象为主体,以教育者及其实践活动、教育内容、教育对象自身为客体的认识活动。
首先,教育对象的认识活动是以教育对象为主体,以教育者及其实践活动为客体的认识活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合格的教育者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其他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包括教育对象都通过教育者主导作用的发挥而相互联系起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也自然使得教育者及其实践活动成为教育对象的认识对象。此外,教育者是在与教育对象的互动中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意图、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信息的。教育者的实践活动作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互动的中介,自然也处于教育对象的认识范域之中。教育者的实践活动虽然不是教育对象认识的最核心性内容,但对教育对象认识最核心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发挥着重要影响。教育者有效的实践活动以一种驱动力量、吸引力量、激励力量,印证、催化力量影响着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认识、吸收和实践转化。
其次,教育对象的认识活动是以教育对象为主体,以教育内容为客体的认识活动。在教育者实践活动的引导下,教育对象从对教育者及其实践活动的形式及其喻含意义的理解进入到对教育内容的认识。对教育内容的认识,是教育对象内化并践行教育内容,形成教育者所期望在教育对象身上实现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必经一环。
再者,教育对象的认识活动是以教育对象为主体,同时又以教育对象自身为客体的自我认识活动。能够以自我为意识对象,是人类的特性,“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4](P96)。教育对象的自我认识是评判性认识。在教育者实践活动的影响下,以对教育者及其实践活动、教育内容的认识为基础,教育对象基本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明确了教育者为其所展现的、自己所应达到的应然状态。这种应然状态为教育对象提供了“反观自我的镜子”。正是以此为参照,教育对象对实然的自我进行比照性认识,从而逐步明确实然自我与应然自我的距离,形成“自我意象不等”,即“人们的个人知觉在自己实际怎样和他们希望自己怎样之间的差异”[5]。这种“自我意象不等”为教育对象自我教育意象的产生、强化,为教育对象自觉地将自身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识,对于教育目的理解予以内化,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目的所展现出的应然的自我状态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进行着方向设定和动力提供。
(二)情感活动
教育对象的情感活动,即教育对象对教育者及其实践活动,以教育内容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的活动。积极的情感活动,表现为教育对象对教育者情感上的接近、尊重、信任,对教育内容及其所表达的教育目的的顺从、认同接纳与强烈的追求、实践欲望。这种情感活动的发生、进行,为教育对象积极接纳教育者及其实践活动提供着积极的和带有催化性质的良好氛围。这种情感活动的发生、进行,又是教育对象追求、内化、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目的的推动力量……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P169),“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6]。这种情感活动还是教育对象由对教育内容的知识型掌握向信念型掌握转化的必经中介,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指出的:“道德情感——这是道德信念、原则性、精神力量的血肉和心脏。没有情感的道德就变成了干枯的、苍白的语句,而这种语句只能培养出伪君子”[7](P157),“只有当行为给学生带来真实感,激动着儿童,在他心里留下愉快、兴奋、精神充沛的情感时,知识才能变成信念。”[7](P177)
教育对象的认识活动和情感活动构成了教育对象的意识活动过程。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转化进程而言,教育对象的意识活动过程担负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二形态转化为第三形态转换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矛盾由外在于教育对象的存在形态转换为内在于教育对象的存在形态,因而,理想的教育对象意识活动过程即是教育目的、内容内化的过程,是使“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的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8]的过程。除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二形态向第三形态转换之外,教育对象的意识活动过程还担负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三形态向第四形态转换,即由教育对象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自我期望与其思想政治素质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向教育对象对教育目的、内容的知识型掌握与其对教育目的、内容的信念型、实践型掌握之间的矛盾转换的任务。
四、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过程
教育对象的意识活动过程是教育对象将教育内容、目的内化的过程,但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并不止于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目的的内化,至于教育对象自我实现目标的确立,它还包括或者说还必须实现教育对象以其意识活动的基础而进行的对教育目的、内容的实际践履过程。这个过程即教育对象“把我的愿望从观念的东西,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转化为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4](P154)的过程。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在更深刻意义上使得教育内容、目的成为教育对象“为我之物”的必经渠道。在自己的意识活动过程中,教育对象已经以知识的形态、观念的形态掌握了教育内容、目的,实现了教育内容、目的由“外我态”向“为我态”、“属我态”的转化。但是这种“为我态”、“属我态”尚需由知识型掌握的层面上升到信念、信仰型掌握的层面。对教育内容的信念、信仰型掌握,只有通过教育对象具体的实践才能实现。
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过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整体过程的一个子过程,它是直观、感性地体现教育者实践活动及教育对象意识活动实际效应的基本形式,并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反馈流程的起点。一方面,教育者不能不凭借任何中介而直接洞察自己教育实践活动在教育对象的头脑中所引起的意识活动,而能够有效充当这一中介的,只能是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教育者借此来判断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目标认识的准确性、深刻度、认同程度及其积极情感体验的强度,并以此为基础,深化自己对处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教育对象的认识,调整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更有针对性地发挥自己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是教育对象新的“实然自我”的展示。这种展示,同时也成为教育对象新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指向。在新的自我认识中,教育对象重新进行自我评价,认识教育者的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示的应然自我与自己当下的实然自我之间的距离或矛盾,产生新的“自我意象不等”,从而生发新的自我教育冲动,推动新的实践活动的展开。
教育对象实践活动过程的上述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在教育对象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体现。就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的转化而言,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过程担负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三形态向第四形态转换,即由教育对象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自我期望与其思想政治素质实际状况之间的矛盾向教育对象对教育目的、内容的信念型、实践型掌握之间的矛盾转换的使命。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由第三形态向第四形态转换的同时,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还担负着推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基本矛盾第一形态确立、向第二形态转换的重要任务。教育对象实践活动过程所应担负的这一任务,来自于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过程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反馈流程起点的性质。
综上所述,教育者的意识活动、实践活动、教育对象的意识活动、实践活动四个子过程的依次展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从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来看,教育者的意识活动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起点,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终点;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而言,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教育者的实践活动过程——教育对象的意识活动过程——教育对象的实践活动过程——教育者的意识活动过程——的依次展开及往复不已,构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整体演进及持续进行。深刻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内在结构及其运作规律,对于我们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