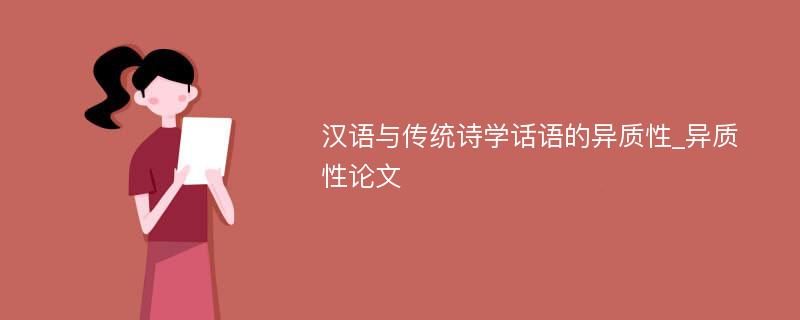
汉语的异质性与传统诗学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诗学论文,话语论文,异质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1)02-0091-07
一
一个民族的语言方式不仅是他们的言说方式,而且是他们对事物和世界的分类方式和感受方式。就此,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在其《词与物》中把中国称之为"heterotopia"。其中"hetero"表“异质的”,"topia"则是"utopia"(乌托邦)去掉"u"。两者合起来其大意为“异质的城邦”。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看法呢?原来是因为汉语。他在书中接着写道:“该国度所使用的语言,它的句法,它对事物的称谓和命名,甚至该语言中联系词语的语法规律,都与我们已知的一切相左。如果在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里,保持语言最基本构成的寓言汉语还能存在的话,那么在诸如博尔赫斯笔下的Heterotopia中,我们平时所惯用的语言系统都将失效,言不及意,词不达意,语法从根本上被取消,我们的神话以及我们的语句中的抒情表达方式都将消解枯竭。”[1]莫尔的“乌托邦”由于是印欧语系(屈折语)的,所以对福柯来说还是“我们”的乌括邦。而博尔赫斯笔下的汉语世界的乌托邦则由于是汉藏语系(孤立语)的,所以就成了"hetero"(异质的)和"the other"(另类)的乌托邦了。叶维廉先生在谈到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时说到:语言行为“是从原来没有关系决定性的存在事物里,决定一种关系,提出一种说明。”[2]更进一步说,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人的世界,因此语言与语言的差异就不仅是语言、语汇、语句等等方面的不同,它们还是思维方式、价值方式、精神方式等等的差异。这样,民族语言即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语言。
汉语的“异质性”导致了传统汉语诗学话语的“异质性”,比如它的内在性、此岸性、意蕴性都不同于西土;它的核心范畴味、神、韵、气、境等也是独特的。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当今背靠母语的“乡土根性”,开掘汉语诗学的文化资源,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诗学话语是有意义的。
二
西学东渐,由于西方诗学话语的比照,传统的诗学话语显出了缺少分析性、逻辑性和体系性的一面,我们曾经把这当作最大的弱点和不足而力图加以克服。百年后,德里达先生又高兴地看到汉语诗学提供了“所有逻各斯中心之外所发展起来的强有力的文明态势的明证。”这真是坏也“非逻各斯”好也“非逻各斯”。不过这倒是启发了我们:不同的诗学话语形式原来深深地植根于不同的语言方式。
德里达先生的意见与中国许多语言学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汉语的异质性首先就表现在其非逻辑形式结构之上,具体说来,则表现在汉语词法的高弹性以及汉语句法的自由性这两个方面。
在汉语语法学界,词类的划分一直是一个难题。外籍留学生学汉语查《现代汉语词典》会发现,在词条后面“居然”没有标出词性,这太令人惶惑不安、大惑不解了。因此,在习惯于有严格词类划分的屈折语的外籍学生看来,学汉语就类似于没有保险绳的攀岩,是一种精神的冒险。事实的确如此,比如“神思”一词就既象名词又象动词。《毛诗序》中有这样的话:“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这同样一个“风”有的是名词(如《国风》),有的是动词(即感化、教化)。这种非常可疑的现象在屈折语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那里,一个基本词根,作名词、动词、形容词时,读音各不相同,同时字也各不相同。词性使用的随机性、滑动性可以说是汉语作为孤立语的第一个鲜明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中国古代流传很广的“易之三名”也说明了这一点:“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名词)一也,交易(动词)二也,不易(形容词)三也。汉语人对这些是习以为常的。涉及诗学话语的一些关键词也是滑动多变的,比如,“美”可以是名词(美不自美),可以是形容词(美不自美),还可以是动词(美死你了)。再比如,“味”可以是名词(味无味),也可以是动词(味无味)。
汉语词法的高弹性除了上述“混淆”以外,还表现在名词的非秩序性(孤立语?)和名词概念的不明晰性上。
在西方屈折语的严格分类视野下,名词是非常重要的。名词承担着对世界和人自我的命名。所谓“能指”/“所指”的种种复杂关系也主要是在名词中展开。名词的冠词(定/不定)、性、数、格的种种规定都在强调特定名词的概念性,并由此开始在这些名词概念间建立起一种横向连锁关系,进而建立起一种名词概念的纵向层级隶属关系,最后完成为一个名词概念的恢恢天网。印欧语系的这种特长,实际上就是用理性或词(logos)把庞杂混沌的对象世界整理和划分成不同的或相同的类别,并探索其特定的基本性质。在此,分类就是用名词来整理和划界;从下到上来说是归纳,从上到下来说是演绎。在西语人看来,分类是“科学”研究的绝对前提。严格而“科学”地对作品进行分类就成了西方诗学的显著标志。而汉语界没有严整完善的分类的逻辑性结构框架,也无明确的分类的逻辑支点和逻辑根据,所以现代汉语诗学的四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散文)按西学标准是暧昧而混乱的。前三类可以说是按性质区分的,而散文一类又是按形式来划分的。这明显地违反了“根据同一”的分类原则。造成这种“不伦不类”的分类方式的根本原因其实是汉语名词的非逻辑化特征。照汉语诗学看来,分类是随机随意的,也是不重要的,“文本同而末异”,分类实在是细微末节之事。曹丕的《典论·论文》分出四类八体,即“奏议”、“书论”、“铭诔”、“诗赋”。陆机的《文赋》分出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这里面很难说有多少分类的根据或语词逻辑。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要有“逻辑根据”一些。他说“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即按作品的语言的有无韵划为文/笔(韵文/散文)两大类。这种分法在西语人看来也是“幼稚而肤浅”的。
总之,作品分类问题折射着汉语和西语之间的异质性,更折射着汉语智慧和西语精神之间的异质性。福柯就是从中国类书的分类方式中感受到“另一种思想体系的奇异魅力”,想到“我们自己思想的限度,那样思维的绝对不可能性”,此发现激发福柯的灵感,写下了著名的《词与物》。
另外,汉语名词概念抽象性不高,它们常常是隐喻性的,具有一种集体表象的朦胧的互渗性质。它们的内涵外延也常常是流动的、不确定的和发散式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这样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此盖道之文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其中有自然之文,有人文之文,也有文学之文。纵观整部《文心雕龙》,其中“文”的含义有:文化、文明、文学、天文、人文、文字、文采、等等。关键在于,在西语人看来,这些“文”的横向连锁关系和纵向层次关系都是“相当混淆”的,因而也是缺乏逻辑性和体系性的(《文心雕龙》在传统诗学中比较而言逻辑体系性还算强的)。
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常常用意象性名词而不习惯用抽象性名词。于是在中国传统诗学中,“不同的写作方法被称为‘隔岸观火’(一种超俗的格调),‘蜻蜓点水’(轻描淡写),‘画龙点睛’(提出作品的要点),‘欲擒故纵’(起伏跌宕)……”[2]正因为如此,索绪尔确认汉语是“不可论证的语言”。在汉语里,名词不依赖冠词、而且不区别阴性阳性而存在,这就使汉语置于一种零度的状态,“这种零度状态同时包孕着所有过去和未来的说明”。词在这里却成了一个难以逆料的神奇之物,每一个名词都是一个潜伏着所有可能性的“潘多拉的盒子”。庄子《天下》篇中就有不少这种名词性词组,它们简洁、突兀而充满爆发性的立在那里:“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
在西方屈折语中,动词因为有严格的时态、语态及语气、人称的种种屈折变化,所以显得非常严整而明晰。比如,"do"这个动词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就有"am doing"、"have done"、"have been doing"以至"should have been doing"等等十六种时态变化,如加上语气、人称所造成的变化其形态就更多了。这些严格的变化对于以汉语(孤立语)为母语的人来说简直太麻烦,叠床架屋、牵丝攀藤,真的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做”(do)就是“做”,在哪里都是“做”,干净利落、简洁明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四个动词精精干干,一路下来、一气贯之且清清楚楚。
汉语句子常可以在同一施事语或主题语下动词连续铺排,而不必交待各词组之间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这就形成了汉语独特的流水句的格局。汉语并没有一个定式的动词核心,其视点是流动的,这很象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汉语的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常常是松散的,究竟是动作者,还是论题、起点、对象、线索都不很确定。我们下面以“洋泾浜”英语为例可以很好地说明屈折语和孤立语的差别。比如说,“文以气为主”,“洋泾浜”英语就说:"Literature importance is Breath"。这在“真正”的英语看来是“太不像话”了,“真正”的英语则应该这样说:"What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in literature is the great vital Breath。"其意为,对于文学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是伟健而充满活力的气息。这对于汉语人来说的确是过于罗嗦和转弯抹角了。
再如,汉语的这样一句,“涧户寂无人”,在屈折语的法则下就应该表达为:Silent is the hut beside the stream:There is no one at home.[4](“涧边的草庐是静寂的:没有人在家”)。加线部分是英文多加的。多加的主要是动词、介词、冠词和引导词。在汉语人看来,清清楚楚的东西,偏要如此穿靴戴帽、自找麻烦,简直是莫明其妙。
汉语是以意联语、以神统形。这很像中国书法中的“笔断意连”,这里讲究的是“气韵生动”。比如《毛诗序》言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一气哈成,颇为痛快,也颇有说服力。汉语的语词往往是言简意赅的,汉语的行文也讲究辞约而意丰,以文从字顺为高。“在汉语交际中90%的句子都不是SVO型以动词为中心的‘主动宾’的句子模式,因为这种心理机制并不适宜于汉族人以及生来就操汉语者的语感。汉语句子是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现的,一个个句读按逻辑事理的铺排才是汉语句子的构造本质。”[5]
汉语还有个特点就是很多句子没有主语,从古至今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有时一段话里,无主语的句子比有主语的句子还要多。这些无主语的句子,有的还可以添得出主语来,有的甚至就添不出来。比如,陆机《文赋》中有这样一段话:“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以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谁站在那里感受、遵循、观察、悲伤和欣喜?是陆机还是准备写作的人,或者是成功的大作家?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也是一个不需要说清楚的“伪问题”。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溅泪”“惊心”的究竟是作者还是花鸟,“实恐起杜老而问之他也未必能够答出来的。”因此,汉语诗学话语中很早就有了“诗无达诂”一说。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说:“置言有位,……位言曰句”,“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看来汉语表达中主语谓语的区分是不重要的,其语法信息主要是从语序中传达出来的。
基于西方屈折语,西方诗学传统中“对定义有一种极大的文化渴求(cultural aspiration),即希望将定义加以稳定并由此对词汇加以控制。”[6]然而,作为孤立语的汉语是重神轻形、重功能轻本质的,其表达式(特别在古代)就没有严格的“命题定义式”语句。因此,中国传统诗学其实对“诗的本质”这类定义性问题根本不感兴趣。我们曾经大量讨论中国传统诗学的本质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发展,很显然是西方诗学体系定义中心论的产物。换言之,我们的那些讨论是建立在根本性的文化“误读”基础之上的。如果说,《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是中国传统诗学对“诗”的本质定义的话,那么,其接着一句“歌永言”,就该是中国古代关于“歌”的本质定义了。“歌”难道“本质”上就不是“言志”的么?另外,关于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一语也不是什么定义。《文赋》中确有“诗缘情而绮靡”,但同时还有“诔缠绵而凄怆”,这“诔”又是不是写“情”的呢?如若说“缠绵凄怆”也是写“情”,那么,“诔”是不是也应“根据定义”而“绮靡”呢?这不全乱套了吗!其实,从汉语的语感来说,陆机这里讲的与其说是在定义(属加种差)“诗是什么?”不如说是在谈论“诗应该怎么写”。
叶嘉莹先生对此也有同感,她认为,“中国的民族似乎一向就不长于西方之科学推理的思辨方式。……我们只要对中国语言的特征一加反省,便可知道这话乃是可信的,因为语言的组织方式也便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具体表现。中国语言的组合在文法上是极为自由的,没有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态的区分,而且对于一些结合字句的词语如前置词、接续词、关系代名词时也不加重视,一切都有绝大的自由,因此在组成一句时,主语、述语与宾语以及形容词或副词等都可以互相颠倒或竟而完全省略。”[7]汉语的确是重意义气韵而不重形式论证的语言,它表现出很强的人文性和风格化。这些特征包括:
(一)重意会默想
洪堡德在《论语法形式的性质和汉语的特性》中写道:“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里,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在汉语表达中语义是中心,只要语义条件充分,语法就会让步,有时甚至是为了语气的原因、语音的原因就可以使语法让步。据《诗人玉屑》卷六载,王仲写了首诗其中有这样一句:“日斜奏罢长扬赋”。王安石看后认为还可以改得更好。他就把它改成“日斜奏赋长扬罢”这样半通不通的句子。后来有人问他为何这样改,王安石说,“诗家语如此乃健”。如若有人要追问,恐怕就只能“欲辩已忘言”,或者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
汉语重意会默想而不重形式结构,给汉语文学留下了相当广阔的创作空间,汉语诗学话语也打上了鲜明的烙印。林纾在其《春觉斋论文》中写道:“……盖用寻常经眼之字,一经拼集,便生异观。如花柳者常用字也,昏暝二字亦然,一拼为柳昏花暝则异矣。玉香者常用字也,娇怨二字亦然,一拼为玉娇香怨则异矣。烟雨者常用字也,颦恨二字亦然,一拼为恨烟颦雨则异矣。绮罗者常用字也,怨恨二字亦然,一拼为愁罗恨绮则异矣……”这种自由的意会意合,在语言层面增加了所述情景的“摩擦力”,使听者读者留连再三;而就人们的生存经验层面而言,则在这些词汇的碰撞中,使这些“寻常”的生存经验达到新的综合。
在汉语诗学话语方面也是这样。叶维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上的批评是属于‘点、悟’式的批评,以不破坏诗的机心为理想,在结构上,用‘言简而意繁’及‘点到为止’去激起读者意识中诗的活动,使诗的意境重现,是一种近乎诗的结构。”“即就利用了分析、解说的批评来看,它们仍是只提供与诗‘本身’的‘艺术’,与其‘内在机枢’有所了悟的文字,是属于美学的批评,直接与创作的经营及其达成的趣味有关……”[8]
(二)重气韵生动
汉语造句追求气韵。汉语人对语法结构不感兴趣,对气韵格律倒是煞费苦心,比如“四声八病”、“蜂腰鹤膝”之类。人们很早就总结出,减少虚字即减少语气语调的松懈和间隙,从而会产生语气急促、紧凑的效果;反之,增加虚字即增加间隙,从而会产生语气舒缓,节奏鲜明的效果。诗学话语更直接宣称“文以气为主”。人们反复比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和“落霞孤鹜齐飞,秋水长天一色”的差异,主要就是在考究哪种说法更符合气韵节律一些,而不是意义或者语法方面有什么分歧。谢榛在《四溟诗话》卷四中说,“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虚字多,则意繁而句弱。”他在卷一中又说,“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字,开合呼应,悠扬委曲,皆在于此。”
下面一个争论也是涉及行文用语的气韵格调问题的:《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中有这样的语句:“季孙行父秃,晋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刘知几看后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将“御”改为“迎”或者改为“逆”,因为“逆亦迎也”。这条意见与本文无关。他还提出第二条意见,即后四个排名太罗嗦。他认为应“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毕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但是,魏际瑞(号伯子)不同意刘知几的第二条意见,他在《伯父论文》中答辩道:“古人文字有累句,涩句,不成句处,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伤气格,故宁存其自然。”
汉语人对气韵生动的重视,来源于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首先,气是万物之源;其次,气是精神之源;再次,气是文章(文气)和语言(语气)之源。所以,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之际,文学家、诗人就要感应宇宙之生气,充实自己之灵气,最后使文气和语气与这些“气”相通相应相和从而创造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三)重感性形象
高名凯先生在《汉语语法论》中写道:“中国语是表象主义的,……就是中国人的说话,是要整个的、具体的,把他所要描绘的事件‘表象’出来。……结果中国的语言,在表现具体的事物方面是非常活泼的,而在抽象关系的说明方面,则比较没有西洋语言那样的精确。”[9]汉语这种表达方式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个性,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中,甚至已内化为一种哲学品格。
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谈想象是这样“谈”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而西方诗学谈想象则是这样“谈”的:首先把想象区分为初级形式和高级形式。初级形式再划分为接近联想、对比联想、因果联想;高级形式再划分为再造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如此等等。
汉语人显然不喜欢抽象的概念,他们习惯于“观物取象”,使概念生动可感,并有所依托。他们对概念往往不说“是”什么而是说“似”什么。中国传统诗学谈崇高风格时“说”:“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过,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姚鼎《复鲁·絜非书》)康德则以这样的方式“说”崇高:“对于自然界的崇高的感觉就是对于自己本身的使命的崇高,而经由某种暗换赋予了一自然对象(把这对于主体里的人类观念的崇高变为客体。”[10]康德还非常之逻辑抽象地把崇高分为“数量的崇高”与“力量的崇高”来言说。
三
作为孤立语的汉语与作为屈折语的西语,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对语言本身的基本态度。在汉语的历史上,我们不断看到对语言的质疑和不信任,“言不尽意”成了汉语人的常识。而在西语人那里,语言一直是一种十分伟大,十分令人崇拜的东西,甚至有语言创世之说。《圣经》开篇就是“太初有言”。列维—斯特劳斯详细研究了西方语言后坚定地认为,“创世”就是以语言为“秩序”进行整理,“创世”就意味着以语言“秩序”进行切分,“创世”就意味着用语言“这样一种编特殊体为体系的编织过程。”[11]
在汉语人看来,宇宙、自然和世界是自足存在的,人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和意义世界也是自足存在的。庄子就认为语言的作用和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表达了对语言的绝望,他说:“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这位汉语思想界的智者就这样逐一从“书”到“语”,从“语”到“意”,从“意”到“意之所随者”层层追究,也层层否定;由外到内,由粗到精,由明到玄展开了语言和表达之物间的环环错位。
汉语与西语对语言的基本态度从“道”与“逻各斯”的差别中也不难见出。众所周知,道与逻各斯在格位、体位及格级含义上都有不少共同之处,但是,两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区别常常为论者所忽略。逻各斯意味着理性,意味着词语,意味着言说。逻各斯就是人通过语言向自然立法,即人通过语词的命名超越自然的偶在性而达到一种逻辑阐明。在逻各斯那里,人通过语言(也就是通过逻辑),打破个别观察材料的孤立封闭的状态,用力把它从其实际发生的“此时此时”中拔拽出来,将它和其它事物一道归集到一个涵盖一切的,具有内在同一性的逻各斯体系中去。在西人看来,“凡无词处,一无所存”。这样,西语中的“逻各斯”(logos)就不可遏止地倾向于言说,以至于他们有了"logorrhoea"(嗜语癖)这一个由"logos"变化而来的词。
汉语世界中的“道”意味着造化,意味着静默的“玄览”,更意味着“无言”:“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就此标示出“道”的不可言说性以及宇宙万物之精的不可言说性。任何言说出来的“道”,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道”的歪曲形式(而且仅仅能暂时歪曲)。汉语人耳熟能详的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辩若讷”……
汉语诗学话语也同样体现了对语言的怀疑:孟子针对拘泥于字词者提出,“故说诗者,不以文言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陆机也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刘勰也认为,“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实而难巧”。(《文心雕龙·神思》)在意识到语言的局限之后,汉语诗学话语又进一步根据“言不尽意”提出“意在言外”、“象在言外”,把遗憾变成了有价值的追求。他们对创作的要求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他们对作品的要求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舍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他们对读者的要求是“但见性情,不睹文字”。
汉语诗学话语对语言的回避,其实是对语言的逻辑功能和知性功能的回避。这种回避甚至常常发展到对语言知性逻辑难度的蔑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因此提出“无理而妙”。贺黄公在《皱水轩词筌》中说:“唐李益诗曰:‘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子野《一丛花》末句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此皆无理而妙。”[12]“嫁与弄潮儿”和“嫁东风”都是不可能、不合逻辑理性的,但是这些似乎无理的言词,反而更深刻地“言说”出了怨妇失望的特定情绪。王禹偁有一首叫《村行》的诗这样写道:“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如此评论说:“按逻辑说来,‘反’包含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并不违反事实;但同时也仿佛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显然也是不合逻辑的语言方式,但它是符合美感的语言方式。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更干脆直接指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
任何语言都有二个维度:一是理性分析的维度,即语言的逻辑维度和命题维度;二是直觉直观的维度,即语言的气氛、气韵、神韵维度。如前所述,屈折性的西语是倾向于语言的第一个维度的,它注重的是语言的实证性、稳定性、确定性和逻辑性;孤立性的汉语则是倾向于语言的第二个维度的,它注重的是语言的心灵性、游移性、模糊性和直觉性。汉语诗学话语正是秉承这一维度才创造出奇观:用语言打破语言的局限,用“说”来言说“不可言说者”。
汉语这种直觉直观的维度,还具体表现为两个向度。这就是第一,感性的直觉直观,在语用学中叫做“喻示”向度,在传统诗学话语中叫做“韵味”。第二是精神的直觉直观,在语用学中叫做“启示”向度,在传统诗学话语中叫做“妙悟”。“喻示—韵味”向度和“启示—妙悟”向度虽同属语言的直觉直观维度,但它们与语言的逻辑推理的知性维度分别具有不同的关系。简单地说,“喻示—韵味”的向度是低于逻辑语言之维的,它以逃避的姿态向感性回归,所以它可以说是“次语言”。“启示—妙悟”的向度则是高于逻辑语言之维的,它以超越的姿态向精神飞跃,所以它可以说是“超语言”。
在“次语言”的向度内,语言更接近于“被感叹地使用”,汉语言的处身性和亲历性就此呈现出来。在这里汉语言的絪蕴、气氛和不清晰是一种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言不尽意”。在诗学话语中,这种追求是起码的:“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所谓“辩于味”就是要求一唱三叹,反复缠绵达到百般滋味。贺贻孙在《诗筏》中这样说:“反复朗诵,至数十百过,口颔涎流,滋味无穷,咀嚼不尽。乃至白少至老,诵之不缀,其境愈熟,其味愈长。”明代陆时雍也认为“少陵七言律,蕴藉最深……一咏三叹,味之不尽。”这就是杜甫之诗沉郁顿挫的韵味。而李清照的词给我们以婉转缠绵的韵味。其调名是《声声慢》,其语句也是声声慢(声声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其韵味恰恰就在于这连下十四个叠字,层层推进,其滋味就在于“思妇之情”曲尽。此词从反复寻找开始,继而细觅,终不可得;继而外感冷冷,内感清清,继而凄凄之冷凝于心,继而惨惨心不堪任,继而戚戚而泣。此可谓词词与心徘徊,字字随情宛转,“咀之而味愈长”。如此观之,韵味是不可“分析”的。韵味是生命的直接经验,其间的缓急、清浊、约放、浮沉要求一种鲜活的感应能力和精微的艺术鉴赏能力,它与“求知”性的文学“批评”是格格不入的。韵味的更加内在性的底蕴是“滋味”。它根源于汉语的“喻示性”,在传统诗学话语中被表达为“比”。刘勰释之为“写物以附意”,(《文心雕龙·比兴》)钟嵘释之为“因物喻志”,(《诗品序》)总之都是以语言穿梭和编织于物我之间、天人之间和景情之间。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告诫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霸岸’等字。……‘玉筋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说“破”了为什么就无味了?说“破”了其实就是用语言的知性概念破坏了物我间的圆整关系。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隔”。
在“超语言”的向度内,语言更接近于“被领悟地使用”,汉语言的空灵性和精辟性就此呈现出来。在这里,汉语言的空疏、跳缺是一种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就是“言外之意”。在诗学话语中,它就是追求简括、冲淡、高远而“澄怀观道”。宋代诗论家叶梦得在其《石林诗话》中写道:“‘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耳。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悟”的本质在于人经由语言,超越语言达到“还原”,这时人与本真自然同在,人与天地精神自由往来,达到“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汉语诗学很早就意识到,在语言之外,物各有性,各得其所,此谓“自然”。草自生、禽自鸣,月自照、泉自流;人看也罢,不看也罢;言也罢,不言也罢。这就是忘言虚静、“返朴归真”。这就是“重现物的光辉与灵气。”“忘言”即忘明辨是非:春草自春草,园禽自园禽;春草不可以责园禽之不生,园禽不可以责春草之不鸣。所谓“可”、“不可”都是在语言中以此责彼。妙悟了除超越语言的“通明了悟”、“洞见直观”以外还可以达到点兴玄观,获得多重启示。叶燮在其《原诗》中这样提出问题:“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汉语诗人似乎是掌握着一种独特的“言之”方式和“述之”方式,从而可能去“言”那些“不可言之理”,去“述”那些“不可述之事”。简言之,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要求诗人必须“言”出“不可言”,必须“述”出“不可述”。这就是“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这就是“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究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13]这就是钟嵘所说的“兴”:“文已尽而言有余”。用语言说出“在场者”,但其目的是让此“在场者”指涉“不在场者”。而对此“不在场者”,要“以神遇不以目视”,要“听之以心忽听之以耳”。梁漱溟先生显然领悟到了这种玄远的洞见,他嘲笑那把“鸟鸣山更幽”改为“一鸟不鸣山更幽”的鲁钝。他深知“如‘潜龙’、‘牝马’之类……若呆板的认为是一条龙、一匹马,这便大大错了。”[14]皎然也对这种超语言的妙悟能力发出了吁请:“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谓淼淼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
由此,我们知道,具有异质性的汉语诗学是植根于具有异质性的汉语方式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能责怪刘勰没有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去说和思,正如我们不能责怪亚里士多德没有像刘勰那样去说和思一样。当他们在各自的语言之内成功地说和思时,他们所显示的就不是“缺点”而是“特点”。而我们一些人却把植根西语的体系性、分析性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科学”标准,这是不是一种与文化多元化相冲突的根本性的误区呢?
由此,我们知道,具有异质性的汉语诗学是植根于具有异质性的汉语方式的,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它还是一种价值。汉语诗学的确缺少“体系”,但它并不缺少“智慧”,汉语诗学的确缺少“分析”但它并不缺少“思”。汉语诗学话语正是依靠对“知性”的拒绝,才紧贴着汉语人当下直接的真实的诗性体验,表达着汉语人的生命感受与艺术精神,刘勰、严羽、叶燮是这样的,王国维、宗白华、钱钟书也是这样的。我们当然更应当以真正具有汉语感的汉语,秉承真正具有汉语性的诗性并由此进入汉语人的真实的生命,敞开汉语本身所意味的东西。我们当然更应当通过汉语诗学话语,追索汉语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根。
收稿日期:2000-09-22
标签:异质性论文; 逻各斯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汉藏语系论文; 乌托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