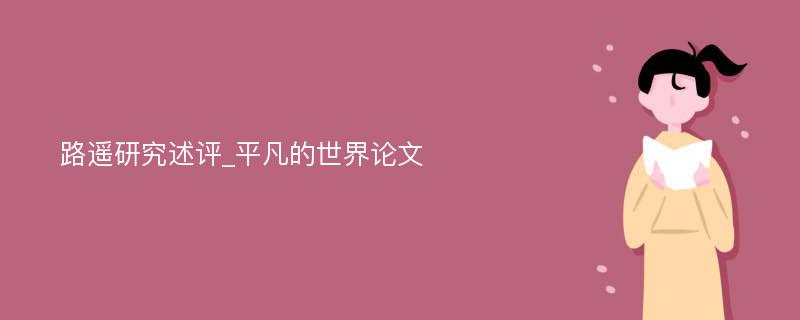
路遥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路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03)01-0089-06
从内容上看,路遥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二是作家研究。从时间上划分,路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主要集中在对作品的评论;第二阶段是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时期,评论家们一方面重点关注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丰富与贡献,另一方面研究其创作心理,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的评论文章;第三阶段是路遥逝世至今,是路遥研究的系统化阶段,出现了一些学术专著。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勾勒路遥研究的运行轨迹,梳理研究成果,供关心、热爱路遥研究的学者参考。
第一阶段: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到《人生》产生“轰动”时期
这个阶段也可以称为路遥研究的初始阶段,它与作家的成长一起同步成长。这段时间,路遥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先后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中短篇小说,这个阶段的评论也多集中在作品评价与创作风格描述上。
1980年,路遥在《当代》第3期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这部中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原来犯过错误,在派性斗争中却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形象,在写法上与当时“写真实”、批判为主的主导叙事风格格格不入,发表前曾一波三折,发表后也获得了一些零散的评论。尤其是资深评论家、编辑家秦兆阳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不是一篇针贬时弊的作品,也不是一篇反映落实政策的作品,也不是写悲欢离合、沉吟个人命运的作品,也不是以愤怒之情直接控诉‘四人帮’罪恶的作品。它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辩不清、思想水平并不很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1]。无庸讳言,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于这部作品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使路遥第一次为全国文学界所注意。
中篇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上发表,标志着路遥小说创作走向成熟。这篇小说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青年人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开掘了现实生活中饱含的富于诗意的美好内容,也尖锐地揭露了生活中的丑恶和庸俗,强烈体现出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正因为路遥与众不同的创作视角,这部中篇小说很快就受到了文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轰动”全国。1982年后,根据小说所改编的戏剧、电影、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出现于舞台、银幕和广播中;评论小说和电影《人生》的文章达120多篇,其中专论高家林的就有30多篇[2](P70),文学界形成研究路遥的一个小高潮。
第一,评论界公认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一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形象。
高家林是路遥在《人生》中一反“十七年”中书写返乡青年的模式,毫无矫饰地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个在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且思想内涵上有争议的人物。(注:参见《作品与争鸣》1983年1、2期“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当时的评论界把问题焦点主要集中在高家林是个什么样的人上:一是高加林是不是“新人”的问题。梁永安称高家林是“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3];雷达认为高家林“有辨不清两种文明的弱点,但主导的方面还是新的因素居多。他是农民母体经历十年内乱后诞生的一个‘应运而生’的新生儿,虽然必不可免地带着旧的胎记,但总体来看,他在精神上是一个新的人物但不是通常所说的‘新人’”[4](P96)。二是高家林是不是个人奋斗者、个人主义者的问题。曹锦清称高家林是“一个孤独奋斗者的形象”[5];而蔡翔认为“高家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而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起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6](P85),他并且认为社会应当对高家林个人主义思想的滋生承担一定的责任。
那么高家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杂人物形象?许多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陈骏涛认为,“高家林是处于人生岔道口的农村知识青年的典型形象。在高家林身上集聚了种种矛盾的性格……种种矛盾汇聚于一身,可能使习惯欣赏简单化人物的读者感到不可理解,但我们却通过这个人物的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像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7]阎纲认为,“高家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8](P404)李劼把高加林放置在中外文学的视阈范围内,同外国文学于连·索黑尔、牛虻、保尔·柯察金等人物形象,以及中国文学中的阿Q、小二黑、梁生宝、高大泉等农民形象加以比较,指出“高家林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一个在当今小说创作中空前出色的文学典型,他既显示了当代中国青年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又镌刻着这一代青年可能具有的种种弱点”[9](P70)。
一番激烈的争论后,评论界的观点虽说有些分歧,但人们公认高家林是路遥为新时期文学画廊塑造的复杂的人物形象,“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之无愧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次胜利。这对我国的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某种深远的影响。”[2](P80)
第二,评论界注意审视路遥作品的审美特质,提出“深沉”与“宏大”是其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
早在1983年,白烨首先注意到路遥结构作品,“不仅注意构筑大起大落而又环环相扣的外在情节,而且注意到铺设涟漪连绵的显现人物内心风暴的内在情节,并常常把二者交叉穿错起来,在波折迭出的矛盾冲突中层层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明晰地揭示出促进人物行动的内在的外在的因素”,并指出路遥作品呈现出“执着而严肃的艺术追求”[10]。到1985年,李星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深沉、宏大正是路遥所具有的艺术气质,也是他在全部创作过程中所苦心孤诣追求的艺术目标”[11](P65),这正是路遥小说创作的审美特征。李勇还注意到赋予这种深沉而宏大的审美品格的精神支柱,是作家强烈责任感、使命感,是“浓烈的情感色调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理想的热情和严峻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化了《人生》的悲剧主题,使之呈现出崇高、悲壮的审美特色。”[12](P76—79)
第三,评论者们还紧紧抓住路遥在书信与创作随笔里反复表述的“城乡交叉地带”(注:路遥关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表述,可参阅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82.3期);《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路遥文集.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的关键词,寻求解读其创作的钥匙。1982年8月17日,评论家阎纲在给路遥的信中,首先谈及“城乡交叉地带”[8](P406);王愚专门就此问题撰写评论,研究“在交叉地带耕耘”[13](P38)的路遥的创作特色;而李勇称“‘交叉地带’这个典型环境和高家林这个典型形象,是路遥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他在自己的创作敏感区最重要的收获”[12](P74—75)。通过“城乡交叉地带”的把握,这为解读路遥小说创作提供了较为准确的视角。
可以这样说,这一阶段的路遥研究,一是公认了高家林是“这一个”典型人物形象,二是把握住了路遥作品“深沉”、“宏大”的美学特征,三是明确了路遥善于在“城乡交叉地带”构建小说世界、表现审美理想的创作特点。
第二阶段: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出版到荣获“茅盾文学奖”时期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在《花城》1986年第6期发表后,单行本相继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1年,出齐三卷本的《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论界以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史诗性的品格”为突破口,重点分析了《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的新创获”[14](P25),全面而深刻地探讨路遥小说的内在特征与创作魅力。这个阶段形成了路遥研究的高潮,出现了一系列有深度、有学术理性的评论文章。
1987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问世后,《花城》与《小说评论》编辑部曾在北京召开了有国内许多著名评论家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上,人们给予其很高的评价,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具有内在魅力和激情的现实主义力作。它以1975年至1978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性的图画,是对十年浩劫历史生活的总体反思。在事件和人物之间,作家更着力表现新旧交替时期农民特有的文化心态,试图探寻中国当代农民的历史和未来。”、“这部作品之所以被称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在于作品展示的大量的生活细节、农村生活图画都相当逼真,而且在于作者众中精细深刻地刻画出了人物的心理、性格,写出了中国农民个体和群体的命运。”[15](P153—154)。与此同时,曾镇南认为“《平凡的世界》采用的创作方法,是非常严谨的现实主义。作家承继了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发生历史性的大挫折和大转机的特定时期内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进行严肃的艺术概括和艺术创造。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既师承了我国当代文学中的杰出的前辈柳青写作《创业史》的那种特有的严谨、深刻、精于典型人物的创造和典型环境的烘托,又有自己的发展”。他还对《平凡的世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及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更为准确的分析,从而进一步阐释“这种异常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采取,决定于两个原因:第一,决定于作家对他所面对的时代和生活过来的世界的独特的认识。第二,路遥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彻底的朴素性,还取决于作家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来面貌的典型理解”,得出了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新创获”[14](P22—25)的结论。曾镇南的评论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是一篇令人信服的评论文章。
到了《平凡的世界》三部全部出版并荣获“茅盾文学奖”后,李星发表《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对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系统分析,认为路遥“坚持 了 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相统一的原则”、“一贯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 义 ’,重视创作题材‘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创造服务于现实人生的活 文 学”、“小说的现实魅力就在于服务人生和取材于现实人生的统一。”[16](P90)。 白 烨还深中肯綮地分析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优势,认为“现实主义创作因直面现实凛 利 、囊括生活广博,兼之有揭示人的命运和洞悉人的心灵的多种功能,它迄今仍是反映 我 们这块多难的热土和表现热土上的子民的最有效的武器”,正因为路遥坚持现实主义 创 作方法,《平凡的世界》“读后使人萦绕于怀的,无疑是普通人在时代变迁和苦难历 程 中昂扬不屈的生命力,以及由此隐含的对于民族近传统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平凡的 世 界》超越路遥以往创作并跻身于当代优秀长篇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17](P18)
我们知道,路遥构思和创作《平凡的世界》的1980年代中后期,正是我国文坛风靡着新观念、新方法的热潮,反映论、现实主义、典型创造等文学观念受到冷落以至贬抑的时代。有责任的评论者们严肃而认真地分析路遥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他们除了指出路遥的创作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继承前人传统之外,还进一步阐述路遥小说的新创获。
首先,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孙少安、孙少平是对高家林形象的突破,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后的座谈会上,人们就把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与高家林的性格特点加以比照分析,研究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指出“孙少安、孙少平是《人生》中高家林形象的延续和裂变,他们是作家将高家林个性和灵魂的自身矛盾进行了调整和融合后而产生的新的形象,孙少安更多地保留了优秀的传统精神和文化观念,孙少平则更多地接受了世界现代意识和文化形态的影响”[15](P156)。李星则认为,“他们有远大的理想,但没有高家林式的好高鹜远;他们有为实现理想的奋斗决心,但却没有高家林式的极端个人主义,比起高家林来,他们更现实,更愿把理想的实现附丽于整个农村现状的改良。从某种意义上说,少安、少平既是高家林追求精神的继续,又是对高家林式的追求方式的否定。”[18](P162)。曾镇南指出,“孙少安和孙少平,是古老的黄土地养育出来的两个历史之子,又是生活大变动催生出的现个现代之子。他们是亲兄弟,从血缘到气质,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但由于生活道路、阅历经验、文化熏陶的不同,思想性格也有很多相异之处。这是具有不同的典型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两个发展中的典型性格”[14](P19)。还有人对孙少平给予更充分的肯定,认为孙少平“是小说作者对生活的一种发现和创造,是作品中最有思想价值和艺术光彩的人物”,“他深刻地反映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破土而出的小生产者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上进一步解放的强烈要求。这是变革时代向往现代文明的一颗不安定的灵魂……他是一个具有丰富时代内容和思想内澄清的艺术典型,是作品中最能引起广大青年读者共鸣的一个人物”[19](P141—142)。当然,人们还对小说中塑造的其他典型人物进行细致分析。
其次,认为路遥的创作具有了“史诗性的品格”。
早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出版座谈会上,人们就认为这部小说“显露出了构思博大,气势恢宏的特点。不能说《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作家的追求赋予了这部作品以史诗性的品格”[14](P154)。评论者们第一次把路遥的创作审美特征从“深沉”、“宏大”提升到“史诗性的品格”上来。王愚也认为“《平凡的世界》通过几个纠结在一起的普通人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内心活动、精神历程,映衬出历史的变化对广大人民心理构成的渗透和影响……作家艺术构思和审美追求的指向,虽不能说已经写出了一部史诗,但却是具有史诗的品格的[20]。李星就此问题展开论述,指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是“诗与史的有机结合,又是诗的内容压倒诗的内容的不均衡体”[18](P158)。待到第三部出版后,雷达进一步分析作品的内在特征,认为作家“抓住了两种最基本的结构力量,那就是史与诗:纵向的史的骨架与横面的诗的情致的融合,对社会历史走向的宏观把握与对人物命运、心灵的微观透视的融合。没有史的骨架作品无以宏大,没有诗的情感作品难以厚重。总的来说,《平凡的世界》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历史化和历史进程的命运化,力图概括我们当代生活中最大的思潮和某些本质方面”[21](P172)。
与此同时,评论界在探究路遥的创作心理上也有了新的成果。
1987年,李星就论及路遥的创作心理,认为“作家的创作活动是作家依据自己的个性、气质、心理,面对前人无比丰富的文学传统的积极的选择过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正是作家无法回避的选择结果。这种选择既是作家主体性的主动,又具有某种无法回避的被动”[18](P163),只是未能展开充分论述。李继凯通过路遥小说中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叉、大众文化与先驱文化的交叉的几种形态,进而推断出路遥在“作家化”的过程中,“地域或陕北文化、中国或民族文化、世界或人类文化这三个层次的文化构成,先后顺序层递地对他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内化为他的文化心理的重要因素,从而由内而外地制约了他生活与文学的理解与选择,写出了一系列属于路遥的作品”[22](P35)。而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长篇论文,应该是我们目前读到的关于路遥意识研究的最为系统与深刻的专论。虽说其发表在1993年,但是它的写作时间在1991年,故我们把它划入“第二阶段”中加以研究。此文的研究视阈开阔,通过路遥的“苦难意识”、“土地意识”、“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哲学意识”、“生命意识”、“悲剧意识”等多种意识的缜密分析,准确把握路遥所拥有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灵世界,提出“路遥的代表性作品,可以说集中了自己在历史转型期两个阶段的人生经历和心灵感受。因而路遥本人和他笔下人物的精神世界,将是我们了解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重要的心灵记录和重要的精神史页。”[23](P73)
总之,这一阶段通过对路遥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研究,发掘路遥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的新成就。这既响亮地回答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坛没有过时,而且也为今后定位路遥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就是在21世纪初的今天,反观这些真知灼见的论述,也深感其意义所在。
第三阶段:路遥逝世至今
1992年,路遥中年早逝后,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悼念文章(注:追悼路遥的文章结集为《陕西文学界1992年增刊·回忆路遥特辑》、《星的陨落——关于路遥的回忆》、《路遥纪念文集》、《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等,除了《星的陨落》、《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正式出版外,其它更多的是内部发行。)。这里要提及高歌的《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和晓雷《男儿有泪——路遥与谷溪》(注:《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发表于《延安文学》1993、1—2合刊;《男儿有泪——路遥与谷溪》发表于延安文学2000、1期。),由于叙述的真实性和缜密性,成为研究路遥生平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当然,随着当事者情感的沉淀,估计还会有一些回忆路遥生平的资料问世。
1990年代,路遥研究进一步走向系统化、体系化,出现了一些研究路遥创作及其作品的学术专著(注:路遥研究专著大体上有: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赵学勇《早晨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宗元《魂断人生——路遥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姚维荣《路遥小说人物论》,新加坡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如王西平、李星、李国平的《路遥评传》,从“路遥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丰富宏大的小说世界”、“路遥的意识世界”三个方面展开。“丰富宏大的小说世界”里,分“人物的世界”、“审美的世界”、“路遥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路遥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突破”四方面;而“路遥的意识世界”分“小说中的意识世界”、“路遥的文化、人生意识”、“路遥的文学背景”三方面论证。应该说,这部专著第一次对路遥创作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论证,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路遥的学术著作。宗元的《魂断人生——路遥论》分为“导论”、“人物论”、“艺术论”、“比较论”四个部分,尽管在外表形式上是路遥的系统研究,然而在内在气质上,更像是一部路遥创作的专论。赵学勇《早晨从中午消失——路遥的小说世界》和姚维荣《路遥小说人物论》是针对路遥小说文本的专论性著作。而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中专门研究路遥创作的章节,把“路遥的乡土情结”、“路遥的文化构成”放置在“20世纪中国作家的乡土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24](P298—357)的宏大背景下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表现出研究者从容不迫的理论功力。
当然,这一时期发表了关于路遥研究的大量学术论文,总体而言,表层阐释与平面描述较多,缺乏理论深度和新意。倒是李建军的《文学写作的诸问题——为纪念路遥逝世十周年而作》[25](P24—30),把路遥研究放置在21世纪中国当下文学的背景下,在研究“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的过程中,重新发掘与定位路遥的当代意义,使文章拥有了新意和价值。
这里还必须提及国外路遥研究情况。目前,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被翻译成法文、俄文等几种文字出版,国外有零星的评论文章(注:可参见《路遥文集·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日本学者安本实先生致力于路遥研究,他先后翻译了路遥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做过系统的资料整理工作,撰写了多篇论文,成为国外为数不多的路遥研究专家(注:可参见《一位日本学者的路遥研究情结——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安本实先生访谈录》,《延安文学》,2002、5期。)。
四、今后路遥研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加强路遥作品的研究。文本研究是作家研究的基础,没有对作品认真地、反复地研读与阐释,作家的研究就无从谈起。目前,研究者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给路遥带来声誉的作品,而对于路遥的其它一些作品的研究远远不够。比如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虽是路遥创作历程上的重要作品,但有待于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就是荣获殊誉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还有个在新的视角与新的经验下“再解读”的问题。我们知道,“再解读”的主要特色就在于文本的重读。重读那些已经被经典化的重要作品,讨论作品的修辞层面与深层意识形态功能(或文化逻辑)之间的关联。而路遥的这些作品,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解读的空间。
二是要加强对作家的本体研究。仔细检讨路遥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过去更多地注重作家文本研究,而对作家本体研究重视不够。路遥作品之所以具有长时间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除了与时代有关,还与他的出身、师承、学养、经历、以及性格、气质、人格、理想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路遥的童年时形成的“自卑情结”以及对其的超越,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这影响着他作品的生成走向。直到目前为止,社会上仍没出现一本拥有学术品格的《路遥传》,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呼唤《路遥传》,应是呼唤路遥本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的出现。
三是关于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定位问题。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位置,似乎是出现了文学史家与评论家、读者评价相背离的尴尬局面。前文已经交代,路遥的作品在发表之时,评论界就给予很高的评价。就读者方面而言,路遥逝世后这些年里,其作品因为具有积极向上和催人奋进的内在精神气质,在广大普通读者心目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华读书报》多次组织的“中国读者最喜爱的20世纪100部作品”的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始终名列前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最喜爱的小说联播”问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名列榜首。可是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对路遥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问题,基本采取一种漠视态度。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仅把《人生》放置在“感应时代的大变动”一章里加以表述,称之为“人生道路的选择与思考”[26](P238)。而在华中师大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和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均未涉及路遥。记得孙犁研究专家张学正先生曾讲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所谓定位,不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作家进行随意的吹捧或贬抑,而是根据已存在的作家作品及其在文学界、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的客观事实,对他的价值和地位给予一种科学的文字表述;或者说,定位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实对作家的一种命名。”[27](P52)那么,如何看待路遥,或者说路遥在当代文学史上究竟有怎样的地位,这应该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者要进行学理研究并要回答的问题,而不是轻易地肯定或者否定。笔者认为,路遥的思想与艺术、人品与道德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说明研究路遥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确认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肯定路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贡献,也是肯定他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这寄希望于更深入、更扎实的研究。
我们知道,今后的路遥研究任重而道远,需要用丰富的研究实绩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正如路遥所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研究也一定会结出累累硕果来的。
收稿日期:2002-11-20
标签:平凡的世界论文; 路遥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读书论文; 人生论文; 孙少平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