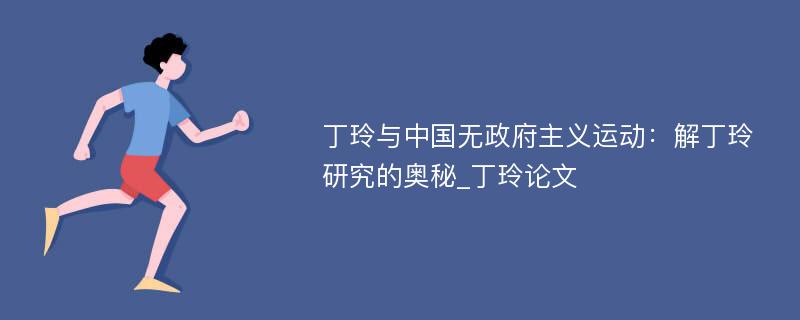
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破解丁玲研究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主义论文,之谜论文,中国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6-0150-06
一、丁玲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基本事实考辨及研究现状
丁玲是否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否参与过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其作品是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在丁玲研究领域一直暧昧不清,成为丁玲研究中的最大谜团。丁玲本人极少谈及自己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与此不同的是,研究者们常常谈及这一敏感话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在平民女学的丁玲女士是一个沉默的青年。她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当这三位青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时候,他们全有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1]
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前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l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在描写同样的青年知识女子苦闷的、无耻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在说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阿毛姑娘》里,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的无政府的倾向。[2]
当时(1912——1921)怀着时代的苦闷,要发泄,要反抗的她,思想上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3]
(1921年)年初,与王剑虹同赴上海,……她们接触了一些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并随他们参加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举办的会议。但丁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不满意。[4]
一九二一年,她进入共产党办的由陈独秀、李达等人领导的上海平民女校,曾上街募捐,为纱厂女工的罢工做宣传:后来结识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二年加入无政府党;随后又脱离无政府党,进入由共产党人办的上海大学学习。[5]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人们还不太了解的是,丁玲还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二十年代初丁玲曾跟活跃于国立北京大学的无政府女权主义组织有过接触。从那些妇女那儿她也许知道曾访问过中国的艾伦·契和多拉·布莱克两人。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参加了一九二三年的玛格莉特·桑格节制生育和性解放运动。丁玲有可能从埃玛·戈德曼的思想中吸取了一点什么,因为她有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6]
人们可以回顾1921年和1922年间,丁玲被它(指无政府主义——引者注)的在普遍和睦中实现完全的人类自由的理想主义的教义所吸引,并参加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活动。然而到了二十年代早期,正如个人主义的结局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破坏了它的吸引力。……因此,与丁玲有一些联系的上海无政府主义协会于1922年中期结束了。[7]
在丁玲研究中,上述说法十分流行。但细读这些文章,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当学者们说丁玲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时,都没有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这类说法是否可信,我们不得而知;二、当学者们指认丁玲作品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时,往往语焉不详,一带而过。这说明,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及其早期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已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但系统的研究至今尚未展开。
丁玲作品既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那么丁玲必定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濡染。一些学者指陈丁玲曾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团体或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都没有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梳理有关史料,考辨丁玲与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就成为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无政府主义在晚清传入中国,五四时期达到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3年,各地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不下80个,他们出版的刊物和小册子不少于70余种。”[8]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等地成为无政府主义传播的中心。这一时期,丁玲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辗转求学,与无政府主义者们有过密切接触,并深受其影响。其中可以确定的事实有:
1.1922年初,蒋冰之与好友王剑虹同赴上海,废蒋姓,改名丁玲,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无政府主义提倡“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之主义也”[9]232,将家庭看作社会腐败(如人人为子女谋私利)和阶级制度的根源,因此它吁求废除家庭(家族),取缔私有财产,使每一个体获得独立和自由。废除家庭的直接表现就是废除姓氏。1912年,中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师复与彼岸、纪彭等人在广州成立“心社”,订立“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等多项戒约,其中有一条即是“不称族姓”。他们依据生物进化论,认为“人类远族同出猿猴,五洲万国凡百族类莫非昆弟,又何一族一姓之可言哉?”现在所谓的族姓,乃“自私之物也。有族姓则有长幼尊卑之名分,长者尊于天,幼者卑于地,蔑视公道,丧失人格,莫此为甚”[9]237。师复原名刘绍彬,早期参加反满革命,易名刘思复,改信无政府主义之后,废刘姓,改为师复。因此,废姓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是极为流行的现象。五四时期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等人也都曾废姓。不难看出,蒋冰之废“蒋”姓,易名丁玲,是她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醒目标志。在其小说中,也出现了废姓的主人公(如《韦护》)。陈明在谈到这件事时作了如下解释:“为什么要废姓呢?表示反封建,我不要姓。她母亲姓余,父亲姓蒋,她说我不要姓。可是一到社会上,走到哪儿人家问你贵姓,你总得有个姓啊。结果她们几个姐妹拿一本字典乱摸,摸到什么字就姓什么。结果摸到一个‘丁’字,好吧就姓丁吧。她那个时候有点无政府主义思想(着重号为引者加)。”[10]反封建有多种方式,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将“废姓”作为反抗家族制度的手段。陈明最后补充的这句话,才是问题的实质。
2.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或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过密切接触,参与了一些他们组织的活动。几乎所有有关丁玲生平的论著都提到这一点,但至今没有见到对该问题的详细考证。如:她接触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谁?她参与了哪些活动?丁玲在回忆1922年就读于平民女校时说过下面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都到平民女校来过。他们三个人搞了个狂飙社,找我们这些小孩子参加,我们兴致很好,但是没有搞起来。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我们去听,由李汉俊讲马克思主义。黄爱、庞人铨那些人死了,开纪念会,我们也参加。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演讲。”[11]这段文字中有两条史实:第一,张闻天、沈泽民、汪馥泉当时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因而他们与丁玲的接触,成为丁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黄爱和庞人铨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两人1922年在湖南遇害后,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纪念活动,丁玲参加的应该就是此类活动。同时在上海平民女校任教的陈独秀,曾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支持者之一,早期也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沈雁冰也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十分倾心,他说:“1917—1918年间,我也喜欢无政府主义的书,觉得它讲的很痛快。”[12]45这说明,当时平民女校的一些人,对无政府主义并不陌生,甚至还不乏好感,这无疑会成为影响丁玲的潜在因素。
1923年,丁玲从南京到上海大学就读,这期间接触的瞿秋白、施存统等人,都有过一段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经历。瞿秋白在谈到他与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时说,他那时“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13]。李达在回忆当初建党的时候也说过:“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发起人中,就有好几个是安那其,施存统、李汉俊、沈定一(沈玄庐)都是。”[12]52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当丁玲接触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时候,瞿、施都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信仰的更替不会像更换一件衣服那样容易,当新的信仰确立的时候,曾有的信仰可能还会留有某些残余。更何况,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体系在基本主张上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否定私有制,崇尚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都诉求未来的大同理想,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两种理论的边界并非十分清晰。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说:“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很安慰,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13]463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对立,而忽视了它们在文化立场上的相似性。正是由于这两种理论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大”时的很多人,都是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进入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如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高君宇等,瞿秋白和施存统当然也属于这种情况。“没有经过无政府主义和空想主义这个环节,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而是少数人。[14]这说明,在1920年代早期,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人员上存在着模糊的交叉地带。就某一具体个人来说,可能在思想上也会存在着“交叉地带”。也就是说,当这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短时间内未必能完全洗掉那种追求极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气质。美国学者德里克分析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在1921年之前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而他们在转向布尔什维主义之后,也仍然与无政府主义保持着亲密的关系。”[15]丁玲与这些人长久相处,有可能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另外,从其他史料看,丁玲与朱谦之交往甚密。朱谦之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宣扬“新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之一派),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俄国十月革命。他后来回忆说:“我自第一部书发表后,当即与无政府主义者有所接触,又和法预科同学郭梦良等合办一种《奋斗旬刊》,我的署名是AA,最初我和无政府主义者兼生(凌霜)大开笔战,接着我们的思想就渐渐接近。”[16]4061923年,朱谦之与以独身主义者自居的杨没累相爱。杨没累是丁玲在周南女学时的同学,彼此来往密切,也很了解。1928年,丁、胡住在西湖葛岭,朱、杨也住在那里,经常来往。但时间不长,杨就病故了,丁、胡帮助料理了丧事。之后,朱谦之依然和丁、胡保持着较为密切的来往。据朱谦之回忆,杨没累死后,他先去广州,后去上海,“常与胡也频、蒋冰之(丁玲)、沈从文等相见,冰之是没累在周南女学时同学,没累逝世时,她和也频适在杭州西湖,曾助理丧事,以后他们创办《红与黑》,在招待上海出版界的席上,我还代他们招呼朋友,这种友谊,直到我出国后,还继续一时”[16]433。1929年4月,朱氏到日本留学时,还带着一本丁玲和胡也频赠送的《和英大辞典》[16]435。详细列举丁玲与朱谦之的交往,只想说明一点:朱谦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丁玲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渠道。丁玲与朱、杨的交往,也同样对丁玲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莎菲就是杨没累”[17]!将文学典型与现实人物简单对应,并不可取,但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确实有杨没累的生活痕迹。且不说莎菲在性格上与杨的相似性,小说中的毓芳和云霖,为怕生小孩,就拒绝同居,这跟朱、杨禁欲式的爱情也有相似之处。
从丁玲当时的交往来看,朱谦之是丁玲接触到的最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对丁玲思想的影响,也自然不可估量。
以上是我们能查到的丁玲与无政府主义者相接触的事实,至于说她“一九二二年加入无政府党,随即又脱离了无政府党”[5],我们没有查到相关证据。据王中忱、尚侠在《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书说,他们曾就该问题请教陈明和王一知,这二人都否认丁玲曾加入过无政府党,陈明只承认丁玲“一度和无政府主义者接触过,并且有过这样的朋友,随他们一同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一次会议”[18]18。丁玲在与王中忱谈及此事时说,当时一位女校的好友经常给她看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但她对此不感兴趣,无政府党人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很恶劣的[18]18-19。这位女校同学很可能就是杨没累。
除了这些有据可靠的相关史料之外,丁玲的《梦珂》、《韦护》等小说中,出现了有关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描写,这说明丁玲对这些人是熟悉的,但似乎并无好感。如《韦护》写丽嘉拜访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形:
她带着热望走到醉仙他们那里去,而他们都只在一种莫名其妙中享受着自认的自由生活。那惟一足以使他们夸耀的,只是他们无政府主义者的祖宗师复在世时的一段勤恳的光荣;然而就只这一点,在他们自己许多人口中也不能解释得很清楚。他们曾吸引过丽嘉,因为丽嘉和他们有同一的理想。而现在呢,他们却只给她失望了。
既然她对无政府主义者心怀不满,那么说她曾经加入无政府党,就显得很勉强,所以只能说,她在思想上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参加过一些活动,但并未真正加入到无政府党的组织中去。丁玲和胡也频在加入左翼阵营之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对政治并无兴趣,对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包括共产党人),怀有明显的排斥情绪。在纪念胡也频的一篇文章中,丁玲曾做过如下告白:“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伤感与虚无。”[11]第9卷,67由于无政府主义对现实社会采取极端对抗的姿态,而其理想又如海市蜃楼一般不着边际,所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很容易堕入孤傲、狂狷、愤懑的境地。丁玲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表现出的愤激情绪,恐怕与其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不无关系。她在纪念向警予的文章中说:“我不是对什么人都有说有笑的。我看不惯当时我接触到的个别共产党员的浮夸言行,我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自然就会有人在她面前说我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说我孤傲。因此她对我进行了一次非常委婉的谈话。”[11]第6卷,29无论事实怎样,丁玲当时疏远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这是确定无疑的。
通过上面的考察,不难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想曾一度在丁玲的思想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直到1930年代,这种思想才得到清算和批判。
二、无政府主义与丁玲作品中的“性爱乌托邦”
从丁玲的文学道路和知识背景来看,她成名之前并没有多少充足的准备。她既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似乎也没有读过多少经典名著。其文学创作的动机和能力,主要来自于她早期在上海和北京那几年的求学生活。在这几年艰苦而又自由的奔波生涯中,丁玲形成了对人生和对文学的基本看法,这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而在这几年中,她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接触,和她周围泛滥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都对其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美国学者白露认为丁玲“有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6]273,这话恐怕不无道理。
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女性解放内容。无政府主义诉求“万人安乐”的大同世界,在那里:“万物为万人所有!无论男女,只要能够分担正当的工作,他们便有权利来正当地分配万人所生产的万物;这种分配足以担保万人的安乐。”[19]在这一理想的世界中,性别差异被取消,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其中的妇女解放思想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发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抨击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重要武器。1907年,何震在日本成立“女子复仇会”,与丈夫刘师培共同创办《天义》报,以无政府主义理论为基底,发动“女子复仇运动”;巴黎的《新世纪》也将女性解放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而发挥鼓噪。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他们的西方同道一样,将家庭看作“万恶之首”①,而对婚姻和家庭的攻击,预示着性解放和性自由的隐秘指向。按照他们的设想,在无政府世界里,男女可以自由交配,孩子由“育婴院”公养,从而使女子彻底摆脱家庭的羁绊,获得独立与自由。无政府主义理论中有关女性解放的一系列学说,为中国近现代的性解放运动提供了助力。《新世纪》杂志公然刊发了《男女杂交说》:“人群治不进化,爱情之不普及,实婚姻之未废也。今欲人群进,爱情普,必自废婚姻始,必自男女杂交始。”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论证说:“不杂交者种不进”、“不杂交者种不强”、“不杂交者种不智”[20]。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引领了更为激进的近代性解放运动,在晚清暗潮涌动的女性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极端的立场,耸动舆论界视听。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新的文化观念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的某些主张合流,汇成了新的文化阵线。在女性解放问题上,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张,使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带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1917年,《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高曼(高德曼)的《结婚与恋爱》[21],在该文中,高氏从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立场出发,否认恋爱与婚姻之间的联系:“婚姻与爱情,二者无丝毫关系,其处于绝对不能兼容之地位”,并认为“婚姻乃人生之不幸事”。一旦割断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或将婚姻彻底废除,“性”就卸下了所有的责任和义务,摆脱了世俗伦理的监督与束缚,走向绝对自由的境地。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论,在性爱问题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在无政府主义的引领下,五四时期出现了“新村”、“工读互助团”等带有实验性质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在胡适、陈独秀等人支持下的“工读互助团”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类社会实验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愿望,但“在参与工读互助团的青年人看来,‘自由恋爱’才是应该首先追求的‘理想旗帜’”[22]209。随后果然出现了像易群先这样的女“性”解放先锋,惹得舆论哗然。施存统回忆说,互助团刚成立后,团员展开了有关婚姻问题的谈论,“讨论的结果,我们全体一致认为(婚姻)无存在的理由,所以对于从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张和对方脱离关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23]。解除了此前的婚姻羁绊,每人都获得了自由,——恋爱自由或性爱自由。施存统后来把“自由恋爱的实践”看作是“工读互助团”的主要精神[22]216,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工读互助团”虽然涉及少数人,但来自无政府主义的那种“性爱乌托邦”,在无政府主义信仰者间有着广泛市场。从一种激进的政治乌托邦,衍生出更为激进的“性爱乌托邦”,是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突出特点。
正是在无政府主义引发的性爱洪波鼓噪激荡的时候,丁玲离开了老家湖南,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对处于青春期的丁玲来说,这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性爱狂潮,无疑会对其性爱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塑形作用。从其早期小说来看,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带有“性爱乌托邦”的浪漫情调。梦珂、莎菲、阿毛姑娘和在庆云里卖淫的妓女,无论高贵还是卑贱,都不拒绝对性爱的享用和幻想。尤其是莎菲,在没有任何婚姻设计,在对世俗生活的警惕与拒绝中,渴望着惊心动魄的性爱体验:“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11]第3卷,76爱情不再需要海誓山盟的承诺,不再需要洞房花烛的映照,只是瞬间的销魂即可告慰一生。小说中的毓芳和云霖因害怕怀孕而拒绝性爱,莎菲嘲笑他们:“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赤裸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有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11]第3卷,52但丁玲或莎菲毕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还不能不顾一切地“将性爱进行到底”。可以拒绝考虑世俗幸福,可以不考虑性爱的后果(如怀孕),但无法忍受“丰仪的身体”里装裹着一个“肮脏的灵魂”!从小说来看,凌吉士并非十恶不赦。所谓“肮脏”,其实主要指他对世俗幸福的沉湎,他需要的“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11]第3卷,62。对于一个世俗中人来说,这并非大错,但对追求性爱乌托邦的莎菲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因为性爱乌托邦具有超越世俗、拒绝家庭生活的高远指向,这与凌吉士的世俗欲望产生冲突,所以莎菲的性爱乌托邦在凌吉士面前彻底瓦解了。
无政府主义性爱观的影响,也使丁玲与五四女作家划清了界限。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爱情自由,反对包办婚姻。而对丁玲来说,道德无论新旧,都是束缚人的桎梏,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不要道德;而地久天长的婚姻形式,也不一定就是爱情的结果,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婚姻、废除家庭的,所以说,爱情或者性爱,就是男女交往的最终目的:“爱情,爱情是什么?享受,是享受呀!”[11]第3卷,165《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薇底,声称很爱自己的丈夫,却时常背着丈夫与其他男人约会,心理上没有任何的道德负担:“她除了尊重自己的冲动,从未把事的轻重放在心上称一下。”[11]第3卷,168当鸥外鸥向她表白爱情,要独自拥有她时,她却在想着自己的丈夫,“但她不能不听这表白,她很鄙视这男人为什么与其它男人一样,在恋爱的时候会想到实际问题上去”[11]第3卷,180。在薇底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阿尔志跋绥夫《萨宁》的中国传人。多情的乡下姑娘阿毛,也有着不着边际的幻想:“在这旅行中阿毛所见的种种繁华,富丽,给与她一种梦想的根据,每一个联想都是紧接在事物上的;而由联想所引申的那生活,那一切,又都变成仙似的美境,把人捆缚得非常之紧,使人迷醉到里面,不知感到的是幸福还是痛苦。阿毛由于这旅行,把她在操作中毫无所用的心思,从单纯的孩提一变而为好思虑的少女了。”[11]第3卷,123她的梦境也与性爱有关:“她希望有那末一个可爱的男人,忽然在山上相遇,而那男人爱了她,把她从她丈夫那里,公婆那里抢走,于是她就重新做人。她把那所有应享受的一切梦,继续做下去。”这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在没有“王子”的年代,“灰姑娘”就只能吞火柴头自杀了。阿毛与莎菲,甚至梦珂、薇底和《暑假中》的那些女性,尽管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都有一个“性爱乌托邦”之梦。他们不再如五四时期的娜拉们,渴望着飞出牢笼,获得自由[24]。而是渴望着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性爱经历,渴望着不顾一切的疯狂体验。
丁玲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莎菲、梦珂、薇底式的女性形象,依然在其作品中不断出现,对“性爱乌托邦”的追寻,仍然是作者魂牵梦绕的心事。《韦护》中的丽嘉,《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中的望微,都带有莎菲、梦珂的精神遗留。直到《水》的发表,丁玲才彻底摆脱了“性爱乌托邦”的纠缠,走向了政治化的文学道路。
因此,丁玲早期小说,成为女性追求性爱乌托邦的典范文本,它标志着中国性爱小说走出了五四“爱情—婚姻—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一个充满梦想与失落、自由与孤独、挣扎与绝望、孤傲与溃逃的痛苦境地。正在这里,女性体验到的,不再是五四式的由束缚到自由的解放历程,而是“自由”之后的痛苦与焦虑,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新阶段。
注释:
①1907年7月25日《天义》发表汉一(刘师培)的《毁家论》,1908年《新世纪》49号(1908年5月30号)发表鞠普来稿《毁家谭》,激烈抨击中国的家族(家庭)制度,基本代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家庭问题上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