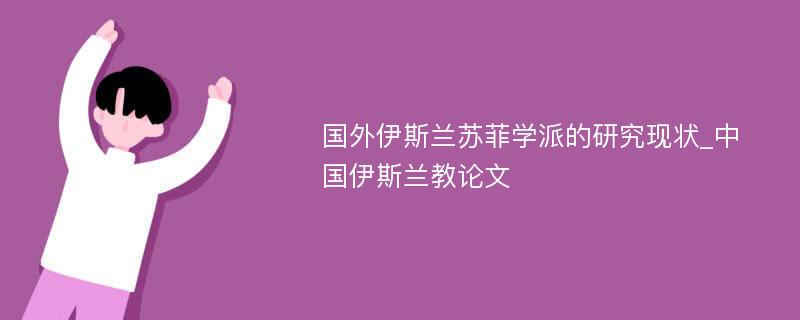
国外伊斯兰教苏非派研究的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态势论文,国外论文,苏非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8)04-0084-04
一
伊斯兰教从兴起到宗教体制的形成,大约经历了三个世纪。最初的一个多世纪,是苏非派形成和发展的时期。苏非派最初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部分门弟子个人的虔敬行为,以崇尚道德、禁欲苦修为基本特征。7世纪末,苦行和禁欲行为在阿拉伯半岛周边地区得到迅速发展,由麦地那、库法、巴士拉等地逐渐扩展到开罗、大马士革和波斯的一些地区。与此,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苦修者、忏悔者和素食者等。后来,这种纯粹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化为一种对奢华风尚的消极抗议,并发展成具有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这一阶段,苏非和苏非派的名称还没有正式出现。8世纪中叶,原来进行禁欲苦修的人士,结成无一定组织的松散团体,开始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人们提出的新问题。8世纪下半叶,松散的团体演变成苏非派。
至9世纪,苏非派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形成,并形成以祝奈德(Abu Qasim al- Junayd)和比斯塔米(Abu Yazid Bistami)为代表的伊拉克和呼罗珊两个主要系统。10—11世纪,苏非派得到广泛传播,同时各地孕育出一批著名苏非大师。11世纪以后,安萨里重建伊斯兰教学科时,把长期受排挤的苏非派纳入正统派学说中,一方面促成了苏非派与正统学者的合流,另一方面为苏非派在伊斯兰教学科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从12世纪起,无组织的松散的苏非修道团体转变为组织严密的教团,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边缘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到16世纪苏非教团臻于极盛,达到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大体而言,苏非派在伊斯兰教的宗教生活中居统治地位长达五六个世纪之久,有“教中之教”之称。18世纪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苏非教团为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独立,揭竿而起并取得胜利。至今,它不仅是宗教中的主要派系,而且也是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主要力量。
二
国外苏非派的研究起于19世纪20年代的西方,1821年法国学者托洛克在其《苏非派或波斯泛神论神学》中对苏非派作了广泛深入地探讨,这可能是研究苏非派的最早著作之一。从这时起西方学者开始对苏非派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之后,英国学者尼克尔森的《伊斯兰教神秘派》(The mystici Islami,伦敦,1914)《伊斯兰神秘主义研究》(Studies in Islamic mysticism,剑桥,1967)等,以大量的阿拉伯文原始资料为依据,通过详细的考证和精辟的分析,说明苏非派形成的历史过程,总括了苏非派的基本内容。
不仅如此,尼克尔森还翻译出版了一些著名苏非学者的著作,如胡吉维里的《掀开帷幕》(Kashfu Al- Mahjūb,伦敦,1936)、鲁米的8卷本《玛斯纳维》(The Mathnavi,8 vols,伦敦,1925-1940)等。尼克尔森著作的问世,把西方学术界对苏非派的研究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另有M·史密斯的《近东和中东的早期神秘主义研究》(Studies in the early mysticism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伦敦,1931)和《神秘者安萨里》(al- Ghazali the mystic,伦敦,1944)等。
在西方学术界,二战后的成绩更为突出。如尼克尔森的《鲁米:诗人和神秘者》(Rumi,Poet and Mystic,伦敦,1950)、阿伯里的《苏非主义》(The mysticism,伦敦,1950)、M·史密斯《苏非的爱之路》(The love's road of sufis,伦敦,1954)、《神秘者之路》(Road of mystic,伦敦,1976)等,这些成果把苏非派的研究引向深入。尔后,在马西农的带动下,法国学者在苏非思想的研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如科尔班的《伊本·阿拉比苏非学说中的创造性想象》(1958)、《阿维森那和直觉的叙述》(1960),安纳瓦迪和加尔德的《穆斯林神秘主义者》(1961)等。日本学者井筒俊彦(Toshihiko lzutsu)的《苏非派和道教关键哲学概念的比较研究》(东京,1966)。对苏非教团的形成、组织、仪式等的研究,特里明汉的《伊斯兰教苏非教团》(The Sufi Orders in Islam,伦敦,1973)最有代表性。全面论述苏非派的著作以安娜玛丽·希梅尔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领域》最具权威。
而与我国西北特别是新疆苏非教团有渊源关系的中亚苏非派研究的成果也较丰硕。如S·M·德米多夫的《土库曼斯坦的苏非派》(1978)、拉赫马诺夫和伊乌苏波夫的《花剌子模的圣地及其渊源》(1963)和A·沙法罗夫的《德尔维什派的起源及社会本质》(1975)等[1](9)。印度学者赛义德·莱兹维的《印度苏非主义史》(A History of Sufism in India,新德里,1978)不仅是研究印度苏非派的力作,也是研究我国新疆苏非派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论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弗莱彻教授的开拓性著作《中国和伊斯兰教内亚研究》(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c Inner Asia,1995)探讨了也门和麦加的道堂与中国门宦的内部联系。而弗氏的《中国西北的纳格什班迪耶》(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1995)则对西北虎夫耶、哲合忍耶门宦与纳格什班迪教团的渊源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当代伊斯兰研究著名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的《伊斯兰教精神性:神秘显现》(Islamic spirituality:manifestations,纽约,1991)和《需要神圣科学》(The need for a sacred science,纽约,1993),威廉姆·W.柴提克的《苏非主义:一个简短的导论》(Sufism:a short introduction,牛津,2000)以及尼克尔森《伊斯兰神秘主义研究》(2004)的再版,使苏非派的研究更加深入。
三
应该说,阿拉伯学者研究苏非派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在二战前苏非派研究基本上是纯西方的东方学者的研究活动。早年,一些穆斯林学者把西方势力统治伊斯兰世界的责任归咎于苏非派的传播。因此,认为西方研究苏非派是“一种殖民主义者的密谋”[2](2)。自19世纪初以来,倡导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学者只限于对伊斯兰教法的恢复和宣传,而忽视苏非派思想,甚至对其持否定态度,造成苏非派在伊斯兰世界长期得不到重视和研究。尽管苏非派在伊斯兰“西化知识分子”眼中一文不值,但在民间却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二战后,当穆斯林知识分子意识到离开研究苏非派很难完整地研究伊斯兰教思想时,波斯、阿拉伯、印巴次大陆和土耳其的学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资料,逐渐地把精力投入到这一工作中。但是,他们转借或翻译过来的研究成果,在学术观点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学者的偏狭和局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开始重视对苏非派的研究,不仅整理出版了历史上一些著名苏非大师的遗作,而且把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乌尔都文、土耳其文著作翻译出版。在黎巴嫩贝鲁特出版了诸如安萨里的《迷途指津》(Al- munqzu min Al- dlāl,贝鲁特,1980)、沙赫勒斯坦尼的《宗教与教派》(Al- milal wa Al- nihl,贝鲁特,1992)、艾布·嘎斯姆·古什里的《古什里苏非学论集》(alrisāl al- qushair fi ílm al- tasawwuf,贝鲁特,2001)、吉里的《完人》(al- lnsan al- Kamil,贝鲁特,2000)、比斯塔米的《苏非派全集》(al- majmū'a al- sufiyah al- kāmila,贝鲁特,2004)等名著和权威性的苏非派术语辞书如由安瓦尔撰著的《苏非派术语词典》(M'ajim al- mustalhāt,al- sufiyah,黎巴嫩书局,1993)和里法格·阿吉姆主编的6卷本《伊斯兰苏非派术语百科全书》(Mwsu'a mustalhāt al- tasaw- wuf al- islami,黎巴嫩书局,1999)以及穆罕默德·杰拉里·舒勒福(Muhammad Jlali shrf)的研究论著《伊斯兰教苏非派研究》(Dirāsāt al- tasawwuf al- islami,贝鲁特,1984)等。埃及自古是苏非派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向来重视苏非派的研究。1960年代重新编辑出版了赛剌吉·图西(Al- sirāj Al- tūsī)的《光耀》(Kitāb Al- lum'a,开罗,1960)、卡拉巴兹的《认识苏非派》(Kitāb al- ta'arrf li Madhhab ahl al- tasawwuf,开罗,1960)以及伊本·阿拉比的《智慧的珍宝》(Fusus al- Hikam,开罗,1967)和《麦加的启示》(al- Futuhat al- Makkiyya,开罗,1967)等名著。
研究性的代表论著主要有:埃及学者阿菲夫(Abūal-'ala Afīfi)的《苏非派:伊斯兰教的精神革命》(al- tasawwuf al- thwrt al- ruhiyah fi al- islam,亚历山大,1963)、伊布拉欣(Ibrāhīm Busyūni)的《伊斯兰教苏非派的传播》(Nasha' t al- tasawwuf al- islam,开罗,1969)、侯赛尼的《存在单一论哲学》(Falsaf Wahdt al- wujūd,开罗,1997)和艾布·沃法·塔夫塔扎尼(Ahū wfa Taftazani)的《苏非派入门》(Dāhl al- tasawwuf,开罗,1983)等,黎巴嫩学者穆罕默德·杰拉里·舒勒福(Muhammad Jlali shrf)的《伊斯兰教苏非派研究》(Dirāsāt al- tasawwuf al- islami,贝鲁特,1984),海湾国家中科威特学者阿布杜·热哈曼的《〈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苏非思想》(al- fikr al- sūfi fi dwu al-Kitāb wa al-suna,科威特,1986)和穆罕默德·阿布杜·茹伍夫(Mahmmud' Abd al- rwūf)的《苏非探真》(Al- kashaf an Haqīqt al- sūfiyah,约旦,1994)等,这些成果的出现使苏非派研究出现了新的高潮。但遗憾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学者对苏非派的研究出现两个极端,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过于标榜苏非派,甚至出现溢美之辞;另一种则过于批评贬损。尽管如此,仍不乏有如埃及阿菲夫那样的公正学者。
四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国外对苏非派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创新性和前瞻性。但美中不足的是因受社会史观、研究方法和资料取舍的影响,东、西方学者的研究亦有较大差异。伊斯兰世界的学者占有原始资料较多,但缺乏足够的理论水平。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虽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但缺乏对苏非派理论和实践更为准确的把握。苏非派既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派别,也是伊斯兰教研究中的核心领域之一,虽然蕴含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在研究中存在很大的难度,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些领域甚至是不敢逾越的禁地,如对苏非教团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学术界对此也有诸多不同的声音,致使苏非派研究处于一种“尴尬”的学术境地。尽管现实研究与苏非派的实际作用还存在一段距离,但长期以来,苏非派在伊斯兰教思想史、哲学史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影响,使得国内外必须重视对苏非派的研究。
首先,苏非派在伊斯兰教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通常认为苏非派只是一个宗教派别,因此对其研究领域仅仅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事实上,从一定程度上说苏非派更是一种认识宇宙的态度,是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在这种认识论和世界观的支配下,历史上孕育出诸如赛剌吉·图西、卡拉巴兹、古什里和伊本·阿拉比等大批苏非学大师和学者,以及如伊本·西那、安萨里和伊本·赫勒敦等著名苏非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整个伊斯兰教精神的构建中却起到重要作用。早一点说,自苏非大师哈拉智之后,苏非派成为继沙里亚(Shar'a)和教义学(Kalam)之后的伊斯兰教的又一重要学科。伊斯兰著名思想家安萨里曾把伊斯兰学科划分为四大门类:教义学、内学、哲学和苏非学[3](55);有的学者分为教义、教法、苏非和哲学四种[4](7),有的学者则从纯粹宗教学角度将其分为两大类:苏非学和教法学[5](43)。从中我们发现苏非派在伊斯兰学科和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产生和所发生的事件是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方面。著名历史学家吉布说:“如果对苏非派的运动及其因果关系不能耐心地并以学者的公正态度进行研究,便不能写出一部令人满意的伊斯兰教历史。”[6](331)
其次,苏非派在伊斯兰哲学史上的地位。虽然宗教也讲世界整体问题,讲最大最高的普遍性,但它与哲学始终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哲学诉诸的是人类的理性。同时宗教与哲学又紧密联系,在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宗教意识就始终渗透着哲学问题。对伊斯兰哲学而言,更为如此。伊斯兰哲学的主体离不开苏非派思想,其诸多不解问题都是靠着苏非派思想来进行解释和回答的。近代以来,苏非派在诸如北非、印巴次大陆、中亚等伊斯兰世界非常盛行,其哲学思想对当地穆斯林影响很大。不仅如此,伊斯兰哲学对中世纪欧洲产生过重要影响,引起西方学术界诸如马西尼翁和尼克尔森等著名“东方学”学者的足够重视。时至今日它仍是整个人类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说伊斯兰哲学史倒不如说是苏非派哲学史更为确切。
最后,苏非派对我国西北地区门宦的影响。我国西北是苏非派最早传入的地区,苏非教团较集中、信众较多,历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在当代伊斯兰世界还是我国穆斯林社会,苏非教团与过去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我国西北教派门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和挑战性的新情况、新问题,给社会和谐稳定、地区宗教和顺带来了诸多复杂因素。因此,开展和加强苏非派及其现实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8-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