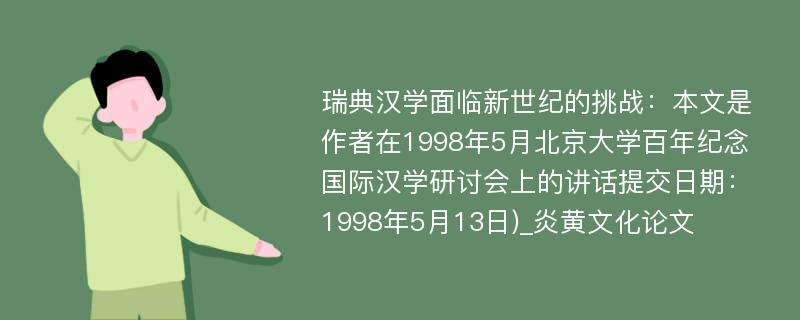
面向新世纪挑战的瑞典汉学——(注:本文系作者在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举行的“汉学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来稿日期1998年5月13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瑞典论文,北京大学论文,新世纪论文,来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瑞典的汉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十七世纪,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就出现了最早的以中国为题目的博士论文。此后,独特的中国文明就让瑞典人感到敬畏,并在瑞典社会日俱影响。本世纪初,一些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 )、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和艺术史家喜仁龙(Osvald Sirén )开始运用现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课题。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也许应归功于这种“文化杂交”(Cultural croSS-fertilization)。
高本汉创造性地把比较历史语音学的方法应用到汉语研究中,并借助这种研究成果去解读古汉语文献,从而揭示了历史语音学对训诂学的重要意义。对高本汉来说,这乃是汉学的精髓,而学习现代汉语,则仅仅是为了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以及阅读汉语学术文章。所以现代汉语和现代中国文化都不成为研究对象。
高本汉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在哥德堡大学担任“东亚语言学和文化教授”,其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还担任了五年大学校长。一九三九年他移居斯德哥尔摩担任东亚博物馆馆长,同时兼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教学,直至一九六五年退休。当时斯德哥尔摩大学还没有独立的汉学系。
一九六五年,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Goran Malmqvist )被任命为“汉学,特别是现代汉语教授”。马悦然在历史语音学和训诂学方面受过高本汉严格系统的训练。他不仅花了大量精力对四川某方言的语音结构进行了科学的描述和研究,而且对今文经学的三个代表性文献《公羊传》、《谷梁传》和据称是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作了卓有成效的细致分析。不过,我以为马悦然的主要贡献更在于他作为一位学者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负责人努力突破原先的汉学研究局限,将其重点逐渐从古典转入到现代,特别是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译介。同时,作为一位研究生导师,他也鼓励学生从事与现代中国文化相关的研究。
至于汉学的定义,马悦然经常说,汉学是以汉语语言材料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工作。这表明他的兴趣是在传统汉学之外拓展空间,而不是划定它的界限。
马悦然教授退休后,这一教席改名为“中国语言和文化教授”。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尽可能地利用高本汉和马悦然教授留下的传统,在面临新世纪对人类智慧提出的挑战时,把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如文化的全球化倾向、以及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划界的思想基础进行重新思考等等。对我来说,坚持高本汉和马悦然的传统并不等于继续在他们所开垦的园地里耕耘,而是为今天和明天找到新的研究课题。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本科水平的教育被称为“汉语”,而研究生课程则被确定为“汉学”,对教授职位重新“正名”对制定我们将来工作的战略方针也至关重要。我愿借此机会提几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与诸位商讨。
汉语
随着经济地位日益提高,中国正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汉语正在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地位。它不仅是研究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文明的不可缺少的工具,而且是不同文化间相互联系以及商务和科技交流的媒介。当然,英语极有可能仍将是服务于这些目的的最主要语言。但在亚洲,汉语似乎已在国家间交流方面取得了第二重要语言的地位。种种迹象表明,汉语将在东西方交流中起更加重要的作用。
汉语地位的提高对我们这些汉语教师和中国研究学者是严峻的挑战。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汉语教学质量。我们的目的不应再仅仅局限于让学生阅读汉语和掌握简单对话的能力,而是要大力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使其达到我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并进而学会用汉语写作。
什么是汉学?
众所周知,“汉学”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其外延宽窄不一。但所有我接触到的定义都打破了大学学科的界限;将语言、历史和文学包括在内。因此,人们也许会问,汉学是否真的是一门独立学科,是否有其自身的概念体系和理论?
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释是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本质上与欧洲不同,因此研究诸如中国历史或文学必须采用与欧洲历史和文学研究完全不同的概念和理论。由此看来,把汉学视为一门学科是很自然的事,尽管人们还可以从中分出一些亚学科。
另一种解释则认定人类的经验尽管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式,但从根本上说仍有着潜在的一致性。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的历史和文学,人们都能够并且应该用一种普遍的关于历史或文学的理论去分析和解释,至少可以使用同样的基本范畴。由此看来,汉学作为一门学科与历史、文学、人类学等等并存相当奇怪。
只有愚蠢而又自以为是的人才会宣称自己拥有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与其说是为了确定真理,不如说是我们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价值选择:我们应该强调相异点还是强调相同点?这一选择当然应以事实的阐释为基础,但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属于价值层面的选择。在这个层面上,我准备捍卫相同优先于相异的观点。具体说来,我看没有什么理由要把中国人的经验当作与欧洲人的经验根本不同的范畴来阐释。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基于这一考虑:强调相异点似乎很容易导致在汉学领域周围筑起高高的围墙,这种围墙又起着维护中国文化周围的围墙的作用。说句不太客气的话,我在一些汉学家身上已发现了这一倾向。这些汉学家批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不够“中国”,理由是他们使用了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从而与自身的传统格格不入。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努力拆毁隔开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围墙和屏障。应该避免把汉学定义为一个排它性的、与其它学科不同的、有着本质上独立的概念体系的学科。
但是,我的这一选择还基于另一重考虑:在历史上汉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突破似乎都是通过把西方科学方法运用于中国材料的研究而取得的。这可视为文化杂交的特例。一种文化的现象由此可以导致无限的阐释,而不同的概念可以使过去未知的方面显现出来。毋须赘言,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在西方文化的研究中使用非西方的概念。
汉学系应该解散吗?
如果人们不认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文化,不认为这种文化只能从其自身寻求解释,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让所有的汉学家集中在一个系里已不再合乎情理?是否应该让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转到历史系,而让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转到文学系去?我的回答是:也许,但不一定。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真正有趣和富有成果的研究,正日益超越传统的学科界限。我不敢肯定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学科划分已逐渐变得过时,但可以肯定的是,为那些并非自然地专属某一学科的研究创造一定的空间是极其重要的。在此,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研究有机会成为迎接和吸引跨学科研究的一块园地。
一方面,我愿意看到年轻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汉语”之外,取得另一学科的很好的理论训练;实际上,目前在斯德哥尔摩,学习另一门学科一年半以上是成为汉学博士生的前提条件。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们系能吸纳独创的、非常规的研究项目,从而使我们系比代表着传统的一些科系更具有开放性。
“临界体”和对某些课题的专注
马悦然通过把汉学定义为以汉语材料为基础的研究,扩大了我们的研究领域,从而带来一种使我们受益无穷的活力。但是,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大也导致了另一种情况,即我们的研究变得太零散:学者和学生们各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因此无法就各自的研究课题进行有意义的相互讨论。如果听任这种倾向继续下去,活力就会退化为惰性。因此,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有意识地对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加以组织,以便创造一个“临界体”(critical mass),这种“临界体”是形成有活力的研究环境的前提条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在保持古典方面的研究力量的同时,把现代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领域。
前面的路
作为结语,我愿在此介绍我们迎接新世纪时的四项工作重点:
一、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们将继续努力提高他们的汉语语言能力,特别加强汉语听说和写作能力的教学。
二、进一步努力建设和保持“临界体”,这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至关重要。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继续把学术研究集中在一定课题上。
三、我们的研究固然要以产生新知识为目的,但着重点应落实在文化间的相互渗透上。我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作出我们自己的阐释。这种阐释既是针对学者群,也是针对一般大众。
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与同行以及其它国家的研究机构的密切接触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扩大我们与中国同行的合作,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同行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