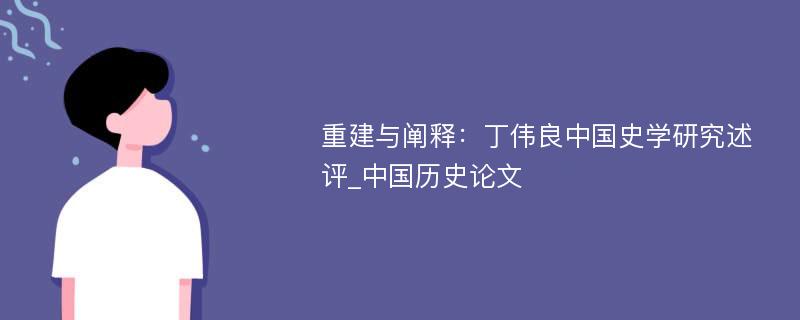
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历史论文,丁韪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102-08
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号德三,别号冠西,新教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早年在宁波、上海以及北京传播基督教“天道”,后在北京以及武昌等地相继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以及湖北仕学院的“讲友”,曾创办《中西闻见录》、《尚贤堂(新学)月报》,致力于传播西方的世俗科学(“实学”、“新学”)。丁韪良倾心汉学,早年加入美国东方学会(1858年)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1864年),并于1885年5月发起成立北京东方学会(Peking Oriental Society),任首届会长。在汉学研究中,丁韪良尤重中国历史,曾在北京东方学会的成立大会上呼吁外籍会员加强研究中国历史,撰有《古代中国北方的夷狄》(1884年)、①《中国历史研究论》(1886年)、②《从长城看中国历史(一份历史提纲)》(1894年?)③专论三篇,以及《中国六十年记》(A Cycle of Cathay,1896年,半回忆录性质)、《觉醒中的中国》(The Awakening of China,1907年)专著两本。
这些文章和著作既涉及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也涉及对中国历史的运动规律、进化分期特征及其近现代命运的探索,总体上可以看作是丁韪良在19世纪西方历史哲学指导下的中国大历史构建。由此,丁韪良为中国通史研究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可资与各国历史比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可以说,丁韪良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奠基者,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代表了19世纪后期中西研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和成就。然而,限于语言以及传教士身份等多种原因,丁韪良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长期为世人所忽略,未曾得到包括外国学者在内的学术界的关注和公正评价。④本文拟据上述文献,对丁韪良的中国大历史观做一个详细的述评,以期填补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空白。
一、中西史观的比较和选择
构建中国大历史观,丁韪良首先要面临如何处理有关中国历史研究的史学理论遗产——包括明末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中国史观、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以黑格尔、兰克为代表的19世纪上半期西方主流学界否定中国有历史与史学的主观臆断[1]等——以及如何选择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视角的问题。明末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消弭中国史书对于中国上古历史的描述与《圣经》年代学之间的不一致,充满臆想和牵强附会,与19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相距甚远,丁韪良因而并未予以重视。作为一个西方人,19世纪西方的主流历史哲学特别是有神论的进化论史观理所当然地成为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但他对于以黑格尔、兰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否认中国有历史并将中国的传统史学归为“原始的史学”的做法,则并不完全同意。他认为,中国是有历史的,这是他能够构建中国大历史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缺乏西方历史哲学的积淀,不能适用于构建中国大历史。
对中国传统的史学方法的批判成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丁韪良认为,在西方是美的观念主导历史作品的创作,而在中国,“历史的概念是一种简单的记录,而非一项艺术的工作”,[2](P2)故而中国完备的历史纪录体系虽成就了卷帙浩繁的历史文学,但历史材料并不能得以消化,“死的过去是被埋葬而不是被解释了”。若以培根为代表的将历史定义为“以例子来教的哲学”的西方眼光和价值标准来看,中国有年鉴(chronicles),没有历史。他说:
他们的年鉴精雕细刻,富于对人物和事件的尖刻的批评,但是他们的全部文学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东西。没有重新架构宇宙并将其原理用于解释人类进步规律的黑格尔;没有追踪旧文明衰落踪迹的吉本(Gibbon)或孟德斯鸠;没有描述新文明兴起的基佐(F.P.Guillaume Guizot,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1812年任巴黎大学近代史教授,1828年著有《欧洲文明史》)。他们甚至没有能由果推因、描绘一个时代全景的修息底德和塔西图。[2](P11-12)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丁韪良认为并不是中国人本性上缺少哲学能力,而应该归咎于中国的历史学之父孔子所确立的《春秋》模式。孔子著名的《春秋》连编年史(annals)也算不上,只是将大大小小的事件像念珠一样以日历串起来的一部日记。这种方法,虽令文体极其简洁,但却很难让人觉察到事件之间的联系。中国史家按照这种模式辛勤搜集资料,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点:
中国的年鉴编撰者们热衷于将所有发生的事件按时间顺序分类,不能觉察到席卷所有国家以及长期持续的许多大的运动的趋势。他的日常琐事的记录如果说是历史,那也只能就每日对星星的记录就是天文学这样的意义上来讲。成千上万的勤劳的观察者所记录下的观察显然是做无用功,而开普勒之眼,掠过众多的事实,就能归纳出行星轨道的椭圆。难道我们不希望能产生一些精神大师,来揭示这些未消化的事实中所蕴含的统治律吗?[2](P13)
基于对中国传统史观的批判,丁韪良1886年首次提出了要用西方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来重新架构和解释中国历史。具体地讲,就是要以19世纪晚期的主流历史哲学(进化论、实证主义及神学目的论)来质变(transubstantiate)中国的历史资料,“按照我们对历史一词的理解,在成为历史之前需要一种与它们在其本地作者手中所受到的解释不同的解释”。[2](P13)但丁韪良所要解释的并非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而是要揭示中国数千年历史运动背后的内在规律及发展趋向,从而成为发现历史统治律的精神大师。简单地说,丁韪良感兴趣的是寻找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背后的“主叙述”(master narrative)或曰“元叙述”(meta-narrative),从而建构线性进化的中国“大历史”(macro-history)。
二、中国前近代历史的动力:三个运动规律
在确立以19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作为研究和重建中国大历史的方法论后,丁韪良开始寻找中国大历史运动背后的动力学原理。1886年,他提出了中国前近代历史运动的三个运动规律(或命题),即“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鞑靼对中国的征服”及“帝国内部向心力与离心力间的斗争”。他认为是这三个运动规律(或命题)的合力作用造就了中国历史的过去和现在,而且“其中的每一个都之于理解中国现在的状况均是必不可少的,犹如开普勒的三个定律之于太阳系的解释一样”。[2](P14)
丁韪良所谓的“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意思是现在的中国人并非原中国的土著,而是一个源于中亚的有着较高文明的外来种族,最早数量很少,疆域也相对有限,后来沿着黄河河道而到中原,一代接一代在冲突中逐渐吸收和同化周边的原土著部落。与其邻居们相比,原始中国人主要在文字知识上突出,拥有较高级的文明,这一早期的文化给中国人比周边阻碍其进步的蛮族以巨大的优势。[2](P68)这些蛮族有“东夷”、“北狄”、“西戎(羌)”、“南蛮”等四个集体名称。被原始中国人征服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南部和东部的非原始中国人部落,而北方、西方的野蛮部落“狄”和“羌”则从未永久屈服(作为部落集体,单个部落则有被完全同化和同一的——作者)。丁韪良认为,中国人与原土著的冲突最早可追溯到《书经》所记的舜帝征“三苗”,这种冲突到近代仍未结束,近的例子是清朝征服贵州“苗子”及台湾。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过程也符合世界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三重过程规律,即由彼此孤立隔绝、各自在语言上甚至都不能相互理解的差异阶段,逐渐过渡到同化(assimilation)阶段乃至同一化(unification)阶段,亦即周边部落消融在中国人中间的过程。但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原始中国人到处都因与土著居民的融合而发生变化,并产生了地域性特征,以至于原始中国人的类型,现在已不再可以分辨出来了。遗憾的是,丁韪良对“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的运动规律并未有专文论述,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逻辑安排和上下文中推测,他所谓的“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含有三层意思:一是从过程角度看是中国农耕文明在地理上的扩张、制度方面的推广、文化上的同化及人种方面的融合过程;二是从规律角度看是优越的中国文明总能在民族交往过程中展示其强大的影响、同化和吸纳能力;三是从被征服对象看主要是中国南部和东部的非原始中国人部落,它们绝大部分被同化或同一。
第二个历史运动“鞑靼对中国的征服”,与第一个运动源起时间相同,以后又与第一个运动并肩而行,并一直延续至今。丁韪良自言,他所谓的鞑靼的征服不是中国人意义上的满洲入关统治,而是包括满洲、匈奴、回鹘、突厥以及他们的叫不同名字的祖先等“几千年来中国北方不管叫何种名字的蛮夷夺占对中国这个由已开化的居民以其勤劳而使其致富的国家的恒常企图”。[2](P16)这些游牧部落,分布在长城以北未被犁耕的辽阔平原上,在长城的南面是盛产农产品的田地果园,中间的界线是长城。[2](P59-60)在丁韪良看来,长城两边的敌对状态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从海边一直延伸到甘肃沙漠的长城是这一尚未熄灭的斗争的纪念碑,这场斗争从其发端起本质上就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只是这里或那里有间歇性的休战。”这场战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1年的夷狄入侵迫使周平王迁都洛阳。后来,整个中国有两次屈从于鞑靼人的统治(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洲入侵建立的清朝),[2](P61)此外,尚有鞑靼“部分征服”中国的三个时期:一是907-1234年间,北方大部分地区相继为契丹、女真鞑靼所统治;二是386-532年间,广大地区屈服于拓拔鞑靼部落的北魏统治;三是公元前202至公元2世纪的汉朝,汉帝国虽未全被外人所征服,但一直处于由一个叫做“匈奴”的集合名字的强有力的部落群所带来的恐惧之中。有时,处于弱势的汉朝皇帝便采取和亲联姻手段。李广、李陵、司马迁、苏武的遭遇即是汉与匈奴间势力彼此消长的反映。[2](P63-65)丁韪良认为,鞑靼对中国的征服完全可以与高卢人和汪达尔人对罗马的连续劫掠以及北方蛮族对意大利的征服相提并论,因为同样都显示了一种民族大潮中的规律,“也即北方的饥饿的游牧部落在各个时代都表现出蚕食更为阳光所青睐的富饶地区(指南方)的趋向”。
与南部及东部的土著居民相比,丁韪良认为,北方的鞑靼民族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更深远、也更复杂。他认为,周之代商以及秦朝的兴起都与北方和西方部落入侵有关,周与秦均是在与同样的敌人的冲突中壮大的。当然,“在所有的时代,鞑靼入侵者都已经屈服于一种更高级文明的影响”,[2](P17)“在任何时代,他们都用从其他更文明的种族那里找到的文明替换了他们的野蛮”。[2](P83)除了在政治上造成影响外,鞑靼人在人种和语言上也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彼此也经历了由差异而至同化而至外表和举止的完全同一化的过程,“早期中国北方的野蛮人呈现出许多种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流逝,又趋于让位于举止的同一甚至生理外表的同一”。[2](P81)原始中国人在北部地带遇到了与蒙古部落亲缘的部落,并逐渐吸收了他们,北方中国人高大健壮的体格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结合,与萨克森人让英语语言日耳曼化一样,[2](P82-83)中国北方的语言也深深地为鞑靼的影响所修正。
丁韪良所说的“帝国内部向心力与离心力间的斗争”,就是封建自治力量与中央化力量之间的较量,亦即今日所谓中央集权制与分封制之间的较量。他将这一运动也追溯到周代的封建制度,并将春秋战国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解释为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由此视角出发,他特别批评中国的历史学家没有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理解了‘始皇帝’这一尊贵称号的意义,他(赢政)以这一称号宣布自己是新的‘独裁统治’秩序的‘第一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觉察到他焚毁儒家经典的动机是要从中国的记忆中抹去封建制度;觉察到他割去儒士们的喉管是要确保这些书及其政治宗旨将不再出现。”[2](P18-19)这种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斗争,并未因为秦朝创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而消失。在此后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离心力和向心力之间的斗争一直是中华帝国政治的主旋律,其结果是帝国兴衰更替、国家的整合、分裂和再整合。
按照丁韪良的设想,上述三个运动规律互相作用、共同影响和塑造了前近代中国的动态历史。“中国人对中国的征服”规律揭示的是中国人在长城以南的兼并和扩张历史,“鞑靼对中国的征服”规律揭示的是中国人在长城附近与北方游牧民族征战、交融的历史,“帝国内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斗争”规律揭示的是中国内部权力的整合与分裂历史。但从阐述的重点看,丁韪良显然非常重视从中国人与其他民族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历史的演进和中国现实的形成。丁韪良不仅敏锐地发现了中国人在长城内外与其他民族的际遇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他将“鞑靼对中国的征服”单列为中国大历史运动规律之一的原因,而且也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的冲突和融合过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三、线性大历史的重构:中国历史的进化与分期
在揭示中国历史运动规律的基础上,丁韪良还得出了以变化(进化)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特征。他认为中国历史一直是发展变化着的,并非原地踏步,在这一点上他显然超越了当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的看法。他说:
我们震惊于这一事实,即中国社会远未呈现出不变的一致性(changeless uniformity)的方面。它的变化也不是像我们的海边观察者所登记的东西那样单调。……中国的人民经历的变化是无数的,他们并不总是踏上恶性循环。历史表明他们在一个人民的伟大性的所有方面已经取得了如果说不是常规那也是一个总的进步;因而在他们纪年的76个甲子之时,比起此前他们的国家存在的四十个世纪中的任一时期,他们的疆域更加扩大了,他们的人口更多了,他们的智慧更高了。[2](P22)⑤
丁韪良并尝试以分期的方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化)进行具体描述。他将中国历史粗略分为四个时期,即周代以前的神话传说时期(历史黎明期)、周代封建制⑥时期、秦代至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时期和1840年以后的近代化时期。但从他的阐述重点看,丁韪良更加注重前近代封建制与中央集权制的分野以及前近代与近(当)代的分野。
(一)秦朝的革命:由封建制走向集权制的前近代
从其关于中国前近代史三个动力论之一的“离心力”与“向心力”论出发,丁韪良认为建立万里长城的秦朝是观察中国历史分期变化的最佳视角:
研究埃及历史的人们应该站在金字塔上,而研究中国历史,则没有比长城顶峰这一更为有利的观察点。长城建立的时间处于早期模糊的传统与不安的、动乱的现在之间,控制着整个移动的全景。长城之于我们的重要性不在其大小而在其时代。[2](P26)
这里,丁韪良特别注意到了中国社会以此为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此前中国是封建社会,此后一直到清朝,中国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丁韪良站在世界史的角度首先提出了先秦社会封建制与西方的封建领主(feudalism)制度的相似。这表现在先秦社会的中国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封建领主制度在组织形式以及权力的运作上是一致的,甚至在爵位五等制上也惊人的相似,但这一制度导致君主控制力削弱,逐步成为影子权力。[2](P27-28)
以秦为分界线,丁韪良构建了一部中国前近代的历史发展纲要。他以尧舜禹禅让的故事为例,指出夏朝以前的中国社会的特征是“简单”:“原始社会的简单是公德与私德之母。”而大禹传位于子则中断了大公无私的传统。夏朝的特征则是“征服与同化”,由夏朝开始的这一工作延续到现在。持续千年之久的周朝则产生了封建制的形式,且文学也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出现了文王、周公这样有文化的政治家,也出现了孔子、孟子这样的哲学家。孔子、孟子灌输德治,反对当时政治活动中最显著的离心倾向,其唯一对付乱世的药方就是回到原始的清纯状态,而这正是长城建立者秦始皇所热衷要废除的,由此他敌视儒家学派和儒生。秦始皇没有走老路,在吕不韦和李斯这两位政治家的帮助下制定了革命性的计划。他改称“始皇”,这本身就意味着政策的改变,不亚于废除这一自古以来就确立下来的封建制度。[2](P41)后又在李斯建议下设立郡县,并以“焚书坑儒”来对付儒生的反抗。丁韪良认为,秦始皇废封建、另立中央集权制度进行政治改革的残忍之举,堪与西方近代历史上的法国大革命、德国以及意大利的统一等重大历史事件相提并论。[2](P43)丁韪良为秦始皇修建长城作了肯定和辩解或曰曲解,他说:“尽管事实上以后的时代看到了许多鞑靼王朝统治中国,但(修建)长城可以说实现了其目的。修建长城的目的不是阻止边界游牧民族的征服,而是防止他们短暂的入侵和劫掠。”[2](P45)⑦
在汉代,儒家虽然再度复兴,但封建制度却再也未能恢复。相反,秦始皇创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却一直流传至今。丁韪良认为这一史实足以说明秦始皇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他将修建长城、称始皇帝以及统一中国并令中国以“秦”(China)闻名于世称为秦始皇的三大功绩或曰“三个纪念碑”,将秦始皇的历史地位抬到了以往中国人闻所未闻的高度,力图洗刷和开脱秦始皇因“焚书坑儒”所负的千载骂名:
而君主则发现自己占有独裁的权力,更不愿意与它分开。中央集权制度在今日还存在,三个纪念碑仍在提醒所有的后代,邯郸夫人之子秦始皇是其始作俑者。这三个纪念碑是:他建立的长城;他第一个用皇帝的称号;中国(China)这个名字显然出自以兼并其他封建国家而闻名的“秦”(Chin)室。[2](P47-48)
总之,丁韪良认为,秦始皇“无疑残暴无耻,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位具有远见、独创性以及行动果敢的政治家”。[2](P48)⑧丁韪良对秦始皇予以高度评价并以秦为界限将中国前近代历史分期的思想,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学术界对秦始皇的看法以及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所持的观点。丁韪良还认为与秦代相比,其他朝代虽不如秦朝那样有革命性的变化,但都各有其特征并相应增加了中国的历史遗产。他对秦以后中国各个朝代的不同特征以及历史遗产进行了概括和勾勒。他认为,汉朝的特点是在智力活动上的丰碑特别多,有儒家文学的复兴和佛教的传入。儒家文学的复兴表现为伪经的盛行,以及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为代表的史学的复兴。汉代纸的发明本身就是文学复兴的结果。儒家的复兴并不压制其他学说和教义,这一时期佛教开始引入中国,并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2](P52-56)唐代的特征是诗歌的高度完善,以李白、杜甫为代表。宋代则以思辨哲学、注经和科举考试重组并最终定型。[2](P57)明朝智力上的特征表现为编撰以《永乐大典》等为代表的百科全书以及法典。而满清这个朝代在历史地位上也不亚于前代。清朝的人口创中国历史之最,八倍于唐朝。清朝在编撰百科全书以及法典方面比明朝更有进步,文学批评也更为兴旺,而且明末以来引入的西方科学在清朝得以更积极地培育和推广。丁韪良深信,与西方科学一起引入的基督教也必将对中国人的精神留下如佛教同等深度的影响。[2](P58)
(二)近(当)代的觉醒:由被动开放走向主动改革
丁韪良虽然为中国前近代史提出了三大运动规律命题,并特别以其中的一个规律简单勾勒了中国前近代历史分期发展纲要,但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归宿或落脚点却是在近(当)代。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1907年的《觉醒中的中国》一书中。在方法论上,他依据的仍然是西方的进化论史观,他在《觉醒中的中国》一书的开篇这样写道:
中国人并没有在各个时代保持一般所认为的铁铸般的同一性。他们虽然崇古并在精神倾向上保守,但他们也不曾如一般想象的那样满足于传承最早期的一小部分结晶的观念而不增加或修正。他们文明的胚胎就像其他任何值得保存的文明中的一样,并非放在匣子中的宝石,而是要种植和改良的种子。[3](P15)
他们文明中不变的因素很少,而变数则很多……在回顾他们的遥远的过去一直都可以看到大胆的革新以及激烈的革命,这为他们预计到同样的未来做好了准备。有了这些先例以及这样一种智力活动的性质,他们与西方文明接触和碰撞不受到深深影响则近乎于不可能。[3](P16)
同研究中国前近代史一样,在建构中国近(当)代史体系上,他仍旧将中国近(当)代史放在中国与域外(西方)文明的关系中来考察。他说:“中国与欧洲的文明,虽然彼此广泛分隔,但每一个文明都受到了另一文明的影响,这虽然难以理解,但确那样真实。”[2](P21)但这次他所赖以分析的动力却变了,西方的冲击已成为中国近(当)代历史进步和发展的主动力。他在《觉醒中的中国》一书的末卷以“转变中的中国”⑨为总标题,将整个中国近(当)代历史描述为在上帝的西方的冲击下从被动开放走向主动改革,走向“觉醒”和自觉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基督教)的过程。
在具体论述上,丁韪良首先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进程定义为一部五幕剧的“中国的开放”。这一“中国开放”的五幕戏剧,是“上帝在历史”中的体现。所谓五幕,第一幕为鸦片战争,第二幕为“亚罗号”战争,第三幕为中法战争,第四幕为中日甲午战争,第五幕为拳民战争。丁韪良将“中国的开放”看成是“远东保守主义与西方进步精神碰撞的结果”,并认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负有正本清源的历史责任。[3](P149-150)从进步对落后和保守出发,他对这些战争的叙述无疑都忽略了这些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他错误地认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原因都是源于中国的傲慢无知,而与鸦片关系并不大。如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他说:“英国与罪恶的鸦片习惯的引进无关,但却利用了这一点。”[3](P152)在第二幕大剧中,他认为“亚罗号”如同鸦片一样只是机缘,而并非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傲慢无知。[31(P162)他甚至对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公使额尔金未要求开放天津提出批评,指责“他的错误导致了战争的复发并延续了两年多”。[3](P166)他将第三幕、第四幕看成是由于中国不明智地保护其附庸国越南、朝鲜所致,而第四幕中光绪帝的改革所引起的反动则导致了第五幕拳民战争。⑩
而对于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中国当代历史,丁韪良则描述为“中国的改革”。他列举了慈禧统治下清末新政的成就,并相信在西方正确的科学和宗教的激励下,不用多少代,中国就可以挺立于基督教世界之林。[3](P279-280)中国的基督化是他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进程以及终点,他深信中国将来必定会出现在基督教兄弟国家的行列,[3](P111)并且会反过来对西方文明产生更大的影响。[2](P21)
总之,在丁韪良看来,中国的近(当)代史是一部由被动开放走向主动的改革、走向基督化的西方文明的觉醒史。作为传教士,他非常强调上帝的意志。他多次言及上帝在中国近(当)代史中的作用。他在评价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二幕剧时说:“一个观众如果没有觉察到上帝之手在掌管国家间的冲突以及政治家的大错,那么很悲哀地他必定是缺少精神上的眼光。”[3](P169)在第五幕剧中他还将义和团不能攻下外国使馆以及后来使馆的解围归结于上帝。[3](P177)1905年12月他在他的英文半自传《中国六十年记》序言中也曾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即上帝在控制着中国历史的进程。[4](P4)这就是说,丁韪良限于自己传教士的立场,与黑格尔、兰克一样,(11)其关于中国近(当)代史的研究也逃离不了神学目的论的指向和归宿。
四、贡献与缺陷
总体上看,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以《圣经》剪裁中国历史,突破了十七八世纪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带有明显的19世纪后半期西方主流历史哲学的印记。通过将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用于分析中国历史进程的变化规律、分期特征及归宿,丁韪良为中国通史研究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作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奠基者,丁韪良在中国史学史上应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应因为其传教士身份而受到忽略。
首先,丁韪良继承了西方的历史哲学,提出中国古代历史学的弊病在于缺乏历史哲学这一颇有见地的观点。他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出发,试图从堆积如山的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发现中国在历史上发生的变化并从变化中找出其中的进化规律,显然代表了中国历史学近代化的努力方向,是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本土“新史学”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声。梁启超对中国旧史学的“四弊病”的批评、对历史哲学(其所谓“公理公例”)的追求以及以进化论取代旧史家的历史循环论的主张与丁韪良不谋而合,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无一不是在试图对中国历史进行规律的总结,只不过方向和具体结论不同而已。
其次,在对中国历史的具体建构上,丁韪良显然又较西方同时代历史学家更进了一步,特别是提出了进化论的线性分期大历史模式。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停滞的中国历史观截然不同,他强调中国历史在不断变化,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其中国前近代史纲要,他是真正第一个提出中国前近代史发展框架的学者。他高度赞扬秦始皇并提出以秦为界线将中国前近代历史进行分期的观点、中国古代历史上边地游牧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冲突与融合的观点以及中国人是“原始中国人”不断与土著融合的观点,也是很有见地的。梁启超建立在中国与域外文化关系上的中国史分期进化观点可能受到了他的影响。(12)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秦始皇的高度赞扬以及以秦朝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水岭的看法与丁韪良的观点如果说不是巧合,则也证明丁韪良颇有过人的洞见力。
再次,在中国近(当)代史的近代化构建上,丁韪良也是中西第一发端人,功不可没。他看到了中国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因受到了西方外来因素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具体分阶段描述了这一进程,这也是很有见地的。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无疑影响了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原同文馆英文教习、后任中国海关职员的马士(H.B.Morse)。马士在其名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实际上完全吸收了丁韪良的观点。他也可能影响了治中国近代史最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蒋廷黻,虽然学术界一般公认蒋氏系受美国“新史学”的影响(13)以及马士的影响,然蒋氏的名作《中国近代史》以近代化为主题的分析框架与丁韪良却近乎一致。丁韪良之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显然也部分影响了包括费正清(John Fairbank)在内的现代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系马士亲传弟子,费氏的“冲击—反应”的中国近代化模式当不过是丁韪良观点的精致版,只不过其中已经没有上帝了。(14)由丁韪良—马士—蒋廷黻—费正清这条路径,我们清晰看到了丁韪良对近代史研究中近代化一派的影响。
当然我们在看到丁韪良中国史研究的意义时,也不应该忘记丁韪良的中国史研究中的不足之处特别是一些负面的地方。如: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或曰纲要的勾勒过于粗线条和简单化,致使一些重要观点论据单薄;对周代以前中国文明史的忽视,使他看不到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发祥地的事实;对秦朝以后两千年文明的单一性概括阻碍了他看到唐宋以后中国文明的重大转变;将西方封建社会直接与中国先秦社会挂钩过于简单,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完全归于西方的冲击所引起,忽略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崇拜和对西方中心论的强烈认同,使他看不到西方列强侵华的非正义性,从而沦为西方列强的辩护士;所坚持的基督教神学目的论,使他错误地认为中国历史进程必然以基督化为归宿;等等。
注释:
①"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Ancient China",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JAOS),XI,No.1,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at Boston,May 7th,1884,cc-ccii; JAOS,XI(1885),XI,No.1,Pp362-374。重登于The Chinese Recorder,XVII(April,1886),Pp125-137。该文后以“Tartar Tribes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的鞑靼诸部落》)为题收入《翰林集》第二编(第59-83页),以“The Tartars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的鞑靼人》)为题收入《中国的学问》(The Lore of Cathay,第409-426页)。
②"Discours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研究论》),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Vo1.I,No.3(1886),Pp121-138。后改名“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收入《翰林集》第二编第1-25页以及《中国的学问》第387-408页。
③"History of China Viewed from the Great Wall",Hanlin Papers,Second Series,Pp26-58。该文具体宣读日期不详,当在《翰林集》第二编出版的1894年前。
④如西方研究丁韪良的学者Ralph Covell在其专著"W.A.P.Martin: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1978)中对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几乎只字未提。
⑤当然这种进步在丁韪良看来是局限在一个精心设定的社会组织的界线之内,也即在国家为君主政体、科举考试的选官制度,在家庭为孝顺父母和祖先崇拜。丁韪良最早关于中国历史变化(进化)的观点见他1868年10月在美国东方学会宣读的文章“The Renaissance in China”(《中国的文艺复兴》),Hanlin Papers,First Series,Shanghai:Kelly & Walsh,1880,第297-332页。1901年丁韪良在《觉醒中的中国》一书的导语中又再次强调了中国历史的变化(进化),见The Awakening of China,New York:Doubleday,Page and Company,1907,第15页。
⑥此处“封建”仅仅是在中国古代“封藩建制”的意义上使用,不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含义。
⑦对秦始皇信仰道教、封禅和求仙等活动,丁韪良则作了否定的评论,他说,秦始皇坑儒信道,并派遣徐福求长生不老药,“他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迷信的”。
⑧丁韪良后来在中文作品中也表达了对秦始皇的肯定,他说:“即秦政暴虐,并吞六国,废弃封建,改为郡县,论者多咎其败废先生之法度,而不知延至今日,中国无列辟争雄之患者,伊与有力焉。”《邦交推原论》,《新学月报》(北大图书馆特藏),第三本,第2页。
⑨丁韪良在中文中表述为“(《觉醒中的中国》)末卷述中国近日之除旧维新也”,见丁韪良《花甲忆记》,第4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10年。
⑩丁韪良将第五幕称为“拳民战争”(“Box War”)而非“拳民起义”(“Boxer Uprising”),这特别得到了李佳白的欣赏,李佳白称丁韪良用这个词很有勇气。见Gilbert Rrid:" Review of The Awakening of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XXXVIII,1907年11月号,第619页。
(11)黑格尔、兰克都相信人类历史的终极意义与上帝相联系,由于人类始祖原罪的原因,人类历史整个是一个赎罪的过程,其兴衰并非随意,而是与上帝互动的一种延续,目的是得到上帝的宽恕,成为其选民而重新回到天国。参见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12)梁启超在史学观上是否直接受过丁韪良的影响目前尚不能证明。但由梁启超与丁韪良的同道李佳白往来密切并曾经在丁韪良主持的《尚贤堂(新学)月报》上发表过文章,也很难说他不曾直接受到丁韪良观点的启发。梁启超关于中国历史“上世”、“中世”、“近世”的三分法分期进化史观与丁韪良的关于中国历史规律、分期论述包括表述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梁启超言:“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居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复次第兼并,力征无已时。……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中国史叙论》(1901年),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53-454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梁启超的三分法暗含中国与域外文化关系的视角,也与丁韪良不谋而合。
(13)参见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
(14)学术界一般认为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系受到马士和蒋廷黻的影响,但亦不能排除费正清阅读过丁韪良的著作。一个例证是在丁韪良死后的1925年,丁韪良的著作《中国的学问》和《中国六十年记》在对在华外人的调查中列“最有用的论述中国的书籍”前十名。参见L.Newton Hayes:" The Most Helpful Books o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Vol.56(May,1925),第417页。费正清30年代来华,离此时并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