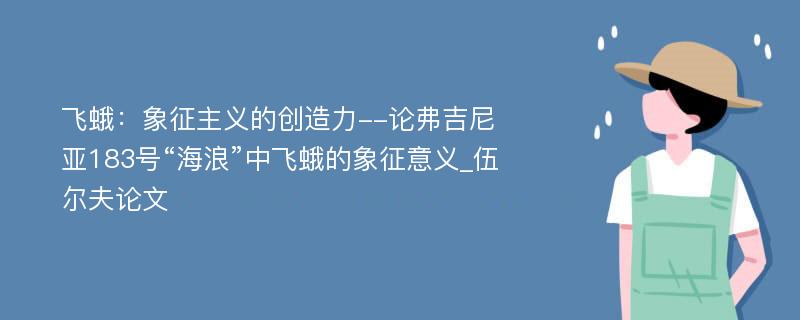
飞蛾: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论弗吉尼亚#183;伍尔夫的《海浪》中飞蛾的象征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飞蛾论文,弗吉尼亚论文,海浪论文,创造性论文,象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文学上,“象征”作为一个名词。“仅指用来表示某一事物或事件的词或短语”[1] ,其特殊之处在于“这一事物或事件本身又代表某一事物,或者超越其自身的参照范围 ”[1],同时该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1]。这里象征 与隐喻有着细微的差别,它们的原则都是在相似性和相关性基础上的类比,差别只在于 象征具有重复和持续的意义;叶芝认为象征是最完美的隐喻;弗莱则指出象征是在语言 中更多地使用“隐喻意义”。
据考证,象征的最初意义大约是这样的:由于天然或者是习惯的原因,两物之间存在 着某种相互契合或类似的关系,于是在交往中一物便被用来代表另一物,前者就成为后 者的象征,并时时提醒人们联想或想像被象征物。从人类学看,人类早期在意识中构造 这个世界时,出于人类认识的严重局限,他们便使用了象征。后来象征物逐渐符号化, 类比被固定下来;只有在人们还记住两物间的自然或固有的关系,也就是在符号有着可 以解释的心理原因的时候,替代物才会被称为象征。这种时候在文学中特别多。由此可 见,象征非常符合作家们的意义观和表达方式。它既指向某一事物又超越了自身的指称 ,既标明了现实的意义又提醒我们注意潜在的意义,这些特点既与普遍感应相符,又表 现出了我们对想像力的强烈需要。
一个人决不会随意地为自己选择一种象征,而是某种内心深处有种需要使它自然而然 产生的,正如梦中出现的形象常常根据个人的需要而变化或发展着。保罗·德·曼认为 象征“构成了一种符号,既指出了某种具体的意义,又在破译它的同时,穷尽了其所暗 示的全部潜在意义”[2]。结构主义者向我们指出,这种“意义衍生”不是简单的意义 转换,而是多层意义的综合和新意义的诞生。因此,又有人认为象征代表“多种关系的 聚合”。
这种“多种关系的聚合”的象征手法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的精髓之一。 她的小说是诗化的小说,可以淡化情节、甚至无情节化,但诗意与象征使她的文本丰赡 而厚实。她善于运用象征暗示等手法去反映人物心灵世界的微妙变化,表现生活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当《海浪》一书最初在她脑海中隐约闪现时,她正在写《到灯塔去》的 结尾部分,当时她就有一种创作欲望。于是1927年6月,她开始写这部书。她把这部作 品命名为《飞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夜晚飞来了一群欢快的蛾子,那女人把最后 那只大飞蛾放了进来。她希望《飞蛾》写成时,将传达一种被理解为存在于现象面纱后 面的现实感,描绘人物一刹那的和谐、美感与丰富的意义,它将是一部抒情的作品,将 表现意识的内涵,将考察潜意识深处的象征体系。而飞蛾从一开始就将是她象征的中心 ,也许它用来象征领悟的哪个瞬间,也许它将是用来象征各种生命以外的生命的延续, 它对各种人的生命都无动于衷。也许,飞蛾被用来作为一种技巧,标志着从一个场景过 渡到另一个场景。但两年过去了,几乎没什么进展。直到1929年,那时飞蛾象征已经形 成了,她才感到可以放手写了。但到了1929年9月10日,她意识到她必须放弃飞蛾了, 她写道:
从现在起卧床六周,就可以使《飞蛾》成为一部杰作,不过书名将不叫《飞蛾》。我 忽然想起,白天飞蛾是不飞的,白天也不点蜡烛。总而言之,这部作品到底是什么样子 ,还需要考虑——但只要有时间,我就可以完成。[3]
在小说中,她所有的意图都得到了体现,但很多设想中的表现手法改变了。持续的内 心独白的创造,排除了不知名的女人(叙述者)存在的必要。散文与诗的交替,取代了飞 蛾的部分作用。书名改变了,飞蛾隐退到背景中去了。
但是,它们并未完全消失,只是改变了形态而已。实际上,对她来说,飞蛾形象不仅 重要,而且含义深刻。它不仅成了她创作本身的象征,而且还是想像活动的象征。在《 海浪》中,飞蛾象征的外表与内在含义融合在一起了,作者与她的作品也化为一体了。 那群“如此狂飞乱舞”的蛾子,变成了起伏万状的“幻觉中的波浪”。在那群飞蛾之中 ,有6只留了下来,并且转化成为小说中的人物了。
那么,飞蛾象征的来源是什么?它在作品中有何象征意义呢?
一、飞蛾象征的来源
飞蛾象征的来源跟植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早期生活。在她的散文《阅读》(1919年) 中,她谈到了她与读者同各自逝去的岁月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文学创作本身。在它的 中心部分,她描述了一次追扑飞蛾的活动。黄昏时分,叙述者——年轻的弗吉尼亚·斯 蒂芬合上了她正在阅读一本书。这时,急促飞旋的灰色蛾子出现了,一群年轻人提着灯 笼,拎着毒药瓶子,扛着捕蝶网,走进了树林。灯笼的火光改变了森林的景象,一切看 上去与白昼时截然不同。随后读者慢慢探索着树林的深处——昆虫在草丛中活动,灯笼 闪射出奇妙的光圈,一块块浸透着糖汁和甜酒的法兰绒吸引着许多飞蛾,最后,那只红 内翼大飞蛾出现了。读者逐渐意识到自己探索的不仅仅是森林,而且是他自己的想像力 ,甚至探索的是作者的脑海。而作者千方百计地要捕捉在自己脑海朦胧角落里一掠而过 的词汇和意念——正如《海浪》中所描绘的那样,“那些词汇就像扑动不停的银灰色飞 蛾的翅翼”[4]。
接着,那只长着猩红内翼的大飞蛾被捉住了,被丢进毒药罐,又被装进了玻璃瓶。它 “合拢双翼”,平静地躺着。在它临死的时刻,人们突然听到一阵响声,那是一棵大树 在森林中倒下了。这时,读者的焦点转到了大飞蛾本身——一个追求甜蜜和光明的牺牲 者。伍尔夫以叙述者的身份试图说明“不论写什么,在这里或那里,甚至无论在哪里, 总是时隐时现地隐现着一个人的形象”[5]。在该文的某处隐现着她本人的形象。她既 是阅读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作品的那个年轻姑娘,也是在潜意识的森林探索的那位成年作 者,又是那只红内翼飞蛾。
飞蛾象征的另一个来源可以从昆廷·贝尔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描述斯蒂芬家 的孩子们多次外出追捕蝴蝶和飞蛾的情景中找到答案。对年轻的弗吉尼亚来说,追捕飞 蛾体现着一种探索、兴奋和潜入未知世界的感觉。她自1919年创作《散文》以来,追捕 飞蛾就使她产生一种被追逐、被不知名的敌对力量摧毁的感觉。
1906年她哥哥索比逝世。至此,飞蛾便以悲惨的形象出现在3部小说之中。第一部《远 航》的女主人公雷切尔也像索比一样死于伤寒病。在小说的中部,雷切尔和特伦斯意识 到他们在相爱(这是一种注定长不了的爱情),此后不久,飞蛾就出现了,猩红色蝴蝶还 有黑色的蝴蝶,在两位恋人身旁飞旋,其中有一只很像那只红内翼大飞蛾。在小说的结 尾,雷切尔逝世后,飞蛾又以几乎相同的形象出现。弗吉尼亚·伍尔夫企图通过创作《 远航》来使自己适应哥哥已去世的现实。弗吉尼亚就是雷切尔,而且还是奄奄一息的索 比。
在《雅各之室》中,飞蛾之死与大树直接倒地是直接与雅各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喜欢 收集鳞翅目昆虫。其中有一只神秘的飞蛾,是雅各于午夜时分在森林中发现的。就在那 天夜里,那棵数倒了下来。小说简略地再现了散文中描述得较为详细的那个场景,同时 也提到了那只红内翼飞蛾,然而,它一闪就不见了,雅各再也没见过它。紧接着,小说 又写到了那棵树的倒毙和一连串的手枪射击声,就在雅各断气之前,传来了一声枪响。 最后,他像红内翼一样“平静地躺着……合拢双翼”[5]。
在《海浪》中,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形象——那个没出场的人物珀西瓦尔,他是以索 比为蓝本的。爱着珀西瓦尔的罗达在他去世后感到“有一把斧头劈开了树干的中心”[4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棵大树倒毙的情景升华了,它即象征着珀西瓦尔的逝世,又象 征着罗达心中的悲伤,就像一把斧头“劈碎”了她的心。
产生飞蛾象征的一个潜在原因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患病的身体和精神状态。1903年, 她谈到她的创作和自己的疾病以及与飞蛾象征之间的关系:
有一两次,我觉得头脑中有翅翼拍打的呼呼声,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我经常生病的 缘故……我觉得我的这种毛病——叫我怎么说呢?——在一定程度上有点神秘。我的头 脑发生了变化。它不在继续接纳印象了。它把自己关闭了起来。它变成了一只蛹。我躺 着,处于相当麻木的状态,尽管肉体常常剧烈地疼痛着……接着,突然什么东西涌了出 来……前天晚上……我产生了那种感觉……所有的门都在打开;而我相信是那只飞蛾在 我内心展翅飞舞。我就开始构思我的故事,不管编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3]
疾病、无意识状态、梦境合在一起,意味着产生一种意念所必需的酝酿阶段,也意味 着那种思想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发展的等待时期。她把这一阶段形象化地称为作蛹期,最 后合成了飞蛾形象。
二、飞蛾的象征意义
语言使用中,象征更多的是作为“隐喻意义”,而想像力的作用在于把事物隐喻化。 如果认为词语只是手段的话,那么“普遍的想像力包容着对一切手段的理解和获得这些 手段的愿望”[6]。在创造“愿望”的支配下,主观想像力每每发挥到极致,于是意义 的本身便可以脱离外界事物,也就是说,脱离对具体事物的感官感受,这时意义反而可 能更加完美和准确。这种脱离使得词语成为隐语。
飞蛾象征着弗吉尼亚的创作过程,象征着她想像力发展的始末:幼虫、蛹和展翅飞翔 的蛾子三者创造性的结合,亦表现为她思想的初步构成、酝酿和产生。
在《海浪》中,她十分注意发挥想像力的作用,它“告诉人颜色、轮廓、声音、香味 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含义”[6]。全书充满了象征意义,每一章的开头都是用一个又一个 的意象来表达人物细致的、隐秘的感受。小说共有6个人物:伯纳德、内维尔、路易、 苏珊、吉尼和罗达,共分9个部分,从他们开始产生意识写到他们离开人世。他们的生 活经历全都深藏不露,大部分属于那片黑暗的森林,较少属于那盏到处去追寻的灯笼。 吸引他们6人的是一位不出场的人物——珀西瓦尔——神秘的第七人——他才是那盏灯 笼,他的朋友们围着他转,就像火焰四周的飞蛾。他是一种能使事物理想化的因素,并 且正是以这种方式使那6位朋友——三男三女——合成一体,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代表着 一个单身男性的各个不同方面。他们也象征着想像力的各个不同方面:它那多种多样的 发展过程以及它那有意识与无意识的领域。伯纳德、内维尔、路易、苏珊、吉尼和罗达 经历着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但却共同显示了意念如何挣扎着开始酝酿一直到产生的过 程。他们象征着富于创造性的个性化。
这部小说是由那6位朋友的独白构成的,其中两位代表创造力的有意识方面,另外四位 代表无意识方面。伯纳德和内维尔属于有意识的那一类。善于措词的伯纳德出口成章, 创造了许多漂亮的词语,不断地虚构故事,企图用词语产生意义。他用词语“拉开了遮 盖在事物之上的面纱”,他用词语把生活加以“具体化”。在他身上还残留着少许原来 飞蛾形象的痕迹。
热爱珀西瓦尔的内维尔是明亮的化身,而明亮则是光的特征之一。他充分表现了这种 想像力。他观察生活,他对真理的直觉最敏锐。他头脑清晰,有着那种在欲望暂停之时 模糊的宁静感。他认为,外部世界本身是无用的,大自然太单调乏味,它“只有庄严浩 渺的景色,只有海水和树叶”[4],因此对他来说,他们不会有任何意义。他把思想编 织成了一只具有含义的茧子。
路易——那位澳大利亚人是女性化无意识状态的男性翻版。他目睹妇女“提着红色大 水罐走向尼罗河”[4]。正因为如此,他是历史和时间观念的化身。而创造性想像力正 是从历史中去汲取的。对他来说,历史是自我的先验的外延,他力图在自己身上把所有 的时间和事件联系起来,以期找到“存在与这两个在我看来更明显不过的差异之间的某 种巨大的混合物”[4]。在他身上还留存着两个飞蛾的特征,其中之一与想像和幻想的 笑声有关,这隐约闪现在“他那含笑的、任性的眼神中”[4]。在前一部小说《奥兰多 》中,有一个奇异的段落可以对此作出解释:黄昏时分有一群飞蛾说:“可笑,可笑! ”并且把“荒诞的胡言乱语”送入人们的耳朵。路易身上的第二个飞蛾特征与神话式的 想像有关,这是他与罗达所共有的一种直觉。宴请珀西瓦尔一事可以对此作出说明,他 与罗达把那次庆祝看作是一次神话式宴会。路易把其他来宾描绘成已经“变得习惯与夜 间生活了,并且还着了迷。他们的眼睛眨得飞快,像飞蛾扑翅似的,而且由于频率过快 ,看上去却像一动也不动”[4]。这种水平的想像力——以神话方式看问题——似乎以 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为基础,并且利用了变形和变时等思想方法。使路易与这种水平的神 话式想像相联系的另一因素表现在那焦急不安的梦魇形象中。他老是听见那只野兽跺着 脚踩踏海滩的声音。那海滩、陆地与海水之间的无人区,或许与醒睡之间的意识状态十 分相似。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曾指出,跺脚的词源被认为是古英语中的mara,即“妖魔鬼 怪”的意思。所以那只跺脚的怪兽与可被称为想像力的某种危机有着隐约的联系。
那三位女性主要与创造性想像力的无意识方面有关。罗达是那只美丽、孤单的蛾子。 她的“两块肩胛骨在背上相逢,就像一只小蝴蝶的一双翅膀”[4]。她的动作总被描写 得像是在飞翔。她是一位白衣少女,在一片黑暗中翩翩起舞,就像一只白色的蛾子,夜 间在森林里拍翅飞翔。当她一声声呼唤着“我梦想,我梦想”时,她的眼睛就像“傍晚 时分吸引飞蛾的浅色花朵”[4],她使人们想起埃及神话中的艾西斯女神——月亮女神 。水和月光与她联系在一起的,她是“永远眼泪汪汪的林泉仙女”[4]。树木、山洞与 泉水是她的象征。因此,她就是伍尔夫在日记里提到的梦魇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在精神 上的源泉。罗达是“没有脸”的,读者总是看见她背着身子,凝视着世界彼岸。她是想 像力中的不稳定因素:她的精神与躯壳相分离,物质的东西崩溃了,她的感觉世界已被 歪曲。她完全倾向与精神的东西,一切肉体的东西都令她讨厌,她最终自尽了。伯纳德 在谈到她的逝世时,仍能“感到她跳跃时所形成的一股飘动的风,就像她在飞翔”[4] 。罗达与恶梦世界的关系在密切程度上胜过路易。她半夜来到路易的阁楼房间(像睡梦 进入脑海一样),她能像恶梦和鹰蛾那样驾驭黑暗:“我下沉,坠落在睡眠黑色的羽毛 上;它厚实的翅膀遮住了我的双眼。”[4]罗达总有一种被追逐的感觉,被人追逐,被 恶梦追逐,被无名的恐惧追逐;人们看见她与路易一起深陷于更黑暗、充满神话故事的 想像境界。
吉尼是性欲力量的化身,她是“用肉体来想像的”[4]。她根据感觉与原动力的标准来 进行创造,并且将火与活力、特别是与舞蹈联系在一起,而后者是一种与创造相类似的 行动。她从不梦想。猩红是吉尼的代表色。她于夜间外出时,用一块“飞蛾颜色的头巾 ”[4]作标记。她象征着女性想像力无止境的执著追求,在黑暗中寻偶(即与头脑中的男 性因素结合),为了享受瞬间的欢乐,就像飞蛾欣喜若狂地停落在浸透着糖汁的法兰绒 上那样。在《海浪》的第五部分中,吉尼说:“我的身体带着我,就像黑暗小巷深处的 一盏明灯,把一样样东西先后从黑暗中引到光圈里来了。”[4]这段话使人想起林中追 扑飞蛾的情景。如果说,罗达是那只孤单、美丽的蛾子的化身,那么吉尼就是那只红内 翼的化身。吉尼是那欢乐的眼睛,是与不可缺少的物质世界在感觉上保持联系的关键。 作为红内翼的吉尼,象征着无意识或“下意识”的隐蔽形态,而这种形态只能在异想天 开时产生作用。
苏珊是大地母亲,她低声吟唱,“引人入睡”。她擅长养育的特点,表现在她自己如 何“被纺成细丝,缠绕在摇篮周围,并用我自己的血作茧包住我那婴儿般幼嫩的四肢” [4]。她用网罩覆盖草莓苗圃,她“缝缀白色的口袋来保护梨子和梅子”[4]。她可以被 称为创造性周期的酝酿或转化阶段。所以蛾蛹是与苏珊相联系的,在孩提时代,苏珊最 早注意到的物体之一是“一条毛毛虫……卷成一个绿色的小圈圈”[4]。
飞蛾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其他象征一样,起着多重作用。对她本人来说,飞 蛾是使她能从灾难中挣脱出来的象征。对读者来说,飞蛾暗示创造力的活动,体现意念 从无意识转化为有意识的活动以及表达豁然开朗的感觉。更普遍的情况是,飞蛾象征着 为表达思想而作的永无休止的努力,为进行创造和判断而进行的斗争,就像飞蛾扑火一 样,它虽然是一只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却是一束充满活力的光,它起的作用是崇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