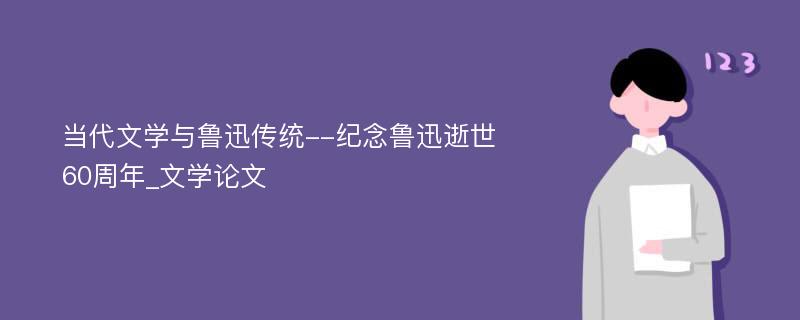
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作于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当代文学论文,六十周年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个很不好写的题目,但又是不能回避的话题。时逢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我把零碎的想法写出,算是对先生的感怀,以及对当代文学一个侧面的提纲式的扫瞄。因为是“提纲式”的,所以便显得空泛,我希望今后会有人,在这个题目下做更详尽的工作,或许,它会给人带来更切实的东西。
1
六十年前,当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的时候,他的好友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沉重地写道: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之一死,使大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许多年来,郁达夫的话,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中,我相信,没有谁的文字,会像郁达夫那样把鲁迅与他的民族,与他的身后的民族历史,阐释得如此清晰。从1936年至1996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在经历了种种苦难后,发生了惊人的巨变。而十分有趣的是,在这一巨变的过程中,在中国人精神的太空,鲁迅的幽灵一直在徘徊着。从抗日战争、延安文艺运动、解放战争、沉重的五十年代、“红卫兵”运动,乃至八十年代的新启蒙、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等等,我们几乎一直未能摆脱鲁迅的余荫。康德曾以他的思维方式,规范了近现代的西方文化走向,那巨人的超常的认知触觉,把人类的智慧表达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一点上,我以为鲁迅是东方的康德。他以狂飙式的气魄动摇了东方传统的思维之树,颠覆了古老的生存童话,把人的存在秩序,引上了现代之路。但鲁迅复杂的精神意象所散发出的诸种不确切性的光芒,又常常使他成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令人困惑的现象之谜。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极左者的呓语,都曾假托着鲁迅而存在。在官方和民间,在孤独的艺术家与学院的思想者那里,鲁迅被撕扯着,组合着。围绕这个已逝的长者,学者们争论着,流派纷呈,甚至烽烟四起。而在文坛上,每一种思潮的涌现,都无法绕开鲁迅。无论你赞扬还是否定,实际上,人们没有谁能够离开鲁迅直面的价值难题。这便是当代中国文人的宿命,我们被困在了这漫长的历史的隧道里。在中国人精神的现代化之旅的进程中,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约而同地与鲁迅相遇了。
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坛,经历了对鲁迅的支解、还原、误读、借代几个时期。每个时期的鲁迅均被涂抹了不同的色调。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来变去,在深层的形态里,鲁迅的遗响似乎从未中断过。其实这并不是简单的影响力的问题,在我看来,鲁迅之于他后来的文学史,更主要的是一种“精神话题”的延续问题。鲁迅的杰出性在于,他在自己的世界里,创造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话题”。这个话题的核心,便是如何在西方夹击下的“被现代化”过程中,确立中国人的生存意义。这里既有对人的本体价值的形而上的渴望,又有对生存意义的深切的怀疑,鲁迅的“精神话题”便纠缠着这一现象之谜。我认为此话题的鲜活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其内蕴上,更主要是它的“叙述语态”上。鲁迅创造了一种中国人的智慧表达式,他以后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未能像他那样,把一种精神结构渗透到文化的母体里,以至成为一切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当代文人思想中的因子。鲁迅既是一种源头,又是一种实在,他矗立在那儿,仿佛是一个不尽的光源,在那周围你几乎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照耀。
鲁迅遗产的广阔性与深邃性,至今尚是一个文化之谜。他太伟大了,在对生命深层体味与拷问中,特别是在对中国人灵魂的审视中,他所产生的引力不仅是前无古人的,而且直到今天,还没有谁能够取代他。他在几个方面规范了后来文学的轨迹。一是在思维方式上,他上接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与欧洲浪漫诗学传统,旁及苏俄、日本诸国个性主义文化,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思维的时空结构,他在科学哲学影响下所形成的认知方式,其特异性与超常性,还未见到有第二个人。在这一方面,他属于世界性的巨人,萨特、加缪、波德莱尔等,在对人类苦难的洞悉上,和鲁迅是处于相近的水平上的。甚至连日本学者也认为,在东方,鲁迅属于“被近代化”过程中,最杰出的思想者,他的深刻性在亚洲诸国,是无与伦比的。二,鲁迅发现了东方人在被西方文化强迫走向近代化这过程中的心理的障碍问题与本来的东西。他受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影响,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不懈的批判。他以形象的笔触,勾勒出了阿Q相这一国民性的典型。在他以前,还没有任何人,对中国人的灵魂,进行如此深邃的、集中的审视。他从司空见惯的,已被国民漠视的社会景观中,抽象出一套沉重的人文话语。这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做了精神内省的准备。三,鲁迅奠定了个性价值与生命价值在新文化中的地位,他彻底地颠覆了专制文化的根基,把人性的声音弥漫到精神的天地间。他的毫不中庸的人生态度,韧的批判意识,对敌手一个也不饶恕的胆识,显示了人的精神的尊严。无论是整理古文化遗产,还是摄取域外文明,贯穿其思想的,一直是鲜活的生命价值和人道感、殉道感。鲁迅的这些精神个性,成了他“精神话题”核心的内容,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人们。
当代中国文学与鲁迅传统的联系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题目。但与时下那些琐碎的、不痛不痒的宏观大论相比,我更喜欢关注鲁迅“精神话题”在新近文学中的转化与流变。它是怎样被衔接了?新一代的作家如何挣脱“五四”式的无奈?还有那些孤独的挑战者为什么不自觉地陷入鲁迅在《野草》中表现出的绝境?张承志、王朔们读懂了鲁迅么?等等。这是必须回答的价值难题。我在王蒙、邵燕祥、张中行、张承志、史铁生、张炜诸人的世界里,谛听到了对鲁迅的某种呼应,差异是如此的巨大!共振又是如此的长久!一颗伟大的灵魂在经历了被切割、被分享、被他人自我化后,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一种原色。
2
似乎不必要引证大量的材料。我们从几代人的思想里,都可以找到鲁迅的痕迹。鲁迅精神的鲜活价值,常常表现在思想界中。中国的思想界与文学界从来是处于相似的形态里的。在这些领域里,鲁迅充当了启蒙的哲学家的角色。虽然他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和思想范畴,但事实上,他给哲学、史学,乃至美学界的启发甚至超过了外来哲学。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八十年代中国的新启蒙运动,有三个思想的来源。一是以康德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二是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说;三是鲁迅传统。在这里,康德启示了人的主体性学说,弗洛伊德和荣格使人看到了心理结构的轮廓,而鲁迅传统则成为新启蒙的内容。回想起八十年代哲学、社会学领域刮起的主体论的文化旋风,至今仍使人神往。那时李泽厚诸人的理论,是以康德、荣格化的术语,在表述着鲁迅的精神话题的。甚至像刘再复的文学理论,也仍然是读解鲁迅后的感性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鲁迅的力量。李泽厚曾直言不讳地谈论鲁迅对自己的影响之深,说:“鲁迅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他培育了无数革命青年。他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他的影响巨大的《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对中国人精神原型的揭示上,显然受到了鲁迅的教益。以李泽厚为中介,八十年代的文学理论,生成的便直接是这一主体精神的果实。我们甚至从巴金、孙犁、吴祖光、柯灵等老一代作家复出后的作品中,亦可感受到对鲁迅的切深的呼应。八十年代文学观念的热点,是围绕着李泽厚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形成的。这一热点的核心,是对生命价值的能动的阐释,它把人的主体性中的人性结构,深切地揭示出来。这个结构是:“理性的内化”(智力结构)、“理性的凝聚”(意志结构)、“理性的积淀”(审美结构)。李泽厚的描述充满了浓厚的学院色彩,但我从他的独语中,似乎感受到了鲁迅精神话题的另一种表达式。鲁迅当年对“国民性”的感性梳理和揭示,在八十年代,被李泽厚等人以思辨的方式重新复述出来。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你读一读那一时期有分量的随笔和杂感,差不多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一余绪。八十年代的思想界并不简单是呼唤“五四”传统的问题,那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创造出一种思想体系,也没有谁简单地提出回到“五四”去。思想界与学术界的首要任务,是对旧有文化遗产的重新解释。在这种重新解释文化旧迹的过程中,马克思、孔夫子与鲁迅,成为三个重要的对象。人们试图以另一种方式,还原这些思想者的精神本质。而这种还原,恰恰导致了文艺思想解放的运动。无论是周扬、王蒙,还是后来涌现出的更年轻的作家学人,都加入了对历史与文化的新的内省的队伍。
1985年左右,王富仁在其博士论文中,明确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这在学术界引起了空前的反响。随后引起的争论与近于冷酷的论争,使人感到对鲁迅的态度,与当时对社会改革的态度,是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富仁之后,更年轻的博士汪晖从更深的精神领域开始思考鲁迅世界不确切的,但却是博大精深的一隅。这一种异常的声音,给文坛特别是理论界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旧有的解释鲁迅的思维模式,把鲁迅精神的更具现代人文意识的东西昭示出来。从王富仁到汪晖,这种学术意识的转换,正是与中国文学思潮的转换相同步。甚至可以说,这些思想者的情怀,在经过无数个文化中介的转化之后,深深地渗透到当代文学的震动中。在北岛、张承志、张炜、刘恒、史铁生诸人的作品中,在诸如余秋雨、王英琦、周涛等作家的吟咏中,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学术思想震荡的余波。学术界与作家之中,那些最孤独的思想者,差不多都带有着鲁迅当年的锋芒。虽然其视野里的景观已多有不同,话语方式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在对人的深层灵魂的体味与中华文化反省的过程中,鲁迅“精神话题”在这一代人的世界中被重新激活了。
3
曾经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中国当代文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这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我曾经很惊异于这个观点,以为言过其实了。但我们如果从另一种进程来思考当代文学的历史,确实可以发现当代文化在二十世纪精神演进中与本世纪初文化的亲缘的联系。在对历史的梳理与思索中,我们至今还没有谁超过鲁迅、周作人这样的文化人。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它在相似的母题下延续着。“新时期文学”在“质”的结构中究竟比“五四”文学有着怎样的飞跃,还是一个疑问。在这个意义上,说七十年代以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其思路,并不能说是妄断的。
周作人谈“五四”白话文运动,把西洋传教士文化,与晚明文人小品,看成重要的精神源头。他甚至把白话文运动,看成明清笔记文学的直接后果。周作人的观点很是深刻,我以为他是看到了中国文学演进中这种逻辑上的链条,七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大陆文学,与世纪初的文学,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上的起承转合。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新生的文学,无论在话语方式还是精神印迹上,还都留有“五四”文学的影像。只不过审视的内容稍有变化而已。那时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刘心武、王蒙、李国文、从维熙等人,其知识结构除了苏俄文学传统外,鲁迅和“五四”精神是其思想中核心的东西。被颠倒的鲁迅在这一代作家那里,被重新颠倒过来。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作品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新启蒙的话筒。刘心武等新涌现出的作家,在借着鲁迅式的话语,述说着对人的尊严和个性的期待。那是一个久违了的声音,在刘心武、北岛、舒婷等人的呼喊声里,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生活在鲁迅当年所说的“瞒与骗”的大泽中。北岛高呼着“我不相信”,其激愤的情怀,令我想起鲁迅杂感的激情。张贤亮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心灵的透视,在宗教式的谶语里,留有着魏连殳、子君等鲁迅笔下知识者的苦痛。那时中国作家所关注的,是对以往三十年生活的梳理,还并未能从更深的文化层面上,来思索那一代人的悲剧。刘心武当时注重的是从政治法则中还原人性的自由。北岛完全凭着直觉来体味虚无与荒谬的含义。张贤亮视野里的灵与肉的角斗,更多地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重新的发现,其意味大多停留在对“左”倾文化的清算上。七十年代末的文学,还不能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向世人展示我们的生活的原色,只是到了“文化热”、“寻根”文学之后,人们才开始从历史的长长的阴影中去寻找中国人生存中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寻根”文学来自于对拉美文化的启示,但当人们真正从乡土文化入手去寻找历史之根的时候,才发现,这类工作,鲁迅、沈从文等人,在许多年前早已做过了。韩少功在《爸爸爸》中大写古中国的意象,许多批评家一眼就看到了其作品主人公与阿Q的联系。但“寻根”派的作品,带有着太多的先入为主的概念,除了从某种程度上弥补早期作家文化底蕴的不足外,在深层文化的意蕴里,显然没有一个人超越《呐喊》的深度。八十年代的作家,对本土文化的揭示,尚无充分的文化积累和准备。许多作家,不久便在作品中表露出文化上的“贫血”。影响八十年代作家的,往往是文化热中的某一流派的口号和观念,而恰恰缺少植根于本土文化,又深味西域文明的大手笔的人物。这导致了文坛五光十色的景观,思潮迭起着,而巨作殊少。在一个文化荒疏多年后的新启蒙的岁月里,人们不久就发现了这一代人在文化哲学中致命的弱点。
这一时期一些更年轻的声音从文坛的一角出现了。我注意到了史铁生、刘恒,他们的孤独的咏叹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不可忽视的景观。史铁生与刘恒的身上,常常有着《孤独者》魏连殳式的苦寂,他们忧郁的,与苍天默然交流的那种冷然的目光,射出的是阵阵逼人的气息。在那落落寡欢的低语里,我听到了鲁迅那种绝望的声音。刘恒承认,自己的世界里有着鲁迅的影子。我读他的《虚证》(这是他最满意的中篇之一),便觉得是鲁迅《孤独者》八十年代的翻版。除了绝望还有什么?刘恒陷入了鲁迅式的绝境里。他以更细致的笔触,把人的与生俱来的无奈,那么鲜活而阴郁地勾勒出来。而史铁生的世界,常常流动的是对人生大限与彼岸世界超越的渴望。这个孤苦的灵魂对世界的打量充满了绝望中的期盼,我从他的隐隐的痛感中,体味到了鲁迅在虚无中摆脱鬼气的那种悲慨之气。当个体的人在一片无物之阵中陷入茫然而又不失其意志的时候,人便不自觉地呈现出鲁迅的那种意象。正如汪晖在其博士论文中强调的那样,反抗绝望便可呈现出个性的意义。这种意象在鲁迅之前的中国,是从未有过的。从新一代作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对鲁迅的某种重复中,可看出中国知识者与传统社会那种悲剧的牵扯吧?
鲁迅的“精神话题”在当代文学中的延伸,最显著的一点,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国民性”一词,最早出自清末,梁启超、章太炎当年曾常思考这类问题。但真正的始作俑者,应当说是西方的传教士。上个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作《中国人的气质》一书,详尽地探讨过中国人的国民精神,其分析之详,论证之深,对晚清的中国文人影响深远。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恰逢《中国人的气质》日文版问世,对其后来精神的形成,起到巨大的作用。他一生所致力的事业,便一直是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七斤、九斤老太太等人物,便留有他关于中国人心理结构的深层拷问。鲁迅一生耗费精力最大的,便是什么是理想的人性,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何在之类的问题。他的小说与杂感最动人心魄的地方,便在这里。国民性问题作为一个未完成的课题,在近几年被重新提起,是历史的必然。当人们直面现代化与传统的时候,这类问题便自然在艺术领域中被再次呈现出来。读一读各式新乡土的小说,民风民俗色彩十分浓郁的地域小说,都有类似的思路。贾平凹、刘恒、陈忠实、陈建功诸人,在自己的世界里,时常流露着对国人灵魂凝视时的无奈。印象较深的,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那里大气磅礴的文化拷问,对中国人心理性格的勾勒,让人感受到鲁迅杂感中的冷峻。王蒙试图写出老中国儿女的魂魄来,当他无情地剥脱着人性的外衣时,他是不是也进入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境地?这种困惑何尝不留在贾平凹、刘恒的世界里?这两位年轻的作家,在精神的跋涉中,时常参照的,便是鲁迅。贾平凹对鲁迅研究论著的热心和关注,绝不亚于一些学人。在灵魂的深处,他或许更喜爱鲁迅吧!你读一读他近年的小说,在古雅的氛围与中原古风的韵致里,是不是也有鲁迅乡土小说式的惨烈?当他陷入中年人的绝望时,我从其灰色的目光中,似乎也感受到一缕鲁迅的忧郁。与贾平凹不同,刘恒视野中的乡土是粗犷的,他缺少中原人的古老的神话,但他精神中的那些不确切的,与历史幽灵无法割断的逻辑联系,在我看来,更多是鲁迅赐予的。他写灰色中国的那一幕幕历史,在底色上直承鲁迅《呐喊》与《彷徨》的氛围。无论这是一种模仿还是精神的巧合,我都从这种历史性的承继中,看到了鲁迅的魅力。他教会了人们怎样抉心自食,怎样以冷酷的目光审视人的自我的灵魂。刘恒在自己的众多作品中,便留下了这种印迹。他在《白涡》、《伏羲伏羲》、《虚证》、《苍河白日梦》等小说里,描绘着的,便是中国人的本来的东西。他试图以新的方式,找到呈现人的精神原态的东西。这种努力是自然而真诚的。《苍河白日梦》雄浑悲怆的咏叹,给予我们的,便是这类全民族的无奈。作者在对中国人生存境地的勾勒上,比王蒙、贾平凹,都具有更为沉重的东西。
这类文化色调浓郁的审美凝视,在八十年代以来,从未间断过。张炜、张承志等个性色彩十分浓厚的人,何尝不也有着这类思路?甚至像周大新、阿成、池莉等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一合唱。“写出民族的灵魂来”,这几乎成了一代人的信条。而这一信条,恰恰是鲁迅给予后人的。我从本世纪末众多文人相似的精神走向里,看到了“末完成的鲁迅”在当代的意义。鲁迅的价值不仅显示在他的同时代里,更重要的是在后来岁月中的不朽的延续。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欲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首先便是人的灵魂的更新。鲁迅最早看到了这一障碍。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深刻、那样猛烈地揭示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然而这样的声音在古老的中国,显得那样弱小。当代有良知者的作家,几乎都意识到了鲁迅精神在当代的价值。当无数个为解决国民性问题而奋斗的诗人、小说家艰难地在文化之旅中攀登的时候,我常常被这一代人未泯灭的良知所打动。鲁迅的魅力是内在于知识分子的性格中的。这正如老庄、孔孟之于后世的读书人,鲁迅也规范了二十世纪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始于呐喊,终于彷徨”,还有那种“反抗绝望”的声音,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从未中断过。不了解鲁迅,便难懂中国;要走出古老的旧世界,鲁迅便是我们的先驱。当代文学的深层文化纽结里,流动着的,便是这一潜流。
4
常常地,在那些孤苦无援的个性主义作家身上,我能够发现他们与“五四”先觉者的深切的呼应。那种复杂的心理体验,与鲁迅、周作人当年的心绪有着十分相似的联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鲁迅在许多青年人那里曾一落千丈。当神话鲁迅的谶语被打破后,鲁迅曾被人们冷落了多时。但是当我们的国土在经历了经济的喧嚣、各种“主义”孳行的骚动后,一批反叛流俗的人们,突然重新发现了鲁迅的价值。尽管不可避免地还有误读者的杂音,但在那些异端者的声音里,几乎处处可以感受到鲁迅的印迹。
当刘晓波猛烈抨击李泽厚的理论模式时,他精神的依傍是尼采与鲁迅。而张承志孤独一人行走在西北荒凉的土地上,在哲合忍耶的教义下获得心灵净化的时候,他身边伴随着的,是鲁迅的影子。一向蔑视权威的张承志,在鲁迅面前却那样恭恭敬敬。他似乎在鲁迅那里,找到独行的力量。甚至像邵燕祥、何满子、张炜、韩少功等人,在他们的回肠荡气的文字中,都不难读出征服苦难的那种勇气。这些鲁迅曾经历过的心绪,如今还如此深刻地缠绕着人们,甚至连话语方式,也带有《呐喊》、《彷徨》的格式。张承志坦言自己受到鲁迅思想的洗礼,除了毛泽东、鲁迅的名字外,他视野中的现代中土文明,是缺少血色的。只有毛泽东与鲁迅,才真正颠覆了一个时代。张承志甚至认为,在直面汉文明陈腐落后的一面时,鲁迅是自己的老师。读一读《心灵史》,你可以感受到来自于鲁迅与穆斯林两种传统的异样的色彩。张承志视野里的鲁迅,被他印上了更为异端的情绪,他尽可能省略了鲁迅世界的秩序化的、文化人类学式的精神话语。而其将非理性的社会意识,引向新的极致。刘晓波似乎也有类似的倾向,他们都从生命的自由意志那里,将鲁迅极端化、神异化。这里有明显的价值误读,但在对个体与群体的态度上,他们确实发现了与世俗抗争的精神源泉。当代文学中一切异端者的声音,都是从这一源泉流淌过来的。
鲁迅遗产的重要价值之一,是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精神。他抗争奴化与物化,抗争灰暗与绝望。在鲁迅那里,“立人”,蔑视权贵乃核心的价值趋向。这一个性在明清为“遗民”情结,到了“五四”,“遗民”情结中的儒学气被扬弃了,鲁迅把一种人本位的个性意志,灌输到生命价值观中。这一个性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知识分子,它突出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对世俗的批判态度,以及与世俗不合作的态度。八十年代以后的独立性很强的文学家、学者,在其内心深处,一直有着这样一种道德律。邵燕祥、李国文、从维熙,以及更年轻的一些作家如格非、莫言、李晓、残雪、池莉、王安忆等人,在他们的作品中,一直保持着对现象界的警惕。邵燕祥、牧惠等人的杂文多么像鲁迅的某些作品的风格!这绝不是简单的模仿,相近的生命体验,使他们在凝视生命个体与文化历史的瞬间,不由地走上了鲁迅杂感式的道路。而在学界,从德高望重的钱钟书、张中行、季羡林,到中年学人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平原、王得后等,那种反世俗的声音,给混乱的文坛,确实带来了一片净土。读一读张中行的《横议集》、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你难道不觉出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高洁的品格?以《读书》、《随笔》、《散文与人》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的园地,保留的便是这种纯正的声音。《读书》的主编与《散文与人》的主编们,公开声明,他们是恪守鲁迅传统的。九十年以来,中国文人最深沉的声音,差不多就来自于这里。当世俗与灰暗把人引向歧路的时候,张承志、邵燕祥、张炜等人的呼号,给人带来的是怎样的清醒!这些鲁迅的传人们,确实把民族的希望之旗,高高地举起来了。
上至巴金、冰心、孙犁,下至王蒙、邵燕祥、张承志,几乎没有谁,不把鲁迅当成自己灵魂的前导。巴金《随想录》里大量的声音,其实正是鲁迅当年《热风》的旋律。张承志《心灵史》中探索者的形象,多么像《过客》的主人公。邵燕祥对世风毫不回避的直面,是只有鲁迅杂文中才有过的情怀。自新文化诞生以来,还没有一位作家在如此广泛的领域,从思想、人格、艺术等方面,如此深刻又如此长久地影响着后人。鲁迅传统的不朽的活力,已被他身后的历史所证明了。
5
鲁迅精神话题在当代的延续,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宿命。看看《读书》、《收获》杂志近些年最有分量的文章,和编辑创意,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九十年代的鲁迅精神话题并不像八十年代那样形成一股主潮和合力。在九十年代,鲁迅思想在文坛上被各种力量所稀释了。王朔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流通领域、变成消费文学时,竟然也从鲁迅那儿寻找依据,他的洞明世事的聪明与学识上的浅俗,竟然在某些题材的处理上,与鲁迅巧合。《我是你爸爸》的内蕴在深层的话语里,弥漫着的是鲁迅当年关于怎样做父亲的主题。王朔消解了鲁迅身上的忧郁与沉重,他把“五四”后在知识者中形成的使命感推到了一旁,以市井中的游戏与调侃,去支解鲁迅当年面临的苦难,至少在平民化与大众化上,走出了别致的一步。王朔的单纯与浅薄之中,并不掩饰着这一代人的无奈。但他的话语结构的最后结果,却使人们从另一角度上看出鲁迅的无法绕过的价值。王朔的成功与失败之处,我以为鲁迅模式便是一种印证的参照。王朔抽走了中国人的神圣的精神,当他打碎一切旧的偶像时,连同人的生命的内驱力——精神价值——也一起驱走了。与王朔形成鲜明对照的张承志,则支解了鲁迅传统的科学理性的一面,从更为原生态生命意志中,去张扬反抗俗世的精神。尽管张承志不止一次地呼唤着鲁迅的亡灵,但在根本点上,他走的是一条反工业文明的宗教情感的道路。张承志似乎不相信科学理性会给人带来福音,他往往从远古的遗风与圣洁的教义里,去谛听人性的声音。当他猛烈抨击中原古文明的时候,那种寒气滚滚的战栗之音是怎样地震撼着人们,但这种批判的武器,不是鲁迅的在科学哲学与德国哲学启示下的人文主义理性,而恰恰是反人文精神的宗教情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之谜。王朔的精神来源是都市平民情趣,张承志思想的源头之一却是古中亚文明。在这里,牛顿力学时代的对理性的确切性的渴望被消解了,爱因斯坦时代的雄浑、壮阔的精神之光隐退了。鲁迅当年精神世界中的德国浪漫诗学精神与俄苏文化传统,乃至魏晋风骨,也统统被以另一种方式代替了。我从这种文化的现象中,确实看到了一种精神的变异。一方面不得不延续着鲁迅的精神话语,另一方面又在远离鲁迅精神的内核,这种文化的脉息,缺少了一种神圣与平和,缺少了多元意识下的健全理性。应当说,“人文精神”话题的讨论,至少在文化价值承担与现代科学理性思索方面,显示出了当下文学应解决的问题。恰恰是“人文精神”的讨论,再一次把鲁迅精神话题明确化和深入化了。
迄今为止,人们对王晓明等人发起的“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讨论,仍有相异的看法。我认为不管这一命题有多大的缺陷,倾听一下这一声音是异常重要的。这一声音的背后,有一种困惑中的期待,和期待中的困惑。它再一次把人们引向鲁迅的“过客”意识面前。不可想象一个民族在失去了健康的精神企盼后,其文化将是什么样子。当你嘲笑了一切文明,鞭笞了一切存在物,你自己留下的是什么?“人文精神”的讨论在立论的基点上,自有它矛盾的、还未自圆其说的地方,但它以“在野”的声音,向商业潮流下的文化,发出的警示,自有其不容忽视意义。我相信这是多元文化开始的一种象征。中国文化向来以一元的格局出现在人们面前,如果仅仅以王朔那样“躲避崇高”的文化矗立在文坛上,而没有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呐喊,殊是可怕之事。“人文精神”讨论中所扩散出的忧郁,至少对大众文化的热潮,是一副清醒剂,它的拒绝媚俗、警惕物化的意识,在我看来,有着不小的价值。中国知识分子欲在新的环境中确立己身的渴望,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得到了。
只有在这种多元格局的文化景观中,我们才可以真正感受到鲁迅的价值所在。“鲁迅精神话题”当沦为了“在野”的声音,才可以真正领悟到它的魅力。这份遗产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对人类僵硬的文化惰性核心,是一个异端,它的意义就是消解惰性的核心,把人从物化的或非人道的文化程序中拯救出来。它告诉你的是你应当拥有自己的东西,而不是非我的存在;它提示你应是人类命运的沉重的承受者,而不是浅薄、轻浮的个人主义分子。这个遗产没有许诺,没有“黄金世界”,它永远纠缠着困顿,纠缠着茫然和孤独,在一种心灵的角斗与内省里,寻求生存的实在。鲁迅模式一旦被定为一尊神像其价值便被消解,或者走向它的反面。“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已说明了这一点。鲁迅的模式的本质是边缘化的,是从“在野”的领域向文化惰性中心发出的冷峻的声音。一切曾在社会底层或文化边缘中孤独前行的人们,大约都会从中体味到此中的要义。当人们一次次寻找,一次次失落的时候,便不得不重复着《野草》里的声音。鲁迅没有为我们寻找到什么,但他的那种状态,那种在没有路的地方踏出新路的悲壮之举,确实是我们灵魂的前导。二十世纪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在这一巨变的岁月里,我们荣幸地诞生了鲁迅这样伟大的寻路人。我们便是这一探索之途上后来的人们。没有既定的目标,也许并不是坏事,人类存在的意义,便在于对人性的寻找。
生在中国,我们常常只能这样;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往往也只有这样。
1996年7月于北京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读书论文; 张承志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文学作家论文; 呐喊论文; 李泽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