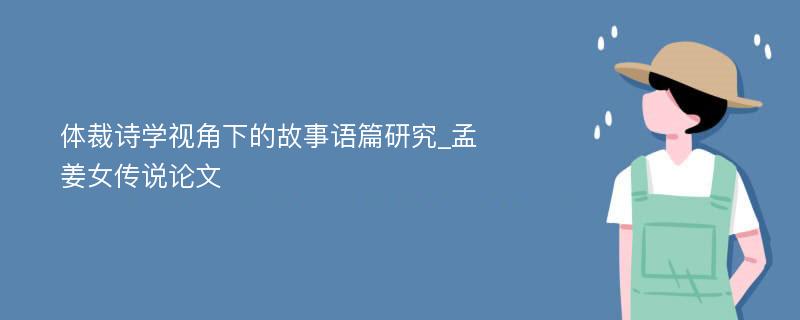
“体裁诗学”视角中的故事文本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体裁论文,视角论文,文本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3)-04-0106-08
20世纪被称为文论世纪,但其实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论坛已是众声喧哗,既有纠结于“文体形式”持续了20余年的新旧语体之争、“自然派”的胜利;又有各路新兴文艺学派,尤其是文艺学学院派,诸如布斯拉耶夫的神话学派、贝平的文化历史学派等的悄然兴起,亚·维谢洛夫斯基院士代表的比较历史学派更是以建立历史诗学理论和科学的总体文学史观,对20世纪以来的东西方现代文艺学和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国文艺学家们坚持实证的科学精神,在民间文学、神话传说等文学、民俗学、人种学、民族学、文化史诸方面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考据论证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各民族文学在统一的世界文学形成过程中的相同点或相似点,探索这些“雷同点”内中隐藏的实质性、规律性以及不同的因果关系。
到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俄罗斯民间文学理论已进入兴盛期,其中,以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奠基人弗·雅·普罗普(В.Я.Пропп)为代表的故事文本的结构功能研究成为最有影响的“主潮”,其1928年发表的《故事形态学》亦成为这一流派的“标志性著作”。主张诗学研究是故事历史研究前提的普罗普,“是位典型的书斋型学者,他的研究活动不是始于田野作业搜集故事,而是对阿法纳西耶夫《俄罗斯民间故事集》的研读,这种方式似乎从一开始就使他将研究视线投向了故事文本,尤其是故事文本的形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故事的‘体裁诗学’”[1:74]。
普罗普曾专文论述民间创作的22个体裁划分原则,指出:“体裁是凭借18-20世纪民间创作的状态来确定的。对体裁的适当的确定又是对民间创作的艺术、思想和历史较为可信的科学研究,并且是对随后的民间创作在总体上所作的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时代性的结论。”[2:219]
普罗普发表《故事形态学》时值1920年代,苏联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空前活跃繁荣,形式主义流派也进入了极盛时期。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继1917年被称为“形式主义学派的宣言”[3:385]《作为手法的艺术》问世后,1920年代又相继发表了《散文理论》等重要论著。他在评析维谢洛夫斯基创立的民俗学理论“情节诗学”时,提出,“事实上,故事不断被打散,又不断重新组合,都遵循着特殊的,尚未为人知晓的情节编构规律”[4:28],与普罗普总结的故事体裁“特殊的情节构成规律”极为接近。当时的形式主义学派其他代表人物都在执著地追究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和结构特征,试图解答文学可能存在的普遍性质、文学的本质。譬如鲍·托马舍夫斯基曾专文阐释文学体裁,他认为:体裁的特点是,“在每一种体裁的手法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该体裁所特有的一组手法——它们是围绕这些明显的手法(或体裁特征)所形成的。”“作品也因所用手法(体裁)的不同产生一定程度的明显区别。”[5:136]
当代俄罗斯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БорисЛьвовичΡифтин,1932-2012)院士1932年出生时,形式主义仍有大量论著问世,但是已经开始在苏联受到冷落,并在之后遭到猛烈批判。上世纪50年代中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维克多·埃利希首次将形式主义理论介绍到西方时也未引起重视。直到1960年代,当时李福清的《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已经出版,形式主义才在苏联国内外受到重新审视关注。形式主义对文学自身结构体系形式、功能材料语言等的关注使文学研究成为了一门现代学科,并对其时和其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学术方法论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濡染其中的李福清实难游离其外。朱自清在《陶诗的深度》里所说:“固然所能找到的来历,即使切合,也还未必是作者有意引用;但一个人读书受用,有时候却便在无意的浸淫里”[6:569],很适合借来喻指李福清与形式主义流派的关系。在谈到胡适关于民间文学与文学的关系论述时,李福清曾批评胡适的论断非常接近形式主义的观点:胡适在其《北京的平民文学》(1922)一文中号召诗人们取法的只是民谣的形式和风格,他关注民间文学只是基于其接近口语的语言[7:27]。
大学期间受教于普罗普的李福清,具有俄罗斯学者特有的学术研究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生涯之始,他便自觉地运用普罗普的“体裁诗学”观,批判地借鉴俄国形式主义的“体裁说”,开始了视野独到的中国民间创作孟姜女传说故事的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李福清在大学期间首次接触到孟姜女传说;1954年在整理已故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藏书时得见顾颉刚编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1955年大学毕业到苏联科学院民间文学研究室工作后,又得到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契切罗夫的指导,更为深入地研究孟姜女传说,1961年研究孟姜女传说的专著《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Сказание о Великой стене и проблема жанра в китайском.фольклоре,М.,1961)完成并出版;李福清以这部专著作为副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
李福清在这部专著卷首指出:万里长城和孟姜女的传说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两千年间文献典籍中的相关记载俯拾即是,由是得以研究民间文学作品体裁、作品人物形象、各种历史阶段主人公的关系如何演变;得以提出不同民间文学作品体裁中同一主人公的描写特点问题[7:1]。全书包括:作者的话、孟姜女的故事(据1957年第3期《民间文学》上登载的李清泉记录的孟姜女故事译出)、序言,以及孟姜女传说研究、古代关于杞梁妻传说和孟姜女故事、唐代(7-10世纪)、宋、元两代(10-14世纪)记载的孟姜女故事、明代(1368-1644)、清代(1644-1911)的孟姜女故事、现代记载的孟姜女故事,共七章以及参考书目。
“孟姜女传说”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并称中国四大民间故事,妇孺皆知,两千余年间,以故事、歌谣、戏曲多种形式广泛流传,在其产生、变异、发展等很多问题上,历来论者存歧异。
李福清在其论著中首先梳理评析了此前中外孟姜女传说故事研究现状,充分肯定了上世纪五四运动时期顾颉刚发轫倡导的“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要贡献和引领作用。李福清认为,顾颉刚1924年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孟姜女的文章《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表明“正是历史学家顾颉刚首次提出了孟姜女故事问题”[7:26]。其时不仅孟姜女故事研究不为中国文人所重视,对中国民间文学,特别是对民间口头创作的科学搜集和研究,也基本属于无序和空白状态。对于西方而言,“民间文学是汉学最小的研究领域。只有中国古代神话通常会引起个别欧洲学者的关注。西方传教士某些极其肤浅的著述也都是关于中国谚语,几乎没有用欧洲语言撰写的关于中国民间故事或者歌谣的著作。德国学者艾伯华(W.Eberhard)编写的关于故事情节系统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是个例外。他将孟姜女故事列入其他情节中。”[7:40]
但是,李福清并不认同顾颉刚所持的“孟姜女故事起源于《左传》中记载的杞梁妻传说”,即“孟姜女故事起源于古籍经典,从书面典籍走向民间”之说,尽管1920年代几乎所有中国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原因在于:其一,杞梁妻与孟姜女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杞梁妻是一位恪守礼教、哀哭逝夫的武士之妻,“孟姜女则是一位万里寻夫历尽艰辛的妇女,为了不屈从于皇帝的淫威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8:190]。其二,孟姜女传说的主题是反抗暴君残酷压迫百姓修筑万里长城,《左传》中却丝毫没有体现这一内容。其三,男主人公的身份不同。史书记载的杞梁是一位攻打莒国的武士;而据大多数传说,孟姜女之夫是一位死于修造长城的儒生[7:45]。其四,孟姜女传说是以民间流传的哭长城传说[7:57]为基础,在唐代以前已经产生,盛行于唐。唐代的《同贤记》和《文选集注》中所记都来自民间口头传说。其中独有的“滴血认骨”情节,其血由苦涩的眼泪变成,是民间文学典型的借喻手法,使传说充满了巨大的感染力[7:78]。
“诗学研究主要研究体裁的特点及演化,因为体裁是古代、中世纪文学非常重要的范畴。”[9:1]《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的研究成就不仅在于这是一位域外学者通过远古文献、古诗等记载的杞梁妻形象,乐府和公元4-7世纪有关万里长城的题材传说,与唐代及后世记载、民间流传的孟姜女传说进行比较研究,就孟姜女传说来源提出一己之见,拓宽了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李福清另辟蹊径,早在1960年代,率先在国外突破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家以“历史”(史传)来考证研究民间传说故事演变[10:9]的方法论局限,提出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体裁与书面文学体裁间相互关系的演变发展特点,以及民间文学的流传更应关注历史现实背景的观点。
在李福清看来:“孟姜女传说故事实际上是在民间产生后,才进入书面文学,其情节变化也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7:31]譬如,他在“清代孟姜女故事”一章中,剖析了从民间传说进入佛教宝卷体裁中的孟姜女作品,指出,清代中国是满族统治,17世纪的反清复明运动此起彼伏。一方面,民间文学反映了这种民众的反抗;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状况也通过民间文学表现出来,出现了一系列充满神秘因素情节的民间故事,许多历史传说人物变成了佛教圣徒和菩萨。
正是基于“宝卷”浓厚的宗教特点,宝卷体裁的孟姜女传说故事从形式到主题都变调为另类“异文”。如,所有史籍传说中讲到的始皇攻侵六国,在佛教宝卷中成为:“六朝来侵……自杀自伤”,需修筑长城抵御外侵。宝卷体裁中,孟姜女传说中的反面人物也变成了蒙恬,孟姜女因为丈夫的死对他充满了仇恨。宝卷通篇对修筑长城的艰辛未及一词,范郎也非被迫,他是一位自愿替年迈的父亲应征苦力的典型儒生、孝子,就像代父从军、女扮男装的木兰;他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而儒家和佛道皆以孝为本。李福清说:“《宝卷》中的孟姜女故事竭力宣扬这一思想(孝),毫不奇怪。”[7:148]对于《宝卷》改变了自唐代以来流传的孟姜女故事情节:丈夫在结婚后三天被抓走修筑长城,被改为“尚未来得及完婚,范郎就去修城”,李福清指出:作者意在强调孟姜女的守德,“既嫁从夫”,虽然他们还未有夫妻之实。“孟姜女形象亦被重新塑造。”在《宝卷》中,她“日日焚香念佛拜菩萨;为尽孝道,和父母相守,甚至不愿出嫁。”[7:149]
巴赫金在阐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体裁特点和情节内容布局时,曾说:“体裁形式凭着自己内在的逻辑,把一切因素不可分地联结到一起”[11:157]。李福清从体裁诗学的视角,深入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更为深刻地解读了民间故事文本体裁形式中情节构成的语料内容实质。
“体裁的真正诗学只可能是体裁的社会学。”[12:182]李福清的中国民间文学体裁研究,试图纠正巴赫金从形式主义割裂作品与社会历史现实的角度对托马舍夫斯基“体裁说”的指责。他在强调形式体裁的同时,注重体裁的本体性研究,没有忽视社会历史现实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形式主义理论的疏失,也弥补了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的不足。
在李福清这部专著发表20年后,1981年,中国著名民间文学家钟敬文在为《孟姜女故事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亦指出顾颉刚研究中的欠缺:“当然,像许多学术上的优秀成果一样,在突出的成就的另一面,往往不免带有一定的缺点。这个在新文化运动后不久产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也是如此……”[13:4-5]
中国民间故事显然是一种集体传承的口头叙事之作,在传承中进入史籍、书面文学;许多成为俗文学的重要主题内容,自身又融汇了许多史籍文献、书面文学成分,并非纯粹的口头文学。在之后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三国文学体裁研究中,李福清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民间口头创作体裁与书写文学体裁的相互影响关系问题的探讨。
“中国民间创作的特点之一,在于大多举世闻名的故事情节常常在所有的民间文学体裁中都有体现。”“孟姜女传说见之于许多文学体裁。孟姜女形象传播之广,甚至用于言简意赅的谚语,所谓的歇后语中。例如:孟姜女拉刘海——哭的拉笑的。”[7:237-238]①对体裁的关注是李福清这部《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的显著特色之一。
李福清在其专著开首综述评析孟姜女传说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时,肯定了1958年出版、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下册)的价值时,也指出这部著述在体裁论述方面的不足之处。他说:“作者在历数某一时期的体裁时,没有考虑到远非所有体裁的作品都可以记录下来(凡记录者则必定会留存下来)。中国人最初的所有口头创作未必只局限于歌谣和神话。恐怕还有民间故事(众所周知,这一体裁产生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及有关祖先的传说等等。”[7:38]
正如“民间文学中某种一般观念常常不是通过一种体裁反映出来,而是贯穿于同时存在的几种体裁之中”[14:255],李福清发现,孟姜女传说故事存在于各种创作体裁,诸如:文史典籍文献、敦煌资料、变文、唐诗、宋代民间艺人的创作、戏曲创作、歌谣民歌、清代宝卷、子弟书、鼓词、弹词、文人小说等中,且有不同的表述。“如在传说中孟姜女到长城的行程叙说得很简略,而在戏曲里则很详细,因为在戏曲里,可以用各种唱腔表达人物的感情。后来我了解到,庙里常演孟姜女戏,因为她走路与死人去阴间相似”[15:3]。李福清“通过对乐府……等种种文本进行的细致、发人深思的解读,首次在汉学领域翔实地揭示出传说中的孟姜女形象和情节在体裁作品中的历代演变”[16:14],并且通过对比研究体裁差异、演变,进一步发掘出中国民间文学体裁的独特性、发展脉络和中国民间文学的特点:
其一,中国民歌体裁充满了抒情色彩,内容平实、自然,故事题材为听众喜闻乐见。从敦煌曲子词到目前最流行的各类体裁中的孟姜女形象,都能发现民歌的残篇断句。民歌中的孟姜女传说追求抒情叙事性描写,核心是表达人物情感,而不似小说重在编织故事情节。
其二,戏曲有别于民歌和神话,情节发展更完整,故事有特定的历史色彩。舞台上的宫廷、多于其他体裁的官吏和奴仆、秦始皇形象的塑造和修筑长城的场景表现等等,都证明了戏曲的历史特征,但是并非戏曲的历史性趋向使之有别于传说。中国传统戏曲常见的典型舞台表现之一,就是传说和民歌中缺乏的、可以让女主人公向观众直抒胸臆的“道路”,可以强调她去长城的艰辛。历史性还使得戏曲富有大量真实的日常生活细节。
其三,说唱文学体裁研究很难,因为内中差异涉及曲调和演唱者的风格。但是仍然可以找寻到说唱文学的某些共同点:故事情节逐渐展开,人物外貌及其活动场所的精细描写和说唱的戏剧性(如在弹词体裁的作品中,是通过引入角色类型的分配加以实现的,而这种角色分配是戏剧的典型特征)。说唱文学通常采用纯粹叙事的第三人称,布局不似戏曲有一场场和一幕幕之分。孟姜女传说广泛存在于说唱文学体裁中。
其四,最初作为佛教教义出现的宝卷是种特殊的体裁,其与佛教的联系反映在主题思想和人物特点上,因此宝卷中的传说故事甚至会彻底颠覆正反主人公的关系[7:238-239]。
此外,“故事传说中的主人公形象以各种形式诠释于各种体裁的作品中,但是其核心却或多或少地保持着统一。”[7:240]李福清将此归之于中国民间文学特有的传统性和稳固性,产生于民间,口口相传,代代相传,本真、鲜活,永远不会被全部记录下来。“尽管情节的稳固性决定于文学类型。戏曲和说唱文学体裁较之民间故事传说更为稳固”,他说:“我们看到的(孟姜女)传说故事的各种变体异文说明,民间文学作品情节可以存在上千年,却不发生根本改变。”[7:240]这也是他在本书中要解决的又一个问题:“一个故事情节在口头传说中可以存活多长时间。”李福清通过孟姜女故事的传承发展,说明了代表民族文化传统的口头传说故事巨大的生命力和中国悠久的民间文学传统,而这“用俄罗斯或其他西方民族的材料无法解决,因为没有像中国那么久远的记录”[15:3]。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中国民间文学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为李福清从“体裁诗学”的视角进行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研究提供了可能。
时至今日,李福清早在上世纪中叶就从“为中国学者所忽略的”[17:91]的体裁形式入手展开对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其独特的视角仍然给我们以诸多有益的启示。如果说普罗普以“体裁诗学“理论,对于研究故事体裁的类同性问题和故事体裁情节结构关系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因为他“找到了神奇故事的‘特殊的情节构成规律’”,提出了故事的“功能”概念。“所有的神奇故事按其结构都是同一类型。”“这一点可以解释故事的双重性质:其惊人的多样性,其多姿多彩,从另一方面看,则是亦很惊人的单一性,重复性。”[1:75]李福清则是在俄罗斯诗学体裁研究的传统上,面向中国传说故事,展开双翅,探讨同一故事在各种结构体裁中的各种形态规律、发展演变,以及相互交融影响,揭示出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独有的结构特质和不同体裁的特征含义。正是对故事文本结构的关注和一脉相承的方法论研究传统,使得两位学者看似研究的问题不同、对象不同,但问题的本质和结论能够奇妙地契合融通:普罗普眼里众多的神奇故事,情节多姿多彩,结构体裁单一重复;李福清眼里单一的孟姜女故事则是结构体裁多种多样,情节统一稳固。中国民间故事文本的特征通过不同的体裁形式显示出来。
李福清关于孟姜女故事文本的研究,不仅梳理了其形成史和发展史,揭示出孟姜女故事传说的发展轨迹、规律特点,其研究中贯穿的诗学体裁视角、历史诗学意识和历史类比方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我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全苏联的民间文学研究。”[18:9]李福清坚持“研究理论”取决于“研究材料”,他融通中西俄旧学新知,在世界人文科学领域的大框架下去把握汉学故事文本。“基于А.Н.维谢洛夫斯基、В.М.日尔蒙斯基、В.Я.普罗普、Е.М.梅列金斯基、В.М.阿列克谢耶夫、Д.С.利哈乔夫的理论观点,李福清开创了中国叙事作品与民间文学关系形成历史的研究……正是由于李福清的著述,中国学者高度评价了俄罗斯的学术经验,并接受了诸多新的理论视点和民间文学分析方法。”[19:198]
①原文是“孟姜女拉刘海——哭的拉笑的”,但笔者查证似乎多为“孟姜女拉刘海——有哭有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