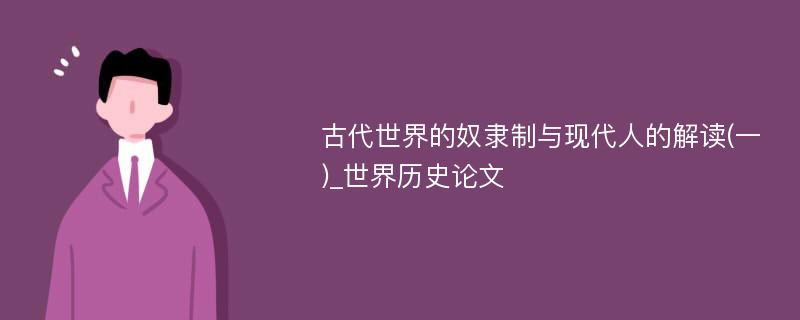
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和近现代人的诠释(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奴隶制论文,现代人论文,古代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一度作为中外史学研究热点的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反复不定的争论之后,已令新老参与者疲惫不堪。对于不大情愿受传统解释体系束缚的我国新生代的史学工作者而言,它似乎是一个陈旧过时、只有形而上学的思辨意义的课题象征。对于国外古史学界来说,它则是一个已被可以观察的证据加以验证并形成定论的问题,失去了讨论的必要。然而一个史学论题的提出,自有它被提出的原因和存在的价值,何况像奴隶制社会普遍说这样一个得到东西方学者广泛持久关注的世纪性论题。因此在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前夕,即使出于敝帚自珍和继往开来的目的,对这个论题进行一番梳理和反思也是必要的。
一、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奴隶制认识的基本线索
(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
奴隶制社会普遍说是一个道地的西方观念,是西方人经验的历史作用于西方一些思想家头脑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由局部经验归纳并进而演绎出的科学假说。
奴隶制曾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制度,现在也没有完全变为历史陈迹,但只有西方人,才两次把它发展到极端。一次在古代:希腊、罗马人曾在古代主要经济部门农业和辅助部门手工业及商业中大规模役使奴隶,并因而出现繁荣的奴隶贸易和世界史上独有的三次独立的奴隶大起义。一次是在中古晚期和近代:西方殖民者(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曾经在新大陆把对人的奴役推到空前绝后的水平,先后役使的黑奴、白奴、印第安人奴隶总数至少在6000万以上(注: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史》( L.S.Stavrianos,A
GlobalHistory),新泽西1988年版,第450、564—565页。作者估计仅供应美洲种植园经济的非洲黑奴便达4千万人,其中3千万在贩奴途中死亡。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奴役的印第安人数目无法估计。),写下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中最丑恶、最黑暗的一页。
由于奴隶制在西方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所以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西方人,对奴隶制的记载和研究可谓史不绝书。在传下来的古典著作中,有关奴隶制的段落之多,远非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典籍可以相比。古希腊、罗马人对奴隶制起源、奴隶的定义、奴隶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合理或不合理性探讨的深度和广度,也堪称古代世界之最(注:参见多瓦杜尔:《公元前6—5世纪阿提卡的奴隶制》(А.И.Доватур,Рабство в Аттикев Ⅵ—Ⅴвв.дон.з.),列宁格勒1980年版,第106页以次对希腊思想家的相关认识有详细的论述。古罗马人(如瓦罗)及一些法学家们也有与希腊人相似的论述。反观古代东方,一直缺少较为详细的讨论,以有最多文字史料的古代中国为例,日知先生考证《论语》只有一处提到奴隶字样(见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而近现代西方人对奴隶制的思考和研究则更胜于他们的前辈,废奴主义运动还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奴隶制的后遗症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严重弊病之一(注:1998年风靡美国影坛的优秀影片除《拯救大兵瑞恩》外,还有由著名电视主持人奥坡拉主演的反映美国黑奴血泪史的《珍爱》(Beloved)。 这种奴隶制情结是非西方人所难以体会的。)。如此大规模的、一古一今奴隶制的客观存在,成为每一个反思自身历史的西方思想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正是西方人的奴隶制普遍说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也是包括原苏联在内的欧美史学界热衷于反省奴隶制问题的根本原因(注:西方对古代和近代奴隶制的研究仍然在继续,参见拙文:《奴隶制:一个历久未衰的论题》,载《世界史研究年刊》第2期(1996年)。)。
但西方人用奴隶制来标志人类史的某个特定阶段则只是近代的事。古希腊和罗马人虽已具有普遍联系的历史意识,并产生了明确的历史阶段性运动的观点(注:如赫希俄德的黄金时代到铁器时代的五段式,亚里斯多德家庭、村坊到城邦的三段式,卢克莱修的石器、青铜器、铁器时代的三段式,波里比乌斯的君主制到极端民主制的六段式,等等。),懂得用一些他们眼中的时代特征(工具、政体和社会组织形式等)来标记各个历史段落,却从未想到把奴隶制同某个历史阶段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后来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革,古代奴隶制也随着奴隶制的逐渐消亡而被中世纪的神学家置于视野之外。
西方人重提古代奴隶制问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对发现古典文化的人文主义者来说,奴隶制是灿烂的古典文化的必要伴随物。据德国史家沃格特考证,第一个提出并讨论古代奴隶制成因问题的是那不勒斯学院院长彭塔诺(注:沃格特:《古代的奴隶制和关于人的思想》(JosephVogt,Ancient Slavery and the Ideal of Man), 巴塞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74年版,第193页。),托马斯·莫尔、 皮格诺里亚等人也注意到了奴隶制(注:沃格特:《古代的奴隶制和关于人的思想》,第190—200页。)。但此时的人文主义者在古代奴隶制的认识上并没有超出古希腊和罗马主流思想家为奴隶制辩护的认识局限,因为那是在一个对刚刚“出土”不久的古典充满敬意甚至崇拜的时代。温和的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改朝换代的雄心壮志,古代奴隶制问题所具有的现实批判意义尚未被他们发现。因此莫尔的《乌托邦》同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把奴隶当作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注:当然同古代一样,也有极少数的反对蛮族人为天生奴隶的人文主义者。参见沃格特:《古代的奴隶制和关于人的思想》,第198页。)。
对古代奴隶制的真正研究始于启蒙时代。这个时代是资产阶级渴望摆脱封建压迫、夺取政权的时代,启蒙思想家高扬的理性、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道等社会政治理念,与以人身奴役为特征的奴隶制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古代和近代的奴隶制便当然地成为启蒙主义者激烈抨击的目标,奴隶起义的英雄也因而成为争取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榜样。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用很大的篇幅提出并分析了古代奴隶制和近代黑奴制的起源、弊端、类型等问题,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法和民法,是少数懒惰、富裕和骄奢淫逸的人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一种无益的制度,是民法应消除的弊端(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洛克的《政府论》表达了同样的反奴隶制意识,认为奴役权是非法荒谬的,“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可恶而悲惨的人类状态”(注: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20页;洛克:《政府论》,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页。)。同样的思想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回应。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米勒、亚当·斯密均认为使用奴隶在经济上代价昂贵,奴隶劳动效率低下,排挤自由人劳动,造成奴隶主家庭成员道德上的腐败堕落(注: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M.I.Finley,Ancient Slaveryand Modem Ideology),企鹅书社1980年版,第28页以次。)。这种从人道、法律和经济角度对奴隶制的批评定下了启蒙主义思潮对奴隶制认识的基调。但也并非完全如此。
在启蒙运动开展相对晚后和薄弱的德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学术界比较注重材料的扎实稳妥,观点的圆熟严谨,缺少法国学者的愤慨激扬的精神,所以对古代奴隶制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评估。法学教授雷特梅埃尔在1789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奴隶制消极面的同时,也肯定奴隶劳动具有一定的积极面,即经济上低廉,补充了劳动力的不足。舒伯尔特和封·汉姆伯尔特则从分工和文明进步的角度分析古代奴隶制的积极意义,认为奴隶制是古典文明的必要前提,其出现减轻了自由人的劳动负担,从而使前者有闲暇从事文化活动(注: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第36页以次,第56页。另见法国史家伽兰:《古希腊的奴隶制》(Yvon Garlan,Slavery in Ancient Greece),勒伊德译,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沃格特:《古代的奴隶制和关于人的思想》,第170—171页。)。30多年后,黑格尔则在其《历史哲学》中继承了雷特梅埃尔等人的价值评估,认为奴隶制是古代民主政治的必要前提(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99—300页。),使这种对古代奴隶制的价值评定带有了显著的德国味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古代奴隶制的辩证认识显然与这类看法有一定的继承联系(注:马克思晚年读过雷特梅埃尔的著作,参见阿多拉茨基编:《马克思年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2页。)。
同知识界对奴隶制的关注相一致,18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也开始在自己的史作中对古典奴隶制做一些初步的复原和诠释的工作(注:18世纪最优秀的史冢吉本可以作为代表。见其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黄宜思、黄雨石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41页。),但那只是他们政治史主题的微不足道的陪衬,没有引起尚处在业余状态的西方史学界的足够重视。但这个时期有一位史家的观点对我们的论题有开创的意义,这就是英国史家兼哲学家休谟在1752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古代各民族的人口密度》中的那句话:“古代人家庭经济与近代人家庭经济的主要区别在于奴隶制的应用”(注: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第30页。)。古代经济在这里首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被贴上了奴隶制的标签。休谟同时也是第一位对雅典尼乌斯提供的古希腊人庞大的奴隶数字提出怀疑的人(注:威斯特曼:《古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W.L.Westerman,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Roman Antiquity),费城1955年版,第7页;多瓦杜尔:《公元前6—5世纪阿提卡的奴隶制》,第30页。),但因批判考据的方法在此时尚未成气候,所以他的看法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
启蒙时代反奴隶制的思想在18世纪后期转化为社会政治领域的废奴主义运动。古代的奴隶制成为这一运动的历史依据。1792年,小皮特在英国国会中的废奴演说第一次赢得了多数议员的赞同,其中一个最雄辩感人的段落就是把近代非洲黑奴的命运同古代不列颠人在罗马奴隶市场上的命运进行了比较(注:见沃格特:《古代的奴隶制和关于人的思想》,第205页。)。在强烈的废奴思潮的冲击下,1794年, 法国议会通过解放法国领地上的所有奴隶的议案。1807年,英国废除奴隶贸易。1830年,巴黎竖起古代奴隶起义的英雄斯巴达克的雕像。同年英属殖民地的奴隶制被彻底取消。美国南部和南美的奴隶制从此成为废奴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
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史学,史家对自己课题的选择、材料的取舍、探索的角度和结论的归纳虽处处浸淫着自己的个性,但也显示他所处的时代的需求、期待和印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点也明显反映在近代奴隶制史的研究中。随着19世纪前半叶废奴运动的高涨,古代奴隶制受到已经完成专业化进程的19世纪西方史家们的广泛注意,成为古希腊和罗马史的基本内容之一。以当时西欧最著名的几位史家为例,德国史家蒙森在其获奖著作《罗马史》中,“从一开始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奴隶制处理为罗马社会和历史的基础”(注: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第34页。)。另一德国大史家伯克在其《雅典国家经济》一书中则对奴隶劳动进行了详细论证,否定休谟的怀疑,认为雅典蓄奴40万的古代记载是可信的(注:多瓦杜尔:《公元前6—5世纪阿提卡的奴隶制》,第30—31页。)。而英国史家格罗特在其《希腊史》大作中则把奴隶和依附人的劳动看作是古希腊大多数地区生产的基础(注:格罗特:《希腊史》(G.Grote,A History of Greece)第2卷,伦敦1862年版,第59页。)。
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导引下,西方史学界于1847年问世了第一部系统复原和诠释古典世界奴隶制的专著,即法国史家瓦龙的《古典世界的奴隶制史》。该书产生的直接原因颇值得注意。1837年,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拟定了两个资助研究的课题:1.古代奴隶制因何种原因被废除?2.在什么时代西欧奴隶制消失而仅存有隶农制(注:库基辛:《作为经济体制的古典奴隶制》(В.И.Кузищин,Античное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рабство как я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沃格特:《古代的奴隶制和关于人的思想》,第172页;芬利:《古代的奴隶制与近代的思想意识》,第31页。)?这两个课题本身表明西欧学术界已充分认识到古代奴隶制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在此稍前(1827年),德国史家克鲁泽尔在法国讲学期间所作的关于“古代罗马奴隶制概述”的报告中(9年后公开发表), 已提出“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它把异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离开来”(注: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第27页。)。这即是说,在19世纪30年代,休谟提出的奴隶制为历史分期鲜明标志的看法,已成为西方学术界的前沿性认识。而瓦龙的三卷本大作则对这一宏观认识提供了史实依据。瓦龙从明确的古为今用和废奴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为参照系,对德国学者肯定古代奴隶制的积极作用的做法进行了激烈抨击,指出奴隶制毁灭民族、腐蚀道德、破坏家庭和国家、损害进步和理智的发展,总之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决定古典文明衰落的根源(注:沃格特:《古代的奴隶制和关于人的思想》,第172—174页。)。他在论证自己基本观点的过程中,详细考察了奴隶制的起源、奴隶来源、奴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奴隶的种类、价格、数量,从而奠定了20世纪古典奴隶制问题讨论的各个分支课题的基础。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代表着西方古代奴隶制研究的顶峰,在史料的收集规模上维持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领先地位,但瓦龙史料考据的功夫却并不到家,没有超越人文主义史家一般对古典史料盲目信任的水平。
瓦龙之后,由于近代奴隶制已为西方各国所普遍废除,所以西欧学界在道义和人性方面对古代和近代奴隶制所进行的激忿谴责也随之淡化,而经济史研究则成为古代史学的热门方向,尤其对处于鼎盛时期的德国专业史学以及经济学界更是如此。关注古代奴隶制的史家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奴隶劳动在生产中的位置、得失利弊等课题之上,而欲确定奴隶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就需要确定不同类型的奴隶数量,于是古希腊奴隶的数量得到了热烈的讨论。谙熟尼布尔、兰克考据辨伪方法的德国史家在这方面用功最勤,其典型代表是19世纪末的古史大家彼洛赫和迈尔。他们将休谟的怀疑变为具体的考证,根据对雅典输入粮食的数量、自由人和奴隶人口的零星数据的细心分析,认为雅典尼乌斯提供的数字严重失实,雅典奴隶的总人数应当在10万以下(彼洛赫认为在7 万左右)(注:多瓦杜尔:《公元前6—4世纪阿提卡的奴隶制》,第29—50页。)。由此两人均认为奴隶制在生产中仅起辅助作用,公民小生产者和雇工的劳动占有优势(注:阿甫基耶夫等主编:《古希腊史》(В.И.А.вдиев,А.Г.иВОКШАНИН,Н.Н.Пикус,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и Гредии),莫斯科1972年版,第405—406页。)。
在客观主义高奏凯歌的德国专业史学精心考证具体的史实的同时,德国经济学家们却在从比较抽象的角度从事他们自己的研究,这就是力求建立“科学”的经济史演化模式。他们普遍把古代经济作为初始的经济类型之一,并试图找出这一类型同中世纪和近代模式的不同之处,于是奴隶制便得到了特殊的注意。芬利对此曾评述道:“社会历史中的阶段观念(或时期观念)是由经济的组织方式——财产、生产与分配所限定或决定的,这是一种新的认识。这种历史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对古代社会范围内的奴隶制予以较先前任何时候都要更多的强调,赋予它更加复杂的作用。”(注: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第39—40页。)德国经济学家罗斯策在自己设计的经济演进模式中(1849年)就坚持了休谟谟以奴隶制为古代家庭经济与近代家庭经济分期的标准;同样企图构建经济进化模式的经济学家布赫则把奴隶制作为判断古典世界(希腊、罗马和迦太基三地)具有最发达的家庭经济的基本条件(注:布赫将经济发展划分成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自给自足的城市经济、国民经济三个阶段, 见伯尔克斯坦:《希腊黄金时代的经济生活》(H.Bolkestein,Economic Life in Greece's Golden Age),莱顿1957年版,第148页;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第40、43页。)。而另一位以形态分类方法研究经济史的马克斯·韦伯则在1896年发表的《古代文明衰落的基础》一文中指出:“古代文明是奴隶制文明……如同在中世纪一样,人类协作劳动的两种形式(指自由劳动和非自由劳动——本文作者注)之间的对立也存在于古代。”(注:芬利:《古代的奴隶制和近代的思想意识》,第44页。)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19世纪末叶之前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西方奴隶制认识的基本线索做一个简要的小结了:1.如同古代西方人因自身的需要创造了奴隶制一样,古代奴隶制问题是因近代西方人自身的需要而提出来的;2.将奴隶制处理为一个时空范围相当大的历史阶段、经济类型或文明形态的基本标志的做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及其同代以及之后均已有过尝试。但有一点与20世纪不同,就是提出和论述这种宏观认识的人绝大多数不是致力于考据和实证研究的专业史家,而是具有比较宏观目光的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这同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学界为寻求历史规律而对人类历史进行宏观研究的时代趋向紧密联系在一起;3.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学者笔下的“古代”专指古典古代(德文为antike,英文为antiquity),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但在国内可以找到的英译本中我们也看到有时用的是泛指的“古代的”(ancient)一词,如上引韦伯的论述。所以,倘若是身处19 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的话,那不是出于他们的凭空想像或是他们的一家之言,而是采摘了19世纪西方学术之树结出的现成果实并对它们多少有所发展而已(注: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中学时便熟识拉丁文、古希腊文,阅读过众多古典作家的作品,终生保持着对古代典籍的阅读习惯,同时也熟悉上面列举的大部分近代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家的著作,他们对奴隶制认识正像他们的其他认识一样,是在西方现成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马克思主义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的提出和发展
奴隶制普遍说是怎样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个史学史问题一直是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关注的课题。参与古代社会性质讨论的东西方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包括原苏联东欧、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史学)无论有多少众人之手的一种“层累”的理论陈述,大体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列宁和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有关诠释,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的再诠释这样一系列成分逐渐积淀而成。正因为如此,各国学者把很大精力用在对这一“层累”理论的各个沉积层面的剥离清理工作上。
经过长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钩沉索隐、穷原竟委的研究,有关材料的收集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但人们对同一些白纸黑字的理解却仍然相去甚远,歧见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比如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句名言,就有传统五形态单线说、一元双线说、一元三线说等多种诠释,这还不包括三形态、二形态等其他另辟蹊径的说法。因此,问题讨论了半个多世纪,奴隶制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演进模式中是否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仍是悬案。归纳起来,各家看法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认为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在自己的社会形态模式中提出过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一元单线的五形态说,现有说法是由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首次提出、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加以确定的(注:国内代表性看法可参见胡钟达先生的论文:《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香港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29页。国外一般认为斯大林是始作俑者,参见帕德古:《关于奴隶制和奴隶社会的一些理论问题》,转引自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23页注释1; 另见捷尔—阿柯宾:《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农村公社看法的发展》,载《亚非人民》(Народы Азиии Африки)1965年第2、3期。)。持这一看法的学者在国外居多,在国内也不在少数。再一类则坚持传统五形态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思想的最合理诠释(注:我国传统解释的辩护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研读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原苏联学者相对更为仔细,因此有关论证更为扎实,见田昌五:《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八章“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周怡天:《关于奴隶制社会的若干札记》,载胡庆钧、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国外论证见尼基福罗夫:《东方和世界史》(В.Н.Никифоров,Восток всемирная истрия),莫斯科1975年版,第113—149页。)。
各种解释之间存在的差异表明,以奴隶制社会为基本环节之一的传统五形态说确实难以满足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古代史的认知需求,因而需要重新加以认识。同时也说明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断并不像我们通常想像的那样简单。问题的难度在于具有终极解释权的马克思恩格斯均已故去,他们的有关论述明摆在那里却自己不会说话。因此参与讨论的每位解释者都必须通过个人的阅读去感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文本的内涵及其表达的基本思想。
从理论上讲,对同一处论述的真实解读应当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解释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思想与文本的交互作用,在头脑中重构或复原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本来思想,从而实现准确领会文本含义的目的。但在实际解读过程中,认识主体(有意歪曲原意者除外)对作品原义予以准确重构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一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
就主观条件而言,解读者是否具备正确领会文本含义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解读者是否对与文本内涵相关的语境(哲学、经济学、历史、德俄文等等)有足够的了解,或在解读过程中认识主体是否做到了小心谨慎,注意到所有给定的条件等等,都对正确解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客观条件而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是否存在一些不甚明确的表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以及两个之间对同一个论题阐释的角度和论点之间是否存在出入,或各个文本的思路虽有清晰可辨的线条,表述也严谨贯通,但因含义深刻,内涵丰富,专门术语和背景知识过多,以及中文译本的误译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解读者的困惑和误读。特别是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性质的说法,缺乏定理式的明确陈述,有多个相异的前提条件,涉及复杂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历史背景,而文本作者又不能出面澄清这种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各种解读都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来最终验证其理解的合理性,从而导致各种诠释中尽管可能包含相对最为忠实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义的理解,却没有任何人有权说自己的诠释是惟一正确的诠释,这同音乐界中“有十个指挥家,就有十个贝多芬”的说法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某位指挥的诠释做出最忠实于原作的价值评判。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传统五形态说还是更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思想。对此,国内外学者已有详细论证(注:一个通行的概念或术语往往形成于它所概括的事物出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如民主、历史哲学的概念都是后来问世的。所以没有明确说过“奴隶占有制社会”之类的术语不等于没有这样的思想。),笔者提不出什么新的论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述的“更接近于”并非是“等同于”,理由有二:
首先,传统五形态模式的陈述毕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陈述不同,带有后人诠释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没有从普遍意义上使用过“奴隶制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奴隶制社会经济形态”这样的术语,只是谈到过古代社会、古代国家、古代经济、古代生产的“基础”是奴隶制,奴隶制是古代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支配形态”、“广阔基础”等等。但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在社会形态进化的有序性中去注意和讨论奴隶制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列举的三大奴役形式有明确的先后次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序言》中的那段话若与前面对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简要地表述”之间联系起来看,以及考虑到其中关于五种形态的话语表述本身的链接关系,将“亚细亚的、古代的……”理解为依次更替的单线序列要更符合逻辑。如果再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社会形态”、“各个世代”这样一些大型历史过程时,总是喜欢使用“依次交替”、“依次更迭”、“过程的连续系列”之类的用语,我们可以认为周怡天先生据德文本《资本论》第3卷所考出的证据(注:胡庆钧、 廖学盛主编:《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第23—25页。),即“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对应“原始共同体”、“古代的”对应奴隶制的传统解释就显得更为合理一些,至少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古代”的生产方式。
其次,马克思的主要陈述同后来列宁、斯大林的陈述在语气上有明显的差异,国内外的学者都广泛注意到这一点,这就是马克思的语气往往是提示性的、大概的(suggestive),而不是权威性的、 确定的(definitive),比如那段五形态的典型陈述就做过一个事先的提示“大体说来”,这一点非常重要。马克思的这种留有余地的态度是一种科学探讨的态度,而现存的五形态说或“五项公式”被列宁、斯大林处理成毋庸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或规律,这是与马克思的态度有所区别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种僵化机械的处理方法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他指出社会历史的资料非常匮乏,根本不能同有机界相比,所以在这个领域中的认识“本质上是相对的”,“暂时的”,“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8—129页。)列宁和斯大林的解释恰恰犯了绝对化的毛病。这个毛病当然不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负责。从这个意义上说,视列宁为绝对化的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的最初倡导者、斯大林为最终确立者的说法是正确的。
列宁在1919年发表的即兴演说《论国家》中首次明确化了五形态说,并且使用了目前标准的术语“奴隶占有制社会”来标志阶级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6页。胡钟达先生对列宁的演说有绝好的考证,他证明发表的演说记录没有得到列宁的审订,而列宁对自己讲话记录向来是不满意的,见胡钟达:《胡钟达史学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227页。)。但当时这个演说并没有在苏联学术界产生任何反响,因为它没有发表,也没有作为内部文件在党内外传达。
1917年至1935年左右是原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时期,学术界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需要分析归纳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思想的脉理,而这种初始的工作又与现实的政治需求联系在一起。20年代末,苏联理论界因确定东方社会性质、主要是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需要而展开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一次讨论。苏联世界古代史学界也参与其中。与政治理论界斯大林派和托派的激烈思想交锋甚至政治冲突有所不同,古代史学界着眼于远离现实的古代东方,所以讨论气氛还是相当民主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尽管在1929年为了配合讨论,《真理报》发表了列宁《论国家》的记录稿,但苏联古史学界大多数人仍敢于坚持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的传统认识,这其中不仅有古史专家赫瓦斯托夫、图拉耶夫、尼科尔斯基,还包括在奴隶制普遍说发展史上颇为有名的斯特卢威(注: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В.Д.Неронова Хормы экспруатации в древнем мире взеркале советскойисториграфии),贝尔米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尼基福罗夫:《东方和世界史》,第176—177页。)。但斯特卢威与其他人有所不同,他的观点变化很大。讨论之初,他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后来又回到封建生产方式的立场。而到了1933年,他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又成为第一个论证古代东方为奴隶制社会的史家。他在报告中指出:“根据我们掌握的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的史料,古代东方的经济结构是奴隶制的结构。”(注: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第22页。)这个论断以及相应的论证为当时极端缺乏史料支持的泛奴隶制社会的说法提供了所谓的史实依据。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对上古阶级社会的论述(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出自古典材料,所以他们关于古希腊罗马为奴隶制社会的认识可以说是在具体分析了古典社会的一些样本之后通过归纳逻辑得出来的,并非是一些人说的纯粹思辨的产物。形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尽可能收集样本材料,特别是要为整个世界划定一个统一的形态模式,需要收集古代世界各个文明地区的样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看,他们在利用古典文献材料方面,与当时的专业史家基本处在同一水平。但在古代东方史方面,他们却只能利用为数很少的三四手史料,并非古代东方的文献和实物史料,也几乎没能利用当时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等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这意味着对于古代东方的社会经济形态,他们极端缺乏可靠的样本。由于证据不足,马克思、恩格斯(尤其是马克思)在做宏观结论的时候才非常注意分寸,不把话说绝,所以我们在本文开头才提出他们关于奴隶社会普遍性的认识是在归纳逻辑基础上通过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一种科学假说。
后来列宁在《论国家》中虽然说几十几百个国家都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社会,但从《列宁全集》中也看不出作者曾经做过几十几百个样本的收集整理工作。所以斯特卢威的结论对奴隶制社会普遍说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是第一个从社会形态角度、利用亚述学和埃及学史料论证古代东方为奴隶制社会的史家,并且是第一个从专业史学角度论证奴隶制社会形态的基本条件是奴隶劳动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的人,这就为后来由斯大林确立绝对化的奴隶制普遍说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史学基础。
不过斯特卢威的看法在发表时和发表后一段时间(1934年)还只是苏联史学界的一家之说,受到广泛的批评。多数学者认为古典世界是奴隶制社会,古代东方是封建社会(注:在发表列宁的演说之前,苏联史家对于古典社会性质的认识均倾向于迈尔的古代资本主义经济或传统的封建经济的认识。在演说发表之后,苏史家接受了社会形态概念,并认为古典世界是奴隶制社会形态,但东方不是。鸠梅涅夫、科瓦列夫等均持这种观点。见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第34页。)。尼科尔斯基指出斯特卢威扩大了奴隶的定义,把不属于奴隶的劳动者,如乌尔第三王朝王室大地产中的劳动者“古鲁什”当成了奴隶。卢利叶、鸠梅涅夫、别列表尔金、科瓦列夫等人则分别指出古代埃及社会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农奴制或其他依附人制,斯特卢威关于古代埃及从事灌溉工程的劳动者是奴隶、希腊斯巴达、克里特、帖撒利的依附人是奴隶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注:涅罗诺娃:《苏联历史学领域中的古代世界诸剥削形态》,第27—31页。)。
但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在1934年底基洛夫遇刺后中断,政治大清洗运动和随之而来的个人崇拜导致思想领域的一言堂,行政领导的指示代替了学术讨论,个人意志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并不一定被列宁认可的列宁关于社会形态更迭理论的陈述成为惟一正确的解释,斯特卢威的论证很自然地得到了官方的确认。作为这一发展的逻辑结果,1938年发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正式将包括奴隶制社会在内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模式规定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公式。
据原苏军总政副主任、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所述(注: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2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77页以次。), 这本书是由历史学家克诺林(在该书未完成前被捕)、波斯佩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根据1937年4月16 日政治局决议全力赶写出来的。它的指导思想是斯大林制定的党史分期提纲以及他确定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主线。后来斯大林在收到各次样稿后做了多处修改,最后三章总共只有70多页,却有60多条斯大林的评语、引文和结论……集中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诠释,所以斯大林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宣言歌之歌。”(注: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2卷,第581页。)因而如果说绝对化的奴隶制社会普遍说是由斯大林最终确立的,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反思起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奴隶制社会普遍说从苏联向国外的广泛传播、并因而成为国际性的史学问题这一点起了决定作用。由于本世纪上半叶各国共产党人的主要精力集中于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遍准备不足,因此这本小书就以它浅显易懂、提纲挈领的陈述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培训党员理论修养的标准教科书。人们不必研读原著,翻阅参考读物,不必进行认真的思考,一切在这里都有泾渭分明的明确表述。而且书中的每一章结尾都有一节定理式的“简短的结论”,人们只要牢记书中的各种“原理”,就似乎等于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本书仅在原苏联就出了300多版, 约4300万册(注: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2卷,第576页。)。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国共产党内的印数也不会小于这个数字。它以速成的方式培养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但也使几代马克思主义者将该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断章取义的误读和曲解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苏共党史。这样一来,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就上升到科学规律的地位,成为所有接受马克思主义ABC 课程教育的人背得烂熟的定理之一(注:《苏联共产党(布)简明历史教程》无疑对普及马克思主义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其消极面也不容忽视,这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学说高度机械化、教条化和简单化,造成了精神的贫乏、理论的简单化,使许多人误以为该书中的定理即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党的历史的主线便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直到苏联解体前,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古代史和地区古代史都是按照这一解释范式编写的,其典型代表、也是对各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示范性影响的著作便是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第一、二卷(1955—1956年),书中把奴隶占有制社会看作世界历史发展的主导线索,是历史发展统一性和规律性的体现(注:见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1卷, 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35—42页。)。
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同列宁、斯大林尽管在定性语气和表述的明确性方面有程度的差别,但在奴隶制社会的定性标准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数量”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奴隶制社会即意味着奴隶劳动大规模排挤了自由人劳动、奴隶制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基础中占有支配或统治的地位,决定了社会阶级结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基本属性(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数量的标准有很好的说明。为此他还援引了错误的史料,即在希腊的一些城邦,奴隶人数均达40万以上,平均每个自由人有10个奴隶。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0页。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重复了这一标准。马克思审议过《反杜林论》,并参与了其中一章的写作,所以书中的意见代表两人的观点。)。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奴隶制社会的解释均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奴隶制社会的定性标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质是一事物区别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具有明确的内容和清晰的外在表现,而这种外在表现就是一定的量(规模、程度、等级、层次等等)。所以量与质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定的量,就不会有一定的质,量是质的存在方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时总是使用了规模量和程度量,即奴隶数量的增多、农民人口被奴隶人口所排挤。这种处理方法显然比后来为奴隶制普遍说辩护的学者孤立使用的“质”的标准要好得多,它的前提是必须有历史事实的充分支持。而遗憾的是,这恰恰是“量”的标准的致命弱点,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争论,归根结底正是基于古代奴隶制量的事实对普遍说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