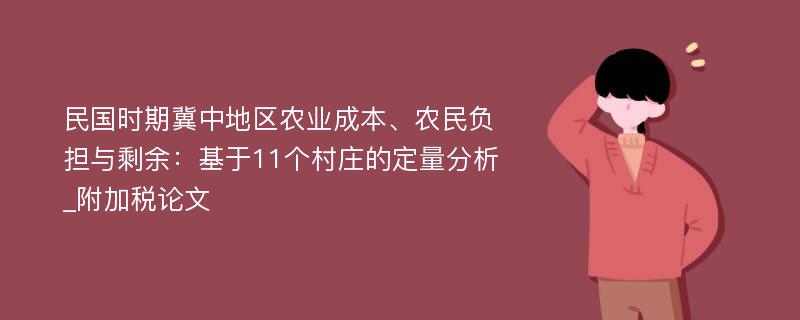
民国年间冀中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与剩余——来自11村的一项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冀中论文,农户论文,民国论文,年间论文,剩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成本、农户负担以及农民家庭的劳动剩余,直接关乎农业效率与农业再生产,至今仍然是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根据陈翰笙先生30年代保定(清苑)农村调查统计资料和解放后河北省统计局追踪调查统计资料(注:陈翰笙先生1930年进行的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统计局50年代所做的关于1936年、1946年两个时点的追踪调查统计资料见《二十八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河北省统计局,1958年。本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于此,特此说明。保定农村实际指清苑农村。),力求反映这一时期冀中农村的上述指标状况。
一、生产费用
中国传统农业固然是以人力为主,但并非纯粹劳动密集型生产。清代农学家已注意到耕作成本,章谦在《备荒通论》中说:“一亩之田……籽种有费,雇募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千钱。”顾炎武说,苏南“类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1]。
清苑农村调查资料表明,农作物生产费用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籽费、肥料费、农具费、农舍费等项。雇工费指雇工的工资,犒赏及衣物等杂项还不包括在内。耕畜费包括耕畜资本息(以耕畜总价值的年利8%折算)和饲养费。种籽费包括自有的与购买的两项费用。肥料费仅就购买的部分而言,实际上自制的土肥占多数。农具费包括折旧费(依农具价值的8%折旧率计算)与修理费两项。农舍费包括修缮和部分租金等。根据上述统计范围,1930年清苑农民家庭农场平均每亩生产费用如下表:
1930年清苑平均每亩生产费用支出
单位:元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平均
雇工
1.50
1.55
0.37
0.08
-
0.65
耕畜
0.12
0.16
0.11
0.08
0.01
0.10
种籽
0.76
0.62
0.69
0.63
0.66
0.67
肥料
0.32
0.60
0.54 0.23
0.23
0.36
农具
0.20
0.25
0.22
0.16
0.25
0.21
其他
0.12
0.19
0.19
0.37
1.01
0.21
总计
3.02
3.37
1.98
1.51
1.15
2.20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2期,1936。
从上表可见,中农平均每亩生产费用1.98元。当时清苑1亩地粮食收获价值为8.1元,所以生产成本大约相当于其产值的1/4。在农户实际支出的每亩生产费1.98元中,种籽费用最高,占30%;雇工费次之,占29%;再次为肥料费、农具费等。较富裕农户的生产支出中,雇工的费用大些,开销占第一位,但种籽费仍居第二位,而且其他方面的投入同样不足。投入产出之比与清代农业相去不远,表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与经营仍然处于比较传统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中,没有多少变化。
按照上述清苑每亩生产成本1.98元的数据,又知中农粮食种植面积为18.68亩,那么一个中等农户粮食的生产成本即为36.99元。按户计算,还须加上棉田生产费用的支出。30年代“满铁”在冀东的一项调查表明,棉田生产费用支出比较高,肥料、雇工费等大约每亩支出6.3元[2]。上面曾推算中农的植棉面积为1.32亩,那么棉田费用支出即为8.32元。粮、棉田合计,一个中等农户的农作物生产费用支出为36.99+8.32=45.31元。按此计算,生产费用相当于农作物(包括棉花)总收入(167.31元)的27.08%。
张培刚利用1930年的清苑调查资料,也做了一项以农户为单位(不是以每亩为单位)的生产性支出统计。生产费也是包括雇工费、耕畜费、种籽费等若干项,每农户田场支出多少,随田场经营规模大小而不同。他以500家农户取样为例,在田场的各项支出中,仍然是种籽费和雇工费所占比例最高,与前面平均每亩生产费用的比例及其特点,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按照平均每家生产性支出的统计,并以中农为样本户,每年生产费用为50.26元[3]。巧得很,此数据与笔者按单项数据所作的中等农户生产支出的估算(即45.31元)非常接近。
上述生产成本,都未计入家庭自身劳动力的投入,清苑调查也没有做这方面的专门统计。不过,根据调查资料中提供的有关数据,可以试着进行一下这方面的间接推算,以期得出一个基本概念。1930年清苑11村共有耕地41514.36亩。而当年参加农田劳动的长住人数共3524人(常住劳动力6979人,参加农田劳动的人数占其50.4%)。参加农田耕作的劳动者可能有临时外来的雇工,同时也可能有临时外出打工的本村人,如果假定打工者流出与流入的数量相当,那么可以认为11村田间耕作者的总人数不变。农业劳作有季节性闲置,一般每个劳动者实际上全年平均131.9个劳动日[4],以不变劳动日利用率计,3524个常住农田劳动力可折合464815.6个劳动日,或者说同等数量的人工数。这些人工数分布在耕地总面积后,平均每亩投入的人工数为11.20个。据估算,清苑三四十年代的复种指数已达126%,即11村的实际播种面积为52308.09亩。按播种面积计算,平均每播亩投入的人工数为8.89个。如果将投入的所有劳动力皆折为货币(包括自家劳动力的投入),生产成本则是其产值的68.40%。
卜凯统计,华北三省农民平均每亩农作物产值为9.59950元,每亩的经营费用(种籽、肥料、牲畜、人工)约占每亩产值的80%以上,以80%计,每亩生产费为7.6760元[5]。
韩德章统计,深泽县梨元村28个田场,平均每个田场每作物亩农业之收入为11.657元,各项费用为10.248元,占每亩农作物收入的87.91%[6]。
二、农民实际负担
租税等赋役负担是农民家庭的另一支出,而且是一项最为不稳定的支出。
先说地租负担。租入耕地者绝大部分是下层贫苦农民,也有一部分中农,为了生活不得不在苛刻的条件下租入土地。租佃前,一般是租佃双方先订立契约,说明所租耕地位置、亩数、租额及地租交纳的办法。如佃户经济条件尚好,也有不订契约,只有口头协议便租种土地的。订约一般在白露前后,租期大多为一年,长期租佃的很少,这样有利于佃主收回土地或抬高租金。地租形式以定租为多,分成租很少。分成租中,如佃主提供牲畜、种子、肥料等,则依提供数量的多少而有主6佃4、主7佃3或主8佃2的分别。在通常实行的定额租中,地租的主要形式还是实物地租。但到1930-1936年间,货币地租占有主导地位,实物地租逐渐减少。1936年后,由于币值暴跌,物价不稳,实物地租又重新流行起来。
货币地租的数量在清苑1930-1936年间,多为3~5元,地租大约占收获量的一半。上缴政府的田赋等一般由佃主担负,1937年后因捐税更加繁重,所以有时佃户还要承担一部分田赋或杂税。关于地租额,当时河北省普遍采取对分制,一部分县按主6佃4比例分配产品,如赵县、大兴、宛平、苏县等。从全国情况看,各地地租额或轻或重不等,对分制仍是比较普遍采用的主佃分成比例。对30年代15省60县的地租率进行的一项统计表明,每亩地租额占产量一半以上者共34县,占统计总数的56.6%[7],可见30年代各省的地租还是比较重的。而且,主佃之间仍然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佃户年年要给地主送鸡鸭、水果等贡品,义务当马夫、车夫,地主家遇有婚丧等事,佃户须前往帮忙等。
不过,从清苑的总体情况看,20世纪上半叶租佃土地的情况已远远不占主要成分。1930年出租的耕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05%,租入耕地的农户仅占总农户的9.06%,1930年后,不仅未增加,还有减少的趋向。
由于清苑自耕农经济占绝对主体,所以农民的主要负担是政府的田赋、附加税和其他行政或驻军的临时征收。清苑农民家庭的负担有:田税、地亩捐、验契费、公债摊派费、军事特捐及其他各种杂捐等。在这些捐税负担中,以田税、地亩捐最为普遍,凡耕田者皆要交纳,而清苑农户大多数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所以交田税和田捐者达90%以上。其次为军事特捐,交纳农户大约占一半。至于公债摊派额及其他有关杂捐,交纳的农户是少数,大约不到1/10。
田赋是农民负担的主项,田赋的数额,据清苑11村农户统计,平均每家担负6.08元;其中中农家庭负担7.77元。中农1930年户均耕地为22亩,平均一亩负担0.3532元。这个数据在华北地区有多大普遍性?
据卜凯《中国土地利用》记载:每公顷普通田地农民向县政府所纳之税额,1932年华北地区为4.15元,合每亩0.2767元[5](445),显然低于清苑的田赋。近年从翰香先生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则比卜凯估算的还要低。该著统计,1932年,河北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为1218.4388万元,山东省为2559.77万元,河南省为2193.837万元,共计5972.0458万元。而三省额征地亩为26470.7769万亩,故华北三省平均每亩田赋额应为0.2256元。该著又说,且此数也不能代表华北三省农民的平均赋役负担,因三省额征地亩数与实际地亩数相去甚远。河北省额征地亩数为8647.0279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0343.2万亩;山东省额征地亩数为10074.4515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1066.2万亩;河南省额征地亩数为7749.2975万亩,而实际地亩数为11298.1万亩,如以三省田赋及附加税额征数与三省实际亩数32707.5万亩相平均,则三省平均每亩实际赋役负担为0.1826元[8]。
按照政府当年征收入库的赋税额,反推回去计算每亩耕地的负担,结果比卜凯调查的数据低不少,比清苑11村的统计数据更是相去甚远,低48.30%。该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其一,各地区的赋役负担是不平衡的,不能排除清苑或卜凯统计地区农民负担高于华北三省平均量的可能。赋役偏重的情况,各省皆有,如河南汜水县即每亩正附税合计竟有三四元之多,但衡之全省,则为罕见,不足为论。清苑有可能高一些,可似乎谈不上赋役偏重的个例。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考虑贪污腐败的黑洞因素对赋税差额的影响。从一县、一省或从数省范围内,经过层层机关最后征收上来的赋税额,与每家每户农民实际交纳的赋税之间,肯定有一个或多或少的落差。在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的国民党政府时期,各级官吏瞒产漏报、巧立名目、层层克扣、中饱私囊的情况,决非偶尔有之,因之而使农民的实际负担量比之应当征收的赋税(也就是实际入国库的赋税)增长一二成、二三成甚或更多,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大概是华北三省估算的每亩地负担低于卜凯的统计、也低于清苑统计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用挨家挨户调查的方法计量而成的11村农民负担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尤其在强调和重视农民的实际负担,即进行农户赋役实际支出量统计的时候,当年入户调查的原始记录的价值更不容忽视。由于赋税征收中的这种弹性而增加农民实际负担问题,在苛捐杂税的征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除所谓正赋即田赋外,清苑还有验契费、公债摊派额、军事特捐、其他杂捐等四项临时性附加负担,大约平均每家负担1.24元。再加田地捐税,平均每户共负担7.32元。负担的轻重基本与各类农户的承受能力相合,中农户居中,为9.71元。
农民负担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清末传统的田亩赋役制向现代税收制转化而法治又极其不健全的情况下,矛盾和冲突变得更加突出。人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
从全国来看,民国田赋总量较清代为重。大约从1909年(宣统元年)开始,田赋附加税逐渐增加,而至民国时期增长尤快,到1927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09年,附加税约占正税的1/12;民国初年曾把附加税限制在30%以内;其后,该限制一再被突破,1927年不得不作出田赋附加税不得超过正税的规定。以后各省的附加税纷纷接近正税,甚至超出了这一限制。30年代,河北、山东等华北各省的附加税与正税基本相当。当时,国民政府也颁布了一些限制附加税增加的措施,并且重申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关于“田赋正税附捐之总额不得超过现时地价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政府有关文件中也经常提到这个标准。但在实际的田赋征收中,不少地区的田赋早已超过地价的1%。根据原中央农业试验所在1936年的调查,包括河北省在内关内各省田赋平均比正常标准高二倍以上。国民政府的这一规定,本意是对田赋的附加税进行限制,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地价并不固定,其随丰年歉年及农产品价格而浮动,不能正确反映田赋及附加税的轻重程度。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地方政府或军队向老百姓预征和借垫田赋的情况,这可视为变相增收田赋的一种形式。1929年,清苑就被当地军阀预征了一年的田赋[9]。四川军阀普遍预征田赋,最贪婪的是28军,在其防区内一年征收了59年的田赋!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向管区居民借垫田赋。民国24年(1935年)9月4日,《天津大公报》报道:“(通县)县政府奉财厅令,挪借田赋一万六千元解省,以应急需。当于昨日召开县政会议,讨论办法。议决:由县印刷一元、二元两种田赋借券抵借,并依例按着商二成、民八成摊筹,债券于夏忙完粮时代银通用。”同时,其他苛捐杂税的种类和数量也有扩大的趋势。
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田赋及各种捐税确有上升,但就规定的绝对量而言,包括冀中及华北等大部分地区在内,农民的赋役负担并非过量,或者说并非畸重得难以忍受。当时,许多研究赋役的著述都指出过这一点。关于与清苑比邻的定县农民的田赋量,冯华德、李陵就曾指出:“定县人民的田赋负担,一般看来,并不为繁重”,“就把现行税率再提高一倍,以图增加收入,也不为过分。”[10]再如朱其华的《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也提到:“河南省田赋正附税捐统计,不过二千万元,比量民力,非为过重。”[11]一方面,人们在抱怨负担愈来愈重,“其重将何以堪”,另一方面有人似乎又不无根据地主张增加税收。答案好像还要回到刚才的话题。
问题是,在一个非法治化的国家里,制度、法令及各种规定与实际上的操作及其结果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相当的距离。农民的赋役负担极其不稳定,在一些地区、一些年代里,这种落差可能不明显,因而农民还能承受得了;而在另一些地区、另一些年代农民的负担就有可能变得相当沉重而无法忍受。影响农民赋役负担稳定性的因素很多,在20世纪前半叶最为突出的是附加税的增加,兵差的摊派和货币价格的涨落。
以上种种,仅在说明中国农村赋役制度特别是农民的实际负担是相当不稳定的,在实际中也是难以统计的,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笔者不能杜撰数字,也不能援引其他旁证代替之。这种不可选择性是微观研究中的无奈,也许它是偏谬的,也许它避免了更大的偏谬。无论如何,按照微观历史研究的法则,在没有获得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仍须尊重和依照1930年的原始统计,并据此继续进行农民家庭的收支核算。当年11村农户的平均赋役量是7.32元,这里仍取中农平均每户的赋役负担量,即9.71元。
三、农民家庭的剩余及余论
在对农民家庭的剩余进行分析之前,我们先计算一下农民家庭经济的总收入。这里所说的总收入系生产性收入,不外乎农作物生产和工副业生产的收入,前者包括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后者包括家畜饲养、家庭织布、食品作坊、贩卖和充作工匠以及苇编、猪毛加工等手工业,还有打工的工资收入等几项。以中等农户为例,每年共收入228.97元。农民家庭的总支出包括生产费用支出、农民赋役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三项。从上文得知,按中等农户的标准计算,粮田、棉田的生产成本分别为36.99元和8.32元,共计45.31元。农民的实际负担量问题也是在本文讨论过的,除地亩捐等正税外,还包括军事捐等各种附加税,仍以中农为样本户,按照当年的统计一年大约支出9.71元,再加以生产成本两项总计55.02元。另从下表得知,以中等农户计,生活消费每年共支出194.75元。下面,综合列表如下:
清苑中等农户一年总收支及储蓄率
单位:元
粮食 2881市斤
151.47
棉花 105.6市斤 16.89
收入部分
工副业收入 41.51
打工19.10
总计
228.97
生产性支出(小计):55.02
粮田支出
36.99
棉田支出
8.32
捐税 9.71
生活消费(小计): 194.75
支出部分
饮食
157.31
衣服18.72
住房 1.38
燃料 5.88
杂项11.46
总计
249.77
储蓄率
-9.08%(-20.80元)
商品率59%
上表中的数据难免存在误差,但它总体上还是给人以大体不差的比例关系:从支出部分看,生活消费占去78%,而饮食部分又占去生活消费支出的80.62%,因此,其恩格尔系数为绝对贫困型。饮食支出占总收入之比则是68.70%,“糊口农业”的经济特征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量化证明。近10%负储蓄率与这样的收入消费结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一种绝对贫困型的生产生活方式中,农民家庭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为继,更谈不上持续的剩余和积累,以及普遍地投入和扩大再生产。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清苑负债户占村民总数的60%以上,以及为什么高利贷经济那么活跃。从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笔者称冀中农业的商品化有一定的虚假成分,因饥饿、负债而被迫走向市场与普遍富裕、追求利润而走向市场,自然不能期许二者产生相同的结果。英国农村商品率达到一定比值的时候,其流通结构、生产结构和阶级结构都相应发生极其深刻且不可逆转的变化;而清苑农产品商品率接近60%,但对乡村传统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冲击远没有英国那么显著,其直接原因不能不归结为农民的普遍贫困化。显然,冀中是糊口农业,甚至是不能糊口的农业。
如按照计算企业经费的方法,将包括自家人在内的所有劳动力投入都计入成本,其结果则是更大面积和更大份额的亏损。
清苑中等水平的农户是这样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农民大致又是什么状况呢?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都是这样,农民以小农最多,每至春夏之交,皆感有青黄不接之苦,衣食尚感不足,春季纳粮,如非富农,未有不感困难者。以每亩之收获量而论,除去人工种子肥料等之种种费用外,实余者寥寥,或辄有不足之虞。据马扎亚尔的统计:华北“棉花每亩生产费用,平均为8.72元,每亩收入,平均为13.84元(棉13.46元,芝麻、黄豆等副产物0.38元),故每亩纯利为5.11元;稻子每亩生产费用为8.48元,收入为6.08元,亏损2.40元,晚稻纯利为0.75元,稷黍纯利为1.68元;高粱净亏2.57元;玉米净亏0.33元;菜蔬净亏0.40元”[12]。
1926-1929年,李景汉对北平西郊和河北省定县农村进行了3次调查,共调查了198户农家。1922-1924年,卜凯等人对河北、山西、河南、安徽等六省进行了13次调查,共调查了2370户农家。他们调查的结果是:在这总共2568户农民家庭中,亏损户占60%以上[13]。
显然,粮食生产率始终没有走出低水平徘徊格局。从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出率上看,近代以来,因战乱等种种原因呈下降的趋势,直到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以前才恢复到清代最高水平,何况冀中的亩产量还低于华北及全国的平均水平。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规模和质量。即使这一时期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善给农民带来一些生计,甚至小小的繁荣,但总的看颇为有限,颇为不充分,而且还有一部分虚假成分,不足以改变个体农民世世代代积贫积弱的状态。前面关于清苑一般农户每年生产储蓄率的计算以及其他地区相关情况的列举,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农民个体财产与财富的积累极其薄弱,在正常年景下都不能收支相抵,稍有三长两短,就难以度日。商品生产说到底是产品剩余的产物,近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尤其如此。显然,众多农户的普遍贫困是农村市场,大概也是全国市场发展的瓶颈。
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没有像工业化以前的英国农村那样,个体农民从物质到精神曾普遍经历了相当一段较为宽松、较为充分发展的时期。在那样的环境下生产者个人财产和财富普遍与持续的积累,社会地位、个人权利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由于没有这样一个前提,所以中国农村既没有普遍出现面向市场、追求利润的经营型农业,也没有产生一批像英国约曼那样的富裕农民阶层,成为现代农业的发起人。即使乡村中一小部分人手里聚积起了一批货币,由于缺乏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那些货币也难以转化为创造利润的资本。
冀中上等农户的状况究竟如何呢?
清苑11村的统计资料表明,富农中也有负债户,但毕竟是少数,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相当比例的剩余,逐年有了一定的积累。个别人丁兴旺的富农户,想方设法增加土地耕作面积,甚至租进土地经营,使用雇工,也有一定的土地投入,出现了扩大再生产的趋势。
对于自耕以外的土地,是出租出去还是雇工经营,人们往往选择后者,他们认为雇工经营比土地出租更有利。人们倾向于选择雇工经济,表明已开始形成比19世纪及其以前更有利于雇佣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而19世纪仍然把出租土地认作地产经营最佳的、也是惟一的选择[14]。不过,大概正是由于那样的社会条件发育还不够充分、不够成熟,当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政治与经济缘由,所以从整体上看农业雇佣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是颇为有限的。清苑农村没有出现一批面向市场、有实力、有地位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同时也没有形成一大批独立的、自由的雇工队伍。也就是说,20世纪上半叶清苑农村没有形成近代有效率有规模的生产组织,当然农村财力与人力的主体也没有向其集中;恰恰相反,就主要的资金流向而言,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储存方式中,而集中起来的货币依旧与高利贷结有不解之缘。
一部分富农和地主,尤其是拥有百亩以上田权并兼有比较活跃工副业和商业收入的大户,已经聚集起一定数量的货币。其中一部分成为农村借贷经济的来源,更大部分资金则在地主和富农手里存储起来。值得深思的是,上等农户手中的这些货币并没有转化为开发现代化农业的资本,而是进入了“沉淀状态”——埋入地下。这些资金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投入,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农业投入的风险成本过高是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没有普遍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一场干旱就会使肥料失去作用,一场战乱会使所有投入化为灰烬,更无完善的法律体系保证投入者切实获得其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愿意在生产要素上投入大本钱。
把剩余的资金埋藏起来,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使急需得到发展的农村和农业不能利用仅有的一点资金。许多急待开发的农业和工副业生产因缺少资金而不能进行,甚至为得到一头牛、一张犁都可能意味着农民全家不得不饿上一年肚皮。生产性资金几近枯竭,一般小农的简单生产都常常难以为继,普遍扩大再生产的前景更是渺茫;同时,剩余资金“沉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得不大批闲置。
这样,在20世纪中叶,冀中农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在国内外市场诱导下,各级交易市场逐渐扩大,自然经济的平衡性进一步破坏,同时化肥良种等新的生产要素初露头角;另一方面,由于战乱与社会动荡,政府低能腐败,缺乏基本的法律制度等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使大部分农业生产者入不敷出,负债挣扎,少部分上层村民稍有剩余,而资金又远离市场,陷于停滞;劳力浪费、技术陈旧、生产凋敞,广大农民仍然在传统经济社会中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