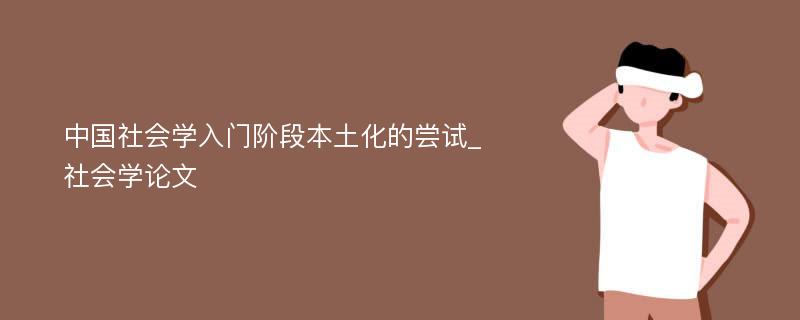
中国社会学传入阶段的本土化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早期的社会学,可分为1919年以前的传入阶段和1919年到1949年间的发展阶段。前者主要是对国外社会学的翻译和介绍;后者则表现为社会学研究和教育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在传入阶段,中国社会学并不是单纯的移植,而是开始了本土化即中国化的尝试,这种社会学本土化的尝试,在严复、章太炎的社会学学术活动以及北京社会实进会进行的实证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严复的社会学本土化尝试
严复是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先驱者,也是19世纪末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其大量的译著中,最引人注目是他以夹叙夹议的形式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而成的《群学肄言》一书,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力图从中国固有的文化理念去理解社会学,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体现出了较明显的本土化倾向。
首先,严复对“群学”即社会学的界说充分体现了中国“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
在《群学肄言》的序言中,严复对群学做了明确的界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治之方也。”在这里,严复实际上是将社会学(群学)看成是一门研究社会治乱兴衰原因、揭示社会所以达到治的方法或规律的学问(学科)。在此后发表的“原强”一文的修订稿中,他又说:“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这功。”由此可见严复对群学界说的强调具有经世致用的性质和价值。
在中国,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产生于古代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我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一项主要规范。这一学术传统强调研究者应具有积极入世的价值观和政治本位的人生观,重视考察、评估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和达到治、兴的方法。在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那里,经世致用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将其与修身联系在一起,如孔子学说中的仁学与礼学。仁学是“上学”以“达天命”;礼学是“下学”以“学人事”。因此,经世与修身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并成为儒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及至清代,方苞将孔子学说概括为“明诸心以尽在物之理而济世用”的实用之学。魏源、章学诚和冯应京等人也对经世致用的思想进行了积极的弘扬和阐释,注入了不少新的内容。可以认为,在清朝末年,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特点。严复对社会学(群学)的界说明显地反映出他深受这一既由来已久又在当时颇为流行的学术传统的影响。
其次,严复将社会学定名为群学,本身就显示出他力图为社会学在中国的生长寻找一定的思想基础,在严复看来这个基础主要是荀子之学,尤其是荀子关于群体的思想。
关于群体,荀子在《王制》篇中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遇离,离则弱,弱不能胜物……。”这段话表明了荀子关于群体的基本观点:人没有群就不能生存,而只有群的结合还不够,还必须有“分”,即必须有一定的标准,将社会成员区分开来、组织起来。
严复认为,斯宾塞的社会学说实际上是与荀子的群体思想相通的。在“原强”中他写道:“斯宾塞尔者,亦英产也,与达(尔文)氏同时。其书……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故曰‘群学’”。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又引用了荀子的论述,并对“群”与“社会”在中国和西方的含义作了分析。他说:“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
最后,严复强调,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与中国的《大学》、《中庸》也有相通之处。由此反映出严复力图使社会学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的意向。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大学》的中心思想在于论述“治国平天下”之道。即要治国须先“齐家”,要齐家须先“修身”,要修身须先“正心”,要正心须先“诚意”,要诚意须先“致知”,要致知须先“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修身的功用。《中庸》的中心论题则是缓和社会冲突与矛盾的论述,并强调把一切社会关系视为伦理关系,从伦理关系着手,重视“仁”与“义”,行忠恕之道,讲求人人安分守己,从而缓和社会冲突和矛盾。
在《群学肄言》的《译余赘语》中,严复明确指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通过分析,严复还发现,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与《大学》、《中庸》在思想观点上,有两方面具体的相通之处或相似关系:第一,斯宾塞认为,社会生活必须用科学方法加以客观研究,这与儒家著作所强调的“士”必须通过分析问题取得学识,进行修身,而后方能“治国平天下”是相近的。正因为如此,严复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应当保留,只不过对士的领导层的培养要加进新的内容,即加进社会学(群学)这一内容。第二,斯宾塞认为社会变迁是长期渐变的过程,是日积月累的结果,故对突变持怀疑态度。这一观点在严复看来,与《中庸》中的观点是相近的。严复认为,渐进是解决当时中国改革派和传统派(即“新旧两家学者”)之间的激烈冲突的最理想的妥协办法,各派人物学了社会学,便会认识到他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只是无谓之争。严复还特别告诫改革者,对复杂的社会有机结构不要横加干预。
总之,严复在其社会学学术活动中主要在以上三方面体现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倾向,对社会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了大胆的尝试。应当承认,严复将社会学视为是对社会治乱兴衰的探讨,既兼顾了社会的变迁问题又涉及了社会的秩序问题。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中国化意向对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主要特点。然而,严复以“群学”一词代替社会学的做法在他以后并没有流行开来,他力图使社会学思想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做法也未获得他以后的社会学者们的普遍认可。原因何在呢?他们认为,除了严复以文言文翻译与此后普及的白话文难以匹配外,更为重要的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型,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影响的儒家文化不断地暴露出它的缺陷和不足,其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儒家文化遭到了学术界的猛烈批评,在这种背景下,严复那种试图使社会学思想与儒家文化相融合的做法也就很难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认同了。
章太炎社会学学术研究中的本土化倾向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也是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主要先驱者之一。1898年,他担任《昌言报》主笔时,就与曾广铨合作,节译了《斯宾塞尔文集》。在社会学方面,他发表了《序种性上》、《菌说》、《〈社会通诠〉商兑》、《原变》、《尊史》、《信史》等著名论文。1902年,他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所著的以介绍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和美国吉丁斯的社会心理学为主的《社会学》一书。一般认为,章太炎翻译出版的此书,是中国社会学史上第一部以“社会学”一词冠名的著作。
章太炎与严复相似,也深受荀子的群体思想的影响,体现出一定的本土化倾向。所不同的是,严复的研究偏重于吸收荀子关于“合群”的思想,而章太炎则既重荀子的“合群”思想又重荀子的“明分”思想,并结合社会进化论提出了他自己关于“合群明分”的见解。此外,章太炎还就斯宾塞的有机论思想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且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之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照搬国外的东西,而必须注意本国的特殊性。
章太炎“合群明分”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899年发表的《菌说》一文中。他深感“兼弱攻昧”是不可回避的严酷的现实,但他又不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应有的合理现象。他从古代荀子的学说中得到了启发,提出了“合群明分”的制衡方案。表达了他对社会应有的群己关系的深刻见解。他在《菌说》中说:“惟其群而有分,故有墨子兼爱、上同之善,而畛域有截矣”。这就是说,既要承认人我、群己间存在着“畛域”(利益的差异),又必须凭借“兼爱”、“上同”精神,使“畛域有截”,即保持合理的度,以增进社会利益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在章太炎看来,群己利益有差异,但从根本上说,二者不仅是一致的,而且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狮子虽大而被杀,蜜蜂“虽细不败”,足见个体的利益必以群体的存在为前提:“苟不能此,则无不受侮”。反之,群体的和谐的利益,也应当以承认个体的利益为基础。人人“自亲亲始”,因“爱类”而扩充亲亲力量,“必以仁民爱物终”。就合群与竞争的关系,赫胥黎似乎也曾陷入了困惑;合群固然可以平群内之物竞,但物竞既去,“其群又未尝不败”。但在这一问题上,章太炎的观点是明快的。他认为,“物竞”只有在“合群”、“兼爱”等的规范下才能成为推进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消除残酷的“物竞”和达到群体的和谐,并不会导致赫胥黎所担忧的群败。章太炎相信,“合群有分”,“以大智而充仁义之量”,才是社会实现进步的真正的符合理智的进化坦途。
在章太炎的社会学研究中,斯宾塞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但他并不盲目地效仿和认同。比如,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中,社会等同于生物机体。但章太炎由于受岸本能武太的影响而不赞同这一观点。岸本能武太在其《社会学》中说:“社会为一种有机体,非一切如有机体”,而社会与生物体的差异主要有两方面,即:“社会部分皆有意识之动物”以及“社会无本社会以外之存在目的”。章太炎在此书中译本“自序”中,充分肯定了岸本能武太的这一见解,他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皆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候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在这里,章太炎意识到,人类是有理性的,可按自己的意志合群求进,从而与无意识的生物体之间存在根本的区别。
关于如何对待外来的社会学说,章太炎更是提出了一种具有明显的本土化倾向的见解。他强调,社会方面的学说不同于自然,对社会进行研究必须注意研究者所在国的特殊性。在1907年发表的《〈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他认为,“社会之学”与自然科学(“质学”等)不同,后者无国界之分,不妨照搬,但前者却不能不注意本国的特殊性。章太炎的这一见解是颇为深刻的,他可能是中国社会学史上最早明确地意识到对社会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本国特殊性的一位学者。
在社会学的传入阶段,社会学本土化倾向除了体现在严复和章太炎的社会学学术研究活动中,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比如,自上海圣约翰大学于1905年首先在中国高校开出社会学课程以来,教育机构的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基本上由外国学者担任。但到1916年秋,北京大学的社会学课程开始由留学日本归来的康宝忠(即康心孚)讲授。康宝忠是最早讲授社会学课程的中国本土学者。
又如,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以认识和改良中国社会为主要目的的小规模社会调查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学者参与或组织的调查活动,是北京社会实进会对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1914-1915年,实进会调查部使用调查表,对北京的302名人力车夫的生活情形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可视为是中国社会学者们对本土城市社会问题调查的开端。据此次调查的参加者陶孟和的回忆,他们对人力车夫的调查除了有学术上的“趣味”之外,还在于寻求“实际的功用”,即:了解中国社会的“好处”以便加以“保存”,寻出中国社会的“坏处”以便制定“改良的方法”。
再如,一些中国社会学者开始运用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考察中国社会治与乱的原因以及达到治的具体策略。在此方面,社会学家陈长蘅的研究是比较引人注目的。1918年,陈长蘅出版了《中国人口论》一书。书中陈长蘅认为,“群之治”,其原因在于贤者、明达者、健康者“众”,而不肖者、昏昧者、瘠疾者“寡”;“群之乱”,其原因与“群之乱”恰好相反。在他看来,不肖者、昏昧者、瘠疾者之所以“众”,原因多在于“无教育”和“无生计”,因此他强调,今日中国要达到治的状态,必须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和教化问题。而在众多的生计问题中,人口问题乃是“根本”的问题之一。那么,如何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呢?陈长蘅提出了“婚姻以时”、“养育有度”、“孳生有道”、“养生有术”等办法,主张推行以节育和优生为主要内容的“生育革命”。可以认为,在人口问题上,陈长蘅是中国社会学史上最早提倡少生优生的社会学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