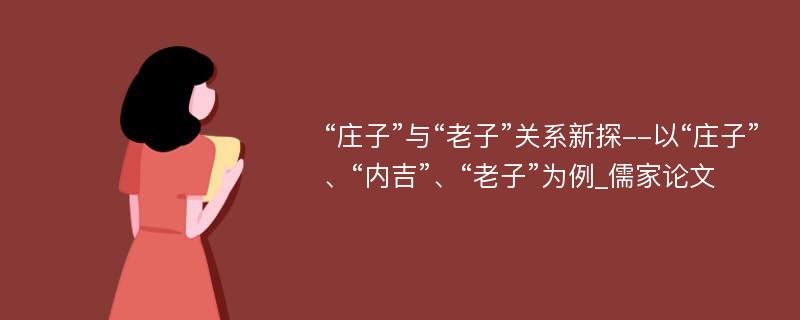
庄子与老子关系的新审视——以《庄子#183;内篇》和简本《老子》为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老子论文,简本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涉及庄子与老子关系时,“庄子”一词应析为“庄子”和“《庄子》”两个概念,因为《庄子》还有内、外杂篇之分,乃庄子及其后学分别所作。有学者指出,《庄子》书中引述《老子》之语、阐述老子思想全部在《外杂篇》,故《老子》成书晚于《庄子·内篇》而早于《庄子·外杂篇》,《内篇》作者还没有见到《老子》一书[1] (P394)。时至今日,这一结论显然已经不能成立,因为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后期墓已经出土简本《老子》,《老子》一书不但早于《庄子·外杂篇》,也应早于《庄子·内篇》。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庄子·内篇》的作者已然见过简本之类的《老子》,为什么只字没有提到《老子》一书、没有一句引到《老子》之语呢?还有,以往关于庄子与老子关系的考察,多因没有区别《内篇》和《外杂篇》以及没有确定《老子》的成书年代而出现诸多分歧,现在在有了简本《老子》的情况下,对于庄子与《老子》的关系,可以获得哪些相对肯定一些的认识呢?
本文关于庄子与老子关系的新审视,即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庄子”指的是《内篇》作者庄子,而非整部《庄子》,《老子》则以新发现的简本为据。
一
本文以《内篇》为依据,探讨庄子与老子及简本《老子》的关系,前提是须肯定《内篇》确为庄子所作。目前学界对此尚有歧见,或认为《内篇》与《外杂篇》已被郭象搞乱,研究庄子思想应以《逍遥游》《齐物论》为依据,打破内外杂篇界限选择有关资料[2] (P353);或认为内外杂篇皆是庄子所作,只不过具体划分《外杂篇》是庄子早期作品,《内篇》是庄子晚期作品[3];或认为《内篇》是汉初庄子后学所作,《外杂篇》才是庄子所作[4] (P386)。这样,内外杂篇孰先孰后及其作者问题仍是庄子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大问题。
对此,笔者认同学者们对《内篇》早于《外杂篇》已经进行的多方论证。这里所要作的补充论证在于,以往论证都还属于个别论证,它们只能解决《外杂篇》中的某一篇或某几篇在《内篇》中的某一篇或某几篇之后,尚没有论证《内篇》作为一个整体先于《外杂篇》,且确与庄子有关。笔者据种种迹象发现,《内篇》很可能曾作为一部《庄子》,在战国时代即先于《外杂篇》单行于世。这个证明就来自《庄子》。《大宗师》有这样一段描述:意而子希望追随许由,许由认为意而子已经被尧的仁义、是非所黥、劓,难以再得“道”,意而子说我可以恢复原貌,“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许由这才说:“噫!未可知也。我为汝言其大略。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吾师乎!”这段话恰恰在《外杂篇》中的《天道》篇中又出现了一次,而《天道》分明说是“庄子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曰:‘吾师乎!吾师乎!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寿,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很显然,《天道》作于《大宗师》之后,其作者认定《大宗师》为庄子所作,许由的话是庄子所撰,代表庄子思想。其实,还有更大的一种可能,即“庄子曰”就是“《庄子》曰”。《天道》篇作者是在引述《庄子》中的语句,才没有称这段话是“许由曰”。
先秦多无书名,惯常之例是以作者名代称书名。《庄子·外杂篇》引《老子》一书即称“故曰”或“老聃曰”。《墨子》引《老子》一书也称“老子曰”,所以,“庄子曰”完全有可能是“《庄子》曰”。上引材料说明,《天道》篇的作者已经见过一部《庄子》,《大宗师》就是其中的一篇。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内七篇曾作为一个整体,以《庄子》为称,在战国时代已经单行?
刘笑敢先生在论证《内篇》先于《外杂篇》时曾提到《天地》第四节有“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之说,而《内篇》中恰恰有几个寓言,即《逍遥游》中的许由教训尧,《齐物论》中的“齧缺问乎王倪”、《应帝王》中的“王倪……行以告蒲衣子(即被衣子)”,不难看出,《天地》篇所述这些得道之人的师承关系,即是对《内篇》中这几则寓言综合梳理的结果[5] (P19)。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则寓言分别出自《内篇》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应帝王》,包括了其中的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可以设想,《天地》篇的作者应是读了包括内七篇在内的这部《庄子》之后而为文的。
此外,《秋水》中有一段借公子牟之口讥讽世俗之人难以了解庄子学说,曰:“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犹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了解“庄子之言”而用“观”字,可见庄子之言已经著于竹帛,在后学中流传。
综上,《内篇》应是一个整体,早于《外杂篇》,乃庄子所作。作为对这一点的一个补充证明,还有学者曾撰文提出应打破内外篇界限,根据《庄子》一书中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划分庄子及其后学不同流派的作品[6]。有意思的是,该文通过思想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内七篇全部属于庄子A系统,外加外杂篇中的《秋水》、《田子方》、《知北游》、《达生》、《山木》。且不说《秋水》等篇是否庄子所作,这个结论起码又一次证明,内七篇全部属于一个系统,乃庄子所作。
二
从《庄子·内篇》看,庄子的确没有引述过《老子》之语。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这说明此时《老子》尚未成书,但郭店楚简本《老子》的出土,已经可以否定这个推测。
据考古专家介绍,出土简本《老子》的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位置在楚国郢都外墓地范围之内,这一带楚墓的序列已经排定,足以说明该墓属于战国中期偏后。具体来说,这座墓最接近离它不远的荆门包山一号、二号墓,包山二号墓所出竹简有一个纪年可确定为公元前323年。比包山二号墓晚的包山四、五号墓也是地道的楚墓,应早于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秦人占领。因此,包山一、二号墓及郭店一号墓估计都不晚于公元前300年[7]。这个时间起码证明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期之前。上面提到《墨子》引用过《老子》,而据李学勤先生介绍,战国中期的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发现有《墨子》佚篇,可知战国前期已有《墨子》流传[8] (P224),那么被《墨子》所引的《老子》自然又在该书之前。这样,二重证据已基本将《老子》的成书锁定在战国前期之前,从而证明了该书很可能就是春秋末年的老聃所作。
庄子生卒年不详,但大致生活在战国中期。《史记》庄子本传明确称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竹书纪年》校订《史记·六国年表》,得梁惠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70—前319,齐宣王在位时间为前320—前302。从《庄子》中可知庄子与惠施同时,且死于惠施之后,而惠施就主要活动在梁惠王时期,其事迹见于记载最晚的是梁襄王五年(前314)出使赵国“请伐齐而存燕”。此时惠施尚能出使,其去世还应晚上几年,庄子则要更晚一些。
这样说来,《老子》绝不会晚于庄子写作《内篇》诸篇之时,明矣。
说到《老子》,其实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还有不小差异,以往学术界持《老子》“晚出说”的一些理由,全部见于今本《老子》,由此有学者提出简本《老子》为《老子》原始本,今本《老子》乃在此基础上增益改定而成,作者很可能就是战国中前期的周太史儋[9]。笔者基本认同此说,但认为此后还应有所增益,因为从后来的帛书本与今本仍有不同看,《老子》有多种传本。这样,对于庄子与《老子》关系的考察,严格说来就应该以简本《老子》为据,因为就时间来说,庄子很可能尚未见到今本《老子》。
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即尽管简本之类的《老子》在庄子撰写《内篇》之时已经流传,而庄子恰巧没有见过它们?回答应该是否定的。这里没有必要以人所共知的庄子“其学无所不窥”来推定这种可能性的微乎其微,即便对照《庄子·内篇》及简本《老子》,即会发现道家一些基本概念、特有范畴也已经为两书所共有,因此就出现先后讲,只能是庄子采纳、吸收了《老子》,而不是相反。
三
或许正因为庄子没有像其后学在《外杂篇》的某些文章中那样宗法老子、引述《老子》,学界还有一种倾向,即认为庄子本人与孔子的关系要比与老子更接近一些。有学者指出,孔子在《庄子》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人物(144次),而作为道家开山的老子只出现了68次,不到孔子的一半,这说明孔子在庄子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分量,甚至超过了老子[10]。
考察《庄子·内篇》,且不说庄子之学是否与儒学有关,仅就庄子对待老子和对待孔子的态度而言,事实并非如上所述。在《内篇》中,庄子虽然没有引述《老子》,却多次提到了老聃,还有一处恰恰涉及到老聃与孔丘:
“老聃死,秦失吊之,……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11] (《养生主》)
“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11] (《德充符》)
“阳子居见老聃,……老聃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11] (《应帝王》)
从中不难看出,在庄子笔下,老聃是一位顺应自然的游于无有的得“道”之人,以致于阳子居诚惶诚恐地求教于老聃,令孔子佩服的无趾请教于老聃,而且从无趾口中,可知孔子也曾频繁向老聃学习。
当然,无论是孔丘还是老聃,其对话大都是庄子根据需要所杜撰。但综合考察《庄子·内篇》,会发现其中历史人物一类,还是大致可以反映庄子心目中关于先贤所臻境界的基本把握的。正如有学者所注意到的,庄子哲学体系涵摄三大人格境界:一是理想人格境界,又称真人境界,超越了时空、生死和物我界限,与天地精神融为一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二是隐士境界,即“游方之外者”的境界,顺天而不顺人;三是“游方之内”的士大夫的境界,是“顺人而不失己”或“内直而外曲”[12]。这三重境界在庄子那里是有高下之分的。《人间世》即重点表述士大夫的境界,庄子让孔子所代言的也都是这一层次的追求。至于得“道”,孔子远远不及,《内篇》中除上引无趾称孔子已经被天“刑之”之外,还有多处借他人之口和借孔子自己之口贬抑孔子,比如《齐物论》:“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德充符》:“仲尼曰:‘夫子(指王骀),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老聃,则大致介于游方外之人和得道之人之间,显然在孔子之上。这反映了老子、孔子学说在庄子心目中不同的分量。不管庄子最初是否曾就学于儒家,出自孔门,在他学术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他对老子思想的认同显然超过了孔学,最终导致将孔学作为了思想桎梏,以致于要解其桎梏。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庄子以老聃为师呢?事实也并非如此。就《内篇》而言,老聃也只不过是庄子提到过的得道之人中的一位,在他之上还有许由、齧缺、王倪、被衣、邈姑射神人等真真假假的真人、神人,丝毫看不出专以老聃为宗师的迹象。
四
现在,在确定了《老子》成书在前、庄子的确了解《老子》一书的情况下,对照《庄子·内篇》和简本《老子》,就会发现,就《内篇》中庄子所阐释的思想看,在他心里潜在地有着超越老子、更透彻地体悟“道”的取向。也就是说,庄子是一位独立不倚的思想家,在他心目中除了师法道之外,别无所师。所以,他没有必要引《老子》为证,更没有必要像弟子或信徒那样亦步亦趋地阐释《老子》思想。相反,对于《老子》书中的许多范畴,庄子都作了更极端化的生发,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庄子还阐发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范畴和思想。
比如简本《老子》明言“天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却说“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11] (《齐物论》),自“有”溯于“无”,更自“无”上溯于“无无”,乃至于“无无无”、“无……”。
再比如关于二元转化,简本《老子》已经充满“变”的色彩,所谓“反也者,道动也”。这个“动”不但包含事物会向对立面转化,而且包含事物本身就有对立两极的相互转化,所谓“进道若退”、“大攷(巧)若拙”。庄子哲学也满篇充斥大小、多少、长短等二元相对的概念。不同的是,在老子那里,进退、巧拙的概念是确定的,只不过看你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说,往往是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短时与长久、手段与目的、态度与功效等等的区别,庄子则完全抹煞二元的对立,“大”本身就又是“小”,“是”本身就是“非”,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11] (《齐物论》)。
再比如体道之用,简本《老子》已经为人生设计了“人法道”的行为方式。其中既包括人君治世,如“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也包括个体的平安康泰,如“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古(故)智(知)足不辱,智(知)止不怠(殆),可以长旧(久)”。庄子也提到过“明王之治”[11] (《应帝王》),但那是指“道”本身的化育之功,即“道”之治。至于个体人生,庄子所阐述的固然也包含有保身之道,但与《老子》单纯强调的保全人的物质、肉体等外在的生命需要不同,庄子更突出地追求体道之后的心灵状态。《逍遥游》、《大宗师》等篇中反复描写的无功、无名、无己、无死生之别的与道合一的至人、神人境界,就是《老子》中所没有的。
这一切,都可见庄子吸取老子哲学又予以超越和突破的方方面面。
除此之外,据简本《老子》考察庄子与老子的关系,笔者认为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关于“一”这个概念的首创问题。今本《老子》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句,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的描写,还有“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之说,然有学者已经指出,《老子》中这所有带有“一”的语句均不见于简本,《庄子·外杂篇》中引用《老子》之语也没有引到这种语句,由此推断“一”的思想乃后来所加[13]。而在庄子这里,“一”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庄子与老子道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即在于强调“道”的整体性,强调道就是“一”,只有道是一,具体事物则有分有成,起灭变化。道是整体,就不能分割,有分割,就不是“道”了,正所谓“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11] (《齐物论》)。而这正是庄子相对论的哲学基础,即只有“道”是“一”,是“全”,世间任何具体的事物便都是非一,都是偏,都是相对的了。庄子不同于老子思想的特色内容,诸如齐万物、一死生、等是非、精神上无我逍遥等等,正都是由此而生发。如前所说,就时间来说,庄子有可能见不到今本《老子》,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就意味着庄子所见到的《老子》尚没有“贵一”的思想,“道一”思想就是庄子所创。这样一来,庄子超越老子独创体系的成分将更加强化。
二是关于庄子对待儒家的态度问题。我们知道,今本《老子》的反儒倾向至为明显。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等等。这些说法在《庄子·外杂篇》中得到强烈回应,《胠箧》直称“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将矛头直指儒家的“仁义”之说。相较之下,《庄子·内篇》对孔子的态度则显得温和得多,以至于学界有“庄子盖助孔者”之说。而对照简本《老子》,会发现上述这些与儒家对立的语句,或者说法有异,或者概不存在,学派对立的倾向至为淡薄。比如“大道废,有仁义”,在简本中为“大道废,安有仁义”,一字之差,意思完全相反。这样,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庄子在道家反儒方面的作用问题了。如前所述,庄子在《内篇》中虽没有强烈反孔,但对孔子是有所贬抑的,是把孔子放在老聃之下的。如果庄子所见《老子》是简本而非今本之类,那么他的贬孔倾向就不是受到《老子》的影响,而是缘于他自己的价值判断。正是出于对“道一”的独特把握,出于对精神上超越一切世俗羁绊的境界的追求,庄子否定了当时各家各派关于是是非非的所有争执,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于是他否定了孔子,也超越了老子,成就了只此一家的庄子。
综上,简本《老子》的出土,肯定了《老子》并不晚于《庄子·内篇》。庄子在《内篇》中没有称引《老子》,显示了他并不宗老、解《老》的态度。庄子是不步人后尘的独创学派的思想家。
标签:儒家论文; 庄子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文化论文; 天道论文; 墨子论文; 大宗师论文; 国学论文; 逍遥游论文; 应帝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