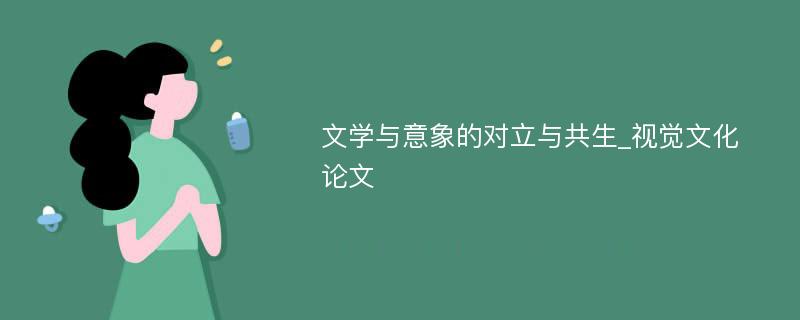
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立论文,图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文学理论界盛行“图像转向”和我们正在走向“图像时代”的说法。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图像并不是一件新东西,图像的作用受追捧也不是第一次。实际上,在人类诸感官中,视觉被认为具有优先地位已经几千年了。但谈论“图像时代”的人努力要说出的一个意思是:“这一次真的与以前不一样了!”那么,究竟怎么不一样?我们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些提法背后的理论预设是什么?这些问题带给我们的,有欣喜,有焦虑,更有思考。
一 图与词之争在希腊
图像的优先地位,本来可以指在思考人的行动、思想,以及世间事实本身与它们的外在表现之间关系时的一种观念。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行动、思想与事实才是优先的,而不是作为它们的外在表现的图像。受欧洲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传统影响,这种关系被转化为图与词的关系。于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被放在一个独特的语境之中展开,这是我们在读西方有关图像论述时感到晦涩难解的原因。
我们在柏拉图的哲学中,看到了理念的世界要比现实的世界更为真实的思想。对于他来说,现实的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镜像,就像我们在洞穴中所看到的透过火光而投射到墙壁上的影子。真实的床不是木匠所打造的床,而是理念的床(注: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和《巴门尼德篇》。)。因此,这种观念具有一种反视觉的特点:眼见不为实。亚里斯多德努力给予视觉以认识论上的证明,从而确认人的感觉是通向真理的途径。在《形而上学》的一开始,亚里斯多德就写道:“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注: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页。) 哲学家们的这种论述和论争,与希腊人当时的艺术状况有着对应关系。在当时,希腊艺术正在完成一种向视觉中心主义的转变。
如果曾经去过大英博物馆,你可能不会忘记从埃及厅走进希腊厅的那几步之遥带给你的震惊感。埃及雕塑的面容僵硬刻板,仿佛这些人像的脸上罩着面具,而到了希腊厅,这个面具被一下子揭开了。希腊雕像的面容、体态、衣褶,一切都向人们宣示,这是一个视觉的盛宴。在博物馆里,从埃及厅到希腊厅只有几步的距离,而在历史上,这种艺术风格的变化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埃及艺术保持其风格有几千年之久,在希腊艺术的古风时期,埃及影响仍保存着。只是到了希腊艺术的古典时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造像的风格就有了彻底的改变。英国艺术史家冈布里奇将这种变化说成是希腊艺术革命。他曾这样概括:埃及人所再现的是他们所“知道”(know)的世界,希腊人所再现的是他们所“看到”(see)的世界。冈布里奇所做的对比简洁而清晰,一下子说出了两种艺术的基本特征:在埃及人那里,图指向了关于对象的知识,而在希腊人那里,图再现了对象的外观(注:参见冈布里奇的著作《艺术与错觉》(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和《艺术的故事》(范景中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特别是《艺术与错觉》一书中的“论希腊艺术革命”一章。)。
二 希伯莱精神进入图与词之争
在欧洲,影响图与词之争的另一条思想线索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在《圣经·旧约》的《创世纪》中,神说要有光,神说水要聚在一处,神说要有草木果实,神说要有飞鸟鱼兽,神说要造人,于是,这一切先后就都有了。(注:这里关于《圣经》中观点的引述来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发的《新旧约全书》(上海1981年)。)这段话本来可能是对从神的意愿到这个意愿的实现所作的描述,并不排斥神的创造活动,但后来却被普遍解读为神只是用词在造物。
在《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铸金牛受到了神的谴责,在《利末记》中明令禁止作虚无的神像,包括偶像、柱像、石像。这些记载成了以后很多世纪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反偶像崇拜的来源。这种观念在宗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早期的人类相信图像与实物具有神秘的联系,因而造像与巫术和原始多神教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对图像的排斥,代表着新生的一神教与原始多神教的决裂。然而,一神教的胜利并不表示“词”一劳永逸地战胜了“图”。历史上,图像不断地,以不同的理由出现。偶像崇拜与反偶像崇拜观念间的斗争曾出现过多次。在犹太教中,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在东正教中,以及在后来的新教的历史上,这种斗争一再重复。甚至在伊斯兰教中,反偶像崇拜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教义。这是由于《古兰经》中有与《圣经》类似的谴责以色列人“认犊为神”,因而是“不义”的词句(注:见《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由于斗争出现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化语境,从而使不同时代的艺术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反对铸金牛,只信奉一个其形象并不向普通人显现的神,这是一种在摩西领导下的宗教的变革,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一种当时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割断与埃及传统关联的努力,其中也包括与埃及人造像传统的决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后来的一个有趣的发展:希腊人从另一方向与埃及造像传统决裂。最后到了中世纪时,希腊与希伯莱这所谓的“二希”文明的造像传统又形成了某种形式的结合。
希腊人的视觉世界被罗马人继承,却在罗马帝国后期随着东方思想影响的增强和基督教的兴起而受到挑战。冈布里奇没有说以色列人再现什么,根据《圣经》的记载,似乎他们要再现一种“不知道”的世界;然而,冈布里奇对在《圣经》思想影响下的中世纪人的造像观念作了评价,他说,中世纪的人所再现的是他们所感到(feel)的世界。确实,我们从中世纪的圣像上可以看到这样的特点。模式化人的面部表情,无肉体感觉的身体,突出的眼睛,神秘符号的巧妙安排,显示出视觉本身只是一种中介,这些作品指向着图像背后的东西。希腊雕塑重视身体,而中世纪圣像则指向内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图与词的钟摆向词的一方所作的新一轮摆动。希腊人的视觉世界,被中世纪心灵的世界所取代。当然,这种心灵的世界仍有其外在的表现,因为希腊艺术毕竟不可逆转地训练了人的眼睛,从而使图与词的争斗盘旋向上发展了一个层次,图成了词的意义的显示。
三 中国人的“书画同源”说
关于图与词的关系,中国古代艺术史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与西方不完全相同的故事。中国古代也有重文字而轻图画的观念。老子书中讲“五色令人目盲”(《老子·十二章》)和“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王充讲“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论衡·别通篇》)。这些都对图像持否定态度。但更多的人还是承认图像的作用。《周易·系辞》中有“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词句,说的是卦象。后来有人提出三种符号说,即图理的卦象,图识的文字和图形的绘画(注:颜延之语,转引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更为著名的是“书画同源”说,认为书画在最早的时候曾有一段“同体未分”的状态,即使后来被区分开来以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书画同源”说,显示出绘画向文字的“双重攀附”。一是论证绘画也像文字一样,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之功,从而通过肯定绘画的伦理和认识的功能而强调绘画及画家的社会地位,二是论证绘画须接受书法的笔法,从而规定绘画的本质不等于物象的再现,而是人的活动的痕迹。(注:对这里所说的“双重攀附”的详细论证,请参见拙作《“书画同源”之源》一文,载《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2年(秋季号)。)在这“双重攀附”中,如果说前者是为视觉艺术的存在作辩护的话,后者则是对视觉优先性的挑战。我们从前者中看到了像格里高里大帝所说的那样,“愚人从图像中所接受的,是受过教育的人从《圣经》中所接受的东西。愚人从图像中看到他们必须接受的东西,从中读到他们不能从书本上读到的内容。”(注:转引自阿列西·艾尔雅维克:《眼睛所遇到的……》,高建平译,《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也就是说,绘画成为道德教化的载体,协助文字完成宗教、思想、政治和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我们从后一个攀附中看到了诺尔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所谓的绘画中的看不见的身体(invisible body),即人的身体运动留下的痕迹的观点(注:参见Norman Brysom,Vision and Painting:The Logic of the Gaze (London:Macmillan,1983)一书,特别是该书的第163—171页。)。也就是说,绘画成了人的身体姿态和手的动作态势的展现,而这种动作展现之中,显示出人的精神状态(注:参见Jianping Gao,The Expressive Act in Chinese Art:from Calligraphy to Paingting (Stockholm:Almaqvist & Wilsell Intenational,1996)一书,特别是该书的第41—33页和第176—193页。)。
两个攀附说明了两种图像制作理想。前一种理想说的是可以制造与词的意义相匹配的图像。后一种理想说的是图像本身并非是与人相对立的对象的外观,而是制作者活动的产物,对图像的接受也与对这种活动的体验联系在一起。
四 现代性与媒体革命
十多年前,在英国美学学会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发言说,照相机这种机器不可能最早由中国人发明。古代中国人有很多的科技发明,他们是恰好没有发明照相机,还是根本不可能发明照相机?这个问题似乎很难一下子说清。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想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说明,中国绘画与欧洲绘画在视觉再现的追求上具有重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欧洲人能够发明照相机,而中国人不能。
在欧洲,照相术的发明的确有着一些历史的准备,与他们的视觉观念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人的视觉观念发展的自然结果。在15世纪,意大利建筑师菲利普·布鲁内斯奇(Filippo Brunelleschi)等人发明了焦点透视,使画家有可能在平面上描绘三维的空间。布鲁内斯奇的这一发现在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名著《论绘画》中得到系统的总结,为欧洲近代绘画打下了基础。在该书中,他叙述了焦点透视法的基本原理。在这本书的一开始,他对绘画作了两条规定:第一,画家只画看得见的东西,第二,数学是自然之根,也是这门艺术之根(注:阿尔贝蒂:《论绘画》,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0—43页。)。我们从前一条可以看出希腊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可与前面所引述的冈布里奇对希腊艺术的评价,以及对希腊艺术与埃及艺术、中世纪艺术的对比联系起来考察。历史经历了一个新的轮回。希腊人走出东方,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人走出中世纪,所采取的办法都是回到视觉。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又与古希腊人不同,这种不同从其对科学的理解上可以看出。古代希腊人讲“认识”,不讲求精确性,而现代科学则追求精确性。海德格尔曾以我们所熟悉的伽里略在比萨斜塔上抛铁球挑战亚里斯多德自由落体理论为例,指出,这不能简单地认定伽里略对了而亚里斯多德错了,只能说明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存在观(注: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的时代》。中译本参见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77—115页;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由此我们再来看阿尔贝蒂的第二条规定,即将绘画的基础归结为数学。绘画被当成一种几何学,经过数学的计算,运用透视规律展现逼真的现实。到了16世纪,一些艺术家使用一个盒状的设备,盒子的一边有一个小孔,另一边有一片玻璃,称为camerao bscura(拉丁语,意思是“黑房间”)。这种盒状设备可以取代计算,画家只要将透过这种装置看到的物象记录下来即可。据记载,当时的著名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都曾使用过这种装置。正是在这种装置的基础上,19世纪初有人发明了照相机(camera)。
致力于在平面上再现三维的对象,运用透视的方法使这种再现显得更加逼真,是照相机发明的前提。英国画家康斯泰伯(John Comstable)说,绘画是“自然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其中,图画只是实验而已”,(注:康斯泰伯1836年给皇家学院的讲演,转引自《美学百科全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卷,第411页。)这种观点在欧洲近代绘画中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近代绘画一直在朝着照相机的方向发展。
照相机与照相术的发展,对于图像技术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从照相,到电影、电视,以及目前数码与网络技术的结合,经过了四个阶段。照相使廉价地再现物象成为可能;电影通过迅速转换胶片而实现了对运动着的图像的再现;电视通过另一种技术原理实现了在电影中已实现的动态图像,使之走进千家万户;而网络则以其所提供的互动的可能性而给人以更为浸入性的经验,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虚拟的世界之中。这种发展还会延续下去,我们会有第五、第六,甚至更多的阶段。然而,我们在考察这些阶段时,不能将照相机出现之前的一个阶段排除在外,这就是焦点透视的视觉观所形成的阶段,而这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视觉优先性思想下形成的。
科学技术所制造的图像,是一种廉价而致力于普世性的图像,但它不是唯一的。在视觉艺术领域,它随着这种图像的日益普及而成为挑战的对象。正如前面所说,照相机实现了欧洲近代画家们再现物象的理想,但照相机并没有取代绘画。现代绘画史的实践以及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力图证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所形成的视觉观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视觉观。一方面,学术界努力证明,其他的视觉观是可能的。例如,鲁道夫·阿恩海姆就指出,“由文艺复兴时期所创立的西方绘画风格,它所再现的事物的形状,总是局限于从一个固定点所看到的那个局部。而埃及人、美洲土人以及西方现代的立体派画家们,却不理睬这种限制(即从一个固定点只能看到事物的局部)。”(注: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不仅是阿恩海姆所列举的这些地方的艺术,而且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的绘画,非洲和大洋洲的艺术,也都没有走向这种焦点透视。世界上众多的民族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觉观,从而产生不同的,非常精美的绘画。更进一步说,恰恰是照相以及随之而来的电影和电视方面的成功,造成了视觉艺术方面的反弹,从而成为现代主义艺术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而这种新的绘画意识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于视觉的重新认识。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在今天,以照相为代表的这种通过技术手段所制造的图像,正在日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于坐在电视机前的时间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得到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但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对于这种图像挑战的力量也越来越强烈。
五 文学与图像
让我们再次回到“图”与“词”之争上来。“图”与“词”之争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古代突出表现为诗与画的关系,而到了现代,文学与电影或电视的关系则成为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这里面是否有某种继承关系,这也许可以成为我们考察的切入点。
关于诗与画的关系,贺拉斯喜欢将两者放在一起,从而对诗歌创作提出一些要求(注:贺拉斯:《诗艺》,杨周翰译,见亚里斯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合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第156页。)。莱辛在著名的《拉奥孔》中则想说明诗与画之间的界限,说明诗歌是时间艺术,因此需要表现,而画是空间艺术,因此需要美。前者是在古罗马时期,带着对希腊留下的伟大的造型艺术作品的崇拜心情,说明诗歌风格方面的道理。而后者则处在启蒙运动中,力图说明诗歌在情感表现方面的力量。一般说来,在历史上的艺术革新中,文学都起着先行者的作用。冈布里奇指出,希腊的造型艺术是在叙事性文学,即史诗和戏剧的影响下才产生了逼真性的要求。文学从再现什么(“what”)到怎么样(“how”)的追求,对于造型艺术逼真性的发展,是一个推动力。罗马帝国后期艺术追求精神性表现,与神学的气氛和抒情诗的兴起有关。在中世纪,《圣经》中的各种描绘,成为造型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文艺复兴中,文学的世俗性引领着艺术的世俗性。在此以后,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都是艺术上相应潮流的先河。只是到了20世纪,文学上的先锋派与造型艺术上的先锋派,才出现了分离。在中国,诗画一律的说法,一方面成为诗的意境进入绘画,从而对绘画进行改造的根据,另一方面绘画业也通过与诗歌的联系而使画家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中国的“文人画”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新画种,而且是一场彻底改变整体绘画风格的艺术运动而出现的。具体说来就是,不是画家上升为诗人,而是诗人兼任画家,进而改变绘画业的发展走向。
《拉奥孔》关注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之分,指出绘画和雕塑长于描绘,只能在空间并列和陈列动作,用姿态暗示动作,而诗则相反,长于记述动作,只能通过动作用暗示的方式来描绘物体(注: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7章。)。他没有也不可能说到一种情况,这就是当图像也成为时间艺术时,情况会是怎样。这种情况在莱辛时代不可能出现,而到了20世纪,这已经成为事实。随着电影和电视的出现,过去的时间与空间艺术的分野就受到了挑战。人们将之说成是综合艺术,这种说法具有一种并不完全正确的暗示,仿佛这些新的艺术在结合不同的艺术门类的特点,特别是文学与造型艺术的特点。实际上,新的艺术并不是传统艺术因素的叠加。随着时间性的加入,原有静态造型艺术的一些规则早就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成为全新的艺术门类,有着自己独有的规律。影视艺术与文学形成新的关系,从而使“图”与“词”之争呈现出新的面貌。
在新一个层次的“图”与“词”之争中,影视艺术与文学作品的改编是一个富有理论意味的现象。大体说来,这种改编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是文学名著的改编,所改编的作品由于原著而闻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被多次搬上银幕和荧屏,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则多次被影视艺术所演绎。这些改编对社会的影响力,常常依赖于原作的权威地位。对于这种改编,我们可能会有改得好与不好的评价。所谓改得好与不好,是否体现原作精神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因此,作为文学作品的原作仍起着主导的地位。第二种是影视艺术创作者选取文学作品作为素材进行再创作。原作可能是不太知名,或者是只在文学圈子里知名,由于影视艺术家的改编而为一般大众所接受。从建立广泛影响方面看,影视艺术家显然在起主导作用,然而在创作方面,仍遵循着从原作到剧本到拍摄这样一个路子。也就是说,这仍是一条从词到图之路。除此之外,还有种种对原作的戏说,这种脱离原作的自由创造,常常借助一种与原作格调的对比和张力关系。
更为重要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挑战:一些影视艺术努力冲击当代技术条件所能提供的视觉效果极限,向观众提供目不暇接的视觉大餐,并有意无意地压抑其中的文学性因素。这一现象作为一种艺术尝试,在倡导多样化的今天,当然可以成为多样中的一样。但是,如果由此而对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进行无限引申和扩展,证明图像性在取代文学性,则根据并不充分。图像艺术的成功并因此而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形成与文学关系的疏离,作为一种新艺术风格创造的尝试是有意义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图像时代的到来或文学的终结。至于那种违背自己的感受,用图像转向的说辞来为一些只提供视觉效果而在审美上不成功的作品辩护,则更不足取了。
六 图像、语言和声音
在中国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说法,图像代表感性,语词代表理性。于是,图像时代的到来代表着感性的胜利,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印象性的描述而已,不能当作学术术语来对待。
一方面,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证的,图像,特别是那种运用透视理论构筑起来的图像观,是建筑在数学和科学观念基础上的;另一方面,那种将语言归结为理性的观点也不符合实际,语言的起源恰恰是建立在人与人感性交往的经验基础之上的。
图像带给现代社会的,恰恰是另外一种东西。图像(image)来源于拉丁文的Imāagō,意思是像某物。人类社会从相信图像与实物间有神秘联系,利用图像施行巫术,发展到认定图像只是实物的摹仿,在摹仿说的引导下迎来造型艺术的繁荣时期,这是“理性”的第一次胜利。图像包围人类,使他们不再过问图像背后的实物,这既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与视觉优先性的意识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理性”的第二次胜利。从照相到电影、电视、数码技术和互联网所代表的恰恰就是这种方向。这时,图像与世界分离,人们生活在一种错觉的世界之中。
人们在谈论图像转向时,喜欢引用海德格尔关于世界图画的论述。本来,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要区分“世界图画”和“关于世界的图画”(注:海德格尔:《世界图画的时代》。这里的解说参见William McNeill,The Glance of the Eye:Heidegger,Aristotle,And The Ends of Theor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p.166-173.)。后者是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都具有的图画。当古代中国人讲“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注:陆机语,转引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之时,说的都是这种图画。这种图画只是世界的再现,我们通过这种图画生活在世界之中。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是由于人的主体性与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人越来越生活在一种所谓的“世界图画”之中。这种图画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它们并不一定指向外在真实的世界,但却具有逼真的外观。一些主张图像转向的人,如弗里德里希·詹明信和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等,都对电视带来的这种幻觉的发展忧心忡忡。
面对这滚滚的视觉洪流,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听觉的文化革命的构想。他说:“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中,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对此,惟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堕落还是得救,灾难还是拯救——这就是不同选择的图景,人们正试图以它来搭救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231—232、168页。)尽管怀有这么大的期待,他却同时仍然对听觉保持一种疑虑的态度。他的文章的题目是:“走向一种听觉文化?”这个问号说明他的一种试探性立场。在文章的最后,他仍回到一个话题:“安静地带”。
看来,这似乎仍符合一个古老的道理,“大音”还是“希声”。感官的轰炸后,人还是需要宁静(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231—232、168页。)。当然,听觉的拯救当然只是假想而已。我们可以生活在视觉的幻觉之中,也可以生活在听觉的幻觉之中,并且,两者都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更逼真,更具虚拟性,产生更具浸入性的经验。听觉的出现,甚至可以与视觉协作,制造更具虚幻性的图像。也就是说,成为制造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图画”的工具。但是,韦尔施的意图仍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目的不在于听觉,而在于拯救,并将拯救寄希望于视与听的竞争和平衡。
七 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中国,谈论“图像转向”的人常常将这个话题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联系起来。但是,他们常常忽视对不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辨析,对这种“审美化”应持什么样的立场,中国的研究者们似乎讨论得也不够充分。
众所周知,审美地看待世界与审美地生活并不是一个现代现象。中国古代的庄子,也许可以说是最早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倡导者。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而人则须“虚静恬淡寂漠无为”(《庄子·天道》),在生活中像解牛时的庖丁那样游刃而有余地(《庄子·养生主》)。除了庄子之外,一些儒家经典中所讲的诗乐舞的统一,具有将礼教制度审美化的功效;至于后来的琴棋书画并举,并不致力于一种艺术概念的寻找和诸高等艺术的组合,而是一种对才子生活方式的描述和提倡。在西方,古代希腊有大量的对世界美和生活美的论述。至于中世纪,《圣经·创世纪》中有一句话:“神看到所造的一切,凝神注目,确实是非常美。”这句话是“世界是美的”的权威证明,在中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是从这些论述中直接生长起来的,而是通过对康德以后的现代美学批判而实现的向古代人审美观念的回归。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具有这样一层含义,即挑战康德所描述的对审美无功利和无目的的片面强调,挑战那种艺术成为封闭、自律、精英性活动的美学观。
艺术的自律或独立,艺术自身生长的有机性,艺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存在,或者说,罩在艺术之上某种特殊的、给人以神秘感的光环,随着一种所谓的“现代性”的发展而得到高度发展。一种本来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发展起来的贵族趣味,在资产阶级新贵们那里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对这种理论的批判,日常生活审美化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美学界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思潮(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参见《第14届国际美学大会论文集》(卢布尔雅那,1998年)和《第15届国际美学大会论文集》(东京,2001年)。)。
在今日世界的美学圈,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述产生最大的影响的还是叙斯特曼和韦尔施。叙斯特曼通过“拉谱”(Rap)音乐的解读和一种“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的思路,从平民的角度对精英性的分析美学提出了挑战(注:参见理查德·叙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彭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叙斯特曼早年曾编辑过《分析美学》一书,常被人误解为是分析美学家,他的《实用主义美学》和近年来的一些其他著作,都表现出他与“分析美学”决裂。)。韦尔施则将审美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1998年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第14届国际美学大会上,他作了题为《体育——从审美的观点看,甚至作为艺术?》的发言,产生了某种轰动效应(注:见Philozofski Vestnik (Filozofski ins titut,ZRCSAZU) 2/1999,第213至236页。)。这篇文章的观点本身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但它却以一个突出的姿态向人们宣示美学正在超出传统的,由黑格尔所规定而由分析美学家们所继承的限定——艺术哲学(注:高建平:《走出唐人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216页。)。
当代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实际上在三个层面展开的:第一是它的治疗性,第二是它的政治性,第三是它的审美性。
从治疗性方面看,现代消费文化为快感的满足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但是,什么是对人有益的快感,这个问题仍然会提出来。欲望的压抑会造成不健康的身体和心理,因此,身体的解放和心理的解放是有益的。这种思路中也许有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子。但是,过度的放纵也会有害健康。如果说甜蜜的生活就像糖一样的话,对于营养不良者,糖的确是一个好东西,而对于营养充足的人,吃糖太多不是好事,糖甚至被一些人看成是毒药。什么样的享受才是健康的享受,这既是一个道德和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生理学和医学问题。
从政治性来看,我们可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倡导平民的文化权利还是赞美富豪们的穷奢极欲?显然,很多当代国外美学家谈论的都是前者。无论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倡导通俗文化的新实用主义者叙斯特曼,还是其他一些学派的美学家,如马丁·杰、詹明信、本雅明、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等人都是如此。与他们相反,一些中国学者说的是后者,他们将日常审美化等同于富人对高档次享受的追逐和不能获得这种享受时的艳羡之情。尽管上面的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冠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名,两者都是对传统艺术概念的挑战,但却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当然,对于西方学者来说,倡导平民的文化权利是一种政治上的正确,这种做法甚至被一些人批评为政治上的左翼机会主义者。但是,这种从《圣经》直到现代社会长期而深厚的为平民服务的观念,这种政治上正确的意识本身,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起着有益的制约作用。然而,一个在革命时代曾长期倡导平民意识的中国,由于政治上的钟摆现象却抛弃了这种“政治上正确”的观念。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公平和正义已经成为强烈的社会要求,希望它们也能早日进入人文学术的视野。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生活在发生变化,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一种潮流,然而承认这一潮流与站在什么立场上对待它,却是两回事。资本与技术合在一起,可以产生种种新的可能性,艺术与美学的存在环境也在不断地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仍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最后,我们再归结到审美性上来。韦尔施指出:“处处皆美,则无处有美,持续的兴奋导致的是麻木不仁”,“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经如此成功之时,艺术不应再提供悦目的盛宴,反之它必须准备提供烦恼、引起不快。如果今天的艺术品不能引起震惊,那它多半表明,艺术品成了多余的东西。”(注: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231—232、168页。)当我们有了美的广告招贴画,美的手机,美的居室之时,艺术的作用改变了。它不再需要给人以甜美,而需要给人以力量。在审美疲劳之际,人们期待一些有阳刚之气的东西出现。
八 视觉、听觉与活动着的人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提出要对语言和逻辑背后的生活予以关注。他指出:“为真和为假乃是人类所说的东西;而他们互相一致的则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2页。)维特根斯坦思想曾为分析美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他的著作是分析美学家的“圣经”,但是,正是上述对“生活形式”的重视,为走出分析美学提供了思想依据。
正像神创造世界不能最终归结为“词”创造世界一样,无论是图的世界,还是词的世界,都不可能是最终的世界,最终的世界是活动着的人的世界。德里达批评语音中心主义,强调书写的重要性,可以被看成是视觉向听觉的挑战。许慎所描述的那种汉字从结绳到书契的过程,暗示着一种书写具有语音之外的独立起源的含义。文字活动与语音是一种相遇并逐渐相互配合的,而不是依附于语音的“符号的符号”。通过对文字意义的重视,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文字符号系统与语音符号系统的相互独立,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对理性主义毒素的消解(注:对这里所说的“双重攀附”的详细论证,请参见拙作《“书画同源”之源》一文,载《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2年(秋季号)。)。梅洛—庞蒂从肉体的活动出发,也是一种走出认识论之后所进行的意义的探寻。对于这种倾向,W.J.T米歇尔强调其重视书写痕迹,从而归结到视觉的一面, 实际上,当我们将之放置在图与词关系的语境中进行讨论时,就可以看出,这是对视觉的挑战。中国古代的文人画,致力于超越形似的气韵和用笔,起的就是这种作用。
从以上所有这些论述中,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对人的活动的重视。在讨论这些观点之时,我还是坚持回到马克思的观点上来,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世界不处在我们的对立面,而处在我们的周围。“图像世界”离我们越来越近之时,真实的世界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回到真实的世界,这才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视觉与听觉,图像与语言,是我们生活所借助的符号,人被这些符号所包围,但归根结底,人仍然会成为这些符号的主人。视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取代听,视与听的平衡基于人性的冲动,但是,处于这种冲动背后的,还是人的活动,人的实践。尽管科技与市场这两大驱动力会使艺术产生种种变化,我们却只可能有这样一种后现代: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会使自身与生活的结合日益紧密,而不是制造一个幻觉的世界诱使人们远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