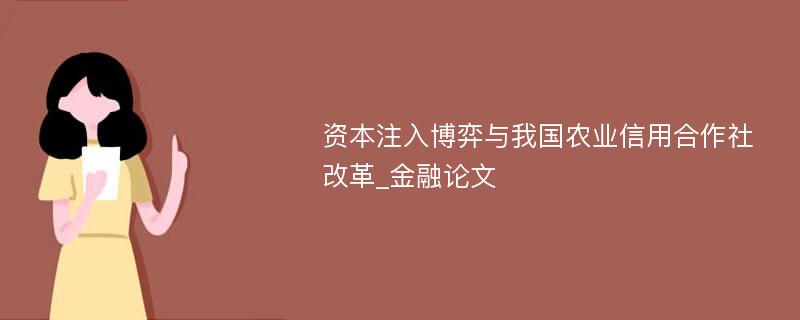
注资博弈与中国农信社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农信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注资博弈: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较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近13亿人口中62%在农村,农村尚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然而,随着国家清理整顿农村“两会一部”、国有商业银行部分机构从农村市场退出,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农村地区唯一的正规金融机构,承担着支持农村经济发展金融支柱的重要职能。截至2005年9月末,全国信用社法人机构33016个,其中信用社30505个,县级联社2408个,市地联社78个,省级联社25个;各项存款余额3146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22359亿元,分别占金融机构境内人民币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的10.8%和11%。同期,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10511亿元,占农信社全部贷款总额的47%,占全部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88%。在此情况下,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不仅关系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个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协调、平稳和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尽快从根本上解决农信社的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已成为一个迫不及待的重大政治追求。正因如此,中央政府才不惜拿出逾千亿资金试图把农信社系统拉出困境,希望通过重振农信社来盘活供需严重失衡的农村金融市场,推动农村经济的新一轮发展。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农信社的发展却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危险境地。2001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52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4%,当年有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金额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账1250亿元;有58%的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总计资不抵债2361亿元,其中严重资不抵债的信用社有1万个,占总数的27%(于宁等,2003)。因此,任何关于农信社的改革方案首先必须面对且无法绕过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农信社积累至今的历史包袱为既有体制埋单,通过财务重组来缓解危机,并更新炉灶、“打扫干净屋子”,为进一步的机制改造和体制重构做好准备。
可以说,农信社的改革最少应当有三个层次的目标:一是财务重组,改善农信社的财务状况,实现农信社经营的财务可持续(financial sustainability),避免出现经营危机;二是健全机制,将农信社改造成所有者明确、法人治理完善、管理和内部控制健全、真正具有活力的农村金融组织。三是改善服务,构建具有适度竞争力和多元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为具有活力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小企业长期、稳定、高效、低成本地提供金融服务。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最初本意在于发展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但在目前农信社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的情况下,不得不倚重于农信社,而农信社又濒临险境,因而又必须现实地正视农信社的历史包袱和财务重组问题。在此方面,中央政府被迫一再退缩。但从三个层次目标的实现条件看,虽相互关联,但仍需做各不相同的政策努力。财务重组主要是花钱埋单、处理历史包袱的问题,它仅是健全经营机制的基础,远非全部。因此,目前所盛传的农信社改革“花钱买机制”实是一种误解,在没有其他政策措施跟进的情况下,花钱最多只能赢取一时漂亮的财务业绩,未必能取得机制方面的长远改善①。
既然当务之急是处理历史包袱的问题,则又不能不追究包袱的形成缘由。从农信社的发展历史来看,农村信用社自成立到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现有的问题也大都肇因于地方政府在人事安排、业务经营等方面的各种干预行为。在农信社现有的不良资产中,大部分都与地方政府的非规范行为有关。据调查统计,这些年来,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镇企业转制共形成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大约860多亿元;所有的县、乡政府及干部借款400多亿。二者合计达1260多亿元,而2001年末农村信用社总的亏损挂账也仅为1250多亿元②。由此可见,农信社大量不良贷款的清收,历史包袱的处理,都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特别是从源头上控制农信社的新增不良贷款、防止既有问题的重演,根本性地解决农信社的问题,更需要切实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既需要尽快解决农信社的风险问题,又无法完全绕开地方政府的干扰。但从历次农信社的改革情况看,始终存在着地方政府与农信社经营管理层的道德风险。每次中央的注资、核销、救助性再贷款等,最终非但未解决问题,反倒可能使问题更趋严重,甚至演变为地方政府攫取中央资金的一种经常性的渠道。地方政府正是看到中央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弃农信社,因而便借农信社“寻租”,不断地侵害农信社的利益,然后将问题与包袱甩给中央。借助“三农”问题的政治化,农信社实际上成为地方政府要挟中央的一种“人质”。利用这一强有力的“人质”,地方政府攫取了大量的中央资金。
中央政府无法放弃信用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同样也无法放弃。只有农信社继续运营,地方政府的利益才能得到持续保障③。因而,维持农信社的持续运营、避免农信社破产倒闭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现双赢的纳什均衡解。最起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农信社的持续运营是对农信社实行市场退出的一种占优解。鉴于地方政府这一顾虑,中央便不会单纯听任地方政府的要挟与摆布,相反也有了向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本次改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中央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动地顺从地方政府和农信社员工的要挟,进行简单的注资,而是设计出了一个与地方政府多阶段动态连续博弈的博弈格局,以降低地方政府和农信社员工的道德风险,避免再次出现“人财两空”的博弈结局。
博弈的开始,作为改革的主导者,中央政府先抛出一个诱饵,承诺中央将部分地承担试点省区辖内各农信社的历史包袱,具体份额是其净值损失的一半即2002年末资不抵债额的一半。同时,中央政府又为此设定了条件,要求参加改革的省、地市、县一直到基层农信社,必须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消化不良资产,同时想办法动员透支户,使自己的净资本从过去的负值达到零水平。也就是,地方政府及农信社自身必须先把自己应负的那一半责任承担到位,中央才可能承担起另一半的责任。
为了克服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的短期行为,真正建立农信社稳健经营的有效机制,中央又提出,即使其承担农信社另一半净值损失,也不是立即便兑付“真金白银”,而是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或再贷款置换农信社资不抵债额的一半,其所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可以计息,但不能作为现金使用。只要当农信社经历两年的实际考验之后,当其真正健全了公司治理机制、建立起了稳健运营的长期有效经营机制之后,才可能真正取得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
从博弈策略的设计来看,这种政策安排步步为营、环环相扣,无疑相当严密,对于中央而言也是占优的。特别是将花钱与机制的改造相关联,力求实现“花钱买机制”的改革初衷。然而,从博弈的实际展开过程来看,由于整个过程仅局限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未真正引入市场化主体,完全由行政推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政博弈的陈规之中。改革主导者为厘清责任、明确标准而不得不设定的中间量化指标,却成为地方政府所追求的改革的全部内容和任务,手段异化为目标,形式沦落为内容,博弈结果与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
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其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条件是,农信社一半的资不抵债额已得以补充;其实际兑付中央银行票据的条件是,2年后农信社资本充足率达到2%,不良贷款率比2002年末下降50%以上。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考核指标,如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完善等,但这些都缺乏明确的量化指标,难以精确考核,真正的硬性指标只有资本充足率与不良贷款率两项。因此,从地方政府与农信社的角度看,真正构成约束的也只有这两项指标。为了达到要求,其当务之急便是尽快增资扩股。
从地方政府与农信社角度来看,正如某试点省一位副省长所说,“这是国家拿资金倒贴,置换农村信用社的破烂,机会千载难逢”。受此激励,便演化出了各地行政主导下的农信社增资扩股“大跃进”运动。为尽早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取得中央的资金,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这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又进一步延伸到农信社与其职工、社员之间。对于其职工而言,“只要先把钱掏出来,中央银行的钱就能马上到位,这样就可以赚钱,马上分红”而且“工作有保证,饭碗有保证”;对于农民社员而言,“不入股就不能贷款”,而且“入股立即就能取得比存款利率还高的红利”(常红晓,2004),再加上其它种种诱惑,使得增资扩股真正成为职工、社员积极广泛参与的一场运动。
对于地方政府、信用社职工和社员而言,唯一所关注的只是近期内资金投入与回报的比较,无一真正关注农信社的经营机制的再造与治理结构的完善。由此使得中央政府再次在博弈中为地方政府所“算计”,一场立意于“花钱买机制”的改革,最终“种瓜得豆”。农信社的历史包袱与经营困难问题虽在增资扩股与中央注资的影响下得以缓解,但根本问题仍远未解决。
二、小农经济与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既有政策的盲区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着农信社改革所进行的注资博弈过程中,双方所共同关注的仍然在于如何再次修补已然千疮百孔的农信社制度,始终未跳出农信社这一体制之外进行求解。双方博弈的均衡不过是如何分摊农信社的修补成本,而不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求均衡,因为在此博弈过程中,农村金融服务真正的需求者始终被置身事外。
饶有意味的是,许多农村地区都流行这样一幅宣传标语——“把农信社办成真正的银行”。可以想象,这一口号绝非农民的要求,因为一旦成为银行,农民便无法享受到其服务。相反,农村金融组织越正规化、越“官化”,越有利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农民则越享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金融服务。这便涉及到目前农村的金融服务需求问题,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现实中来。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至今所持续推进的农村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对1950年代初农村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失当的纠偏。特别是,全面推进的家庭联产责任制,重新恢复了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制度基础。而此前,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近乎军事化的手段管理农村,彻底打破了作为封建制度特征的农村宗法势力与地主豪强,同时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持续数千年的农村经济制度。但这种外生性的制度变革忽视了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试图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直接替代绵延近千年的小农经济。在整个农村经济水平尚未演化到相应程度之前,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做法显然过了头。其结果不是农业的持续性大发展,相反却使得农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境地。而在近千年小农经济的发展历史中,灾情似乎都从未如此严重过。
小农经济是中国数百年来农村经济的一种基本制度特色,也是与当时的生产能力与政治文化融为一体、相互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自给自足、自担风险。鉴于农业本身的产业脆弱性,用托尼的话形象地说,这些小农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水中,只要涌来一个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斯科特,1976)。由于不存在正规的家庭外社会保障体系,小农经济的风险基本由农户家庭承担。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建国后所实行的单位内保障,实质上便是家庭内保障的自然延伸。以家庭为核心,逐渐向外辐射延伸,由小家到宗族,由宗族到村,由村到乡镇,由镇及县,再依次到地市、省、方言区、民族、国家等,一圈圈扩展开来,便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这种圈层结构又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社会文化基础。农户的所有行为,都由此打上了强烈的文化印记(费孝通,1947;Skinner,1964-1965)。作为家的扩展,任何一个亲戚朋友都可在某一层次的圈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家庭内保障的要求,也因此赋予每个人为其亲戚朋友提供必要帮助的义务。由此便成就了农村社会之中普遍的熟人借贷与友情借贷。这种经济制度及其文化特征,为小范围熟人社会中合作金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而使得各种民间合会这种充满合作理念和商业智慧的古老的融资方式绵延数百年而不衰。
同时,这种“圈层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特殊的信任结构。由于圈层之间的壁垒,阻碍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体系的建立,使信任仅局限于圈层之内,而在圈层之外则戒备森严。因而中国农村社会既有着小范围内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极端不信任和无序,形成具有强烈反差的二元信用体系。这又进一步限制了现代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发展,使得合作金融一旦走出一定的圈层边界,便无法存续。近几年,江浙地区民间标会的“倒会”风波以及合作升级后农信社对合作金融的实质背离,都是有力的例证。
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农村社会既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也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由于小农经济本身周而复始重复的简单再生产,难以进行规模扩张,其相当窄浅的经济剩余空间无法有效平抑以往年度的损失,也难以为以后年度的损失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因此,以平滑生产波动、有效参与剩余分配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性金融,显然难以适应萌生于这种小农经济条件的金融服务需要。
然而,由于熟人社会在地理分布上一般较为集中,在农业仍然“靠天吃饭”的情况下,家庭内保障难以有效分散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特别是中国本身又处于自然灾害较多的地区,根据历史统计,两千多年来,平均每年1.72次大灾(邓拓,1958)。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时动辄绵延数省,绝大多数家庭无力承担这样的风险,熟人社会内的互助也无法继续。为不破坏国家与小农之间的脆弱均衡关系,防止饥民铤而走险,政府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赈济,国家农贷体系自西周以来绵延数千年,虽周期性地废了又立、立了又废,但其基本性质与格局没有多大改变。
此外,由于农业收入本身的不稳定性与农业剩余的有限性,小农经济又呈现出典型的“拐杖经济”色彩。所有农户都秉承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基本传统。土地不仅是农户生活的基本保障,是一种生活保险,而且由此衍生出了许多特殊的情感、文化与传统,难以割舍和替代。作为农户家庭经济的重要“拐杖”,非农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农户农业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而成为农业经营的重要补充④。根据这种“拐杖逻辑”,农户的普遍心态就是保持温饱无忧,当家庭预算出现赤字时,首先就是争取非农收入,然后才是谋求熟人借贷。非农收入除了贴补农户生活消费所需之外,也倾向于增加农业的生产资金,如购置土地、购买机车农具等。因此,非农收入的多少,与农民生产性的金融服务需求成反比(黄宗智,1985、1990;林毅夫、Feder,G.刘遵义和罗小朋,1989)。
总之,对于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次序和金融需求结构便是,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如果家庭预算仍然存在缺口,就去寻求外源融资。外源融资的次序则是,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其次则谋求国家的信贷支持,最后不得已便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以争取生存所需的非生产性资金。对于农信社这种制度,从一开始便既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圈层结构相背离,又未遵循国际公认的合作制的基本原则,以致“从来便没有实现真正的合作制”(谢平,2001)。农信社作为政府外生供给的一种金融制度,既秉承着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传统思想,但又实行采取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化之间,背负着双重的职能,最终在地方政府干预和内部人控制双重压力下难以为继。
三、农信社体制:国家无法割舍之痛
上面的讨论表明,对于国家而言,维持农信社这一既有的农村正式金融制度供给,注定难以逃脱地方政府及农信社职工等内部人的“算计”。另一方面,农信社这一外生的金融制度供给又不是目前中国农村所真正需要的。但为什么国家仍然如此痴心不改、不遗余力地向农村提供着这种并不完全符合农村金融需求的金融制度,为什么国家不能从农村金融市场退出,放任农村内生金融制度自主发展?
从农村内生金融的发展来看,正如前面所分析,小农家庭的生存经济决定了其资金需求的非生产性,主要是突发、大额以及明显的特殊消费如丧葬婚嫁或用于建造新房舍等,这部分资金主要依靠亲朋好友的友情借贷解决,一般不计息。这种非正式借贷几乎总是用于各种特定的目的,通常不增加农业生产中的净流动资金。也正是由于这种资金需求通常与生存相关,资金需求弹性极小,当友情借贷无法解决时,便只有求助于民间的高利贷市场了。友情借贷与高利贷统一组成农村社会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并且已成为目前农户资金需求的主要提供者。农户的大部分金融服务需求都由这些非正式金融市场提供(张杰、谢晓雪、张淑敏,2005)。
目前农户的金融需求基本依靠友情借贷、高利贷与官方的信用社借款三者来共同满足。从三种不同信贷制度的提供方式看,友情借贷较为普遍,但不确定性较大,不可持续性强,面子成本高,只能偶尔为之;高利贷则无面子成本问题,也无数额限制,但利率负担重,常常难以承担;官方的农信社贷款,常常实行较低的优惠利率,但限制条件多,数量有限,难以取得。
尽管数千年来,高利贷一直为上层统治者与基层民众所共同谴责,但由于正式信贷市场与非正式信贷市场的严重分隔,彼此之间一般不能有效替代。正式贷款一直严格限制其生产性用途,且期限接近生产周期长度,无法打破市场的分割,替代非正式信贷市场。尽管历史上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试图以正式信贷制度将高利贷等非正式信贷制度挤出农村信贷市场,但始终未能成功。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即是此例(张杰,2005)。
从非正式信贷制度存在的基础看,根本在于农户的低收入水平与“生存经济”状态。家庭保险功能与低收入水平只能与传统的金融需求和信贷制度诸如官方借贷、友情借贷以及高利贷相伴随。小农经济本身的运营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内生出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制度。因此,为了将农村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相对接,通过引入现代金融制度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政府要做的不是一厢情愿地直接去推动某种自己认为是好的金融制度,而是要想方设法让农民积累财富和提高收入,让他们逐步具备提出正常金融需求从而有能力利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让其自己选择合适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只有当农民收入普遍提高之后,面子成本提高,友情借贷才会减少;同时,其资金需求弹性也将随之提高,逐渐便会减少了对高利贷的需求,也会减少对政府低息救济性的国家信贷的需求。相反,在此过程中,其金融服务需求将逐步转变成对现代商业性信贷的需求,信贷市场的分割问题将逐步得以消除。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经营较好的原因。
但问题是,怎么提高农民收入?单靠农业似乎不是根本出路,根据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提高土地收入有极限。因此,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根本仍在于农业之外,是农村大社会的问题,必须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农民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而农民的非农转移,其根本环节又在于农地问题。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了,中国便不可能彻底完成工业革命和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需要农民增收,而增收的关键又在于土地所有权改革,界定和落实农村土地的产权。但从目前来看,基于土地本身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实现农地产权的清晰界定,较长时间内仍将是农民与少量土地相关联的小农经济,短期内不可能在农村地区内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中央勉力维持农信社体制,实质上就是数千年来国家农贷制度的合理延伸。即便是中央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变形、严重背离政策初衷,也并不意味着中央注资政策的失败,注资是由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小农经济自身的逻辑所内在决定的。而且可以预见,这次的注资绝非最后的晚餐。在农村内生金融市场获得长足发展之前,国家外生提供的信贷制度便不可或缺,农信社体制即使再不合理,作为唯一的农村金融机构也仍有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因而,从长期来看,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要充分考虑并尊重农村经济主体的内生金融需求;但从短期看,考虑到农村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发展的长期性,必须继续维持农信社体制,竭力避免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真空。缓解国家与小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使事先已预见注资的悲观结果,也不能放弃改良的努力
四、结论
本文以中央注资承诺引发的新一轮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为背景讨论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困境与内在逻辑。本文的研究发现,此次中央政府的注资行动引发的是又一轮政府间的金融博弈。由于受信息不对称因素的扰动和约束,这场看似顺理成章且不存在明显逻辑缺陷的改革行动最终只能因一厢情愿而无功而返。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深层次的原因仍然在于,以政府间利益博弈为主线而展开的农信社改革行动无一例外地将农村金融的真正需求者置于事外,从而每一次改革行动都注定沦为参与改革的金融利益各方瓜分改革收益的游戏;只不过这种金融利益的瓜分游戏总是被涂上“为农村社会引入现代金融制度”的绚烂脂粉而具有强烈的政策宣示效应。
本文的结论是,从长远来看,只有在充分考虑农村金融需求者的愿望而重新安排金融博弈格局时,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乃至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才会找到真正可行的出路。但在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下,不惜巨资维持农信社体制也实属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悲壮之举。目前,不管是决策层对现有政策的辩解和改革成效的渲染,还是理论界的质疑与批判,大都立于现实与长远的不同角度各执一端。最为关键的是,如何有效弥合传统与现代、现实与未来之间的鸿沟,在保持现有体制稳定的情况下,引入新的博弈主体,改变现有博弈格局,构建一个充分考虑农村、农民金融需求的现实要求的农村内生金融体制。
①后面的分析还将证明,即使在花钱的同时引入了其他外部投资者,企图借助外部投资者的力量完善农信社的经营机制,但从实际博弈的结果看,这种想法仍是一种一厢情愿式的简单幻想。
②数据摘自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前主任张功平的媒体报道,见中国金融网2003年9月28日标题新闻“正确理解农信社改革”。
③既有的案例表明,农信社的清算关闭,对于当地政府而言,最少有三个方面的损失:一是失去了一个要挟中央的“人质”和获取中央资金的有效渠道;二是丧失了实施地方金融控制的基本工具,无法攫取地方金融剩余;三是降低了地方金融供给水平,无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④与过去农村大量存在的“不在地主”相对应,目前散落于城市之中的农民工,其实就是农村的“不在农民”。
标签:金融论文; 小农经济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农村信用社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农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