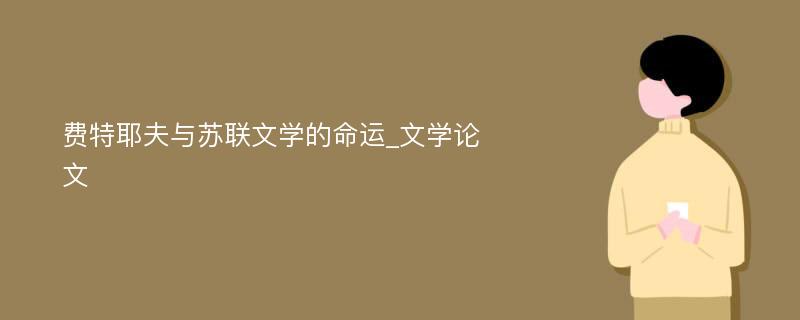
法捷耶夫与苏联文学的命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耶夫论文,命运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十六年前的1956年5月13日,“苏联文学的大总管”法捷耶夫在地处莫斯科西南的别列捷尔基诺的别墅家中开枪自杀。这位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而失势的前作协总书记,被定为死于醉酒自杀。而他有一份遗书则秘而不宣,直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才露面。
遗书中,这位与斯大林时代的文学共命运的文学总管控诉着自己的和苏联文学的命运:文学,这新秩序的最高产物,已经被玷污、戕害、扼杀……我被变成一匹拉车的马……我们被贬低到孩童地位,被消灭,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之为“党性”。他用自己最后两部经典的创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写的一成一败两部小说——作为该遗书的证词。
第一部是小说《青年近卫军》,它属于斯大林时代不多的经典文学“珍品”。它的遭遇,对于思考苏联经典文学的创作动因、过程、功能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
首先,写作这部反映卫国战争中共青团地下斗争的小说,是接受苏联共青团中央的任务。法捷耶夫1943年8月开始创作,1944年底完成。小说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1946年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接着被拍成电影。看来,似乎一切顺利。但事情突然发生逆转:1947年秋天,斯大林看了电影,发现有“一系列不完善的地方”。于是,《真理报》登出题为《“青年近卫军”在小说里和舞台上》的文章,指出:“小说没有写出能说明共青团的生活、成长和工作的最主要的东西——这就是党和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作用……在法捷耶夫的小说里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管理部门’,没有组织。”
这真是严重的失误。幸亏法捷耶夫有机会悔悟:“在三个不眠之夜后,我决定像每个作家该做的那样去做——重写自己的书。”“一次不成,将写两次、三次。一定执行党的指示。”
很多材料证明,法捷耶夫在三四年里是怎样惨淡经营、重煮这锅“夹生饭”的。他感慨道:“你瞧,新增写了10章,如不这样做,我能写一部不比《毁灭》差的中篇小说。”《青年近卫军》的新版本加入了党组织地下活动的章节,突出了党的领导。虽然许多人评说“还是第一个版本好”,认为第二个版本在“把愿望当作现实”(西蒙诺夫);认为这些“补充和牵强附会的修改,冲淡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感染力”(李英男);甚至指责法捷耶夫“根据批评修改自己已经发表的小说,这证明他不是作家”,“是作家的怯懦,是不相信自己本身和不相信自己眼光的正确的表现”(沙拉莫夫)。但是小说毕竟符合了当时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卫国战争胜利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1951年12月,《青年近卫军》新版的发表成为一个文学工程:首先,《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经过创造性的改写之后,好书变得更好了。这部作品,特别是对青年来说,加强了长篇小说应具有的教育意义。法捷耶夫虚心地接受了党的批评。党的批评的鼓舞力量帮助作家把他的优秀作品提到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随后,12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法捷耶夫第二枚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文学艺术发展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法捷耶夫后来这样说:“开始对于那种批评我非常生气,非常!事实就是事实嘛!我是使用了文献资料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员直接参与青年近卫军的活动嘛!……可是,可以这么说……生活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总是在摧毁人的自负。批评是对的,文献找到了根据……”
实际上,摧毁他的自负的未必是生活,而是斯大林的思想。他自杀前不久还把小说又读了一遍,觉得新的章节与以前的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甚至为过去小说里没有这些章节而感到奇怪!这时候的法捷耶夫是多么容易说服自己的创作灵感啊。
这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珍品”到此本可盖棺论定,但是之后几十年间又此起彼伏地生出许多是是非非。
1960年,当年担任过“青年近卫军”第一任政委的特列季亚克维奇(不是小说中所说的奥列格·柯舍沃伊)得到平反,并授予勋章。接着就有文章跟进,宣称柯舍沃伊不是“青年近卫军”的政委;1991年11月,《自鸣钟报》刊登沃林娜的题为《柯舍沃伊的母亲哀悼的是谁?》的文章,文中甚至说柯舍沃伊是个爱出风头的冒名顶替者,一有危险就溜了,并没有被德国人杀害。另一篇题为《奥列格·柯舍沃伊是虚构人物》的文章说,“青年近卫军”根本没有政委,这是法捷耶夫捏造出来的,又说柯舍沃伊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安插的人,而“青年近卫军”则是在顿巴斯地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的一个分支。1999年《绝密报》第5期上刊登了舒尔的一篇题为《“青年近卫军”:真正的历史还是第20056号刑事案件》的文章,干脆认定,“青年近卫军”被虚构了两次:它先是当年克拉斯诺顿警察当局为了邀功请赏而虚构出来的,后来又被法捷耶夫虚构了一次,当年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克拉斯诺顿的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
从文学视角看,这些对“青年近卫军”史实上的探究,无论真伪是非,无一不是和法捷耶夫的小说紧紧勾连。而愤怒斥责这些充满“歪曲、诬陷、诽谤”的揭秘文章也无一不是和捍卫这部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或许就是因为法捷耶夫的小说已经不再是一本单纯的文学读物,它已经成为一种能够直接影响现实、影响人的命运的东西。
例子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星火》杂志(1990年第44期)刊登过小说中描写的两个姑娘在几十年间四处申冤,最终平反的信息。一个是小说中描写为撅着两个小辫子的维里科娃,一个是小说中描写为棕红头发,高颧骨,染着红指甲的利亚茨卡娅。她们每月领取23马克为报酬为盖世太保当情报员。小说这样描写道:“他们从小就从父母和亲朋那儿学来了一套世界观,那就是世上人人都只为自己个人的谋好处,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拼搏着不让别人排挤掉而是踩着别人捞到好处。”在苏联通用教学参考书中指导中写到:“课堂上应当讲清我们社会的渣滓们的变节行为的根源,应该指出使维里科娃和利亚茨卡娅走上叛变道路的那种没有坚定立场、乐于在德国人统治下苟生的心理。为了自己的小命,她们葬送了多少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员的生命。”(《中学俄罗斯文学教师参考书》,基辅,1977)而在《中学苏联历史录音文选》中也谈到:“维里科娃出卖了克拉斯诺顿市的小组,而利亚茨卡娅在狱中……还为了得到几件衣服和巧克力而供出她在牢房里偷听到的谈话。”
文学想象和历史纪录交织在一起,可以用于爱国主义教育。可见,法捷耶夫天才的想象力和栩栩如生的表现力的价值怎么估计也不为过。
但是冤案一被平反,就有文章为这些“传奇故事的人质”鸣不平。其中讲到《青年近卫军》发表后,小小的利亚茨卡娅怎样离奇地一变成为国家要犯,被押到莫斯科国家安全总部的监狱,侦查员换了许多,问题就是一个,让她承认出卖了青年近卫军(实际上,她被德国人抓捕时青年近卫军已经被摧毁,她也不知道有这么个青年近卫军)。她不承认,他们便笑道:时间会为我们工作的。她终于吐血了,承认了,签字了。于是被押往斯捷普拉格。在那儿,利亚茨卡娅作为一名“特别危险的罪犯”、“青年近卫军的叛卖者”备受痛苦。1956年她被放了出来。她向各方申诉,但回答都是一样:“没有重审此案的根据”。直到1990年3月16日,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以“在她的行为中缺乏犯罪要素”而予以恢复名誉。
小说中的另一位主人公维里科娃战前曾在共青团斯大林州委工作过。德军撤退后她被自己人逮捕。理由是:“你这么一个积极的共青团员,怎么能活下来了?”人们追问道:“你说说,你是怎么出卖青年近卫军的?”可是她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么个青年近卫军。她被关押了1年零9个月,又没经任何审理就释放了,不过被开除了团籍。她改换姓氏,迁居别市,可还是被“认出来”:“这就是《青年近卫军》里的那个某某……”斯大林死后,她写信给法捷耶夫,但杳无回音。多年后,当她带着儿子来到克拉斯诺顿博物馆,馆长送给她儿子一本《青年近卫军》,扉页上题道:“读完它,自己作结论。”
那些批评这部作品的文章质问到:“应当向法捷耶夫提一个向上帝回答的问题。他在准备自杀时,是否还记得一个17岁的小姑娘,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用无情的笔法把这个小姑娘描绘成一个同德寇睡过觉的狡猾的小妓女,一个每月从警察局领取津贴的间谍。”
本来人们没有权利要求一个作者负起这个责任。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法捷耶夫会感觉自己是无辜的。而且法捷耶夫早就声言,虽然小说中的一切“基于实事之上”(有提供给他的资料为证),“虽然我的小说的主人公用的是真名实姓,但是我写的不是青年近卫军的真实历史,而是艺术作品。其中有很多想象的东西,甚至有想象出的人物。小说有这个权利。”
“那么,青年近卫军历史上的真正的主人公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幸命运该由谁来负责呢?”批评文章提出的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文学问题,但却是一个与苏联文学特色紧紧相关的问题。不理解这个文学的特色,就不能理解这种文学和现实的微妙而可怕的关系。法捷耶夫坚持“基于实事、使用真名实姓、但不是真实历史”的写作权利。因为他要写的是“第三种现实”。高尔基在苏联作协二次全会上就指出,我们现在应该设法把第三种现实列入我们的日常现象,应该描写它,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会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什么。高尔基说,这“是时代的革命的命令”。看来,法捷耶夫听从的也是这“时代的革命的命令”。他这么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他的权利。
而有趣的是,当“第一种现实”(我们只好创造这个词来指代生活中的现实)和这“第三种现实”(小说中的现实)不太一样的时候,第三种现实的护卫者表现出的态度。按理说,在“第一种现实”中,“青年近卫军”政委的平反、几个人被证实没有叛变祖国,没有斯大林时代认定的那么多叛徒,对革命事业本应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大好事。即使小说中的人物原型不那么光辉,也无损于小说形象的高大,但是事实上引起的却是不安和愤怒。在第一种现实和第三种现实有所出入的尴尬处境中,一些人与其说关注的是在“第一种现实”中那几个人、几家人几十年受到的凌辱,倒不如说更关心维护第三种现实的“稳定”,更愿意相信法捷耶夫当年的文学资料和充满革命浪漫激情的描写。毕竟,“青年近卫军”的文学形象要比那几个第一种现实中当事人的命运更有价值。为了证实这种心理,笔者可以举个例子。
苏联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1947年11月18日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呈送过一份报告《关于筹备有关罪恶迫害克拉斯诺顿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的参与者一案的诉讼程序》,其中说到,“必须指出,在对残害青年近卫军的罪犯的审讯中,克拉斯诺顿部分居民称,德军占据的煤业公司大楼不是如作家法捷耶夫书中说的,是青年近卫军烧的,……也没有证实青年近卫军烧了德国人的职业介绍所,青年近卫军领导者科舍沃依的母亲科舍沃娅没有参加地下组织工作,相反,她和住在她家里的德国军官们关系甚密。”
苏联国家安全部长要为这样一个地区性的案子上书领袖,的确有点惹眼,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在诉讼案件中为什么要一刻不忘地把询问记录和一部文学作品的情节相比对。而微妙之处还在于,国家安全部长提请领袖放心:在这一准备公审的案件中,“所有这些(和书中)分歧不符之处在侦查过程中都已经绕过去了,而在庭审时则将不提及这些事情”。庭审要小心翼翼地“避让”文学情节,避让第三种现实。
斯大林不仅没有怀疑这位部长有否心理疾患,而且没有同意安全部长提出的公开审讯。看来这是对的,万一德国俘虏的供词不按脚本,冲撞了小说的情节呢。“第一种现实”看来应该追随法捷耶夫的小说情节,目的是让“忠实反映和热情歌颂他们的英雄事迹的小说《青年近卫军》将会永远流传下去。”
由此看来,这里的斗争已经和文学无关。这里,文学的功能、作用、品格已经完全变异了。文学不再以教化、感染的方式影响现实,而是要直接创造现实。在第三种现实灼烈的光焰下,真实应该避让,应该闭嘴,应该隐没。可以想象,在当年,这种第三种现实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具有多么强大的能量。它不仅仅是碰伤了上述几个误判者,还将扫荡一切不符合这种第三种现实的东西。一句话,它将直接改造现实!或许这正是它被捧入云天的原因。但是其前提,则是首先被贬到斯大林体制的脚下。
至此,我们才悟出了法捷耶夫的遗书中为什么称文学是“这新体制的最高产物”。因为关键在于,这种“文学”和一般文学有着区别,这是“新体制的最高产物”,是“第三种现实”,至于这种“第三种现实”的设计师,肯定不是法捷耶夫或是其他什么笔杆子,而是法捷耶夫说的,“他一生最怕的人”——斯大林。不知法捷耶夫是否思考过,《青年近卫军》的成功,和他宣告的“文学,这新秩序的最高产物,已经被玷污、戕害、扼杀”是一种什么关系?
如果说《青年近卫军》是成功的案例,那么接下来法捷耶夫创作的小说《黑色冶金》则是失败的案例。改正了《青年近卫军》的错误,法捷耶夫马上从斯大林(也有说是贝利亚或马林科夫)那里请来了《黑色冶金》的题材——主题。它的主要冲突是围绕革新炼钢方法的实验展开的革新派和保守分子之间进步与落后的冲突,这是紧密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主题。按法捷耶夫自己当时的话说,这应该是“献给人民、献给党和苏联文学的一份真正的礼物”,它“要歌唱我们的黑色冶金,歌唱我们的苏联工人阶级,……歌唱我们的党”,它将是自己“一生中所写得最好的作品”。
可是生活不太听话,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时局变幻,“精神”变迁,“提法”换了。原来的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既定的主题越来越被生活本身证实是掩盖着重大社会矛盾的虚伪主题。小说写了一年又一年,法捷耶夫恍然发现:“我完了。作为一个作家我完了。尽管我有创作经验和生活经验,我却不能一眼看出,分不清真假。”总之,他这次没能跟上形势,“第三种现实”没有创造出来!
在给瓦日达耶夫的两封信(1955,8)中,他痛苦地述说自己的《黑色冶金》的主题和人物为何如此短命,是因为自己没有跟上形势:“我的小说需要根本性的修改。那些在1951年到1952年开始写作时构想和编撰的东西中,在我们今天,很多已经陈旧甚至不正确了。在为那些当时称作‘冶金业革命’的技术发明而进行的斗争中,正确一方看来不是那些‘革新者’,而倒是那些守旧派。”而“现在,对于我的那些正面主人公,也得让他们转向……去对官僚主义保守性作斗争。关于向西方学习技术以便赶超的问题,应该有新的提法;……对外国专家的作用也应该有新的提法。一句话,我的一些人物‘已经陷入绝境’。而新的人物已经出现,所以,第一部只得整个重新修改。”在另一封信中,法捷耶夫承认,“我这本小说中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中心的主导冲突……而剩下的只有由众多冲突解决着的中心思想。”
法捷耶夫这篇具有讽刺性的自述,道出当年多少紧跟精神、追赶潮流的文学者、作家们所遭遇过的背运。为了符合一种创作模式,图解一种思想、迎合一种“精神”,一位以创作“基于实事之上”自居的作家的创作境界竟然沦落到何等可悲可笑的地步!无论他的主题和人物如何东扭西转,也不能使他挣脱越陷越深的创作泥沼。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符合创作的基本规律,它不是来自于真实生活的提示,不是来自作家的思考和灵感,而是领受于“上边的”难测而多变的意图。
同时代人科洛索夫回忆起法捷耶夫晚年曾带着醺醺醉意地失声痛哭,对他这样诉说道:“要是你能知道,我有多么痛苦,我站得离那个高峰太近了!”人们说,这本书最终夭折,是他自杀的重要原因。的确,法捷耶夫创作《黑色冶金》的故事应该轰毁了他所忠诚的文学思想,也构成对“文学,这新秩序的最高产物,已经被玷污、戕害、扼杀”这句话的又一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