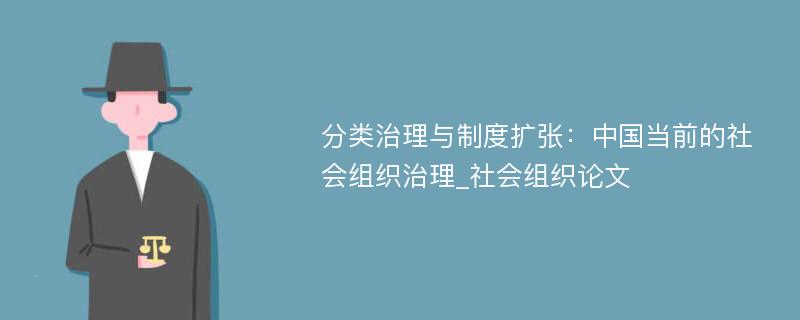
分类治理与体制扩容: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体制论文,组织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以来,社会组织的崛起及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几何级数的数量增长、服务性与表达性的组织类型趋于多元、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各领域、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发生方式,无不昭示社会组织的崛起。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社会组织逐渐放弃非黑即白的极端对立(近代西方的抗争模式与传统中国的民间与朝廷二分)思维,发展出不同于西方与传统的“意义框架”,构建出非对抗的,甚至是建设性的行动框架。①在此背景下,“社会组织”概念逐渐取代了过去常用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不同称谓,被政府接受且初步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中国特殊语境和制度环境中的概念。然而,中央政府的社会组织治理却较为迟滞,仍在沿用饱受诟病的1998年制定的“双重管理”制度。与此同时,深圳、南京、广州、上海、江苏、云南、海南等地政府已经在以“规定”、“通知”等方式,探索备案制、直接登记等降低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实践,行业服务、公益慈善、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区服务等四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社会组织登记制度的地方改革,意味着必须对现有社会组织模式及其治理制度加以拓展与改革,以期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在实践上,地方政府正在传统分类控制体系的基础上探索更为细密、具体化与精致化的分类治理模式。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对于利益表达性组织与社会服务性组织②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这种分类治理模式比单纯的行政控制或强硬的分类控制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它是体制扩容的政治转型结果。尽管现有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都在地方政府层面展开,但是,从效果看,它确实能够遏制全国性或行业性社会组织联盟的出现。 社会组织治理:文献与进路 从发生形态上说,社会组织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事物。近代中西遭遇,整体性社会的权力崩解与重建,使各种社会组织匍匐于国家或革命政党之下;革命后社会,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使社会组织成为执政党与政府的“螺丝钉”。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到重塑,政府权力在经济领域的部分撤出(政企分开),导致从体制松绑中逸出的个体直接受到强制资本及裸露社会的侵害,公共产品与社会服务急剧匮乏,进而形成要么个体之间各自为战(自焚、跳楼、杀医),要么个体结社而抱团取暖。由此,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生发,1998年制定的“双重管理”制度捉襟见肘。③ 相较于社会组织崛起的现实,社会组织的治理研究明显不够,现有研究集中于社会组织治理研究的两端,而非直面社会组织治理。一方面,从研究旨趣上说,社会组织治理研究更多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案例对象而加以审视,并未直接成为研究对象。关注政治事件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进入了“市民社会反抗国家”时代,关注新型社团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正在出现“市民社会”④,关注人民团体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属于“法团主义”⑤,关注社团“官民二重性”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一个“社会中间层”⑥,而且社团之间的平等合作构成了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结合⑦。另一方面,从研究对象上说,研究者多数未对社会组织加以类型化区分,要么将社会组织视为无差别的整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要么只是在特定个案上深入分析,陷入“局部观察”(康晓光语)状况。相较而言,较为成熟、大体代表中国市民社会整体性研究视角的分析模式是“分类控制体系”的“行政吸纳政治/社会”。⑧康晓光认为,研究结论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自研究者关注的社会组织类型的差异,局部或个案的结论正确,恰好说明政府治理社会组织的手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是一种“多元化管理策略”的“分类控制”。⑨ 分类控制模式承认威权主义的政治现实,从“政府理性人”的假设出发,构建出考察社会组织的“双重属性”——挑战政府与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由此形成了政府的不同控制策略。2007年,康晓光、卢宪英、韩恒将上述分类控制体系模式进一步精细化,提出“行政吸纳社会”的分析模式,⑩将控制策略界定为“限制”和“功能替代”,进而结合实证案例资料,按照结构、行为、功能三个指标将当前中国的民间组织归纳为15种类型,将政府的控制策略归纳为准政府、事业单位、双重管理、归口管理、代管、放任、禁止等7种多元化分类控制模式,而政府的发展策略则包括延续、新建、收编、合作、无支持5种。 康晓光等人的研究提供了社会组织治理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此后的研究大多以支持、反对或修正的方式进行。韩恒指出“行政分割与分类控制”共同建构起分类治理的“条块管理体制”。(11)首先,政府利用行政区划从空间上把社会领域分隔开来,禁止社会组织到其注册机构管辖范围之外的区域活动;其次,在既定行政区划内,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分门别类的分类管理,业务范围相似的组织不能设立第二家,严格限制社会组织的分支机构设置,分支机构下不得再设分支机构,也不允许社会组织及其分支机构从事跨区域的活动。行政分割与分类控制限制了社会组织的规模扩张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 唐文玉将康晓光的“行政吸纳社会”模式修正为“行政吸纳服务”,(12)但其分析对象却局限于服务性社会组织,强调政府的支持与社会组织的配合。“支持”指政府培育和促进民间组织的发展,为其提供场地、资金、信息、技术、组织与合法性等方面的资源;而“配合”指民间组织配合政府的工作,响应政府的组织、号召与政策执行,从而获得政府的支持。尽管唐文玉试图弱化政府控制、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却也不否认这种合作关系中,政府处于主导性的地位,二者是一种依附性的合作关系。“行政吸纳服务”模式并未改变“分类治理”的基本逻辑。 刘鹏虽然试图以“嵌入型监管”模式突破“分类控制体系”(13),但其与唐文玉类似,分析对象局限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而不是康晓光的整体性类型分析。刘鹏认为近年来地方政府的社团管理体制探索(尤其是登记注册体制与政社合作、购买服务、扶持等政府行为)反映出,国家利用其特定的机制与策略,营造符合国家政治偏好的组织运营环境,从而达到对社会组织的运行过程和逻辑进行嵌入性干预和调控的目的,这种干预和调控作用也使得社会组织乐意借助于其所提供的政治机会对国家职能进行反作用,从而促使国家与社会外化为某种合作性关系模式。嵌入型监管模式注意到国家在“特定社会组织”类型上的更细密、更灵活与更精致的治理模式,但是,它也并未超越康晓光的“分类控制体系”,人民团体与免登记社团以及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并不在其考察范围之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分类控制”体系确是政府治理社会组织的研究共识,因此这也构成我们的立论基础。分类控制体系及其变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治理框架,实质上确定了社会组织治理的两个政治背景:第一,“国家主义”与“威权政治”政治权力形态,使国家权力具有优先性,对社会组织抱有戒心而必然进行一定的控制或功能替代,当代中国不存在“不受制于权力支配的自由社团”(14);第二,“民生政治”与“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职能,要求政府必须提供有效而多样化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任何全国性或行业性社会组织联盟必然带有强烈的利益表达倾向,因此,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登记门槛的降低,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国家治理必然从控制“出生证”转移到控制“全国性或行业性社会组织联盟”上,社会组织国家治理的战略目的是如何防止或避免出现体制外全国性或行业性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的分类或类型由此成为治理的关键。从社会组织的类型学上说,康晓光的15种社会组织模式几乎穷尽了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类型。康晓光同时按照政府性程序与营利性与否,将15种社会组织分作四类社会组织类型:“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组织、草根维权组织。(15)依据社会组织的性质功能及其影响力,可以将上述四类社会组织进一步整合为三种:(1)国家财政供给的人民团体与事业单位;(2)政府支持,经费自筹,能够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的营利性、服务性社会组织;(3)草根性、多元化、维权性的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至于政治反抗组织,因其政治性本身就被政府列为异议团体而坚决取缔,而并不在社会组织治理的范围之内。 对应于上述三种社会组织类型,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三种相应的治理模式:第一,推动人民团体及免登记团体的枢纽性社会组织建设;第二,对服务性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制的组织治理;第三,通过领袖吸纳、组织(结构)吸纳与职能吸纳的方式,将草根化、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并入政治体制。 人民团体的枢纽性社会组织建设 人民团体与免登记社团作为法定的全国性或行业性的社会组织联盟,曾被视为中国国家法团主义社会组织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16)但是,关注实际运作的研究者认为人民团体不接地气,它更像“政府职能部门”而不是社会行业群体的代表。为了更好地承接转移出来的政府职能,培育和整合自发性社会组织,更大程度地发挥其行业代表功能,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相继以“暂行办法”、“行动方案”等次法律形式出台文件政策,推动人民团体的枢纽性社会组织建设。 2009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关于构建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暂行办法》,正式提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概念,认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10家单位作为第一批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到2013年,北京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渐趋成熟,实现了对市级社会组织的全覆盖。在广东,政府出台了《关于印发〈2009年珠海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实施计划〉的通知》,开始进行试点式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到2010年又增加了佛山和东莞两个试点地区,发展到2013年,广东省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模式由试点逐渐转向了全省。在上海,从《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2013年工作要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的枢纽型社会组织由最初的地区自主建设逐步向同国外合作建设的模式进行发展。5年间,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形式上更加多样,其范围也实现了由点到面,由少数试点到全面建设的发展。 在新中国的社团制度安排中,人民团体的制度地位符合法团主义的三个特征:第一,一个强势主导的国家;第二,对利益群体自由与行动的限制;第三,吸纳利益群体作为国家系统的一部分,让他们呈现成员的利益,帮助国家管理和开展相关政策。(17)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研究者也发现,在原有体制的惯性下,社会原子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到国家体系”中去,在宏观结构上呈现出不是分立而是多边合作、混合角色及相互依赖的发展形态,(18)在城市社会、农村社会与基层政府都形成了法团主义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空间。(19) 与西方社会组织极力谋求垄断性政治地位不同,人民团体作为枢纽性社会组织,具有政府授予的先天“公共政治身份”,在代表、资源、程序、组织等方面拥有其他团体无法竞争的实力。第一,代表地位。尽管人民团体的社会代表性或许会受到质疑,但是,完善的科层制组织体系确实能够反映内部成员的利益与意志。同时,作为垄断性组织,其代表地位来自国家权力的授予,这表明人民团体具有社会与国家的“双重代表”功能。当然,从代表性的结构偏重看,枢纽性社会组织的社会代表地位更多来自政府的认定,认定条件与认定程序都来自政府。从现实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的主体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还没有民间组织被认定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先例。(20) 第二,资源地位。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民间双方力量的“资源中心”与“转换中介”。(21)政府为枢纽性社会组织提供优厚的政治资源(国家资源、行政资源与合法性资源),枢纽性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首先,国家为枢纽性社会组织提供较为充裕的经费拨款,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组织偏好明显向人民团体或官办NGO倾斜。其次,在行政资源上,枢纽性社会组织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科层制结构依托于政府的行政层级架构,每一级政府相应建立一级人民团体组织,同时还孵化了大量的同类组织。再次,垄断性社会组织利用政府合法性有力地支持或供给了其垄断性的地位,其资源垄断性地位的获得深深依赖于政府。与此同时,枢纽性社会组织还承担着资源分配的角色,在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它是市一级的“项目主责单位”,负责所主管和联系社会组织申报项目的指导、协调和筛选,将政府项目交给有资质和潜力的社会组织承接。换言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外包与发包项目,是通过枢纽性社会组织具体实施的,因此它不但汇聚而且分配着政府的社会建设资源。 第三,程序地位。枢纽性社会组织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或制度程序,将社会个体与群体组织的利益表达输入到政府系统,同时将政府政策贯彻到相应的社会领域与社会群体。枢纽性社会组织的程序地位具体表现在立法环节,参与制定国家层面的行业性法律制度。例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在2003年以来,先后参与了60余项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工作,重点参与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物权法》、《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集体合同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等十几部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还对《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就业促进法》、《物权法》、《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集体合同规定》、《最低工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法律法规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枢纽性社会组织参政议政的程序性地位,是其他社会组织所难以想象的。 第四,组织地位。相较于一般社会组织,枢纽性社会组织具有严密的科层制组织结构。以妇联为例,妇联的纵向结构以行政地域层级为主轴,从中央到省、市、县、区、乡镇五级都相应地建立一级妇联组织,到村则成立了妇女代表会,建立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层级结构;在横向上,涉及海外妇女、女企业家、女法官、女检察官、女科技工作者等女性优势群体的协会和商会、家庭妇女研究会以及儿童福利会和妇女儿童基金会等方面;(22)而在妇联组织内部,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研究室、联络部、妇女发展部、权益部、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和妇女儿童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无一不备,各部门间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沟通,相辅相成。从组织结构上说,枢纽性社会组织具有强烈的封闭性与强制性特征,层级关系加强了组织的内部服从,个体成员也不能自由进出,这使组织从自愿、松散的群体变成紧密内聚的、高密度的统一团体。(23) 尽管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法团主义的基础并不具备欧洲境况下社会发达、国家权力界限清晰、国家与社会分立的基础,社会组织与政府具有亲和甚至附属关系,尤其是政商联盟形成了“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24)、“地方政府法团主义”(25)。但是,不可否认,利用垄断性的全国性或行业性社会组织的地位,枢纽性社会组织建设正在逐渐改变人民团体的“行政化”倾向,政府也试图推动其转型,使之实现一定程度的全国性、行业性全国组织联盟的功能。 服务性社会组织的项目制治理 民生政治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社会服务与公共产品,为此形成了三条相对独立的政策演进的合流。从政府治理社会组织的角度看,项目制最终成为既能满足民生政治需求,又能实现防止全国性或行业性社会组织出现的组织分化策略。 项目制社会组织治理模式是渐进性政策试错的结果。它主要由三条相对独立而又最终合流的政策渐进形成。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最终走向服务型政府。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经历了两个逻辑过程,政企分开调整的是政治与市场的关系,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它意味着全能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渐趋退出,社会组织逐渐形成功能替代。二者以2004年为界,2月21日温家宝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此后,它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目标。第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最终走向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政策经历了从地方政府创新到中央政府推广的演变过程。(26)1995—2002年是起步探索阶段,2003年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代表的试点标志着进入试点推进阶段,宁波、无锡、深圳、江西等地市均开展了相关政策创新。2011年以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进入制度化推广阶段。第三,项目治国模式在上述两个政策脉络上的使用,最终形成项目制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政府通过项目制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并不是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政治运行的耦合,项目制自成一套治国模式(27)。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治理理念在财政政策上体现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类项目措施,从而项目制逐渐作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不再局限于国家治理模式。2012年,中央财政拿出2亿资金购买社会服务,同年3月国家发布《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公告》,11月份出台《关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指导意见》。在中央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积极跟进,出台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暂行办法”、“服务目录”。 项目制的社会组织治理,其内在逻辑是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发包体制。“减少政府许可制度”或“减少行政审批”的职能转变与公共产品的供给空间,最终交给社会组织承接,这一点可以从山东省《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办法》(鲁政办发[2013]35号)看得出来。 发包或外包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体制,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形态与生存空间。尽管从购买方式看,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包括合同制、直接资助制以及项目申请制等多种形式,但是,无论是政府独立性购买还是依赖性购买,都选择了一种非竞争性的“定向”购买。(28)首先,从市场交易的成本收益理性角度看,竞争性购买的招标模式更能体现政府物超所值的购买原则,但是,政府宁可花更多的财政资金定向购买公共服务,而不是彻底地通过市场招标方式购买社会服务。这表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发包体制并未改变政府控制公共产品供给的模式,它只是将原本政府供给的全能模式转变为政府购买的外包模式。其次,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依赖性非竞争式定向购买,有社会组织“内部化”或政府部门延伸的意味。(29)有些社会组织甚至是在接到特定购买任务以后才专门成立的,它与社会组织自身的生长与公共产品供给并无关联,甚至压抑社会组织的自然生产,结果使社会组织对自身活动缺乏完整和长期规划,生存激励并不明显。 不可否认,也有独自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最终进入政府购买的范围,但是,它们一般不是政府的偏好选择,即使被幸运选中也会在购买过程中受到严格的过程监控或嵌入式监控。中国法律向来严苛,“选择性执法”的实质是权力控制。《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民发(2011)209号]对于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项目制有着严厉的过程性规定。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在向“心贴心老年服务中心”购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北京市宣武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供给养老服务的案例中,为了监控项目实施过程,成立了政府相关部门(民政局、街道财政科、监察科、组织部、社区办)组成的申请管理委员会与评估委员会,要求项目执行“一月一检查”,执行环节严格检查,评估结论也非常严谨。显然,任何环节的偏失都可能招致政府的“合法性”批评,甚至丧失“服务提供者”身份。 项目制自身也带有天然的分化性控制因素,即通过功能需求的天然分工而使社会组织无法形成行业性或领域性社团,因而削弱其潜在的利益表达性。这一视角尚未被当前学术界充分关注。这种组织分化策略是通过三种分割实现的:第一,社会服务内容的具体化与专项化形成服务功能分割,导致社会组织的强功能化与弱联合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部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施准则,哪些实行政府购买都有明确规定,并以《项目指南》的方式呈现出来。“项目指南”通常将购买任务分解为数个方面、数十个类别以及数百个具体项目。例如北京市2013年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分为5方面、45个类别、500个项目,项目名称诸如“扶老助残”服务项目、“北京精神”宣传践行推进项目、“一刻钟服务圈”便民服务拓展项目。这些项目名称充分显示了项目的细化程度,终端项目着眼于“具体的工作”而不是“某类型的事项”,这直接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宏观社会功能,也就客观上控制了社会组织的规模化发展趋向;第二,购买社会服务的地域分割、政府主体多元化造成社会组织的分割与分化。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对于组织联盟有两个方面的禁止性规定,不得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严格限制设立分支机构,同时,现有的政府购买是由中央政府确立公共服务类别,地方政府根据中央规定自行确立购买服务,因此,不同地域的政府、不同行政层级的政府以及不同政府部门都在进行类似的“购买服务”,其结果虽然能抑制全国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形成,但其公共服务效果必然差强人意;第三,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种类偏好与限制造成社会组织类别的结构失衡。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的社会服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社区服务与管理类服务,二是行业性服务与管理类服务,三是行政事务与管理类服务。相应地,四类服务性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已经可以直接登记。这意味着,民生服务与民生组织得到了支持与鼓励,而表达性组织受到忽视或限制。这样,民众生活中同样重要的权利保护与意志表达及其社会组织仍然付之阙如。 项目制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选择性”社会组织治理模式,从治理效果上看,它既契合政府职能转变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民生政治需要,又在嵌入式治理中有效分化了社会组织的生长形态与类别结构。而且,其分化策略来自于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与社会服务的专业化,这种自明性掩盖了社会组织的全国性或行业性功能。显然,这是更为高明而符合自然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 草根维权组织的体制性吸纳 199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滋生蔓延直至推翻政权的教训,让政府对自下而上的维权运动保持高度警惕。(30)草根性维权组织作为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一直陷于艰难的身份困境,双重管理制度像一个魔咒使其更多处于“地下状态”。但是,随着政治体制的逐渐开放,其非法身份逐渐改观,政府以某种“默认”(31)的方式“选择性”地接受了它们的存在,并通过体制吸纳的方式实现组织治理。 从社会组织的结构与职能角度,政府的体制吸纳主要有领袖吸纳、组织吸纳与职能吸纳三种形式,后面的吸纳模式一般都包含前面的吸纳形式。领袖吸纳是个体吸纳,领袖吸纳后的组织可能被遣散,维权职能亦被消解;组织吸纳通常延续精英领袖对原组织的领导,或者将之整合进现有的政府体制之中而原有组织得以保存,但是领袖离职或去世都将导致原有组织的衰败与离散,人亡政息;职能吸纳可能表现为领袖与组织结构的“一股脑”吸纳,也可能将草根维权组织的职能吸纳进体制之中而将原有组织的领袖与组织结构遣散。 领袖吸纳,指将草根维权组织的领袖吸纳进政府既有的维权体制中,变政府外领袖为体制内工作人员。领袖吸纳通常运用于公共事件中的危机管理或政府公关,它是体制吸纳中最容易发生,效果最易受限的一种。例如在农民工讨薪事件中,往往有传统遗传下来的“老乡会”等地缘性社会组织的背影,这是“工会缺位,帮会补位”的结果,(32)老乡会中的精英自然成为组织领袖。在讨薪性恶性事件频发的浙江义乌,2000年前后形成了“衢州帮”“定远帮”等地域同乡帮派,它们成为外来务工人员为权益保障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义乌市总工会发现了这个问题,组建职工法律维权中心,“老乡”代言人则被推选为维权中心的联络人员,同乡会自然逐渐破败。再如2012年乌坎事件中新产生的村党总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广东省接受了选举产生的事件组织者林祖銮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后来他被选为村主任,而杨色茂被选为村副主任。(33)精英领袖吸纳,在某种情况下,可能成为政府危机公关的“灭火”环节,而其进入体制之后,会被体制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湮灭或同化。 学界关注最多的是组织吸纳或结构吸纳。组织吸纳或结构吸纳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政府治理困境迫使基层政府理性地扩容体制以接受社会“自然生长”的创设,“以避免非制度化的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34);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草根维权组织既体现出“帮忙而不是添乱”的维权行动逻辑,又体现出较强的社会整合能力。组织吸纳是将正在组织化过程中而又没有正式编制和明确法律地位的草根组织以一定政府授权的方式,纳入到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加以管理。组织吸纳一般是整体性吸纳,内部结构与组织形态均被吸纳进政治体制之中。 首先,组织领袖按照体制要求被改造吸纳。深圳“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案例(35)显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13名联络员中,吸纳了4位业主委员会主任、2位业主委员会秘书,4位小区管理处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附近两所学校的主要领导。在浙江杨家村农民工工会案例(36)中,东阳市总工会采用“地域平衡”、“老乡管老乡,有事好商量”的方式吸纳原有的精英领袖,每个省籍大致设一位工会领导(工会副主席或工会委员)。在领袖吸纳的体制扩容中,不但政治上可靠且有合作精神的社区活动精英,而且社区精英与抗争领袖均被作为整合民意的重要手段而被纳入体制管理范围之内。其次,组织功能再造后被吸纳。“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联络员主要在3个方面开展活动:一是受人大代表委托收集社情民意,开展专题调研形成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或议案提交给人大会议;二是定期安排人大代表与居民面对面交心座谈;三是参与片区公共事务管理,协助街道和社区解决居民反映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此外还组织环保宣传、配合政府部门做好片区环境监督管理,推动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从而使人大代表工作站由一个纯民间性质的草根组织发展为带有些许官民合作色彩的机构。杨家农民工工会被列入东阳市总工会的工作计划,东阳市委、市总工会及白云街道的领导多次深入杨家村指导农民工工会的筹建工作,并向其提供了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组织吸纳的内在悖论是,它以精英领袖和组织结构为吸纳对象,精英领袖离职或去世往往导致组织解散,最终人亡政息。这也是政府的社会组织治理创新此起彼伏却难以为继的内在原因,政府并未创立一种制度性、职能性的社会组织再造。 相较而言,职能吸纳是最深入、也最难发生的一种。职能吸纳涵盖精英领袖吸纳与组织吸纳,但是,与后者的不同在于,它可能改变既有的政治运行或职能设置,创设一种新的官民沟通渠道。温岭民主恳谈会(37)与阳村“叙事活动”(38)是职能吸纳的突出例子。温岭民主恳谈会最初是乡镇与村级内部事务讨论的组织,2000年以后扩展到温岭市所有政府职能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最终被落实到温岭市人大会议期间的预算讨论、咨询与监督过程,被学界成为参与式预算的模板。阳村叙事活动缘起于农民听信谣言发动抗争活动,镇政府因势利导村民“叙事活动”,任何有困难、有想法、有意见的村民都可以到村委会参加每月两次的“叙事”;由驻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组成的“叙事接待小组”相当于村民同村委会、镇政府的联络员,专门负责收集村民的利益诉求,并及时向村党支部、镇党委、政府反馈,为村委会、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叙事制度有效填充了由于农业税取消而失去功能的村干部基层社会的治理空白,通过“叙事——知民情;理事——解民意;议事——集民智;评事——赢民心”使之成为政府体制的重要职能。 我们也发现,国家建构的社会资本在组织(结构)吸纳与职能吸纳中发挥着重要的联结作用。这些组织的发起者大多与政府有关,人大代表、政府职能部门、基层干部都参与了组织的发起、动员;在体制吸纳的运行过程中,政府组织或党员干部个体(“党员亮牌”等形式)积极参与了社会组织的再组织及推动工作;同时,在确认吸纳之后,政府积极为社会组织提供基本的人力资源、经费资源及场地资源。 结论:分类治理、体制扩容与实践性政治知识的生长 分类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治理的基本模式。枢纽性社会组织建设意味着,政府将原本是政机构延伸的人民团体加以改造,一方面使之继续占领全国性或行业性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地位,另一方面使之更接地气,发挥社会/行业整合功能,从而抢占与挤压其他组织联盟的可能空间;项目制社团治理模式表示政府正视民生需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一方面使服务性社会组织提供民生政府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与公共产品,另一方面通过项目分化与过程性嵌入监管避免全国性或行业性服务性社会组织的形成;草根维权组织的领袖吸纳、组织(结构)吸纳与职能吸纳,则表明政府柔性对待原本严防死守的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试图通过体制吸纳实现自身职能增容。显然,这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而精致的分类治理体系,它通过功能替代或分化分割而遏制自发性组织联盟的形成。 这种分类治理,且不论其政治性质是“控制”抑或“支持”,从事实上看,其精细化与强弹性确实显示出政府的体制扩容。之所以是体制扩容而不是政治扩容,是因为社会组织治理并未在国家或基本制度层面,并未出台替代“双重管理制度”的国家层面的制度规定,或以自上而下的规划性、正式性或强制性形式展开,而仅仅是具体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实施的局部性行为,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局部性与具体性,因此,它只能被视为政府体制或政府结构对社会组织的功能性治理。此外,这一分类治理仍然有赖于政府的整体性规划与服务类别建构,发包与外包的社会服务供给机制并未彻底改变全能政府的权力痕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社会组织无法实现自生自治,也无法实现长远规划与规模化发展,无法使社会组织通过行业性、地域性联合而提供更好的社会服务,因此,体制扩容的分类治理是“功能替代”的高级版。 分类治理的政府治理社会组织模式的地方性,说明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并非有意识的结果,也并非“知识导向”的理性制度设计,而是基于治理经验“实践性知识”的生长(39)。邓正来将这种实践探索的知识称为“未意图扩展”的“生存性智慧”,它体现为“渐进性地——而非革命性地——对国家及其治理机构提出新问题和新挑战作出反应,使之调适自身并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促成经济利益驱动在意图之外对政治结果的影响,最终将逐步导致国家原本未设定的改革领域出现重要的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的变化。”(40)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分类治理模式就是上述“未意图扩展”的地方政府回应结果,国家及其治理机构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作出反应,调适自身并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促成在意图之外对政治结果的影响。我们把国家及政府的这种“生存性智慧”的变迁结果界定为体制扩容,用来解释政府采用分类体系具体化地治理不同社会组织的发展需求。 显然,地方政府的实践探索“自然地”符合中国社会组织治理的政治底线——避免全国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出现,社会组织无法在国家层面实现权力竞争。但是,现有的分类控制策略仍有其局限性,枢纽性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任重而道远;市场激励的自发的公共服务性社会组织突破项目制控制而形成全国性或行业性社会组织仍有可能;草根维权组织的社会自主性仍然无法消极对待。 注释: ①朱健刚:《行动的力量:民间志愿组织实践逻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73、277页。 ②从性质上说,社会组织有利益表达性社会组织与服务性社会组织两种。参考:鲁佩特·格拉夫·施特拉赫维茨:《德国的社团和基金会:服务提供者还是市民社会主体?》,载[英]阿米·古特曼等著:《结社:理论与实践》,吴玉章、毕小青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68—382页。 ③中国社会组织的发生学逻辑,参考拙著《社会组织的发生学与类型》,载王向民等著:《危机事件中的社会组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④White,Gordon,“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Xiaoshan City”,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1993,pp.63—87; White,Gordon,Jude Howell & Xiaoyuan Shang,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08. ⑤Unger,Jonathan,“Bridges:Private Business,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147,1996,pp.795—819; Unger,Jonathan & Anita Chan,“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1995,pp.29—53.(安戈、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陈佩华:《革命乎?组合主义乎?——后毛泽东时期的工会和工人运动》,《当代中国》1994年第4期;Saic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New York:Palgrave,2001,pp.207—210; Oi,Jean C.,“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 45,1992,pp.99—126. ⑥王颖:《中国的社会中间层:社会发展与组织体系重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2月号。 ⑦高丙中:《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结合》,《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⑧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康晓光、卢宪英、韩恒:《改革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行政吸纳社会》,载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邓正来曾经对国内市民社会研究状况及康晓光“分类控制体系”、“行政吸纳社会”模式进行了认同与批判性的评论。参考邓正来:《“生存性智慧模式”: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⑨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⑩康晓光、卢宪英、韩恒:《改革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行政吸纳社会》,载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1)韩恒:《行政分隔与分类控制:试论当前中国社会领域的管理体制》,《中国行政管理》2008年第4期。 (12)唐文玉:《行政吸纳服务: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诠释》,《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1期。 (13)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14)查尔斯·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冯青虎译,载邓正来、[美]杰弗里·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15)晓光、卢宪英、韩恒:《改革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行政吸纳社会》,载王名主编:《中国民间组织30年:走向公民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16)Unger,Jonathan,“Bridges:Private Business,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 147,1996,pp.795—819; Unger,Jonathan & Anita Chan,“China,Corporatism,and the East Asian Model”,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1995,pp.29—53.(安戈、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陈佩华:《革命乎?组合主义乎?——后毛泽东时期的工会和工人运动》,《当代中国》1994年第4期。 (17)Adams,Paul S,“Corporatism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Is There a New Century of Corporatism?”,in Wiarda,Howard J.(ed.),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Colorado:Westview Press,2002. (18)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4页。 (19)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0)王鹏:《什么是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国青年报》,2013年10月28日。 (21)王向民:《双重代表、资源中心与转换中介:将工会建设成枢纽性社会组织的内涵》,《工会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22)广东省《关于加强广东社会建设的重要决定》,2011年7月21日,http://roll.sohu.com/20110715/n313491659.shtml。 (23)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24)张钟汝、范明林、王拓涵:《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25)Oi,Jean C.,Rural China Takes off: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Refor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26)刘翔:《中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研究:基于社会治理结构变迁的视角》,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61页。 (27)项目制研究成果有:张良:《“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2012年第1期;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8)王浦劬、[美]莱斯特·萨拉蒙等著:《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22页。 (29)王浦劬、[美]莱斯特·萨拉蒙等著:《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页。 (30)劳工NGO的处境与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维权理念有很大关系。相关研究参考和经纬、黄培茹、黄慧:《在资源与制度之间:农民工草根NGO的生存策略——以珠三角农民工维权NGO为例》,《社会》2009年第6期;和经纬、黄慧:《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维权NGO:描述性分析》,《21世纪的公共管理:机遇与挑战: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08年10月;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何艳玲、周晓锋、张鹏举:《边缘草根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解释》,《公共管理学报》2009年第1期;陶庆:《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社会》2008年第4期。 (31)相关研究参考:邓莉雅、王金红:《中国NGO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因素:制度与资源分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赵甦成:《中国大陆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资源网络的观点》,《非政府组织学刊》2007年第2期;岳经纶、屈恒:《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权益的维护: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为个案》,《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2)赵东辉、吴亮:《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多难》,《瞭望新闻周刊》,2003年第16期;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3)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乌坎事件始末》,《中国非营利研究》2012年第2期。 (34)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35)相关研究成果有:邹树彬、张旭光:《权益性参与的理性运作:对“月亮湾人大代表工作站”实践的考察》,《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陈文、黄卫平、王永成:《“组织(机构)吸纳”的现实运作:以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为例》,《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黄卫平、陈文:《民间政治参与和体制吸纳的互动:对深圳市公民自发政治参与三个案例的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3期。 (36)陈玉华:《社会整合、组织生长与和谐社区的建构:杨家村农民工工会的调查与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37)相关研究,参考:陈家刚、陈奕敏:《地方治理中的参与式预算:关于浙江温岭市新河镇改革的案例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褚隧:《参与式预算与政治生态环境的重塑:新河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和逻辑》,《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何俊志:《民主工具的开发与执政能力的提升:解读温岭“民主恳谈会”的一种新视角》,《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3期;何俊志:《权力、观念与治理技术的接合:温岭“民主恳谈会”模式的生长机制》,《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38)陈朋:《体制吸纳与嵌入:农民利益诉求的有效回应——一个东部沿海城市的案例启示》,载《“关注省情民意、促进社会和谐”研讨会论文集(上)》,2009年6月。 (39)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在《政治理性主义》中区分了“技术知识”与“实践知识”,认为“技术知识”可以从书本上学,可以死记硬背,是“书本知识”,它关注确定性,可以通过理性的完美计划得到呈现;“实践知识”是存在于应用中,在实践中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有创造性与独特性的经验。以此而论,地方政府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探索是实践知识的生长结果,而不是书本知识的理性规划结果。参考[英]欧克肖特著:《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7—12页。 (40)邓正来:《“生存性智慧模式”:对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既有理论模式的检视》。标签:社会组织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项目组织论文; 政府服务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