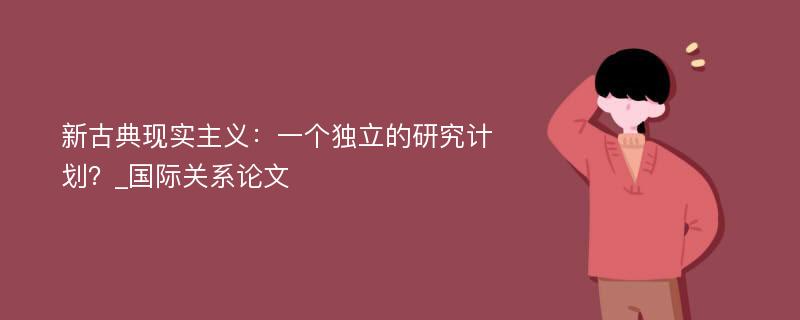
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纲领论文,现实主义论文,独立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之后,许多学者对现实主义的解释力和生命力提出了普遍质疑。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古典现实主义逐渐兴起并成为现实主义阵营内部最为活跃的理论分支之一,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广泛关注。①但是,一些学者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归属仍然存疑,认为这一理论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向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学派靠拢或妥协,导致了现实主义的退化。由于存在这种批评,在认识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新兴理论时,我们首先有必要准确判断其理论归属和理论定位,在此基础上拓展其学理空间。
近年来,有关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学术特点、代表人物、研究成果等问题,国内学术界已经发表了不少相关评介和论述。②不过,对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归属和学理定位问题,国内学界还缺乏清晰的探讨。鉴于此,本文拟对以下几个问题做出回答: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否属于现实主义理论传统?如何从学理上对这一理论进行定位?该理论是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本文第一部分概述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质疑,第二部分判断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否归属于现实主义阵营,第三部分探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学理定位,最后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发展为一个独立研究纲领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质疑与争论
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任何新兴学术思想和理论都是在激烈争议和批判中成长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也不例外。自从这一理论分支兴起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认为它背离了现实主义传统,倒向了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使得现实主义在整体上走向退步。在这些质疑中,莱格罗(Jeffery Legro)、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以及瓦斯克斯(John Vasquez)等人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在《还有人是现实主义者吗?》这篇颇具争议的文章中,莱格罗和莫劳夫奇克认为,作为一个“理论范式”(theoretical paradigm)的现实主义有三个核心假定:首先,在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中的行为体在本质上是理性、一元的;其次,国家偏好是确定的、一贯冲突的;最后,在国际结构方面,物质能力是第一重要的。③通过考察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一批现实主义学者的著述,莱格罗等人认为,现实主义正在逐渐把其他理论的核心概念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之中,由此破坏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核,出现了背离现实主义理论范式的严重问题。基于这种判断,莱格罗等人声称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是现实主义者了。
仔细考察莱格罗等人的批评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其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严密的、统一的科学理论。在分析结构上,莱格罗和莫劳夫奇克谋求在现实主义内确立拱卫范式的“核心假定”,然后框定“现实主义范式”内各个离散的理论分支,进而保证范式的统合和一体。④这种分析在本质上意味着对内部分支众多的现实主义进行“理论综合”(theory synthesis),将现实主义人为规定为一种整齐划一的范式。⑤但实际的情况是,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family of theories)。正如吉尔平所说,现实主义是一种悠久的思想传统或学派,其中包含诸多离散的理论分支。⑥也如其他学者所指出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学派之所以得名,不在于它们存在一组不变的“核心假定”,而是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存在着共性。⑦莱格罗和莫劳夫奇克认为,当代现实主义学者把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等变量也纳入其研究范畴,这不仅仅是利用特设性变量来修补理论反常,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已经彻底地接受了其他范式的论据和变量。这一观点错误地认为现实主义主张国家仅仅注重物质能力,也误解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精英感知和国内结构的理解,曲解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⑧
与上述观点类似,瓦斯克斯也对新古典现实主义表示质疑。瓦斯克斯主要从研究纲领的角度来评估新古典现实主义,尤其是关于国家是否采取制衡行为的研究,他认为这一理论纳入了结构以外的变量,而且并没有解释新颖的事实,因此不是一个进步的“理论转变”(theory shift)。⑨按照他的观点,在现实主义理论家族中,新古典现实主义同结构现实主义是纵向的继承关系,而非横向的并列关系。
然而,瓦斯克斯的评估明显失当。其一,他把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纳入同一个研究纲领,并且把新古典现实主义看做是结构现实主义内部的自我修补。实际上,二者存在巨大差异,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核。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谋求建立一种外交政策理论,研究国家如何应对国际环境的行为,制定特定的外交政策,这与结构现实主义以国际结果为研究对象、建构国际政治理论的定位有着本质的不同;⑩其二,瓦斯克斯把结构现实主义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运用等同于理论建构本身。理论建构的目的在于适当简化繁杂的因果关系,发现并解释其中的规律,进而建立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理论应用则是对理论使用范围内的具体事件进行解释分析。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划分理论归属时不能混淆。
由于学术界对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否属于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与结构现实主义是否同属一个研究纲领等问题存在争议,没有形成定论,我们首先需要考察其理论归属问题。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归属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理论家和理论流派进行归类的确存在着分歧,甚至一些理论家本人也不承认其他学者对其研究的归类。但是,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相对成熟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其哲学基础、核心概念和分析单位是相对明确和稳定的,这些可以作为某理论分支是否归属于现实主义阵营的主要标准。
尽管现实主义内部各个分支之间包含一些基本的共有特征,但是通过硬性地“理论综合”,错误地对其核心假定进行裁剪,或者把现实主义各个理论分支看做前后继承的关系,这都是有失偏颇的。本文认为,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独立的学派,并不是基于一套科学的理论假定或者共同的研究变量,而是在哲学基础、核心概念和分析单位三个方面存在共性。
首先,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哲学基础来说,现实主义属于保守主义传统,其核心特征包括对人类理性的怀疑和对国际政治秩序和传统的维护,这在根本上有别于激进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11)在哲学立场上,人类行为“本性难移”和人类历史的不断重演是现实主义的固有信念:有史以来人类行为和社会关系未见实质性进步,凡对人性进行改造的政治试验均遭失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不会改变,这是无情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吉尔平认为当今国际政治的特征同修昔底德时代并没有太大区别的原因。(12)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安全资源是稀缺的,国家间充满了竞争,人类的各种群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这是人类社会难以改变的本质。就人类来说,人类本性是恶的,人类社会的政治弊病都源于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欲望。所以,人性恶和安全资源稀缺成为人类社会两个难以改变的状态,这也成为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两个逻辑出发点。就新古典现实主义来说,它仍然秉持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承认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无政府状态下安全资源的稀缺性,强调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竞争。新古典现实主义关注的是,在这个竞争的体系里,国家如何采取模仿、追随、制衡等特定的战略,通过国内层面的协调,以实现国家特定的外交政策。(13)就其哲学基础而言,它与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一脉相承,与自由主义“利益和谐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其次,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权力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追求利益。权力与利益是现实主义各个理论分支共有的核心概念,尽管权力包含多种因素,但是物质权力居于首要地位。并且,较之绝对收益,相对收益更加重要。对以上观点,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基本赞同,他们坚持国家权力在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古典现实主义之所以是隶属于现实主义,原因在于他们坚持认为,国家外交政策的第一推动力是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和国家的相对物质权力。(14)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同结构现实主义和古典现实主义的侧重有所区别。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权力的各种因素在不同的时间发挥不同的作用,权力结构受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所以,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加注重权力在国家社会层面的作用机制,关注一国在国家制度层面的动员(mobilization)和资源汲取(resource-extractive)能力,也更加侧重于研究国内社会和精英集团对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重要作用。(15)
最后,现实主义的分析单位。在社会科学中,分析单位的选取往往反映了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分歧。大多数现实主义理论都假定,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单元,并且,国家是一元(unitary)、理性(rational)、自主(autonomous)的。(16)这也是现实主义被称为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应作为区分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首要(当然并非全部)标准。不过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并不仅仅聚焦于国家,而是人类历史上居于主导性的团体(group)。这区别于自由主义对“个人”的关注以及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关注。随着经济、人口和技术的变迁,这种团体的名称、规模和组织也在发生变化,在历史上曾经以城邦、封建诸侯国、帝国等其他形式出现过。(17)新古典现实主义仍然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并且认为国家机器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不过如果要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外交政策,在关注体系层面压力的同时,还需要开启“黑匣子”,研究国内公众、精英团体等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如何制定和运转外交政策。打开国内政治的“黑匣子”,可以增加足够的变量来建立和检验理论。(18)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和集团的关注使新古典现实主义放宽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单一、自主性单元的假定。但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关注国内变量,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国家这一基本政治组织形式的自主性,这一点显然没有背离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而是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衣钵。摩根索等古典现实主义者一直关注个人和集团,为了建立更简约、科学的理论模型,结构现实主义才抛弃了这个假定。
新古典现实主义最受一些学者诟病的是引入其他理论所强调的变量。但是,对于任何科学研究范畴,概念都只是理论用来分析现实世界的基本工具,它本身并不具有理论专属性,在国际关系领域也不例外。某些概念可能在某种理论的分析工具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也不表明这种理论能够垄断对这些概念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在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诸如权力、利益和国际制度等概念在各种理论中的理论化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权力和利益是现实主义用于分析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而自由制度主义最关注的是国际制度的作用。但是,现实主义也有关于国际制度的理论阐述,自由主义则与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权力观和利益观。(19)这种状况表明,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在各种理论中的区别主要是理论化程度和立场上的不同,而并不意味着某种理论绝对排斥或者否定某些概念。
可见,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阵营内部兴起的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在哲学基础、核心概念和分析单位上,都没有背离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因此,从理论归属来看,它仍然是现实主义理论,而不是对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的妥协。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定位
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一样,现实主义阵营本身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理论,因此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划定。现实主义内部各种理论分支有着不同的学术定位和研究范畴,决定了不同分支之间的差异性。(20)随着近年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理论定位已经非常明晰:就理论类型而言,是外交政策而非国际政治理论;就研究层次而言,是单元层次而非体系层次理论。
(一)一种外交政策理论
一般来说,外交政策研究是一个理论化程度较低的领域,人们更多地谈论的是外交政策的研究路径、分析框架、决策模式,而在谈及“外交政策理论”时,这里的“理论”概念只能作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在社会科学中,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寻找规律性的行为模式和结果,并且对其中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做出说明。因此,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沃尔兹明确区分了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21)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它所解释的对象是不同国家在体系中的位置大致相当时为何具有彼此相似的行为,由此产生了反复出现的国际结果(诸如战争和均势)。而外交政策所涉及的变量相当繁杂,尤其要纳入许多单元层次上的变量,因此外交政策的理论化相当困难。
沃尔兹关于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区分,主要依据的是两者所要解释对象(因变量)的不同。国际政治理论解释一般性的国际结果,而外交政策分析研究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所具有的不同意图、目标和偏好,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选择。(22)外交政策理论化的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研究外交政策时总是集中在某个具体的政策过程和结果,一般只能作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涉及不同分析层次上的许多因素,而理论不能是各种事实和要素的简单罗列,需要考虑多种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将它们有机地整合到一个因果机制中。尽管存在着理论化的难题,国际关系中不同层面的研究领域都可能进行不同程度的理论化,因为各领域总是有可以发掘的规律性。比如,凯格利(Charles W.Kegley)等人指出,外交政策中具有很明显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可以发现其中的政策模式(policy pattern),即对政策的总体趋势和方向做出一般性的概括和描述,在此基础上,再做出一般性的解释就可以形成理论。(23)由此可见,特定国家的外交政策也有一般性的模式可循,外交政策研究也可以抛开对具体事件和政策的关注,构建具有一般解释力的理论。
自从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以来,其体系与单元、结构与进程的分离一直受到批评和指责,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努力可以视为现实主义内部对这种批评的回应和尝试性解答。新古典现实主义明确地走向构建外交政策理论的路径,这与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理论大相径庭。这些学者不赞同将考察国家外交政策的外部环境与国内要素分割开来,也无意建构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一般性理论,而是专注于对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的解释。特定国家的大战略、军事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结盟偏好以及危机处理等行为都被新古典现实主义纳入研究范围之内,国家内部的公众凝聚力、精英集团、国家能力及其资源汲取能力等成为考察的变量。当然,外交政策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解释和分析是情势性的,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可能仅仅适用于特定国家的特定行为。而且,在指出单元层次上几种同时起作用的因素之后,更细致地分析因果关系也是必要的,即回答单元层次上的某种因素是否比其他因素在传导体系诱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
(二)一种单元层次的理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诉求之一就是关注国家内部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外交政策是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内部以及两个层次之间的各种要素复杂互动的结果,尽管国家的权力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对国家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国内因素同样能够影响外交政策。有些变量(比如国内政治)在现实主义内部的理论化程度不高,但并不等同于这些变量专属于自由主义或者建构主义理论,现实主义同样可以利用这些变量进行理论推理和建构。试图将体系层次诱因与单元层次要素结合起来,这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研究的主要特色。因为一方面,有关外交政策的传统研究主要立足于国内政治层面,另一方面,立足于体系层次建构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反对将其用作外交政策理论。(24)但是一个国家实际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将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上的影响因素完全割裂开来,架构起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其统一到外交政策的解释中就成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议题。
从分析层次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架构结构现实主义的体系层次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单元层次的桥梁。与一些学者不分主次地同时强调体系和单元两个层次的自变量不同,这一派学者更明确地指出了两个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即体系要素是国家行为的自变量,而单元要素是国家行为的干预变量。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体系诱因和单元要素在导致外交政策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将体系诱因作为外交政策的自变量,单元要素就是连接二者的干预变量,它的作用可能加强也可能减弱体系诱因对单元行为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强调,一种好的外交政策理论首先应该回答国际体系对国家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最强有力的一般性特征是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相对位势(relative position),但是要理解国家如何解读和回应外部环境,更需要分析体系压力是如何通过决策者的认知和国内政治结构等单元层次要素传导的。(25)这就是为什么新古典现实主义者试图对不同国家或者相同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所采取的特定战略做出解释,进而建立外交政策的分析模型的原因。可以说,新古典现实主义既区别于结构现实主义,又在单元层次上做了补充,将结构现实主义应用于外交政策分析。(26)
四、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基本定位是构建一种外交政策理论研究纲领,它在分析方法上将体系与单元两个层次结合起来,并且运用科学的案例研究方法对一些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一理论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外交政策理论研究纲领呢?
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认为,在严格意义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并不能应用于国际关系学科,但是如果较为宽泛地定义科学研究纲领,新古典现实主义不仅是一个研究纲领,而且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27)尽管瓦斯克斯并不承认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认为其观点和分析结构都存在问题,但是他也把这一理论流派作为一个研究纲领来进行评估。(28)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倾向于把新古典现实主义视为一种“模型”。(29)如果严格遵循拉卡托斯的界定,在国际关系领域,即使像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这样简约、科学的理论也很难符合科学研究纲领的标准。不过,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确为我们看待各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及其分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视角,国际关系学者也越来越倾向于从研究纲领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估国际关系理论。(30)
根据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研究纲领由硬核(hard core)、保护带(protective belt)、正面启发(positive heuristic)和负面启发(negative heuristic)等四个核心要素构成。在这四项要素中,真正能够辨别出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将其与其他纲领区分开来的是“硬核”,因为保护带是根据保护硬核的负面启发和拓展硬核的正面启发而增设的,实际上其他三个部分都从属于硬核。因此,识别研究纲领的关键在于区别不同的硬核,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硬核就是一种理论的内核,它由理论的基本假定、核心概念以及对因果关系的解释构成。(31)
既然“内核”是一个研究纲领得以存在的前提,我们在判断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不是一个独立研究纲领时,应该首先辨识其是否具有一个独立的、稳定的内核。
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目前已经建立了多个分析模型,但是仍缺少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沃尔特曾经精辟地概括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不足。他认为,由于这一理论回避了仅仅关注国内或体系变量的单因分析,它更适合于在历史叙事中建构理论,它精于对历史细节的描述,主要着眼于对单个国家或个别现象的历史事例进行解释,缺乏一般性推理。(32)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都主张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结合起来,但是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是多元的,并且一国外交政策要应对国际环境的情势变化。因此,其已经建立的模型主要集中于一国应对外部压力的不同策略,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起一个核心的基础理论。基础理论的缺失是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研究纲领的最主要障碍,也是其目前面临的主要理论难题。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正朝着一个研究纲领的方向前进,但是,在没有形成一个核心的基础理论之前,很难说其已经确立了研究纲领。
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独立研究纲领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如何协调与结构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解释国家行为时,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联系起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是,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新古典理论通常解释的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异例,即不符合国家指令的行为。(33)换言之,作为干预变量的单元层次要素常常起到的是抑制结构层次要素的作用。但是,从类型化的角度看,单元层次作为结构层次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干预变量,至少可以起到加强、传导和抑制三种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化过程中应该将这三种作用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不仅仅只解释结构现实主义的反例。
那么,新古典现实主义是否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针对上文指出的两个方面的难题,这一理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加以解决。首先,通过总结外交政策中那些反复出现的模式,确立一个核心的解释变量,并在此之上建构一个基础理论。外交政策理论所解释和预测的不是日常的事件和暂时的摇摆,而是这些具有持久性和延续性的政策模式。为了归纳这些反复出现的模式,进而建构出一个支撑新古典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研究纲领的基本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需要框定自我研究领域和界限,保持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与其他理论重合。就核心理论的建构而言,一种可能的改进是以“国家能力”作为核心变量,将现有研究中提出的其他变量作为操作化指标,研究这些指标如何作用于国家能力,从而转化为实际政策结构。最近的研究也表明,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正在进行构建统一分析框架的尝试。(34)其次,建立真正的跨层次分析理论,对自变量和干预变量的作用都能够充分地加以揭示。坚持国际—国内跨层次研究是新古典理论区分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通过国内政治分析构建外交政策理论的特色之一,为了真正实现跨层次分析的可能性,新古典理论需要改变将结构层次变量仅仅作为背景性因素考察的做法,使其真正发挥自变量的作用。与此同时,改变仅仅研究单元层次变量抑制结构因素的做法,完整地揭示其作为干预变量可能以及实际发挥的作用,厘清结构与单元层次之间互动的方式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如果能够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改进,新古典现实主义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并且在此基础上演化为一个进步的研究纲领。
五、小结
作为一种新兴理论流派,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其成长过程中遭遇了众多学者的批判,但是,它在学理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在实践上对一些具体的历史案例提供了新颖的解释,充分表明了其理论生命力。不过,作为一个庞杂松散的阵营,新古典现实主义无论是在理论框架的严密性还是连贯性上,都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
本文认为,首先,尽管有学者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归属和理论定位存在质疑,但是,就理论归属而言,不管是哲学基础、核心概念,还是分析单位,这一理论都没有背离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其次,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也是一种单元层次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定位使之明显区别于结构现实主义;最后,由于核心基础理论的缺失和跨层次分析的不完善,新古典现实主义目前仍不是一个成型的研究纲领。就其发展空间来说,广泛拓展现实议题和经验研究当然重要,但也需要注意理论内在逻辑的统一和完善。新古典现实主义既重视国际体系的外部压力,也关注国家制度层面的制约作用,同时强调国家与国内社会、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这种多层次的研究给理论的建构增添了诸多困难。随着理论模型的增加,如何处理这些单个理论模型之间的关系,进而统合在一个研究纲领之下是其必须面对的难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难题,才能保证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生命力。
注释:
①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October 1998,pp.144-172; Randall L.Schweller,"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2003,pp.311-347.
②相关中文评介,可参见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第32-33页;郑端耀:《国际关系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问题与研究》(台北),2005年第1期,第115-140页;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20-121页;王公龙:《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与缺失》,《国际论坛》,2006年第7期,第36-41页;刘丰:《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及前景》,《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3期,第155-168页。
③Jeffery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Fall 1999,pp.12-18.
④莫劳夫奇克曾经努力建构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范式”,相关论述参见Andrew Moravcsi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4,Autumn 1997,pp.512-553; Andrew Moravcsik,"The New Liberalism",in Christian Reus-Smit and Duncan Snidal,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234-254.
⑤关于理论综合的论述,参见Anderw Moravcsik,"Theory Synthe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al Not Metaphysical",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1,April 2003,pp.131-136.
⑥Richard G.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2,Spring 1984,p.297.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对一些概念的使用比较模糊。比如,现实主义被称为理论、传统、学派、范式等等。但细究起来,这些概念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现实主义显然比理论更为宽泛,它是一个理论家族,因此,吉尔平倾向于称之为“传统”,沃尔兹称之为“思想”。我们认为,“思想传统”或“学派”更适合。“研究纲领”更适合用于“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分支。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刘丰:《从范式到研究纲领: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欧洲研究》,2006年第5期,第52-66页。
⑦Gunther Hellmann,"Correspondence:Brother,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5,No.1,Summer 2000,p.173.
⑧Jeffrey W.Taliaferro,"Correspondence:Brother,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Fall 1999,p.178.
⑨John Vasquez,"Kuhn versus Lakatos? The Case for Multiple Frames in Apprais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pp.440-450.
⑩关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比较,参见Jeffery W.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Security Studies,Vol.15,No.3,Summer 2006,pp.480-482.
(11)关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三者之间竞争与区别的相关介绍,参见〔挪威〕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3-167页。关于现实主义的怀疑主义道德观,参见Marshall Cohen,"Moral Skeptic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Kenneth Kipnis and Diana T.Meyers,eds.,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Morality:Ethics in the Nuclear Age,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7,pp.15-35.
(12)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28.
(13)参见Jeffery W.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p.467.
(14)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146.
(15)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托利弗(Jeffrey W.Taliaferro)、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和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分别关注了国家动员、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国内社会和精英凝聚力、国家能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参见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Jeffrey W.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 Randall L.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
(16)有关现实主义对“国家”所做的设定,参见Joseph M.Grieco,"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 Michael W.Doyle and G.John Ikenberry,eds.,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Colorado:Westview,1997,pp.164-166。
(17)对这一点的说明,参见Robert G.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pp.290-291; 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p.470。
(18)Bernard I.Finel,"Black Box or Pandora's Box:State Level,Variables and Progressivity in Realist Research Programs",Security Studies,Vol.11,No.2,Winter 2001/2,pp.212-218.
(19)关于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权力观,可参见Felix Berenskoetter and M.J.Williams,eds.,Power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2007。在有关国家利益的专著中,伯奇尔(Scott Burchill)分章评述了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参见Scott Burch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The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基欧汉、米尔斯海默等人的辩论则反映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不同的国际制度观,参见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December 1988,pp.379-396; 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 No.3,Winter 1994-1995,pp.5-49; Robert Keohane and Lisa 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p.39-51; Charles A.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The Promise of Collective Securit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p.52-61; John Gerard Ruggie,"The False Premise of Real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p.62-70; Alexander Wendt,"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p.71-81; John J.Mearsheimer,"A Realist Repl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Summer 1995,pp.82-93。
(20)出于研究目的的考虑,本文并没有细致讨论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对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可参见Steven E.Lobell et al.,eds.,Neoclassical Realism,the State,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3-20。
(21)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Vol.6,No.1,Autumn 1996,pp.54-57.
(22)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p.14.
(23)Charles W.Kegley,Jr.and Eugene R.Wittkopf,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ces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p.8.
(24)关于结构现实主义是否适用于外交政策理论,埃尔曼(Colin Elman)曾对沃尔兹提出质疑,两人曾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重要的辩论,参见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Vol.6,No.1,Autumn 1996,pp.7-53; 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pp.54-57; Colin Elman,"Cause,Effect,and Consistency:A Response to Kenneth Waltz",Security Studies,Vol.6,No.1,Autumn 1996,pp.58-61。
(25)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Summer 1992,pp.197.
(26)正因为此,一位学者主张新古典现实主义应该明确作为结构现实主义的特例来对待,参见Brian Rathbun,"A Rose by Any Other Name: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Security Studies,Vol.17,No.2,April 2008,pp.294-321。
(27)Randall L.Schweller,"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pp.312-320.
(28)John Vasquez,"Kuhn versus Lakatos? The Case for Multiple Frames in Apprais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p.440-450.
(29)Jeffrey W.Taliaferro,"State Building for Future Wars: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esource-Extractive State",p.468.
(30)对科学研究纲领在国际关系领域适用性最为详细的论述,参见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也可参见刘丰:《从范式到研究纲领: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
(31)参见〔英〕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56-58页;刘丰:《从范式到研究纲领: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问题》,第58页。
(32)Stephen M.Walt,"The Enduring Relevance of the Realist Tradition",in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eds.,Political Science:State of the Discipline III,New York:W.W.Norton,2002,p.221.
(33)Brian Rathbun,"A Rose by Any Other Name:Neoclassical Realism as the Logical and Necessary Extens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pp.294-321.
(34)Steven E.Lobell et al.,eds.,Neoclassical Realism,the State,and Foreign Policy,chapter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