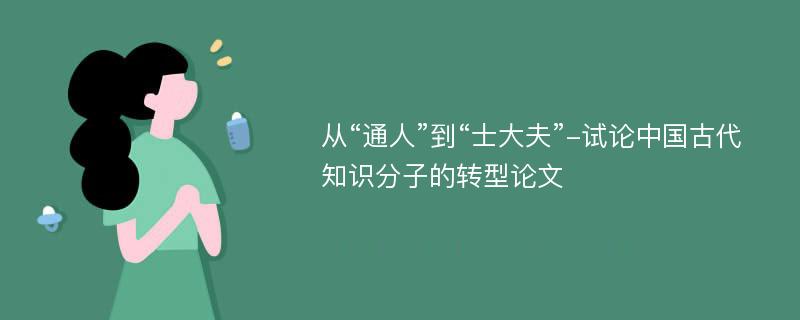
从“通人”到“士大夫”
——试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肖 航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经历过漫长的演变,而汉代作为中国学术的奠基时期,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和认同具有极其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大体而言,汉代思想中,最为推崇“通人”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知识背景称其为知识分子的必备素养。最终,“士大夫”阶层得以形成,这个阶层不仅是一种体制化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更重要在于这个名称确立了这一阶层以“道”作为独有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这种价值追求和精神取向与天子诸侯的精神境界可以达到同样的高度,深刻地契合天地之道,具有天然神圣性的尊严。
[关键词] 古代 知识分子 通人 儒学
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漫长的演变,而汉代作为中国学术的奠基时期,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和认同具有极其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就此,本文拟从历史演变角度,以汉代为例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具体转型过程。
一、关于“通人”
汉代对于“通”的崇尚与其政治理念中以“道”作为指导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当时行政需要顺天而行、仿天而治,故在政治理念上提倡顺应自然、因循无为的“道”。在这种崇尚“道”的前提下,“通人”成为了汉代思想家相当推崇的一类人物。而所谓“通人”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明晓万物之理,与道合一。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言“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推崇易道,而只有作为通人的孔子才能够注意幽远高明的易术,这是强调“通人”对于高深玄理的明达。贾谊还曾讲过“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这是“通人”对于阴阳造化、自然万物的了悟,没有以分别心作为障碍,自己与天地万物精神之合一。东汉赵咨给儿子的遗书中有“夫含气之伦,有生必终,盖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数。是以通人达士,鉴兹性命,以存亡为晦明,死生为朝夕,故其生也不为娱,亡也不知戚”,这是讲“通人”能够对于生死问题的达观,对人生的了悟。而“汉自楚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将微义未译,而但神明之邪?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东汉佛教思想初步传入中原之时,连见识最为广博的“通人”对于异域传来的佛教教理也有些疏隔,可见佛教初传之不易。但整体而言,“通人”在当时是知识渊博、贯通万物、与天地同精神境界,与道同往来的一类人。
第二,擅长处理实际事务。《荀子·不苟》中有“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这里“通士”是能尊君爱民,对于任何事物都能妥善办理之人。在“通人”所办理的事务中又以治国理家最为重要,所谓“通人积文十箧以上,圣人之言,贤者之语,上自黄帝,下至秦汉,治国肥家之术,刺世讥俗之言备矣,使人通明博见,其为可荣,非徒缣布丝绵也。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天下之富孰与家人之财”(《论衡·别通篇》),这说明了“通人”能够运用自己的广博知识治国富家,并将萧何作为善于运用书本知识的典型例子。
201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获刑的还有其妻子、儿子。法院查明,2002年至2014年间,尹一家三口共收取多家生物制药企业给予的财物共356万余元。
闪烁液通常由一种或多种荧光体和溶剂混合而成,溶质的浓度一般在1%以下。常用的第一闪烁体是PPO。它的荧光量子效率高,能在低温下工作,是目前用量最大的第一闪烁体。有时为了使闪烁溶液与光电倍增管更好地匹配,除使用第一闪烁体外,闪烁溶液中还需加入第二闪烁体——移波剂。第二闪烁体的主要功能是吸收第一闪烁体发出的光以后,再发射波长较长的荧光,以增加光子的产额。常用的第二闪烁体有POPOP和bis-MSB等。
就治国而言,以三代之治最为合乎天道,所谓“或问道。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或曰:可以适它与?曰: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法言·问道卷》)。要追寻三代之治的最佳路径则是学习“五经”,所谓“凡人情忽于见事而贵于异闻,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后汉书》卷28上《桓谭冯衍列传》),在此,东汉思想家桓谭认为先王治国以仁义为正道,谶纬喜谈天道性命这类玄远的事情不能当作正道,五经中的大义才是根本性知识,其中蕴含的智慧才属于通人的智慧。
第三,因具有丰富的学识又能妥善处理各类事务,故汉代提及“通人”还含有人生际遇较好、能在仕途上通达荣显的内涵。西汉陆贾在《新语》中就认为“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故事闭之则绝,次之则通,抑之则沈,兴之则扬,处地楩梓,贱于枯杨,德美非不相绝也,才力非不相悬也,彼则槁枯而远弃,此则为宗庙之瑚琏者,通与不通也。人亦犹此”(《新语·资质》),他强调资质良美、才能优异的人要追求仕途通显,如此方能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符合西汉初期统治阶级求贤若渴的时代背景。在西汉中晚期,刘向提出“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故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有博通之士,则入主尊固,非成之所议也”(《新序·杂事》),强调“通人”应该处于国家高位,国家才能够稳固。东汉大儒郑玄也在《戒子书》中写道“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后汉书》卷35《郑玄列传》),郑玄以在朝廷有官位的为“通人”,以隐居不仕的为“大儒”,可见在他心目中“通人”也是仕途通显之人。
汉代“通儒”并非仅是学养上博通古今、知识渊博,而是有着自身特殊的内涵,有知识分子曾将汉代儒生的这一类区分总结为“纯儒、儒宗的成就,在于他们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阐发和传授,学术地位是无尚崇高的;通儒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把儒家学说贯彻到时政、教化中去”[3]。西汉末年的大儒扬雄就认为“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明达天地之道而不能通达人事的只能叫做技术工匠,明了天地之道又能够通达人情世故的才能叫“儒”,扬雄心目中的儒生应擅长处理人类社会的具体事务。东汉初年,桓谭也认为士人当以知大体为贵,所谓“大体者,皆是当之事也。夫言是而计当,遭变而用权,常守正,见事不惑,内有度量,不可倾移而诳以谲异,为知大体矣。如无大材,则虽威权如王翁,察慧如公孙龙,敏给如东方朔,言灾异如京君明,及博见多闻,书至万篇,为儒教授数百千人,只益不知大体焉”,在桓谭看来,富于现实精神与实践品格、能够对事务予以恰当处置的人才能叫做“识大体”。这种人言行得体、计谋合宜,遇到突发事件能够权变,平时处理事务又能守持正道。任何事情都不能让其对内心的道产生疑惑,他们心胸宽广,不会被人轻易蒙蔽。相比较之下,尽管学问渊博、弟子众多,如果不能在实践中行道,则也是不识大体的人。
在常委会审议阶段,我国目前通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尚缺发言的礼节、主持人的惩戒权及议题的拆分等规定。修改后的《立法法》增加了单独表决的规定,在保证民主议事的基础上提高议事效率。事实上,该条款所涉及的意见分歧较大的重要条款,通常产生于审议阶段。因此,如果这类事项需要单独表决,可考虑在审议阶段就将其拆分出来单独审议,进一步提高立法效率。
比较特殊的例子是王充,他以职位较低的兰台令史作为“通人”经常所居官位,以著述宏富作为评判“通人”的标准,故其言“或曰:通人之官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紲,大用于世……以心如丸卵爲体内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虽微,典国道藏,通人所由进”(《论衡·别通篇》),他强调兰台令史这类纯文学性官员尽管不能亲自治民,然而他们主管编著事关经国大道的典籍,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种独特的看法与王充自身经历与人生追求有关,当时并不占据主流思想的地位[1](P344)。
在汉代儒学逐渐兴盛的背景下,儒学素养成为了“通人”所必备的知识涵养。“通人”往往因其深厚的儒学涵养被称为“通儒”。就博通之学风所成就的儒生群体而言,还可大致区分为知识分子型人物与实干型人物两类,如张衡、贾逵、郑玄等人多为知识分子型人物,他们均以著书立说、传授弟子为毕生志业,最终都成为了一代儒宗。而实干型的人物则以卓茂、刘宽等人为代表,尽管学术影响不如前者,但仕途显达、学以致用,此类人才可称为名副其实的“通儒”。
二、关于“通儒”
水库长年较低水位运行,原本在水面线以下的土地常年暴露在外,土地被村民或企业侵占从事其他活动。①从事农业耕种。通过多年的耕种,村民把土地据为己有,土地耕种仍由原镇、村经营,没有真正实现由水库管理单位使用管理。②建造房屋居住。村民私自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建造房屋,并长期居住,水库管理单位没有执法权,发现后不能驱离人员、拆除违建设施,苦于无应对措施,形成现状。③被企业填土造地并建设厂区。水库原有土地闲置后,疏于管理,被企业填土造地,并建设厂区,水库管理单位难以收回土地。
除了制定各种礼仪制度之外,“通儒”还致力于将儒家学说贯彻到行政教化中。如“(卓茂)……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性宽仁恭爱。乡党故旧,虽行能与茂不同,而皆爱慕欣欣焉”,他的宽仁恭爱体现为不好争,被人误解也不辩解,他为官则“劳心谆谆,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而他对于亭长接受百姓赠送米肉一事的看法为“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主要指导思想都是用礼仪制度劝导民众向善、不汲汲用律令法制苛责民众,行政以宽厚仁爱感化为主(《后汉书》卷25《卓茂传》)。刘宠“以明经举孝廉,陈东平陵令,以仁惠为吏民所爱。母疾,弃官去。百姓将送塞道,车不得进,乃轻服遁归。后四迁为豫章太守,又三迁拜会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颇为官吏所扰。宠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刘宠传》),他的行政理念也是仁厚慧慈、简除苛政,为民众所深深喜爱。刘宽以教化手段行政,“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尝疾言遽色。常以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终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灾异或见,引躬克责。每行县止息亭传,辄引学官祭酒及处士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后汉书》卷25《刘宽传》),刘宽也是以宽恕温厚仁爱来行政,从不疾言厉色训斥小吏百姓,行政中注重讲经讨论、劝课农桑、勉励孝悌,这也是典型推行儒家教化以行政之官员。可见,“通儒”之“通”不局限于书本知识之渊博,而在于通古今、通天人、通人事,要在生活的具体实践中贯穿大道大义才能够称为“通儒”。
(一)优化时间管理。结合寄宿制学校工作和中学生身心学习生活特点,我们把德育教育集中于周末时间、午休时间和下午放学后时段,基本保证一周不少于15小时的课外德育教育时间,既保证学生文化课学习和睡眠休息时间,又能腾出充足时间用于体育锻炼、参与文娱活动和专题教育活动,也留出寄宿生自由支配时间,达到寄宿生在校学得有效、睡得安宁、玩出名堂、全面发展。
大体而言,汉代人所言“通人”大致具有上述几个特点:与道合一,明晓万物之理;知识与经验丰富,能够妥善处理各种实际事务;仕途通达,才干优异,等等。“通人”正因符合当时最高政治理念“道”,故实为治理国家时所急需的人才。
总之,核心素养下的小学数学教师应该相信学生,给学生搭建起自主学习与探究的学习平台,进而使学生在自主、类比、探究、论证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同时,也为学生基本数学学科素养的全面提升夯实基础。
到了东汉中后期,应劭对儒者区分为“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后汉书》卷27《杜林传》),“通儒”重在区分古今,平时居家时能学习琢磨圣贤的言论,在行为实践中则要贯彻实现典籍中所阐述的大义,考察前代制度是为了帮助应对现实中的时政教化,这才是“通儒”。如果只是学习经典、讲习读诵,但是却不能按照经典所阐述的大义行动,不能够应用于生活实践与政治实践中去,这就只能算作“俗儒”。
汉初受秦朝焚书坑儒政策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以刘邦、项羽、韩信等为代表人物,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都不喜读书。但汉代建国之后,局势渐趋稳定,出于治理天下的需要,统治者对于书本知识开始逐渐重视,如刘邦给儿子刘盈的书信中坦白到“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2](P131),书本作为载体的文化知识之益处已逐渐被急需守成之道的统治阶级所意识到,于是,社会上读书习字、讲论问学的风气得以培养,学术也得以兴盛起来。
汉代“通儒”所从事的实践大体有两类:一类在于礼仪制度建设,这是儒家特别重视与擅长的事务;另外一类则体现在顺应人情的教育感化工作中。这里首先考察“通儒”在汉代礼仪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儒家本以“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周代礼制作为政治理想,极度讲究礼仪节文,故西汉前期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于儒家学术特色总结为“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他批评了儒家所推崇君臣父子之礼繁缛复杂,难以学习贯通,但礼主别异,在区分男女长幼顺序、规范社会秩序这点上,儒家思想有着独特功效。重视礼仪制度的这一特色后来被汉代“通儒”发扬光大。从汉元帝时期开始,宗庙、郊祀等各项制度的改革一度是西汉中后期制度建设的焦点。
在汉代学术逐步兴盛的过程中,以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为划时代的标志。此前,战国时期留下来的百家思想各有发展;此后,天下知识分子多宗儒家,故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汉书》卷88《儒林传》),这种设立博士弟子的政策,将国家官位俸禄与读书明经结合,博士弟子享有不用服兵役、劳役的特权,这些现实利益都诱使有读书条件的人争取通经。故博士弟子由最初几十人,增加到后来连经学大师都有千余人的宏大规模。汉代兴盛的儒学之风潮同时伴随着知识分子自发兴起的博学风尚,其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不守今文经学的章句、举训诂大义而已,兼明天文、历算、谶纬、诸子百家等各种典籍,知师法之所以然,但又不固守一家章法,致力于打通学说之间狭隘的限域,出入通脱,无所胶滞。这种“通学”以儒家经学为主导,贯通其他各类知识,这类知识分子也往往在当时被称为“通儒”。
三、关于“士大夫”
不少知识分子更加偏向将秦汉时期得以定型的官僚阶层称为“士大夫”阶层。而“士大夫”这个称呼亦古亦新,其所蕴含的思想意味实在值得重视。针对“士大夫”这个词的内涵,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士大夫”一词词义有所偏重,主要偏于“大夫”,这种观点以阎步克先生为代表,阎先生认为:“战国有‘士大夫’与‘官人百吏’的两分法。春秋以上无‘士大夫’之称,只说‘大夫’、‘士’。战国的‘士大夫’一词,是‘士’与‘大夫’的合称吗?我想不是。据《荀子·荣辱》,‘士大夫’是取田邑的,而这与《韩非子·和氏》所云封君子孙收爵禄、百吏绝减禄秩是一致的,那么‘士大夫’是有田邑的封君,不是‘士’;‘士’字是修饰‘大夫’的,我想它与‘子大夫’一词的‘子’意思相近,系美称。‘士大夫’为他称,‘子大夫’为对称而已。‘士大夫’主要就‘大夫’而言,‘官人百吏’则对应着原先的‘士’等级。昔日‘士’所承担的事务,已被‘吏’接任了。”[4](P54)另一种看法认为“士大夫”是合称,“士”与“大夫”合而言之有特定意味。于迎春先生认为:“‘士’在汉代的士大夫化,相当程度就是被体制化。随着他们获得了稳定的做官途径,参与意识形态建设,成为合法的政治管理人选,士人在出路、思想、学养上也逐渐官方化、规范化了,在秦汉以来士人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互动中,经过一系列调适,事实上,证明没有比他们双方更为彼此需要、更能互相满足的了。‘士’是一个无组织的社会群体,士人的身份缺乏鲜明、固定的外在标志,国家行政官员、知识和道德的教育者、文化的创造者,这些角色不仅分别,而且往往同时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另一方面,‘士大夫’一词意味着,被体制化了的士人显现出相较清晰、统一的整体面貌,国家行政官僚几乎就是他们的组织形式;以学识、道德为人生之本的士,与社会政治有着难分难解的密切关联,换言之,士人复合的角色状况乃是以政治为重心,对社会政治的态度如何和与之的距离远近决定着他的人生大概。”本文比较赞同第二种看法,但认为还有一些情况要补充。“士大夫”的确是战国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公、卿、大夫、士”被用来称呼朝廷百官,而这种官位排序中“士”按一般排列在“大夫”之后。所以,直到战国时代在表示等级序列时,不少典籍中仍然沿袭了“大夫、士”这种排序惯例,如《荀子·礼论》中有“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有“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也是在同一时期,“士大夫”这个概念开始在典籍中出现,这可从当时典籍的各项记载中得到充分证明,在先秦文献《论语》《左传》《国语》《孟子》《老子》《庄子》中基本看不见“士大夫”这个词汇,而在战国中晚期的《荀子》《吕氏春秋》包括西汉刘向编订记录战国纵横家事迹的《战国策》中,“士大夫”这个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其中,最喜谈“士大夫”者莫过于荀子。
《荀子》一书中对于“士大夫”意义的探讨恰好反映了新旧两种观念交替的实际状况。第一,荀子对于“士大夫”与“官人百吏”是有区分的,如《荀子·君道》中言“故天子诸侯无靡费之用,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无盗贼之罪,其能以称义遍矣”,这里将天子诸侯、士大夫、百吏官人、百姓列为四个等级,而从事具体事务的是百吏官人。该篇还有“愿悫拘录,计数纤啬,而无敢遗丧,是官人使吏之材也。修饬端正,尊法敬分,而无倾侧之心,守职修业,不敢损益,可传世也,而不可使侵夺,是士大夫官师之材也”,这里将小心谨慎地从事文书记录、会计有无的官员归为“官人使吏”,将自身修饬端正、明习法令、遵守职分、功业传世的官员归为“士大夫官师”。“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上则能顺天子之命,下则能保百姓,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职也”(《荀子·荣辱》),强调士大夫要按照较为抽象的道义修志行、顺上守职;而官人百吏则是遵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这些外在固定程式,尽管不明白其中的大道理,但是要遵循这些规矩度数以获得俸禄职位。由以上这些材料,可见荀子对“士大夫”强调的乃是对于自身心性志节的修行,对于“官人百吏”则强调对于规则度数的谨守、严格执行具体职责。
与此同时,荀子对“士大夫”与“官人百吏”有着明显的区分,故《荀子·强国》中还有“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这里官人庶人赏赐的都是实际利益,如增加俸禄和提高职务;而士大夫享受的却是贵族待遇,赏赐的是爵位。战国时期的爵禄意味着世世代代可以享有的特权,显然比一次性赏赐的俸禄与职务要高明。故在两军对阵之时,士大夫誓死也要捍卫自己的尊严与等级,故《荀子·议兵》中还有“临武君曰:‘善!请问王者之军制?’孙卿子曰:‘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这里明确了在战斗中,将军就应该拼命厮杀,驾车的人应该紧守自己的马鞭,百吏要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士大夫则要重视自己的尊严等级。这种为维护尊严而死的典型例证莫过于为了系好帽缨而不幸战死的孔子高足子路。荀子对于当时秦国吏治评价很高,其有言“其固塞险,形执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他将百吏恭俭敦敬、士大夫公正通达作为政治状况良好的表征。
第二,荀子也开始用新兴的社会阶层即士、农、工、商四民的区分来明确“士大夫”归属的阶层,将士大夫与农民、商人、工人并提,实是将“士大夫”归入了“士”这一阶层。如《荀子·荣辱》中有“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此处将“士大夫”归为仁厚而能守官职的人。《荀子·王霸》中还有“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和“朝廷必将隆礼意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均是将农、贾、百工、士大夫作为四种职业,认为从事这四种职业的人都是国家安定兴旺所不可缺少的人。同时,荀子比较重视农业,他强调了“观国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荀子·富国》),这里荀子认为士大夫、工商业者太多容易导致国家贫困,抓住农时、耕种收获才是国家的根本,这点与秦朝奖励耕战、汉代鼓励“孝悌力田”的政策是相符合的。
第三,荀子将“士大夫”划分标准进一步明晰,这一点继承发扬了孔子论“士”的传统。“士”这个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人,其中不少人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有权有势的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周初,士的社会地位,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大多为卿大夫的非嫡长子,也有周天子与诸侯加封的士大夫,是西周最低级的贵族。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的诸侯大夫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不免随之大增”[5](P10),如此社会上便形成了一大批有学问有知识的士人。这批士人大都以做官作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如“臣邻家有远为吏者”一语中可见当时士人远游为吏者也不在少数。但是最先明确提出如何可以称为“士”的理论标准是孔子。
孔子对于“士”的定义是与“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里强调了“士”不在乎衣食等外在物质条件的好坏,而应该有志于道。“有志于道”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要严于律己并善于完成自己的职守。故《论语·子路》中有“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在各种行为过程中要有羞耻心、道德心,要时时约束自己身心,在此基础上能够顺利完成国君交付使命的人就可称为“士”。其次,“士”要善于反思,如“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这强调了不同情境下“士”要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项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为人处世要顺人情也要合道义。再次,“士”要有坚强弘毅的品格,用生命的厚度与深度来诠释道,故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而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是表达了如果士人的生命能够与道合而为一,死生的大限可以打破,个体的生命迷局可获得根本性的突破。
孔子重视用“道”作为衡量士大夫的标准被荀子充分继承下来,他明确提出了“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意,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意,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打破了封建时代的血统论,将王公卿相的子孙不能守礼仪的人群归于庶人,而将平民子孙中能够学习文化知识、行为举止端正、信守道义礼节的人归为“士大夫”,这点与孔子是一致的。不仅打破了血统论,他还强调贤能的人不仅可做士大夫甚至还可以成为公卿诸侯,如《荀子·君道》中就有“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荀子强调士大夫与“道”偕行的言论还有“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万世不能易也”“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别贵始;贵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可见士大夫是可及“道”且可为“道”的。尽管士大夫不能像天子诸侯那样制定法令、进行郊祭社祭,但就这些法令礼仪背后蕴含的“道”而言,士大夫对其领悟贯通是可等同于天子诸侯的。也就是说,就精神境界而言,士大夫与天子诸侯是相通的,这点非常重要,这也是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逐渐寻求恢复其神圣性与独立性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严可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3]赵国华.说“通儒”[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1).
[4]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03(2019)03-0025-07
[收稿日期] 2019-03-28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东汉儒学的演绎与发展”,教育部重大项目“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阐释和实践路径研究”(14JZD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肖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副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 胡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