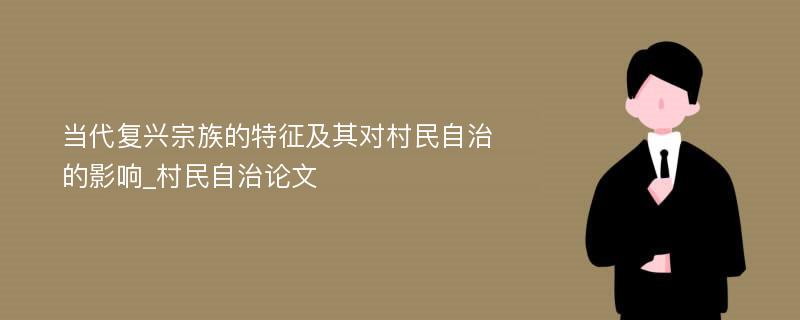
当代复兴宗族的特征及其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族论文,其对论文,村民自治论文,当代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3)03-0016-004
我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的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挑战,这些传统文化主要 体现在物质、制度、精神心理层面上,它们与现代生活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在当前推 行的村民自治的村政民主化建设中表现较为突出。在当前的我国广大西部农村村民自治 建设中,宗族对村级选举和村民自治的影响十分明显,它既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也关系 到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日益倍受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为此,学界政界一些人 倾向于强制性取缔。本文就当代宗族复兴的特征、影响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进而认为 在宗族消解过程中,如何加以引导,以促进农村的村政建设,加快西部农村现代化进程 。
一、现状:当代宗族的复兴与变异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为本位的社会。宗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众多海内外学者眼中,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它的宗族性或曰宗法性。正如冯尔康先 生所说:“宗族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流布最普遍的社会组织,拥有的民众之广 泛为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所不能比拟。”(注: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 版社,1994年,第27页。)宗族制度产生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对乡村统治,有意识 地利用宗族组织加强对农村的控制。随着历史的发展,宗族制度愈来愈强化。我们剖析 我国传统农村社区的运行机制及历史变迁。不难发现,1949年前,宗族组织一直是中国 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权力一直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补充。1949年后,国家权力全面深 入乡村,采取一种激烈的毫不妥协的方式对待宗族组织,取缔了乡绅阶层和宗法秩序, 靠人民公社体制直接控制乡村秩序。宗族组织虽然一度被人为的强制外力所遏制,但是 宗族赖以存在的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农耕性等基础并未真正动摇,这些基础不加 以消灭,那么它的内在生命力就难以消灭,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大多数农民的传统乡村 生活方式依然如故,也就是说,中国农村社会的血缘性、聚居性、礼俗性、农耕性的村 落生存状态并未改变。因而,一旦人民公社体制改变,强制性外力削弱后,沉寂了近40 年的农村宗族文化在广袤的农村大地逐渐复活并迅速蔓延,对我国广大农村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后重生的宗族尽管其作为 农村自然组织的基本特质没有变,但当前,农村宗族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社 会条件等与传统的宗族截然不同,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现代文明的外部冲击,使当代 宗族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一,聚族而居的宗族环境的变化。
聚族而居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在地理环境上,人为地构筑了一个宗族活动的理想场所 ,它是宗族得以存在的条件,随着现代社会关系向着现代化、开放化、民主化的方向演 进,乡村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发生变迁,农民要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原 来狭小的宗族框架内难以实现。于是,在国家现代化外部力量冲击下,传统的均衡被打 破,使农民的社会生活由过去封闭开始走向开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非农经济的 扩张,比如:离土的乡镇企业和离乡的农民“打工潮”,这导致了乡土性的断裂,从而 促使了宗族观念的淡化。
第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成员间聚合性的松驰。
宗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血缘性是宗族文化的生长点。血 缘关系愈直接,其聚合性就愈强。同一宗族成员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过去, 宗族内人们社会交往互助的圈子也比较狭小,多以堂/族亲圈、姻亲圈为主。现随着社 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不再是传统的单纯划一的血缘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导致血缘关系 网络以外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产生了譬如“同学”、“工友”关系即“朋友” 关系,非血缘关系网络的增多,就意味着发展的机遇多。同时也意味着宗族赖于存在的 血缘纽带的松驰。
第三,以礼俗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动摇。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现代文明通过不同渠道传播到乡村,对农村的宗族产生了巨 大冲击。比如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许多农户家里购买了电视,订阅报纸、杂志 等,还有许多青年农民到外地打工,直接经历了现代文明的洗礼,这些都源源不断地将 现代价值观念、都市生活方式输送到偏僻的乡村。加之,现阶段,国家正在农村推行的 村民自治等民主化建设措施,法制逐渐成为调节农村社会关系的有力手段,市场也成为 调节农村经济结构的方式,这就对宗族生存基础的礼俗性社会秩序产生了冲击。
因此,在此文化背景下复兴的宗族,就不可能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原始生态的宗族了 。据笔者这几年来对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宗族现状进行的调查来看,目前,湘西土家族地 区的宗族的影响力还依然存在,呈现出宗族组织形态残缺不全的特征。
到目前为止,在笔者所调查的地方,还没有发现一个完全地复制传统特色的宗族。重 建后的宗族都多多少少有了变迁,跟传统的宗族已不一样了。那么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宗 族的复兴呢?为此冯尔康先生提出了两条标准:一是是否修了谱或者是否有谱?另一个是 否维修或重建了祠堂。(注: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第27页。)若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湘西土家族地区确实复兴了大量的宗族组织。但从 当代复兴的宗族组织特征来分析,体现原始生态的宗族的相关载体与人们有关活动不易 看到了。
在笔者所调查的地方几乎都发现新修的家谱、族谱,比如:《田氏新族谱》、《王氏 族谱》、《彭氏族谱》、《瞿氏族谱》等,但是将新旧族谱进行比较研究会发现,二者 在写作体例上已有许多不同。传统的谱书一般包括谱名、谱序、凡例、恩荣录、先世考 、祠堂五服图、族规家法、传记、年谱等内容。而现行的谱书则较传统谱书简化多了, 主要内容是宗族源流、世系和字辈谱,而且对不合时宜的族规家训进行重新修订,与现 实结合得较紧。
没有族长之类的宗族领袖了。平时调查时,当你去问农民“你们这个宗族有族长吗?” 他们会说“没有”。但当你要详细了解该宗族情况时,他们会说:“我们宗族的事归某 某管,你去问他吧。”其实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现在明确的宗族族长虽没有,但是某些 姓氏暗中会有个头头。本宗族内部大小事,大到宗族内的救灾互助,小到兄弟分家、夫 妻吵架多半要找到族长处理;与外族间、宗族间的纠纷磨擦那就更少不了他。使他成为 社区里经常抛头露面的人。当前,这些人一般都有些文化,大多是国家退休干部或教师 ,在本姓的族人中具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
同姓不同婚,同宗不婚的族规虽也仍然执行,但执行起来已不如过去严格,比如,笔 者所调查一位田氏宗族女子,在读书期间找了一位同姓的男朋友,结了婚,虽在当时遭 到其父母和全族人的“不相认”处罚。这与过去宗族的“沉塘”或“打断腿”等的处罚 要轻多了。
二、后果: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1982年《宪法》中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这一乡村的基层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直 接民主治理的形式,它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依法 办理与村民利益有关的各项村务,实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经过近 二十年实践,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但由于村民自 治在推行过程中,其本身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比如:民主选举不规范、规章制度不 健全、乡村人民参政质量较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没理顺、村干部工作困难得到上 级有关部门支持力度不够,村务管理的民主化程度低、方法简单等等。从而导致村政工 作推动困难,甚至有的班子瘫痪,久而久之也得不到村民的信任,导致村干部与村民之 间关系紧张,有的村民不服。这给宗族组织的复兴以可乘之机。当我们在调查问到“当 你家有困难时,你首先想到的是想请谁帮忙?”这样的问题时,“当然是自己的亲戚啰”,这是大多数村民的直接回答。可见宗族能给他们提供亲近感、安全感、归宿感。在 我国广大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不健全,我国的农村经济不发达的今天,宗族能为村民提 供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寄托和依靠。因而,农村宗族的存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对村民自治工作影响很大,不管是经济落后的乡镇还是经济发达的乡镇,也不管是村民 自治推行早还是村民自治工作推行得晚的村镇,都或多或少存在宗族势力影响。宗族势 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已渗透到工作的各个环节。“宗族势力的强弱主要体现为其在农村 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是否重要,一般说来,宗族势力越强,其在政治中的作用则越活跃” 。(注: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在我们 这样传统文化氛围较重,宗族势力较强的广大西部地区,村民自治受宗族势力的阻力就 越大,其对村政的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第一,严重干扰村民依法的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是村民自治的一个核心内容,它也是村民行使自治权利的起点。 村委会的选举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村级领导班子的质量,而且直接关系到村民自 治的效果和村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级干部由 村民选举产生,村级党支部书记由上级党委任命,村长与组长则采取上级提名与村民选 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随着宗族势力的不断壮大,在选举中,某些宗族为了本宗族的利 益,徇私舞弊,扰乱选举的现象比较普遍。笔者在永顺县的一些乡镇参加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工作调研时发现,选民在选举投票时,一般以血缘关系来确定自己的选择对象。在 选举过程中,往往会形成几个不同利益集团。当一个村庄存在着几个大姓宗族时,往往 同姓宗族就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但当一个村庄中是同姓宗族,或某个大姓占绝对优 势时,则该宗族内又会按房族分为几个利益集团。比如笔者曾经在永顺调查这样一个村 庄,它由瞿、彭、田、吕、李等几个大姓组成,而彭氏与瞿氏势力最大,结果该村的村 长就由该两姓轮流担任。而现在瞿氏宗族势力明显占强,这几年村长都由该宗族成员出 任,既然是没有其他势力与它可匹敌,于是在此情形下,该宗族内部发生了分歧。瞿氏 宗族本身就分成后头屋、老屋长、河对门等几大房。为此,在每届村长换届选举时,这 几大房就会为此争吵不休,几乎是轮流出任。而且从其他学者调查的材料中,也显示类 似情形。譬如: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山西省长治市的南常村和南通村,被调查的49名选 民中,有18人在投票前与其他家族成员进行了商量,占被调查者的36.7%,其中有11人 是与家族成员进行商讨后投的票,占22.5%。为此,在投票选举前,互相串通,走访拉 选票的更是屡见不鲜。笔者在调查时,某乡的一个宗族能人对我说:“为了将我宗族的 某某人推上村长的位子,我真是挨家挨户、反反复复做工作,直到投票这一天,叫全族 的老小全都参加,一个也不能缺席,原准备赶集、砍柴的都不去了。就这样才好不容易 将他选上了。”另在我所看的资料中,有的村庄的选举更糟,有的村在选举唱票时,乘 机抢走一部分选票;有人在选举时竞抱走了投票箱,使选举被迫中断……这样,致使有 的村委会的选举反复多次才成功。相当部分村委会选举还算不上真正成功。其领导班子 的组成只不过是宗族之间权力均衡的舞台。由此可见,如此的选举是不公正的,不公正 公平的原因在于宗族操纵。
第二,严重影响了村政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将干部治村转变为村民治村,使村民成为自治的主体,它使亿万农 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基层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和保障。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扩大基层民主,保障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 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实行村民自治实际上是落实村民的主体 地位,还民主权利于民。《村委会组织法》规定,除少数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 “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 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村民通过“村民大会”和“村民 代表会议”参与村务、政务以及决定自身重大利益的决策和管理,村民会议有权依法罢 免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涉及全体村民共同利益和村里的大事,都由村民认 真讨论、决定,村委会仅是村民会议的执行机构,全体村民通过村民会议直接行使当家 作主的权利。通过村民自治,使广大村民直接参与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自己管理自 己身边事务,使主人翁的地位得到充分体现。
但在80年代后,随着宗族势力的活跃,一些热衷于宗族活动的人,被本宗族人封为族 长或能人,宗族往往通过宗族能人来影响村治。在村委会的选举中,各个宗族都通过各 种手段将本宗族的能人选进村委会领导班子。尽管各宗族推上来的人选都是本宗族中威 望高、“能力”强的人,但是,试想一想,被某宗族认定的“能人”,放在全村那就不 一定了。由于宗族的操纵,在宗族势力活动猖狂的地方,宗族势力与地方政权相结合, 形成了党政族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如湖南省道县的祥林镇,由族长担任或操纵支书的 行政村竟多达14个。(注:陈光金:《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回顾与前瞻》,湖南人民出版 社1996年版,第511页。)自宗族能人介入村政后,村政决策和管理因受宗族观念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血缘、地缘的影响,倾向于关照本族干部,大宗族利益,有的事要事 先请教所谓“族长”、“能人”。这当然使本宗族利益得到巨大满足,然而它是以牺牲 它宗族的利益为代价的,使代表公共利益的村委会成为维护本族利益的私家机构。这必 然导致干部与群众、族与族之间矛盾激化,甚至械斗。可见这些村政的决策不可能体现 最广大村民的民主权力,只能是以“我族中心”为基点。
其结果,使村民的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其体现为轻“民主”,重“权威”。它操纵 、架空了村政的基层政权,这样就有可能以宗规族约代替村规民约来处理村务。尤其是 这些利用宗族势力被选上的村委会领导,他们以自己是群众选出来的民选干部自居,上 任后公开维护本宗族利益,有的将宗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对抗基层政权,这严 重地干扰了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施。严重影响了乡镇工作的正常开 展。
第三,严重影响以法治村和村民对村政的民主监督。
实行“村民自治章程”和《村民自治法》是实行以法治村和村民对村政的民主监督的 前提和基础。也是村民自治主体地位的体现。完成村政选举只是为村民自治开了个头, 还有许多后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要使村民自治走向民主化道路,我认为“村民自治法 ”和《村民自治章程》是关键,因它们对村政的管理一切制度化,转变以前“人治”局 面。从笔者所调查的现实表明,一旦村委会选举之后,怎样去治村、管村,许多村民就 不去管了,认为那是村干部思考的问题,对于“你认为你们村应采取什么措施,村才会 更富更强呢?”的问题,大多数人投以的只是茫然的目光,或是淡然的唐突的一句话语 :“那是干部们的事,我们老百姓哪管那么多。”大多数村民参与民主管理意识淡薄, 更不用说去监督什么领导。因而大多数村虽搭起了村民自治的架子,却没有什么真正的 内涵。
农村的村政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规章制度不健全或者有章不循,这样干部治村的局面没 有得到改观。在宗族势力把持的村政,出现旧宗族族规取代乡规民约或村民自治章程, 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弃法治取人治。因为在宗族观念中人们普遍信奉着“亲三代,族 万年”、“同宗同族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于是在村务管理中,对同族干 部监督较松,对异族干部说是严格按原则办事,不如说是斤斤计较,吹毛求疵。把别族 人对自己本族干部提意见,认为是找岔子,与本宗族过不去,于是千方百计想法子要保 护本族干部,甚至放出话说:“你们想出这样的法子,想把我们的干部拱倒,没门。” 这样在村委会正式之外,就游离着非正式组织的具有一定自治功能的宗族组织,扮演着 “压力集团”的角色。它们在每当村委会制定、执行相关政策时,以“代言人”身份介 入,迫使村委会做出有益本宗族利益的妥协和让步。封闭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势力浸润在 乡村基层政治生活,影响了村务监督工作的严肃性,影响着开放的民主政治在乡村的健 康发展。
为此,要使村民自治制度落到实处,就必须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制定村民自治章程, 严格按程序操作,尊重村民意见,要经过村民反复讨论修改,最后交由村民大会或村民 代表会议通过,严格规定村民组织、干部管理、经济管理、社会公益保障和社会治安等 ,涉及农村社区管理方方面面。尤其明确干部的职责范围、工作要求和监督机制等,然 后用《村民自治法》加以保障,上升为法律效力。每隔一定时间,村委会对这段时间所 做的一切工作进行村务公开,然后召集村民进行评议,只有如此村民才真正参与村政管 理,才能真正实现其民主监督的权力,也才能使村民自治逐步走上以法治村的民主化建 设道路。
通过村民自治,增强了村民的民主观念,养成了民主习惯,学会了民主方法,它代表 着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方向,为全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了全 民族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的提高,它是建设基层民主政治的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力量 源泉。宗族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村民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和乡村社会稳定,影响了未来乡 村的政治走向和我国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然而宗族文化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宗族文化的复兴是一种内在的自发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下的产物,有其深刻的历 史和社会的根源,同时我认为,当代宗族的复兴并不是原始生态的宗族的复兴,它是有 变化的复归,处于消解中的复归。有鉴于此,我们对其应采取正确的对策,必须进行积 极地引导和限制,不断注入现代文明理念,淡化其封建落后的意识观念,通过加强农村 的精神文明建设,促成其消解,从而使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走向民主健康的建设轨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