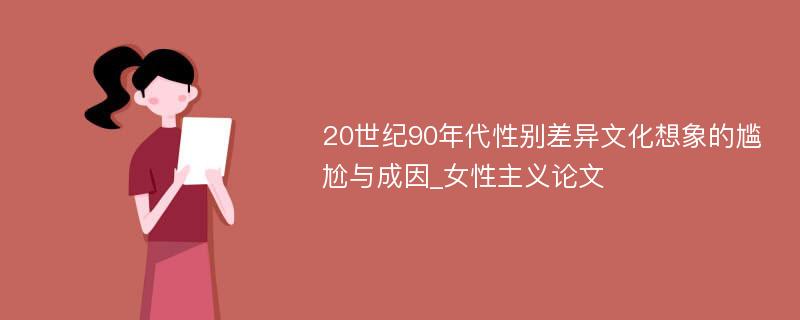
90年代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的尴尬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想像论文,性文化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尴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性别差异性,构成女性的性别意识,所以性别差异性是女性主义理论一个基本范畴和 研究视角。同时,对性别差异性的肯定或否定也构成女性主义理论长久以来关注与争论 的焦点。性别差异性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90年代具有自觉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的 视角,这样的写作可以命名为“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或“性别差异性文化书写”。我 们将选择90年代富有代表性的女性本文来审视这一文化想像的样态。
(一)
如果说“只有当女性作为一个差异性的群体重新聚集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反身 观察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的现实”,①(注:戴锦华:《犹在境中》第179页,知识出版 社1999年版。)那么,正是对“差异性”的关注带来新时期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但由 于“男女都一样”这一关于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长期的覆盖,也由于80年代以来男 权成功地利用差异性疯狂地反攻,“差异性”在80年代初语境中身份十分暧昧,它在被 带入本文的同时又常常遭遇否定。以张洁、张辛欣为代表的80年代早期的女性写作就常 常陷入做人与做女人两难这一古老的悖论中不能自拔。
尽管70年代末那场人道主义启蒙思潮在与五四思想对接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为后 者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妇女解放这一重要内涵,但毕竟随着人道主义话语的深入,人性 的幽深与丰繁在文本中徐徐展开,对性别差异性的知性认同终于姗姗来迟,80年代中后 期“三恋”、《岗上的世纪》、《玫瑰门》、《女人组诗》、《静安庄》等一大批女性 文本正是基于这一认同的出色的文化想像。
90年代的文化语境如春风化雨喂养了更加缤纷芜杂的性别差异性想像。这不仅是一种 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须。因为正是性别差异性奠定了女性作为独特的文化群 体的类的本质,而这一本质又是女性作为一个相异于男性的性别主体的历史性出场所必 需的。
从哲学层面而言,所谓类的本质是对某类人某类事物的抽象概括。“人的类的特殊性 恰恰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 识的类的存在物”。②(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6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妇女作为类的存在,其类的本质在千千万万的个体那里既有千差万别 的一面又有普遍共同的一面。“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 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 知的社会自为的主体存在”。③(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6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那么,90年代女性个人化的写作正是在作为性别差异性的本 质与女性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对立统一中建构女性的主体性的。事实上,80年代王安忆、 铁凝们的性别想像同样也包蕴这一内涵,只不过,90年代的女性写作呈现更加尖锐的个 体的姿态。
作为姿态最鲜明的表现的无疑是以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为代表的私人写作。 她们以自我生命最隐秘的经验叩问作为性别个体的女性深层的意义。这是对80年代性别 差异性想像的延展与深入。这种延展与深入在90年代获得一个完全崭新的想像空间—— 女性自我的生命之躯。“躯体写作”和性话语成了陈染林白这一支脉女性写作确立自己 独立性别精神立场的重要路径,但遗憾的是90年代的女性“躯体写作”几乎普遍遭遇误 读,成为男权文化消费的热点。
90年代出现的另一种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的景观是对一向为主流中心话语所忽视与无 视女性边缘性琐碎生存经验的书写,《长恨歌》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段落——以张爱玲 式的“琐碎政治”来追问男权社会中心化生存的意义,从而对后者充满了“绵里藏针” 的解构意味。但这一想像的空间在90年代的独特语境中大量繁殖歧变为闲适平庸富态的 小女人散文:津津乐道于闲妇们梳妆打扮,养尊处优,恋爱性事,女性琐碎的生存经验 在这里不仅已然丧失了边缘性所应具有的个性与追问式的解构意味,而且衍化为对男性 把玩心理的一种潜在的召唤。
与这一流脉性别差异性相关联的还有这样一种性别书写——在对旧时代闺阁文学的重 新的认同中想像性别差异性,这里固然有对性别历史经验的体认,也有汉语写作的语体 自觉,却更有对繁复凄艳,慵懒娇憨千娇百媚的闺阁风情的仿制与复归。就在这仿制与 复归中古老的父权文化规约得到又一次优雅的默认。
就这样,90年代的女性写作在以缤纷的态势丰富着性别异性文化想像的天空的同时, 也频频成为男权文化消费的热点与装饰。以建构与男权文化相抗衡的女性独特的文化价 值为旨归的差异性文化想像,何以在纵情飞翔的同时又重新落入男权的藩篱,暗合父权 秩序对女性的规约?这正是90年代女性写作的宿命。让人想起90年代初林白的谶语般的 命名“致命的飞翔”。
(二)
造成90年代女性写作尴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些文学之外的原因,是否女性写作 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悖论?女性主义文学评论界的解释一直十分暧昧,这就给男性 话语霸权对这一写作姿态的非难留下了许多口实。实际上导致90年AI写作作尴尬的原因除 了宿命般存在商业话语和男权话语这两个巨大的阴影外,更为内在的原因是知性认识的 含混性。这种含混性几乎是西方女性主义漫长历程中的理论宿命。在这一理论话语本土 话的过程中这种含混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势必影响到了创作。比如直接造成上 述写作尴尬的原因主要是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对两个基本概念的模糊认识。
首先是对“身体”这一概念的含混认识。以埃莱娜·西苏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躯 体修辞学无疑对90年代女性躯体想像产生深刻的影响,陈染林白们的躯体写作显然有很 自觉的理论意识。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文化秩序中女性的躯体只是用以建构男性 主体性的场所,一种不是主体性的物的存在。因此尽管这一文化秩序有着无比丰富的关 于女性躯体的代码系统,但这只是“空洞的能指”,真正的女性躯体始终是历史与文化 的缺席者,这也正是菲勒斯(phallus)得以统治的原因。“父权制文化秩序中躯体作为 女性的象征,被损害被摆布,然而却未被承认。躯体这一万物和社会发展永恒的源头被 置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之外”。④(注: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359页 ,39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那么,由女性自己把躯体带入本文进而带向历史 与文化的空间,无疑具有性别意识形态的意味。同时,身体写作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 也是别无选择的书写策略。因为,现存的语言系统正是菲勒斯中心语言系统,妇女用这 样的语言写作是无济于事的。妇女必须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 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⑤(注:埃莱娜·西苏《美杜 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01页,194页,188页,北京大学出 版社1992年版。)“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 源泉才会喷涌,我们的气息才会布满世界”。⑥(注: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 见张京媛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01页,194页,1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版。)
由上面的引述我们不难看到,在以埃莱娜·西苏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身体修辞 学中,女性的躯体被看成与女性的主体具有统一性的。这显然受到德国哲学家梅洛庞蒂 的《知觉现象学》对躯体认识的影响。“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身体取代思想主体的认识 论至上性,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关键,是我们直觉被设定的关键。也是我们获取 经验和意义能力的关键。身体代表着外在世界和我思得以发生接触的内在世界场所…… 所有的主体性都是一种被设定或被肉体化的主体性,因此是身体而非关于某个纯自我的 科学构成开启了我们同对象及其他(肉体化)主体的关系样式……”⑦(注:理查德·沃 林《文化批评的观念》第171,172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人类的意义和审美的 意义只有通过感性肉体的本体论中介才能得到自我揭示”。⑧(注:理查德·沃林《文 化批评的观念》第171,172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与此同时,后现代女性主义又深受福柯关于身体(body)理论的影响。比如,后现代女 性主义者莱克勒克(AnmeLeclerc)在谈到身体快乐时说:“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 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女性的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女性的阴 道,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⑨(注 :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第128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版。)正如特里· 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从梅洛庞蒂到福柯的转移,是作为主体的身体向作为客体的 身体的转移。对于梅洛庞蒂来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身体是有事情可做的地方,对 于新的身体学来说,身体是有事情——观看铭记规定——正在做给你看的地方。”⑩( 注: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幻象》第83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这种对身体 认知的理论暧昧无疑影响了90年代的女性躯体想像。即便90年代最严肃的女性本文的躯 体想像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歧义与疑义。这种暧昧到了90年代末的一些女性书写中成了 一种有意策略。这正为受众的误读和男性期待想像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另一个充满暧昧性的概念是性别差异性,这一概念对女性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已在前 面提到过。长期以来女性主义理论界一直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性别差异性 有时被当做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规约而遭致否定,有时又被看成足以与男性文化相抗衡的 女性独特的文化意义而被强化与张扬,这种强化与张扬又时常导致对差异性的异化。
事实上父权文化秩序所认同的并不是女性的性别(差异性),即性别意识,而是这一秩 序为这一性别所规定的职能(对差异性的文化价值定位),即通常所谓的角色意识。比如 封建时代的妇女根本没有性别意识,只有角色意识,为女,为妻,为母。当然,性别意 识的某些基质往往会被畸变异化后包裹于角色意识中。例如作为女性合理的生命欲求的 母性却异化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性。于是,面对性别历史经验,我们往往需要非常小心地 加以甄别。这样的甄别过程几乎如履薄冰,歧路丛生,随时都可能在认同差异性的同时 也认同对差异性的价值定位,即父权文化秩序的规约。我想,这正是90年代差异性话语 遭遇尴尬的内在原因。其实在90年代最出色的性别差异性书写之一的《长恨歌》中,作 者就颇具用心地甄别过女性的角色意识与性别意识,刻意将主人公的性别身份确认置于 新旧种种女性角色意识的层层剥离中。(11)(注:参见拙作《主体性建构:对近20年女 性主义叙事的一种理解》,《小说评论》2000年第6期。)遗憾的是在对《长恨歌》的众 多女性主义解读中,却鲜有注意到这一点的。
当然,在甄别角色意识与性别意识的过程中也可能导致将婴儿与脏水一同泼掉的结局 ——否定差异性的反本质主义。这也是西方从经典女性主义到后现代女性主义漫长的历 史过程中经久不息的声音。国内的女性主义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应这种声音。
我们固然赞同波伏娃那个著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反对女 性的本质先在性的预设,反对西方传统文化对男性/女性二元对立划分的刻板模式。但 倘若像反本质主义宣称的那样不存在着普遍的女性本质,那么,女性主义理论的立足点 又何在?女性的性别主体性何以建构?反本质主义并未使90年代女性写作摆脱尴尬,相反 的,还将导致一个更致命的悖论。
“对性别差异性的更完整的女权主义理解不否认两性之间可能存在的深刻的差异,但 它不假定这些差异是妇女处于普遍明显的不平等和从属地位的确凿原因”,(12)(注: 王政 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第202,203,20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西方经典女性主义认为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形成经历三个转变阶段。首先是从生理差异 向社会差异的转变,然后是社会差异产生价值关系,价值关系引出不平等观念。比如, 女人生孩子,男人不能生孩子。这是最明显的生理性别差异(sexual difference)。既 然女人能生育哺乳就适合于家里照管抚育孩子,男人外出干活,这便导致社会性别差异 (gender difference)或者说社会分工。在这种社会分工中,男人所承担的工作被认为 是重要的,而女人所承担的部分则是次要的附属的。这便导致价值差异,最终导致不平 等。这便是传统自由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 Theory)的理论基础。(13)(注 :参见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第2,6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这里我们不 难看到,差异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而对可见的性别差异性的评价才可能既是不平等 的原因又是不平等的结果。
“最初出现的是人的一系列潜在的特性和性情的分化,变成男性和女性。后来男性的 支配地位导致主要用那种肯定男性性别特征的优越性的语言来规定真正的人的品格。这 样,人类的成就就被视为主要是由男性决定的(realization of maleness)”。(14)(注 :[美]郝大维·安乐哲第《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第8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赋予女性的性别特征以优越性的社会评价,比如,前面 所说的女性的孕产能力一向被看成次要的附属的,不如男性在外的工作有价值。而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戈尔·卢宾(Gayle-Rubin)就认为人类本身的再生产方式先于任何人 类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行为开始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时建 立的关系比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更重要。”(15)(注:参见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 究评价》第2,6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因此,分娩是女性特有的创造生命价值潜力 的体现,同时分娩的潜在价值还在于“导致具有潜在特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这种方 式可为女权主义的重建提供基础”。(16)(注:王政 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 》,第202,203,20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王安忆80年代的文本《小城之恋》正是把女性精神上对男性的僭越,从而获得的救赎 与提升建立在对生命的孕育上。母性的价值并非如男权秩序所界定的那样是为家族提供 后代而获得的。在这里,母性是一种女性的性别意识而非男权秩序所指派的角色意识。 所以,郑敏在谈到女性诗歌时说过这样的话:“女性最伟大的特点是母性,女性诗歌要 尽可能地展现母性景观。”把母性作为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的一个基点并不意味着主张 性别差异的生理决定论,但人性毕竟是生理基质与历史文化深刻而久远的嵌入与缠绕, 生理的差异毕竟导致男人与女人的不同性别境遇并因此对两性的心理结构行为方式产生 影响。
(三)
当然,其实人的自然属性中也已然包含了社会历史内容,恩格斯说:“妇女的皮肤是 历史发展的,妇女头发是历史发展的,如果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一起统统去掉 ,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原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呢?干脆地说,这就是雌的人类。”(17 )(注: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马恩全集》第37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因此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来看待性别差异。差异性文化想像中应该包含女性不仅作 为话语主体而且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内涵。女性自我的生成应当被置放于社会历史的联 系当中,“如果说自我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东西,那么缺乏构建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必然 会阻碍自我力量的发展。无论是从缺乏深层次自我的女性联系当中还是从缺乏深层次联 系的男性自我当中都不能产生出一个具有稳固基础和丰富关系的自我”。(18)(注:[美 ]凯瑟琳·凯勒《走向后父权制的后现代精神》,见[美]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 精神》第111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认同女性琐细边缘的性别生存经验(包括 身体的经验),追述那个古老的岁月中“苍凉而莞尔的手势”(张爱玲语)固然能够彰显 特定的“女性对繁华与毁灭的审视,对文明的质疑与彻悟。”(19)(注:戴锦华《奇遇 与突围——90年代的女性写作》,《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从而具有多重的文化意 义。但假如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仅有这样一些逼仄的翱翔地,却又是对那个古老的规约 的默认,即男人/女人,主外/主内,也许我们要做的既不是花木兰式的化妆进入历史, 也不再是一味的规避“历史叙事”,而是改写和重构“历史叙事”。正如伍尔夫所说的 ,女性写作与男性写作的本质区别“不在于男人描写战争女人描写生孩子,而在于两个 性别都表现自身”。(20)(注: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359页,395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如果说80年代方方的《埋伏》、《行为艺术》,90年 代初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90年代中后期徐坤的《狗日的足球》、《先锋》、《游 行》等都是以性别书写的立场对现实历史事件进行迥异于男性叙事惯例的书写,呈现出 对男性文化精神的坚硬与虚妄的颠覆与戏弄。同样出现于90年代后期的须兰力作《纪念 乐师良宵》则是对以往历史叙事的一种回应式的补充,文本以90年代叙事少有的心灵力 度,以女性对生命独特的理解与张望,将南京大屠杀的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场景衍化为 一个民族乃至人类所遭遇的永生永世心灵的杀戮与劫难。这样一种有着女性独特精神内 涵的历史与现实的叙事向度在90年代末以卫慧为代表的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的“另类” 写作中下滑为“现时性”,“这个现时性如此的膨胀,如此的泛滥,以至于把过去推到 我们的地平线之外,将时间缩减为唯一当前的分秒”。(21)(注:米兰·昆德拉《小说 的艺术》第18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真正的现实在卫慧们的叙事中是沉默的。所谓 的“另类”事实上也只是一种自我作态的时尚表演并不是真正具有解构性的性别精神立 场。在现实与精神双向度上同时被抛的写作只能是一种轻虚的时尚写作,并没有为90年 代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提供新的话语空间。
性别差异性的历史内涵还应指涉“它与其它从属历史群体的交叉是如何形成并继续形 成两性差异以及我们看待和评价这些差别的方式”。(22)(注:王政 杜芳琴主编《社 会性别研究选择》,第202,203,20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我们承认性别类群的特 性同时也不否认亚群体的差异性,即妇女群体的内部关涉到种族阶级及族裔的差异性, 在90年代的本土语境上,性别书写理应关注不同阶层妇女性别境遇差异,关注分别基于 中西方传统宇宙论的两性关系阴阳互补关联模式和两性关系二元对立排他模式之间的差 异,并以此作为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的重要延伸点。遗憾的是90年代的女性写作在这些 方面都不尽如人意。90年AI写作作女性更多的把目光投向自身或“类自身”——都市的白 领女性(文化或商业白领),抑或是古老岁月中庭院深深帘幕低垂的女人们。在两性关系 式的书写上大都呈现出一种对抗与决绝的模式化状态。也许王安忆写于90年代末的长篇 《富萍》是个很例外的文本。
尽管人们大可以把《富萍》看成是始于《长恨歌》的关于上海这座大都市叙事的继续 ,但毕竟《富萍》讲述的是上海最底层的劳动妇女——保姆与运送垃圾的女船工们的生 存境遇(底层劳动妇女的境遇几乎是90年代女性叙事的盲点)。而且,虽然相比于90年代 其他的女性本文,《富萍》似乎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性别立场,文本中还出现了一些有血 有肉的男性形象,如舅舅、戚师傅等(这的确不同于90年代性别叙事惯例中男人不是面 目模糊就是面目可悲可憎),但那《长恨歌》式的鸡零狗碎,絮叨繁复的叙事方式,那 对琐碎边缘的日常生存经验的诗意认同,都在指认着王安忆式的独特的性别叙事立场, 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些独特性使它从本世纪末性别叙事符号化类型化的惯性滑行中凸现出 来。这种凸现似乎更得力于文本叙事对本土性别气质的指认。它表现女人对苦难命运的 挣扎与抵抗、承受与包容,也表现女人与男人互相以自己卑微而韧性的生命支持着对方 ,点点滴滴共同求取生存之光。弄堂街巷,灶间柴房,低矮破旧的棚户区,苍蝇成堆跟 随的垃圾船……但你只要看看船两边河岸“遍地的油菜花,瓦兰的天”,那“炊烟四起 ,饭香四起连成一片”的棚户区院落,一股股民间本色的生存的暖意与诗意便从文本中 冉冉生起,那样的亲切而久远,正如这天地间的女人和男人,生生不息……
性别关怀衍化为一种民间关怀,也许这正是西方女性主义这一“他者”话语的本土化 。女性叙事与民间叙事已然成为共谋,毕竟两者有着共同的边缘化的文化境遇。这一叙 事倾向在《长恨歌》中已经存在,在这里作者兴许有意延续与拓展。
如果说90年代中后期以来性别想像日益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那么,王安忆的叙事立 场是否为新世纪的性别想像启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话语空间?当然了,在这广阔的空间 中飞翔,该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的路径,这又是一个必须小心翼翼的关口,否则,将又 会是一次“致命的飞翔”。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 差异性论文; 富萍论文; 文学论文; 性别社会学论文; 性别文化论文; 长恨歌论文; 王安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