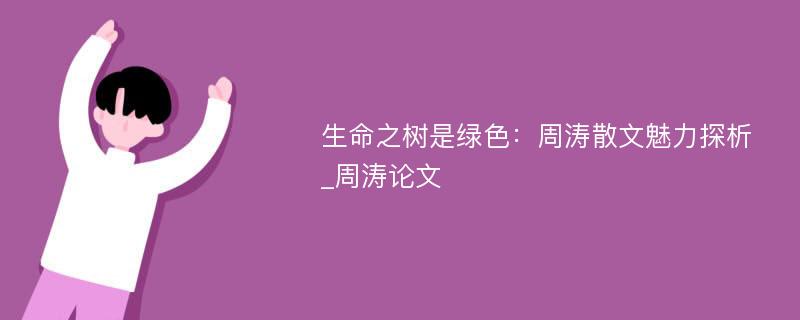
生命之树长绿——周涛散文魅力探寻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之树论文,魅力论文,生命论文,周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散文界,周涛的散文与贾平凹、余秋里、史铁生等人的散文一样被称为“大散文”。有评论家认为:周涛散文之“大”是气势沉雄、意蕴深远、笔力雄健。这样总体上的归纳我以为是准确的。如果作深入的探究,我们会发现周涛的散文都贯穿了一个大的主题——对生命(包括生命激情)的颂赞、崇敬和对生命本质的探索与参悟。在周涛的散文中,对生命现象的描绘和对生命本质的探索总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家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思考亦如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这种清醒的生命意识,就使他的散文呈现出当代散文界少有的、野马般的生命活力以及对读者的巨大冲击力。可以这么说,周涛的散文已真正触摸到生命的底蕴。
一
周涛散文世界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在周涛的笔下,草原、戈壁、雪山到处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空中有猛禽苍鹰、鹞子,稀世之鸟的朱鹮以及气质高贵的红嘴鸦,地上有奔驰的马、牛、羊群、细狗和雪地中如“红色的火焰”的狐狸,草原上那些野菊、毛地黄、风铃草、冰草、马铃、蒲公英、野葡萄和草莓盛开怒放,欢度着自己的生命节日。但比较起来,周涛写得最多、最倾注感情的是两个主题——一个是马,一个是骑手(牧人)。
既然周涛认为:游牧文化是马的文化,他就必然对文化的主体——马,寄予满腔的热情,进行热切的赞美。在周涛的散文中,就有《巩乃斯的马》、《饮马》、《高榻》、《白马夕阳》等篇章,对这些“奔腾的诗韵”、“草原的油画”、“荒原上的小群雕”、“散铺在山坡上的好文章”的美丽形象和生命激情作了倾心的描绘,并发出这种情与理融合的感叹:“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让人随意欺凌,并不懦弱,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巩乃斯的马》)这种带有古典情绪的英雄崇拜,实则是对活泼、坚韧、充满野性力量的生命激情的崇拜,是对生命理想的追求。对马的赞美崇拜必然会导引出对驾驭马的骑手的赞美崇拜,在周涛的笔下,那些骑手——无论是驱马狩猎的牧人,还是踏雪而行的边防战士,抑或是那些垂垂老者,只要一跨上坐骑,他们的青春活力就会在马蹄的叩响中迸发,他们的生命激情也会随之而升腾。《过河》是一篇充满传奇色彩的散文,读后令人感慨唏嘘:作者驭马过河,但马却逡巡而退缩,想尽一切办法仍不奏效后,他准备把马寄放在河边的毡房,自己先过河去办事。毡房中一位80高龄的哈萨克族老太太,衰老枯瘦,卧病在床,当作者说明请求事宜后,老人竟示意将她扶起走到河边,又示意将她扶上马鞍。在作者惊恐惶惑的目光中,这位哈萨克老太太竟有力地控制了马缰,策马跃入河中,把这匹看似顽愚实则机灵的马驾驭过了河!老人策马过河的画面是那样充满诗意美,然而它的象征含义却清晰地蕴含其中:马背上的骑者是永远充满生命活力的,马背上的民族是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的,生活在这充满活力的世界,就应当做一个敢于并善于驾驭任何骏马的好骑手。
在《周涛散文》三卷集的第一卷中(以西部题材为主),我们发现开头的三篇文章是《巩乃斯的马》、《过河》和《猛禽》,作者将这三篇文章放在文集之首,足见他对这三篇散文的重视。其实,三篇文章也概括了周涛西部散文的主题,不仅表达了周涛的生命崇拜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善良生命遭毁灭的悲怆和感慨。
《猛禽》是周涛的一篇散文力作。文章以鹰眼为视点,以充满情感的、极富表现力的语言,叙述了一个生命毁灭的故事:那只年轻的鹰由于扑击恶狼时,一只利爪深陷在狼身上,被锁在骨缝里无法拔出,被狼活活拖死。故事充满英雄主义的豪情,也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周涛因之而为鹰的家族如此衰落而感慨:渺小、平庸、自私最终总是战胜强大、美丽和献身精神。《红嘴鸦及其结局》写那只红嘴鸦被人逮住活活气死的故事,也展示了一个不愿失去自由的高贵生命毁灭的悲剧,与《猛禽》有异曲同工之妙。是的,生命是美丽的,它的升腾、张扬,呈现出勃勃生机是一种怡人的美,它的陨落、毁灭是一种悲剧的美,周涛的散文在表达生命这一主题时,善于从两方面去展示其丰富的内涵,让我们看到周涛的血液中有一种英雄式的悲壮与高贵。
二
周涛散文的魅力,不仅是因为它展示了生命的激情和悲壮,而且因为他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探索和参悟是那么鞭辟入里,那么睿智而启人心智。在当代散文创作中,不少作家也注意从生命的意义发掘出新意,但相对而言,他们的视角狭小了些,因而视野不够开阔。而周涛在表达对生命的参悟时,视野相当开阔,由物及人,由人及民族,由民族及历史,而且思考更为深邃,能够由表及里把这种思考提升至文化的层面,这就显现出周涛在探索生命意义时所达到的深度。
在周涛的心目中,生命是美丽的。美丽得如同那鲜艳的花朵一样,“花开放了,但是花是为什么开放的呢?是为了让公园更漂亮、游客更愉快吗?不是,花开了是生命本身驱动的,花朵美丽是生命本身美丽。”(《命里的街道》)因而,他从窗台上的那充满了生命的夸耀和欲望,显得性感的腥红色的令箭荷花上看到了这种生命的美,感悟到“这就是生命”,“寂寞一季也要赢得一个美的透彻”(《令箭荷花》)。而且他从那“花茎紫红,充满强烈的生殖欲望”的昙花上,悟出:“越是大的花朵,越就显得性感”,他对生命的理解更透辟了:“青春是生命欲望最活跃的阶段。”(《吃昙花》)周涛从花上,阐发了这么多关于生命的思考,实则是昭示了自己的生命哲学:生命是美的,是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是美的,是充满生命的欲望的。所以对这生命本身显示的美和驱动的欲望不必指摘和禁锢,应当善待之。在周涛的心目中,生命又是顽强的。他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株近800 年高寿的巨树已存敬畏之情,他从这棵树上看到了“伟大”,认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正是这样”(《巨树》)。周涛敏锐的目光就这样掠过红的花绿的树,从花开的短暂生命和巨树的漫长生命中发掘出自己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感悟生命当然要返回到人自身,返回到认识自我,诚如蒙田所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自我。”周涛从自我和人自身感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时,常常能够坦率地解剖自己,并且结合日常生活的体验,阐发出独到的见解,使人感到他对生命的感悟是与人的一种平等的对话,而非形而上的理论说教。在《某片树叶》一文中,他坦率地解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并且觉察到人生的困惑:生命的本质是扩张自己,实现自己,伟大自己,生存的局限却是缩小自己,限定自己,消失自己,人的一生常在矛盾中磨损了。人是伟大的,亦是微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树叶——可以被时间的风轻轻吹落的一片东西。这种见解实在深刻,也由此让我们看到了周涛同情、理解生命的原因所在。在《甘肃篇·病理研究》一文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他在人生的特定时期——生病住院时对生命的感悟:
我觉得,一个长期健康的人突然进入病境,有助于反观和领悟很多东西。病情使人换了一种眼光,一副心态,病情使人暂时脱离现实、与世无争,因而有了“超现实”的条件。所有的病人住在病院里时,都像是从现实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兵和缴了械的俘虏,他们眼下不具有战斗力,因而较大程度地受到人道的待遇,被人谅解和关怀。他们一般也由于自己的病况而悲天悯人,变得比平常善良一些;互相之间由于没有利害,同在受难而变得容易倾吐心曲,真诚了好几倍;再加上病体一般减却了性的冲动,他们往往平静了,自我表现的行为减少,不再狂妄浮躁,眼神里有一种哀伤的美……哦,病人原来就是圣人!集真善美于一身!难怪人们称医生护士是天使,原来他们的职业是围绕在这类圣人之间。
真是“蚌病成珠”,病人生病反倒使人的真善美的一面真实地凸现出来。周涛的这种生命的体验,决非消极的生命哲学,而是对一种圆满的生命境界和生命品格的追求,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启发尘世间为既得利益纷争敌对的人,从中体味到一些有益的东西。
周涛对生命本质的探索和参悟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能够将自己的体验提升至文化的层面,从一个比较新鲜的角度分析问题。周涛出生于山西,从小受到汉民族文化的熏陶,中原文化是其文化之根,但新疆和西部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西部文化又渗入了他的文化内质结构,两种文化的结合,就使得他切入生命这一主题时,与别的作家相比,就更多了一些比较的成分,更多了一个切入的角度,就能够发现生命的差异之因——是文化的差异所致。比如作者在维吾尔族真诚的家宴中,深切感悟到汉民族的“食文化”是一个民族病态的反映,而强健的民族,他只要痛吃,不需要太多的花样。作者的感悟是如此的犀利:“生命力衰退的族类丧失了性的原始力,故而发明了‘玩女人’,丧失了吃的原始冲动,所以搞出这花样翻新的所谓‘食文化’。”(《和田行吟》)这是对生命力强盛的礼赞,也是对生命力萎缩的鞭笞,而将之上升至文化的层面,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作者对它们的臧否态度。同样,作者游牧长城,目光穿越历史的烟云,从长城为什么不能拦阻外族一次又一次的入侵,来分析其根本原因:是游牧文化(西部文化)战胜了农耕文化(中原文化)所致——游牧文化的侵略性、扩张性战胜了农耕文化的保守性、狭隘性,而其根本原因,是这两种文化之根——生命品格的差异所致。为什么呢?因为耕耘者在庄稼面前,其心情和方式更像庄稼的仆人。这种生产方式,就使忍受、屈服的习性、品格沉淀在遗传的基因里了。而牧民放牧,更显出统治者、征服者、驾驭者的意味,策马而行,吆喝驱策牛羊,优游任性,威风八面,这样的劳作方式培养了牧民的心理优越,就使牧人的生命品格中少了一些忍受和屈服,多了一些征服和扩张的欲望。这样从生命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解释战争,是一个别具只眼的新角度,它给我们洞穿了一扇观照历史和民族的新窗口,也是周涛散文气势沉雄、意蕴深远的原因之一。
三
在当代作家中,散文创作具有深刻生命意识的另一个作家是史铁生。正是因为他的身体残疾,所以他对生命的思考比正常人深刻得多。而身体健壮,既能文又能武(有很好的摔跤天赋)的周涛为何在其散文作品中贯穿着生命的红线呢?我以为这是与他的生存环境和自身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气质紧密相关的。
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似乎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像周涛那样,长期生活于西部边疆,并且运用散文的长卷大作,对西部的山川和其间生存的生命倾注了这么多的激情。置身于辽阔广袤、人烟稀少的西部大地,面对这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原,很容易比照出人的渺小,更易产生孤独、悲哀、凄凉的真实情感。这个时候,作家的社会联系被隔断,文化的鳞片一点点剥落,就很自然地关注周围的生命之物,并以审美的眼光来注视它们的生命状态,进而把这种关注和审美转化成对这块土地和生命万物的理解和亲和。加之西部文化的影响,他的生命品格里也多了一些激情张扬的因素,因而他笔下的生命之物总是充满鲜活和野性,甚至涂抹了性感的色彩,而少有含蓄和委琐的一面。
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作家的“生命观”——“生命第一”的观念,他在《散文和散文理论》一文中说道:“实践第一的观点就是生命第一的观点。世界上没有什么理论比人和人的生活欲望更重要。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精神品格比人的生存要求更重要。”这种观念贯穿于周涛的散文创作中,我们就看到了作家笔下的生命之树是那么永远青绿,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另一方面,由于周涛的诗人气质和充满情感的细腻表达,也使这种生命意识在周涛的散文中得到了强化。周涛是一位诗人,诗人对生活总是有着真挚的情感和细致的观察。面对西部这生命顽强坚韧生存的地方,他总是很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生命的雄姿,体察到那些生命的状态,而且能够把自己对万物的观照化为一种生命的体验,以“物我合一”的方式去参悟生命的欢欣和痛苦、高尚与卑俗。当“亲爱的麦子”被倒进磨坊,在水磨上被磨碎、被咀嚼、被粉化时,作家感受到自己也像麦粒一样被一点一点地、慢吞吞地磨损着(《麦子》)。当二十四片犁铧插入草原,切断了绿色植物的根系时,作家体察到它们疼痛的撕裂声,神经被切断时的痛苦呻吟(《二十四片犁铧》)。这样的表达,就有别于那种虚玄的生命哲学的说教,而让我们感到亲切,能够进入这种意境,去真切感悟生命的意义。
是的,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周涛散文的魅力,正是在于他给我们展示了生命之树的翠绿色泽和精神风貌,加深了我们对平凡而又伟大的生命的认知和参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