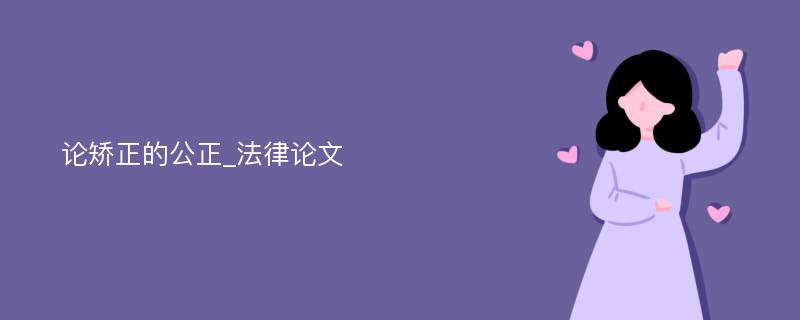
论矫正的正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矫正的正义是对分配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一种补充。它以分配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为前提,反过来又对分配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起到保障的作用。因此,矫正的正义也是正义类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矫正正义的含义
人们的各种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或者是从分配而来,或者是从交换而来。在符合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前提下获得的财富自然是合乎正义的,个人有正当的权利拥有这些财富。但如果有人违反了分配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不正当地获取了本来不应该获取的财富,就造成了对正义的损害和侵犯。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定的途径来予以矫正。而矫正,本身也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这些符合正义要求的矫正规则和原则,就是矫正的正义,它是一种补偿性正义,事后追加性正义原则。
矫正的正义这一概念,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的“矫正的正义”这一概念中,实际上包含着我们今天所说的交换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他那里,“矫正的正义”一方面是指人与人之间经济上的交往和制定契约所遵循的原则,这一意义上的“矫正的正义”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交换的正义;但是同时,他所说的“矫正的正义”也包括民法上的损害的禁止和补偿的原则,这一意义上的“矫正的正义”,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矫正的正义。“矫正性的公正,生成在交往之中。交往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非自愿的。它不按照几何比例,而是按照算术比例。这类不公正是不均等,裁判者用惩罚和其他剥夺其得利的办法,尽量加以矫正,使其均等。均等是利得和损失,即多和少的中道,即是公正。裁判者是公正的化身,是中间人。公正就是平分,人们称裁判者为平分人,仲裁人。”(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9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里,作为“算术比例”的“公正”,相当于上一节所讲的“交换正义”;而“裁判者用惩罚和其他剥夺其利得的办法”对“不均等”所作的“矫正”,则相当于本文所讲的“矫正正义”。
然而我们对于矫正的正义的思想的回顾,可以追溯得更远。在古代,人们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种同态复仇作为正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若有伤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注:《旧约全书·出埃及记》)这里面就已经包含着“损害的禁止和补偿的原则”,也即包含着矫正的正义的思想萌芽。这种“同等报复在人类头脑中撒下了正义思想的种子”。(注:[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第95页,北京,三联书店。)在古希腊人的原始正义观中,把正义理解成一种超人世的对超越自身规定地位的事物的惩罚,以恢复那种永恒的秩序。这里也明显地蕴涵着“损害的禁止和补偿的原则”,也即蕴涵着矫正的正义的思想。可见,矫正的正义的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正义思想本身同时产生。这说明它是正义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矫正的正义的观念也由古代转向了现代。现代的矫正正义观念具有与古代的矫正正义观念明显不同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矫正内容的多样化。由于人们之间的交换行为日益频繁,并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违反交换正义的现象不但发生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涉及的内容更为多样。除了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的对他人财产和人身的侵犯之外,还包括对他人政治权利的侵犯、对他人名誉尊严的伤害、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犯等等;除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纠纷之外,还包括个人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利益纠纷。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不仅矫正的正义在社会生活中愈显重要,而且在对矫正正义的内容的规定上也要求更加丰富,更加细致,否则就不足以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的规范。
第二,矫正范围的扩大化。古代的交换关系一般只是在狭窄的地域范围内发生,而在现代,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则更加广泛,不仅达到了全国的范围,甚至还达到了全球的范围。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经济活动和信息往来层出不穷。于是,各种跨国经济纠纷日益增多,跨国犯罪、跨国诈骗、跨国贩毒、走私等案件不断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正义的违背及其矫正、补偿过程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表现为时间上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在时间——空间上的多维关系。因此,在对矫正的正义的理解和规定上,必须既考虑到时间因素,而且还要充分考虑到空间因素,规则将更加复杂。
第三,矫正行为的社会化。古代的复仇和补偿一般都是个人的行为或者家族的行为,其行为的社会影响不大。而在现代,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利益关系日益错综复杂。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因而一个事件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后果。例如,一个国家的金融风波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个国家的环境污染往往会对邻近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对违背正义行为的矫正往往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对矫正正义的理解上着眼于它的社会内涵和社会意义,而不要仅仅局限于该行为所涉及到的某个具体的个人。
第四,矫正形式的法律化。社会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由于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法律所规范的范围,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依法治国的方略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类社会中侵犯正义行为的补偿和矫正将不但不可能表现为由一种“超人世的力量”来完成,而且也不再表现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个人自发的复仇,而是表现为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纠纷,制止侵犯,获得补偿。因此,现代意义上的矫正的正义必须同时是法律的正义。
矫正正义的根据
矫正的正义,就其功能来说,主要在于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维护和保障。在正义的原始含义中,就包含着超人世的力量对侵犯者的惩罚和对秩序的恢复的含义在内。在现代意义上,矫正正义虽然不再表现为由超人世的力量来实现,但对侵犯者的惩罚和对正义关系(秩序)的恢复,仍是正义的基本内容和功能。
具体说来,矫正的正义对侵犯者的惩罚和对秩序的恢复,主要包括赔偿和惩罚两方面的内容。而赔偿与惩罚的功能就在于纠正与禁止两个方面。纠正就是通过赔偿和惩罚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秩序得以恢复;禁止是通过赔偿和惩罚使这类对正义的社会关系和秩序的侵害停止。洛克说过:“纠正和禁止是一个人可以合法地伤害另一个人、即我们称之为惩罚的唯一理由。”(注:[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第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对正义的侵害必然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使另一部分人得到不该得到的利益。对正义的恢复,就必须使这种侵害得到纠正。纠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受损害者的利益得到补偿,二是使侵害者失去他本来不应该得到的利益。矫正正义的纠正功能,就是对不正义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予以纠正,是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一种恢复。这种对不正义的纠正和对正义的恢复,可以采用两种主要的方法: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在没有第三方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商议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寻求一个相互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这种解决方法称之为协商。第二种方法是通过第三方的干预使纠纷得到解决。在这种方法中,具体又包括调解、审判和仲裁三种方式。调解虽然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更主要的是依赖于调解人的说服力,而且调解成功还需要双方的赞成。审判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其特点在于第三方的干预来自任职者具有决定案件的公职,并且这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仲裁就双方当事人必须同意仲裁人的参与而言与调解类似,从其结果是一个裁决来看,它又与审判类似,尽管第三方干预是双方已同意接受的。
对侵害的禁止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层次。直接的层次是就某一案件而言的。就是要使在这一案件中的侵害得以制止,使被侵害所破坏的正义关系和秩序得以恢复。而间接的层次,是就整个社会而言的,就是使侵害所造成的对整个社会的正义关系和秩序的破坏得以纠正、使这种被破坏的关系和秩序得以恢复。而要使这类侵害得以有效的禁止,就必须使对案件的处理具有惩戒和威慑作用。要达到此作用,就必须在纠正和补偿之外予以进一步的惩罚,即在使正义得到矫正之外,还要使“矫枉”有适当“过正”。在矫正的正义中,矫枉不过正,对于侵害者来说,只不过是回到了原先没有侵害时的状况,并没有变得更坏,所以也就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应该看到,这种惩戒和威慑对于侵害者来说并不是一种额外的强加,它也是有充足的理由的;因为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侵犯,除了是对某个个人的侵犯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正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侵犯。因此他除了需要对自己所造成的对具体个人的伤害和损失予以补偿外,还必须为自己对正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损害而付出代价。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当某人违背另一个人的意愿掠夺了他的财产,此行为超过了仅仅使后者失去那件东西所造成的痛苦,……他要受到的惩罚要超过他所造成的损失数倍多,因为他不仅伤害了某个人,而且伤害了公众的幸福,或者说他侵害了公众的安全。”(注:[美]艾德勒等编:《西方思想宝库》,第946页,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讲到通过审判的方式对正义的侵害者给予惩罚,就涉及到一个法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即刑罚的根据问题。社会为什么要对罪犯施以刑罚?施以刑罚的根据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法哲学上存在着大量不同意见的争论。美国法学家舒曼等人把历来的惩罚理论归纳为以下八种:同态复仇论,功利论,实用主义理论,报复论,符号论,超自我论,个性论,复归论。(注:见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第172—174页,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美国法学家戈尔丁主要考虑了三种惩罚理论:威慑论、报应论和改造论。(注:[美]戈尔丁:《法律哲学》,第140页,北京,三联书店。)这里我们取后一种分类。因为后一种分类更为简洁,也更有概括性。
按照报应论的说法,罪犯是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因此对社会有一种“应偿付之债”。与此相应,社会则因罪犯的恶行而有向其“回索”的权利,两者针锋相对。这种理论蕴涵有报复与复仇的含义在内。德国哲学家康德持有一种古典形式的报应论。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人们的道德行为是不考虑功利后果的,一种行为是善的,就在于它本身就是善的,而不在于它能达到其他某种善的结果。同样,一种行为应受惩罚,也在于这种行为本身就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在于恶行所带来的后果和惩罚所可能带来的结果。这意味着,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违反了法律,这种条件决定了他的违法行为或过失是应受谴责的。他说:“法院的刑罚绝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对犯罪者本人或者对公民社会。惩罚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只是由于一个人已经犯了一种罪行才加刑于他。因为一个人绝对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人的目的,也不能与物权的对象相混淆。……刑法是一种绝对命令。”(注:[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第164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这样,一个人就是应受刑罚制裁的,而且社会有责任惩罚他。
报应论是一种“向后看”的刑罚理论,与此相反,威慑论则是一种“向前看”的刑罚理论,这种刑罚理论把惩罚当作对犯罪或其他不道德行为的一种威慑。在威慑论者看来,刑罚本身并不是件好事,它是根据有可能带来的好结果(即减少犯罪)而具有正当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持有一种威慑论的观点。他认为,“刑罚并不是对过去的报复,因为已经做了的事是不可能再勾消的,它的实施是为了将来的缘故,它保证受惩罚的个人和那些看到他受惩罚的人既可以学会彻底憎恶犯罪,还至少可以大大减少他们的旧习。”(注:[美]戈尔丁:《法律哲学》,第141页,北京,三联书店。)显然,与报应论相比, 威慑论更具有经验上的可接受性,也更少学究气。然而,威慑论也有它的内在缺陷:如果仅仅为了威慑,是否可以过重处罚?例如,在“杀一儆百”的时候,是否允许为了儆“百”而不问这个“一”的罪行大小?如果说允许,那么对于这“一”来说显然是不公正的。即使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而对某一个体作出了过重的处罚也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然而如果说必须考虑“一”的罪当不当“杀”的问题,那么这种考虑的依据又何在呢?似乎依据并不在威慑论中。
与威慑论一样,改造论也是“向前看”的。但它“向前看”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并不是对犯罪者本人和其他人的威慑,而是对犯罪者本人的改造。改造论也就是复归论,即相信罪犯是可以再社会化的,再社会化是一种强制的教化过程,如通过一些强制性的生活方式促使罪犯改掉恶习;通过教育促使罪犯改变原有的一些认识;通过心理治疗促使罪犯改变心理品质;等等。改造的结果和威慑的结果相比较,前者使人不敢再犯罪,而后者则使人不愿再犯罪。这种理论与相应的做法更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也能更加彻底地控制社会犯罪的数量,然而在现实操作中要达到理想的效果也有相当的难度,而且在这种改造中,威慑的因素也是不可低估的。“不愿再犯罪”的前提往往是“不敢再犯罪”,或者说,在“不愿再犯罪”中,实际上往往包含着“不敢再犯罪”的成分在内。
上述三种关于刑罚根据的理论,都各有长处和不足。而且每种理论内部也都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存在着种种争论。我们认为,可以把这三种理论加以综合:报应论的作用在于要求我们根据犯罪的程度予以惩罚,威慑论的作用在于充分重视威慑在惩罚中的作用,改造论的作用在于要求我们力求达到改造罪犯的目的。
矫正正义的原则
矫正的正义具有丰富的内容,因此矫正正义的原则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这里仅就其主要之点进行分析。
第一,矫正途径的法定性。这一原则的含义是指:对于在分配和交换中所发生的伤害和不公,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途径、由法律规定的部门、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来进行矫正。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存在着“一剑江湖,快意恩仇”的复仇方式,存在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思维惯性。在西方社会,也同样存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这些都是个人式或家族式的矫正方式。即使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决方式,如很多人在遇到伤害或不公待遇时往往选择“私了”这种个人式的解决方式,还有人选择或被迫接受了家族复仇或家族内部调解这种形为“公了”实为“私了”的解决方式。即使是在选择了“公了”的情况下,也有很多人不是选择法律的解决方式而是选择非法律的解决方式。而有些社区和单位的领导法律意识淡薄,不用法律的手段和原则来解决纠纷,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意愿一“断”了之,结果无非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在现代法制社会,要实现矫正的正义,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来选择合适的矫正途径。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人们可以选择协商的办法,即双方在没有第三方干预的情况下寻求一个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也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调解来解决纠纷。然而,对于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或通过协调和调解无法解决的纠纷,则必须通过司法机关或由法律规定的相应机关进行判决或仲裁,否则,用个人复仇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寻求“私了”,结果不是无力讨回公道,便是造成“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恶性循环。而寻求违反法律规定的所谓“公了”,也同样不是“不了了之”,便是“胡乱了之”,缺乏应有的强制性和公正性。矫正途径的法定性,这是现代意义上的矫正的正义的基本前提。
第二,矫正程序的公正性。矫正程序的公正性,就是要求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不能对法定程序的各个环节作出任何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改变或省略。坚持矫正程序的公正性,就是要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原则、判案过程中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原则、以及程序原则,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据当前我国的现实,为了坚持矫正程序的公正性,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使有关部门在处理与矫正的正义相关的案件时,偏袒本地的一方,使案件的处理缺乏应有的公正性。二是要改变人情大于法的局面。法并不排斥情,法本身已经包含着情,只不过这种情是人类普遍的公正感情而不是私情。私情对于法律程序的干预,使处理案件时在责任的划分、罪与非罪的判定、以及量刑的轻重等方面采取特殊主义的态度,从而影响了司法和执法的公正性。三是要避免行政干预。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对分离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行政干预的出发点可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也可能是个人人情的考虑,但又不限于这两种。行政干预的存在,使司法独立的原则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也就无法保证案件处理的公正性。四是要防止法官和行政执法人员不负责任、随意处理案件。即使是在没有人情影响和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有时候法官和行政执法人员也会因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个人偏见、缺乏原则性等原因而在处理案件时马马虎虎、草率从事,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处理案件,这种情况也会使办案的公正性受到严重的破坏。总之,只有坚持矫正程序的公正性,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一视同仁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严格保证法定程序的各个环节之间的互相衔接和互相制约,矫正的正义才能得到实现。矫正程序的公正性,是矫正的正义的根本保证。
第三,矫正程度的适当性。矫正程度的适当性,是指对侵害的补偿与惩罚的程度要与其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侵害程度相适应。对于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侵犯行为的矫正,不论是补偿还是惩罚,都必须保持适度。所谓适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第一,要使受害者受到的侵害得到等值的补偿,使侵害者得到的利益予以取消。也就是说,补偿要与受害程度相一致,惩罚要与侵害程度相一致。这一条实际上是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恢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受害者的补偿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物质的经济的损失的补偿上,而应该同时考虑受害者所受到的精神上名誉上的损失。第二,要有一定的惩戒和威慑作用。如果对侵害者的惩罚仅仅保持在取消其不当得利的程度上,就对他起不到惩戒作用,对其他人也起不到威慑作用,就不足以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因此,矫正正义所包含的惩罚,应该在惩罚与侵害程度相一致的前提下,再适当加重,以起到惩戒和威慑作用。这一条,是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保障。没有这一条,就还会发生更多的对分配正义和交换正义的侵犯。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采取过重的惩罚。从他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的损害来说,对他的惩罚必须与他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的损害程度相适应,过分和不足都是不公正的;从对他人的惩戒和威慑来看,为了惩戒他人而过重地惩罚侵害者,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正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说:“处罚每一种犯罪的程度和轻重,以是否足以使罪犯觉得不值得犯罪,使他知道悔悟,并且儆戒别人不犯同样的罪行而定。”(注:[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第9—10页,北京, 商务印书馆。)如果说,矫正程序的公正性是从法律的形式上、程序上保证矫正的正义的话,那么矫正程度的适当性则是从法律的内容上、赔偿和量刑的数量上保证矫正的正义。矫正程度的适当性,这是矫正的正义的核心内容。
第四,矫正手段的文明性。在古代,由于人的尊严没有得到广泛而充分的认识和尊重,因而在对犯罪的惩罚上往往采用一些极其野蛮的手段。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一书的一开头,就用文学的笔调记述了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因谋刺国王而被惩罚的情况:“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五马分肢,最后焚尸扬灰”。接下来,他笔峰一转,又记录了“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规章,所引部分包括了起床、穿衣和整理床铺、祷告和诵读经文、劳动和学习、就餐和休息、卫生等方面的规定,细致而又周全。然后福柯指出:“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惩罚方式,期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但这是一个时代。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整个惩罚体制在重新配置。”(注:[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第7 页,北京,三联书店。)不论福柯如何理解这种转换的实质,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转换标志着文明的进步,意味着人性的复苏,它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黑格尔也曾经说过:“由于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已比较缓和了,今天刑罚早已不象百年以前那样严峻。犯罪或刑罚并没有变化,而两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野蛮的惩罚方式已彻底绝迹。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体罚和逼供、打骂和虐待,在某些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那里还是一种时常使用的手法。因此,有必要继续强调矫正手段的文明性:现代意义上的矫正正义,必须保证用文明的而不是野蛮的手段来惩罚罪犯。要尊重其人格,保障其生活,除了依法剥夺某些权利之外,必须保障和尊重其其他权利。矫正手段的文明性,这是现代矫正正义的必然要求。
这四个方面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矫正的正义的最基本的要求。它们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综合成了矫正正义的完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