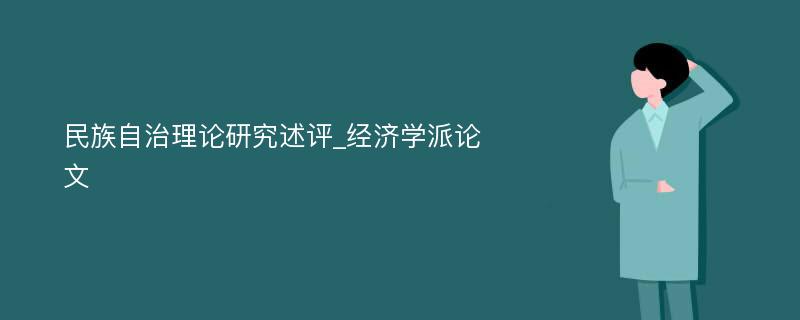
国家自主性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自主性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3
本文旨在介绍和评价英语学术界关于国家自主性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国家自主性是国家独立于社会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来行动的能力。这意味着社会力量的某一项安排并不能惟一性地决定特定的国家行动。①这个领域主要受到英语学术界中左翼思想家的关注,以国家理论为核心而展开。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视角是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其核心是用“社会中心论”的方法来解释政治和政府行为。他们认为,国家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几乎是隐而不显的,只是一个黑匣子。②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不满于多元论者和系统论者把国家视为“黑匣子”的预设,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和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各自进行了重要的奠基性工作,国家理论开始在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中复兴。③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共同讨论作为一种行动者或制度组织(institution)的国家。这些大规模的讨论标志着“国家中心论”(state-centered theory)和新国家主义(neo-statism)的兴起。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是这场理论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在英语学术界,国家自主性讨论的广度和深度要远远超过国家能力;在中文学术界,对国家能力的强调要多于对国家自主性的深入研究和探讨。④本文试图对国家自主性这一长期被国内学术界忽视的重要论题进行文献评估,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国家自主性争论的概念演进
英语学术界对国家自主性的讨论,经历了一个从承认国家具有相对的、潜在的自主性到对国家自主性讨论的渐进和深化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左翼学者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潜在自主性等概念;80年代,“国家回归学派”开始兴起,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对国家自主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90年代以来,学术界进一步把国家自主性进行细分,用不同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的公共政策议题来探讨镶嵌于自主性、孤立自主性和社会中的国家等概念。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者对美国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多元论和系统论分析范式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必须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国家的属性。普兰查斯首先提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个概念,后来米利班德、佩里·安德森、高兰·瑟本、克劳斯·奥菲等马克思主义者都沿用了这个说法。普兰查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指“国家对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特别是其针对权力集团的阶级和派别的相对自主性,并扩大到针对权力集团的同盟和支持力量的相对自主性”。国家自主性的高低取决于国家内部阶级之间、派系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情况。⑤而且,根据资本积累的进展,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后福特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都对这种形式和职能上的变化作出了解释。⑥可惜的是,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参与争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倾向于完全以一种功能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国家,要么视国家为阶级关系或阶级冲突的一个方面,关于国家潜在自主性问题的争论似乎陷入了困境。
斯考切波在分析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时候,不满足于“国家仅仅被看作是争夺基本社会经济利益而展开冲突的舞台”的流行看法。她坚持认为,国家具有“潜在的自主性”。国家不仅是一个各种利益集团角逐的竞技场,它的形式不仅是占优势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反映,国家也是一组征收税赋、使用强制手段以及在许多方面管理居民的组织的一个宏观结构,并在社会革命中居于中心地位。简言之,她将国家看作一种行政和强制组织,拥有潜在独立于社会经济利益和结构的自主性,这是斯考切波的国家理论的出发点。⑦
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埃里克·诺德林格(Eric A.Nordlinger)比斯考切波走得更远。社会中心论者一般认为,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在任何领域中无论是谁占有力量,都可以控制国家。他们把国家视为一个傀儡、一部机器或者一面镜子。诺德林格认为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国家的偏好至少与公民社会的偏好同样重要,其意义在于说明民主国家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民主国家不仅在其偏好所及的范围内是具有自主性的(autonomous),而且甚至当国家的偏好与公民社会中大多数权势群体(the most powerful groups)的需要发生分歧时,国家也会表现出显著的自主性”。⑧这标志着国家自主性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正式被提出。
1985年《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出版,标志着国家主义(statism)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最终形成。国家主义也称国家回归学派、国家中心论,其研究国家的新策略是把国家研究当成一种研究路径,或者企图建构一种新的国家理论,并努力使之成为一种范式(paradigm)。斯考克波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指“作为一种对特定领土和人民主张其控制权的组织,国家可能会确立并追求一些并非仅仅是反映社会集团、阶级或社团之需求或利益的目标”。只有国家确定能够提出这种独立目标时,才有必要把国家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行动者。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实施其官方目标的“能力”,“尤其需要考察其遭遇强势社会集团的现实或潜在的反对,或者是面临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时的情况”。⑨简单来说,国家自主性是指国家独立于社会自我决策的程度,国家能力则是指国家通过社会执行其政策的能力。前者是在政策制定层面讨论国家独立于社会的自由度,后者是在政策执行层面讨论国家通过社会实现其目的的能力。⑩
随着对国家自主性的深入讨论,其解释力的不足逐步显现出来。埃文斯(Peter Evans)发展、深化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解释。他用“镶嵌自主性”作为描述与解释国家与市场互动关系的新概念。“镶嵌”作为一个描述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概念,是由格兰诺维特于1985年首先提出的。格兰诺维特主张经济活动镶嵌于社会关系中,但是,他的“镶嵌”只表达经济活动单向地、被动地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而忽略了经济活动同样也会影响社会。(11)埃文斯把“镶嵌”这个概念运用到政治经济学里,用“镶嵌自主性”来说明并解释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欠发达国家如何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埃文斯认为,现今所有成功发展的国家,其国家机构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主张官僚制度应包含或镶嵌在无形的社会中,并与社会相结合,只有官僚自主性(bureaucratic autonomy)与社会镶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相结合,这个国家才能发展,只依靠市场的力量似乎不太可能造就这种发展。(12)
维斯和霍布森提出了国家与市场是共生相连的关系的观点。他们采用“镶嵌自主性”和“孤立自主性”(isolated autonomy)两个概念来区分强国家和弱国家。他们认为,“镶嵌自主性”国家善于协调合作,并和社会交融,易于取得在发展政策上的主导性。“孤立自主性”国家常以专断和强势的姿态凌驾于社会之上,扮演政策指导者的角色,却无法获得社会重要团体的参与和支持。因此,他们强调“把国家找回来”,但不要“把社会踢出去。”(13)
乔尔·S.米格代尔(Joel S.Migdal)对国家中心论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批评,并发展出了“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的分析路径,强调必须平衡地看待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中的作用,既要看到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他特别强调国家自主性在社会控制方面的作用。他认为,为了建构有效的公共秩序,国家在其社会管理职能的行使过程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相对自主性非常重要。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相对较低的国家自主性会直接影响国家的秩序供给能力,甚至导致整个社会转型进程的失败。(14)因此,从社会控制的角度重新评估国家自主性的理论意义,是国家自主性理论争论中一项较新的进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学者在国家自主性的讨论和辩论中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的学者针对的论辩主题和具体对象不同,因此提出的概念也就不一样。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国家自主性理论论争的全貌,笔者试图从不同的论辩主题来分析国家自主性争论的具体分歧点。
二、国家自主性理论分歧的焦点
根据国家自主性理论争论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笔者从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之争、国家回归学派的视野、国家与经济发展三个不同的主题对国家自主性问题进行讨论。
1.普兰查斯与米利班德之争
1969到1970年间,普兰查斯和米利班德在《新左派评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被学界描述为“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之争。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普兰查斯反对把国家当成资产阶级掌握的简单工具来看待。他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著作中找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个术语。普兰查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强调国家的功能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结构的制约和决定。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中扮演一种“阶级斗争压缩器”的角色。(15)国家的功能在于确保资产阶级整体的长期利益,通过“相对自主性”限制狭隘的、个别的资本家的利益。简言之,国家既不是绝对自主的,又不是没有自主性,而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普兰查斯有力地反驳了“阶级意识”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揭示出调整各种不同功能性关系的社会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也忽略了国际竞争体系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
工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米利班德认为,多元论者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一开始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与普兰查斯相反,米利班德并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国家的论断是错误的;他认为这比任何别的看法都更接近阶级社会的政治现实。(16)他认为,资产阶级由于掌握生产工具而拥有庞大的经济权力,能够利用国家作为统治社会的工具。同时,米利班德也承认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但他对相对自主性的理解不同于普兰查斯。米利班德认为,只有拥有权力的事物才是相对自主的,不讲国家权力就不能确定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家往往看到的是自己眼前的、局部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作为资本家总代表的国家则要着眼于整个阶级的全局的长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因此,国家不会简单地服从某个或某些资本家的利益,这就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17)米利班德揭开了资产阶级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合法性”面纱,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但是,他的解释最后往往归结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和动机,忽视了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
普兰查斯的美国学生马丁·卡诺伊认为,把米利班德看作是工具主义者(即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的直接工具的一种国家理论),以及把普兰查斯和米利班德的争论视为“结构主义”与“工具主义”的争论是错误的。他强调,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是一种科学方法,用以反对米利班德的经验主义,即国家以生产关系结构和生产关系固有的阶级斗争为条件,用来反对米利班德的以下观点:经济上的统治阶级都直接在国家机构中寻找其政治表达。两位学者都批评对方是决定论的象征。(18)
然而,普兰查斯和米利班德所说的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不是泛指任何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自主,而是特指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资产阶级的自主。但是,由于相对自主性理论没有超越不同研究路径(结构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分歧,没有形成一个内容比较完整、含义清晰的理论,往往被批评为“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而且,他们往往在“社会中心论”的前提假设下来讨论国家的自主性问题,即国家的政策和行动都只是反映社会团体或某一阶级的利益,而国家本身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特定的利益。在这些假设下,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去质疑国家是否真的是从本质上就是阶级或阶级斗争的体现,其职能是否真的就只是维持和扩大特定的生产方式。(19)而且,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理论过于强调“相对性”,反而无法对“自主性”本身进行更为深入和有效的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随着国家回归学派的兴起而不断深入。
2.国家回归学派视野中的国家自主性争论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欧美社会科学家特别是政治科学家纷纷开始重视国家这个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声称“把国家带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国家越来越被作为一元的整体(unitary entity)来分析,并涌现出了一批从国家的视角来分析和解释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重要著作。(20)
当代政治理论中的社会中心论者(无论是多元主义的、新多元主义的、统合主义的,还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任何领域中无论是谁掌握力量,都可以控制国家。诺德林格反对这种论点,他认为自由民主国家是具有“显著的自主性的”。他把国家自主性分为三种形式:(1)最弱的形式(Type Ⅰ),即国家官员以自己的偏好行事,而社会的偏好并不与其发生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精英或行政官僚以自主的方式行事,并与社会偏好相一致。(2)中间的形式(Type Ⅱ),即国家官员以有效的社会行动改变社会偏好,即说服社会群体中的多数与统治精英的需要保持一致。(3)最强的形式(Type Ⅲ),即国家官员以自己的偏好行事,同时统治精英的喜好与社会偏好存在明显的差异。(21)诺德林格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自主性形式,但其理论的主要缺点是未能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清晰的、操作性的区分。
诺德林格和新马克思主义都倾向于认为国家具有高自主性的一面。但是,国家回归学派并不认为国家自主性是恒定不变的。斯考克波认为,国家自主性不是任意政府体系中的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性特征,它可以获得也可能会丧失。(22)由于国家回归学派的不同研究者对国家的定义、社会结构、研究方法、推论方式以及关注焦点的不同,特别是对国家自主性的定义存在差异,导致其建构的变量关系也有非常大的差别,致使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从表面上看,国家的自主性似乎和其能力息息相关:具有强而有力的国家能力,应该就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国家自主性是指构成国家的系统是否可以不理会社会中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要求而独立地决定其行动,与国家能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国家与社会在结构上的关系。而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在执行其目标时是否有效率、有效能,国家可能没有自主性,但在追求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目的时,表现出强劲的能力。如果加上其他条件之后,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就未必如此了。比如,国家对内可能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一旦受到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的干预时,这种自主性就可能大打折扣。所以研究国家自主性,可能需要对特定的国家作周密的观察,然后才能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就不同的政策作自主性强弱的比较,也可以是跨国的比较,对于国家能力也是如此。(23)换言之,国家的自主性程度会受到国内外社会结构的限制。一个国家实际的自主性程度,取决于特定个案的不同情况。
简言之,国家回归学派文献的核心特征是把国家描述为部分独立的行动者,它与社会中的其他主要权力行动者争权。批评者认为,国家回归学派把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假设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也认为社会经济关系影响并限制国家的结构与行为,却没能仔细地描述什么是国家,而是以国家自主性的高低和强弱表示国家,并未能深入讨论国家组织内部的权力分布、对责任与义务的理解。这说明,国家回归学派确实“带回了国家”,却只是强调国家的重要性而已,并没有形成完整和明确的理论,也没有提供明确的方法论和研究指南。(24)也有评论者认为国家回归学派在“把国家找回来”的同时,“将社会踢了出去”。(25)
3.国家与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争论
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新国家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彼得·埃文斯强调国家“自主性”本身并不能完全解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完全隔离,纵然有品德操守良好的官僚体系(meritocratic bureaucracy)与绝对的自主性,也不可能达成产业发展的目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但缺乏信息来源,也没有能力与私人企业相互配合来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埃文斯认为国家的自主性太低,将不能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引进与晋升政策的官僚体系,有德有才的优秀人才无法也不愿意进入公务员队伍为国家服务,因而造成国家能力的低下,以至于无法主导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因此,埃文斯相信国家必须保持自主性,同时也要与社会(市场)保持适当程度的联系。埃文斯把这种国家与社会的适当的结合称为“镶嵌”。
埃文斯从社会与工业化发展的层面,提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4个主要角色:(1)监督人的角色,政策制定和对工业发展制定规则;(2)助产士的角色,借助补贴、资助、减税等措施,吸引私人企业进入新的领域;(3)当家人的角色,教导、培育、激励驱动力量,使企业更加积极;(4)供给者的角色,直接参与和支援私人投资的生产活动,在私营企业已经相当健全时才解除支持。(26)
维斯和霍布森认为,应该放弃冷战时“计划对市场”的说法,提出了国家与市场是共生相连的关系。他们指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说法的正确性:强国家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改革的关键。(27)在国家自主性方面,他们强调,国家精英的偏好、方案和政策,可以不受其他权力来源影响而独立产生。国家机构的行动不只是对社会需求的响应,也不只是对国际竞争的简单反应。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不是“绝对”或“相对”的自主性,而是肯定地不受其他有组织性的权力行动者所影响的自主性。当然,国家的自主性是有不同变化的,关键是在不同时期和环境下,它如何进行以及如何算是成功。(28)他们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相对自主性”的国家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对扩大市场的追求超过了对国家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因为市场占有率的扩大不一定能够增加利润。由此,他们点出了“相对自主性”概念的缺陷。
简言之,维斯和霍布森提出了“新国家主义”的三种主要解释办法。第一,必须认真对待国家;第二,无论相关与否,新国家主义的解释尝试把国际系统、国家结构和社会的可变因素结合起来,以解释国家自主性、战略和能力;第三,新国家主义从未假设国家机构的立场必须“反对”社会,这是对“自主性”的终极考验。总之,维斯和霍布森跳出了国家与社会对立的窠臼,特别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零和关系,它们可以通过合作来增强国家能力并促进工业化进程的成功。
三、国家自主性理论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共同构成了国家回归学派讨论的核心概念。在学术界,政治学者较早地关注到了“国家能力”这一理论。早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王绍光就写了一篇名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文章,来区分“国家能力”和“政权形式”的差异,指出国家能力对一个民主国家的重要性。1993年,胡鞍钢和王绍光又出版了在学术界引起巨大争论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进入新世纪,王绍光又把“濡化能力”作为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提出来。(29)此外,王绍光在其新著《祛魅与超越》中反复强调,没有一个有效的国家,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民主。正是因为看到了国家对于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重要性,他提出了国家能力与民主的分析框架,并阐述了国家能力与民主质量的关系。(30)可以说,国家能力已经得到了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特别是王绍光等人相当程度的重视。但根据笔者的阅读,在国内学术界,除了少数人(31)之外,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普兰查斯和米利班德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的理论争论,(32)对英语学术界其他学派、学者的国家自主性理论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讨论国家能力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来说固然重要,但是中国各级政府面临的国家自主性问题越来越不可忽略。事实上,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国家自主性相关的理论问题。比如,针对过去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成就,经济学者姚洋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是指政府对待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没有任何差别,它是奥尔森所说的“泛容性组织”,这种组织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重合;也就是说,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而不是增加它所代表或与之相结合的特定集团的利益。(33)
因此,本文希望引发国内学术界对国家自主性问题更多的关注,用国家自主性的理论视角来观察和解释转型中国各级政府的具体公共政策和行为,用中国不同层级、不同地方的政策经验来深化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讨论。
注释:
①[美]卡波拉索、莱文:《政治经济学理论》,刘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
②Robert Dahl,Who Govern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Nelson W.Polsby,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David Easton,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Prentice Hall,1965.另见[英]帕特里克·邓利维、布伦登·奥利里:《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欧阳景根、尹冬华、孙云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31页。
③Barrington Moore,Jr.,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Boston:Beacon Press,1966; Ralph Miliband,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1969.
④中文学术界关于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肇始于王绍光和胡鞍钢的研究。详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⑤[希腊]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王宏周、马清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85~293页。
⑥[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彼得·布拉提斯:《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李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7页。
⑦[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另见[英]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⑧Eric A.Nordlinger,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
⑨[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找回国家》,方力维、莫宜端、黄琪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0页。
⑩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11)[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载[美]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3页。
(12)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39~42.
(13)[澳]维斯、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廖志强译,黄玲校,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9~13页。
(14)[美]乔尔·S.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Joel S.Migdal,State in Society: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5)[英]帕特里克·邓利维、布伦登·奥利里:《国家理论:自由民主的政治学》,欧阳景根、尹冬华、孙云华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16)[英]拉尔夫·米利班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黄子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1~72页。
(17)[英]拉尔夫·米利班德:《英国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博铨、向东译,马清槐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
(18)[美]马丁·卡诺伊:《国家与政治理论》,杜丽燕、李少军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127页。
(19)[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2009年,第5页。
(20)主要包括:Alfred Stepan,The State and Society:Per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Ellen Kay Trimberger,Revolution from Above:Military Bureaucrats and Development in Japan,Turkey,and Peru,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Books,1978; Eric A.Nordlinger,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Stephen D.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Raw Material Investment and U.S.Foreign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Theda Skocpol,State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1)Eric A.Nordlinger,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11,19,27~38.
(22)[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2009年,第18页。
(23)高永光:《论政治学中国家研究的新趋势》,台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63,82~83页。
(24)Forrest D.Colburn,Statism,Rationality,and State Centrism,Comparative Politics,Vol.20,No.4,1988,pp.485~492.
(25)[澳]维斯、霍布森,2009年,第10页。
(26)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188.
(27)[澳]维斯、霍布森,2009年,第1页。
(28)同上,第9~13页。
(29)王绍光:《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濡化能力》,载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30)王绍光:《祛魅与超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22、154页。
(31)杨雪冬:《国家的自主性与国家能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6年第1期,第109~117页;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第64~74页;陈舟望:《政治现代化与国家自主性》,《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第27~30页。
(32)郁建兴、周俊:《马克思的国家自主性概念及其当代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第63~72页;范春燕:《“国家相对自主性”含义辨析》,《理论探索》2007年第1期,第47~49页;范春燕:《国家相对自主性理论视野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学术论坛》2009年第9期,第34~38页;范春艳:《西方左翼关于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9年9月11日。
(33)姚洋:《中性政府与中国的经济奇迹》,《二十一世纪》2008年6月号,总第107期,第15~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