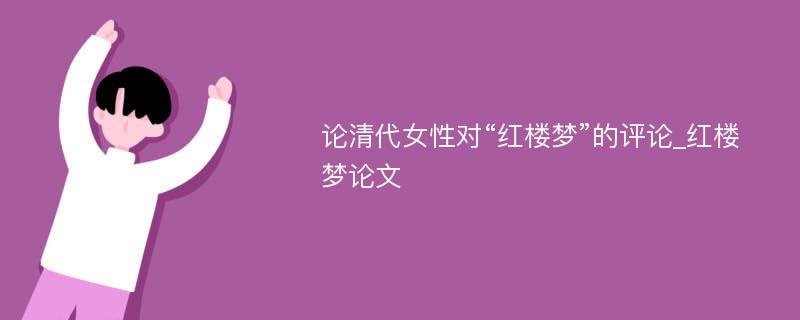
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清代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红楼梦》问世以至清末,女性一直是它积极的阅读者,清人笔记及其它文献资料中有不少女性嗜读红楼的记载,痴迷者甚至以《红楼》为性命①。不仅如此,她们还将自己的感触与观点形诸笔墨,留下了品题与评析文字。但学术界对女性红楼梦评论的研究较为冷落,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少。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中《买椟还珠可胜慨——女诗人的题红篇》一文,是当代较早全面研究清代女性《红楼梦》题咏的文章。近年则有付天先生《咏红诗略谈》②一文,下篇专论女性诗人的题红诗。台湾吴盈静女士《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一文,选取西林春与周绮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认为前者的红楼续书《红楼梦影》与后者的《红楼梦题词》“以细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③
上述研究者所论对象为女性题红诗及女性红楼梦续书,研究方法为个案式或个案比较式。本文则就笔者所见全部清代女性《红楼梦》评论资料,综合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论析的问题及其文学史价值。这些评论资料不仅包括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还包括她们为《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讨论《红楼梦》的书启等。女性创作的《红楼梦》续书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红楼梦》评论,目前仅见太清《红楼梦影》。笔者前有专文论此书,本文只就论题所及而讨论之。至于蔚为大宗的红楼梦评点,我们尚未见到清代女性参与的资料。周汝昌先生认为脂砚斋即史湘云,果真如此,则最重要的《红楼梦》评点家即为女性。不过此论只是周先生的推想,无充分证据。本文只以性别身份确定的女性评论者为研究对象。
一粟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搜罗宏富,其中收录了不少清代女性《红楼梦》评论资料,但仍有遗珠。周汝昌先生文中论及的数首诗即为一粟先生《红楼梦卷》所未收。付天先生所论题红诗资料均来自一粟先生《红楼梦卷》。吴女士所论周绮诗亦为一粟先生所收录,《红楼梦影》则是1989年为赵伯陶先生考定为太清所作。本文所论女性评红资料除前辈学者所收录与论及的以外,也有笔者在阅读清代女性作品集时所见到的。
一、女性评红活动的突出特征:家庭成员、戚友间的互动
考察一下留下评红文字的女性家庭背景与交游情况,不难发现一个突出的特征,即这些女性阅读并品评《红楼梦》大多不是个人的孤立活动,往往是母女、夫妻、兄妹或戚友之间的倡和、商讨等互动式行为。如著名诗人张问陶之女弟张问端的咏红诗题为《和次女采芝阅红楼梦偶作韵》,这是母女倡和,可惜不见女儿丁采芝的原诗,但从张问端的诗中可见母亲的和诗与一般和诗不同,尾联曰:“梦短梦长浑是梦,几人如此读《红楼》?”④估计是丁采芝嗜读红楼以至于陷溺其中,混淆了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故母亲作此诗予以警醒与劝诫。
道光中周绮《红楼梦题词》自序曰:
余偶沾微恙,寂坐小楼,竟无消遣计。适案头有雪香夫子所评《红楼梦》书,试翻数卷,不禁失笑。盖将人情世态寓于粉迹脂痕,较诸《水浒》、《西厢》尤为痛快,使雪芹有知,当亦引为同心也。然个中情事,淋漓尽致者固多,而未尽然者亦复不少。戏拟十律,再广其意,虽画蛇添足,而亦未尝以假失真。⑤
周绮是王希廉(号雪香)的侧室,她病中读丈夫所评《红楼梦》,意有未惬,于是作《红楼梦题词》申述自己的观点,有与丈夫商讨之意。王希廉是评红大家,周绮所作在女性评红文字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夫妇共同留下精彩的评红之作,这在红学史上也是一段佳话。
清末邱炜萲将其亡妻王阿玖所作的题红诗《偶阅红楼梦有咏》收录于《菽园赘谈》中,并叙其妻生平及录诗情况曰:
亡室王氏,幼入蒙塾,粗解文义。归余后,授以唐宋诗词,渐获妙悟,灯下观余作韵语,辄戏为之,平仄虽调,押韵时复出入,倘假以年,必斐然者。何期结稿二载,遽殒昙花。……兹适编辑是集,因援东坡妇以起例,略说其梗概如右,删润其旧作如左,盖不忍其终死也。(一粟,P396)
王阿玖因得丈夫指授而对诗词获“妙悟”,观丈夫“作韵语,辄戏为之”,她的题红诗极有可能是受丈夫影响而作的,且邱炜萲对她的旧作有所删润,题红诗或可视为夫妇合作的产物。
嘉庆中陈诗雯与道光中范淑的评红之作则均与阿兄有关。陈诗雯为其兄陈少海所著《红楼复梦》校对并作序。范淑为其兄范元亨(字直侯)所作《红楼梦评批》题了一首七言歌行。周汝昌先生并推测兄妹对《红楼梦》的题咏应不只此。元亨所作《白秋海棠》七律,全用小说中原韵;所作《空山梦》传奇从《红楼梦》十二曲的体例而来。范淑曾与兄弟姊妹结菊花社,也是受《红楼梦》影响的一种痕迹。⑥可惜范淑评红诗只存此一首。
女诗人沈善宝自妙龄以至老年,均与《红楼梦》有不解之缘。笔者发现她的诗集中有四首与《红楼梦》有关的诗,均未被前辈学者注意。她的《鸿雪楼诗选初集》中有三首诗与《红楼梦》有关。其一为卷一《题葬花图》:
自怜清瘦不禁春,强起携锄病后身。燕子不来红满地,葬花人是散花人。⑦
此诗做于道光丙戌(道光六年,1826),作者时年19。观诗意,图中葬花者应为黛玉。自然,当时亦有仿效前代文人或黛玉而葬花者,但若为他人,诗题中应有其人名号;若为作者自己,则诗题中亦应点明“自题”,故笔者以为从诗题与诗意看,此诗应为咏黛玉葬花之作。卷五又有一首《题葬花图》可与卷二的同题作品合观:
千红万紫满园林,转瞬飘零感不禁。收拾残香归净
土,惜花心较葬花深。⑧(P14)
此诗作于道光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作者时年30。二诗合观不难看出均是写黛玉葬花的场景,且能隐括原著内容,对黛玉形象与心绪及环境气氛的理解与把握是颇为准确的。故此二首诗是与《红楼梦》有关的题画诗。
沈善宝还有一首诗也写到黛玉葬花。《鸿雪楼诗草》卷十《观杂剧取其对偶者各成一绝》是一组组诗,作者选取了十二对可成对仗的杂剧齣名,写了24首诗。其中第九首即为《葬花》:
何处红楼问大观,名花原当美人看。埋香不接眠香梦,辜负春风芍药阑。⑨
此诗与前二首题葬花图不同,前二首重在写黛玉葬花的场景,此诗则纯从观剧的角度写。“名花原当美人看”为诗眼,第三、四句则从听曲的角度,写黛玉葬花一齣后,应接演湘云醉眠芍药裀一齣。此诗作于甲辰(道光二十四年,1844),作者37岁,虽无前二首体会黛玉境遇的深心,内容空泛,但“红楼”、“大观”等语明确点出此乃据《红楼梦》而写的戏曲。此组诗所咏其它齣名如“叫画”、“拷红”等为《牡丹亭》、《西厢记》等剧中著名齣目,可见“葬花”在当时已跻身于这些著名剧目中。
《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二的《读红楼梦戏作》⑩则是一首直接评论作品的题红诗,此诗作于戊子(道光8年,1828),作者时年21。从这首诗及上引诸作可知湘佩青年时代即接触红楼,且发之于吟咏。到了晚年,她与《红楼梦》的缘分又更深一层。她的女友太清撰写《红楼梦影》,她不但为之作序,更有促成之功。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沈善宝即为《红楼梦影》作序,其时作品尚未完成。太清《天游阁诗集》卷七《哭湘佩三妹》(其二)云:
红楼幻境原无据,偶耳拈毫续几回。长序一编承过誉,花笺频寄索书来。
诗后太清自注曰:“余偶续《红楼梦》数回,名曰《红楼梦影》,湘佩为之序。不待脱稿即索看,尝责余性懒,戏谓曰:‘姊年近七十,如不速成此书,恐不能成其功矣。’”(11)《红楼梦影》直至光绪三年(1877)太清去世那年才付梓。若无湘佩督促,太清缺乏写作的外部动力,恐怕我们今天就见不到24回《红楼梦影》全帙了。
太清与红楼有关的诗今只见上引《哭湘佩三妹》(其二),末句提到湘佩“花笺频寄索书来”,她与沈湘佩的往来书信中应有评红文字,惜乎不存。否则,两位才情出众的女诗人往复论红的文字当为女性评红史增色不少。
太清晚年始续《红楼》,早岁是否读过红楼,无资料佐证。但她的丈夫奕绘青年时代即读过《红楼梦》。奕绘《观古斋妙莲集》卷二《戏题曹雪芹石头记》(12):
梦里因缘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楼春。形容般若无明漏,示现毘卢有色身。离恨可怜承露草,遗才谁识补天人。九重斡运何年阙?拟向娲皇一问津。
此诗作于嘉庆己卯(1819),太清时年21岁。此诗颇得雪芹用心,“离恨”、“补天”,正《红楼梦》两大关键。
同治年间刊刻的西园主人《红楼梦本事诗》后附刻了王素琴、谢桐仙、莫惟贤、姜云裳、王猗琴、胡寿萱六位女性的《红楼梦题词》诗二十二首及胡寿萱《论红楼梦小启》一篇。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曰:
考解盦居士《石头丛话》,有祥符家西园大令林元配王友兰夫人猗琴、继配莫惟贤夫人孟徽等语,知主人与居士同姓,名林,祥符人,官知县,而王、莫二女史皆其妻也。(13)
由此可知,六位女子中,王猗琴与莫惟贤为西园主人的原配与续弦。王素琴为王猗琴之妹。王素琴诗题为《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则此诗之作因读其姊题红诗而引发。谢桐仙诗题为《读红楼梦传奇漫成七绝六首并柬呈猗琴姊妹、霞裳、寿萱两女史》,姜云裳的诗题更长:《偶读红楼梦传奇并孟徽叔芳仲嘉季英四小姑题词率成四绝以博一笑》。从这两个诗题中可知这六位女士的关系:谢桐仙与王氏姊妹及胡寿萱是相识的女友,莫惟贤与姜云裳则为姑嫂。她们的题红诗是戚友之间的倡和。从姜云裳诗题中还可知莫惟贤的三个妹妹叔芳、仲嘉与季英也有题红诗。这样,这个女性戚友评红团体中至少九人有作品,在当时亦算盛事。
上述清代女性评红的互动特征,不仅是清代中后期女性文学活动昌盛的表现,更显示出女性文学批评自觉意识的进一步加强。
女性评红的互动特征,也显示出《红楼梦》巨大的艺术魅力。它的情感力量使得女性读后渴望与人交流阅读感受,欲一吐为快。它丰富的内涵则为互动提供了说不尽的话题。《红楼梦》对女性感情世界的细腻描写与对家庭生活场景的生动展现,也更贴近女性读者的生活,易为她们所接受。
二、女性评红关注的焦点:人物命运
《红楼梦》最吸引读者的是书中人物特别是那些女子的命运,而众多女性人物中,女性评论者最为关注的是黛玉的命运。黛玉的孤苦身世,她与宝玉的悲剧情缘,她多愁善感的气质和出众的诗才,都使得不少本身即为女诗人的评论者对她的处境与心境有更深入的体会与理解。
现存最早的女性题红诗是宋鸣琼在乾隆时期所作的《题红楼梦四绝句》,其中第二首是咏黛玉的:
病躯那惜泪如珠,镇日颦眉付感吁。千载香魂随劫去,更无人觅葬花锄。(一粟,P427)
黛玉病弱、忧郁,长年以泪洗面,宋鸣琼抓住这一形象特点,又以葬花这一典型的细节入诗,充分表现了对黛玉的悼惜。
嘉道年间孙荪意的词《题红楼梦传奇(贺新郎、凉)》将这种悼惜之情铺叙得更充分:
情到深于此。竟甘心,为他肠断,为他身死。梦醒红楼人不见,帘影摇风惊起。漫赢得新愁如水。为有前身因果在,拌今生滴尽相思泪。凭唤取,颦儿字。潇湘馆外春余几。衬苔痕,残英一片,断红零紫。飘泊东风怜薄命,多少惜花心事。携鸦嘴为花深瘗。归去瑶台尘境杳,又争知此恨能消未。怕依旧,锁蛾翠。(14)
孙作开篇即写黛玉甘为情死,意思比宋作更为显豁。次将黛玉还泪债及葬花事入诗。“飘泊东风怜薄命”句化用了黛玉柳絮词中的句子:“飘泊亦如人命薄。”(15)
吴藻《读红楼梦(乳燕飞)》与孙作词牌相同:
欲补天何用?尽销魂,红楼深处,翠围香拥。騃女痴儿愁不醒,日日苦将情种。问谁个是真情种。顽石有灵仙有恨,只蚕丝烛泪三生共。勾却了,太虚梦。喁喁语向苍苔空。似依依,玉钗头上,桐花小凤。黄土茜纱成语谶,消得美人心痛。何处吊埋香故冢?花落花开人不见,哭春风有泪和花恸。花不语,泪如涌。(一粟,P460)
吴作下阕写到宝玉为晴雯所作诔文的改句“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16),成了宝黛结局的谶语,埋香故冢提到黛玉葬花,“花落花开”等句亦是化用了黛玉《葬花词》。吴作是从宝玉的角度来写,下阕主要写的就是对黛玉夭逝的悼惜之情。
周绮《题红楼梦十首》第一首即为《黛玉焚诗》:
不辨啼痕与墨痕,无情火断有情根。者宵果应灯花谶,他日空怜蜀鸟魂。慧业已随人遁世,痴鬟休为竹开门。鸭炉兽炭寒如水,剩得心头一缕温。(一粟,P494)
黛玉焚诗是高鹗续书中的情节,虽然高续一直为人所诟病,但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悲剧力量却一直震撼着读者。此诗即是一个例证。周作首联“不辨啼痕与墨痕,无情火断有情根”,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以为“不得谓非名句也”(17)。
汪淑娟《题石头记(沁园春)》亦写黛玉:
何处红楼,几日西风,娇颜悴零。悔轻轻罗帕,打伊呆雁;些些诗句,教熟鹦鹉。不及芙蓉女儿坟上,犹受怡红一哭情。堪伤处,是绛珠有泪,顽石无灵。秋窗风雨凄清,问絮果兰因是怎生。算潇湘一梦,了完公案;袈裟半袭,救了神瑛。只怪桃花和它柳絮,恁把凭空谶作成。痴儿女,被聪明两字,断送伊行。(一粟,P507)
汪作词句不甚雅驯,显然作者的词学造诣不高。上阕写到黛玉以手帕打宝玉头(第二十八回)及鹦鹉听熟黛玉念诗的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汪作认为黛玉一往情深,尚不及晴雯能得宝玉一哭,感慨“绛珠有泪,顽石无灵”,对宝玉深致不满。下阕提到第四十五回黛玉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本事。“只怪桃花和它柳絮”句指黛玉曾做《桃花行》和《柳絮词》,成了她自身命运的谶语。
扈斯哈里氏的《观红楼梦有感》五首,其中第三、四慨叹黛玉命运:
其三:
青埂峰前一石头,携来偏自落红楼。绛珠有草随缘化,离恨天中不了愁。(一粟,P508)
其四:
幻境虚成一段缘,红楼奇事千古传。半生洒点相思泪,不免魂归离恨天。(一粟,P508)
第四首直接用了高鹗续作第九十八回回目中“魂归离恨天”的措辞,也正可见高续黛玉之死的情节在读者中的影响。王猗琴《读红楼梦传奇口占》四首七绝,后两首悲黛玉身世:
其三:
潇湘孤馆莫相依,竹泪当年染帝妃。鹃婢外家亲付与,声声叫道不如归。(一粟,P522)
其四:
葬花即是葬颦卿,神祭芙蓉句改明。谶语新诗随意写,桃花柳絮两同情。(一粟,P523)
王素琴《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亦是七绝四首,前二首亦悲黛玉:
其一:
美人自古称林下,十二金钗第一人。最苦伶仃携小婢,外家竟作雁来宾。(一粟,P523)
其二:
杜鹃湘馆一知心,镇日熏香侍绣衾。叫道不如归去好,胜他鹦鹉解诗吟。(一粟,P523)
王氏姊妹的看法大体相近。两姊妹都怜惜黛玉少失怙恃,寄人篱下;都认为紫鹃之名寓意“不如归去”。姊姊认为“葬花即是葬颦卿,神祭芙蓉句改明”,颇得作者本意,她亦注意到黛玉《桃花行》和《柳絮词》成为其命运的谶语。妹妹以黛玉为十二钗之首,则明示尊林之意。但她对续书中玉、钗婚后宝玉出走、宝钗独守空闺也颇同情,《偶成》其三曰:
神瑛底事没归期,辜负姻缘金玉词。解得辽西惊妾梦,明明黄姓有莺儿。(一粟,P523)
姜云裳则显然属扬林抑薛派,钗黛纠葛在她看来是宝钗蓄意“夺婿”、“谋婚”,她的咏红四绝第二首曰:
册定三生薄命司,笑他夺婿暗争持。绛珠一死神瑛去,雪冷空闺悔已迟。(一粟,P524)
讽刺宝钗费尽心机夺婿,只落得个独守空闺的下场。第四首更认为宝钗的谋婚之意,作者早已安排下伏笔:
合欢酒本为颦卿,偏是蘅芜把盏倾。咏菊当年知伏线,谋婚雪意早分明。(一粟,P524)
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讽和螃蟹咏”中写到众人做菊花诗,构思时,黛玉因想喝热酒,宝玉令人烫来一壶合欢花浸的酒,黛玉吃了一口便放下,宝钗不请自来,自己拿杯来,也喝了一口(P521)。姜云裳认为这个细节为以后谋婚伏下了线索。此处姜云裳的思路受高续影响,恐并不合雪芹本意。但姜云裳对宝钗的厌恶则表露无遗。
胡寿萱《读石头记偶占》七绝三首,后二首亦悲黛玉遭遇:
其二曰:
黛钗国色两倾城,瑜亮原来又并生。读到潇湘焚稿日,负心转自恨神瑛。(一粟,P523)
其三:
一窗风雨独悲秋,公子知心为解愁。何事瞒婚来设计,高堂偏听凤丫头。(一粟,P523)
她虽然为黛玉的悲剧命运而慨叹,但并无贬抑宝钗之意。她认为黛钗均为倾城国色,如周瑜与诸葛亮并生,黛玉的婚姻悲剧是凤姐使调包计造成的。这与姜云裳尊林贬薛的观点不同,属钗黛双美派。
清末徐畹兰的《偶书石头记后》七首全为黛玉而作:
其一:
情天同是谪仙人,两小无猜镇日亲。记否碧纱厨里事,戏呼卿字作颦颦。
其二:
又送春归感岁华,阿侬生小恨无家。伤心一样同飘泊,凄绝东风葬落花。
其三:
菊花香里快飞觞,斗韵分笺粉黛场。试问清才谁冠首,当时独让病潇湘。
其四:
凉月模糊香不温,懒调鹦鹉掩重门。窗前悔种千竿竹,赢得斑斑渍泪痕。
其五:
药炉茶鼎篆烟浮,风雨幽窗一味秋。知否多情天亦妒,罚卿消瘦罚卿愁。
其六:
儿家因果自家知,作茧春蚕自缚丝。了尽相思还尽泪,三生误煞是情痴。
其七:
梨花落尽不成春,梦里重来恐未真。漫道玉郎真薄倖,空门遁迹为何人。(一粟,P550)
徐作七首全属黛玉,正可见其对黛玉命运的关注。周汝昌先生认为徐作结篇结句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了向空门求取一种慰藉,其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反对只论形迹现象的表面看法。就程本续书的结局来说,这首诗是一佳作”(《新证》,P1110)。作者在第七首诗结句中以反问句式点出宝玉遁迹空门正为黛玉,反对以宝玉为薄倖之人的看法。徐作选取作品中最具典型性的七个情节与细节,以组诗的形式写出了黛玉的生平,如同黛玉的诗化小传。诗中倾注了对黛玉的悼惜之情,也道出了自己对宝黛爱情悲剧的看法。在女性的题红诗中,这种以组诗咏一人的写法亦别具一格。
如上所述,女性评红者在红楼人物中最为关注的是黛玉,这显示了她们对人物的感情取向,其中有象姜云裳这样明确的尊林抑薛者。虽然也有如胡寿萱这样持钗黛双美说者,但笔者尚未发现有尊薛抑林者。这与男性论者的情况不同。男性论者尊薛派与尊林派常势同水火,一个常被征引的例子出自邹弢《三借庐笔谈》,书中记许伯谦尊薛而抑林,而邹弢本人则反之,是尊林抑薛派,“至愿为潇湘馆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一粟,P388)。二人某次论红楼,“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一粟,P390)。女性论者中未发现与许伯谦同一立场者,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黛玉的命运是女性评论者关注的焦点,作为黛玉影子的晴雯也受到她们的怜惜,如周绮《题红楼梦十首》第四首《晴雯死领芙蓉》:
一现优昙命太轻,临题那得不怜卿。便填痴诔难偿恨,真做花神始称名。素愿何尝形色笑,平生端的误聪明。从来此事销魂最,已断尘缘未断情。(一粟,P495)
周作对晴雯抱屈夭逝深致感慨,与之异曲同工的有王阿玖的《偶阅红楼梦有咏》第三首:
一刹人间事渺茫,前生幻境认仙乡。如何尽领芙蓉号,不断情缘反断肠。(一粟,P396)
紫鹃虽与黛玉为主仆,但情同姊妹,上引王氏姊妹诗中已提到她,周绮的《题红楼梦十首》第六首《冰寒雪冷慧婢恨怡红》则特以她为题而作,对她的重情义赞赏有加:
妒花风雨瘁花姿,义愤偏钟小侍儿。果易分明仍一梦,信难凭准是相思。怡红意气能无恨,湘馆情怀为甚痴?几许伤心何处诉,自教呆立不多时。(一粟P495)
其它受女性评红者注意的人物还有湘云、李纨、妙玉、香菱、鸳鸯、平儿、袭人、尤氏姊妹等。周绮的题红十首各分咏一人,所咏人物最多。除上述黛玉、晴雯、紫鹃外,另有《香菱学咏》、《湘云醉眠芍药》、《青女素娥李纨悲黛玉》、《二姐遭赚堕计》、《平儿被打含情》、《妙玉听琴警悟》、《鸳鸯殉主全贞》,从诗题即可知所咏本事及作者态度。香菱身世悲惨,令人同情,第四十八回“慕雅女雅集苦吟诗”写香菱学诗,其慧心与诗才令人怜惜,周作《香菱学咏》本事出此。王素琴《偶成》四绝第四首亦咏香菱:
小妾甄家旧日莲,好花真个是应怜。须知被拐香零落,人抱衾稠雪一天。(18)
诗写得不高明,但注意到“英莲”与“应怜”谐音,“雪”与“薛”谐音。
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是《红楼梦》中的著名场景,最能表现湘云的娇憨、洒脱,向为读者与红楼画家所欣赏。周绮《湘云醉眠芍药》尾联曰:“一种痴憨又娇怯,画工要画费平章。”正是此意。沈善宝则有所不同,她将湘云与黛玉作对比,其《读红楼梦戏作》颔联曰:“争羡春风眠芍药,谁怜秋雨病潇湘!”她的感情天平倾向于黛玉。
周绮《妙玉听琴警悟》,本事出自续书,姜云裳题红四绝第三首亦注意到这一情节:
多少名花百美香,弹琴独记一潇湘。大观尘世知音少,槛外人来辨羽商。(一粟,P495)
此诗如姜云裳的其它诗作,表达了对黛玉的偏爱。后二句以妙玉为黛玉知音,这恐怕并不合乎雪芹本意。不过,就程本续书的情节来看,此诗能与作品本事扣合。
周汝昌先生对他所列举的女诗人评红“集中在感叹情缘、悼惜黛玉、自伤身世这一面”评价不高,并认为“显然是受了程本的局限”(《新证》,P1110)。上引诸作除周先生文中列举的外,还有周先生未论及的,但“自伤身世”的成分均不易看出。女作者们虽然受了程本局限,对原作者构思的推测不一定符合其本意,但对人物形象特别是对黛玉形象的把握是准确的。上引那些饱含感情的题诗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物评论。人物评论作为小说评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
三、女性评红的深入:对作品写作手法、主旨与价值等的论析
虽然女性评红者十分关注书中人物命运,用了大量笔墨题咏人物本事,但她们的目光也并不仅限于此。不少女性评红者都注意到《红楼梦》中人名的谐音双关,论到了作品的写作手法。前述王氏姊妹以紫鹃寓意“不如归去”,王素琴并注意到“英莲”即“应怜”即是。此外,谢桐仙题红六绝第三首前二句曰:“情文自古两相生,二字晴雯特唤名。”(一粟,P524)以“晴雯”为“情文”;第四首前二句曰:“分明儿女情话真,弟是情钟姊可亲。”(一粟,P524)以“秦钟”为“情钟”,“可卿”为“可亲”。第五首咏袭人曰:“谗从暗里袭无形,人是花言最易听。谁料此身同腐草,珍珠一粒付优伶。”(一粟,P524)将袭人之名与其作为相连。莫惟贤《读红楼梦传奇偶感》曰:
红楼一部特言情,情有可亲唤可卿。尤物从来为祸水,名花毕竟要倾城。湘江洒泪妃原死,杜宇思归婢借名。寄语聪明娇女子,莫将幻境认三生。(一粟P524)
莫氏与谢桐仙同以“秦”为“情”,“可卿”为“可亲”。“尤物”句应是从尤氏姊妹姓上而来,但观诗意似是泛指,并非特指。黛玉号“潇湘妃子”,即以其出典与黛玉的命运相连。“杜宇思归婢借名”与王氏姊妹以紫鹃寓意“不如归去”意同。
谢桐仙与莫惟贤均指出“秦”谐音“情”,谢诗首句“情文自古两相生”与莫诗首句“红楼一部特言情”,均触及《红楼梦》一书的主旨与性质,但二人均未对此更作发挥,下文只是着眼于具体姓名的谐音双关。莫氏身为女子,却认同红颜祸水之说,如周汝昌先生所言,“以女道学的见解和口吻来教训女流”(《新证》,P1108),令人遗憾。
但亦有女性评红者由谐音双关进而探讨作品性质,如王猗琴咏红诗第一首:
贾字当头莫认真,尘缘梦境两无因。分明一管生花笔,幻出群芳卅六人。(一粟,P522)
胡寿萱咏红诗第一首:
宝玉分明有两人,如何言贾不言甄?只因幻境非真境,荣府通灵故细陈。(一粟,P523)
王、胡两位女士由“甄贾”与“真假”的谐音论到作品的“真假”观念与作品的虚构性质,颇有见地。扈斯哈里氏也谈到了真假,她的咏红诗第一首曰:
真假何须辨论详,斯言渺渺又茫茫。繁华好是云频幻,富贵无非梦一场。仙草多情成怨女,石头有幸作才郎。红楼未卜今何处,荒址寒烟怅夕阳。(一粟,P508)
第五首曰:
是是非非地,空空色色天,红楼如一梦,警世悟禅缘。(一粟,P508)
她认为真假无须细论,并进而指出繁华如过眼云烟,富贵如梦一场。她认为《红楼梦》有警世之意,能让人悟到禅理。她以“是是非非地,空空色色天”点出这禅理即是佛教空观。周汝昌先生认为她的看法“带有空幻虚无思想色彩”(《新证》,P1109),不过,她的这种认识较之上述王、胡二人是更为深刻的。
胡寿萱不仅以诗论红,还留下了一封论红楼梦小启(19),以较长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她对《红楼梦》一书主旨的看法,值得特别注意。她认为作者身份是侯门幕宾,作者写书缘起是因为目睹“富贵浮云,邯郸一梦”,“不特云散风流,盛衰兴感,而且世态炎凉,门稀车马”,“故作书以梦命名”。(一粟,P197)她认为作者开篇“即以神瑛侍者灌溉仙草、绛珠今生还泪发端,明明示人以趋炎附势者流,不念故侯,尚不如草木之有情,犹思图报也”。当时不少读者以为《红楼梦》乃“情史”,胡寿萱认为这是误读。她指出作者“恐阅书者不知其无情,误以为情史,则将秦钟之死,可卿之亡,卷中先后叙明,大书特书,一情不留,使读《红楼》者瞭如指掌”。她指出“一百二十卷中尽皆纨绔成风,饮食论交,中山狼、王仁、邢大舅辈笔不绝书,所谓豫让国士之风缺焉不讲,酬恩知己、以死相报者独得于姽婳将军之一女流”,作者于此“有微词”、“有隐痛”。(一粟,P197)
对其它有关《红楼梦》作者命意的观点,作者逐一进行了反驳。有论者从作品写到王熙凤首恶,花袭人改名,推测此为作者命意之所在。胡寿萱认为“此皆作者推源其致祸之由,实叙其事,非雪芹命意之所在也”。又有论者以为“尤家姊妹相与俱来,一则吞金,一则饮剑,作者盖警世人晏安酰毒,毕集愆尤,以身相殉,悔莫能及”。(一粟,P197)还有论者认为薛氏之由盛而衰,“作者三叹息也”(一粟,P198),“所以此书以王夫人始,以薛宝钗终,贾府赫奕门庭,其旺者王也,其灭者雪也,而其中尤物之来,尤悔之丛,皆安乐所由亡也。尤、王、薛三姓皆作者点睛之笔,大旨不离乎是”。作者认为这些观点“皆非余之所知也”。信尾,她以七绝一首总结自己的看法:
绛珠还泪日消魂,草木犹思灌溉恩。愧煞趋炎多热客,秋风冷落故侯门。(一粟,P198)
她在小启的开头说自己读《红楼梦》的心得“未识有当于作者之本旨否”,这是自谦之辞。从她文中论述时斩钉截铁的措辞看,她对自己的观点颇为自信。《红楼梦》的主旨至今仍是言人人殊,她的看法亦可备一说。不过她将作者主旨归为感慨趋炎附势、忘恩负义者尚不如草木,未免将一部复杂作品的内涵简单化了。且以书中所谓“一情不留”的情节安排显示作者写的是现实的无情,以此证明自己的观点,也有些牵强。其实,她对《红楼梦》命意的看法与她反驳的那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将作者命意归结为道德讽劝,而在论证时也都注意到作品中姓名的谐音双关,论证方法也都是以局部细节来推测作者的总体命意。
不过,专文探讨《红楼梦》本旨,正面提出并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对时人的看法进行反驳,这在清代女性评红的文字中仍有突出意义,显示了女性文学评论的自觉意识。吴克岐认为她的评论“小中见大,警醒痴顽不少”(20)。(《忏玉楼丛书提要》P233)虽然只是从评论角度与道德功能上着眼,但也可见其对胡文的欣赏。
另外一篇重要的评红作品是女诗人范淑的《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这首诗为周汝昌先生所激赏,诗云:
独立苍茫愁里住,古今一个情回护;别抒悲愤入稗官,先生热泪无倾处。潇湘水上发蘅芜,香草情怀屈大夫;天名离恨无由补,泪洒苍梧竹欲枯。繁华馨艳传千载,买椟还珠可胜慨!作者当年具苦心,哪知竟有知音在。天机云锦妙无痕,指月拈花与细论,情里夺来南董笔,梦中吟醒石头魂。说部可怜谁敢伍,庄、骚、左、史同千古!纷纷说梦几痴人,请君一听鲸鱼声。(21)
这是范淑为其兄范元亨(字直侯)所作《红楼梦评批》所题的诗。周汝昌先生认为这首诗“用笔可以说是双管齐下,既是说范元亨,也在说曹雪芹,—‘别抒悲愤入稗官,先生热泪无倾处’,正是如此。她慨叹那些读《红楼梦》而只知着眼于繁华香艳的,完全是买椟还珠,倒置了本末。这种见地,也和孙荪意、吴藻、金逸等江浙女士专门悲悼黛玉身世遭际的并不全同,值得我们十分重视”(《新证》P1113-1114)。
周先生特别重视这首诗是有道理的。她的评论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在她看来,《红楼梦》是有所寄托的,继承了屈原作品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蕴含着作者的一腔悲愤。范淑独具只眼,“香草情怀屈大夫”句指出了作者与屈原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她点出“天无由补”,“泪洒苍梧”,这正是红楼梦的大关节。女性评红者中,范淑可谓曹公的知音,她抓住了作品的精神实质。
(2)她认为说部中没有一部可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在她的价值天平上,《红楼梦》是与庄、骚、左、史那样的子、史经典一样千古不朽的伟大著作。一些男性评论者也将《红楼梦》与经典相比附,如同治年间丁嘉琳在《红楼梦本事诗》序中曰:
《红楼梦》一书为小说之祖,久已不胫而走,家置一篇。然细绎其文,皆可通乎经义,毋得以家常琐事忽之乎!《易》言吉凶消长之道,《书》言福善祸淫之理,《诗》以辨邪正,《礼》以别等威,《春秋》寓褒贬,经天纬地,亘绝古今。而不谓《石头记》一编竟能包举而无遗也。贾氏之盛衰,互为消长;众人之寿夭,悉本善淫。其中或叙淫荒,或谈节烈,明邪正也;或言宫禁,或及细民,判等威也。至全书叙事,或明或暗,或曲或直,无非寓褒贬之意。(22)
他认为《红楼梦》通乎经义,儒家的五经各有其内容与作用,而《红楼梦》能包举无遗,这种比附未免牵强,虽是想借经典抬高《红楼梦》的地位,却是对《红楼梦》的曲解。而范淑是在准确把握《红楼梦》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将它与庄、骚、左、史并列,对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做了恰当定位。这在红学研究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陈诗雯和沈善宝所作的两篇红楼梦续书的序,前者早于范淑之作,后者则晚于范诗。其中均涉及到红楼梦的主旨和自己的看法。陈诗雯《红楼复梦》序中曰:
封姨漫妒,名花本自天来;月老留心,绝世宁真命薄?问天不语,伤心代人诉衷肠;补天何难,有情的都成眷属。灵根未断,前生种向蓝田;智月常圆,隔世重修玉斧。人间儿女,无劳乞巧天孙;意外姻缘,一任氤氲大使。笔妙总归心妙,人工可夺天工。(23)
她此处谈《红楼复梦》的写作宗旨,是要改写原书人物的命运,让薄命的绝世佳人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虽因为阿兄作序,满纸谀词,但她对阿兄续书的大团圆安排是无异议的,由此也可知她对《红楼梦》精神实质的认识去雪芹本意甚远。
沈善宝的《红楼梦影》序中曰:
《红楼梦》一书,本名《石头记》,所记绛珠仙草受神瑛侍者灌溉之恩,修成女身,立愿托生人世,以泪偿之。此极奇幻之事,而至理深情,独有千古。作者不惜镂肝刻肾,读者得以娱目赏心,几至家弦户诵,雅俗共赏。咸知绛珠有偿泪之愿,无终身之约,泪尽归仙,再难留恋人间;神瑛无木石之缘,有金石之订,理当涉世,以了应为之事。此《红楼梦》始终之大旨也。(24)
她所见的版本是通行的程本,对作品大旨的概括就程本来说是准确的。她对一些续书作者为黛玉翻案,“将红尘之富贵加碧落之仙姝”的处理深为不满。“至理深情,独有千古”显示出她对作品的推崇。对比一下早年她的《读红楼梦戏作》,可以看出她的看法是变化的:
无端炼石笑娲皇,引得痴人入梦乡。争羡春风眠芍药,谁怜秋雨病潇湘!缠绵独抱情千古,寂寞难消泪数行。不信红颜都薄命,惯留窠臼旧文章。
她21岁所作的这首诗的尾联颇引人注意,她对《红楼梦》中“红颜薄命”的安排表示质疑,斥之为“惯留窠臼旧文章”,显出年轻人的锐气。太清称她“平生心性多豪侠,辜负雄才是女身”(《哭湘佩三妹》其一),这首诗的尾联也正是她个性气质的流露。她晚年为女友的书作序,持论较为平和,不像青年时代那么锋芒毕露了。
四、结语:女性评红作品的文学史价值
清代女性评红作品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清代以前,女性文学批评著作甚少,宋代李清照《论词》是中国第一篇女性文学评论专文,易安在文中提出了自己对词的见解与主张,大胆地对晏殊、欧阳修、苏轼等词坛名宿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清康熙年间《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则代表了古代女性戏曲评论的最高水平,它虽然遭到一些道学家的攻击,但其价值与贡献也得到了男性评论者的承认(25)。
从数量上看,清代中后期女性在传统诗文批评方面的成果远远超过前代,著名者如女诗人汪端曾编《明三十家诗选》,撰《颐道堂诗说》,其诗集中有多首题前人诗集之作,并有很多品题女诗人及其作品的论诗诗。(26)熊涟著有《澹仙诗话》,“书中多叙当时名人之诗”(27)。其时搜集、整理与评论女性诗歌创作的风气甚炽,一些女性编撰有闺秀诗集与诗话,如恽珠编辑了《国朝闺秀正始集》,沈善宝撰有《名媛诗话》等(28)。这些著作在当时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此期女性亦继续关注和参与对《牡丹亭》等戏曲作品的评论与笺注。而女性评红作品则显示此期女性文学批评成果超出了传统的诗文范围,亦不仅限于戏曲,而是大规模地扩展到了小说领域,在女性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女性评红作品不仅在人物评论方面成果甚丰,还涉及到《红楼梦》的写作手法,如谐音双关、伏笔等,有的更进一步论到作者的身份与命意、作品的性质和主旨及作品的地位与价值等诸多问题,其中不乏有见地的观点。这在红学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注释
①如乐钧《耳食录》二编卷八《痴女子》篇中记载一痴女子读《红楼梦》有感于心以至于死。见《耳食录》P285,济南:齐鲁书社,1991。一粟《古典文学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收录此篇。本文所用版本为中华书局2004年新印本,新改名为《红楼梦资料汇编》,以下仍简称此书为《红楼梦卷》。
②见《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四辑。
③见“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④见一粟《红楼梦卷》P457-458。以下引文出自本书的,在正文中引文后注明:一粟,P××。不另出注。但若与他本字句有异,则另加注说明。
⑤此处引文出自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P224,北京:北图出版社,2002。版本下同。亦见一粟《红楼梦卷》P494,文字有所不同。一粟所引版本中未提所读《红楼梦》为雪香夫子所评。
⑥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P111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以下简称《新证》。以下引文出自本书的,在正文引文后注明:《新证》,P××。不另加注。
⑦沈善宝《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一P16,清刻本。
⑧沈善宝《鸿雪楼诗选初集》,卷五P14,清刻本。
⑨沈善宝《鸿雪楼诗草》,卷十P3,清刻本。
⑩张宏生先生《才名焦虑与性别意识—从沈善宝看明清女诗人的文学活动》一文注意到此诗,见《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P82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版本下同。
(11)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P16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本下同。
(12)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P370-371。
(13)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P232。
(14)一粟《红楼梦卷》,P434。周汝昌《新证》依手稿本,认为字句较刻本为优,见《新证》P1104。
(15)见《红楼梦》第七十回,P99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本下同。
(16)《红楼梦》第七十九回,P1142。
(17)吴克岐《忏玉楼丛书提要》,P225。
(18) 此据北图所藏红藕花盦主人刊西园主人《红楼梦本事诗》附录,一粟《红楼梦卷》(P523)作:小妾甄家归日莲。笔者按:当以“旧日莲”为是。
(19)胡寿萱论红楼小启中谈到对方“抄寄王谢争论《红楼》两启,以及吾姊愿为宋牼一说”,则王谢二人亦有论红书信,惜乎不见。
(20)《忏玉楼丛书提要》,P233。
(21)范淑《忆秋轩诗钞》,光绪辛卯(光绪十七年,1891)冬良乡县官廨刻本。
(22)见《红楼梦本事诗》,清红藕花盦主人刊本。
(23)《红楼复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24)《红楼梦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25)参见郭梅《从今解识春风面,肠断罗浮晓梦边——〈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述评》,见《艺术百家》,2004.1。
(26)参见蒋寅《开辟班曹新艺苑扫除何李旧诗坛——一代才女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收于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
(27)见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P7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8)笔者按:诗话中亦有收录并评论词作者,如沈善宝《名媛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