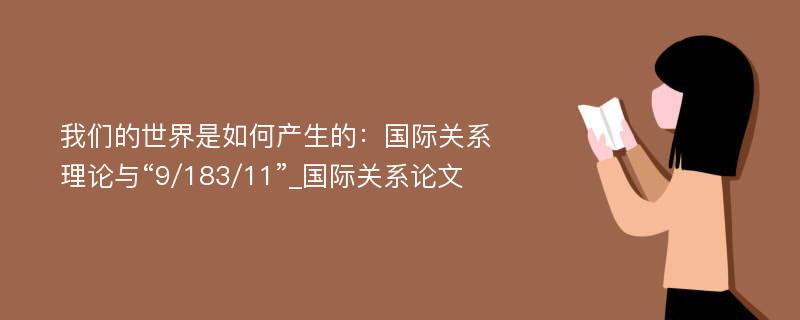
我们的世界何以生成:国际关系理论与“9#183;1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门学科在建构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relations)世界的过程中是“同谋的”,不可能存在“价值无涉”、非 规范性的社会科学。这门学科(我们的或美国的)构建我们赖以解释这个世界的思想范畴 的方式强化了西方力量。我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权力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哪些问题、如何研究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这是个道德问 题,但一开始我就不打算将道德规范与学术研究相分离。没有无来源的观点,也没有可 靠的免受道德与权力影响的“纯粹”的学术观点。
我试图通过对“9·11”事件的分析表达这些看法。我确实感到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我 们,应该反省我们的工作方式。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创建了关于世界政治的理论,而这些 理论支持特定的社会力量,并且毫无疑问地、明确地表现出主要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就 这个方面而言,国际关系对这个世界“一家之言式”的述说在多大程度上使“9·11” 成为可能。我们应该自问我们在“9·11”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 工作(著述或教学)同国际事件的关联性。
韦伯与“以科学为业”
在论述“9·11”之前,我要涉及马克斯·韦伯“以科学为业”的论点的本质,以此作 为一个论述的背景。韦伯的论点因把学术与政治相区别而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韦 伯认为在诸如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文化哲学这些学科中,政治必须被排除在课堂 之外。对韦伯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将个人的公民角色与学者角色相区分的问题 ,也是因为“科学”(广义的定义)的范畴同政治实践有很大的不同。韦伯将它们视做拥 有不同价值的方面,用科学不能解答生活中大量的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问题。韦伯的这 一立场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它们最相似之处就是 在学术研究中寻求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相应地,学者说他们自己“仅仅”是报告世界政 治,而不是对其有某种规范性立场。因此,呼吁“包含价值”或“规范性”的学术研究 根本上就是奚落学术。
从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开始,在过去的大约50年里,这种观点一直在国际关系 研究中居主导地位。这些观点充斥在行为主义者的研究中。然而,学术研究处于危险境 地。通常来讲,主流的看法是学术研究应该关注“事实”,祛除价值见解。最近这些年 ,在“第三次辩论”中,以这种观点为基础产生了许多回应性成果,如后结构主义、女 性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作品。并且,这种回应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什么可以被视做合法 的“社会科学”。这种辩论开始的著名的标志性事件是1988年罗伯特·基欧汉在国际研 究协会(ISA)的主席就职演说。他指出国际关系主要有两种研究方法,理性主义和反思 主义。尽管他承认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做出了重要的批评,“严肃考虑它们的论点要求 我们质疑理性主义的知识霸权”,(注:R.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CO:Westview,p.1 72.)然而他接着解释到没有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完整的。他认为反思主义学者需要发展 可证实的理论和细致的经验研究,如果反思主义学者没有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就无法评价 他们的研究计划。这种挑战不是针对反思主义研究中的本体论研究,而是在什么是合法 的社会科学的疑问中产生的。
最近,基欧汉和前《国际组织》编委彼得·卡赞斯坦及斯蒂芬·克拉斯纳,一道使理 性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新的论战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发展的主要标志。他们看到了三种建 构主义的替代形式(传统理论、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并强调把前两者和后现代主义 相区别的重要性:“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学者来说,现在提供了主要的 辩论的着眼点……(这可能因为)批判性建构主义者(接受了)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愿意公 开参与同理性主义的学术辩论”。(注:P.Katzenstein,R.Keohane and S.Krasn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1998,pp.645—685.)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
什么样的社会科学统治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就像美国政治学会表明的那样,在改革运 动中,美国学术界逐渐集中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理性选择理论。这种方法的核心 假设可简单表述为:理性选择理论把行为体看做是理性的、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 。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关心行为体内部的互动,研究国家不关心国内政治争论;研究个体 ,不涉及他的心理。理性选择理论家在固定的、事先给定的认同与利益基础上塑造了行 为模式。因为“太吝啬、太节省”,这样一种研究方法竟然令人难以置信地“高产、多 产”。这种方法不关心历史、文化与差异,只关注行为体处于何种博弈之中。这是一种 “暗箱”模式,只关注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联性。
现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这种方法也逐渐成了主导方法。这种方法完全是一种可用的 方法,但这只是分析国际关系的一种可用的方法。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一般 都涉及哲学方法论和认识论,因而与理性选择理论相比有很大不同。从这一点可以得出 两个结论:第一,理性选择理论只是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方法,不应被视做“社会科学 的精髓”。第二,理性选择理论既有长处,也有缺点。明显的缺点就是把利益与认同看 做是既定的,这样只要你接受了过程的第一步,你就必须接受结果。总之,重要的步骤 是塑造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塑造问题被理解为能将一些抽象的概念性表述具体化,如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行为体是自私的”、“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那样的” 。理性选择理论对这些先决的条件是从不涉及的,因为它认为这些条件是适合于理性选 择理论的。
理性选择理论在技术上是非常有效的,它可以得出结论,可以预测行为,它获得了预 期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它得到了预期的结果?是因为它正确,在于表现的与事实一致 ,并被承认?是因为它确实发现了理解世界、并与世界是什么保持一致的方法?还是因为 它为某些利益服务从而主导学术活动?要知道,这一方法存在于某些特定的有影响力的 学术团体中,而这些学术团体是以世界的主导权力为基础的。事实上我想问,国际关系 这门学科所体现出的霸权行为就比国际政治体系本身少吗?
谈到政治活动的本质,韦伯把可能影响我们政治活动的两种伦理立场做了一个著名的 区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信念伦理”谈及的是——道德的人正确行事, 而不要管结果;如果良好的目的导致不良的结果那不是人们的错。另一方面,根据“责 任伦理”行事的人必须对其行动考虑可预知的后果。然而,哪一种情况也不能逃脱一个 逻辑问题——有时候你必须采用一种在道德上有问题的方法来达到“好的目标”。对韦 伯来说,政治是“一件用力而又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道德的人不能简单信赖“ 信念伦理”概念。政治包含判断与选择。“判断与选择”被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称之为“弄脏手”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可能中立地从技术上决定“正确”的前 进的方式。这种情况也存在国际关系学科中。不可能有“信念伦理”等同之物,即不可 能对国际关系有一个中立的观察。所有的观察皆是部分的,所有观察都部分地带有伦理 后果,最终分析起来,就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
从本质上讲,学术不可能是中立的;它不可避免地是部分的、政治的,不可避免地带 有伦理影响。就像韦伯在几篇论文中所论述的那样,只要持一种政治观点,就不会有比 “让事实为自己说话”更为有效的方式。在我看来,在国际关系教学或研究中,没有学 者能够避免“弄脏手”的问题。
“9·11”与国际关系理论
在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概括时,我仍然要对这门学科如何与“9·11”相联系说几句。 我关注的是主流理论的核心假设,以及这些核心假设如何牵连于“9·11”事件。我想 列举国际关系理论的10个核心特征。我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帮助”创造了导致“9·11 ”事件发生的这个世界。
第一个核心特征是,关注作为分析单元的国家,不是人类整体,也不是个人。这个学 科一直把国家的诉求当做分析的要点,从而使国家具有某种“特权”。在国际关系中, 国家安全最重要,国家是分析单元;并且重要的是,国家是道德单元——道德指涉的要 点。个人安全被看做是国内政治问题,甚或是地区法律和秩序问题。对国家的过分关注 ,使国际关系理论几乎已经被界定。国家变得物化了,国家的中心性使这个学科如何看 待世界变得多余了。
第二个假设与国内、国外的区分相联系。就像国家被视为核心行为体一样,国家的边 界被视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分界点。一旦这样认定或假设,国家就有自己的生存方 式。因“国内”议程和“国内”需要与国际关系无关或被视为“非国际关系的”,国际 关系对这些问题不予考虑。抬高国家地位和构筑国家边界的行为不仅产生了相互分离的 学科——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而且是为特定社会力量和社会权力服务的。这样,政治学 和国际关系学就从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角度,再造和强化了那些特定的有关这个世 界的观点,并将这种特定观点表现为永恒的、自然的和经验主义的。
第三个假设是,这一学科一开始就建立在清晰的经济与政治相区别的基础上。从这门 学科成为学术性学科开始,其关注的中心就是解释国际政治关系,而非经济关系,除非 它们作为界定国际权力的一部分。当然,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是这一学科中重要的一个 分支,但国际政治经济学仍未对主流理论(特别是本体论)形成挑战。
第四个假设与人类必将共同走向一种终结状态的观念相联系,这种终结状态在大多数 有关全球化的文献中都有论述。这些文献把全球化描绘为所有国家和社会一定要经历的 过程,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差异只在于在“传送带式的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福 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就以此为基础。这种观念把主观性和差异看做是历史的暂时性, 只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展现。人类走向一致的进程中的驱动力是自由民主的力量,特别是 市场的力量。在这种看法下,说“他们”没有走向像“我们”(西方)一样的道路是不被 接受的,这些差异被解释为“不过”是先前历史意识形式的残存。
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五个特征是,主流理论缺乏对性别与种族的考虑,以白人和男人为 视角。这种理论说得好听是对国际关系不完全的描述,往坏处说是对国际关系的歪曲。 这种视角是对特定社会力量的支持。然而这门学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偏见,这些偏见 使这门学科存在性别与肤色盲点。这一假设视行为体为无性别的,将行为体的动机与考 虑问题的方式视为男性式的。同样,主流理论忽略种族因素,认为种族问题不属于这一 学科的范畴。
第六个核心假设涉及充斥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暴力概念。这门学科为解释战争而产生 ,但这一学科的特征太表现为暴力形式。并且,被界定为国际关系最核心内容的暴力是 一种由军事冲突引起的暴力,尽管存在远为更多的由经济因素引起的暴力。这一学科并 不关心其他形式的暴力,如国内暴力,除非国内暴力威胁到国家的生存。这就牺牲了其 他可能的学科指涉对象,特别是个人与种族群体的利益。
第七个特征是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结构重于施动者。在这门学科中,最有影响力、最流 行的理论是解释单元(通常是国家,处于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之中)行为的理论。这些 理论从体系结构推导国家行为,在解释权力方面很有竞争力。这些国际关系理论关注不 变性,而不关心变化性,这就降低了施动者的作用。而对建构主义者来说,无政府状态 是我们造就的。
第八个特征是普遍理性观念的重要性。普遍理性观念是多数流行理论的基础。这一点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最为清晰、明显,也因为结构理论的解释能力而充斥于这一学科。在 构建行为体认同与利益时,结构的作用与此假设相联系:通过社会化,行为体被迫接受 共同理性;人类朝着市场和狭隘的民主参与前进。在这个世界中,不管行为体处于何种 历史阶段,处于何种文化发展状态,所有的行为体最终共享根本的理性。
第九个特征与国际关系理论轻视认同的重要性相联系。因为上述理由,国际关系已经 表现出忽视认同问题的倾向;相反,国际关系喜欢以共同性作为论述基础。国际关系很 少注重行为体之间的主观理解,对它们之间的认同如何影响行为体理解世界政治的就更 少。把国际关系建立在共同性这一前提上,就意味着这一学科把世界上强者的议事日程 ,从而强者的认同看做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行为体的。如此,教科书中的世界和真实的 世界是不同的。这一学科在“再造”这个强权世界的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扮演一个重 要的角色,而解释强权世界在这一学科看来是“自然”的关注。
第十,寻求解答而非理解在这一学科中占支配地位。在过去的50年中,国际关系的任 务一直致力于解释世界,而非理解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一学科一直致力于提供一 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解释,很少有工作试图去理解思想趋向和非西方的“其他”的 关于世界的看法。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是,贬低了规范性问题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认 为规范性问题不处于“合法”的社会科学范畴之内。介绍规范性问题被视为是不合法的 ,如同价值不能支配中立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论述一样。问题是,这样的立场绝对要依赖 于一个暗含的前提假设:这样的价值中立立场的确是可能的。
因为这些原因,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是不完整的,这一学科关注富有世界、帝国权力。 这一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反映的是不列颠的利益,二战结束以后就一直反映了美国的利 益。以解释为名,这一学科再造了美国权力和美国霸权;以合法的社会科学为名,这一 学科反映了对窄小的国际关系的议事日程的看法;以客观为名,这一学科有意识地避免 了道德的或伦理的看法。
暴力与“9·11”
“9·11”事件对我们如何看待暴力有很大的影响。随着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印象永远 蚀刻在世界众人的心灵上,这么大的死亡所带来的公众影响已远远超过了所涉及的死亡 人数。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与这些事件相联系的方式不能简单地以死亡的人数来解释,这 种联系更多地与我们如何看待因政治暴力而死相关。我们的学科对“什么构成暴力,什 么样的死亡可用来解释国际关系”做了非常重要的假定。实际上,这些假设建立在一系 列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先验的假设之上,因而这些假定反映了社会的、政治的最终是经济 的权力。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最近几年一直在挑战这些假设,最显著的是发展了人的安全 的概念。1994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最先探讨了这一概念。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把对核 安全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安全的关注。人类安全不关心武器——它关注人类生活和尊严。 这份报告列出人类安全概念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人类安全普遍关注所有地方的所有的 人,因为威胁对所有人是共同的;人类安全的要素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对人类安全来说 威胁不仅在民族疆界之内;人类安全通过早介入而不是晚介入很容易达到;人类安全以 人为中心,人类安全关心人如何在社会中“生存和呼吸”。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认为,尽 管人类安全已经有两个主要要素——免于恐惧和免于饥饿,但安全概念一直表现得更加 注重前者而不是后者,根据人类安全概念应该从强调领土安全转向强调人的安全,从专 心于以武器得到安全转向关注以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实现安全。这一报告列出了人类安全 的七个领域: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个人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 安全。这一报告还指明了人类安全的六大威胁:失控的人口增长、经济机会的不均等、 移民的压力、环境的退化、毒品贩卖和国际恐怖主义。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2002年报告,对任何关心国际政治中暴力的人来说都是认真、严肃 的。当然,报告中所讨论的暴力并不真正符合国际关系这一学科对国际暴力的定义。这 份报告描绘了一个极为暴力的世界,并且暴力形式多样。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并不把这些 形式的暴力看做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当然,这些暴力绝对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性别研究 和发展研究等领域内学者研究的中心。但是,这些研究领域从未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 中心内容之一。如果我们的研究视界(purview)的确是世界政治的话,尽管与国家间关 系不同,但这些暴力的范围并不比更传统的国家间暴力形式更远离理解问题的中心。
然而,这些暴力的某些方面对解释“9·11”事件绝对是批判性的,因为它们能帮助解 释为什么世界上许多人对恐怖袭击拍手称快,为什么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如此不受欢 迎,甚至遭到仇恨。问题在于国际关系这门学科已经以如此方式界定其核心问题:将世 界政治中大多数形式的暴力排除在外,只关注相当狭小的领域。这些领域从根本上是建 立在把国内外事务相分离,经济与政治相分离,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相分离,“自然” 世界与“社会”世界相分离,男女相分离,道德与行动相分离和因果相分离的前提步骤 上。可以说,这一学科关于暴力的定义看起来如此紧密地与对白人、富人和权力精英中 的男人的关注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仅仅“看见”了国际暴力冲突的一部分呢?问题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这一学科发展过程中一直关注“大国”和作为行为体的国家间互动导致的结构 变化。第二,作为一门学科,国际关系首先产生于那些称得上是大国的国家(先是英国 ,然后是美国),因此,国际关系毫不令人惊奇地以“忧大国之所忧”,并以“虑世界 之所虑”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三,这一学科长期以来以“什么构成知识”的定义为基础 ,主张在一个紧密的推导分析框架内,有效地解释可测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学科 中,另一个与“9·11”事件相关的主要特征是,在解释世界政治中认同的重要性。国 际关系一直倾向于把认同问题置于无所不包的工具性的理性定义之中。这种理性仅仅是 对利益的计算,相对于对国际关系的窄小解释,认同被认定是不能适用的。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认同视为受人性的需求或体系的结构或制度环 境支配的,尽管行为体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经验主义的 方法论为基础,致力于解释而非理解,认为同解释行为体的认同和主体性的任务相比, 理解只是次要的。这种寻求无所不包的解释带有一系列的对社会的假定,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寻找广泛适用的解释的观念,一种适用于所有行为体的概念,不管身份,不管它们 的主体性。实证主义国际关系解释预先界定的行为体的行为——将行为体放在一个预先 界定的结构中,并带有预先设定的利益。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把“他们”的议事 日程或有关“他们”的利益的理解作为学科的主题。
除了对认同的关注,这一学科还需要更多地重视主体性问题,并以理解的观点来努力 审视这些主体性问题,而不要强迫以狭窄的社会科学观点来解释它们。在寻求终极真理 的过程中,不存在一个可以建立合法的、远离规范因素的社会科学的坚实基础。最重要 的是,真理不是“在那里”等着你去发现。国际关系中的难题和冲突不能按照一种难题 的逻辑去“解决”,相反,这些问题必须从相关行为体的看法中展开和理解。如果以真 理为手段就意味着这种真理是认识论法则所强加的,这门学科应该避免这样的观念—— 论述和理论能决定和区分何为世界之真理。真理经常是偶然性的,经常是有争议的问题 ,经常是部分的、片面的。佯称真理可以被发现,并且自称真理只能通过一种方法(西 方的方法,而不是其他的方法)才能被发现,最终只能是政治的行为。
艺术、理解与表现
通过对两位画家的分析,可以提供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和表现的观念,可以发现这种 观念在社会科学中是广泛的,在国际关系中是特定的。第一个是雷恩·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1898~1967)。马格利特颠覆了表现现实所采用的标准的、公认的和看问题程 序化的方式,冲击着人们日常的理解。(注:下面的讨论依据:J.Meuris,Magritte,
Koln:Taschen,1998.M.Foucault,This is Not a Pipe,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M.Kemp,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Art,Oxford:Oxford Univer sity Press,2000,pp.415—424.)他的画作通过真实地再现实物、情势和人,可以使画作的旁观者自问他们的状态。他把日常事物糅合进一种意想不到的或不习惯的方式,像翻手套一样,把传统逻辑的里面翻出来,由此逐渐削弱被共同认可的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含义。如此,“真实”(the real)和“现实”(reality)的概念就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含义。马格利特采取的做法是通过写实主义的画品去打碎那些假设,想用已知来揭示未知。
马格利特的画品表现了艺术从描绘世界的真实到从根本上质疑艺术家与被观察对象、 绘画中的现实主义与整个印象中现实主义缺失的关系的转变。在马格利特看来,这些问 题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人类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质疑我们表现现实的方法。有一点非常 清楚,即我们不能通过简单地判定哪一件作品最符合“现实”而对其画品进行解读。观 察者在解释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人们永远无法直接接近现实。他的作品抓住 了社会世界中某些重大的,而精确的理性选择理论不能看到的东西。在理性选择理论看 来,社会世界是人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理论的“用处”就在于理论如何准确地与现实相 符,这就是我为什么对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感到担忧的原因。
委拉斯盖兹(Velazquez)的《侍女》(Las Meninas)画于1656年。在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1966年初版的《事物的秩序》一书中成了概论一章的题目。在这幅画 之前,没有一幅画质问画品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就像福柯所说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 处于不停的交换之中。没有凝视是稳定的……主体和客体,旁观者和原型,无限地转化 他们的角色……巨大的油画布只以背面朝向我们……防止将这些凝视与任何可发现的或 明确的(事物)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只能看到相反的一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或我 们正在做什么。被看(seen)还是在看(seeing)?”(注:M.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New York:Vintage Books,1966[1973],pp.4—5.)
马格利特、委拉斯盖兹质疑了表现的本质。因此,没有无来源的看法,我们对社会世 界的看法不是简单的语境式的,而是来源于社会世界的。
结论
对理解和差异避而不谈,而偏好的解释又基于明确的西方理性观点,国际关系一直像 “侍女”一样有力地服务于西方权力与利益。这门学科的本体一直是那些强权,本体论 决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反映的就是历史的、文化的、特定的理性与认同观念。这门学科 “帮助”造就了“9·11”事件。
这些说明一点也没有暗示本学科内的主要作家一直有意识地试图让“9·11”事件发生 ,相反一些学者做出了值得注意的鉴戒,力图避免这种灾祸的发生。(注:这些学者主 要是:Richard Falk,Ken Booth,Cynthia Enloe,Robert Cox,Christine Sylvester,
Johan Galtung,David Campbell。)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特别对我们当中在行为主义 全盛时期受教育的人来言,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仅仅是对世界提供了基于某些“证据” 的说明。我们从没有意识到这门学科的广度,就像E.H.卡尔所说的,国际关系是带着来 源于某处的观点和为了某些当代的目的的人而写的。在这个意义上,像其他所有的历史 一样,这门学科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今天,我对这门学科的主要担忧是,在主要的国际关系学术团体中存在着强大的理性 主义传统,而在我们如何认识、如何建构我们的知识这些问题上存在的理性选择一致性 ,又使这种传统得到支持并被合法化。这种方法应该是国际关系教学中必要的一部分, 但不应该是这门学科的全部。我强烈地、热情地呼吁学术的多元化,这也是基本的政治 见解。从根本上我认为社会世界就像《侍女》或马格利特的画一样,核心的问题不是准 确的表达,而是理解。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决新千年世界政治中的问题。国际关系理论 一直专注于关注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他们”关心的事务,影响“他们”的暴力,“ 他们”所受的不平等,都不在这一学科的关注之内。这一学科因为以特定的方式为特定 的社会利益服务和解释他们的议程,应该受到谴责。
在这个新千年我想看到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理论?首先,我想看到一门开放的学科,而不 是把强者的议程看做自然和合理关注的学科。我想看到一门探究在文化上不同于那些统 治性世界力量的个体的意义与主体性的学科,而不是去假定它们的理性、利益,从而它 们的身份的学科。我想看到一门承认多元理解的学科,而不是把一种社会科学模式当做 是惟一正确的。我想看到一门意识到与事实相符合的理论具有局限性的学科,因此不要 把事实当做世界的属性等着去被发现,而是当做一个可以协商和理解的问题。最后,我 想看到一门不再藏在价值中立和经验主义面具后面的学科。只有通过意识到人类状况的 特性,意识到理解与表现社会行为的特性,我们才能构建国际关系理论,这种国际关系 理论同时显示伦理责任和委拉斯盖兹凝视中(同样,也凝视他)的谦卑。我们让这个世界 变得如此,但难得反思世界为何如此。事实上我们从没有关注非西方世界,直到他们偶 尔迫使我们陷入沉寂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