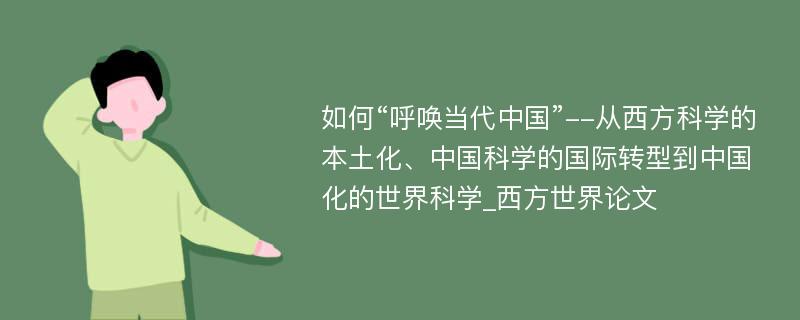
如何“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從西方學術本土化、中國學術國際化到中國化的世界學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世界论文,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论文,中國學術國際化到中國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圜分類號]K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4)01-0125-11
1929年,馮友蘭先生在《清華週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寫道:“在德國學術剛發達的時候,有一個人說,要想叫德國學術發達,非叫學術說德國話不可。我們想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達,也非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不可。”①“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可以看做馮友蘭為中國學人指出的治學路徑。對此至少可以做出三種不同的解讀:一是西方學術本土化,即把西方學術著作翻譯成漢語,同時也意味著西方學術範式的引進,這應是馮氏之原意;二是中國學術國際化,即以英語等國際通用語言發表中國學術成果,在國際學術界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三是中國化的世界學術,即進行根植於中國文化傳統、母語思維和生活實踐的原創性研究,做出兼有中國品格和世界水平的學術貢獻,並以全球化的形式進行表達。
以上三種解讀,恰好也是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發展的幾種典型取向,本文將以馮友蘭等學者的有關言論和做法為例,就這些學術取向進行討論,並對中國學者和學術期刊的使命進行思考。
西方學術本土化
從上下文看,馮友蘭所說的“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原意其實很簡單,就是用漢語翻譯西方學術。他說的“現代學術”其實就是西方學術,“中國話”就是漢語。有些論者把本土化與國際化、西化等相對立,強調中國本位的文化,其實本土化應該指某種外來的事物為適應本地特徵而進行的改變,如跨國公司麥當勞為適應中國人口味而賣油條。儘管本土化過程必然有本地文化的參與和改造,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甚或霍米·巴巴的“雜交性理論”,但其基本範式和概念仍然是外來的而非本土生長出來的。西洋學術的本土化與中國學術的西化,實乃一體之兩面,只是從不同的視角來看而已。
馮友蘭在這篇文章中寫道,“我覺得現在中國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譯書”。②他強調:“我們要想叫現代學術到中國來,我們還是要先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我們還要用張百熙、盛宣懷的譯書政策。”③他把引進西方學術看做一條發展學術、實現強國目標的捷徑。這讓人不由想起20多年前梁啟超的話:“今日之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④馮友蘭認為清華大學應該做到教學、研究及翻譯三足鼎立,翻譯甚至比教學研究更重要:“我並非不主張教授要做研究的工作,研究是必要的。不過研究工作見效遲,翻譯工作尤適合現在社會的需要。”⑤此時馮友蘭剛卸任清華大學秘書長,來年即將實際主持清華校務,這番議論自然不是興之所至的閒談,而是深思熟慮的產物。其實幾年前在中州大學時,他就有了類似的主張:在中國辦有規模的大學,應設本科、研究部、編輯部三個部分,大學教員教學研究的同時,還可以兼任編輯員。⑥按他的設想,編輯部的工作就是編譯西方學術書籍,這與他後來在清華提出的“教學、研究及翻譯三足鼎立”的主張並無二致。
比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更重要的是,中國學者引進了西方學術的觀念和學術範式。所謂中國現代學術,就是在傳統學術於劇烈世變中走向衰微之際,以西方學術為鏡鑑而形成的。本文僅以中國哲學的學科建構為例,做簡單的討論。
馮友蘭把胡適看做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開創者:“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⑦余英時曾借托瑪斯·庫恩的理論,指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意義在於建立了新的範式,在他看來,章太炎、梁啟超和王國維都已經走到了新範式的邊緣,而“最後一小步”則由胡適來完成,從而實現了學術范式的現代轉化。⑧馮友蘭曾說起一件事:1921年蔡元培訪問紐約,在中國留學生歡迎會上講了一個點石成金的故事,並說:“你們在這裡留學,首先要學的是那個手指頭。”馮友蘭補充說,那個手指頭就是方法,即西方學術研究的方法,中國較早使用這個指頭的人是胡適。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既然接受了“哲學”這一西方舶來的學科概念,走上了中學西解的理路,便如蔡元培在該書序中所說的那樣,就“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⑩
在馮友蘭撰寫其《中國哲學史》時,胡適所開闢的道路已是大勢所趨。但其過於西化的疑古傾向也遭到不少質疑,故馮友蘭試圖在自己的著作中兼有“哲學性”與“民族性”。馮友蘭在多處談到自己與胡適的差異,如在《三松堂自序》中他花費了大量筆墨與胡適劃清界限,比如胡適是“疑古”而自己是“釋古”,胡適是重考據的“漢學”傳統而自己是重義理的“宋學”傳統。儘管這些區別確實存在,但從學術範式的層面,兩人都取了西方哲學的基本概念和框架。金岳霖在審查報告裡敏銳地指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把中國的哲學當作發現於中國的哲學”,這意味著該書完全符合哲學這一西方學科的要求,即遵循了現代學術的範式。馮友蘭說得很清楚,“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敍述之。”(11)他所說的中國哲學,“即中國之某種學問或某種學問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也”。(12)
馮友蘭明確指出,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第一條就是“鑽研西方哲學”,因為“西洋哲學史之形式上的系統,實是整理中國哲學史之模範”。(13)馮友蘭本人的學術生涯,就起始於對西洋邏輯學的興趣,進而喜歡上了西方哲學。當年考北大哲學門的時候,他就是沖著西洋哲學門去的,只是因為西洋哲學因故沒有開成,無奈之下才進了中國哲學門。從1919年底開始,他才如願以償地在哥倫比亞大學開始系統地學習西洋哲學。他後來走上研究中國哲學之路也並非初願:“回國以後,本來想繼續研究西方哲學,作一些翻譯介紹西方哲學的工作,當時的燕京大學叫我擔任中國哲學史這門課,講中國哲學史”。(14)
有趣的是,金岳霖在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寫的審查意見中,用了不少篇幅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原稿作‘美國商人’,發表時,我徵得金先生的同意刪去‘商’字);胡先生於不知不覺中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15)金岳霖以為,馮著優於胡著的關鍵點,即在於胡適是以一種哲學的成見寫中國哲學史,馮友蘭雖有自己的成見,卻沒有全以成見來處理哲學史,而是對中國固有之哲學抱有同情的態度。比如馮友蘭講到中國哲學之弱點時說:“中國哲學家之哲學,在其論證及說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學家之哲學,大有遜色”。但接下來,他又話鋒一轉,為中國哲學家辯護:“此點亦由於中國哲學家之不為,非盡由於中國哲學家之不能。”(16)
從胡適這一代學者開始,中國現代哲學的主流,走上了一條脫離經學、與西方“接軌”的道路。胡適、馮友蘭等人起到了現代學術“轉轍器”的作用,他們的貢獻在於輸入和移植西方學術,乃至以西方為藍本,用西方的方法和眼光研究中國本土的問題。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也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中國意識和觀念,促成了水平各異的中西融合,這就是“西方學術本土化”。直到今天,儘管在主導範式上出現過“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輪換,但“西方學術本土化”始終是中國學術生產的主導邏輯。
致力於“西方學術本土化”的同時,馮友蘭也非常強調“學術獨立”:“中國現在須力求學術上之獨立”。(17)馮氏講的“學術獨立”,從上下文看大約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不依傍於政治或資本的力量,沒有實用之目的,奉行“為學術而學術”。這不同於儒家學與政互為表裡的傳統,主要源自西方學院傳統,是“五四”前後中國學界的一種流行觀念。馮友蘭認為“為學術而學術”包含三方面的思想:“一方面是有關於個人研究學問的目的的思想。另一方面是有關於對於學術的看法的思想。更另一方面是有關於對於研究學術的方法的看法的思想。”在馮友蘭看來,在第一方面,“照主張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想,學術的價值就在於發現真理,而真理的價值就在於其本身”。(18)第二方面,“學術”應該是獨立的,而不是任何東西的附屬品。馮友蘭引了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一條隨感錄《學術獨立》為這種觀念的代表,其中說道:“中國學術不發達之最大原因,莫如學者自身不知學術獨立之神聖。”第三方面,馮友蘭引用了嚴復的《救亡決論》來說明研究學術不可有致用之心,反而能得到學術的大用。(19)
學術獨立的第二層含義是中國本土可以獨立培養掌握現代學術的學者。在馮友蘭看來,若“教學、研究及翻譯三足鼎立”的設想可以付諸實施,“再假以時日,中國亦可有像樣的學者,而中國學術亦可獨立矣”。他認為,中國學術之所以不能獨立,就是因為“中國現在對西洋學術有較深的研究之人甚少”,而解決的途徑恰恰是“充分地輸入西洋學術”。(20)他在19世纪80年代的一次訪談中還強調:“清華發展的過程就是中國近代學術走向獨立的過程”,其中重點講了羅家倫任校長期間的一些舉措,如提高中國課程地位、壓低洋人地位等。(21)這還可以與胡適任北大校長時擬定的《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相對照,其中第一條就是“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22)
值得反思的是,不論馮友蘭還是胡適,都沒有覺得輸入西方學術會對中國學術獨立造成絲毫損害,正相反,他們恰恰將其視為中國學術獨立的前提。換一種眼光看,這種所謂的“學術獨立”之路,是否也是一條通向學術依附之路呢?
馮友蘭1921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系會上宣讀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他的導師杜威的一段話:“中國正在急劇變化,若還是用舊時帝制的中國那一套來思索中國,就和用西方概念的鴿籠子把中國的事實分格塞進去來解釋中國,同樣地愚蠢。”(32)杜威在此處強調了“變化”,不能用古代的範式來思考今天的中國,正如不能用西方的範式來硬套中國一樣。在擺脫傅統範式這一點上,馮友蘭無疑做得很好。但是,他真的擺脫了“西方概念的鴿籠子”嗎?
中國學術國際化
如果不把“中國話”的含義限定於“漢語”,而理解為“中國的聲音”,則“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發出自己的聲音,當然一般而言使用的語言不是漢語,而是以英語為主的國際通用語,這就是“中國學術國際化”。
隨著中國國力和民族自尊的增強,特別是到了90年代之後,學術界出現了國際化的熱潮。其實,“中國學術國際化”並非一個新現象,而是與“西方學術本土化”相伴發生的。有論者指出:“百年多來的中國現代學術史就是一部國際化的歷史,早在19世紀末中國漸漸融入世界體系時,‘國際化’就已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宿命”。(24)
梁啟超曾這樣總結晚清新學失敗的教訓:“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為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為社會所輕。”(25)沒有精通西洋語言文字的、有國際化交流能力的學者,引進西學,進而實現“西方學術本土化”就是不可能的。
待以胡適為代表的“五四”一代學人進入學界,梁啟超所遺憾的狀況終於得以改觀。中國文化界寄希望於西方文化,而限於語言和學力,絕大多數人對西方文化還很茫然,此時最需要的就是熟悉中西語言和文化,把西方文明帶到中國來的文化“傳教士”。胡適就在這個恰當的時刻扮演了恰當的角色。胡適不但在國內暴得大名,在國際上也成為知名度很高的學者,被西方人稱為“白話文之父”、“中國文藝復興之父”。他頻繁參加各種國際交流和演講,長期在美國旅居,抗戰期間還曾擔任中國駐美大使,其國際化程度之高毋庸置疑。
馮友蘭與胡適有很多有趣的共同點,比如他們都曾在中國公學就讀,都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完成博士論文。馮友蘭和胡適一樣,在國際學界享有很高的名望。他的《中國哲學簡史》據他194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上課的教材編寫而成,此書譯為十多種語言,銷售數百萬冊,是西方各國大學中國哲學史課程必用的教科書。民國時期,像胡適、馮友蘭這樣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不在少數,比如陳寅恪、趙元任、金岳霖、錢鍾書等,不勝枚舉。
所謂的中國學術國際化,有兩個最值得注意的特點:一是注重語言能力,特別是能否使用以英語為代表的國際通用語;二是學術上以歐美為尚,比如學術上唯歐美學者馬首是瞻,看重歐美留學背景,學術評價上向歐美看齊,強調以歐美學術慣例為基礎的學術規範等。
先來說說語言問題。一個現代學者具備較強的外語能力,可以閱讀外語文獻和參加國際學術交流,當然是非常必要的。正如一位國外學術雜誌主編看到的那樣:“我認為中國學術若要走向世界,將其翻譯成英語以及其他語言至關重要。除東亞研究尤其是漢學領域之外,國外絕大部分學者並不熟悉漢語,因而無法閱讀以漢語出版的學術著作。目前,即使是中國最優秀的學術著作,若不以國際通用語言出版,恐怕也難以為世界學界所知。”(26)但這種對外語的重視不可推到極端,如果產生了英語等外語優於漢語的觀念,甚至認為英文論文的水平高於中文論文,英文刊水平高於中文刊,就有點走火入魔了。近年來,中國人文社科學界掀起了興辦英文學術期刊的潮流。英文刊對促進國際交流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擔憂的問題:比如,在2011年對200多種英文刊的質量檢查中,編校質量合格的英文刊只有20%;大多數英文刊發行量和國際影響都很小,很難得到西方學者的關注。我們應該努力辦出更多更好的英文學術期刊,但就中國學術期刊總體而言,首要的使命還是用漢語傳播中國學術。
語言絕不僅是一種簡單的工具,正如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所說,“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屬於某個人類群體的概念和想像方式的完整體系”。(27)日本思想家竹內好也說:“語言是意識的表像,故語言沒有根即意味著精神本身並非是發展著的,這也意味著文化成了沒有生產性的東西。”(28)只有懂得一種語言,才能真正了解說這種語言的人們和他們的文化,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人文學科是根植於母語之中的。一位学者这样描述人文社會科學與母語關係:“人文社會科學成果是否立得住,一定是要求通過母語表現出來,思想只有在母語裡才能產生足夠的震撼力與吸引力。翻譯過的作品畢竟是二手作品。近代德國人一開始用拉丁文做哲學,慢慢開始用母語做哲學,一直做成了偉大的德國古典哲學傳統,以至於今日做哲學,好像不懂德語便總覺得愧疚。”(29)
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馮友蘭認為:“‘數學就是數學’,沒有‘中國的數學’。”(30)趙元任也曾這樣討論數學問題:“算學就是算學,並無所謂中西,斷不能拿珠算、天元什末跟微積、函數等對待;只有一個算學,不過西洋人進步得快一點,他們是世界上暫時的算學先生,咱們是他們暫時的學生。”(3)其實,數學儘管不像人文學科那樣有明顯突出的文化屬性,但其本身也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思維特徵,未必沒有“中國的數學”。不過基本可以達成共識的是,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民族差異,確實不像人文學科那麼突出,而社會科學的情況則介於二者之間。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人文學科與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有更加密切的血肉聯繫。馮友蘭曾區分過不同學科在民族特性上的差異:“確實有‘中國的’哲學,‘中國的’文學,或總稱曰‘中國的’文化。”(32)他認為,中國哲學之所以不同於其他民族,原因之一“可能是語言、文字方面的問題。中國的語言是單音節的。中國的文字一直到現在是方塊字的權字,其來源是象形文字。這都不利於用字尾的變化表達詞性。”(33)
此外,語言中还包含著一種權力和尊嚴。比如,在19世紀中葉之前,中國人比較自大,不肯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外交文書都是用漢文書寫的,並且拒絕設置翻譯人員。這一狀況到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才因為軍事上的失敗而被徹底打破。條約中有這樣的規定:“嗣後英國文書俱用英字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此句英文本無)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為正義。”(34)通過確立本國文字在條約中的優先地位,英國顯示了作為戰勝國的優越感。
如果放棄漢語的中心地位,而把漢語看做英語的附庸、一種次等的語言,我們不但會遠離中國文化的精髓,同時也失去了民族的尊嚴。對於一個中國學者而言,首要的能力應該是用漢語表達中國學術,這不僅是語言工具的選擇問題,更是選擇一種有清醒自我意識的學術取向。
下面僅以國內學者對國際引文索引的態度為例,談談“學術上以歐美為尚”的問題。
由於學術評價機制的原因,中國學者非常青睞被SCI、SSCI、A&HCI等幾大引文索引收錄的學術期刊。SCI、SSCI等的開發者加菲爾德2009年訪華時,對自己受到的隆重歡迎感到驚訝。這一場景正好就是中國SCI、SSCI熱的最好表徵,好像合情合理,卻又莫名其妙。近年來,中國作者SCI期刊發文量不斷攀升,目前數量已僅次於美國。然而,這卻造成了科技期刊優質稿源流失嚴重,中國學者的成果反而不能被中國學界首先獲知,大量科技經費被用於支付國外期刊版面費或國外數據庫回購。更值得反思的是,相對於中國學者文章驚人的數量,其總體影響力之微弱卻是令人遺憾的。
筆者在與清華大學一位社會科學領域青年教師的交談中瞭解到,他把主要的時間精力用來撰寫英文論文,投向國外的SSCI期刊。因為在考核時SSCI期刊上的文章與《中國社會科學》上一樣是最高分,而在後者的發表難度要大得多。他還透露了發表英文文章的一些小竅門:一是從小處著手,注重計量和實證;二是投合其意識形態偏好;三是選擇中國特有的,對西方人而言具有獵奇性的題材。以SSCI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價標準有“自我殖民化”的風險:首先,要接受英語,而放棄母語寫作和母語思維;其次是學術語言的西化,大量運用移植來的術語;再次是從西方社會的歷史脈絡思考問題,從西方人習慣的視角觀察和分析問題。這些傾向都可能使中國學者迷失主體意識,淪為西方學術的模仿者和附庸者。
乍看上去,“中國學術國際化”與“西方學術本土化”處處相反。從語言上說,一個是把中文翻譯成外文,一個是把外文翻譯成中文;從學術流向上說,一個是學術的輸出,一個是學理的輸入。但無論是“西方學術本土化”,還是“中國學術國際化”,都未能擺脫“西方中心”的主導邏輯,都包含著一種迫切希望獲得西方承認的心態。從客觀上看,學術上以歐美為尚,既是不平等歷史產生的結果,也是當代國際學術體制和權力關係的折射;從主觀上看,這是一種在文化上缺乏自信的表現。
正如一位論者所言:“人文社會科學有太多的不能抽去和歸一的東西,其國際化必定是有限度的,其標準必定是多元的,其平臺必定是多樣的,其語言必定是豐富的。”(35)因此,中國人文學術真正地實現國際化,最關鍵的障礙恐怕不是語言,也不是與西方學界接軌不夠。中國學者還是要回到自身,思考如何創造出既根植於中國語言文化,而又能豐富和發展世界學術的新貢獻來。
瓶與酒之辯
馮友蘭很喜歡以瓶和酒為喻,他的瓶與酒之辯,大致上是在內容與形式的意義上談論的,瓶與酒可以看做學術思想與學術範式的隱喻。關於瓶與酒的討論是西方學術本土化過程中出現的重要話題,胡適、鄭振鐸、郭沫若等學者對此都發表過重要的議論。此處我們僅討論馮友蘭與陳寅恪的瓶酒之辯,因為從中可以看出對西方學術和中國傳統態度上的微妙差異。從對瓶與酒的關係的思考中,也可以隱約窺見“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的門徑。
《中國哲學史》下冊序言中寫道:“蓋舊瓶未破,有新酒自當以舊瓶裝之。必至環境大變,舊思想不足以適應時勢之需要;應時勢而起之新思想既極多極新,舊瓶不能容,於是舊瓶破而新瓶代興。”(36)這可以看做馮氏瓶與酒理論的基本原理。馮友蘭先是用這樣一套瓶與酒的理論描述了西洋哲學史上古、中古、近代的更迭,然後便按照西洋哲學史的模式,也把中國哲學史分為相應的上古、中古、近古三個時期。不過美中不足的是,中國哲學史實際上只有上古、中古兩個時期,因為按照西方哲學史的標準,中國的近古哲學不過剛剛萌芽而已。上古是孔子到淮南王的子學時代,中古是從董仲舒到康有為的經學時代,“此時諸哲學家所釀之酒,無論新舊,皆裝於古代哲學,大部分為經學之舊瓶內”。直到近代西學傳入,經學的“酒瓶”才被打破:“西洋學說之初東來,中國人如康有為之徒,仍以之附會於經學,仍欲以舊瓶裝此絕新之酒。然舊瓶範圍之擴張,已達極點,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終為所撐破。”(37)
陳寅恪在1933年為《中國哲學史》下冊撰寫的審查報告中說:“寅恪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承審查此書,草此報告,陳述所見,殆所謂‘以新瓶而裝舊酒’者,誠知舊酒味酸,而人莫可酤,姑注於新瓶之底,以求一嘗,可乎?”(38)這段話往往被看做陳寅恪思想的一次重要表述,近年為越來越多人所重視。其實,這正是陳寅恪對馮友蘭瓶酒之喻的回應。
馮友蘭本人對陳寅恪的這段話有過解釋,他認為咸豐同治之世的主要思想鬥爭,是曾國藩和太平天國之間“名教”與“反名教”的鬥爭,曾國藩認為太平天國是用西方基督教毀滅中國傳統文化。曾國藩、張之洞的“同治維新”,是要引進西方的科學和工藝,但要使之為中國傳統文化服務,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還舉俞樾會試試卷中的一句詩“花落春仍在”深受曾國藩賞識,作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寓言。馮友蘭對“中體西用”不以為然:“我是主張體用不可分的,有什麼體就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就可以知道他有什麼體。”他對王國維、陳寅恪雖不能認同,卻存有一份深切的同情和尊敬,讚美他們是當代文化的伯夷叔齊。(39)在馮友蘭看來,王國維之自沉,陳寅恪之突走,都是因為聞革命軍至,以為花落春亦亡,他們的共同點是“愛國家,愛民族,愛文化,此不忍見之心所由生也”。
其實陳寅恪並不是像張之洞那樣以體用對待中學和西學,他真正關切的是如何為中國文化之舊酒鑄造出新瓶,進而使之得以存續。他指出中國思想文化於其他思想“無不儘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來民族之地位”,(40)因而能發展擴大。他非常重視佛教思想傳入中國後,宋明理學吸收佛家思想後形成的新義理,因為這使中國文化延續傳承了幾百年。陳寅恪對馮友蘭的期待,或許是像儒學吸收佛學而產生宋明理學那樣,在西洋思想傳入之後,開創一種新的學術系統來承載中國文化,延續他心目中的“文化神州”。(41)然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寫法,基本上要算是“新瓶裝新酒”,直到“貞元六書”特別是《新理學》,接著程朱理學講,才有了些“舊瓶裝新酒”的意思。(42)然而,由於馮友蘭對陳寅恪所說的“舊酒”並不以為然,他的工作與陳寅恪“新瓶裝舊酒”的旨趣還是相去甚遠。
那麼,在瓶與酒的問題上,馮友蘭和陳寅恪的實質性差別究竟在哪里呢?
馮友蘭曾這樣講述自己的思想演變:“我的思想發展有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我用地理區域來解釋文化差別,就是說,文化差別是東方、西方的差別。在第二階段,我用歷史時代來解釋文化差別,就是說,文化差別是古代、近代的差別。第三階段,我用社會發展來解釋文化差別,就是說,文化差別是社會類型的差別。”他發現當時流行的主張文化是東西方差別的見解不對,因為“向來認為是東方哲學的東西在西方哲學史裡也有,向來認為是西方哲學的東西在中國哲學史裡也有。我發現人類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問題。”(43)在馮友蘭看來,似乎人類的哲學存在一種共通的體系,只是不同地域的哲學發展的階段不同,存在古今差異,或者說是進步與落後的差異。
在馮友蘭和強調東西文化差異的梁漱溟之間,於是有了一道明顯的分野:像梁漱溟那樣過於強調東西文化的差異,容易把文化差異本質化,可能忽略不同文化間的共同性,也可能忽略某種大文化之下具體的區域、民族和個體差異;但像馮友蘭這樣,用古今差異和社會類型來解釋東西文化差異,會把文化看成普適的,而忽略文化的複雜性和傳承性,馮友蘭的這種觀念與胡適是很相似的。胡適曾說“文化之進步就基於器具之進步”(44),在他看來文化不過是一種工具,所以他會說“東西洋文明的界線只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線”。(45)坐人力車的中國處於中世紀,而騎摩托車的西方人則進入了現代。難怪汪榮祖說:“從胡適的觀點看,所謂西化也就是走出中世紀而進入現代”,胡適眼中“只有文化進步問題,並無文化衝突問題”。(46)正因如此,馮友蘭對待“酒”的態度和陳寅恪迥然不同,陳寅恪視為至寶的“舊酒”,即“中國文化”,在馮友蘭那裡卻可以很輕鬆地被替換為“新酒”,即西方學術,更不用說“舊瓶”了。
我們還可以從“中國觀”和“文化觀”兩個角度,進一步比較馮友蘭和陳寅恪在“瓶與酒”問題上的差異。
先來看看他們對“中國”的理解有什麼不同。馮友蘭很喜歡引用《詩經》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說自己的使命在於“闡舊邦以輔新命”。“舊邦”指的是中國,而“新命”則指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很明顯,馮友蘭所講的“中國”,主要是一個政治、民族、地理上的概念。他曾這樣表述:“就現在說,‘中國’就是中華民族所佔有的疆域和所組織的國家。”(47)而陳寅恪心目中的中國則是“文化神州”。馮友蘭與陳寅恪心目中,一個是“中國的”文化,一個是“文化的”中國。無論是張之洞賞識的“花落春仍在”,還是馮友蘭說王國維、陳寅恪誤以為的“花落春亦亡”,其中的“春”指的都是文化上的中國,而馮友蘭心目中的“春”,則是政治、民族、地理意義上的中國。正因為是從政治、民族、地理層面而非文化層面來認同中國,胡適等“五四”一代學人,才會認同西方文化而採取“全盤性的反傳統態度”;(48)也正是因為從文化的層面認同中國,王國維和陳寅恪才會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那樣的深情和眷戀。
我們再來借助汪榮祖對“文化單元論”和“文化多元論”的區分,瞭解馮友蘭和陳寅恪“文化觀”上的差異。汪榮祖認為康有為和章太炎分別代表著兩種文化觀:康有為認為文化的發展像科學一樣沒有國界,放之四海而皆準,是“文化單元論”的;章太炎則認為各國家民族有其獨特歷史經驗形成的文化特性,不必互斥而應該共存,中國文化可以吸收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不能取代中國文化,否則就等於中國文化的滅亡,這是一種“文化多元論”。(49)馮友蘭似乎和康有為、胡適一樣,傾向於“文化單元論”的文化觀,而陳寅恪則類似於章太炎,採取了“文化多元論”的態度。汪榮祖構建的兩種文化觀,儘管仍有簡單化的嫌疑,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馮友蘭和陳寅恪的文化觀念。
綜而論之,馮友蘭所說的“新酒”指的是西方學術思想;而陳寅恪的“舊酒”則指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馮友蘭看來,既然中國有了“新酒”,“舊酒”是不那麼值得留戀的;而在陳寅恪看來,倒掉“舊酒”,就連“中國”也一起倒掉了。
“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達”的根本辦法
馮友蘭說譯書“不是根本辦法,但這是根本辦法的先決問題”。(50)那麼,“叫現代學術在中國發達”的根本辦法是什麼呢?對此,他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中國人文學科和部分社會科學學科,本來就有著獨立於西方知識體系的優秀傳統。中國學者的目標應該定位於開掘中國文化和思維中的智慧,通過學術概念的鑄造、學術方法的生成、學術範式的突破,改變世界學術的面貌,而不只是做一些枝枝節節的工作,我們可以大膽地將其稱為“中國化的世界學術”。“中國化的世界學術”並非是要建立某種中國的學術霸權,而是在歐美主導的世界學術中,發展一種原創性的、根植於中國語言文化的、具有跨文化啟示意義的學術。
一位學者曾寫道:“當年陳康曾發誓,做存在論一定要讓西方人以不懂中文為恨,他當時做的畢竟是西方的存在論……今日中國人要做的,恰是形成與這一時代中國人的追求相匹配並為中國未來發展立道立言的哲學;這樣的哲學,如果外國朋友們真的看不懂,那才真的叫以不懂漢語為恨。”(51)他的說法揭示了“中國化的世界學術”的部分要義,即根植於中國生活實踐和母語的學術,他的目光主要指向現在和未來。他沒有強調但或許更加重要的是,中國學術還應把目光投向過去,從被漸漸遺忘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獲得更多的滋養和靈感。唯其如此,中國人文學術才能為人類的現在和未來做出獨特的貢獻。
這是一項複雜的長期系統工程,特別是百年以來,漢語和中國文化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國學術界需要進行更長久的積澱,付出更艱巨的努力,才有可能實現。從大端而言,中國學界應當樹立以下一些基本共識:
首先,中國學者應該樹立起一種文化上的自信,並敢於把中國傳統文化看做自己學術上的根基和源泉。陳寅恪寫道:“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52)在接受國際化這一宿命的同時,中國現代學人不能放棄創建與“本來民族之地位”相稱的學術系統這一理想。傅斯年在撰寫於1928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我們要使科學的東方學正統在中國”。當年的陳垣也曾對漢學中心不在中國而在歐洲和日本的狀況心有不甘。然而,八九十年過去了,我們似乎仍然很難理直氣壯地說東方學或漢學的正統在中國,也沒有像薩義德那樣對東方學和漢學提出深刻而有力的批判。這表明我們民族文化的自覺意識和自信心還有待加強,沒有自信和自立的國際化只能是邯鄲學步。
其次,中國學者應該要看到,“現代學術”已經不像“五四”時代一樣,只是“西方學術”的另一種說法,而具有了涵括東西的“世界學術”的含義。二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後,世界的概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正如有論者指出的:“21世紀的世界已從西方稱霸的一元化、中心化的世界逐漸發展為經濟一體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各民族國家差異共生的世界。”(53)今日的狀況已經與半個世紀前發生了重要變化,因為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趨勢日益強化,西方中心論在其故鄉也遭到了質疑和批判。王元化敏銳地指出:“我不認為‘五四’時期對待西學的態度及吸收西學的方式都是天經地義不可更改的。我認為那時以西學為座標(不是參照系)來衡量中國文化,是和國外那時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論有著密切關係(‘五四’時期陳獨秀即稱西學為‘人類公有之文明’),二戰後西方批判了西方文化中心論,而提出多元化的主張。”(54)其實,早在1906年,王國維就提出了“世界學術”的觀念:“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夫尊孔孟之道,莫若發明光大之,又莫若兼究外國之學說。”(55)
最後,中國學者需要一種更加包容和多元的學術智慧。王元化曾表述過一種學術姿態:“研究中國文化不能以西學為座標,但必須以西學為參照系”,因為“出自任何單一文化視角的價值觀都無法提供合適的框架去理解波及全球的種種變化”。為要想實現“中國化的世界學術”,既不能像胡適那樣以西學為主體,拿中國的東西去比附;也不能以國情和特色為理由,拒絕承認各民族共通的人性原則和價值準則。他很欣賞的湯用彤和陳寅恪“提倡中外文化融貫說,主張將西學化於中國文化中”的治學取向,並對湯用彤的《魏晉玄學論稿》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進行過比較和點評,認為從中可以看到汲取西學的兩種不同態度。他批評道,“胡適以傳統文化去比附西方文化,阻礙了他對傳統文化進行比較深入的理解”,“胡適既以西學標準為本,因此他將文化傳統中不同於西方標準的許多成分一概置於繩墨之外”。(56)而湯用彤雖然“學兼中外,通梵文、巴利文,在印度文化方面有精深的素養。早歲留學美國,曾鑽研西方哲學”,但在《魏晉玄學論稿》中卻無一字談及西方哲學,“他所具有的深厚的西方哲學功底,倘不細察,是無法從字裡行間尋出蛛絲馬跡的,如撒鹽水中,化影響於無形,不露任何痕跡”。(57)這種不拘泥於西方範式、“將西學化於中國文化中”的治學境界,已經離“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的理想不遠了。
從中國期刊界的角度看,為了實現“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的理想,也有不少事情可以做。比如:應當向致力於開掘中國傳統文化、深入辨析不同文化中的特有觀念、努力實現中西融通的稿件和作者傾斜,而對套用西方學術模式分析中國材料的研究持謹慎態度。同時,應當向扎實深厚的基礎研究傾斜,而不追求時髦新穎的方法,即便影響了刊物的轉載率和影響因子,也應堅持自己的學術理想。此外,努力提升辦刊水平,創建有中國氣質和風度的名牌學術刊物,努力提高刊物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比如規範英文標題、摘要和DOI(數字對象唯一標識符)等,並通過主動接觸和談判,努力使更多中文學術期刊加入國際學術索引。再有,中國學術期刊應當加強協同合作和數字化水平,比如學術期刊之間聯合起來成立刊群或聯盟,建立像愛思唯爾(Elsevier)和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那樣的大型期刊集團。最後,宜加強大陸學術期刊與港澳台及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協作,聯合漢語文化圈的學術力量,共同維護和發展“文化中國”。
“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是馮友蘭先生的夙願,中國學界和期刊界有責任在馮先生所做思考和學術實踐基礎上更進一步,真正推動中國學術之發達。但願以上圍繞“叫現代學術說中國話”所做的粗淺闡釋,能夠促使更多的學者和期刊人關注和思考中國學術的未來,相信這也是馮友蘭先生願意看到的。
①②③⑤⑥⑦(17)(18)(19)(20)(21)(39)(40)(50)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40、42、43、30、195、30、179、189、30、221、307~309、307~309、42頁。
④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52頁。
⑧參見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見氏著:《現代危機與思想人物》,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184頁。
⑨(12)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5、249頁。
⑩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頁。
(11)馮友蘭:《中國哲學小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頁。
(13)馮友蘭:《怎樣研究中國哲學史?》,上海:《出版週刊》,233、234期,1937年5月15日、22日。
(14)(30)(32)(33)(43)(47)馮友蘭:《馮友蘭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501、501、497、4~5、501頁。
(15)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194頁。括弧中的話係馮友蘭所加。
(16)(36)(37)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2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9、9、9頁。
(22)胡適:《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上海:《教育通訊》,1947年第4卷第6期。
(23)馮友蘭:《中國哲學小史》,第81頁。杜威的原文發表於《新共和》(New Public),xxv卷,1920年,紐約,第188頁。
(24)(35)朱劍:《學術評價、學術期刊與學術國際化——對人文社會科學國際化熱潮的冷思考》,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
(25)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18頁。
(26)《學術期刊“走出去”:中國學術國際對話的橋樑——訪〈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主編斯科特·斯洛維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12月14日。
(27)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姚小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0、70~71頁。
(28)竹內好:《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第192頁。
(29)(51)鄒詩鵬:《“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國際化”的質疑與反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3月18日。
(30)趙元任:《趙元任全集》,第8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7頁。
(34)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一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第102頁。
(38)(52)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第285頁。
(41)陳寅恪“挽王靜安先生”詩中有“文化神州喪一身”之句。
(42)馮友蘭在寫《新理學》時,金岳霖也在寫一部哲學著作,他們的主要觀點相同,但馮友蘭是接著程朱理學講,而金岳霖是西學的脈絡,於是馮友蘭說:“我是舊瓶裝新酒,他是新瓶裝新酒。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並且創造了一些新名詞。”見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5頁。
(44)胡適:《胡適選集》,“雜文”,台北:文星出版社,1966年,第17頁。
(45)胡適:《胡適文存》,三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26頁。
(46)汪榮祖:《學人叢說》,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99頁。
(48)參見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8頁。
(49)參見汪榮祖:《康章合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22頁。
(53)張政文:《差異中的共生與共生中的差異——走向世界的中國學術道路與價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3月22日。
(54)(57)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2、40頁。
(55)王國維:《王國維文集》,第3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71~72頁。
(56)王元化:《胡適的治學方法與國學研究》,北京:《讀書》,199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