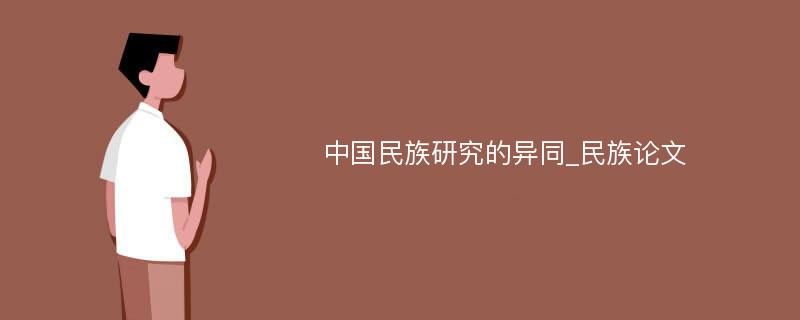
中国民族研究的识异与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文献关于不同民族的记载,其由来非常古远。以近代学科形态出现,则1902年梁任公《新史学》、1906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及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已越来越明确民族史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民族学自19世纪中叶在欧美形成学科,1903年,林纾、魏易即将德国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t)的民族学由英译本译成中文,书名《人种学》,交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中国正式使用民族学的名称从1926年蔡孑民先生发表《说民族学》到现在也有70年。当前,在中国大陆,将研究民族问题诸学科,统称为民族研究,已成为一个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族问题理论、民族经济等诸多学科的学术部门。
这是中国民族问题所占重要地位决定的。
1949年以后,民族研究在中国海峡两岸不同的环境中发展。回顾大陆上民族研究的总体情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50年代。当时是以民族识别为中心,进行了广泛的访问、调查和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完全废除历史上遗留的民族压迫制度,制定和推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这就需要识别和确定到底有多少民族。据1953年统计,全国各地所报自称或他称有四百多个,经过50年代的识别,以后60-80年代又依据新的调查材料,确定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除汉族以外,其他五十五个兄弟民族称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指人口数量与汉族比较居于少数,政治权利无论人口多少,各民族一律平等。
民族识别工作,一是区分汉族和少数民族;二是区分是单一民族还是同一民族中具有不同地区性或其他特殊从业、生活方式等特点的人们群体(台湾学术界称为族群);三是要确定各民族为大多数人民乐于接受而且较为科学的名称。
这是一项政策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工作。因为中国是个很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地域广大,民族众多,语言多样,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要把民族识别的工作从理论到实践都解决得非常圆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依愚所见,民族识别工作的主要成果,是确定了当代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这样才能顺利推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全面开展民族工作。在科学上和理论上,坚持民族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古代某一英雄人物或氏族、部落简单的血缘延续。各民族有共同的历史,却不一定是单一的来源。事实上,在中国这样有数千年民族共处历史的国家,不可能有单一来源的民族;必然是以古代某一族体为核心,在发展中涵化吸收了不同来源才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某一民族。在科学研究方面,依据各民族的客观实际,确定其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形态、族体特点,但在民族识别上,则凡有民族认同要求,并具备确定为单一民族的条件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确认的,一律称为“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
上面我只能简单陈述一孔之见,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则有黄光学、施联珠两位专家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民族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和该书所收录费孝通、林耀华两位教授的专论,可供参考。
第二阶段,自1958-1965年,以对少数民族的族别研究为主,中心是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特点,并且结合文献、研究各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同时进行了最广泛的民族语言调查。此项规模浩大的调查研究,1956~1958年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主持,当时从专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抽调了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和学生组成八个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分赴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区对二十个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调查。1958年以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改由国家民委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具体事务由民族研究所主持,调查组由原有八个增至十六个,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分布较集中的省区进行调查研究,人员最多时调查组人员达到千余人,其中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和民族学系的前身)参加调查的师生达二百四十余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953年开始试点到1956年形成八个调查组,1958年形成十六个调查组前后所获资料三百四十余种,总计三千万字左右,此外还有大量文物、照片和民族学电影片。在此基础上,由国家民委主持编纂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到目前“五种丛书”已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一批研究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族别史、族别风俗志及语言文字与文化的专著。对少数民族族别研究的深入和推进,也促进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其它各相关学科的发展。
第三阶段是1978年到目前。这一阶段以地区民族研究、民族关系研究的发展较突出,汉民族研究的课题也提到了日程上来。在这些综合性研究进行相当进展的条件下,80年代末叶,及时提出了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的研究的任务,其中尤其是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发表以后,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研究引起了中国的两岸三地及国外学术界的关心与瞩目。当然,上面所说三个阶段只是就其突出的特点而言,并不是能截然分开的。实际上1978年以后,对各民族的族别研究仍在发展而达到较为成熟,族别研究的著作大多是在1978年以后成书。对中国各兄弟民族的族别研究,任何时候都是民族研究不可缺少的课题。
综上,除1966~1976十年“文化大革命”空前浩劫学术研究遭到破坏而停止以外,在1966年以前,大陆上的民族研究集中在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当前社会、经济、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等各个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着重点放在研究其区别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特点方面,换句话说,着重点放在“识异”上。在当时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古代虽然有记述边疆各民族的传统,积累了大量资料;30~40年代对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也取得了若干可贵的成果,但对于全面推行民族工作,贯彻民族平等、团结与区域自治的政策而言,古代与30~40年代积累的知识与资料,都显得非常不够用,必须通过艰苦、细致、全面的科学调查研究,才能为全面开展民族工作,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较为系统和科学的知识。这样的调查研究不仅对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有积极的意义,对提高各兄弟民族的自信心和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积极性也有重大的意义。深入地、科学地认识各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特点,也是促进兄弟民族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谅解、互助协作的必要条件。所以,民族研究方面的“识异”,不是使各兄弟民族越来越疏远,而是为促进各兄弟民族越来越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发展团结和互助提供必要的科学知识,为民族工作适应各民族历史、社会和文化特点,提供参鉴和决策的依据。所以不仅是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是具有广泛应用性的调查研究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民族研究学术界共同感到,重点放在对少数民族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调查与研究,在一定阶段上有必要,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弱点。这些弱点集中表现在不能很好地阐释各民族发展中的相互关系,不仅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包括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70年代末,有些学者反复撰文阐释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对中国、中国民族等范畴进行探讨,以中国如此众多民族、悠久历史、广大疆域如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为何会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而不是各民族分别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国家为中心,研究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的联系。1981年,在翁独健、白寿彝等老前辈的指导下,在北京香山召开了“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推动下,中国民族关系史、地区民族关系史、兄弟民族间的关系史以及民族关系的各个层面的研究工作十分活跃,每年都发表大量论文,而且80~90年代先后出版了通史体及地区的、民族间的关系史专著近二十部。80年代末开始的对中华民族整体性进行研究,是在以往族别研究、地区性综合研究、民族关系史研究已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进行的。1951年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曾发表《中华民族的发展》一文,实际上提出了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的任务,但由于当时缺乏族别研究、地区性综合研究和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础,对中华民族整体研究的任务提出来而未能得到推进。停顿了四十年以后,才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等著,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费孝通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中华民族研究初探》(陈连开著,知识出版社,1994)。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学会,先后召开过三次讨论会,均出版了论文集。四川重庆史式教授,联络台湾及新加坡和大陆一批学者,共同研究和撰写《中华民族史》,已出版一本论文集。
如果说族别研究着重点放在“识异”,那么地区性的民族研究、民族关系史研究、对中华民族整体的研究等,着重点就是放在“求同”。这个“同”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整体不可分割性、根本与长远利益的一致性、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共同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大认同与凝聚力等等,而不是人们主观上的虚构。对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挖掘、研究和阐释,就是“求同”。所以“求同”不是虚构“同”,而是把未能被认识的“同”通过调查、研究,反映与阐明清楚,成为民族的觉悟,或称民族的自觉意识。也可以说“识异”,是“求同”的学术基础,“求同”是“识异”的旨归。传统中国哲学较重视“相辅相成”却忽视了“相反相成”。实际上这两者往往在同一过程中相互作用。在民族研究上,如果我们不关心和重视各兄弟民族之“异”,当然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果看不见各兄弟民族间的“同”,也违背了中国民族发展的客观实际。在实践中,如果片面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忽视了各民族的特点与利益,或反过来片面强调民族特点与利益而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整体不可分割性与共同利益,都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必然给中华民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发展带来损失和挫折。这是近现代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笔者自知不学,然而为使命感所驱使,正在主编《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试图从中华民族整体的形成、发展过程及主要层面,作一个较为全面的叙述和论证。此书主要观点和基本学术构架,在拙著《中华民族研究初探》中已有所论证,其中错误与缺陷,希望得到方家与广大读者的批评,以利在即将成书的《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能有所提高。
大陆与台湾民族研究学术的接轨,已有一个可喜的开端。大家在相互接触中,深感到彼此多接触、了解、取长补短的必要。同时也感到,无论对学科名称、研究范畴,还是理论、方法和术语,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在彼此隔绝的不同政治环境中形成的,有些需要在学科接轨与整合中求同,使彼此能顺利交流、讨论,否则,各自所云、所指不同,无法达到交流的目的;有些是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同流派,彼此并存,争鸣竞长,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很想认真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可惜对台湾学术界的了解还刚刚起步,远不像台湾学者那样有较多来大陆的机会可以较全面而深入对大陆的学术界进行直接的了解,同时,台湾学界,与国外学术界接触较多,也是我们长期缺乏的条件。总之是学力有限,力不从心。最近十余年来,费孝通、李亦园、乔健等位教授,创造条件,使两岸三地学者在香港、苏州已举办过四次“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着重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讨论中国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诸问题。今年夏天,由费孝通教授倡导,中国两岸三地和日本、韩国几位人类学、社会学名家:费孝通、李亦园、乔健、中根千枝、金光亿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授课。这些活动和两岸关于民族史及民族研究共同探讨的活动一样,都充分表现了学术接轨中识异、求同的热忱和愿望。
我自知不学,最近几年才有机会拜读台湾学者一些论著,也有幸结识学界同仁,亲自领教。但究竟了解肤浅,可能有些言不及义。但初步接触中,深有感受,觉得求同的基础非常雄厚。
首先是两岸学者,都发自肺腑,认定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汉族占绝大多数,无论人口、文化、经济都是中华民族的主干,同时还包括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和众多少数民族结成的一个整体,中华民族的各个成员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兄弟民族。海外华人,大多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居住国的国民,有些仍是旅居海外的华侨。无论有居住国国籍的华人还是华侨,一般也都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海外发展的子孙。这种一个民族分别为不同国家国民的情况,在当代世界上并不仅仅中华民族如此。
其次,中国的两岸三地和海外华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烈的民族亲情以及振兴中华民族的愿望。两岸学界都怀着共同的使命感:通过自己的研究,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共同性,以促进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和在现代化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的振兴。
再次,我们高兴地看到台湾学术界所持有的客观与求实的严谨态度。在80年代以前对汉族以外的中国各民族称为边疆民族,主要是指文化上有别汉族的各民族。1980年以后称汉族以外的各民族为少数民族。台湾的少数民族学者还提出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称为兄弟民族。实际上大陆在政策上称汉族以外各民族为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称当代中国各民族为兄弟民族。从此次与会学者的一些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学者对大陆少数民族的研究,其中包括大陆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都怀着浓厚的兴趣。杨嘉铭先生初步统计,主要是发表在近二十年的专书论文共六十种,从内容上加以区分,“其中一般性论著二十三种,以大陆为研究对象者二十六种,专门研究台湾原住民者十一种,三者比例为2.1∶2.4∶1”。
第四,我怀着很大的兴趣,希望了解关于台湾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或称本土化的讨论。作为一种近代学科,这些学科都是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或本世纪初叶传入中国。又都是上世纪在欧洲形成学科;本世纪,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有很大发展,并对这些学科的传播有世界性的影响。台湾研究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学者,大多有受欧美,尤其是美国专门教育的背景,有这些国家的高层次学位。他们运用所学来研究中国的民族、中国的社会,自然有其特长;在大陆,我们这一代在成长时基本上与外界隔绝,缺乏这种特长,此是我们深感所缺,需要补课的。可惜我们已迈向老年,补课也很有局限,于是鼓励年青一代不固步自封,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充实自己,取其所长,扬弃不适用的部分。另一方面,大陆上的学者,生活在各民族之中,接近研究对象,作了长期的实地调查,结合文献、考古、语言等方面资料,熟悉研究对象,有些方面的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已获取一些较为成熟的成果,这是大陆学者的优势与特长所在。如果两岸学者和衷共济,共同努力,取长补短,一定会在民族研究领域中,创造出有中国特点的新学科,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化,必然是世界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西方文化的附庸,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的模仿。它既不是洋装土货,更不是土装洋货,而是吸收了西方理论和方法并与中国国情及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出来的中国学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可能有一种完全国际化的文化,但可以期待一种与西方文化取得平等地位,并且与西方在现代化基础上交相辉映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我们的祖先以其灿烂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相辉映,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中华民族的子孙应该发扬祖先的传统,创造出现代文化去充实丰富人类文化的宝库。中华民族的民族结构有其特殊性和典型性,我们不需拿任何一种理论套用,却需要吸收各种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去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概括出新的理论和方法,以丰富世界民族学科的内容,从而使世界的民族学科更富于普遍性和科学性。长期以来,我从事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主要以历史学的方法,同时也吸收民族学、考古学、古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试图阐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其中的内在联系。台湾学者将这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称为科际整合。在此次研讨会期间,林恩显教授多次提到民族关系史研究,并建议大陆学术界在进行民族关系研究时,应吸收台湾学术界族群研究的理论。这是本人乐于接受的。记得前年,听李亦园院士介绍台湾学术界关于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的努力,有感成八行打油,曰:
西学中国化,自古有传统。唐僧不畏难,取经集大成。六祖灵根硕,本土立禅宗。两岸同努力,可期成大功。
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而不失民族特性,外来文化经过再创造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深信两岸共同努力在民族研究领域中创立的诸学科,既是中国的,又完全是可以与国际学术对应交流的,它们是中国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标签:民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民族学论文; 费孝通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人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