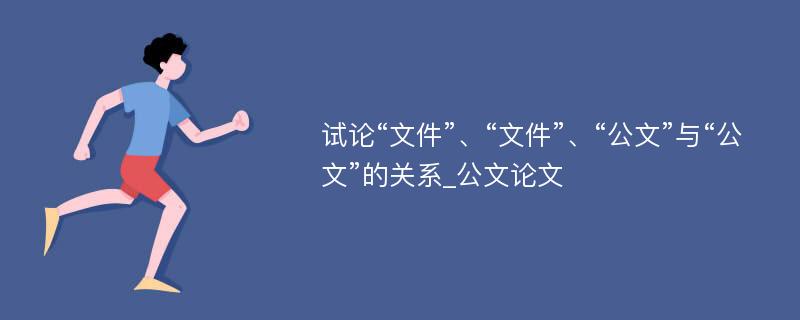
关于“文件”、“文书”、“公务文书”、“公文”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书论文,公务论文,公文论文,关系论文,文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件”、“文书”、“公务文书”、“公文”是文件学(由传统的文书学扩展而来)的基本理论概念。理顺这四个概念的关系对文秘工作、档案工作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档案界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众说纷坛,无有定论。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定,必然造成实际工作中使用的混乱。人们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名词概念时,他人究竟作何理解,全凭该名词当时所处的语言环境以及人们头脑中约定俗成的一般印象来确定。如何界定这四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不能再囿于传统的观念认识基础,而应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研究视野的拓宽,重新整合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此,笔者将它们之间的关系界定为:文件=文书〉公务文书〉公文
一
关于“文件”与“文书”的关系问题,档案界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但较有影响的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文件〈文书。如“文件——既包括各机关向外发出和收进的公文,也包括机关内部使用的文件。但不包括内部使用的其他书面材料,例如簿册、帐本、表格之类。因为人们并不习惯把簿册、帐本、表格之类称为文件,但它们仍属一种书面材料,毕竟也是一种文书。”(注:梁毓阶编著:《文书学》,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另一种认为文件〉文书。如“文书是文字的材料,是书面方式的文件。文件的范围很广,它可以用语言、图像等方式直接记录和传递信息,也可以用文字方式直接记录和传递信息。如用语言和图像方式记录信息的材料,我们可以称之为录音文件、图像文件,或合称为音像文件。文书必须是文字材料,它的概念范围较文件要小些,文书只是文件的一种。”(注:窦晓光主编:《文件管理》,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的不足之处,陈作明教授在《文书学若干问题的推敲》(注:载《档案学通讯》,1996年第1期。)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剖析,笔者也十分赞同他的结论:“文件”与“文书”应为同义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详细参阅该文)在此,笔者再作以下几点补充:
(1)“文件”和“文书”实为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如果“文件”和“文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则其内涵必然具有差异,亦即它们的本质属性必然有所不同,因为“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注:崔渭田主编:《形式逻辑》(修订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但谁都不会否认,“文件”也好,“文书”也罢,它们都是机关、组织或个人为实现特定目的(如沟通联系、记载事物、处理事务、表达意志、交流情况等)而制作的记录材料,它们的功能并无本质区别,它们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一样的。至于对这种记录材料,我们或称之为“文件”,或称之为“文书”,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一则“文书”、“文件”称谓的出现有先后之分,是先有“文书”后有“文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取代前者,而往往是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同时运用。如“文件标题”(先)和“文件题名”(后)、“文件作者”(先)和“文件责任者”(后)等等就是如此。二则,概念是由语词来表达的,“同一概念可以由不同的语词来表达”。(注:崔渭田主编:《形式逻辑》(修订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这在实际生活中是很普遍的。如“医生”、“大夫”、“郎中”三个语词表达的就是同一概念——以医疗为职业的人。“文件”、“文书”也是如此。
(2)文件(也就是文书,本文将它们作为同义词使用,下同)的外观形态——信息的记录方式和载体材料的演变并不会改变其本质属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文件的记录方式和载体材料也在不断改进,由文字的到图像的、声音的,由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到胶片、磁带、磁盘等,但这只意味着文件种类的增加,而不会触动其本质属性的改变。因为“文件”是一个普遍概念(类概念),它的外延包括所有种类的文件,而它的内涵则是揭示所有种类文件的共同本质。如果文件记录方式和载体材料的改变会导致其本质属性改变的话,则它不再成其为“文件”而应是另一种事物。(当然得另取称谓)如此看来,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将“书面方式的文件”(文件的一种)单独称之为“文书”。(叫“书面文件”或“文字文件”即可)如果“文书”的外延只能局限于文字方式的记录物而不能扩展到其他新生方式形成的记录物,那么,以数字代码记录在磁性材料上的新生记录物是否也应该撇开“文件”之名而单独另取称谓呢?而我们现在统称为“电子文件”(称“电子文书”亦无妨),因为“电子文件”仍然是“文件”,即符合“文件”的定义。其实,新的记录材料(不管其记录方式、载体材料多么新颖)只要它的内涵没变,就仍可纳入文件的范围之内。“文件”是不论其形式和载体的,这正如“人”的内涵是不论其种族、肤色一样。
(3)把“文件”和“文书”作为同义词,不会影响与国际“文件”概念的接轨。国外广泛使用的“文件”一词其实与“文书”并无多大区别,它的含义为“机构(公共或私人性质的)以及个人在处理事务、记载事物过程中形成的凭证性记录材料,包括政府机构及其它社会公共机构形成的文件,公私企业或商行的文件,以及家族、个人的私人文件等,如政府管理文件、国会文件、会计文件、投标文件、商业信用单据、汇兑凭证、有价证券、毕业证、日记、感谢信、照片、音像文件等等。”(注:杨霞:《论文件的概念》,《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1期。)只不过在译成中文时,囿于对“文书”一词的传统的狭窄的理解——“书面方式的文件”而选用了“文件”一词。如国际档案理事会所编的《档案术语词典》中有关的词汇(英文:Document,法文:Document,荷兰文:Document,德文:DoKument,意大利文:Documento,俄文:доКуМеНТ,西班牙文:Dcumento)在中译本(注:丁文进、何嘉荪、方新德、许士平编译:《英汉法荷德意俄西档案术语词典》,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中全部对译成中文的“文件”一词。其实,笔者认为译成“文书”亦无不可。
“文件”和“文书”作为同义词,其含义可以如陈兆祦教授所揭示的:“文件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为了相互联系、记载事物、处理事务、表达意志、交流情况而制作的记录材料。”(注:陈兆祦:《在山西省和太原市直机关企业单位档案干部大会上的学术报告》,《山西档案》,1986年第3期。(顺便提及,他在《档案学通讯》1987年第2期上发表的《再论档案的定义——兼论文件的定义和运动周期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文件和文书没有什么差别”。)
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大家一致同意上述“文件”含义的表述,但在具体运用“文件”概念时仍会出现分歧。这主要是由于“文件”在我国档案界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所致。狭义的文件仅指现行文件,即正在使用的文件。广义的文件则指文件在整个运动过程(从文件的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中不论其价值形态如何的各种记录材料。广义的文件概念也就是所谓的“大文件观”。笔者是赞同这种“大文件”概念的,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解决许多档案学中的理论问题,如文件和档案的关系问题,档案是否全由文件转化而来(即档案中有否非文件成份),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文档一体化管理的问题,及至文件学和档案学的关系问题等。(笔者将另文阐述)
二
文件(也就是文书,下同)就其形成者和使用的活动范围来说,可以分为两部分——公务文件(也就是公务文书,下同)和私人文件(也就是私人文书,下同)。公务文件是机关、组织为公务活动需要而制作的记录材料。私人文件是个人、家庭、家族为自身事务活动需要而制作的记录材料。而我们以往的文书学教材中对公务文件和私人文件所下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如公务文件“是指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在处理公务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文字材料”,私人文件“是指个人、家庭或宗族根据自身处理事务的需要形成和使用的文字材料”。(注:松世勤主编:《文书学基础》(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且不言将公务文件和私人文件局限于文字材料范围之内不妥,就是将机关、组织或个人活动中使用的全部材料分别纳入公务文件和私人文件的范围之内也是不妥的。因为机关、组织在活动中使用的(自然包括收到的)材料中难免会有私人文件,如个人寄给单位的意见、建议等信件而为单位采纳或个人就有关问题向单位提出的申请、申诉等材料为单位受理;个人活动中使用的(自然也包括收到的)材料中也难免会有公务文件,如单位发给个人的证书、奖状等或单位发给个人的有关申请、申诉的答复材料。如此交叉重叠,不仅有违逻辑规则,而且有损定义的科学性。
值得研究的是,由于机关、组织在公务活动中使用的文件既有公务文件又有私人文件,个人、家庭、家族在自身处理事务活动中使用的文件既有私人文件又有公务文件,因而机关、组织反映自身公务活动的档案(姑且称为“公务档案)中自然会包含有一些私人文件,相应的反映个人、家庭、家族活动的私人档案中亦会包含一些公务文件。可见,公务文件与公务档案、私人文件与私人档案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一对应的转化关系,即公务档案并非全由公务文件转化而来,私人档案并非全由私人文件转化而来。这正如单位的档案并非都由本单位制作的文件转化而来,也包含有单位收到的外来文件一样。(但并不能由此推断:档案并非都由文件转化而来)(注:档案是否都由文件转化而来,或者说,档案中有否非文件成份,是近来档案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笔者坚持认为,档案都是由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中并无非文件成份。笔者与何嘉荪教授合作的《论文件运动的特殊形式——跳跃与回流》(载《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3期)一文中对此已有所认及。)这是由于区别公务文件与私人文件是以文件的形成者(作者)及该文件的应用的活动领域(是公务活动还是私人事务)为根据的,而区别公务档案与私人档案是以档案的形成者(是机关、组织还是个人、家庭、家族)为根据的。这有点类似于一全宗档案与另一全宗档案的区别是以档案形成者(立档单位)为根据的,它们可能包含有相同的文件,如上级机关的重要普发文件、相互之间商洽重要问题的来往函件等,但由于立档单位(将文件作为档案保存的行为的实施者)不同而分别划归不同的全宗。
三
长期以来,我国许多文书学教材一直将公文作为公务文书的简称来对待。笔者以为公务文书简称为公文实乃一种字面的苟简,极为不妥。“公务文书”与“公文”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不同,外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许多文书学教材将公文的特点概括为:公文必须由法定的作者制成和发布,具有法定的权威和效力,有特定的体式和处理程序等。显然,公文的这些特点不是所有公务文书都具备的,如有的公务文书根本不是由法定作者制成和发布的,有的公务文书并无严格的体式要求,有的公务文书并未经过正规的处理程序。如把不完全符合公文特点的公务文书也列入公文的范围,则很难自圆其说。其实,笔者以为,从量上来说,公文只是公务文书中的一部分;从质上来说,公文应是“价高质优”的公务文书。从具体的严格意义上说,公文应是指由有关公文法规专门规定的、具有标准格式的公务文书,(注:目前关于公文的定义也有许多种,尚无定论。即使同意公文只是公务文书的一部分,但公文到底具体指哪些公务文书,也有不同的认识。)如《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关公文处理条例》等公文法规规定的公文文种。只有这样的公务文书才能充分体现目前已被公认的那些公文的本质特点。当然,究竟如何给公文下一个科学的定义,我们仍然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其前提是必须弄清公文和公务文书两者之间的关系。“公文=公务文书”与“公文〈公务文书”两者比较,笔者认为后者的界定较前者更为科学合理。因为如果将两者的关系界定为前者,那么我们就无法将公务文书中具有特殊价值、特殊意义、尤其应该引起重视和研究的部分单独划分出来。以往也有人将这部分公务文书称之为“文件”,但其不足之处十分明显。因为“文件”的概念早已有了发展变化,这在本文前面已有阐述。其实,从有关公文法规名称的改变中也可略见端倪。如《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文件处理条例(试行)》(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后来改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1996年5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说明这儿用“公文”比用“文件”一词更为科学合理。这从革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本文的一些观点。
标签:公文论文; 文书论文; 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论文; 公文文种论文; 档案学通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