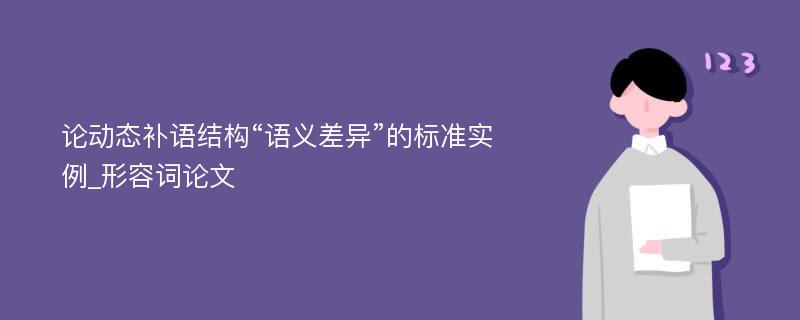
动补结构“语义差”标准例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结构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古汉语动补结构的判别标准问题一直困扰汉语史界,由此而牵连到动补结构起源的时代以及先秦两汉一批动补结构疑似之例的判断,动补结构起源的早出派与晚出派所认定的动补结构起源的时间竟然相距逾千年。
我们认为,动补结构起源等问题的讨论很有必要回到学术研究的原点,即对“动补结构”这个概念的定义的讨论上来。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判别古汉语动补结构的“语义差”标准,这里将继续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太田辰夫(1987:196)、梅祖麟(2000:222-246)、蒋绍愚(2000:250-251)等先生曾经试图通过分析“V死”对“V杀”的替代这个典型例证来论证动补结构的判别标准和起源时代,使得该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诸位先生这种注重解剖个案的研究方法具有强烈的实证性和科学性,实在是值得提倡的,因比,本文的讨论将循着先贤大家开辟的研究思路,从剖析一些汉语史界有代表性的疑难例子入手,来探讨汉语史上动补结构的生成机制,故谓之“例说”。
一、判别动补结构“语义差”标准的意义
1.1 动补结构判别标准诸说要点
王力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就从形式和意义两方面来认识动补结构,我们此处引述后来成书的《汉语语法史》(王力,1989:262)的说法:“使成式……从形式上说,是及物动词加形容词(如“修好”、“弄坏”),或者是及物动词加不及物动词(如“打死”、“救活”);从意义上说,是把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用一个动词性词组表达出来。”王先生的这个说法具有真知灼见,后来论者的思路大多不出这个范围。我们将各家研究的要点综合如下:
1.1.1 王力先生关于动补结构的定义和条件规定:作上字的必须是及物动词,作下字的必须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王力在《汉语史稿》(1980:403)的注中对此特别作了说明,明确表示“现在我以为使成式的第一成分应该限于外动词”。
1.1.2 梅祖麟先生对动补结构起源的研究是从个案分析入手的,在王力、太田辰夫等人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梅先生(梅祖麟,2000:230)判别动补结构的标准有4点,现引出第1、2点。
Ⅰ动补结构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复合动词。前一个成分是他动词,后一个成分是自动词或形容词。
Ⅱ动补结构出现于主动句:施事者+动补结构+受事者。
梅先生用“V死”对“V杀”的更替作为形式标准之一来判断动补式产生的年代,他因此还归纳了“V杀”、“V死”可能出现的四种句型(梅祖麟,2000:223)。梅先生特别看重丙型句:(丙)施事者+V死+受事者,并以丙型句在西汉尚未出现为理由,认定动补结构在汉代尚未产生。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文献材料来看,“V死”在汉代没有丙型句可能是符合事实的,但能否以此作为判断动补结构出现的形式标志似应另当别论。
1.1.3 蒋绍愚先生(2000:240)主张动补结构的下字必须“虚化”,他说:“有很多动结式‘VI+V2’是由动词并列式‘VI+V2’发展来的。”又说:“如果V2是他动词,或者是用作使动的自动词和形容词,和后面的宾语构成述宾关系(包括述宾和使动宾语的关系),那么这个结构实际上是并列式。只有当V2自动词化或虚化,或者自动词不再用作使动,和后面的宾语不能构成述宾关系,这才是动结式。”蒋绍愚先生(2000:244)因此把是否存在逆序形式(AB,BA)作为一个判别动补结构的重要依据。不过,其理由是什么,蒋先生没有详论。
1.2 规定动补结构的上下字必须为“他动+自动/形容词”也好,下字必须虚化也好,以上诸先生都是担心把动补结构与连动或并列结构混淆起来。这种良苦用心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为动补结构附加这些条件的意图却使问题遇到更多麻烦:
第一,某字作动补结构的上字抑或下字,并非一成不变的,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情况:某个他动词可以作动补结构的上字,有时也可以作动补结构的下字,某个自动词可以作动补结构的下字,有时却也可以作动补结构的上字,以太田辰夫、梅祖麟先生都特别重视的“死”字为例,“杀死”之“死”或许可以认作“自动”,符合“上他下自”的格式,但到了“死掉”里,“死”又变成上字,而“掉”却反而是他动,那么按“上他下自”的格式,我们是否该说“死掉”不是动补结构呢?显然不能,因为“死掉”可以扩展为“死得/不掉”,是典型的动补结构,但这个结论又与“上他下自”的格式不相符。可见,动补结构的上下字与他动、自动并无关系。
第二,“虚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漫长的历史过程,究竟虚化到何种程度才算具备作动补结构下字的资格,这个节点如何把握,实在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况且,作动补结构下字的词未必都有虚化的过程,如“看见”之“见”,从古至今都未虚化,并不妨碍“见”作补语。可见,是否虚化与动补结构也没有关系。
1.3 有鉴于上述动补结构判别标准的难以客观化的不足,我们认为,判别动补结构应该从上下字关系着眼,而不是孤立地关注上字或者下字是否及物与虚化。我们通过对动补结构上下字关系的考察发现:动补结构上下字的语义之间存在一种语义落差——上字的行为动作性质往往强于下字,下字的状态结果性质往往强于上字,无论V+A的动结式,还是V1+V2的动结式或者V1+V2的动趋式莫不如此。各类动补结构上下字的动作性“语义差”可以归纳为一个序列:
行为动词>状态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注:此处的“行为动词”、“状态动词”是为了简明起见的提法。“行为动词”实际上包括了一般所谓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包括了一般所谓结果动词。状态结果动词不排除也有一定的行为动作性质。)
在这个动作性语义序列里,越接近序列的左端,动作性越强,反之越弱;越接近序列的左端,越有资格充当动补结构的上字,反之就充当动补结构的下字。
我们不妨依据这个设想重新考察一下汉语史上的几个颇具争议的例子。
王力先生曾经讨论过先秦时期的一个动补结构疑似之例:“助长”。《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王先生以为“助长”不是动补结构,而是兼位名词的递系式(兼语结构),其理由是这段文字“只有一个‘助长’,其余都是‘助苗长’、‘助之长”’(王力,1980:404)。我们赞成王先生的结论,但理由与之不同。我们认为,《孟子》的“助”和“长”都是行为动词,“长”是“生长”义,“助长”之间没有语义差,类似于“帮助干活”、“领跑”、“进行革新”、“请吃请喝”一类结构。但现代汉语的“助长”是动补结构,如“你这样做只会助长歪风邪气”。因为其中的“长”意思是“增加、增多”,是“助”的结果。王力先生还讨论过《左传·成十三》:“扰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中的“扰乱”(王力,1980:404)。周迟明(1957)认为“扰乱”是动补结构。王力认为“扰乱”是用同义的词素构成的双音词,理由是《诗经》有“乱我心曲”的句子,“乱”用为动词,是所谓“使动用法”。我们认为王力的结论是对的,但原因并不在“乱”是否为动词,而在“扰”字上。先秦时期,“扰”也是“乱”的意思,如《国语》:“国乱民扰,得国在乱,治民在扰,子盍入乎?”因此,“扰”、“乱”之间不存在语义差。但到了后世,“扰”的行为动词性质增加了,义为“扰动,搅动”,“乱”的形容词性质增加了,义为“混乱,纷乱”,“扰乱”之间出现语义差,这时的“扰乱”才是动补结构。
1.4 我们提出的动补结构“语义差”标准,至少有以下优势:
其一,可以较好地解释动补结构的语序问题。
蒋绍愚先生认为,存在逆序形式的词语不是动补结构。这有一点道理,但不是绝对的,并列结构固然可以逆序,但可以逆序的不一定不是动补结构,这要看逆序以后两个词或语素的语义和语法关系是否改变,例如,状中结构逆序后就常常变成动补结构,如“回收→收回、晚来→来晚、极好→好极”之类都是例子;有些并列结构逆序后也可变成动补结构,如“开放”是并列结构,“放开”是动补结构;有的连动结构逆序后也会变成动补结构,如“开走”是连动结构,“走开”是动补结构。所以,是否可以逆序用于判别动补结构基本上是无效的。
动补结构之不能逆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动补结构上下字存在语义差,并列结构前后字之所以可以逆序,那是因为不存在语义差。有的词语逆序后,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上下字的关系也随即发生改变,在“开放”里,“开”和“放”都是“打开、放松”义,是结果动词,因此“开放”是并列结构,而在“放开”里,“放”是“放松”义,“开”是“离开”义,上字“放”与下字“开”存在语义差,所以“放开”应该认定为动补结构;在“开走”里,“开”是“开始”义,“走”是“行走”义,所以是连动结构,在“走开”里,“走”是“行走”或“离”义,“开”是“距离拉大”义,是“走”的结果,所以“走开”是动补结构。
其二,可以有效地规避“虚化”、“及物”问题。
“虚化”是历时平面的概念,而对动补结构的判别是共时平面上的问题,我们判断一个结构的性质时,只要考察该结构在某一历史节点上的上下两字即时的语义特征即可,无需过多考究它们的历史身份。如:“看见”和“看望”,前者是动补结构,后者是并列结构,尽管“看见”之“见”没有虚化,但“见”是结果动词,而“看”仅仅是行为动词,“看”、“见”之间存在语义差,所以“看见”是动补结构;“望”虽然虚化,义为“拜访”,但仍是行为动词,在“看”、“望”之间不存在语义差,所以“看望”不是动补结构,而是并列结构。
当然,行为动词与状态动词或形容词之间是会互相转化的——这就不仅是“虚化”问题,有时甚至是“实化”问题,这为我们判断动补结构造成了一些麻烦,如“热”原本是形容词,后来也有他动的用法,如“用炉子把饭菜热一下”。诸如“热透”一类的结构,究竟是什么结构呢?这就不是“虚化”所能解释的了。但如果从语义差的角度来认识的话,就可以减少一点困难,历史上有一些原来的并列式结构,由于上字在后来的发展中行为动词化了(如“扰乱”中的“扰”),或者下字状态动词化、形容词化了(如“助长”中的“长”),那这个结构就很容易变成动补结构。“热透”中的“热”变成一个状态动词,而“透”还是一个形容词,“热透”存在语义差,因此是动补结构,这可以用“热得/不透”来检验。由于我们对某一历史断面上的词语可以对其行为动作性质或状态性质进行精确的语义描写,因此,在判别动补结构时比较有客观性,这样一来,某个词时而作上字、时而作下字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另外,由于语义差理论关注的是结构内部上下字的关系,下字或整个结构是否及物(包括下字是否有“使动用法”)这些难以统一解释、令人困惑的问题也可以忽略了。
二、以“澄清”为例讨论动补结构的语义差
这里,我们以“澄清”由并列结构变成动补结构的过程为例来讨论动补结构的语义差问题。
2.1 柳士镇先生(1992:312)认为“澄清”在魏晋时期已是动补式了,他举了《世说新语·德行》的例子:“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他还举了同书中“隔开式”例子:“澄之不清,扰之不浊。”蒋绍愚(2000:254)也肯定了《世说新语》中“澄清”为动补式的说法,其根据是“清”在该书中“没有用作使动”的(注:蒋先生的理由难以接受,我们认为下字是否有“使动用法”与动补结构的判别没有关系。即使魏晋时期“清”没有“使动用法”,但现代汉语“清”却肯定有“使动用法”,如“清嗓子”,那我们也不能说魏晋的“澄清”是动补结构而现代汉语的“澄清”反而不是动补结构。)。
如果依据蒋绍愚先生用是否存在逆序形式来判断是否动补结构的条例,那么只能说《世说新语》的“澄清”还不是动补式,因为在与《世说》时代相近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大量“清澄”的用例:
(1)吴国勤任旅力,清澄江浒,愿与有道平一宇内。(《三国志·吴书十二》)
(2)(刘向)经深涉远,思理则清澄真伪,研核有无。(《抱朴子》卷2)
(3)虽有发觉,不务清澄。(《后汉书·郭陈列传》)
(4)水清澄,醴味,汲引不穷。(《宋书》卷29)
(5)出梅,令汁清澄。(《齐民要术》卷9)
(6)清澄后一月,接取,别器贮之。(《齐民要术》卷8)
据我们对文献的调查,“清澄”的例子最早见于《楚辞》:
(7)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远游》)
汉代也可见个别用例:
(8)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若光耀之间于无有。(《淮南子·俶真训》)
(9)超纡谲之清澄。(《汉书·杨雄传》)
不过,例(7)-(9)都是形容词的用法。例(1)、(2)、(6)是肯定的动词用法,但若据此下结论说“澄清”一定不是动补式则为时尚早。
2.2 我们来考察一下“澄清”的情况。据所见资料,最早的“澄清”用例见于汉代的《太平经》,其后还有很多用例,现罗列于下:
(10)澄清大乱,功高德正,故号太平。(《太平经·甲部》)
(11)允以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后汉书·陈王列传》)
(12)(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汉书·党锢列传》)
(13)事务澄清,天下狱讼察以情。(《宋书》卷22)
(14)水犹澄清,洞底明静,鳞甲潜芷,辨其鱼鳖。(《洛阳伽蓝记》卷1)
上述例子中的例(11)、(13)、(14)的“澄清”是形容词,例(10)、(12)的“澄清”是动词用法。但是用作动词的“澄清”不一定就是动补式,因为和“清”一样,“澄”最初也是一个形容词,例如:“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管子·轻重乙》)/“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礼记·礼运》)/“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饮”(《淮南子·精神训》)。正因为如此,“清澄”也可以带宾语,如“原赦莹罪,哀矜庶狱,清澄刑网,则天下幸甚!”(《三国志·吴书十三》)/“清澄朝位,旌叙俊。”(《国志·吴书二十》)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更有“澄清”、“清澄”互用的例子:“欲清澄邪恶者也。”(《悲回风》)又:“已欲澄清邪恶,复为谗人所危、俗人所谤讪之。”这种带宾语的“澄清”、“清澄”可以视为并列式动词。
2.3 “澄清”究竟是如何演变成动补结构的,则要考察“澄”如何由形容词演变成动词,并且携带表示结果的成分。下面是我们所调查的“澄”带宾语的情况:
(15)通于治乱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终始,可谓知略矣。(《淮南子·泰族训》)
(16)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略)。(《论衡·薄葬篇》)
(17)顷连雨水浊,兵饮之多腹痛,令促具罂缶数百口澄水。(《三国志·吴书六》)
(18)澄其源者流清,混其本者未浊。(《后汉书·郎觊传》)
(19)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后汉书·黄宪传》)
(20)属箕伯以函风兮,澄而为清。(《后汉书·张衡传》)
(21)明公启晨光于积晦,澄百流以一源。(《世说新语·文学》)
(22)夷胥山之险,澄瀚海之波。(《宋书·后废帝纪》卷9)
(23)澄四海,清三光。(《宋书》卷20引晋傅玄《羽龠舞歌》)
(24)澄瀚海之恒流,扫狼山之积雾。(注:《南齐书》(《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点校本)“瀚海”作“澣渚”,今据《艺文类聚》校改。)(《南齐书·王融传》卷47)
(25)研尽,以杞子就瓮中良久痛抨,然后澄之,接去清水。(《齐民要术》卷5)
(26)用驴乳汁二三升,和马乳,不限多少。澄酪成,取下淀,团,曝干。(《齐民要术》卷6)
(27)易器淘治沙汰之,澄去垢土,泻清汁于净器中。(《齐民要术》卷8)
(28)率一石水,用盐三斗,澄取清汁。(《齐民要术》卷8)以上为自汉至魏晋“澄”作动词所见文献及若干典型用例。两汉时期仅有(15)、(16)寥寥二例(注:据《初学记》等书,东汉张衡《髑蝼赋》有“澄之不清,浑之不浊”的句子。但正史并无此记载,故此例存疑。),这或许还可以用形容词临时的“使动用法”来解释。到了魏晋时期,“澄”的动词用法呈现了若干前所未有的特点:
第一,例子大量增多,这从我们列举的书证中可见一斑;
第二,不仅出现在骈体文中,也出现在散文特别是口语化的作品中,如例(17)、(19)、(25)-(28);
第三,魏晋时期的“澄”后所带的宾语绝大多数都是具体名词,相应地,动词“澄”的动作性也较强,这又与两汉“澄”后都是“心意”一类意义虚灵的宾语不同;第四,“澄”与表示结果的形容词、动词共现于某一语境,“澄”仅承担行为动词的语义,意为“使液体中的物质沉淀”,侧重表示造成某种结果的原因,例(19)的“澄”与“清”,例(26)的“澄”与“成”,例(27)的“澄”与“去”,例(28)的“澄”与“取”。其中例(27)的“去”、例(28)的“取”也是“澄”的补语。
2.4 鉴于以上四个特点都发生在魏晋时期,我们因而得出结论:魏晋时期的“澄清”已经可以认为是动补结构了。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再举几个魏晋时期佛典中的例子:
(29)置余众生五无间罪四重禁法浊水之中,犹可澄清发菩提心,投一阐提淤泥之中百千万岁不能令清起菩提心,何以故?(《大盘涅盘经》卷2)
(30)譬如净水珠,澄清诸浊水。(《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4)
(31)譬如水珠置浊水中,水即澄清。菩提心珠,亦复如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卷59)
例(29)上文用“澄清”,下文用“令清”,表明“清”是“澄”致使的结果;例(30)上文“净”是所谓“使动用法”,下文“澄清”是动补式;例(31)“水即澄清”是“澄清浊水”变换后的受事主语句。
“澄清”发展至唐代,出现了可能补语的否定式:
(32)自古澄不清,环混无归向。(《韩愈集·古诗·岳阳楼别窦司直》)
2.5 小结:“澄”和“清”原本都是形容词,可以构成并列式双音词“澄清”、“清澄”,二词既可作形容词,也可作动词。“清澄”带宾语时并不是动补式,后世也没有演变成动补式。“澄清”从汉代始就有带宾语的用例,如例(10),但汉代的“澄清”还不是动补式,此时的“澄”主要仍是形容词用法,用为动词的例子还相当少,只能说东汉时期的“澄”还处在从形容词向动词的过渡阶段。魏晋时期“澄”有了大量的作典型动词的例子,已经完成了由形容词向动词的转化,此时的“澄清”才可认作动补式。虽然魏晋时期仍然有逆序词“清澄”存在,也有作形容词的“澄清”,但都不妨碍一部分“澄清”已经变成动补式了。
三、结论
我们将上文讨论的问题梳理为以下几点结论:
1.动补结构的上、下字可以是自动词,也可以是他动词,因此,动词的及物性与动补结构无关;作动补结构上、下字的词语在历时演变中可能发生虚化,也可能不发生虚化,因此也不能根据是否虚化来判别动补结构,虚化是历史演变的概念,我们判断动补结构,应该从某一历史横断面上来衡量。
2.我们认为,判别动补结构的意义标准是上、下字之间的语义差,亦即:上字的行为动作性质强于下字,下字的状态结果性质强于上字。各类动补结构的动作性语义差可以归纳为一个序列:
行为动词>状态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
按这样的序列组织的动补结构,上、下字是不可逆序的。
3.“澄清”由原来的并列结构演变为动补结构,其演变机制是:“澄”在汉代时还是一个典型的形容词,而后逐渐有了动词的用法(所谓“使动用法”),到了魏晋时期,变成了一个典型的行为动词,义为“沉淀,使水清洁”,这时“澄清”就变成了动补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