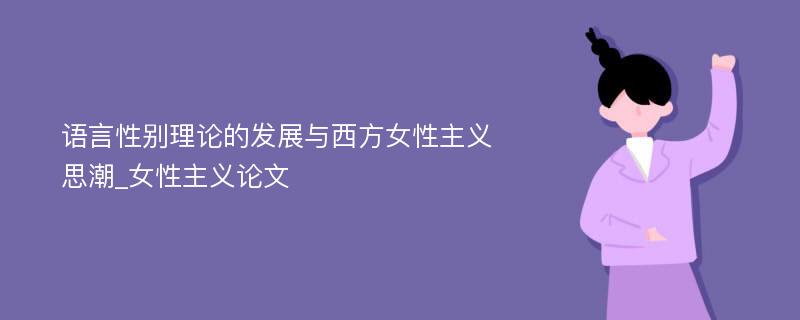
语言性别理论发展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性别论文,理论论文,语言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性别语言可以追溯到公元1664年。[1]一直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对语言性别的研究还只是零散的讨论或个人的观察和体会。20世纪60年代中叶,随着社会语言学的诞生以及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的鼎盛发展,特别是当时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对性别语言的研究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语言性别研究与席卷欧洲的妇女解放运动联袂而行,进入自己的理论发展阶段并与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于考察角度不同、观察视野互异、研究的内容有别,有关语言性别的理论林林总总、十分繁杂。本文将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结合社会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归纳表述,并探讨其与女性主义理论思潮发展的关系。本篇采取确立主干理论和合并同类项的方法将各种相关性别语言研究的理论加以归纳,共总结出六种理论学说:生物决定论、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社团实践论和表演论。这些理论基本上按时间先后顺序出现,其中有一些理论在实践上与其他理论并行交错,共同发展。
一、早期语言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
早期的语言性别研究主要可归纳为生物决定(biological determinant theory)论以及对两性语言各自特点以及语言中所反映的性别歧视的研究。生物决定论基于这样的假设:男性与女性有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生物决定的、天生的、上帝赋予的。这种观点渗透于整个西方父权制文化中。这种传统男权社会观念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代表。语言学家们也研究了男女双方由于发音器官的不同所造成的声学或语音学上的性别差异。在色觉感知方面,语言学家们的研究也表明,女性不但拥有一个更大的色彩词库,其色彩词库的种类与质量也往往优于男性。以生物决定论为基础从语言学角度进行性别差异研究的还有派克(Pike)、皮特森(Peterson)等人。[2]遗憾的是,除了一些尚未完全证明的假设之外,语言学家目前尚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说明语言性别差异现象同说话人的生理结构之间有何种必然联系。这些研究正好顺应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以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为主要特征,主要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反对性别歧视,要求对男女同样对待,强调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地位。从女性主义角度看,生物决定论单纯从生物性别的角度来界定女性经验,实质上是雷同化所有女性,因为生理性别仅仅是形成女性经验的纬度之一,只能提供女性多维现实的一维图景。性别语言研究中生物决定论的出现以及语言学家等对语言中性别歧视的发掘,也使女性主义者看到了女性受压迫的现实,这一时期的妇女从要求改善她们在就业、教育、政治和家庭中的位置出发,逐渐集中于为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19世纪20年代,全美各州通过了妇女选举权,英国也在1928年达到这一目标。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至此落下帷幕,并主要因政治环境的不利而一度消沉。
二、语言性别二元对立论与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
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政治气候出现,酝酿了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家和女性主义学者均承认两性差异的存在,因此这一阶段关于语言和性别关系的研究主要是语言性别差异理论或二元对立论的研究,主要包括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亚文化论。
缺陷论(deficit theory/deficiency theory)认为,语言反映社会规约,同时起到强化社会规约的作用。男女在语言使用上反映出的性别差异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在男权社会里,男人的讲话方式被视为标准和规范,而女人的讲话方式则被看作是对这种标准的违反和偏离,女人使用的语言被认为劣于男人使用的语言。这就意味着做女人本身就是一种缺陷,男人被置于优势地位,而女性被置于卑贱、他者地位。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罗斌·雷可夫(Robin Lakoff)。[3](P45-79)70年代初,她发表的Women's Place in Language一书开始了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新的里程碑。在该书中,她十分清楚地把妇女语言中的一些特点集合于“妇女语体”(women's style),指出妇女语体的音系、词汇和句法特征都表明妇女的语言具有从属性,属于“无力语体”(powerliess style)。她还认为女性特有的讲话方式在她们小时候就形成了,女性语言的缺陷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果。由于她的观察聚焦于妇女语体特征,微妙地强化了“男性标准”的假设。她研究语言性别差异的方法是直观假设法(intuitive hypothesis approach)或经验感知法(empirical and sensitive approach),这种方法导致了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比如关于女性语体为“无力语体”的假设在Crosby和Nyquist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了相反地证实。[4](P313-322)尽管她的其它许多假设不少被后来的语言学家的调查所证实,但总的来说,Lakoff对于性别语言的研究过于笼统,并且缺乏实际的语料和量化的分析论证,其学说因此显得苍白无力,最终缺陷理论就被支配论所代替。
支配论(dominance theory/power approach)盛行于70年代初80年代末,该理论是对早期缺陷理论的重新表述,把性别看作社会权力。按照这种学说的观点,男女性别差异是男人统治、压迫,女人从属、被支配的关系。男女在权势上的不对等最终导致了男女在语言交际中的不均衡现象。持支配论观点的学者有齐默尔曼(D·Zimmerman)、韦斯特(C·West)、[5](P105-129)费什曼(Pamela Fishman)[6](P89-101)[7]和斯宾达(Dale Spender)[7]等。在她们的调查研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女性与异性交谈时,她们更经常被对方打断,在选择的话题和话题量上也都受一定的限制。因此,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从谈话风格和策略上看,男性明显表现出很强的支配性。桑恩与亨利所编著的论文集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更加确认了“男性支配”对于语言性别差异现象形成的影响。[8](P105-129)支配论对性别语言的研究侧重于语言交际中的动态使用现象,研究成果建立在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此这种学说具有较强的说眼力。但该理论虽然对语境十分敏感,并很注重话语的“社会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 of the society”),但仍然建立在语言性别研究二元对立论的统一模式之上,这一理论暗含着一个男性统治的“笼统概念”(“blanket conception”of male dominance),即所有的男人统治所有的女人。[9](P134)这一笼统的概念很容易通过明显的例子被反证。需要指出的是,影响语言变异的因素很多,人们很难确定到底何种因素在起作用,来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在使用语言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替代支配论的另一个框架——差异论/亚文化论就应运而生了,它对语言性别差异提供了一个更加中性的解释。
差异论(difference theory/sub-culture model/cross-culture model or two-culture model)最早由马尔茨和博克(Maltz and Borker 1982)提出。[10](P196-216)该理论认为由于男女分别成长于不同的亚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但两种语言风格同样有效,并无优劣之分,只是反映了不同的交际亚文化。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坦嫩(Deborah Tannen)、卡梅伦(Deborah Cameron)和古德温(M·H·Goodwin)等人。[11][12]该理论的重点是社会化了的性别研究。有许多研究表明,男女学生在同性伙伴中习得了言语和非言语交流技巧。[13](P45-68)也有许多研究指出,儿时获得的言语技巧对成人之后的言语风格仍然有很大影响(Wodak,1986等)。[14]坦嫩发现,在语言交流过程中,男人谈话为竞争性的(competitive),喜欢引人注意,表现身份,充当领导;女人谈话则是合作性的(cooperative or supportive),注重与对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她称男人的谈话为“报道式谈话”(“report talk”),女人的谈话为“关系式谈话”(“rapport talk”)。[11]坦嫩认为,男人和女人堪称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环境的群体,就像来自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一样,他们生活和成长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使用习惯,而社会分工和人们的传统影响使之更加牢固。约翰·格莱(John Gray)的著作《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Women are from the Venus,men are from the Mars)也表述了与坦嫩相似的观点。像支配论一样,差异论也用了量化调查法,并且也同样受到交际人种志学的影响,研究结果具有相当的信度和科学性。但该理论只是反复强调了亚文化交际的影响,而忽视了“权力关系”和父权制的存在,因而未能表现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并且该理论也没有解释儿时的“性别类型社会化”,是如何产生的,[15]以及为什么男女应分属于不同的亚文化。[16](P8-26)该理论同样建立在男女性别两元对立论的基础之上,对男女言语交际风格做出了刻板式的描述,暗示每一性别都有一个单一的、固定的言语交际风格,然而两种性别的人很可能采纳彼此间的谈话方式。
上述这些理论都强调了语言性别差异的存在并分别从地位、权力和文化三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语言性别差异现象。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阶段,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平等论者的话(他们只是对平等的具体理解上有争议),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则展开了围绕平等/差异问题的大讨论,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们也都强调差异并讨论和探讨性别差异的根源和逻辑。第二次浪潮开始于女性主义自由派,但主要以女性主义激进派为代表,激进派又分为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时期,语言学研究正渗透到西方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女性主义者及时吸纳了这一股新兴的知识浪潮,对性别差异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马丽·沃尔斯通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抨击“女人缺乏理性”的男性中心论开始,到西蒙·波夫娃(Simone de Beanvoir)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这一反父权神话的宣言,代表了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要求打破父权论述中男尊女卑是生理差异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和缺陷论观点,她们接过启蒙主义“平等”、“自由”的旗帜,强调妇女与男性同样具有理性。[17]戈尔·卢宾(Gayle Rubin)指出男女权力不均是社会性别制度形成的,要求和男人一样具有教育、法律、职业等权利。[18]凯瑟琳·麦金侬(Catherine Mackinnon)主张在女性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国家法律体系,提倡以实用主义的方法解决现存机构里的不平等现象。如果说60年代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之初,在妇女运动的影响下,女性主义理论仍然注重揭示男女两性生物学上的差别以批判男性偏见。到70年代这种方法受到了批评,女性主义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注重分析妇女的被支配地位、社会性别角色以及女性的身份等问题。支配论所揭示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性别关系使激进派女性主义认识到父权制的社会关系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并认为这种关系建立在男人对女人的控制之上,于是同样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妇女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剥削形式联系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女性主义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妇女受压迫问题;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特别关注的是探讨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在当代社会中相互作用的方式;激进派女性主义则要从政治上彻底摧毁这种性别阶级体制。从70年代开始,以自由女性主义为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关注点从性别平等转向女性独特性和性别差异,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打开了思路。产生于80年代初的差异论/亚文化论使女性主义者看到女性并不从属于男性,女性语言也不劣于男性,一些女性主义者甚至认为女性优于男性。激进女性主义把女性独特的优越推向了极致,成为非常激烈地抨击父权制的理论流派。她们强调女性的独特经验以及女性内在经验的丰富性,褒扬女性的独特品质。而主流社会男性独尊,所以她们主张彻底革命,认为女性解放除了走分离主义的道路别无他途。还有一些激进主义者提出必须断绝同男人的性关系,甚至宣扬女性之间的爱情与性关系。卡梅伦(Cameron)评论道:“支配论和差异论代表了女性主义的不同时期。支配论代表了女性主义的愤怒时期,证明了女性在生活各方面遭受的压迫,而差异论则代表了女性主义的欢庆时期,反映了她们要求恢复和重新评价女性独有文化传统的呼声。”[19](P20)
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这种“转变话语”和“重估女性”的理论策略的确颇为令人振奋,但在一开始时很有用的“差异”这个观念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很多学者曾经深深地被差异这个观念所困扰,因为他们感到这样一个偏颇的立场会导致对社会性别的意义和关系的严重误读。白尼娜(Nina Baym)的文章认为,“当你从一种差异的理论出发,你除了差异外什么也看不到。”白尼娜对“差异”观念的质疑,对后期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W.Scott)发表的独创文章“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之际。该文对社会性别概念作了更深刻的界定:(1)社会性别是基于能观察到的社会性别差异之上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个成分”。(2)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运作。该文还严肃地质疑了固定不变的“男人”和“女人”的范畴。她感到,对社会性别差异的简化式理解,如卡洛尔·吉里根(Carol Gilligan l982)的关于女性的不同声音的理论观点所表现出来的,很容易加剧性别间的对抗局面,这与当今的社会是有害的。[20]琼·斯科特对于差异观念提出的批评被人们广泛引用,这样就对90年代建立一种新的性别理论起到了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旧的二元对立语言性别理论包括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都强调差异却忽略了相似性以及男女之间其它相互重叠的成分,因此都不够完美,都无法表现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因此一些学者提出统治关系和不同交际模式应该被整合到一种更为复杂的性别语言交际的解释框架中。[21](P461-490)于是有些学者提出了“性别连续体”模式(如,Bern,1995),又有些学者提出要超越交际框架中对男女两性对立的研究,从而对具体环境中的特定的妇女群体进行研究。[22](P98-125)人们还提出了言语社区、社会集团、社会网络等概念,并以此作为语言分析单位,其中以米尔罗伊(J·Milroy)提出的社会网络对语言性别的研究较有影响。[23]在应用社会网络对性别语言进行分析时,虽然避开了两分法,但该概念强调成员之间的数量,忽略了成员之间联系的质量,因此同样不足以说明语言性别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到了90年代,语言学家们在语言性别差异问题上不采取事先预定的立场和前提,从而使性别研究得以开放,突破了旧有的框架。
三、语言性别建构论与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后现代女性主义
90年代,面对全球化浪潮,语言性别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动态化、微观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趋势。语言性别建构论正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性别建构论主要包括两种理论:社团实践论和表演论。
社团实践论(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又称行为集团论,它汲取了言语社区、社会网络等概念的积极因素,但又有所创新,在解释语言性别差异的成因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将社会性别的建构视为一个社会过程,用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看待性别差异。社团实践论由社会学家魏恩(Lave Wenger)创立,然后由艾科特和吉奈特(Eekert & McConell-Ginet)首次将其引入了语言性别研究领域。
她们对行为集团定义如下:行为集团是由参与共同活动的人们组成的团体。他们所有的行为,包括行动方式、说话方式、信仰、价值观和权力关系都体现在对统一活动,即实践的参与过程当中。[24]根据魏恩的论述,社团实践的主要概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共同参与的活动、合作协商的计划和共享的可调整的资源。行为集团的形成并不以某一地域或某个群体的言语行为为标准,它以个人德行为尺度划分其归属: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的个体可以形成一个行为集团,言语行为只不过是人们共同的行为方式之一,它不再是形成集团的核心。行为集团将言语行为和社会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行为集团所关注的语言是作为行为的语言而不是作为符号的语言。
社团实践这一概念对语言性别领域的研究表明:(1)人们从事的活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性别,并使他们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语言和性别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它们通过不同的行为模式相互作用。例如,在教师行为集团和护士行为集团中男性语言带有更多的女性特征。与此相应,女政治家和女企业家的语言带有更多的男性特征。[25](2)在不同的行为集团中,同性之间的语言活动表现出更多的差异而不是类同;而在同一行为集团中异性的言语行为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3)在社团实践论中,个体的身份是由行为决定的,它不再是一个固定的范畴,这样就有可能将身份的多样性纳入视野,包括种族、阶级和年龄,藉此,它将性别语言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需要指出的是,在行为集团这一概念之上还应添加更广大的“社会”这一概念并意识到社会公共制度对社团及个人施加的压力。没有更大的“社会”这个团体的概念,就无法超越社团实践论去解释为什么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比另一些更能被普遍地、全球化地接受。这不是要重新确立诸如“社会”或其它一些早已被社团实践论摈弃的观念,而是要人们意识到法律制度、学校制度、教堂等公共制度对个人施加的压力及其所提供的可供个人采纳的、可能极具说服力的立场。特定的行为集团与更广大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它们往往相互冲突而不是相互肯定。
表演论(theory of performance)作为表演性的社会性别概念,由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她的批判性著作《性别麻烦》中引入。[26]她跨越了多年来一向处于两难中的“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的窠臼,超越了社会性别二元论,指出性别不是预定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征是靠表演决定的。男性和女性都被看作社会演员,服装、发式、举止就是表演的道具。他们在交际过程中表演着自己的性别,性别身份在表演过程中不断被协商,但永远没有终结。她认为,社会性别不是一个固定的身份,或各种行为所遵循的媒介位置,社会性别是一种在实践中不断建构的身份,通过风格化的重复行为在一个外部空间中得以构成。她还认为社会性别独立于生物性别而存。她甚至认为生物性别也是由社会和话语构建出来的。巴特勒的理论对语言性别差异有解体性的认识。
在研究语言和性别关系时,表演(performance)或表演性(performativity)是一个潜在的、有用的概念。从一些研究中很容易看出特定的讲话是如何被分析为不断重复的风格化行为的。例如,Kira Hall描述了电话性工作者如何使用风格化的语言(这常使人想起罗宾·雷可夫的女性语体)以表演她们认为顾客愿意购买的色情的和无力的女性气质。[27](P183-216)对语言性别中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探讨,原因之一是它承认语言使用的能动性,同时也为语言使用者留下了行动和创造的空间。语言学家们没有人把我们看作完全自由的行动者,但对于那些把讲话者看作像早年被输入了程序的机器人,只是机械重复适合于自己性别的言语行为的观点感到大为不满。她们认为哪怕是最主流的、最传统的性别身份都可以甚至必须被用不同的方式来表演。对表演论也有严厉的反对,因为,如果给了说话主体更大程度的能动性就意味着他们有更高程度的自由来否认性别和权力关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还是需要考虑性别被表演的公共环境和其所处的权力关系。
性别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t gender theory)既调节了支配论又调节了差异论,比传统理论更全面、更客观地揭示了语言性别差异,它对同性之间的差异和异性之间的类同的诠释更具说服力。正如Holmes所言:“社团实践论所拥有的理论特征和描述方法,有可能解决传统语言性别差异研究在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上面临的一些难题,有可能成为指导该领域研究范式的主干理论模式。”[28](P173-183)卡梅伦(Cameron)和Bing and Bergvall也号召女性主义学家使用巴特勒的社会性别观,把性别看作不断构建的、一系列的表演。[29](P945-973)[30](p1-30)
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融合,已经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从此进入女性主义第三次浪潮——后现代女性主义发展时期。后现代女性主义以解构为目的;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反对普遍化的、统一的宏大叙事;反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的存在;挑战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上帝的视角”;挑战静止的社会性别观。他们的这些观念正好与性别建构论的观念一脉相承,因为,一些性别建构论的语言学家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者,因此,性别建构论与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的关系当然密不可分。
一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反对谈论作为总体的、全球性的男性和女性的语言差异,主张把个人和环境如何相互影响交际的产生和进行作为关注的焦点(Troemel-Ploetz,1998;Bergvall et al.1996;Bucholtz,1999)。这一点与社团实践论相一致。还有一些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对“妇女”或“女性”这个过度概括的宏大概念以及妇女确定的身份提出质疑。朱迪斯·巴特勒就批评了传统女性主义的“女人接受男性压迫”的大一统理论,她认为,传统女性主义过分地自我中心化,把自身的经验当成全球妇女的普遍经验,“女性”应该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丹尼斯·赖利(Denise Riley)也指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一种身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社会的理想形象——男性的反衬。因为男性的标准不稳定,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产生不同的标准,因此女性的标准也是不稳定的、暂时的。另外,每一个具体的女人都与其他女人有不同的经验,因此广义上的女性经验就不成立。所以坚持追求女性权力就会在实际上堕入了男权个人主义的怪圈。艾科特(Eckert)也认为,性别不是固定的、与生俱来的,它是一个变化的动词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名词;社会性别和其他社会身份相互作用(阶级、种族、民族和年龄等),不可能轻易将其从中剥离出来。[31]Henley & Kramarea[32](P18-43)和Uchida[33]同样都持类似观点。很多女性主义者汲取巴特勒的表演论观点,认为性别身份是交际过程中所作的事情而不是所拥有的东西。[34]Kate Bornstein用性别生产(production of gender)阐明了在多大程度上社会性别可以独立于一个人的生物性别被表演出来。
当然,对性别建构论也有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持批评态度。她们认为性别建构论或多或少地削弱了女性主义的政治性和实践性。苏珊·博尔多(Susan Bordo)认为走极端的构建论实际上是“社会性别怀疑论”。如果性别角色完全由话语、由社会构建而成,天经地义地不稳定,不断地自我解构产发新义,两性的意义不断变化增加,那么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理论就不复存在。[35]
总而言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语言性别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相伴相生,语言性别论从早期的零散发展到男女二元对立的差异论再到多元性别观的建构论,经过了不断的创新、挑战、质疑与突破。这种种理论的发展与流变,诸多流派的辩驳论争和多元并立,为我们展现了语言性别理论舞台和女性主义舞台上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