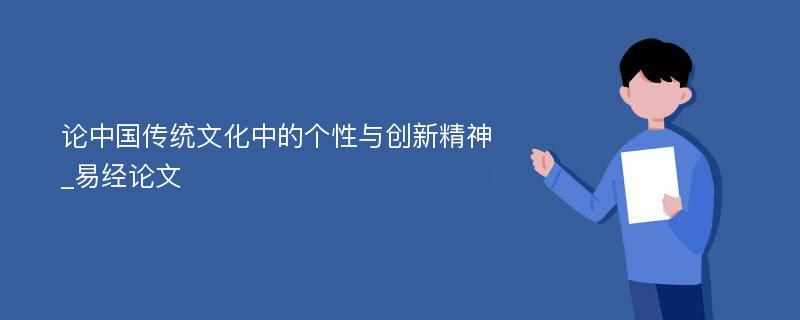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性与创新精神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新精神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个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有种偏颇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漠视个性,滞塞创新,是发展创新精神的障碍,是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这未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曲解和误读。
人的个性特质与创新精神往往紧相关联。个性,指一个人以与生俱来的天资为基础并在后天的习染中形成的精神素养、心理特性,是人作为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与其他个体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创新,指创造与更新,意味着“无中生有”,新事物产生、新思想形成;标示出“推陈出新”,在旧有基础上的变革,使旧的事物增加了新的机质、旧的理念孕育出新的生理。词义上的“创”,有创始、创造、创举等义,开拓性、独特性、新颖性是其词中应有之义;“新”,则区别于旧有、现存事物的新质新态,是新鲜的,因而也是独特的、新生的。创新是主体个性的突出表现。没有个性,就构不成大千世界;缺乏创新,就形不成历史卷帙。浩瀚宇宙,万事万物皆因其个性独具而取得存身世界的可能;悠悠万世,人类社会正因其不断地创新而获得进步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个性,追求创新的品格,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之中。
一
提到中国文化,不得不从《周易》说起。《周易》是中华文化之源,它以“易”为名,易者,变也。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注》引郑玄解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涵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变化、出新是它的基本含义。从《周易》的内容看,它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是周人占卜用的书,指书中的卦象和爻辞,《易传》则是相传孔子对《易经》蕴含哲理所作的阐释。《周易》在对宇宙人事的推演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三大理论精华:一是,阴阳对立统一论。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阴阳两个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二是,五行生克制化论。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按水、火、木、金、土五种属性归类,事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生成。三是,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与宇宙是相融互渗,相感相通,和谐一体的。这些,是宇宙自然、社会人事中最高的道理,最普遍的法则,它包涵了科学、哲学、人文、宗教等等一切范畴,对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以及天文、历史、数学、医学等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都享有极高地位,被誉为“群经之首”、“宇宙代数学”、“智慧中的智慧”。
贯穿于《周易》始终的便是关于宇宙万物变化的思想。变化,也就是与原事物产生了不同,就是个性,就是创新。这从《易传》诸篇对于“乾”卦的阐释中即可见一斑。《经》曰:“乾:元亨。利贞。”《彖》释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文言》释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这里表达的思想是,乾卦象天,天是派生宇宙万物的本体,纯粹的元精。天也是宇宙间善、美、义、正的总会、根源。天的体性是刚健中正。天派生出地,天与地交会再派生出万物。《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作为本体,它派生出地,从而有了阴阳间的对立和变化;继而派生出万物,万物之间也就有了对立和变化。可见,对立与变化是万物的普遍属性。在《易传》里,乾与坤、阴与阳、刚与柔、进与退、动与静等等都是对立着的统一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同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变化寓于一切事物之中。“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下》)总之,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一切事物或事物的一切变化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结果。
《周易》不仅昭示了变化、创新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现象,而且揭示了宇宙万物变化发展的深刻原因——变与通的辩证法。事物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的统一。变化不但是宇宙间万物运动的普遍形态,是一切事物生发的原因,而且是事物发展存续的动力,是事物在原有形态范围内发展到极致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转折。因此,变,也必然表现为旧的发展过程的中断和新的发展过程的兴起。但这新与旧之间又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那就是“通”。通,就是两端之间的贯通,就是发展过程的畅通,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易传》讲“通”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讲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如《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讲的是天人相通以及天下万事万物的相通性。二是,讲同一事物特定形态发展过程的持续。如“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推而行之存乎通”。化裁是事物的新旧质变,是旧的发展过程的终结;而推行则是新的发展过程的延伸、持续和扩大。三是,指事物发展的最终归宿,矛盾斗争的最终结果,对立归于同一,发展趋势转入复归本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变是对穷的一次否定,通则是对变的二次否定。变是穷与通之间递进的中介。通过否定前两个阶段的片面性以后,与本体归一,因而获得了恒久的物质。如果我们联系到《周易》里的“反复”这个范畴,就能更清楚地理解穷、变、通之间的关系。《易经·泰十一》:“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彖》:“‘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可以说,从穷到变是“反”,从变到通是“复”。一反一复,即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复归于何?《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系辞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复即通,被理解为向天地本体的回归。而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新事物的孕育、新生命的开始。这从古人对“天地之心”的解释可见。《周易》本义解释复卦之卦象曰:“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其端也。”孔颖达正义:“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不为而物自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动,此天地之心也。”[1](P245)《周易》的“通”即是指事物生生不息的状态、相互转化的过程、不断生发的本性。
可见,《周易》作为中华文化之源,讲的就是变的哲学,创新的哲学。变就是承认不同的事物有着自身的特点、独特的个性,要尊重事物的个性,顺其自然;变就是创新,就是变革;通则是事物的生存、发展、承续。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得变,变才能通,通才能久。要不断创新,不断变化,以求发展延续,这是由事物内外因素、主客观条件所决定了的,是宇宙万物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
《周易》的变革、创新精神直接孕育了先秦的思想家,催生出战国时期“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壮丽景观。从总体来看,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等不同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个性张扬、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就个体而论,各学派的创始人都是个性鲜明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也都是以张扬个性与开拓创新而著称于世的。
道家的创始人老聃就说过:“众人熙熙,若享太牢,若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若婴儿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忽兮若晦,飘兮若无所止。众人皆有以,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所谓“贵食母”,即以食于母为贵,“母”即“道”,意即从道中吸取营养。(注:见《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段话说出了老子“独异于人”的个性特征:众人是那样的欢乐,就像参加盛大的宴会,登临春意簇拥的高台;只有我淡然独处,无动于衷,如同一个还不会笑的婴孩。我是如此的狼狈,不知何处安身。众人都过着富足幸福的生活,唯有我像被遗弃了一样;我怀着一副愚人的心肠,长着一副无知的模样。世人是那样的明白,而我却如此昏愦;世人是那样的聪明,而我却是这样糊涂。我的生活是那样的坎坷多难,晦暗恍惚,漂浮不定,不知何处才是归宿。众人都有用,只有我冥顽无能。虽然惟独我与众人不同,但我仍要继续探索“道”的精神。这里列举了一系列“我”与众人不同的特点,表现的是老子因坚持操守矢志不渝地探索“道”的精神而特立独行、“独异于人”的秉性,一个思想独行者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孔子独创儒学,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他非常注重学生的个性。《论语·公冶长》记述了孔子对门下几个弟子的评价:“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求(冉有,名求,字子有)、赤(公西赤,复姓公西,名赤,字子华)等都是孔子的学生,孔子认为他们个人的秉赋和才能各不相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性格,适合于不同的岗位、宜于从事不同的工作。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对其弟子的个性特点作了简要的概括:“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他对学生的性格秉赋、特长爱好了如指掌。教学中,孔子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据《论语·先进》记载,一天,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一起陪老师聊天。“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孔子首先打消学生的顾虑,说:“不要因为我年纪比你们长,你们就不敢说话哟。”接着提出问题道:“你们平常总是说,‘别人不了解我’,假如别人了解你,你又将有什么作为呢?”弟子们果然畅所欲言,表达了各自的志向,而其极富个性的言论,也都受到了孔子的赞许。性情率直的子路是“率尔而对”,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意思是,如果让他治理一个千乘之国,即使这个国家夹在大国之间,甚至外有战祸,内有灾荒,不出三年,他可以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勇于征战,明辨是非。其抱负之大,信心之强,溢于言表。孔子虽觉得他太直露,但也只是笑了笑,未作评判。冉有则谦慎一些,当孔子问到他时,他才回答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他认为自己在发展经济方面有一定的才能,如果治理一个小一点的国家,经过二三年的努力,足以使老百姓丰衣足食,至于礼乐教化则不是自己的长处,需待修养更高的君子来实施。公西华则更谦虚,说:“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够胜任,但表示愿意在工作中学习。可以穿戴礼服,做一名为国君主持赞礼、司仪的小相。唯有曾晳则似乎志不在此,当同学们高谈阔论之时,他却在一旁鼓瑟,老师问到他头上,他才从音乐的陶醉中回过神来,“舍瑟而作”,说:“异乎三子者之撰。”称自己的志向与上面三位同学所说不同。孔子鼓励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这有什么关系呢,各抒己见嘛。也许曾晳还沉浸在刚才鼓瑟的审美境界中吧,他的陈述竟引起了老师的共鸣与神往,他说:“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原来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倒是期盼着在暮春之时,脱去冬衣,换上春装,邀同五六个成人,带上六七个小孩,到沂水中游泳,到舞雩上乘凉,然后吟唱着歌儿走在回家的路上。孔子听后“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意即我也想像曾点那样啊!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中是十分尊重人的个性的,他不随意臧否学生,而且鼓励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不同个性的充分表现,可谓创新教育、素质教育的典范,这对我们今天的教育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庄子更是个性的积极倡导者和捍卫者,他认为凡天下事物都有自身的本然真性。“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他主张事物各依自身的规律生存和发展,而不宜以规矩绳墨加以限制。他反对一切对个性的束缚和压抑,以至把社会的一切法制、伦理、道德都看成是约束个性发展的桎梏,是对自然本性的戕害。“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骈拇》)[3]他认为用绳墨规矩来矫正事物,就伤害了事物的本性;用绳索胶膝来加固物体,则侵害了物体的本德;靠举乐行礼伪施仁义来安慰天下人心,就违背了社会正常的状态。在《马蹄》篇中他指出:“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絷,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筴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3]用蹄来践踏霜雪,以毛来抵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跳跃,这些本来是马的天性。然而到了所谓善于治马的伯乐们手里,这生性活泼的马却被无端地打上烙印,套上蹄铁,剪去粽毛,戴上笼头,绑上络头,系上绊索,或被栓于马厩担饥渴之忧,或为整修马饰而受缨衔之缚,或被驱驰疆场挨鞭笞之苦,本真被废而天性尽失。《秋水》篇更明确地提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表现了对压抑个性、扭曲本真自然的行为的批驳,其张扬个性的态度更是强烈而至于偏激。
孟子是儒家礼乐仁义的弘扬者,同样十分重视人的个性发展。他认为圣人君子之所以出类拔萃,正在于他们的与众(常人)不同,也就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而圣人之间,彼此又是个性鲜明的,“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2](P233)。同为圣人,个性秉赋也各有不同,伯夷是圣人之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之中负责的人,柳下蕙是圣人之中随和的人,孔子则是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同时又是集圣人之大成的人。在孟子的论述中,曾多次提到性情独特的柳下惠,指出:“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然不忍去也。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蕙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万章下》)[4](P232)显然,孟子这里高度赞美了个性独具的柳下蕙,称他不以侍奉昏君为可羞,也不以官小而辞职。立于朝廷,不隐藏自己的才能,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操守。自己被遗弃也不怨恨,穷困也不忧愁;同乡下人相处,高高兴兴地不忍离开。他常说“你是你,我是我,你纵然在我面前赤身裸体,那又怎么就能沾染我呢?”所以,了解柳下蕙高风亮节的人,胸襟狭小的也会变得宽大起来,为人刻薄的也会厚道起来了。这是对柳下蕙独特品格的充分肯定。
从以上先秦诸子的为人及其原创理论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鲜明的个性,大胆的创新,鲜活的生命。
正是它们,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础,成为中华文化璀璨炫丽、生生不息的不竭源头。
三
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她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善于处理变与通的关系。以汉魏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为例,正体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演进过程。
汉代统治者出于专制的需要,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阻滞了先秦以来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令中华文化的发展步入了“穷”的境地。但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个性和创新精神仍是一脉相传的。
汉代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对不同时代统治者的治术进行总结,指出历代统治者一方面强调“奉天法古”,继承前代基业;一方面创新机制,鼓吹“王必改制”,体现当代特点。他认为“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变,即变革、创新。常,即恒久、承传。任何社会的发展总是继承与革新相伴而行的,每个朝代的统治者对前代的统治方略既要有所借鉴、有所继承,又要有所变革,有所创新。当然,封建时代新王的改制,“非改其道,非变其理”,更多地表现在“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等的形式枝节方面,而对于“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更多的是一仍旧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而往往是“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然而,在“乐”——艺术方面,却是要求“变”的,即要进行实实在在的变革与创新。董仲舒认为,“乐”与政治不同,“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而“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轹而不可得革也”。意思是说,“受命于天”的人,有着各不相同的秉性,他那善善恶恶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可以培育而不可改变,可以引导而不可禁绝。“乐”正是培养、引导、调节人的个性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乐的创作,一方面要适应统治阶级的教化要求,一方面要符合人的个性心理需要。“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成者本末质文,皆以具矣。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要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和人的个性心理发展的特点而不断地创新。正因为要不断地创新,所以,不同的时代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乐(艺术形式),“舜时,民乐其昭尧之业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时,民乐其三圣相继,故夏。夏者,大也。汤之时,民乐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乐之,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卷一:楚庄王第一》)在董仲舒辈看来,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政治伦理是顺乎天意而不可更改的“常道”,但作为发自于人内心情感的“乐”——音乐、艺术,则是随人事的更替、情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事,因而便产生不同的乐。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中,个性与创新精神,在政治、教化方面虽受到扼制,乃至于到宋明之时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境地。但在艺术领域却是始终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充分地发展着的。中国艺术上诗、词、曲、赋等形式的兴衰与风格的更递,中国文字中籀、篆、隶、楷等书体的创新及书法风气的演变等等都可以作为中华民族追求个性、崇尚创新的明证。而文学史上,个性鲜明的艺术家为世人所称羡,风格独特的艺术品为历代所欣赏的事例,更是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标志。
魏晋之时,随着人的意识的觉醒,文学自觉的发生,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体现在学术思想上便是由汉以来的儒学一家独尊发展而为百花竞放,儒学绵延,玄学日昌,佛学也勃然而兴,学术理论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为人处世方面,张扬个性,追求独特的所谓魏晋风度成为社会潮流(如《世说新语》中的记述);在文学创作与艺术鉴赏方面,追新逐异,标举个性更是时代风尚。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主张“文以气为主”,所谓气,指的是一种气质、气势、气概、气节,而这种气,正是作家独特个性的集中体现。曹丕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同,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3](P158)曹丕强调,气是与生俱来、因人而异的,就象吹箫奏乐一样,曲度虽然一样,不同的人吹奏起来效果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是由作家的个性所决定和制约的,是无法模仿,无从依傍,且不能血缘自授,即使在其父兄,也不可能自授给子弟。同时,曹丕还把文艺的这种个性化创造与人生的价值联系起来,认为著文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事业:“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优秀的文学作品确实是作家心灵创造的结晶,它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带给人的也将是全新的感受。刘勰是这一时期人文、美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文心雕龙》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人文产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文学创作、鉴赏的基本原理,不但以其“体大思精”,代表了当时理论探索的最高成就,而流传数千载,播誉海内外,对后世的人文、美学理论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书中,主体的创造精神和艺术的独创要求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如《原道》篇,作者把人视为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且誉人为“天地之心”、“有心之器”,与“无识之物”的自然万物相区别,视创造性为人的天性,人的本能,体现了强烈的主体意识。《神思》篇指出:“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4](P493)《才略》篇中,作者历数了虞、夏直至晋宋凡十代、近百位作家的不同个性及其作品的不同特点。创作主体的个性差异和艺术作品的独特风格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体性》篇中,刘勰更通过对“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的创作活动的论述,不但分析了创作风格的不同特点,而且揭示了风格形成的深刻原因;不但阐发了创作个性的构成要素,而且提出了“模体定习,因性练才”,陶钧文思,培养和发展个性的具体途径[6](P505)。同时,他还专列了《通变》一篇,论述文学创作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强调继承与创新在人文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发挥《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提出了“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6](P521)的主张。认为文学的发展是循环往复持续不断的,文学的面貌也应与时俱进,创新变化。只有变革创新,才能传承久远;只有持续发展,才能永不匮乏。这些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精妙之思,深邃之想,在当今人文精神的重建中仍不失其耀眼的光芒。
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乏个性与创新精神,同样,中国人并不乏个性与创新意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并不能归罪于传统文化,而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告诉我们,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个性、创新作为一种意识,是由社会的物质存在所决定的。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社会,自给自足,也就没有产生机器生产、工业革命的内在要求;清朝晚期,统治者固步自封,闭关锁国,阻断了西方工业革命对中国的冲击,使中国失去了现代工业革命的机缘,现代意义的民主与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这才是导致中国现代民主与科学落后的根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