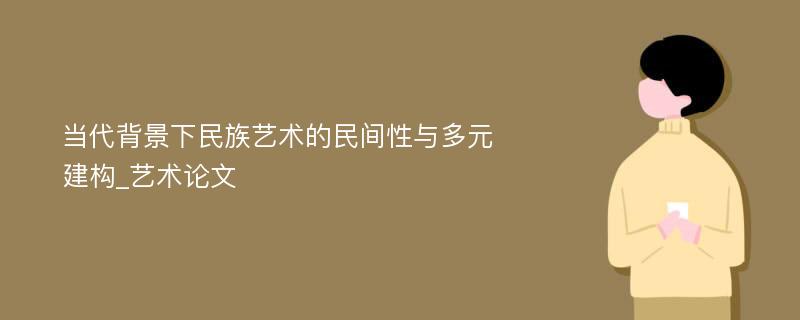
民族艺术的民间层面特性与当代背景下的多重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层面论文,当代论文,特性论文,民间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292(2008)05—0087—05
从大的人文视野看,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堪称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种突出体现或曰表征,当然,其本身也正是构成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具有浓重文化意味的民族艺术,在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之中,如同其文化结构会有若干不同层面一样,它也会有不同的层面。这不同层面往往是随着大的人文背景与文化机制的变化而生成和变化的,一方面关系着其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有益于实现丰富的美学价值取向的选择。
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艺术,从产生到发展都普遍具有突出的民间性特质。而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各民族艺术的特色性状,其中有的是属于根性关系。可是,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民间艺术面临着强有力冲击,出现被冷落的处境,甚至有的面临消逝的危局。这会直接影响到民族艺术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建设。因此,我们有必要同时面对这样两个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一是从民族艺术的生成规律而认识其民间性特质,以把握其内在血脉,再者即面对当下而探寻其新的生存与发展之路,以激发其新的生机。
民间性是传统的少数民族艺术的一个重要特性。历史地看,各少数民族的艺术几乎毫无例外地产生于民间。民间是民族艺术的土壤,也是其根系所在,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艺术都不可能缺少“民间的”这个层面——可以说,没有这个层面的存在,便意味着本民族艺术事实上的衰亡。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往往从本民族民众间的日常生活中自发地产生,以表现民众通俗的趣味和自娱的需求,它是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朴素且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与传承关系。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通常是与本民族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相适相谐的。恩格斯指出:“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1]401与“民间故事书”一样,其他种种民间艺术形式也都是为民众所乐于接受或参与,并可从中获得愉悦或精神调适。
考察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尽管可以发现彼此间有着种种显而易见的差异,同时可见出其在产生和发展轨迹上的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体现在民间层次上就有这样几个相同点:一是生成于本民族人们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习俗之中,是自然而然的;二是每个民族的艺术都经历过民间层次较长久的传承和演化过程;三是各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基本特色与风格主要形成于民间层面,而且由此而形成的特色与风格影响深广,包括影响到专业层面。
蒙古族是音乐的民族,而其丰富的音乐构成首先当推来自民间的民歌。茫茫草原可谓民歌的海洋,曾有过狩猎歌、牧歌、赞歌、宴歌、情歌、思乡曲、婚礼歌、长篇叙事歌等多种体裁的民歌。这各种体裁的民歌都与生息于内蒙古大草原的人们的劳动、生活、习俗等密切相关,并形成鲜明特色。如蒙古族牧歌便产生于蒙古族人长期的游牧生产劳动,是牧人们放牧时唱的歌,是游牧生活的一种写照。
与蒙古族民歌相同,回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之一“花儿”,也是首先突出民间性的。“花儿”是地处西北的回族人民在特定地域环境和生活、生存状态中传情达意的产物。其歌词往往是即兴创作,十分口语化,且不避俚语俗词,质朴粗犷,而且歌唱者往往十分投入与执著:“花儿本是心里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人们在山间、田野等空旷的环境无拘无束地唱和应答,交流感染,既快且乐,不失为一种美的境界。
再从舞蹈艺术来看。舞蹈也是各个少数民族普遍产生最早、流传久远且影响很广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无论是创生,还是接受与传播,它的民间层次同样是十分重要的方面。从处于北疆的蒙古族舞蹈、维吾尔族舞蹈、哈萨克族舞蹈、藏族舞蹈等,到置身南国的苗、壮、侗、水、瑶、黎、傣、彝等各少数民族舞蹈,都无不具有突出的民间性。
民间层面的各少数民族的艺术是非常丰富的,除上述的歌舞之外,还有文学、绘画、雕刻、工艺、建筑、服饰、戏剧,等等,都无不在各民族的民间获得丰厚的滋养,并得到了充分发展,以至形成底蕴深厚而又独具特色的美学品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间不仅是各民族艺术的沃壤,而且同时蕴含着丰富的艺术智慧和超拔的创造力。就少数民族的长篇叙事诗而论则堪称奇观。在中国的民间文学艺术宝库中,少数民族长篇叙事诗占有重要地位。与汉族的长篇叙事诗相此,这一特点尤为突出。在汉族民间文学史中,长篇叙事诗并不多,其代表性的作品只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几篇,而且规模也算不上宏大。而少数民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则展现出了各民族五彩缤纷的世界,如维吾尔族的《艾里甫与赛乃木》、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彝族的《阿诗玛》等。据有关资料介绍,仅云南傣族地区就有长篇叙事诗五百五十多部,目前仍在民间流传的有三百多部。少数民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其规模也往往十分宏大,有的堪称是本民族的“百科全书”,其影响力既广且深。
再从表现、传播与接受方面来看民族艺术民间性特质。民间化、仪式化、传情化,是“原生性”民族艺术的基本特性,在传统的艺术活动中,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与接受者各方通常是共时态直接参与的,并共同营造着“即时即地”的艺术情境与艺术氛围;有些艺术活动中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接受者的身份角色是在随机互换着的(有的则是创作者、表演者、接受者“三位一体”),如许多民族地区民间节日的歌舞活动、对歌活动等。这表现出传统的民族艺术活动就其主导形态而论是属于群体性的,体现的是人际传播下的“人—人”关系,信息传递与感受反馈当面进行,从而共同构成艺术活动和谐而有机的整体。
在传统的民族艺术传播与接受中,许多都是以双方主体身心俱至的直接参与、直接感应并及时传递信息而进行活动的。从其活动行为本身来看,传统的民族艺术的传播与接受的直接性方式其实就是双方主体直接性参与方式。在这种“即时即地”亲身直接参与的活动中,包括传播者(表演者)与接受者在内的参与者双方的诸多感官、机能、才情(包括即兴调节与创造性表现)都可能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以尽可能多地捕捉信息并有所回应。信息的直接感应交流往往在客观上决定了审美接受者必须全身心投入其中。所以,人们参与传统的民族艺术活动时,其心理上的“在场”性的入乎其内,与行为上的亲身参与通常是—致的。审美接受者既在内心确认自己是文艺活动的主体,并以浓厚的兴味意趣将自己溶入其中,同时又以外在的亲身参与方式实现着自己的审美行为。这样的审美体验自然会是真切而深刻的。
这种传统的民间性的民族艺术传播与审美接受中的“人—人”关系的直接性、亲历性及群体化特性,其背后同样潜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就中国众多少数民族来看,他们普遍在文化精神方面有一个极为相同或相近之点,那就是群体为本位的精神。这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生存现实诸多因素有关。在群体本位精神指导之下,传统社会的各种活动都往往以整体和谐为追求目标。即民族艺术在民间的表演、传播,通常具有原位性、“在场”性和群体参与性,这会营造出特有艺术活动情境,产生特有的审美效果——以某种艺术形式在创作者或表演者与受众共同生息并熟悉的环境中展现本民族的历史或现实生活,自然会感到亲切并因此而身心俱至地投入;在此情境中,创作者或表演者与受众往往会当面直接感应交流、相互感染,融为一体继而即兴生发,甚至出现人人都成为创作或表演主体的“忘我”境界。《蒙古秘史》最早记录了蒙古族古典舞蹈激昂奔放的气势:“绕蓬松茂树而舞蹈,直踏出没肋之溪,没膝之尘矣!”流传很广的民间歌舞《安代》继承了蒙古族古典舞蹈激烈豪放的传统风格,“通宵达旦的高歌狂舞使人如醉如痴,不能自抑。许多人把喉咙唱哑,把崭新的布鞋踏裂,甚至顺手撕下蒙古袍的前襟,上下挥动着当作助兴的手帕”[2]260。其豪放激昂之情可见一斑。这是民间的民族艺术活动的又一独特魅力所在,无疑这同样也是包括高雅的、大众的等在内的其他非民间的艺术活动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民族艺术传播与接受共同构成的完整的活动,正是在客观上为参与活动的各方创造着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殊交际的环境。另外,实现主体精神的高扬,也是传统的民族艺术活动中接受主体直接参与的重要审美需求和指向。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及艺术活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契合生命律动的最佳方式,它往往与人的生命发生共振。以许多民族的歌舞为例,合乎人的生命运动状态这一特点便使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显示着一种生命状态的呈现,成为生命冲动的舒泄。因此,直接参与者往往会受到强烈感染并获得深刻的审美快感,进而激发起精神的振奋,使人的主体性得到高扬。
以上是对民族艺术的民间层面特性的历史性考察,认知所及主要是原生性的(含原位性)。其中有两个极为关键的要素,一个是原生性环境(包括自然的与人文的),另一个是本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习俗。那么,如果这两个方面的要素发生了大的变化后,情况会如何呢?
我们现在即从历史的回眸中转过身来,把视点落实到当下。显然,当下的许多方面已大不同于古往,宏观上看,这是一个以高科技、现代化为先导和基础,打破许多时空局限而形成全球化语境的时代。它首先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冲击力影响人们的生活与认知,并不断引发人们的新的生存需求。尽管其中不免有种种负面的东西,但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它在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改变人们的生活环境、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以至改变人们的生存关系与生存状态方面的突出的有效性,则还是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的,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相对比而言,中国的少数民族多数处于偏远、闭塞地区,但在普遍意义上,他们同样不慢待,更不放弃对现代化的追求。所以,我们所面对的现状是,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或努力进入城市图求发展,或虽在故乡故土,却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将现代化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新的观念一同引入,以努力改变其生存条件与生存方式。
的确,较之于各民族艺术创生时期的古往,现在从环境(包办自然的和人文的)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些“要素”的变化,则必然导致民族艺术乃至民族艺术活动及价值判断上的变化。我们这里主要讲与民族艺术的民间性相关的两个方面的情况。首先从创作与传播方面看,民间艺术人才的明显稀少,甚至断代、失传现象出现。民间艺术人才,是世代置身于本民族特定地域环境、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优秀人才,是“源于民间融于民间的基层文化活动者”,而且通常具有过人的才艺智慧和对本民族文化艺术的极大热衷。他们生活于民族生活中,深谙其文化精神,在文化艺术的传承中处于前沿,尤其在民族文化的整合体—民俗文化的活动中处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民族文化艺术在其实践活动中得以加工、创新与保存,并代代相传;他们个人的东西渐渐融入了民族文化之中,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活水源头之一;他们从历史走来,带着民族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传递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所以,历史地看,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中,都必然有一代代民间艺术人才的突出、甚至是卓越的贡献。
可是,当下民间艺术人才这类传承主体的变化却是令人惊诧的。从上世纪末开始,我们便时时可以听到来自许多民族的关于民间艺人断代、技艺将失传的慨叹,包括抢救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呼吁,而且此类呼声愈来愈急,愈来愈大。
我们知道,那种真正的所谓的原生态地域性民族艺术,往往正是产生和存活于民间艺人“身上”的,即通过民间具体的有才艺的人创作与传承的。如民族地区民间歌、舞、戏等,只有当它们存在于现实的人们的身上时才算是保存下来,也只有“活”在艺人的“身上”才表明它的存在。而那些只留存于纸面上的乐谱、舞谱、脚本、程式等,则并不算生态意义上的存活;经过生活在都市文化氛围中的职业艺术家加工而搬到舞台上的作品,则又必然不可避免地带入方方面面的文人化、当代性的因素(通常看到或听到那种对这类艺术称作保持了“原汁原味”的说法,细究起来便知事实上往往是一种不实之词)。这便意味着,如果缺乏作为原生态地域性、民间性民族艺术的重要创作者与传承者—民间艺术人才,那么,便难以保证这种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事实上的真正存活。而现实的如上所述的情况是,老的民间艺人越来越少,而在当代年轻人中真正的传人也已很少,这必然会对民族艺术的民间层面的存在情况产生很大影响。
其次,从接受群体方面来看。所谓“接受群体”,指包括参与某一文化艺术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有时甚至是可以超越地域与民族的。具体到某一民族文化艺术来说,当然主要是本民族的成员群体。从历史生成及传统结构方面看,一个民族的群体往往是相对集中地生活在某一特定地区。他们共同面对大致相同的自然环境,遵循相同或相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生存状态。在文化上有其独特的“自组织”系统,即拥有自己的政治、宗教、文化、艺术、经济手段等,并在此“自组织”系统中而构成某种群体模式与更内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这样,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的群体在共同的生产生活范式,共同的信仰习俗、审美价值取向等形成的内聚性文化结构的影响下,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与途径把本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渗透于每个成员身上。显而易见,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活动的进行,这种群体性的作用是最根本的。考察中国各少数民族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凡是一个民族的艺术得以有机而稳固的传承,便无一例外地必然拥有这样的稳定的群体。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一个民族的群体结构及其传承行为一经形成便一成不变,也绝非是说中国各民族艺术在以往的传承过程中未发生过变化。在发展观的视野中,变是必然的、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民族艺术活动也是如此。只是在没有经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冲击以至重构这样深层次的重大的变化时,其传统的稳态化的传承系统及惯性一般是不会有明显改变的。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变,科技发展迅猛,各种现代生活和现代文化形式交错演进,生活被艺术装点,艺术被生活同化,以电视传媒、时尚杂志、卡拉OK、休闲度假为表征的当代大众文化占据了艺术生产与消费的中心,而许多传统艺术却落入“边缘化”。从接受群体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如不少传统民间艺术的欣赏者大多只是老年群体,而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许多农村、牧区的青年进入城市。多彩多姿的城市不但是这些青年人打工谋生的地方,而且也是他们接受现代化生活和大众信息(当然包括众多的文化艺术信息)的场所。这里所提及的,当然远不是当代现实社会与文化景观的全部或典范,但却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其变化的广泛与深刻,以及不可逆之势。
从民间性的层面看当代民族艺术接受群体性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这样几点:一是中国当代民族艺术接受群体的变化中,存在年龄段的差异,就当下来看,可以50岁为大致界限,愈是年长者,其身上愈保留有较多传统中的东西,而年轻者中则更多现代化取向与趣味。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出现民族艺术传承上的代际间的错位。二是这种变化突出体现为价值取向的变化,即由生存(生活)价值而到文化—审美价值,与之相关便自然涉及艺术选择。三是民族语言的作用与意义是格外重要的。倘若一个民族的语言得不到保留和继承,那便等于丢失了本民族艺术传承的手段、依托,甚至根本,但这个问题在当代却很严峻。四是从“活”的艺术形态来看(不是像历史博物馆内存放着的固态物件),所谓民族艺术的真正的“原生态”越来越少,同时,其接受群体范围也在不断缩小。
通过以上从创作、传播到群体接受两个方面考察分析中国当代民族艺术在民间层面的现状,可以说,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显著的,由此实际出发,笔者进而认识到了多重构建的必要性。
民族艺术的“多重构建”,是在当代背景下而言的,因而也可以称之为当代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的一种选择。所谓“多重”,主要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层面这“一重”而言的,即在纵向上形成从民间层面到专业层面的内涵丰富的立体结构,在横向上形成形态多样、各种表现形式与表现手段并举的开放域面。这样,既可以为民族艺术的生存与发展争得更多机遇与拓宽新的空间,又可以满足当代更多接受者不同的审美需求。
民族艺术民间层面的存在及特性,前面已作详述,现在着重从专业化层面来看。所谓专业层面的民族艺术出现,首先是其创作者、表演者与传播者等主体自觉及专门化所致。当然,这也正是文化发展、社会分工细化的一种体现。专业层面的民族艺术,主要由知识分子或专业艺术家遵循一定的专业规律进行创作、表演与传播,表现创作(表演)主体专业技能与水平,更要表现其独特的感悟、思考、发现,并以形式创新和个性突显为重要美学追求。除此之外,作为某一民族的专业层面的艺术,还应必须表现本民族的内容,传达本民族的精神(包括人文的和艺术美学的)。
传统的各民族艺术都具有一个格外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传承。长期的传承使其拥有了异常丰厚的积淀,但同时也往往会形成稳态性的人文心理结构与艺术表现形式。所以说,其中既有丰富的资源可开掘,又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对其稳态性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及惯性化艺术活动模式的突破。这方面,有创新的民族艺术显示着自身优长。
一般而言,专业的民族艺术创作总是善于研究和总结前人的形式惯例,并从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民间文化传统中汲取资源,从外来文化中获得启迪,在开阔的视界中创造出新的原创性作品。这类创作中,艺术形式的创新特征往往格外突出。例如,云南傣族人以孔雀为题材的艺术活动历史悠久,方式众多,其中以舞蹈为最。在《顺宁府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四时庆节,大小男女皆聚。吹芦笛,作孔雀舞,踏歌顿足之声震地,尽欢而罢。”原始形态的孔雀舞是一种民间的化妆舞蹈。舞蹈者仿照孔雀样子,面上戴孔雀的面具,或尖塔形白净菩萨面具(体现了孔雀与宗教的联系),腰上会有用竹篾、彩纸扎成的孔雀身子和尾巴,两手牵着孔雀翅膀,随着锣鼓的节奏舞出孔雀的动作。这套动作通常都有比较固定的形式套路:从孔雀出窝、下坡、起舞、找水、顾影、饮水、洗浴,直到展翅飞翔。整个舞蹈有着严格的步法和方位,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程式。民间传统中的孔雀舞表演者限于男性,而且有着更多宗教仪式成分。[3]290-291现在,经过专业艺术家对于傣族传统的孔雀舞进行提炼和艺术创新,其欣赏价值与审美品味大大提高。首先,从形式上脱掉了传统的笨重的道具,换上了有孔雀形象象征性的长裙,并在表演时充分运用舞蹈语汇,体现舞者体态的曲线变化与艺术形象之美。通过这样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使这美丽的孔雀“飞”上高雅的艺术舞台。特别是经过刀美兰、杨丽萍等优秀艺术家具有个性化的、炉火纯青的舞台艺术形象创造,使艺术中的孔雀之美成为少女之美的化身,也使《孔雀舞》成为美好女性心灵世界的表现。此例可以表明:一方面,传统的民族文化资源在民族艺术发展中具有很大的可开掘性和可利用性,另一方面,艺术形式的创新足可以使高雅的民族艺术实现新的美学超越。而且可以说,此例所表现出的情形是有普遍性的。
专业性的民族艺术的创新,往往是现代意识与民族精神自然融合的体现。现代意识是一种文化观念,是现代文化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重新认识与适时提升,高雅的民族艺术中的现代意识是可以融通本民族艺术美学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的。这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主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见出:其一,在新的创作理念指导下而进行艺术表现上的探索,以形成新的形式美感;其二,新的形式美感自然而相适地呈现新的现代气息;其三,艺术家在对客观现实生活深刻体验的基础上,用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辨去创造与时代相适的艺术形象。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之下,面对经济的、文化的等方方面面新的变化、新的机制,作为富有开创精神和提升审美品格的高雅民族艺术,则更应该以新的现代意识去解析民族传统、利用其文化资源,并以积极的创新精神,创造新的艺术形象,展示新的艺术形式,突出新的艺术价值。如内蒙古广播艺术团、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等专业院团演唱的无伴奏合唱,云南的大型舞剧《阿诗玛》、大型舞蹈诗《云南映象》,内蒙古的独舞《翔》、《意如乐》和群舞《草原酒歌》,贵州的群舞《水姑娘》,等等,都是以新的美学理念进行创作的优秀之作,很受观赏者、特别是中青年观赏者的欢迎。
民间层面的民族艺术的创造与传播,离不开民间艺术人才,同理,专业化层面的民族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应有高水平的专门人才。与民间艺人不同,这一类人才一般都接受了现代知识的教育(大多数经过专门院校的培养),具有系统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化知识与专业知识)与鲜明的现代意识。他们有的在民族地区的基层生活与工作,而有的则身居城市;有的以文化艺术为职业,而有的则是业余为之,而且在创作、表演、组织、宣传、教学、制作等各个方面都有。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各民族地区的中高等艺术教育的快速发展,这方面的人员明显在增多。他们与民间艺人相比,除了受教育的条件、方式以及知识结构不同之外,普遍还有如下显著特点:能在一定的距离感中审视民族艺术,即既“入乎其内”,又能够“出乎其外”,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开阔的视野进行选择和判断;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理性精神较强,能够从主客双向互动的多视角、多维度对本民族的文化艺术进行冷静的知性的客观分析与思考,并有能力作出富有学理的阐释;现代意识强,从观念到实践都与现实社会的诸多方面密切相关,适应性强,创新欲望(包括某些标新立异)突出。当然,与前者相比,其弱项也是显然的,对于民族文化原生态的感性体验不够,民间性弱化等。
进入现代知识分子行列的民族艺术人才的创作通常是具有明显的当代性的。笔者从一些民族地区的艺术院校到艺术团体,粗浅地考察分析当下的民族艺术创作,发现无论是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门类的创作,也无论是哪个民族地区的创作,其中都有一个十分趋同之处,即力图以现代通行的创作手法而尽量展现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以期达到既有地区与民族特色而又能适应当代接受群体的审美趣味,同时又符合当代大众文化的运作逻辑。这事实上就是将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填入主流叙事的基本框架而运行。譬如蒙古族歌曲创作,有许多作品在结构与配器上都具有当代音乐创作中流行的模式特征。我们这里无意评说其利弊得失,而只是在指认其现象,并从一个侧面说明其显在的当代性。另外,作为艺术家的专业化创作,往往突出个性并力争创新为追求,这便自然形成了民族艺术大花园的丰富性与多彩性。
艺术的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它的发展变化不同于科学的更新换代,凡是新的就一定是先进的或好的,或者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方式的出现一定意味着原有的方式被替代。但是,艺术的存在与发展又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同样与相适的生存条件和激发其生命活力的系统机制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人类在剧烈生存竞争中,出于体现观念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开拓出种种新的艺术行为和表现方式,形成了艺术在人类的新的生存背景下的新的特色与发展轨迹。笔者认为,实现民族艺术的多重构建,正是当代背景下发展民族艺术应该面对的新课题。当然,最后还须指出,民族艺术要保持其本民族文化的特质与精魂,就绝不能丢弃其根性的东西。一方面,民族艺术专业化层面的发展,原本即与民间层面的根性特质血脉相通的,或从中获得了重要资源,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所以,无论其在专业化的层面上如何求新多变,但最终不能脱离根本;另一方面,同根同源的民族艺术实现不同层面上的有机共存,目的正是在于通过向多层面的立体结构生发,从而获得富有张力效应的机制和多维性的丰富形态,既有利于拓宽其生存与发展空间,又可适应不同审美层面的受众需求。总之,合规律且与时俱进的多重构建,则可以使民族艺术在不断获得新的增长点的同时,更加富有生机地彰显其文化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