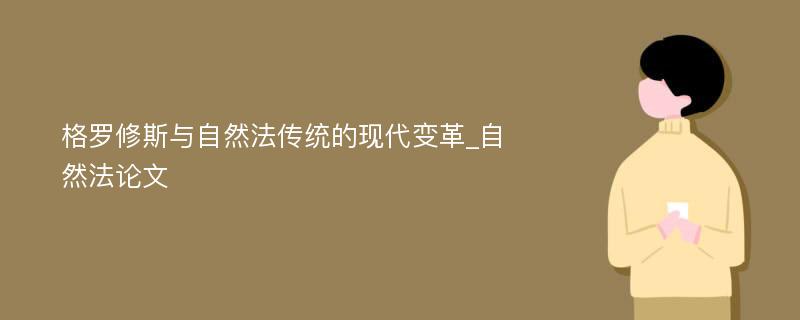
格劳秀斯与自然法传统的近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法论文,近代论文,传统论文,格劳秀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法是西方最古老的法律思想之一。自古希腊最早产生自然法的萌芽以来,西方自然法传统历经了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和近代三个阶段,由此形成古典自然法、中世纪自然法和近代自然法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主要区别有二:其一,作为一种普遍适用而永恒不变的法律原则,自然法在各个阶段的价值判断的来源不同,三者依次为:自然、上帝的启示和理性,①因而近代自然法也被称为理性自然法;其二,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年)认为古典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都是以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为旨归,而近代自然法强调自然权利和个体本位,两者截然有别。②本文亦接受这一理论前提。
虽然理论界通说认为,17世纪荷兰自然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是近代自然法的开端。③但近年来,对这一观点的质疑屡见不鲜。例如,海因里希·罗门指出,格劳秀斯并未完全将完整自主的人类理性作为自然法的唯一源头,仍然承认上帝是自然法的渊源;他将自然法界定为自然理性,也是中世纪哲学家苏亚雷茨(Francisco Su á rez,1548-1617年)的翻版;他与古典思想家非常类似地都极为强调人类的社会性本质;他的国际法理论与苏亚雷茨也相似。④登特列夫转述的一种理由是:格劳秀斯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借来的自然法概念,是中世纪自然法传统的延续;他关于自然法不需上帝存在的论断,可以在中世纪找到根源。⑤詹姆斯·斯科特形容格劳秀斯的成功只不过是摘取了苏亚雷茨成熟的理论果实。⑥以上种种观点都是对格劳秀斯历史地位的质疑。笔者不能赞同以上质疑,并将通过本文论证,格劳秀斯对于自然法传统从中世纪到近代的传承与变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认清格劳秀斯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对于我们理解西方自然法传统的发展脉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古典和中世纪自然法中的待决命题
虽然从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思想在自然法对于实在法的超越性上是一致的,但古典自然法和中世纪自然法为后世遗留了两个有待争议的命题:其一,人类的自然本性界定为社会性;其二,自然法是事物理性本质的反映。
首先,古典自然法将人类的自然本性界定为社会性。古典自然法并不强调自然权利的优先性,而更注重个体对于社会共同体的义务。这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学观。亚里士多德在考察城邦政治时曾经指出,虽然从发生的先后顺序上,城邦后于个人和家庭而产生,但是,“城邦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人类生来即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⑦。据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人在本性上就是社会性”。⑧这一观念被其他古典自然思想家接受。例如,西塞罗认为人天然就具有社会性,它与人类的存在相始终。⑨阿奎那忠实地重复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说:“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⑩
既然人的本性是社会性,古典派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存续和发展是首要的,因此要求每一个体都要为此做好份内的工作,履行自己的义务。亚里士多德说:“保证社会全体的安全恰好是大家一致的目的。”(11)而且,在他看来,社会共同体的目的并不在于谋求利益。他指出,城邦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生活或生存,即防御侵害和促进经济往来,而是“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12)阿奎那也认为,个人是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律必须以社会福利为其真正目标。(13)总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社会共同体的价值相较于个人利益居于优先地位;社会制度的出发点不是权利、而是义务;(14)社会制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个体利益,而是为了促进社会共同体的“善”。近代自然法思想家与这些观点发生重大分歧。
中世纪关于理智论(intellectualism)和意志论(voluntarism)的争议,遗留给近代自然法思想家另一个重大问题。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上帝以类似于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并赋予人类以灵魂,而理性(理智)和意志就是人类灵魂本质的两个方面,这使得人类与其他灵魂区别开来。那么,理性与意志哪一个在先呢?阿奎那认为,人的意志使人具有自决能力,但是,意志要作出决定,首先必须有善的观念,而善的观念则是由智慧来决定,从而理性处于主导地位。(15)换言之,首先应根据理性对人类行为是否符合善作出判断,然后意志据此决定是否去从事该行为。可见,理性是“人类行动的首要原理”、“人类行动的准则和制度是理性”(16)。
与阿奎那相反,中世纪唯名论者则主张意志论。约翰·邓斯·司各特(Johannes Duns Scotus,1265-1308年)认为,一方面,上帝的意志是无限的、绝对自由的,他的意志力可以支配对他来说一切可能的东西;另一方面,上帝的意志高于理智,他不被理性所决定,因而我们不能通过推断而认识他的目的和了解他的活动。我们也无法预测上帝如何按照其意志创造任何一个世界,宇宙并非产生于必然合理的思想。否则,人类就能推论出全部事态,似乎可以按照上帝的方式来思维上帝的思想。(17)就法律而言,上帝命令我们按照某种法则行动,并不因为它的自明理性,而是因为上帝给人类作出规定,这些法律才是必然的。(18)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1290-1349年)赞同唯名论并指出:“一个行为是善的,不是因为它与反映了上帝对人的本质和潜能的观念的人的基本天性的对应,而是因为上帝希望它是善的。……因此,法律是意志,是纯粹的意志,根本不以万物的本性为基础。”(19)由此推论,世界上并不存在基于事物自然理性的法则,上帝意志才是人类行为的主宰者。他最终得出人的道德活动被上帝意志直接地、偶然地决定的结论。(20)
理智论和意志论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法律本质观,即法律究竟反映理性(或理智)还是意志。换言之,它是因正义(自然本性)而成为法律,还是因命令(立法者的意志)而成为法律。(21)意志论者主张上帝意志的绝对性和无限自由,从而上帝决定的法律也是偶然的、任意的,它甚至取消罪行中的道德因素。(22)而理智论者认为法律反映事物的自然理性。虽然从根本上说,理性是上帝赋予的,但是正如阿奎那所说,人类分享上帝的理性和智慧产生自然法,这无疑抬高人类理性的地位。登特列夫(A.P.d'Entrèves)对此评论道:“这股自然理性之光使我们能够分辨善恶。……人被认为具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他既是上帝的从属,又是他的合作者。”(23)以此为起点,近代自然法思想家只需跨出世俗化的一步,剥离自然法中的上帝,即可完成人类理性作为自然法基础的思想论证。近代自然法正是对意志论的摒弃,对理智论的复活。(24)
二、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自然法
在近代自然法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16世纪西班牙的晚期经院哲学家对自然法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起到关键性作用,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是萨拉曼卡大学的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1483-1546年)和科英布拉大学的弗朗西斯科·苏亚雷茨(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年)。
维多利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自然权利论方面。他在界定Ius(权利)一词的含义时,一方面在客观意义上将Ius定义为“正义的事物”,另一方面认为Ius是“一种根据法律属于某人的权力或能力(power or faculty)”(25)。事实上,中世纪学者早已提出Ius在主观权利的意义上是一种权力或能力。(26)但维多利亚在反对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天然地享有统治权时,运用自然权利论,凸显出它的现实意义。他在《论美洲印第安人》中提出如下质疑: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究竟美洲野蛮人是否享有私人的和公共的统治权?即他们是否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人以及他们中间是否存在君主或类似的统治者?一种观点认为,印第安人是囚犯、异教徒或非理性的人,所以他们不应享有任何权利,对此维多利亚一一批驳其理由。其一,犯人是否能作为所有人?他回答说:有罪并不是享有民事权利尤其是所有权的障碍。其二,异教徒是否能作为所有人?维多利亚引用阿奎那的理论指出,不信教并不等于取消了自然法和人法,而所有权正是出自这些法律制度,不信教也不是享有所有权的障碍。其三,非理性的人是否能作为所有人?事实表明野蛮人并非疯人,他们在社会事务方面形成井井有条的秩序,因而不能否定他们的权利。(27)维多利亚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印第安人确实享有私人的或公共的统治权,他们的财产权也不能被任意剥夺。(28)即使是犯人、异教徒、心智不成熟的孩子也应享有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根植于人类的自然本性。(29)在梯尔尼看来,这些都说明印第安人应享有自然权利,其根植于人类的自然本性之中。(30)
苏亚雷茨早年在萨拉曼卡大学学习教会法,以后在西欧多处神学院教授神学,1579年接受葡萄牙科伊布拉(Coimbra)大学的教授教席,1615年告别讲坛。苏亚雷茨是一位“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巨大创作力的思想家,是西班牙引以为自豪的17世纪的欧洲精神领袖”(31)。哲学史家称其为“在近代哲学改变西方哲学的方向之前,他也许应被看成是那个传统中最后一位世界级的人物”(32)。他在法学方面出版的最重要著作是《论法律和立法者上帝》。
与维多利亚相比,苏亚雷茨的思想更为哲学化、体系化。苏亚雷茨在中世纪法学家对法律(Lex)和权利(Ius)界定的基础上,全面地总结两者的含义。首先,他指出,Ius具有正义、公正的含义。如果在抽象客观意义上,它可以指任何与理性一致的正义事物;如果在具体的层面上,Ius可以指主观权利的意思,即“个人拥有的某种特定的道德权力。”(33)基于Ius的主观权利涵义,苏亚雷茨进一步阐述自然权利:“如果我们说到可支配的自然权利,自由属于一项自然权利……因为自然使人类实实在在地(享有)自由,即天赋的自由权。类似地,自然也授予人类对于万物的共同所有权,并且让每个人都有利用它们的权利。”(34)
就自然法而言,苏亚雷茨指出:“理智的自然之光就被称为自然法,它驻留于人类的心灵之中。”(35)有些自然法已被人法所推行,例如关于誓约、契约,权利等;但即使没有人法,某些自然法也具有直接的拘束力,例如虔诚、仁慈、救济邻人、不伤害他人。关于自然法与人法的关系,苏亚雷茨主张:“人类没有权力(即使是教皇的权力)废止任何自然法的正当规则,也不得对它进行实际限制。”这是因为:(1)自然法的规则有关人类的自然本性,人类不能改变事物本性;(2)上帝是自然法具体规则的立法者(Lawgiver),人类不能改变上帝确立的法律规则;(3)自然法是人法的基础,人法不能与自然法背离,否则,将摧毁人法的基础及人法本身;(4)与自然法相对立的人法,在本性上是恶的。(36)
关于法律的本质是理智(intellect)还是意志(will),苏亚雷茨企图调和中世纪以来两者的矛盾。他首先认可理智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求理智的判断,而不需要意志行动,因为后者对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来说是必要,但是对于法律的存在来说则不必要。法律(的存在)先于主体的意志,并且约束该意志。……一般来说,自然法就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判断。”(37)
但是,法律的颁布和执行又离不开立法者的意志。立法者为了实现公共福祉,达到保护和平和促进人们幸福的目的,需要将这种意志加于主体之上。因此,理性审慎地决定法律规则,但需要通过立法者的意志去贯彻和实施。(38)总之,苏亚雷茨认为,法律是理智和意志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它是关于“事物的正确判断,以及使其得以被服从的有效意志。因而法律是由意志和理性共同构成”(39)。
16世纪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一方面传承了古典自然法传统,保留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论和社会共同体优先论;另一方面,他们在区分法律与权利的基础上,推进了自然权利论,强调自然法的本质是事物的自然本性(理性生),(40)从而开启近代自然法先河,并为格劳秀斯的转折铺平道路。
三、超越理智论与意志论:作为正确理性命令的自然法
格劳秀斯的代表作包括1604年撰写的《捕获法》(1609年部分内容以《论海洋自由》为题出版,1864年全文出版)、1619年完成的《荷兰法学导论》(1631年出版),以及1625年完成的《战争与和平法》。他的自然法学综合经院哲学、人文主义、罗马法和教会法等各方面的传统思想,并在国际法与自然法两方而取得卓越的理论成就。
虽然自然法在中世纪被誉为“自然理性之光”,但神学家们最终还是将自然理性归诸于上帝意志。这个问题在苏亚雷茨那里开始有了转机。在他看来,理智论和意志论分别反映中世纪法律理论中“指示性法律”和“命令性法律”的区别。(41)指示性法律是自然理性向人们揭示何为正当、何为错误;规范性法律则是立法者的意志命令人们履行或禁止某种行为。(42)14世纪的哲学家格里高利·里米尼(Gregory of Rimini,1300-1358年)最早提出两者的区别,他认为,罪恶的事物之所以有罪就是因为其违反正当理性,即使上帝没有发布相应的命令甚至假设上帝不存在也是如此。由此,格里高利作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假如(一个不可能的假设)神的理性或者上帝不存在,……无论天使、人或其他存在物,违反正当理性的行为都是有罪的。”(43)
苏亚雷茨引述格里高利的观点作为理智论的证据,并将之改造转述如下:“格里高利说:即使(假设)上帝不存在,或不能运用其理性,或判断事物不正确,然而,如果同样正确的理性指示居于人类之中,并恒久地对其确信,例如,撒谎是恶,那么人类事实上拥有的这些(理性)指示仍然具有同样的法律特性,因为它们作为一种法律指明了内在于(被谴责的)事物之中的恶。”(44)
支持理智论虽有强大的理由,但在苏亚雷茨看来,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不能缺乏命令性,即不能离开立法者的意志而存在。如果说,自然法独立于所有的意志,甚至是上帝的意志,那么根本不是真正的法律。(45)为了使自然法成为令行禁止的规则,必须有一个超越的、权威的立法者(上帝)来发布命令或禁令。(46)因此,他采取折中路线,调和理智论(指示性法律)与意志论(命令性法律)的分歧,最终得出结论:“自然法不仅表明什么是善恶,而且进一步也包括对恶的禁止和对善的命令。”(47)这既体现自然法的理性基础,又维护立法者上帝的尊严。换言之,自然理性已然揭示内在于事物自身之中的善恶本性,它只须借助上帝意志的权威,就能完成从自然本性到自然法则的转变。
格劳秀斯对理智论与意志论的看法,从早期《捕获法》到《战争与和平法》发生了重心转移。(48)他在《捕获法》(1604)的序言中,提出九项法则和十三项法律,并强烈表现出一种意志论色彩,例如首要的几项法则是:(49)“法则I上帝显示出来的意志就是法;法则Ⅱ体现人类全体意志的共同合意(common consent)就是法;法则Ⅲ每个人表示出来的意志就是关于他的法;法则Ⅳ国家所表示的意志就是所有公民整体的法。(49)”
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还保留些许意志论。例如,他指出,自然法基于人类本性,但本性是上帝愿意它如此,所以上帝的意志也是一种法律的本源。(50)但是,他此时显然受到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的影响,(51)对自然法采取调和理智主义和意志主义的定义:“自然法是正确理性的指令,它表明一项行为符合或者不符合理性自然,并具有道德基础或道德必要的性质,因而,这种行为就被自然的造物主(上帝)所禁止或命令。”(52)
布赖恩·梯尔尼指出,上述定义也许是受到苏亚雷茨的直接启发,因此,格劳秀斯只是在宗教改革时代以一种新的写作方式重述了中世纪的理论。(53)但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中世纪到近代的政治法律思想转型的枢纽人物,格劳秀斯确保“法律并不仅仅是意志之体现”的观点得以劫后重生。(54)而且,更重要的是,格劳秀斯对格里高利和苏亚雷茨的“无神论假设”的接受,使得意志论实质上被悬置起来。
在《战争与和平法》的序言中,格劳秀斯首先从人类趋向社会的本性寻找法律的基础。他认为,确保人类社会秩序的存续是一切法律的渊源,同时对此又附加一个假设:即“如果没有上帝,或人类的事务与上帝无关”,上述理论仍然是有效的。(55)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轻易认为格劳秀斯是无神论者,因为这一假设从14世纪以来就被频繁引用,几乎成为经院哲学家普遍使用的惯用语。(56)而且,身处基督教神学传统之中的格劳秀斯,并没有明确将自然法与神学相分离的愿望,也从未想建构一种无神论的伦理观。(57)但是,这一假设毕竟为自然法从上帝意志的分离开启一种可能性。正如格劳秀斯所说:“自然法是如此不可改变,甚至连上帝自己也不能对它加以任何变更。尽管上帝的权力无限广泛,但有些事物仍然不受其左右。因为这些事物既不与具体现实相对应,也不会自相矛盾。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那么,他也不能使固有的恶变得不是恶。”(58)
实际上,早在格劳秀斯之前,西班牙经院哲学家加布里埃尔·瓦兹奎茨(Gabriel Vasquez,1549-1604年)已经指出:“上帝的意志或理性都不是善恶的首要标准,而是包括理性人的本性在内的事物本质。”(59)格劳秀斯虽然不如瓦兹奎茨激进,但是,他已经试图在上帝之外寻求自然法的根基。在早期著作《荷兰法学导论》中,他就指出:“人类的自然法是一种本能的判断,它使得人们根据其自身本性就能够判断何为廉耻。”(60)沿着这个方向,他在《战争与和平法》中确认自然法的本源时,认为首先是人类本性,其次才是上帝的意志,(61)并最终得出结论:“人类的本性……它引导我们相互走向社会的联系,正是自然法之母”。(62)
德国学者奥拓·基尔克(Otto Gierke)指出,当格劳秀斯及其他先行者,提出“假设没有上帝”自然法也不失其有效性的观点后,就会产生如下后果:近代自然法的后继者,完全可以放弃从上帝意志引申出自然法的观念,而直接求助于“自然秩序”,从而使自然法与上帝的联系逐渐消失。(63)换言之,近代自然法完全有可能建立在一个世俗的人性基础之上。例如,深受格劳秀斯影响的德国法学家萨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1632-1694年)(64)明确指出,“没有比通过仔细思考人类自身的本性、状况和欲望来学习自然法更合适和更直接的途径了”,因此自然法就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之中。(65)法国自然法学家让·多玛(Jean Domat,1625-1696年)借鉴哲学家笛卡尔所谓一切事物都形成无限数量的“自然秩序”(66)的哲学思想指出:“所有民法上的事物在其自身之中,形成一个简单而自然的秩序,并成为一个整体。”(67)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开篇就说:“有一个根本理性存在着。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68)可见,近代自然法思想家不再讨论上帝的意志,自然法的基础就在于人类的自然本性。
四、格劳秀斯论人类本性与自然权利
既然自然法的基础是人类本性,那么,它究竟是个体性还是社会性?对于这个问题,古典思想家的回答无疑是后者,他们认为,人不可能脱离社会状态和政治生活而孤独存在,所以“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存在。……人性本身就是社会性”(69)。但是这一点在格劳秀斯那里开始发生动摇。
格劳秀斯在《捕获法》中首先从人类自利和自爱的本性展开论证:“上帝创造万物并决定其存在,每一个别部分从上帝获得自然属性,借此维持其存在,并被引导向自身的善……从这一事实出发,古代的诗人和哲人正确地推断,其基本力量和作用都导向自利的爱,就是全部自然秩序的第一原理。从而,贺拉斯(Horace)不应因为他模仿柏拉图学派时说道:利己可以被称为正义和公平之母而受到责难;西塞罗也反复坚持,就本性而言,所有的事物倾向于精心地关照自己并寻求其自身的幸福和安全。”(70)
他由此推演出两条自然法则:(1)应当允许保护自己的生命和避免可能造成其伤害的威胁;(2)应当允许为自己取得并保有那些对生存有用的东西。(71)但是,格劳秀斯又说,上帝宣称如果每个人只为保全自我,而不关心同类的安全和幸福,这是不够的。“爱”应包括了自爱和他爱,前者是“欲望”,后者是“友善”。(72)人类必须与他人进行交往,并彼此确保安全,互不伤害,为此必须补充另外两项自然法则:(3)不得伤害他人;(4)不得侵占他人已占有之物。(73)
在此,格劳秀斯显然是从自我保存推导出人类的社会性,即自利的本性先于社会本性,人类结成社会、合作共生,是基于自利和自我保全的需要,相对于社会性而言,自我保全才是最为根本和优先的。(74)换言之,社会性是偶然的,人类仅仅需要一种较弱意义上的社会性,以确保最低限度共同体生活的要求。(75)但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强调的重心发生转移:“人类的特性是一种强烈的社交愿望,即一种与同类共营社会生活——和平的、基于人类理智的准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的愿望。这种社交倾向被斯多葛派称为‘合群性’(sociableness)。所谓的普世真理,即每个动物都被自然迫使而只寻求自身的好处,并没有获得承认。”(76)
接着,他又指出,有人说利己是公平正义之母,这有失准确;其实,导向人类联系的社会本性才是自然法之母。(77)这一表述,与《捕获法》中对“利己”毫无保留的推崇显然不同。(78)而且,格劳秀斯还将法律的本源界定为人类的社会性:“我们已经阐述,与人类理智相符的社会秩序的持存,就是法律的真正渊源。这个法律的范围包括:禁止对他人造成损害、返还他人的财物及收益、履行允诺的债务,赔偿因自己过错造成(他人)的损失,施予罪有应得者以惩罚。”(79)
总体而言,格劳秀斯并未赋予自我以绝对的优先性,也没有将个体与社会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两极。因此,我们还不能匆忙认定格劳秀斯已经完全倒向个人主义立场。但无可置疑的是,格劳秀斯通过自我保全的本性确认人类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捕获法》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自然法则(参见上文),实际上就是对生命和财产自然权利的确认。此外,格劳秀斯还将“天赋自由”类比为财产权。他说:“每个人的行为及对自己财产的使用,只应由自己决定,而不服从任何他人意志。这种观点得到所有民族的共同认可。“天赋自由”这个众所周知的概念,不就是指个人根据自己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力吗?行动自由相当于财产所有权。正如谚云:‘每个人都是关于自己财产事务的管理者和裁决者。’”(80)
根据自然权利论,格劳秀斯认为每个社会都要努力保护个人拥有的东西,包括生命、身体、自由,即使在法律和习俗制度尚未发明之前也应如此。(81)如果发生侵害个人的行为,每个人都拥有惩罚的权利。因此,国家的权力来自于私人惩罚权利的转让。(82)
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在格劳秀斯那里,自我与社会性哪一者更为根本和优先。至多只能认为,自利自爱和社会性都是自然法的两个基本原则。(83)但是,格劳秀斯已经由自利自爱和自我保存论证自然权利的存在,而且摆明自我与社会性何为本源的问题,后世的自然法学家只要沿着自然权利的思路,就会得出更为激进的结论。
普芬道夫首先对此作出回应。他在《自然法与万民法》中从“自爱”出发来论证社会性的产生和自然法的基础。他说:人类与动物一样,“对自己尽最大的关爱,力图以各种方式保护自我,并获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避免在他看来可能造成损害的事情”(84)。人们将自爱放在首位,是因为“他考虑自己的生命先于其他人的生命,这是他的本性”(85)。但是,除了自爱,人类限于自身的力量和时间,不能满足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因而还必须得到他人的帮助,并且自己也应该为他人作出同样有益的贡献。(86)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人类结成社会,对他人采取“合群态度”,即每个人都有义务对他人友善、和平与关爱。(87)但由于每个人原本无权要求别人履行上述义务,所以普芬道夫只好将相互负担这些义务归因于上帝的命令。(88)
普芬道夫也提倡自然权利论。他认为,自然权利的首要来源就是人类自我保全的本性,理由有二:其一,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和获取对人类公开的共同资源,以保存自我,但不得侵害他人权利;其二,自然状态下的人们,不服从于任何他人的指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和决定、都不处于他人权力之下,每个人也都是平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然状态就是一种“天赋自由”的状态。(89)
17世纪以后自然法学家更强调人类自我保全的本性和自然权利论。例如,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年)说:“每个个体应竭力以保存其自身,不顾一切,只有自己,这是自然最高的律法与权利。”(90)卢梭说:“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自身所应有的关怀。”(91)洛克将其政治理论奠定在生命、自由、财产这些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其中最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当属霍布斯。
霍布斯以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为起点,他指出,最大的损害莫过于死亡,“死亡的发生就其真正起于自然的必然性而言就如同石头必然要下落一般”,每个人都应尽全力去保护他的身体和生命免遭死亡,这与正确理性是相符合的行动,“因此,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92)为了保全自我,每个人需要获得有助于自我保存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可以拥有万物以及做任何事情,但如果缺乏公共权力机构维持秩序,人类就陷入一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从而没有法律和公正。于是,人们必须放弃或转让一些自然权利,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将所有权力交给一个集体行使,由此诞生国家。(93)
格劳秀斯还在自我与社会两极之间进行挣扎,而霍布斯则预设自然状态下绝对在先的个体,从而使自我保全“变成了一种绝对的天赋,绝对的冲动”(94),他将此作为唯一有效的论证起点,赋予个体以优先性。在卡西勒看来,霍布斯的方法是将整体社会分解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或元素,首先分析作为构成社会单元的个人本性,然后再通过社会契约将这些组成部分连结成一个整体,即由个体元素推演出社会整体和国家。(95)因此,由格劳秀斯提出的个体与社会的两极问题,完全被霍布斯推向极端,从而完成自然法向个人主义、权利本位的近代转型。
五、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在16、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在伽利略、培根、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取得巨大的成功。随着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的长足发展,自然科学方法也逐渐渗透各种社会科学之中。在欧陆最有影响的是勒内·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年)提出的直观和演绎方法。笛卡尔的方法,是从具有常识的人都会承认的一些确实而自明的原理开始,运用人类理性的推理能力,即可获得全部的知识,包括“直观”和“演绎”。所谓直观,就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产生的理性光芒,例如三角形具有三条边、圆周仅在同一个平面上等类似的定理;所谓演绎,“是从某些已经确知的事物中必定推演出的一切”(96)。完全适用这种演绎方法的是数学和几何学,因为它们能够从一些原则和定理中推演出一切知识。虽然其他科学不能达到犹如数学般的精确程度,但应以数学作为精确性、科学性的榜样。
笛卡尔方法固然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理性化具有极大的影响和助益。但是,早期自然法思想家,如西班牙经院哲学家以及格劳秀斯等,尚未接触到这种方法论。确切地说,直到理性法时代中期,自然科学方法才蔓延到自然法。霍布斯、斯宾诺莎、普芬道夫、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年)等人的著作才体现数学和几何方法的影响。(97)虽然如此,笔者基于格劳秀斯论著的研读发现,与经院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相比,他在方法论上确有重大改进之处,并预示理性主义方法论时代的来临。
格劳秀斯在《捕获法》第一章介绍全书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他首先引用西塞罗的观点指出,法律科学应通过推理而来,而不是得自于长官命令,因此,我们应该学习和运用自然推理方法。格劳秀斯所建议的推理方法如下:“首先,我们要确认什么是真正普遍的、一般性的命题;然后,我们逐渐缩小这种一般性,使其适合于当下所考虑问题的特殊本性。正如数学家常常在具体演算之前,先确定那些所有人都乐于认可的概括公理的预先陈述,从而据此证明一些可靠的论点。所以,我们也应该指明那些最具普遍性的法则(rule)和法律(law),将其作为预先假定,……目的在于给我们的其他推论奠定可靠的基础。”(98)
在随后的一章(《捕获法》“序言”)中,格劳秀斯完美地展示这种方法论。他从九项公理性的法则推论得出十三项法律,其推理方法显示出环环相扣、逻辑严密的特点。例如,他首先确立第一条公理性法则是:“上帝显示出来的意志就是法。”(法则I)既然万物是上帝根据自己意志的创造,那么他就让每一造物依其本性而存在,因此,每一造物都要“自爱”并保全自我,才能符合上帝意志,由此推论出两条法律:(1)应当允许保护自己的生命和避免可能造成其伤害的威胁;(2)应当允许为自己取得并保有那些对生存有用的东西(法律I、法律II)。(99)
接着,格劳秀斯又说,人类的理性源于上帝,由此产生第二条公理性法则:“体现人类全体意志的共同合意就是法(法则II)。”人类全体意志的存在基础是社会共同体,因此,他援引塞内卡的说法:“我们(人类)天生就要过与他人交往的生活。社会只有通过对其组成部分的关爱和悉心呵护才能确保安全、避免伤害。”“惟有相互确保安全,才能获得安全。”据此又推论得出另外两项法律:(3)不得伤害他人;(4)不得侵占他人已占有之物。前者保障生命安全,后者产生财产权观念。(法律III、法律IV)(100)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其全部论证,但通过以上介绍,他的演绎方法可见一斑。
在《战争与和平法》的序言中,格劳秀斯有意识地突出其方法论。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方法就是以自明的和具有体系特点的自然法公理为基础进行推理。因此,他希望首先明确那些不容置疑的自然法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他说:“只要你对那些法律原则予以严格的关注,它们显然都是自明的,几乎如同我们通过外在感官感知到的那些事物一样明显。”(101)不仅如此,自然法具有普适性,易于形成体系;相比之下,实在法容易变化,不适宜作为体系思考的对象。(102)
格劳秀斯认为,如果贯彻上述方法,可以预期《战争与和平法》能够达到如下三个目标:“(1)使得我给出结论的理由尽可能一目了然;(2)将需要研究的对象阐明为一个清晰的秩序;(3)明确区分各种相同以及不同的事物。”(103)在《战争与和平法》序言的结尾,格劳秀斯更自信地宣布:“我所断言的真理就是,在我论述法律时,已使我的心思完全离开任何特殊的事实,正如数学家在处理数字时完全把它们从物体抽离出来一样。”(104)
随后,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前几章作为基础理论探讨的概念,包括什么是正义、法律和权利,什么是自然法、神法和人定法,什么是战争(公战与私战)和正义的战争,什么是国家主权,等等。通观《战争与和平法》,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即使最复杂的问题,格劳秀斯也是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概念和公理出发,逐步进行推理论证,以获得可靠的结论。
格劳秀斯虽然身处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和人文主义学术传统中,尚未接触到近代理性主义方法论。但依笔者所见,格劳秀斯已经自觉运用一种类似笛卡尔的方法论,努力将法律的科学性与数学相类比。因此,笔者赞同哲学家卡西勒的观点,他说:“从格劳秀斯开始,法律与数学就被联系在一起,法律有如纯算术,因为关于数及其关系的算术学说包涵着一种永恒和必然的真理;即使整个经验世界被毁灭,即使根本没有用数来计算的人,也没有任何需要计量的对象,这种真理也不受影响。格劳秀斯在其杰作(《战争与和平法》,引者注)的序言中集中论证了这一点。”(105)
比格劳秀斯晚出的下一代自然法学家,更自觉地运用理性主义方法论。例如,托马斯·霍布斯希望摹仿数学的确定性建立一门哲学。(106)基于这一思想,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把世界看作由因果链组成的一架大机器,将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进行类比,认为人与钟表一样,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一切事物都可以按照机械规律进行计算。(107)人的基本能力就是推理,而推理不过是在内心进行加减运算,数学家在数字方面做加减,几何学家在线、形、角、比例、倍数、速度、力量等方面做加减,逻辑学家在词语序列、断言、三段论方面做加减。同理,政治学家把契约加起来确定人们的义务(社会契约论),法学家则把法律和事实加起来以找出私人行为中的是与非。(108)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更有过之,企图统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事件与自然事件一样,都处于一种因果序列之中。如果设想从一些自明的原则出发,用几何学方法进行论证,就能在道德领域建构像数学一样确实而普遍的真理系统。(109)在《伦理学》一书中,斯宾诺莎以定义、公理、命题、证明几个步骤,完成对伦理规则的几何学证明。
在德国,普芬道夫借助笛卡尔的方法,把推理与归纳、公理与观察、分析与综合等多种科学方法结合在一起,构造自然法体系。(110)他认为,自然法的结论如同数学公理一样可以被证实,因为法律和数学都是理智思维的产物,正如心灵能够凭借“天赋观念”完全自力地构建数和量的领域一样,它在法律领域也具有同样的建构能力。(111)此后,普芬道夫的继承人克里斯蒂安·托马休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年)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进一步奠定了近代自然法的科学化和体系化发展趋势。(112)
六、结论
综上所述,从格劳秀斯开始,近代自然法发生决定性转变,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古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遵循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的区分,(113)体现为自然法—实在法二元论。但是中世纪神学将二元论扩张为永恒法(上帝的理智或意志)—自然法—实在法的三元论,而且自然法始终位于永恒法之下,人类法律秩序根源于超越尘世的上帝。(114)但是,近代自然法思想家则将自然法归因于事物的自然理性,自然法以及整体人类法律秩序都获得独立性。正如卡西勒指出:“从格劳秀斯开始,(自然)并不是指事物的存在,而是指真理的起源和基础。无论其内容如何,凡属自身确定的、自明的、无需求助于启示的真理,都是属于自然的。人们不仅在物质世界,而且还在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中寻求这样的真理。17世纪将这两个世界合在一起,以构成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自足的宇宙。”(115)
由于近代自然法获得新的根基,即自然理性或人的本性,从而开启了自然法世俗化、理性化的进程。
第二,古典自然法把义务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要求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践行自己的义务,以成全共同体的普遍善。然而,自格劳秀斯以后,多数自然法思想家以人类的自我保全、自利自爱的本性作为论证起点,并确认自然状态下人类享有天赋自由,从而开启近代自然权利论。如此一来,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事实就不再是古典自然法学家所说的“义务”,而是“权利”。近代自然法教导人们如何获取和保护权利,权利才是界定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权利是根本性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义务不过是从权利中延伸出来。(116)就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而言,“人的自然权利先于一切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而存在。因此,国家的真正功能和目的在于把这些权利纳入它的秩序,从而保留并且保障这些权利”(117)。
第三,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l)在论述近代科学精神的起源时指出,数学在近代社会被赋予一种普遍的和无限的使命,即用数学对世界在整体上进行把握和控制。他说,数学给予我们的力量就在于:借助于数学我们能够对一切有形世界中展现的各种事物“作出一种完全新的归纳的预言,即能够根据已知的、被测定的、涉及形状的事件,以绝对的必然性对未知的、用直接的测量手段所达不到的事件作出‘计算’”(118)。在近代社会,数学的计算精神不仅运用在“数”的领域,而且由于其巨大的成功,使得它也侵入质的领域,(119)即体现纯粹理性的数学方法扩展到人类社会伦理的研究领域。正如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年)所说:“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从于计算的精确性”,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就是数学,他盛赞数学语言“是目前仍然存在的唯一真正精确的、真正分析性的语言”(120),并且把它推广到一切观念领域。因此,他相信道德科学和自然科学遵循相同的方法,都应该获得相同程度的精确性。(121)
应该指出,从格劳秀斯开始将法律与数学进行类比,近代自然法学家大多希望以自然科学的标准建构一个理性化的公理和规则的自然法体系。他们相信法学也适用理性主义方法论,即从抽象的基本概念、公理和原则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就可以得出一个概念精确、逻辑严密的理想法律体系。这种追求,对于古典自然法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但是,在格劳秀斯之后却成为自然法理论建构的常态。
尽管现代理论家对于格劳秀斯是否应该作为近代自然法的思想转折点仍然存在质疑,尽管格劳秀斯大量重述晚期经院哲学自然法思想,但评估一位思想家的贡献,不能仅仅从他是否提出个别原创性的理论命题出发,而应将其置于整个思想史脉络之中,观察其历史地位。根据本文的研究,格劳秀斯上承中世纪经院哲学自然法,下启近代世俗化、理性化的自然法,他标志着近代自然法的思想转型,无愧于“近代自然法之父”这一美誉。
注释:
①[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②[美]列奥·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1、148页。
③Franz Wieacker,A History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ermany,Translated by Tony Weir,Clarendon Press,1995,pp.227—238.[英]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湾联经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爱]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④[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5—68页。
⑤前引③,登特列夫书,第48页。卡内冈也赞同此说。参见R.C.van Caenegem,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Private Law,translated by D.E.L Johnst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18.
⑥J James Brown Scott,The Catholic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Francisco de Vitoria,Founder of the Modem Law of Nations,Francisco Suarez,Founder of the Modem Philosophy of Law in General and in Particular of the Law of Nations:A Critical Examination and a Justified Appreciation,Originally published: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34.THE LAWBOOK EXCHANGE,LTD.Clark,New Jersey,2007,p.127.
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9页。
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18—19页。
⑨See Robert N.Wilkin,"Cicero and the Law of Nature",Arthur L.Harding(ed.),Origins of the Natural Law Tradition,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Press,Dallas,1954,p.19.
⑩[意]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页。
(11)前引⑦,亚里士多德书,第120页。
(12)同上书,第137—138页。
(13)前引⑩,阿奎那书,第105页。阿奎那还论述道:“正如一个人的幸福并不是最后目的,而是从属于公共福利一样,任何家庭的幸福也必须从属于作为一个完整社会的城市的利益。”同上书,第106页。
(14)正如斯特劳斯所说,古典自然法学家不是教导人们如何争取个体的权利,而是教导人们如何尽义务。前引②,列奥·斯特劳斯书,第186页。
(15)[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17—218页。现代基督教思想家保罗·蒂利希总结阿奎那的思想指出:“理智意味着人在理性的意义和结构中生活的能力。不是意志而是理智使他成为人。人的意志是与低级动物所共有的;而人的理智,即人的心灵的理性结构是为人所特有的。”[美]保罗·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从其犹太和希腊发端到存在主义》,尹大贻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16)前引⑩,阿奎那书,第102页。
(17)前引(15),梯利书,第233页、第235页。
(18)同上书,第235页。
(19)Die ewige Wiederkehr des Naturrechts(Munich,1947),66转引自[爱]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20)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21)前引③,登特列夫书,第61页。
(22)[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3页。
(23)前引③,登特列夫书,第37页。
(24)前引③,登特列夫书,第68页。
(25)De justitia,2.2ae.62.1,转引自Brian 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Natural Law,and Church Law,1150-1625,Scholar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1997,p.259.
(26)Ibid.p.261.
(27)Vitoria,Political Writings,ed.Anthony Pagden,Jeremy Lawrance,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41,p.244,p.250.
(28)Ibid.pp.250—251.
(29)Brian 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Natural Law,and Church Law,1150-1625,Scholar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1997,p.271.
(30)Ibid.p.271.
(31)[德]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6页。
(32)[英]约翰·马仁邦主编:《劳特利奇哲学史Ⅲ:中世纪哲学》,冯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33)Suárez,De Legibus,ac Deo Legislatore(A Treatise on Laws and God the Lawgiver),in Selection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árez,J.B.Scott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44,p.30.
(34)Suárez,De Legihus,4:2.14.2,17,转引自Brian 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Natural Law,and Chrch Law.1150-1625,Scholar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1997,p.306.
(35)Suárez,De Legibus,ac Deo Legislatore(A Treatise on Laws and God the Lawgiver),in Selection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árez,J.B.Scott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44,p.186.
(36)Ibid.p.271.
(37)Ibid.p.53.
(38)Ibid.p.54.
(39)Ibid.p.70.
(40)昆廷·斯金纳指出,根据理智论强调自然法独立于神启或《圣经》是西班牙经院哲学的主流思想。参见[英]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宗教改革》,奚瑞森、亚方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13—214页。
(41)See M.B.Crowe,The "Impious Hypothesis":A Paradox in Hugo Grotius? In Grotius,Pufendorf,and Modern Natural Law,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Datmouth,Ashgate,1999,p.16.
(42)前引③,J·M·凯利书,第178页。
(43)Cited from M.B.Crowe,The "Impious Hypothesis":A Paradox in Hugo Grotius? In Grotius,Pufendorf,and Modern Natural Law,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Datmouth,Ashgate,1999,p.21.
(44)Suárez,De Legibus ,ac Deo Legislatore(A Treatise on Laws and God the Lawgiver),in Selection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árez,J.B.Scott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44,p.190.
(45)See M.B.Crowe,The "Impious Hypothesis":A Paradox in Hugo Grotius? In Grotius,Pufendorf and Modern Natural Law,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Datmouth,Ashgate,1999,p.16.
(46)Suáfez,De Legibus,ac Deo Legislatore(A Treatise on Laws and God the Lawgiver),in Selection from Three Works of Francisco Suárez,J.B.Scott ed.Oxford:Clarendon Press,1944,p.194.
(47)Ibid.p.191.
(48)Brian 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Natural Law,and Church Law,1150-1625,Scholar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1997,p.327.
(49)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Translated by G.L.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p.8,p.12,p.18,p.23.
(50)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14.
(51)从《战争与和平法》的引注资料中,显示格劳秀斯熟悉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的观点。See M.B.Crowe,The "Impious Hypothesis":A Paradox in Hugo Grotius? In Grotius,Pufendorf,and Modern Natural Law,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Datmouth,Ashgate,1999,p.9.
(52)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p.38—39.
(53)Brian 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Natural Law,and Church Law,1150-1625,Scholar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1997,p.327.
(54)前引③,登特列夫书,第69页。
(55)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p.12—13.
(56)See Brian 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Natural Law,and Church Law,1150-1625,Scholar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1997,p.319.See Knud Haakonssen,Hugo Grotius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In Grotius,Pufendorf,and Modern Natural Law,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Datmouth,Ashgate,1999,pp.44—45.
(57)See M.B.Crowe,The "Impious Hypothesis":A Paradox in Hugo Grotius? In Grotius,Pufendorf,and Modern Natural Law,Edited by Knud Haakonssen,Datmouth,Ashgate,1999,p.5.
(58)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40.
(59)Welzel认为,瓦兹奎茨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上帝不过是何为正当的引导者,而不是法律的创设者,自然法完全可以脱离上帝而寻求其世俗化的起源和基础。Welzel,Natur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Goettingen,1951,p.97.转引自前引③,J·M·凯利书,第179页。
(60)Hugo Grotius,The Jurisprudence of Holland,translated by Robert Warden Lee,Vol.I,Scientia Verlag Aalen,1977,p.5.Richard Tuck指出,这一自然法的定义,脱离了意志主义传统,上帝的意志不是道德品质的唯一渊源,事物的善恶来自于它们自己的本性,而且在逻辑上,先于上帝的指令或禁令。Richard Tuck,Natural Rights Theories:Their Origin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68.
(61)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p.12—14.
(62)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p.15.
(63)Otto Gierke,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1500-1800,Translated by Ernest Barker,Cambridge,1950,p.289.
(64)普芬道夫明确承认受格劳秀斯的影响很大。John Macdonell ed.,Great Jurists of the World,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14,p315.
(65)Samuel Pufendorf,De Jure Natr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On the law of Nature and Nation in Eight Books),Translated by C.H.Oldfather and W.A.Oldfath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34,p.205.
(66)[法]勒内·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2、53页。
(67)Jean Domat,Civil Law in its Natural Order,Translated by William Strehan,LL.D.,Boston:Charles C.Little and James Brown,1850,Vol.I,p.96.
(6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
(69)前引②,列奥·斯特劳斯书,第130页。
(70)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Translated by G.L.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p.9.上述思想延续在《荷兰法学导论》中:“正如一切事物均要寻求普遍的善,因而它们都拥有自我保存(本性);正如动物通过雌雄结合孕育和抚养它们的后代;人类也如此行事是有意识地做正当的事。但是,因为人类是理性存在物,他更进一步地被引导向宗教以及理性地与他人交流沟通,并且其基础在于:你如何对待他人就如同希望他人将如何对待你。”Hugo Grotius,The Jurisprudence of Holland,translated by Robert Warden Lee,Vol.I,Scientia Verlag Aalen,1977,p.7.
(71)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Translated by G.L.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p.10.
(72)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Translated by G.L.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p.11.
(73)Ibid.pp.13—14.
(74)See P.C.Westerman,The Disintegration of Natural Law Theory,Aquinas to Finnis,Brill,1998,p.140.
(75)[美]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罗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页。
(76)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11.在另一处,格劳秀斯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如西塞罗说,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夺取他人的所有,是与自然本性相违背;………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人类社会以及普遍的善就必然遭到破坏。……塞内卡也说,每个个体的保全都有利于整体的福利,这是由于我们都是为了社会共同体而生,因而人们之间应避免相互损害。社会只有通过人们的互爱和对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才能持存。”Ibid.,p.34.
(77)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15.
(78)塔克也注意到格劳秀斯对“利己是正义之母”前后不一致的表述,并认为格劳秀斯是想让持亚里士多德观点的人更容易接受格劳秀斯。参见(美]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罗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18-121页。
(79)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p.12—13.
(80)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Translated by G.L.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p.18.
(81)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54.在另一处谈到法律对自然权利的保护时,他说:“要是以合法的方式获取的所有权及其他权利,自然法就规定:不能毫无理由地剥夺这些权利。”Ibid,,p.385.
(82)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Translated by G.L.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p.92.
(83)See Brian Tierney,The Idea of Natural Rights:Studies on Natural Rights,Natural Law,and Church Law,1150-1625,Scholar Press for Emory University,1997,p.323.
(84)Samuel Pufendorf,De Jure Natrurae et Gentium Libri Octo,Translated by C.H.Oldfather and W.A.Oldfather,Oxford:Clarendon Press,1934,p.205.
(85)(86)Ibid.p.207.
(87)Ibid.p.208.
(88)Ibid.pp.217—218.
(89)Ibid.p.158.在《论基于自然法的人和公民的义务》中,普芬道夫也谈到:“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除了服从上帝和对自己负责,不服从于任何人的权威,自然状态又称为自然自由。”Sarnuel Pufendorf,On the Duty of ran and Citizen According to Natural Law,Translated by Michael Silverthorne,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90)[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2页。
(9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页。
(92)[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在《利维坦》中霍布斯重申了这一点:“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7页。
(93)[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2—132页。
(94)前引(22),海因里希·罗门书,第86页。
(95)[德]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249页。
(96)前引(66),勒内·笛卡尔书,第12页。
(97)See Franz Wieacker,A History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ermany,Translated by Tony Weir,Clarendon Press,1995,p.204.
(98)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Translated by G.L.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p.7.
(99)Ibid.p.10.
(100)Hugo Grotius,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Prize and Booty,Translated by G.L.Willia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50,p.13—14.
(101)Hugo 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23.
(102)Ibid.p.21.
(103)Ibid.p.29.
(104)Ibid.p.30.
(105)前引(95),卡西勒书,第230页。应当指出,在《战争与和平法》的另一处,格劳秀斯直接将数学和自然法作类比,以证明自然法的不可改变性,“正如即使上帝也不能使二加二不等于四,那么,他也不能使固有的恶变得不是恶。”Hugo Grotius,DeJure Belli ac Pacis,Translated by W.Kels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p.40.
(106)参见[英]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志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107)参见前引(93),霍布斯书,第1页。
(108)参见前引(107),霍布斯书,第27—28页。
(109)参见前引(15),梯利书,第327页。
(110)See Franz Wieacker,A History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ermany,translated by Tony Weir,Clarendon Press,1995,p.245.
(111)前引(95),卡西勒书,第230页。
(112)See Franz Wieacker,A History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ermany,translated by Tony Weir,Clarendon Press,1995,pp.251—255.
(113)前引(8),亚里士多德书,第149页。
(114)See Franz Wieacker,A History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ermany,translated by Tony Weir,Clarendon Press,1995,pp.207—208.
(115)前引(95),卡西勒书,第235页。卡西勒还指出,与伽利略捍卫了数学物理学的自律一样,格劳秀斯指出法律知识不是天启,而是由事物的本性所决定,从而为法学赢得了自律,因此他可以与伽利略在自然科学上取得的成就相媲美。前引(95),卡西勒书,第235页。
(116)参见前引②,列奥·斯特劳斯书,第185页。斯特劳斯在政治哲学领域,是对近代自然权利观最有力的批判者。
(117)前引(95),卡西勒书,第243页。
(118)[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论的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119)参见前引(95),卡西勒书,第22页。
(120)[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2页。
(121)参见[美]托马斯·汉金斯:《科学与启蒙运动》,任定成、张爱珍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