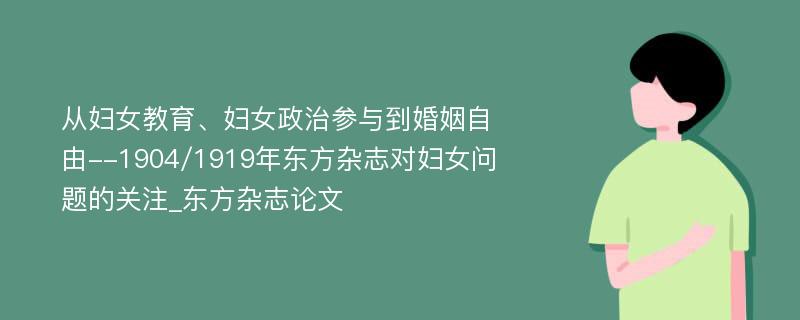
从女子教育、妇女参政到婚姻自由——1904-1919年间《东方杂志》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年间论文,婚姻论文,女子论文,杂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4-0177-09
《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历时最长的大型综合性杂志。“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思想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①自创刊以后,妇女问题就受到了它的关注。本文研究它自创刊(1904)到1919年这段时间内对妇女问题的探索。从创刊到1907年,女子教育是《东方杂志》关注的重点;辛亥之后,妇女参政问题吸引了它的目光;1915年以后,婚姻问题则成为它争论的焦点。除此之外,女子职业问题也得到了它的关注。这三个问题前后相续,正与此时中国社会妇女问题的发展变化相一致,也与当时世界妇女运动的潮流相关。
一、热心女子教育
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男女在受教育方面极不平等。不仅很少有女子接受教育,女子更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之外,没有外出求学的机会。即使是官宦之家的女子也只能是在家庭内接受教育,教育内容无非是纲常伦理之类,目的是使女子学习为妻、为母之道。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目的在中国开办女学,开了风气之先。至于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女学则是到了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开办经正女塾。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兴女学,提出了“相夫教子”、“兴国智民”②的教育观。随着中西交往的增多,兴女学的思想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同,民间和教会办的女学也不断增加。
《东方杂志》从创刊之始就开始关注女子教育,它从中国古代和西方为兴女学寻找根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引进新事物的惯常方式。凡一新事物,若是古已有之,那么就可以拿来堵一部分反对者的口,对于女学也不例外。《东方杂志》强调女学古已有之,以此来对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它指出“妇学见于周官,师氏见于风诗。以女子为不必学者,古无有焉”③。近代西方是中国的一个参照系。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衰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凡西方所以强大之理由都可以拿来鞭策中国,也可以成为中国必须加以改变的理由。西方的女子教育成就卓著,正可以作为中国兴女学的有力理由:“西国教育不偏于男子,故虽弱质裙钗,亦多读书明理,而其尤者乃能陶铸人心,破坏专制。”④“东西洋国力之浸盛,由于女学勃发。”⑤
至于兴女学的诸种好处,《东方杂志》则是从女学与母教(或蒙学)、女子与男子的关系、女子与社会风俗的关系这些角度来讲的,归根结底兴女学是为了强国。它反复强调的内在逻辑是强国需要人才,人才来自教育,教育须从儿童教育(或蒙学)开始,而儿童教育来自母教,母教来自女学。“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盖欲强国者必以教育人才为首务,岂知生材之权实握乎女子之手乎!儿童教育之入手,必以母教为基石。女学不兴,虽通国遍立学堂,如无根之木。”⑥“国家强弱之大原在教育,教育之大本在家庭。家庭教育者,所以立蒙养之基础而作成人之本始,实为万化之原,故女学最为重要。”⑦这些思想与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的言论如出一辙。1897年,梁启超就提出:“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⑧
女学与社会风俗的关系也至为密切:“凡社会人情之趋避大都偏视女子之习向好恶以为衡。……如英吉利贵女重视海军中人,其缔婚恒以得匹海军士官为荣,故英人多乐从海军。德之女子重视陆军中人,……故德之人多艳羡陆军。”⑨女子与社会风气相关,所以要兴女学,改良社会风气以强国。
女学不兴、女子无学对男子不利⑩:(1)女子无学则无法执业,成为分利之人,男子为其所累,因此女子无学则害男子之生计。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就曾拿这种分利生利说来作兴女学的理由。他指出“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者”(11)。女子分利由于女子无学,所以无业。(2)女子无学,以妖艳媚惑男子,使男子沉溺享乐、损害身体,所以女子无学则害男子之身体。(3)女子无学对男子之品格有害。夫妻关系最亲密,“其妻苟贤,虽强顽之徒间或为其感悟;其妻苟不贤,虽明理之人亦或被其转移”(12)。
除了宣传女子教育的意义,驳斥保守人士的非议外,《东方杂志》还为兴女学献计献策。关于如何兴办女学,它提出“教育之法,当以德智体三育并重。男子然,女子亦然”(13)。但尤其强调德育,“以吾国风俗人情论之,则三者之中,实宜以德育为重”(14)。其德育的内容,“非必世俗之以无才为德也。内则所载、女诫所言固不可以稍背,而国家思想、公共观念亦不可无”(15)。目的在于“使女子有国家思想、公共观念,以为异日陶铸幼童”(16)。因为“家庭之间若无国家思想,则男子出而任事必薄于爱国之感情”(17)。而在伦理方面则“不外孝舅姑和妯娌,相夫教子数端”(18)。具体做法是,先从贤妻良母派入手,同时注重国文教育以激发学生的爱国心。这些不过是传统的女德加现代国家观念的混合体,要使女子具有旧道德和新思想,既能成为传统家庭的贤妻良母,又能够成为具有现代国家观念的未来国民之母。
女学虽在当时引起人们关注,兴女学的诸多好处、女学与强国的关系被再三强调,但是女学在国家的教育体制上仍无明文规定,因此女学没有合法地位。这种状况直到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改变。由此,女子才有了接受学校教育的合法权利。此前,女学多开在上海等思想开放地区,因此让女子就学并非易事,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方法。为此,《东方杂志》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女学的建立、强制入学、学费的缴纳、中西教员的选派、教学经费的筹措等提出了一系列方法:“明谕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州县,无论城市乡镇,有子女者,每百家设一高等蒙学兼设一女学。高等之蒙学男女自六岁至十二岁不入学者,罪其父母”,“按编户上中下三等,岁缴学费若干”,“其中西教员由各省学务处慎选充,厚其薪资,严其考核”。在经费上如果难以筹措,则建议移用21行省民间建醮、演剧、出会等的费用(19)。传统社会女子结婚早,“早婚者举其修学年龄最要之部分消磨于治家养子之事,虽有美质,亦终归无用”(20),所以为了兴女学,还要禁早婚。
办女学必须有章可循,人们才不至于茫然无措。为此,《东方杂志》刊登了许多女学堂的章程,为各地兴办女学提供了参考,如《直隶天津县详送试办女学章程》(21)、《日本东亚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速成师范学堂章程》和《日本实践女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规则》(22)、《北京预教女学堂章程》(23)等,这些章程的制定也可以体现出当时兴女学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兴母教,培养贤妻良母,“人才最重母教,母教不明人才何出。创女学所以立他日母教之基”(24)。1907年《东方杂志》还刊录了《学部奏议女子师范学堂及女子小学堂章程折(章程附)》(25)这一使女子教育获得合法地位的重要文献。此后直到1919年,它就很少再关注女子教育问题了。
在《东方杂志》创刊之前,中国的女子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近代中国最初的女子学校教育是由教会开办的。早在1844年,爱尔德赛就在宁波创办了女塾,只是由于当时风气未开,加之人们对教会充满敌意和猜疑,入学者甚少。后来教会开办的女学在通商口岸地区逐渐发展。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1851年美国圣公会的琼司女士在上海设立文纪女塾。1844年至1860年间,教会在五个通商口岸共设立了11所女子普通学校(26)。19世纪80年代后教会女学的招生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并有了女子中学,如上海的中西女塾。到1902年全国教会学校中已经有女生4373人(27)。20世纪初年教会开始在中国办女子高等教育。教会在中国办女学的初衷无非是为了传教培养人才,但是教会女学的发展为中国女子教育提供了示范,开通了风气。
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女学则是到了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才出现。戊戌维新时期,维新人士大力兴办女学,认为女学关系母教,母教影响人才培养。要强国就要兴女学。在这中间梁启超是兴女学的积极鼓吹者。受梁启超的影响,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经正女学。1898年6月经正女学正式开学,它是国人开办最早的女学。虽然它于1900年停办,但是风气既开,国人纷纷创设女学,如1901年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开办爱国女学,1902年吴怀疚在上海创办的务本女塾。不过这一时期的女学集中在东部沿海和通商口岸地区,尤其是上海。1901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内容之一,科举废,学校兴。女学虽然已经在民间多有开办,但是清政府1902年8月15日公布的《壬寅学制》中并无提及女子教育之处,不过该学制并未实施。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施了的学制。该学制仍未给女学以应有的地位,女学被纳入家庭教育之中,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28),但是毕竟女子教育成为了教育的内容之一。此后创办女学成为一股社会潮流。1907年3月,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及《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从此中国女子教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可以说在《东方杂志》创刊之前,中国国内的女子教育,无论是教会所办,还是国人自办,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女子教育并未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女子教育更多的只是民间行为。从《东方杂志》创刊(1904年)到1907年这段时间内,正是中国的女子教育被纳入清政府官方学制体系的过程,也就是女子教育获得合法地位的过程。《东方杂志》这一时期刊登的关于女子教育的文章,正反映了此一时期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女子教育问题的认知程度。它热心提倡女子教育,但只是把女学作为强国的手段之一,终极的目的不是为了妇女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男子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强盛。这和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等人的看法并无二致。在教育宗旨上则注重德育,强调传统的女德,但也提出要让女子具有国家公共观念,培养女子的爱国心。它对女学的这种认识和1907年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宗旨相吻合。它所强调的兴女学的理由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子教育的普遍认识,即女学被置于强国的背景之下,人们注意的是它对于国家的意义,正是这种社会共识,女学才得以纳入清政府的官方学制体系,获得官方承认。在《东方杂志》关于女学的文章中,女学对女子自身的意义则被忽略,这也是近代以来在许多事情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因为落后于西方,急于迎头赶上,所以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一目的,也都可以此作为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以减少阻力,至于事物自身所蕴含的意义则往往略而不谈。
二、关注妇女参政运动
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有少数女子曾经获得了最高统治权,但是在制度上,女子参政不具有合法性,妇女参政历来受人非议。辛亥革命前及革命中,妇女们曾为民国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盟会中更是不乏女性。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妇女要求同男子一样获得参政权,民初的妇女参政运动曾经轰动一时。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给妇女以参政权,一部分妇女为争取参政权而组织团体,甚至采取激烈行为,但是随着1913年11月13日女子参政同盟会被内务部勒令解散,女子参政运动沉寂下去了。这次轰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虽然无果而终,但是却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女子参政问题。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运动也在广泛开展,尤其是英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尤为激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国以后,《东方杂志》开始关注妇女参政问题,初时曾对国内的妇女参政运动简略评说,但并无详细报道,即使在文中提到也不过是只言片语。它的主要的贡献是把世界各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成果和发展状况及时展示给国人。
1912-1913年,正是国内妇女参政运动兴盛之时,1912年5月1日《东方杂志》录《大共和报》译稿并注,指出:“近女子参政之声,呶呶于耳,使人不耐烦。平心而论,吾国男子无参政能力者尚多,况女子乎!明理者已多辨其不当,而女子犹不知止。故吾特译注是篇,以为他山之石,可以功错云而。”(29)文中列举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对妇女参政的言论,并加按语以反对当时国内的妇女参政运动(30)。罗斯福说自己非不赞成妇女参政者,但男女各有天职,不能弃天职而损害国家和人类文明。妇女参政影响婚姻,而男女第一责任在为贤父良母,可以让妇女自由出入政界,但是不能使社会受其害。罗斯福认为妇女对社会的感化力非常薄弱,所以妇女参政对社会改良的实际效果尚有疑问(31)。罗斯福虽未明言反对妇女参政,但是对妇女参政的消极后果却所论多有,这正符合当时中国国内反对妇女参政者的心思。所以该文在按语里根据罗斯福的言论,对妇女参政多方反对。译者认为,男女分业,女子主内,“他日社会进化,内政不必由妇人主持,则妇人欲得参政权,宜与之”,“惜今日尚非其时”(32)。中国妇女昌言参政的不过数十人,只在南京、上海等处,不能以此认为其参政要求得到女界的同意。“况吾国女子,素锢闺中,文明教育一时犹未普及,遽欲实行参政,是未学操刀而制锦也。”(33)贤妻良母之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抚育子女是女子天职,若因参政而不事生育则于社会国家为祸甚大。女子天性温柔敦和,无刚果宏毅之风,所以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很小。
1912年9月1日,《东方杂志》上刊登了陈霆锐的译作《世界女子参政之动机》,介绍了美国、英国、英属殖民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俄罗斯及其属国、奥地利、匈牙利及巴尔干岛诸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及其属国等国家妇女获得参政权的情况。作者在译者案中指出欧美女子从事职业,能够自立,因而有参政的资格,但我国“女子中之有普通智识者,仅千之一万之一而止耳。……吾固知其有参政资格也,然其奈此大多数目不识丁之女子何哉?故吾谓今日中国女子所亟当请愿者,在予全国女子以教育,不在参政权之有与无也。若女子教育,已能普及,徐议参政,未为晚也”(34)。
这两篇文字是难得的《东方杂志》对国内妇女参政运动进行正面评说的文字,且都是在译作的按语中表明作者的看法,无论是认为女子的天职是主内为良母,还是认为女子教育程度不够无法参政,都反对在当时给妇女参政权,不过不否认将来妇女可以获得参政权。由此可知,《东方杂志》并非绝对反对给妇女参政权,只是鉴于中国妇女当时的情况而反对,所以1913年后当国内的妇女参政运动平静下去以后,欧美妇女参政运动尤其是英国却异常激烈,而《东方杂志》密切注视其发展动态,对其每一变化都译文介绍,并未回避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中妇女的激烈行为。
20世纪初,西方国家妇女经过一番斗争在参政权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东方杂志》介绍了法国、英国、瑞典、挪威、意大利、俄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妇女参政权的情况(35)。但是1913年以后它主要关注英美两国的妇女参政运动,尤其是英国,无论对其历史还是现状,都有文章论述。如介绍英国自17世纪末叶以来直到当前妇女地位的变化和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过程(36)。1832年英国在选举法中,加“Men(男)”于“Person(人)”字之前,使妇女不得参与议员选举。1850年规定法律中所称之“Men”,“非有特别之制定,不得包括妇女”(37)。1867年,国会议员约翰·穆勒在议会讨论选举法修正案时提出削去“Men”,使男女平等,均获选举权。国会中有妇女参政权问题由此开始。此后有妇女参政团体相继成立。1903年全国妇女社会政治会成立,由战斗派妇女政治家班霍斯德夫人(Mrs.Pankhurst)领导。1910年妇女选举权案在下议院被提出,但是几经周折最终因全国妇女社会政治会的激烈行为激起公愤而未得通过。妇女社会政治会最初时行为尚且稳健,后来行为日益激烈。在商业繁华区见窗即砸,试图袭击博物院的藏书楼,毁园林、杀花木、藏炸药、毁寺观,“殆无日不以破坏为事”(38)。她们因此被捕,在狱中也坚持抗争,相约不守狱则:却罪服、拒劳役、抗狱吏、绝食。1912年10月英国妇女争取参政权者分裂为温和派与强硬派(39)。1913年1月23日,英国下议院提议修正女子参政案,首相爱斯克斯明确反对给妇女参政权,“妇女参政案,不得已而被取消”(40)。此后强硬派更采取激烈行动,不惜闯入议会,遭逮捕。她们在狱中采取绝食斗争。1914年2月8日,英国妇女参政会首领班霍斯德夫人在伦敦举行示威运动,1914年9月1日的《东方杂志》就报道了这一事件及此后女权党人的激烈行为,如:班霍斯德夫人当众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讲、与会者与警察发生冲突、班霍斯德夫人被捕后在狱中实行绝食同盟、女权党人毁坏价值四十五万元之名画、放火焚烧公私房屋、毁损邮件、袭击监狱医生、乔装成男子入议会旁听席等(41)。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妇女参政运动暂时平静下来,《东方杂志》则重视妇女们在国内忙于支持本国政府的参战活动,如德国妇女代替男子从事各项职业,英国妇女激励男子从军,对于以“在国内有必要业务”为借口不参军的男子,“先夺其职业”(42)。由此预测妇女参政运动的将来,关注妇女参政运动在战争中和战后的发展。英国妇女在战争中代替男子从事各种职业,所以战后“妇人参政权问题似乎应当如愿以偿,可无疑义”(43)。因各国女子在战争中的表现,所以预料战后妇女参政权问题可以解决,并且认为女子参政有利于世界和平,因为“女子之性质为兼爱的温慈婉顺”,“政府及国会中有半数慈祥柔顺之分子,野心家之势力将大减削”(44)。
民国以后《东方杂志》关注妇女参政问题,这和当时国内的形势不无关系。辛亥革命的成功女子也有一份功劳,诚如江纫兰所说:“鄂江起义,四方响应,吾女界联合同志,号召从戎,若龙韵兰、文乐迦诸女士,运筹帷幄,奋勇疆场,诚足为民国元勋。厥后义风所激,杰士踵兴,而女子北伐军、女子后援会遂出现于淞滨沪渎间。至若战祸方殷,张竹君女士发起中国赤十字会,以救护军人,保障人道为宗旨,弹雨枪林,活人无算,尤开中国未有之盛举。而女子劝捐会之成立,或撤环助饷,或出队募捐,即贫寒女士,亦举针指勤劬之所积,慨以委之军需,民军饷糈之不甚匮乏,吾女界实有力焉。”(45)女子既然在革命中尽了和男子同样的义务,革命胜利后当然希望享有和男子同等的权利,要求和男子一样拥有参政权。但是革命胜利后,虽然孙中山在1912年1月5日林宗素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来见时面允国会成立女子有完全参政权(46),但立刻遭到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反对,“乃闻一女子以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虽未明定法令,而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古人有言,慎尔出话。愿大总统思比良箴也。”(47)孙中山解释说:“至女子参政,自宜决之于众论。前日某女子来见,不过个人闲谈。”(48)表明其在女子参政问题上,只能表示个人赞同。民初女界为争取女子参政权组织纷纷组织团体,如吴木兰组织女子同盟会、沈佩贞组织男女平权维持会、张昭汉与伍廷芳夫人联合发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上海女界组织中华女子竞进会、浙江女界组织女子策进社、湖南女界成立女国民会、广东女界组织女权研究社等。但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未将女子参政权写入,此后的临时参议院也否决了女子参政权的议案。以致发生了请愿女子大闹参议院的风波。这引起社会舆论不满,多怀疑女子的参政能力。临时参议院北迁后,讨论国会组织法与选举法,女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仍未获通过。国民党改组以后也删除了“主张男女平权”的政纲。宋教仁更是反对女子参政。虽然一部分女子为争取女子参政权四方奔走,在报章发表言论。张纫兰更列举了给女子参政权的十种理由,从能力、经验、历史、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家政进步、社会进化、天赋人权、刑事诉讼、监督国务、造就人才等方面论证,得出结论:“民主共和,实行平等主义,男女平等,即男女平权。”(49)但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多反对给女子以参政权,《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时报》、《民立报》多有文章质疑女子的参政能力(50)。民初的妇女参政运动只如昙花一现,在1913年后便沉寂下去了。与其他媒体相比,《东方杂志》在女子参政运动激烈开展期间,也未有详细的正面报道,有的不过是在译述西方妇女参政运动文章后的简单按语。即使这样的文章也不过两篇,这在其介绍妇女参政的文章中所占比重很小。从这两篇文章的按语中也可隐约窥见它对国内妇女参政的态度,它虽不是摇旗呐喊的激烈反对者,但是也不赞同,起码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女子参政的条件。这或可解释它对当时妇女参政运动未加详细报道的原因。这也正和民初中国社会对妇女参政权的态度相吻合:多数人怀疑妇女参政的能力,不赞成在当时给她们以平等的参政权。1913年后,《东方杂志》刊登了大量介绍西方妇女参政运动的译文,即使是英国女权党人的激烈举动也有详细的文字介绍,但是此后它对中国的女子参政问题始终未置一词。20世纪初西方的妇女参政运动,尤其是英美两国发展很快,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它以旁观者的角度密切关注西方的妇女参政运动可说是因应了世界妇女参政运动的潮流。只是国内妇女界的形势非欧美可比,它虽极力向国人展示欧美妇女参政的斗争和成绩,却始终未提出要国内妇女效仿。这或可以说是反映了《东方杂志》对妇女参政问题的态度:关注而非提倡。
三、婚姻问题上的论争
中国传统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男女双方毫无自主权。在这种婚姻中女子受苦尤深,男子可以纳妾,可以休妻,女子妒忌却是恶行。宋以后女子更无再嫁的权力。婚姻论财讲门第,仪式繁琐,且早婚现象严重。破除旧婚姻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部分。晚清以来,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和西方婚姻制度被介绍进来,进步人士就力图仿效西方,改革旧婚姻,实现婚姻自主。新文化运动中,旧婚姻遭到猛烈抨击,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被提倡。许多青年为反抗旧婚姻而离开旧家庭,也有女子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51)。但是青年们通过自由恋爱组织的新家庭也并非都美满。人们在盲目追求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以后发现自由结婚也非尽善尽美,西方美满婚姻也不是只凭恋爱。婚姻到底应该由父母做主还是男女双方自主,一时间成了争论的焦点。
1915年以前,《东方杂志》就介绍过西方妇女在婚姻家庭上享有的权利,如美国妇女在财产方面离婚时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对子女有同样的抚养义务(52)。挪威妇女在家庭财产上与丈夫共有,离婚时两人均分。婚姻由男女自主,离婚上也男女平等,女子可以提出离婚,并且有分居制度以解决夫妻中有一人不愿意离婚的情况(53)。1915年以后,《东方杂志》注重婚姻问题,伧父(54)与恽代英围绕婚姻主权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
伧父说自己从前对自由结婚曾经心向往之,且曾与守旧人士辩论,可是中年以后思想变迁,转觉我国往日礼教“较自由结婚理论更为精当”(55)。他以甲代表昔日主张自由结婚的自己,以乙代表今日主张礼法婚姻的自己,通过让两者展开争论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观点(56)。甲认为夫妻终身互相结托构成家庭养育子女,关系个人幸福,所以要在婚前详慎选择。我国礼俗仅依父母之命凭媒妁之言,让素不相识的男女结为夫妇,无异于拈阄掷骰。乙则认为父母学问见识或未必尽胜于子女,但大体而论作家室之道比子女有经验。而青年男女则血气未定,听其自行选择则对于将来的幸福不无危险。西方虽实行自行选择但也要父母同意,且西方人结婚年龄较长,谋虑自深。而我国则早婚之习未除。所以要父母做主。甲说今之父母为子女选择配偶于学识品行体格性质多不考察,而仅以金钱门第为重。所以不合理。乙则提出输入西洋结婚学来补救父母不能为子女慎重选择的弊端。西方自由结婚男女惑于金钱与势力而危及幸福的也有。甲认为恋爱关系复杂神妙父母无法参与。乙则反驳说恋爱父母固不能参与,但是就幸福而言,则要依从有经验且忠实者之教训。甲指出乙把恋爱和婚姻分割开了,婚姻要以恋爱为基础。乙则强调恋爱与幸福是两回事,恋爱也有不幸福的。恋爱为大圆,幸福为小圆,选择配偶注重恋爱不如注重幸福。甲认为结婚由于恋爱,恋爱神圣。乙则认为恋爱由于兽性,但非含侮辱之意,不过是言此人与动物相同。结婚的最高主义在繁殖子孙。甲认为我国现在要矫正幽闭女子的风气,必须开男女交际,男女交际则不能禁止恋爱的发生。乙则反驳我国农工劳动社会男女共同操作自由谈话,并不发生自由结婚的风习。这“实礼教防维之效也。吾国有此礼教,吾人不可不保存之。西洋诸国以无此礼教之故,今日虽有哲人志士大声疾呼,冀唤醒青年恋爱之迷梦,卒无大效果。吾人可不警乎”(57)!
恽代英则针对伧父的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结婚的主权应该属于男女自身还是男女的父母,就我国社会看,其主权属于男女的父母的弊端很明显;从西方社会和我国一二自由结婚的成绩看,其主权属于男女自身的弊端也不可掩饰。他因此就结婚权属于男女自身和属于父母两种方式的理由分别进行评说(58)。主张结婚主权应该属于男女自身的人认为夫妇终身互相结托,所以应由自己详慎选择。男女为自己选择必较父母代子女选择详慎。结婚为恋爱的结合,所以必由子女自主。恽代英则指出男女自己选择详慎与否无法担保,人们为自己打算也有不详慎的时候。结婚后之共同生活关系极为复杂,非恋爱所能包括的。仅凭恋爱而结婚的,其选择十分之九不得当。西方婚姻美满也不是光靠恋爱。
主张结婚之主权应属于男女父母的人认为父母爱子女甚于子女自爱,父母更事多,智识较确,所以选择比较详慎。结婚乃人类对于祖宗神明子孙乃至社会全体所尽生殖之责任。故结婚应由父母详慎选择。恽代英反驳说父母爱子女不都甚于子女自爱,并且有不爱子女的。贪资产门第的父母也并非不爱子女。更事与智识是两回事,更事多而智识不确者车载斗量。人类最初对祖宗神明子孙乃至社会全体并无责任。结婚而生殖不过是性欲相引之自然结果。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使妇女因此受相邻、舅姑等的讥笑,女子自身也觉得是自己的罪过。
结婚无论是由男女自主还是其父母做主,在恽代英看来都有弊端。但是他还是明确提出,“结婚之主权仍应属于结婚之男女自身。此理由极简单,盖结婚为男女自身之事,故当以男女自主为正也”(59)。不过基于男女婚姻自主存在的弊端,他提出在男女各中学加结婚学为一种必修学科或更另设研究结婚学之速成学校。预料到有人会提出与其灌输结婚知识于血气未定的男女使之能养成自主结婚的能力不如灌输结婚知识于更事已多之父母,恽代英认为灌输于前者收效更为容易,因为后者思想不易改变。
针对恽代英的观点,伧父在恽代英文章的末尾附有自己的反驳(60)。他说智识与经验并非不相干,智识来自经验。若两者无关,让子女研究结婚学使其只有智识,这与只有经验而无智识的顽固父母相等。结婚为男女自身的事所以当自主,可是我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自身之事上也并不能自主。生殖也不是无责任,责任心左右性欲。他承认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弊端,认为不应根本推翻,而是要加以矫正。不过伧父又说他“近阅一书,预言二十世纪之社会内,概守独身主义。鄙人颇信其言之将实现,……待时会之自至可耳,结婚既不成问题,吾辈亦何苦饶舌乎”(61)!以此来结束与恽代英的这场争论。
关于婚姻的自主权问题,早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已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主张婚姻自由,康有为更是在《大同书》中对包办婚姻大加挞伐,主张“婚姻皆听女子自由,自行择配,不须父母尊亲代为择婿”(62),不过“仍限二十学问有成以后乃许自由,二十以前,仍须父母约束”(63)。对女子的婚姻自主权有一定的限制。辛亥革命时期,金天翮在《女界钟》中力主婚姻自由,要国人仿效欧洲(64)。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份子更深入剖析婚姻自由的实质,认为婚姻的缔结如同契约的缔约,应该出自双方的自愿,并受法律的规范(65)。而《东方杂志》这场关于婚姻主权问题的讨论,伧父以一个从前向往自由结婚到现在转而传统礼法婚姻的人物身份出现,与主张婚姻自由的恽代英论辩,正反映了从清末以来婚姻自由虽然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赞同,礼法婚姻的影响力仍然很大,更何况自由结婚也有弊端。这也表明婚姻自由问题并非少数先觉者的激烈呼吁就能解决的,许多人仍然不赞同给子女婚姻自主权。《东方杂志》上的言论便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除了婚姻主权上的论争外,《东方杂志》也提出戒早婚,因为早婚为害甚多:“男子以色欲不节而妨其发达,女子以生育过早而损其康健,子女多孱弱,则遗忧于种性。教养不完全则流毒社会。”“今欧美各国富力之厚,国民程度之高,虽有种种原因以致此,而予谓结婚之迟,必为其最重大之原因矣。”(66)中国若实行晚婚也有利于国富。《东方杂志》也提倡一夫一妻,宣扬一夫一妻在经济上可以免除因蓄妻妾之后子女多、负担重而导致的家庭贫困,可以减少因嫡子与庶子争产而导致的诉讼,可以使家庭和睦(67)。总之,“一夫一妇主义,合于自然之天理,为社会计、为国家计、为将来人种之强弱计,皆不可不有赖于此制”(68)。
除了教育、参政、婚姻这些问题外,1904-1919年的《东方杂志》也研究过女子职业问题,指出女子有职业可以增加国家税收,美国女子可从事各种职业(69)。在当时的中国提出“与其提倡新式之职业,无宁注意旧有之职业;与其为少数妇女启辟都市中执业之新途,无宁为多数妇女维持乡里固有之生计”(70)。也把西方国家妇女从事警察职业的成效展示给国人(71)。
总之,1904-1919年《东方杂志》从热心女子教育到关注妇女参政再到开展婚姻主权的争论,中国社会妇女问题在这段时间内的每次发展变化都有它的参与,世界妇女运动的潮流也得到了它的回应。女子教育方面,它强调兴女学以为兴母教,以此来强国;妇女参政问题上,它不愿意过多直面国内而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始终注视着欧美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婚姻主权问题上它允许不同主张之间的争论。《东方杂志》正视妇女问题,研究妇女问题,但是它在妇女问题上不是激烈的呐喊者,而是以温和的态度来对待妇女问题。它看到了西方妇女在教育、参政、婚姻、职业等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也把这些展示给国人,这些介绍无疑给国内妇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系。但是面对国内女界的现状,《东方杂志》始终保持冷静的态度,它可以容纳西方女权党人的过激行为,但是不会为过激行为呐喊助威。可以说,在妇女问题上,1904-1919年《东方杂志》的时时关注、热心参与,体现了媒体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它的观点冷静、温和,既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在妇女问题方面注重现实的态度,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注释:
①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原文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11月15日),载陈书良编《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495、496页。
③④⑩(12)(13)(14)(15)(16)勇立:《兴女学议》,《东方杂志》第3卷第13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241、241、242-243、243、244、244、244、244页。
⑤⑦《论女学宜先定教科宗旨》(录丁未三月十八日南方报),《东方杂志》第4卷第7号(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第129、130页。
⑥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录大公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第110页。
⑧(11)梁启超:《论女学》,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77、75页。
⑨《论女学所以兴国》(录乙巳八月二十五日南方报),《东方杂志》第2卷第11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255页。
(17)(18)《论女学宜重德育》(节录丙午第十三期北洋公报),《东方杂志》第3卷第6号(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第119页。
(19)《论中国当以遍兴女学蒙学为先务》(录八月十七日大公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12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270-271页。
(20)勇立:《兴女学议》,《东方杂志》第3卷第13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244页。
(21)《东方杂志》第1卷第6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22)《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23)《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24)《直隶天津县详送试办女学章程》,《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第142页。
(25)《东方杂志》第4卷第4号(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26)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27)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28)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6页。
(29)(30)《美国前大统领罗斯福妇女参政评议》(录《大共和报》译稿并注),《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1912年5月1日),第29、30页。
(31)(32)(33)《美国前大统领罗斯福妇女参政评议》(录《大共和报》译稿并注),《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1912年5月1日),第29、30页。
(34)陈霆锐:《世界女子参政之动机》(译美国评论之评论),《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1912年9月1日),第17页。
(35)《列国女子选举权考》(录《时事新报》译论),《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1913年5月1日);高劳译:《妇人参政运动权小史》(日本新公论摘译伦敦发行之《妇人参政年鉴》),《东方杂志》第13卷第4号(1916年4月10日)。
(36)(37)(38)章锡琛:《英国妇女之参政运动》,《东方杂志》第11卷第6号(1914年12月1日)。
(39)许家庆:《英国女子参政党之分裂》(译日本外交时报),《东方杂志》第9卷第8号(1913年2月1日)。
(40)许家庆:《英国女子参政案之顿挫》(译三月份外交时报),《东方杂志》第9卷第11号(1913年5月1日)。
(41)章锡琛:《英国女权党之狂暴》,《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1914年9月1日)。
(42)(43)许家庆:《大战争与妇女问题》(译太阳杂志载工藤日自伦敦投稿),《东方杂志》第13卷第2号(1916年2月10日),第19页。
(44)愈之:《女权发达与平和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15日),第66、67页。
(45)江纫兰:《说女子参政之理由》,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46)《社会党南京支部致本部等电》,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60页。
(47)《中华民国联欢会复临时大总统书》,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页。
(48)《临时大总统再复中华民国联合会书》,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49)江纫兰:《说女子参政之理由》,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50)李细珠:《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51)如1919年11月在长沙,赵五贞女士为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自杀,当时不仅轰动长沙,而且影响遍布全国。
(52)《美国女界之情形》,《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1912年8月1日)。
(53)《挪威妇人在法律上之地位》,《东方杂志》第9卷第3号(1912年9月1日)。
(54)即杜亚泉,当时《东方杂志》的主编。
(55)(56)伧父:《自由结婚》,《东方杂志》第14卷第5号(1917年5月15日)。
(57)伧父:《自由结婚》,《东方杂志》第14卷第5号(1917年5月15日),第12页。
(58)(59)(60)(61)恽代英:《结婚问题之研究》,《东方杂志》第14卷第7号(1917年7月15日)。
(62)(63)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62页。
(64)熊月之:《晚清上海:女权主义实践与理论》,《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
(65)炳文:《婚姻自由》,载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66)伧父:《戒早婚》,《东方杂志》第12卷第4号(1915年4月1日),第13页。
(67)(68)《一夫一妇主义之提倡》,《东方杂志》第14卷第2号(1917年2月15日),第169-170页。
(69)《论女工》(节录甲辰第二十二期商务报),《东方杂志》第1卷第8号(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
(70)高劳(即杜亚泉的化名):《妇女职业》,《东方杂志》第14卷第3号(1917年3月15日),第7页。
(71)裘剑岑:《论女警察》(译十九世纪报),《东方杂志》第12卷第5号(1915年5月10日);罗罗(即为胡愈之):《英国女警察》(译Contemporary Review),《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号(191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