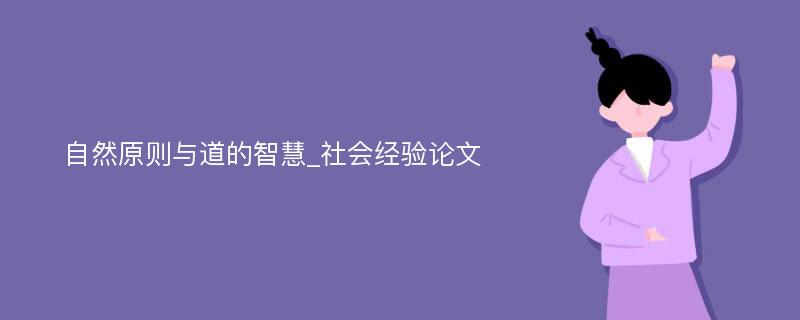
自然原则与道的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则论文,智慧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老子》哲学以道为第一原理。作为存在的终极根据,道并不是一种外在的主宰;毋宁说,它更多地表现为存在的自我统一。循沿这一思路,《老子》进一步提出了“道法自然”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从本体论上看,所谓“道法自然”, 也就是道以自身为原因。《老子》在第42章曾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也就是道自身,道生一,犹言道自生或道自我决定。在生成关系这种外在形式之后,是对自因(道以自身为原因)的肯定。《老子》强调“反者道之动”,同样意味着将变化理解为一个自我运动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发展原理与自因的统一。
法自然的自因义,主要侧重于天道。从人道的角度看,法自然又与人的行为相联系。在第53章中,我们读到:“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从字源学上看,“道”本有道路之意,引申为主体应当遵循的规律等。《老子》在这里似乎利用了“道”这一词的双关性,在行进于大道这一语义之中,同时寄寓了推行、遵循大道之意。后者在第41章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所谓勤而行之,便是指自觉地推行、遵循道,在此,法自然取得了合于道的形式。
人道意义上的自然,在《老子》哲学中往往又与价值领域相联系。在价值观的层面,自然常常被理解为一种与人化相对的存在形态,而法自然则相应地具有保持或回归前文明状态之意。正是在后一意义上,《老子》对人化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文化形态提出了种种批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第18章)从本体论上看,道具有未分化的特点,后者同样体现于价值领域。作为人化过程产物的文明形态,往往有善恶之分,诚伪之别;相对于此,与道为一的自然状态,则是无分别的。以道观之,无论是正面的仁义、智慧、孝慈,抑或负面的大伪、六亲不和,都是人为的结果,二者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对自然的偏离。在这里,大道已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而文明社会的规范,则被视为对自然原则的否定:大道废,有仁义,便展现了二者的这种紧张关系。
人文与大道、文化与自然的如上紧张,使法自然逻辑地导向了对人化过程及其产物(文化)的疏远,所谓“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19章),便表明了这一立场。作为一般的价值取向,这种立场既体现于个体的人生理想,也渗入于普遍的社会模式。在人生理想之域,法自然取得了“见素抱朴”(同上)的形式,就社会模式而言,法自然则意味着回归小国寡民的社会形态:“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80章)什佰之器包括广义的工具,结绳而用则与文字的运用相对。在自然状态下,从工具到文字,文化的各种样式似乎都失去了其存在价值。
与自然相辅相成的,是无为,《老子》所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64章)便肯定了二者的这种联系。如前所述,法自然既以自觉地行道为向度,又意味着向自然状态的回归。前者主要从积极的方面——推行并合于道——展示了法自然的内涵,无为则首先从消极的方面——避免反乎道的行为——表现了类似的趋向。在《老子》看来,人为的过程往往会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57章)反之,遵循无为的原则,则能达到国泰民安:“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同上)在这里,无为与自然是一致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17章)从无为的原则出发,《老子》要求对“欲”加以限制,所谓“是以圣人欲不欲”(第64章),等等,便表明了此点。这种无欲的主张,在形式上与儒家无疑有类似之处。不过,儒家所理解的欲,首先与感性的欲望相关,而无欲或寡欲也相应地意味着以理性的观念抑制感性的欲望。这里内在地蕴含着某种理性优先的原则,在尔后的理欲之辨中,便明显地表现出这一趋向。较之儒家主要从理欲关系上讨论“欲”,《老子》着重将“欲”与有意而为之的人为过程联系起来,而“欲”则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有所为的意向。无人为之欲与顺自然之化往往被视为同一过程的二个方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老子》强调:“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37章),亦即将消除人为的冲动,视为达到自然之境的前提。
当然,无为并不是一无所为,《老子》要求“为无为”(第3章, 第63章),亦意味着将无为本身看作是一种特定的“为”。与法自然的要求相联系,以无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为”,首先相对于无视自然之道的人为而言。在第37章中,《老子》对无为之“为”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在此,无为之“为”(无不为)与万物之自化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难看出,这种无为之“为”的特点,在于利用对象自身的力量而不加干预,以最终达到人的目的。《老子》以政治领域的实践为例,对此作了说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第68章)这里的用人之力不仅仅是指善于选用人才,它的主要涵义在于利用各种政治势力。高明的当政者并不直接与人相争,而是善于利用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这一意义上的“无为”,同时便表现为一个合乎自然(配天)的过程。用对象之力而不加干预作为无为之“为”的形式,不仅体现于政治领域,而且构成了“为无为”的一般特点。所谓“事善能,动善时”(第8 章)便从更广的意义上展示了以上原则:事、动属广义的“为”,而善能、善时都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为”应当合乎自然(配天)。
《老子》所说的无为之“为”,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起黑格尔所谓“理性的机巧”。关于理性机巧,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有过如下论述:“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2〕在此, 理性的机巧具体展现于人的活动,而这种活动首先又表现为一个合规律性的过程:它让对象各按自己的本性而相互作用,而不作人为的干预。质言之,一方面,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无所作为,相反,整个过程一开始便引向主体的目的;另一方面,主体又并不违背事物的固有本性而横加干预,这里蕴含的内在观念,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老子》主张“为无为”,并把无为之“为”理解为利用对象的力量以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一意义上的“无为”,无疑近乎理性的机巧。
“为无为”的原则贯彻于治国实践,便要求尊重被统治者意愿。《老子》在谈到圣人与百姓的关系时,曾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第49章)与无为非完全无所作为相一致,无心也并不是无任何意念;但正如无为之“为”并非以人为干预自然过程一样,统治者之有心,并不意味着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被统治者。在这里,合乎百姓之心(以百姓心为心)可以看作是合乎自然的逻辑引申。以此为前提,《老子》对各种人为的统治方式提出了批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74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第75章)如此等等。这里显然包含着一种社会批判的趋向。从中国文化尔后的演进看,道家与儒家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批判传统,而道家批判传统的历史源头,则可以追溯到《老子》。就其内在特点而言,由《老子》开其端的这种社会批判,既以自然状态的理想化为前提,并相应地表现出对文明和文化的某种疏离,又以“为无为”为根据,并多少相应地渗入了尊重民意以及宽容和不干预等观念。
自然无为的原则在《老子》哲学中不仅展开于社会领域,而且亦体现于天人之际。在第5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论述:“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仁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建立于其上的儒家仁道原则,要求确认人的价值并以人为关切的对象,孔子所谓“仁者爱人”,便言简意赅地表明了这一点。与之相对,将人与万物都视为刍狗,则似乎使人的价值失去了存在的根据。《老子》的这一看法无疑表现出以自然原则消解仁道原则的趋向:等观人与物,意味着人与物在自然这一层面并无本质的差别,而人的优先性亦相应地不复存在。
然而,如果由此而把《老子》哲学理解为一种反人道的系统,则往往不免失之偏颇。事实上,如前文所述,人的存在始终是《老子》哲学沉思的重要对象。在“四大”之说中,人即被规定为域中四大之一。正是以此为出发点,《老子》一再表现出对人的关怀:“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第27章),并要求“爱民治国”(第10章),与之相联系的是反对战争和暴力,“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30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第31章);“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同上)。在肯定人(救人)与否定人(杀人)的对峙中,《老子》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价值立场。
由以上前提反观人为刍狗之说,便很难将其列入反人道之列。从其内在逻辑看,视人为刍狗,首先是相对于“仁”而言(所谓“圣人不仁,以人为刍狗”)。作为一种价值原则,“仁”既意味着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亦包含着某种人类中心的观念,在后来儒家对仁道的阐发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以仁道为原则,儒家往往强调人超越于天地万物这一面,这里无疑渗入了从自然状态走向文明形态(自然的人化)的要求,但同时也表现出人“最为天下贵”的价值取向,后者若进一步加以强化,便很容易导向以人为万物的中心。相对于此,《老子》在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前提下视人为刍狗,似乎将人与物置于相等的地位。不难看出,这里的核心观念是自然的原则:由自然的观点视之,人并不具有对于物的优先性。如果说,“仁”的观念内在地蕴含着人类中心的价值取向,那么,以自然原则消解“仁”,则多少意味着对人类中心观念的疏离。
对天人关系的如上理解,同时亦内含了对天人统一的确认。对《老子》来说,就本然的形态而言,天地万物与人一开始便是彼此统一的,“道”、“朴”、“玄同”等等,便从不同的角度肯定了这一点。经过由道而德等过程,往往形成了区分,所谓“朴散则为器”(第28章),亦隐喻了这种转换。但在既分之后,又应向原始的统一回归,这一过程在《老子》那里往往被称为“归根”、“复命”:“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16章)这里不仅涉及道与物的关系,而且在广义上指向天人之际。就后一意义而言,天人之间同样应当重建统一,所谓“绝仁弃智”、“绝圣弃义”、“见素抱朴”,等等,都意味着从“仁义”、“圣智”等人化形态回归与自然为一的理想之境。
在合于自然的思维趋向之后,可以看到某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过,与儒家要求化天性(人的自然之维)为德性(人的社会之维),亦即在自然的人化的基础上达到天与人的统一有所不同,《老子》更多地表现出对自然的认同。如果说,在儒家那里,天与人似乎统一于人化过程,那么,《老子》则要求天与人合一于自然。这里既呈现出对文化创造及其成果的不同态度,又交错着人类中心与自然至上的不同价值取向。《老子》对人化过程和人文价值的批评,当然有其历史的局限,它将自然状态加以理想化,亦包含着内在的理论偏向。不过,人道原则的过分突出,也往往潜含天(包括人的天性)与人(包括社会规范)的紧张,《老子》所确认的自然原则对于化解如上紧张、抑制过强的人类中心价值定势,无疑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
自然无为作为一般的原则,不仅仅体现于价值之域;在更广的意义上,它亦涉及为道的过程。《老子》对为道与为学作了区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第48章)为学是一个经验领域的求知过程,其对象主要限于现象世界与人化世界;为道则指向本体世界,其目标在于把握统一性原理与发展原理。在《老子》看来,经验领域中的为学,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益)的过程,以本体世界为对象的为道,则以解构已有的经验知识体系(损)为前提,后者构成了无为的另一内涵。
从为道的角度看,无为首先意味着回到事物本身:“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第54章)身、家、国、天下等,可以表现为现象层面的存在,也可以指身之为身、家之为家、天下之为天下的本质规定。与区分呈现于外的现象和现象之后的存在,并进而追寻万物的统一本源相应,这里的“身”、“家”等等,主要不是作为外在呈现的现象,而是现象之后的存在;而所谓以身观身、以天下观天下,则要求超越外在的呈现,而深入到对象的内在规定——亦即从本体的层面来考察存在。当主体的视域尚停留在现象层面时,他往往自限于为学的过程,唯有从本体的层面切入存在,其思维才具有为道的性质;前者(限定于现象)属主观的人为,后者则顺乎道而无所为。
可以看到,以身观身、以天下观天下旨在回到事物本身,而事物本身又被理解为本体世界。在《老子》的系统中,向本体世界的这种回归,同时表现为一个“日损”的过程。作为为道的内在环节,日损所指向的,首先是现象世界。在第56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论述:“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兑”按俞樾之说,当读为“穴”,引申为耳目口鼻等感官〔3〕; 门则泛指面向外部对象的通道。由感官的门户所达到的,是现象世界;作为为学过程,它所积累的,主要是经验领域的知识。《老子》要求“塞其兑,闭其门”,意味着关闭通向现象世界的门户;它从一个侧面表明,以身观身等等并不是从现象的层面把握对象。如果说,回到事物本身(以身观身等等)的内在意蕴在于复归本体世界,那么,塞其兑、闭其门则将悬置经验领域的知识规定为达到本体世界的前提。从“塞其兑”到“玄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逻辑的进展。
“塞其兑”主要相对于现象之域而言,与之相联系的是“绝圣弃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仁义属社会的观念与规范,圣智与仁义并提,主要亦涉及人化世界。如前所述,人化的世界与自然相对,是经过人为的过程而形成的,圣智作为人化过程的产物,也具有人为的性质。惟其人为而非出于自然,故往往不免导致负面的社会后果,所谓“慧智出,有大伪”,便强调了这一点。与人化世界中的圣智相对的,是以知常为内容的“明”:“知常曰明。”知常亦即把握作为统一本源的道,而明则是关于道的智慧。较之人化世界中的圣智,道的智慧具有不同的形态:“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第20章)此所谓愚,乃大智若愚之愚。世俗的圣智往往长于分辨,昭昭即为一种明辨形态;道的智慧则注重把握统一的整体,沌沌即为合而未分之貌。执著于分辨、智巧,伪与恶等等往往亦随之而产生,达到了道的智慧,则趋向与天地为一之境。正如塞其兑、闭其门旨在从现象世界回归本体世界一样,绝圣弃智意味着从世俗的圣智走向道的智慧,后者既表现了对人化世界的疏离,亦蕴含着超越对待、追求统一的形上意向。
相对于道的智慧,世俗的圣智似乎处于知性思维的层面。知性思维的特点在于分别地从某一方面或某一层面把握对象,而未能进一步再现对象的整体。尽管它不失为面向存在之思的必要环节,但停留于此,则往往不免明其分殊而昧于统一。为道的过程力图超越对分殊的这种执著,回到统一的道。就其关注整体,追寻统一而言,《老子》的为道确乎有别于昭昭于分殊的知性思维。由此进而反观《老子》的绝圣弃智之说,便不难看到,其中既渗入了从人化世界回到自然之境的意向,又包含着悬置知性思维的要求。
当然,悬置了世俗的圣智,并不意味着道的境界亦将随之而至。在既成的视域与道的境界之间,往往存在某种距离,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是为道过程的重要方面。《老子》指出:“知不知,上〔4〕。 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第71章)知不知,即自知无知,这里涉及了知与无知的关系。关于知与无知的关系,先秦的另一些哲学家也已注意到。如孔子即指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5〕按通常的看法,不知便是缺乏知识, 而在孔子看来,对“不知”这种状态的认识,本身也是一种知。不过,孔子更多地把知与无知的统一视为求知过程的开端:自知无知构成了“知”的出发点。相形之下,《老子》所谓“知不知”,主要突出了为学与为道之间的张力:通过为学过程而积累经验知识,并不逻辑地导向对道的认识。后文的“不知知”,从反面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不知知在于忽略了为学与为道的区分,将为学之知等同于为道之知,以致虽对道无知,却仍以为有知。
与知和不知相联系的,是名与言的问题:“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按《老子》的看法,作为第一原理的道,并不是言说的对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第1章)、“道常无名”(第32章)、 “道隐无名”(第41章),便表明了这一点。这里的名与言,首先涉及经验领域。就本然的形态而言,道表现为“无名之朴”(第37章),随着由道而德的分化过程,逐渐形成了经验领域的具体对象,如言:“朴散则为器”,名则由此而产生:“始制有名。”(第32章)作为朴散而为器的产物,名的作用范围亦有自身的限制:“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同上)名与现象领域之“器”的以上联系,决定了它无法把握普遍之道。而从另一方面看,“道常无名”也突出了道超越名言的性质。概而言之,塞其兑,表明感官的门户无法达到道;绝圣弃智,彰显了世俗的圣智与道的智慧的差异;道常无名,则突出了道与名言之间的距离。道对现象界、经验界与名言界的如上超越,决定了为道的日损之维:所谓日损,便意味着悬置经验领域的知识、名言系统。
悬置经验、圣智、名言之后,如何走向道?《老子》提出了静观玄览之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16章)就本体论而言,“复”所表示的是向统一本源的回归,从为道的角度看,“观其复”则意味着回到世界本身——本体层面的世界,而这一过程又以虚与静为前提。所谓“致虚极”,也就是剔除已有的认识内容,净化内在的精神世界;守静笃则表现为一种静观反省,二者的统一,又称玄览:“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第10章)这种以悬置日常经验和知识名言为前提的玄览,显然带有直觉活动的特点。
静观玄览是就得道(把握道)的方式而言。广义的为道过程不仅涉及道之“得”,而且关乎道之“达”(对道的表达)。从后一方面看,为道过程又无法割断与名言的联系。如前所述,《老子》曾强调了道的超名言性质(“道常无名”),这里的无名,首先是在“为道日损”的意义上说的,而其中涉及的名言,则主要与日常经验相联系。除了这种日常经验意义上的名言系统外,还有另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所谓“正言若反”(第78章),便肯定了这一点。这是一种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名言表达方式,《老子》常常以此来概述有关道的智慧:“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第37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第38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第81章),如此等等。如果说,与道相对的日常名言基本上处于知性的层面,那么,以“正言若反”的形式出现的名言,则似乎带有辩证的性质。
不难看出,《老子》对为学与为道的辨析,主要围绕日常的知识经验与道的智慧而展开。日常的知识经验所指向的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对象(亦即作为“朴”散产物的“器”),它总是分别地把握具体事物或事物的某一方面、某一层面,并以确定的名言概括认识的内容。道的智慧则指向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和发展原理,它所要把握的不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一个一个具体对象,而是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贯穿于宇宙人生中无不通、无不由的统一原理。质言之,这里所涉及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它显然很难仅仅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来达到,因为经验知识所把握的,始终是有限时空中的对象。从日常知识经验到道的智慧,本质上表现为一种认识的飞跃,而这种飞跃的实现,往往意味着突破日常的逻辑运演模式,其中亦常常渗入了直觉等思维形式的作用。《老子》强调“为道日损”,要求悬置日常的圣智,并以静观玄览为回归道本身的方式,似乎亦注意到了从知识到智慧转换过程的某些特点。
与日常知识经验和道的智慧相联系的,是道与名言的关系。名言的自然形态首先存在于日常经验领域,日常语言是名言的本然形式和原始形态,知识经验与日常的名言往往亦有较为切近的联系,在涉及特定时空中的对象这一点上,二者无疑有一致之处。然而,在把握普遍之道方面, 日常名言却有自身的限度:道作为统一性原理或最一般的存在(being),总是具有超越于特定时空的一面, 以特定时空中的具体存在为对象的日常名言,往往难以完全表达道的这种无限性。同时,对统一性原理的把握,并非仅仅以言说为其形式,它总是进而化为主体的境界,并融合于主体的“在”(existence)之中。从这些方面看, 道确乎又有超名言的一面。《老子》认为道不可言说(道可道,非常道),强调“道常无名”,似乎亦有见于此,它在某种意义上以否定的方式,展示了道与日常名言之间的距离。
当然,日常的知识经验与道的智慧、道与名言之间固然存在某种张力,但二者亦并非截然相斥。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而言,仅仅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诚然难以实现二者的转换,但如果完全离开知识经验,飞跃往往便会导向虚幻的思辨或神秘的体悟。对统一性原理的把握,总是既表现为对日常之思经验的超越,又以知识经验为其出发点并不断地向其回归。《老子》将为学与为道的过程截然加以分割,显然未能注意到这一关系,而它由此而渲染的静观玄览,也确实带有某种神秘的意味。同时,宇宙的第一因和人生最高境界诚然有超越日常名言的一面,但亦并非完全隔绝于名言;辩证的概念在拒斥静态形式的同时,本身也包含着确定性的要求。《老子》由强调道与日常名言的距离,进而突出正言若反的名言形式,虽然对辩证的思维形式开始有所注意,但似乎未能全面地把握道与名言的关系及名言的确定性。
注释:
〔1〕《老子》第25章。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章节。
〔2〕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页。
〔3〕参见俞樾《诸子评议·老子评议》。 又, 奚侗:《老子集解》注曰“《易·说卦》:‘兑为口’,引申凡有孔窍者皆可云兑。《淮南子·道当训》:‘王者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高(诱)注:‘兑,耳目口鼻也。老子曰塞其兑是也’。”
〔4〕此句《帛书》甲本作“知不知,尚矣”。
〔5〕《论语·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