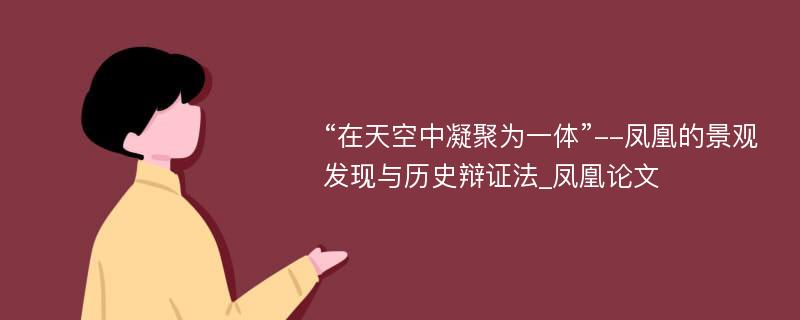
“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凤凰》的风景发现和历史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凤凰论文,风景论文,发现论文,天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发表于《今天》2012年春季号“飘风特辑”,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底出版单行本。整部长诗共19节,三百三十八行。在单行本的“序言”中,李陀对该长诗作出了高度的评价:“长诗《凤凰》的问世对当代诗歌写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只限于诗歌,还应该放在当代文化环境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去评价和理解。”①长诗从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雕塑“凤凰”中获得灵感,以凤凰为核心象征体,重塑现代主义诗歌的叙事视域,结构出“凤凰一般”的社会现实,进而勾勒资本逻辑、词语逻辑和历史逻辑在社会结构中的重叠互置,在反讽、驳诘、词语狂欢和欧阳江河式的历史辩证法中全景式地呈现了当下中国“如古瓮般的思想废墟”。长诗气度恢弘同时又泥沙俱下,思辨深刻但又若无所依,结构精致同时又“漏洞百出”。长诗是一个真正的综合性文本,它以诗歌的形式重塑现实,但又非常现实性地——同时也是无可奈何地——将诗歌的“猛兽”②驯化为一个观念中的“全体”。与此同时,又不断地对这一“全体”进行拆解③:从雕塑始,以反雕塑终,从时间始,以反时间终,从诗歌始,以反诗歌而终——对一个读者来说,也许不得不遵循这种正反的隐秘秩序,从解读始,以反解读而终。
一、因为大我已经被小我丢失
5
得给消费时代的CBD景观
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
因为神迹近在身边,但又遥不可及。
得给人与神的相遇,搭建一个
人之境,得把人的目力所及
放到凤凰的眼瞳里去,
因为整个天空都是泪水。
得给“我是谁”
搭建一个问询处,因为大我
已经被小我丢失了。
得给天问,搭建鹰的独语,
得将意义的血肉之躯
搭建在大理石的永恒之上,
因为心之脆弱有如纹瓷,
而心动,不为物象所动。
这是欧阳江河长诗《凤凰》中的第5节,之所以挑出这一节来开始这篇解读之文,是因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句——“因为大我已经被小我丢失了”。这是这首长诗首先值得注意的地方,如果我们已经用足够的耐心——当然也许是足够的激动——阅读完了这首机械复制时代的“飞翔”之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悖于现代主义诗歌传统的事实,在整个诗篇中,没有出现第一人称主语“我”。我相信这是欧阳江河的刻意为之,实际上,如果在某些诗句的前面加上“我”这一主语,这首诗也许读起来会更亲切一些。但是欧阳江河刻意地将“我”删除了,这让阅读这一行为本身变成了一个“悬空”的动作,现代诗歌阅读的基础建立在“我”与读者互为主体的原则之下,也就是说,读者通过阅读假想自己为诗歌的主体从而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但是在欧阳江河这里,因为“我”的缺席,读者将不得不寻找另外的想象的替代物。欧阳江河以这种方式来逼迫读者跟随他的诗歌一起“飞翔”,飞离原有的创作惯性、阅读惯性和想象惯性。
第一人称主语的消失意味着某一类个人的退场,现在,出现在诗歌中的场景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走过傍晚的广场,在那个广场里,主体的内省和自恋是主要表达的主题。现在恰好相反,广场被纷繁嘈杂的现代性的景观所“填充”:
3
身轻如雪的心之重负啊,
将大面积的资本化解于无形。
时间的白色,片片飞起,
并且,在金钱中慢慢积蓄自己,
慢慢花光自己。而急迫的年轻人
慢慢从叛逆者变成顺民。
慢慢地,把穷途像梯子一样竖起,
慢慢地,登上老年人的日落和天听。
中间途经大片大片的拆迁,
夜空般的工地上,闪烁着一些眼睛。
4
那些夜里归来的民工,
倒在单据和车票上,沉沉睡去。
造房者和居住者,彼此没有看见。
地产商站在星空深处,把星星
像烟头一样掐灭。他们用吸星大法
把地火点燃的烟花盛世
吸进肺腑,然后,优雅地吐出印花税。
金融的面孔像雪一样落下,
雪踩上去就像人脸在阳光中
渐渐融化,渐渐形成鸟迹。
建筑师以鸟爪蹑足而行,
因为偷楼的小偷
留下基建,却偷走了它的设计。
资本的天体,器皿般易碎,
有人却为易碎性造了一个工程,
给它砌青砖,浇铸混凝土,
夯实内部的层叠,嵌入钢筋,
支起一个雪崩般的镂空。
这些景观包括:拆迁的工地、急迫的年轻人、夜里归来的民工、站在星空深处的地产商、蹑足而行的建筑师、偷楼的小偷、钢筋混凝土的楼体等等。这些景观在两个层面被处理,第一个层面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写实”层面,具体的身份、场景被展示。第二个层面是在“隐喻”的层面,每一种现实的具体性都被转喻进一种隐晦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系统,地产商由此对接上“印花税”,而金融如雪,形成“鸟迹”。资本贪婪和狡猾的本性得以暗示。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景观是“景观”与“奇观”的综合体,欧阳江河以其惯有的悖论性的语言将这两者锻造为社会性的“现实”。这种现实既不同于马克思、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也不同于90年代以来盛行的“日常事实”,这是一种综合的现实。它本身建立在高度象征化的“日常事实”中,或者说,“日常事实”在高度景观化的当下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对于“日常事实”的书写应该首先破除象征化,但是这种破除又并非简单地还原,而是通过另外的象征体系予以对话、辩驳和拆解,我觉得这正是《凤凰》本质性的修辞原则。在这个修辞原则之下,一种“新现实”被呈现出来,它不仅仅是视觉意义上的,也不仅仅对应于现实中的徐冰的“凤凰”雕塑,而是重新发现了诗歌、修辞和现实的对接术,并在这个意义上改写了现代主义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将现代主义日益内倾化的个人视域转化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视域。
视域的转化意味着“大我”和“小我”之间关系的调整。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大我”与“小我”有着明确的政治内涵,“大我”指的是那种大公无私、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往往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集体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个体,而“小我”则与“大我”相对,指的是仅仅关注自我发展和自我完成,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个人。欧阳江河很明显地在此借用了这两个词语的意识形态背景并获得了一种张力。但他同时又抽空了这两个词过于明显的意识形态含义,而对之进行了抽象化的处理。“大我”在这里被普遍化为一种“思想”“神”“心”,而“小我”则是“人”“人之境”,“大我”与“小我”之间的政治张力转化为一种哲学(神学)张力,这种哲学,既有一点柏拉图的意味,又有一点老子的气息,这种拼接与作为雕塑的“凤凰”形成奇特的同构。“大我”与“小我”之间的关系由此变成了“道”与“人”、“神”与“人”、“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当“大我已经被小我丢失”变成一种既成的前提和事实,那么,找回“大我”的方式就是“得把人的目力所及放到凤凰的眼瞳里去”,也就是将“我之眼”放到“凤凰之眼”,然后获得一个更高、更阔大、更全面的视域,“小我”由此通过凤凰找回了“大我”,在这种“凤凰的眼瞳”的观照中,“小我”获得新生。因此,“我”的缺席又是一种“我”的回归,这里面有着双重的寻找:在小我中找大我,在大我中找小我,并在一种“重瞳”(我之眼和凤凰之眼)中焕发出逼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④
二、“人变成一种叫凤凰的现实”
借着“大我”“小我”重叠的观察和透视,《凤凰》中可以说有一种“风景的发现”。这种发现同样是多重的,第一重发现在于徐冰的大型雕塑“凤凰”对于中国现实的高度象征化再现,在这个庞大的雕塑中,废弃的工业原材料被锻造组装为金碧辉煌的凤凰塑像,这是工业社会“有用”与“无用”的直接美学化;而当这只凤凰在各种博览会上被展览、观看之时,它本身就构成了资本的矛盾性隐喻,它必须借助资本才能流通,但同时却在倾诉资本的暴力性和侵略性。第二重发现在于欧阳江河在观看、接触这样一个庞大的雕塑时所产生的震惊感,他可能意识到了这是一种巨大的发现⑤,并在这一发现之中产生了另外一种发现的冲动,他试图在这个雕塑身上发现词语叙述的可能,具体来说,是艺术行为(诗歌行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凤凰》,徐冰创角度与涉及的领域远远超出了美术创作,我们应该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去看。这个角度不光包括我们的审美、思想的阐释、对世界的理解,同时也包括了应该怎么从行为的角度去介入和改变这个世界。”⑥由此产生了第三重发现,在这一重发现里面,作为雕塑的凤凰消失了,而作为诗歌(词语)的凤凰起飞了,更重要的是,在发现词语的凤凰的同时,现实洞开,词语发现了新现实,也就是长诗第2节所言的——“人变成一种叫凤凰的现实”:
2
人类并非鸟类,但怎能制止
高高飞起的激动?想飞,就用蜡
封住听觉,用水泥涂抹视觉,
用钢钎往心的疼痛上扎。
耳朵聋掉,眼睛瞎掉,心跳停止。
劳动被词的力量举起,又放下。
一种叫做凤凰的现实,
飞,或不飞,两者都是手工的,
它的真身越是真的,越像一个造假。
凤凰飞起来,茫然不知,此身何身,
这人鸟同体,这天外客,这平仄的装甲。
这颗飞翔的寸心啊,
被牺牲献出,被麦粒洒下,
被纪念碑的尺度所放大。
然而,生活保持原大。
为词(梦)造一座银行吧,
并且,批准事物的梦幻性透支,
直到飞翔本身
成为天空的抵押。
什么是凤凰一样的现实?耳聋、眼瞎、心跳停止,“它的真身越是真的,就越像一个造假”,这是一个感官遭到废弃,无法辨别真假的现实,在这样一个现实中,感官所经验到的世界未必是“真”的,因为“飞与不飞”都是“人工”。这里或许会让我们想到本雅明经典的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论述,因为“光晕”的消失,伟大的作品将变得不再有神圣的价值。而在后工业社会,因为高度发达的技术,甚至连“感觉”本身也已经真伪难辨。也就是说,“真”作为一种概念或者范畴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因为“真”的消失,所以“假”其实也就不存在了。这不仅仅是某种哲学上的诡辩术,同时也意味着欧阳江河所一贯赖以写作诗歌的修辞术遭遇到了现实性的危机,因为在以往的诗歌中,欧阳江河修辞上的反讽、悖谬几乎都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的现实结构和哲学对位中,但是,如果“真”与“假”已经完全合二为一,就像“人鸟同体”一样,那么,这种修辞术还有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欧阳江河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以为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在词语的危机和匮乏之中他不得不借助资本的逻辑——“为词造一座银行吧”。非常有意思的是一处小小的改动,在《凤凰》的第四次修改稿中,这一句是“为梦造一座银行吧”,但是在《今天》“飘风特辑”以及《凤凰》的单行本中,这个“梦”被“词”所替换。梦是一种更感性的表达,仅仅通过“梦”并不能完成对整个资本现实的表述,虽然资本主义一直以“好莱坞梦工场”的形式向全世界批发其“黄粱美梦”,但是,“梦”最终也不得不诉之于“词”(修辞和表达),因此,“词”具有了“硬货币”的功能,现在,它可以在“银行”里被无限地复制和生产,并用来交换一切。
“为词造一座银行吧”暗示了“凤凰一般的现实”与资本的发展密切相关,与其说是人造就了凤凰一般的现实,不如说是资本的逻辑造就了这种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凤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结构。对这一社会性结构的肌理、组织进行全景式地分析叙述构成了诗歌最重要的篇幅,接下来的第3、4、5节从两个方面叙述了这一社会结构的两个支撑性的逻辑,一是资本本身的逻辑,这一逻辑的主体是我在上文中提及的社会化视域中的“个体”,这些个体由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组成,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互相纠缠,“在金钱中慢慢积蓄自己”的“年轻人”,“慢慢从叛逆者变成顺民”,然后又“以穷途”为天梯,登上“老年人的日落和天听”;而民工则“倒在单据和车票上,沉沉睡去”,地产商则用“吸星大法”将“烟花盛世”变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很明显,这一资本的逻辑由利润、税收、剥削、剩余价值等现世的规则构成,在这一规则中,似乎很难作出善恶的道德价值判断,欧阳江河在此保留了一种“客观化”的暧昧。但第4节的最末一句又留下了空间,“资本的天体,器皿般易碎,有人却为易碎性造了一个工程。”这里的疑问是?谁为这个“易碎性”造了一个工程?如果天体如此易碎,又如何能将其整合起来?这正好是第二个支撑性的逻辑,即词的逻辑。词在这里是“古瓷般的思想废墟”,是“鹰的话语”。“人”通过“词”将资本的逻辑与词的逻辑结合起来,也就说,通过“词”的象征性叙述,资本的逻辑才能找到意义,“得将意义的血肉之躯搭建在大理石的永恒之上”。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词”的象征性的叙述系统,尤其是诗歌、小说和电影等一系列艺术形式,来构建其历史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词”比“梦”更重要,也更有其功能性的作用,“词”可以移形换位,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指鹿为马,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当然需要一座“词的银行”。通过“词”的炼金术,资本主义洗白自己,隐去罪恶,“凤凰”优美地重生:
为什么凤凰如此优美地重生,
以回文体,拖曳一部流水韵?
转世之善,像衬衣一样可以水洗,
它穿在身上就像沥青做的外套,
而原罪则是隐身的
或变身的:变整体为部分,
变贫穷为暴富。词,被迫成为物。
三、“有人在太平洋深处安装了一个地漏”
借助社会性视域的观察,呈现了多重的风景,而这种风景中最突出的是层级分明的社会现实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因为资本和词的逻辑互为作用,它简直就成了一个“永恒的大理石般”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存在中,即使“小我”找回了“大我”,似乎也无法击毁“词”的银行,反而是深陷资本的内部运作逻辑之中,并参与其“易碎性工程”的涂脂抹粉。这似乎是《凤凰》第1—7节给我们的阅读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欧阳江河完全“客观化”的诗歌叙述仿佛是这座“银行”的一名出纳员,以其娴熟而冷酷的工作方式来印证资本社会亘古不变的神话。但是,这并非欧阳江河的目的之所在,虽然这个开头显得稍微有些冗长,而转机似乎也姗姗来迟,但是,转机毕竟来了,在第八节中,我们读到了重要的信息:
8
升降梯,从腰部以下的现实
往头脑里升,一直上升到积雪和内心
之峰顶,工作室与海
彼此交换了面积和插孔。
一些我们称之为风花雪月的东西
开始漏水,漏电,
人头税也一点点往下漏,
漏出些手脚,又漏出鱼尾
和屋漏痕,它们在鸟眼睛里,一点点
聚集起来,形成山河,鸟瞰。
如果你从柏拉图头脑里的洞穴
看到地中海正在被漏掉,
请将孔夫子塞进去,试试看
能堵住些什么。天空,锈迹斑斑:
这偷工减料的工地。有人
在太平洋深处安装了一个地漏。
这一节的关键词是“漏”,八个“漏”字构成了一幅“漏洞百出”的视觉图景。“漏”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漏水,电,也漏人头税,还漏柏拉图和孔夫子的思想。漏的对象越来越阔大,从一滴水开始,到漏地中海和太平洋。“漏”同时剧烈而势不可挡,即使将伟大的孔夫子塞进去,也无法“堵住些什么。”这是一次绝妙的讽刺,含有深刻的政治隐喻,如果说柏拉图指的是西方的什么东西,毫无疑问孔子指的是东方的什么东西,如果说当下的中国现实是朝资本主义的方向一路狂奔,因为漏洞百出而将孔子抬出来作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修补,那么,“能堵住些什么”就是一个辛辣的嘲讽和讥笑,因为没有什么是完美的世界,柏拉图的西方不是,孔夫子的东方也不是,后毛泽东时代的非驴非马的“四不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更主要的是,无论被词语叙述得多么光鲜动人的人物、思想、世界,其实都有绕不过去的漏洞,在这个“漏洞”里面,暗含着另外的历史和另外的可能性。
于是顺乎自然地,从长诗的第10节开始,一种历史性的叙述开始。凤凰从“资本主义的逻辑”中“漏”出来了,并开始其漫长的“寻根问祖”之旅。从古人的“凤凰台”开始,历庄子、李贺、李白、韩愈,这是古典中国的凤凰图腾,带有传奇和梦幻的色彩,并与古典中国的神秘保持着一致性,这是一种古典的凤凰试图在现代飞翔的可能。然后凤凰一跃而到现代,在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终结晚清,“凤凰党人”则以“武器的批判撕碎地契”,这是革命的凤凰。“去丈量东方革命,必须跳出时间之外”,如果跳出了时间之外,东方的革命是否会呈现出另外的模样?列宁和托派都没有见过凤凰(如果凤凰是一种历史的话,也就是说列宁和托派都不了解东方的历史),那么,马克思见过凤凰没有?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更多的人只是“坐在星空读资本论”。东方的革命如果跳出了时间之外——毫无疑问,这个时间指的是由黑格尔所奠定的西方时间观——也许革命的凤凰会有新的“涅槃重生”的机会吧?那么毛泽东时代呢?北京被想象为世界的中心,凤凰被想象为所有的鸟儿,但实际情况是,“十年前,凤凰不过是一台电视。四十年前,它是两个轮子”,是“26寸的圆:毛泽东的圆”。虽然它一直在试图开辟另外的时间和空间,并不惜为此进行文化上的大革新,但时间的强大惯性还是将它留在了历史原地:“但一辆自行车能让时间骑多远,能把凤凰骑到天上去吗?”
在整个长诗里面,这是我最喜爱的几节。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写作要么陶醉于修辞的锤炼,欧阳江河也一度是其中的代表;要么沦为一种过于简单的文化表演,这种表演或者以口语的粗俗来对抗虚构的“知识分子姿态”,或者在这种虚构的“知识分子”镜像中自恋自大,刻意塑造受难者的形象并以殖民主义的媚态去迎合西方对于中国的政治想象。这种种写作,都在写作行为中抽离了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历史,因为自我的视域仅仅指向自我本身,现实和历史也就对其关上了洞察的大门。欧阳江河在《凤凰》中则重启了这一大门⑦,长诗的第10—14节以“凤凰”为主导性的符号,几乎将整个中国历史浓缩其中。历史被凤凰激活,历史的每一次可能性都是凤凰的一次“飞翔”,这种“飞翔”越是现代,就越是艰难。凤凰的飞翔可以说是一次次的历史势能,是一次次的历史冲动,在这种势能和冲动中,历史得以辩证地完成自身。欧阳江河在这一部分展示了非同一般的历史视野,他以辩证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态度去面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史,在这个意义上,这首长诗是一首兼具历史意识和当下性的现代史诗。正如吴晓东所指出的:“在欧阳江河的《凤凰》中,‘现象学’的阐释结构与史诗品质的追求之间具有一种同构性。而当代史诗的尝试,不仅追慕了以庞德、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所贡献的现代史诗的高度,而且在复杂幻变的新世纪探索了一种开放性的史诗理念。”⑧
四、“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
如果剔除出于智力优越感的炫技和对词语象征化的迷恋,《凤凰》对于历史的辩证法的书写可以说构成了另外一种逻辑,即历史的逻辑。这一逻辑区别于资本的逻辑,它以交换为原则;也区别于词的逻辑,它以修辞为原则;历史逻辑则遵循可能性的原则。以诗歌的形式来展示历史逻辑的可能性原则,这里暗示了某种“诗歌”与“历史”的天然契约关系。诗歌——尤其是长诗——必须在历史的逻辑中才有可能重新找到自己的修辞方式、表意系统和象征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凤凰》具有了独特的症候性,它指向一种“大诗歌”的远景,这种“大”,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体量庞大,而是指通过重新疏通诗歌、历史、哲学之间的通道——这些通道一度畅通无阻,却被现代这一装置幽闭——展示具体现实的生存图景。
历史逻辑因为暗合诗歌的可能性原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断言的),因此隐约具有了某种反抗的冲动,这种反抗既指向历史,同时又直指当下,但这种反抗似乎被卷入一种宿命式的失败之中,或者说,借助这种不断的反抗,历史反而建立起了更稳固的秩序,更空虚但是却更“辉煌”的世界景观——在第14节,我们不无悲哀地发现,那只一再想“一飞冲天”的“凤凰”最终还是变成了徐冰重量级的钢铁怪物:
空,本就是空的,被他掏空了
反而凭空掏出一些真东西。
比如,掏出生活的水电,
但又在美学的这一边,把插头拔掉。
掏出一个小本,把史诗的大部头
写成笔记体:词的仓库,搬运一空。
……
凤凰彻悟飞的真谛,却不飞了。
“凤凰”在茫茫虚空中神游一番后,再次一头扎进现实的世界,对于这种情况,拥有上天下地之力、拥有“人之眼”和“凤凰之眼”的大叙述者似乎也无能为力,他只是发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感叹:“这白夜的菊花灯笼啊,这万古愁。”这一声感叹似乎颇具古意,但有经验的读者立即发现,欧阳江河在此非常巧妙地挪用了两个重要的意象,一个是白夜,它是女诗人翟永明经营的一家酒吧的名字,而菊花灯笼则来自翟永明作于1999年的一首诗《菊花灯笼漂过来》,它们构成了一种现时性的对话,当古典的意境遭遇冰冷的现实雕塑之后,当菊花灯笼漂到CBD的铁流中,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除了“万古愁”,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如果将整部长诗视作一个整体,我觉得它的结构可以概括为“正—反—合”,第1—7节为“正”,以完全客观化的视角去描写现实,第8节以“漏”为核心,可视作是一个过渡段落,第9—14节则为“反”,以辩证法的方式勾勒历史的逻辑,并在这一过程中展示可能的维度。第15节则又可以视作为一个过渡,这一过渡段首先承接上文的历史叙述,“李兆基之后,轮到了林百里”,这是已经软下来的“铁的事实”,这一事实由地产商(李兆基)和电脑商(林百里)所构成,“鹤”变成了“凤凰”,历史的可能再次回归为不可能。⑨唯一存在于当下的只是“不朽”,其原因在于“没有人知道不朽的债权人是谁”,因为“不朽”没有主体,没有所属,所以它才能得以逃出时间和资本的控制。我觉得欧阳江河在这里遭遇到了深刻的历史观的分裂,非常明显他并不愿意停留在古典的“哀愁”传统中,所以只是以揶揄的方式发出轻微的喟叹。他愿意在当下为当下寻找出口。所以这一节虽然是过渡,却有复杂的纠缠在里面。一方面时间被命名为“不朽”,却又心不甘情不愿,害怕失去时间“与不朽者论价,会失去时间”,于是他采用了一种看起来很奇特的方式——“对表的正确方式是反时间”。在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小说《返老还童》的开篇,钟表匠制作了一个逆方向行走的大钟,于是时间成为了“反时间”,这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时间的一种诅咒和嘲弄。在《凤凰》中,历史的秩序已然无法通过“飞翔”来予以颠倒重置,那就只有通过“反时间”的方式固守在当下,并对当下给予一种“英雄般的赞美”。这就是第16—19节“合”的内容,这是一种波德莱尔式的赞美⑩,赞美的对象包罗一切,有当下性,有众人和个别人,有凤凰和鸟群,有火树银花,有天空和星星,总之——是“全体”:
一堆废弃物,竟如此活色生香。
破坏与建设,焊接在一起,
工地绽出喷泉般的天象——
水滴,焰火,上百万颗钻石,
以及成千吨的自由落体,
以及垃圾的天女散花,
将落未落时,突然被什么给镇住了,
在天空中
凝结成一个全体。
这“全体”是什么?
它可能是黑格尔的以资本主义精神为主导的历史景观。
它可能是被马克思所讨论过的不断重复的悲喜剧结构。
它也有可能是柄谷行人所谓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的资本体系。
它更有可能是一个杂糅的后现代事实:中国和世界同尘,资本与革命盟约,凤凰与人类合体,真实与虚假同一,可能与不可能反复轮回……
注释:
①李陀:《〈凤凰〉序言》,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里尔克有名诗《豹》,威廉·布莱克有名诗《虎》,都可视作以诗歌喻猛兽的佐证。
③吴晓东指出:“《凤凰》虽然在诗艺结构上具备了一种堪称完美的完整性——一种由核心意象‘凤凰’所凝聚的完整性,但从诗歌的意识形态远景以及史诗内在的视景的双重意义上看,《凤凰》也同样是一首无法完结的诗作。”见吴晓东:《“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评欧阳江河的〈凤凰〉》,《凤凰》单行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师力斌在《飞得起来落不下——读欧阳江河的〈凤凰〉》一文中征用李陀和苏炜《新的可能性:想象力、浪漫主义、游戏性》一文的观点,认为想象力实际上不是形象创新和思维开放的问题,而是思想力和观察力自由的问题。从而得出“作家的想象力与其思想力和自由度成正比”的观点。将“凤凰”的飞翔与诗人的自由作了非常有意思的类比。见师力斌:《飞得起来落不下——读欧阳江河的〈凤凰〉》,未刊。
⑤欧阳江河在《“凤凰”的意义重叠》一文说:“在我看来,徐冰考虑了三方面因素:作为一个图纸上或二维平面的概念;凤凰是由工业废料品的搭起来的作品,徐冰考虑更多的是工业体量感,而不是雕塑本身的空间占有和暗示性。其次是考虑作品的构成材料,这些材料全都保持生活的原尺寸大小,比如搅拌机、钢筋骨架、水泥、安全帽以及各种工具。这些被触摸过的劳动工具还保留了劳动的真实性,也包含着对劳动的一种尊重,或者是礼赞,以及种种批判性的思考:劳动和财富的关系,现代和古代的关系,艺术和资本的关系。”“这些生活中原尺寸的物体,与工业的体量感合并后,触及了我想指出的第三方面的因素,将艺术品本身作一个夸大——以纪念碑般的史诗尺寸,构成反讽的、相互抵触的、过度的比例关系。这三种因素构成了凤凰的重量以及它的体量感。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从雕塑的角度考虑。这与其说是雕塑,不如说是反雕塑。”见欧阳江河:《“凤凰”的意义重叠》,载《艺术时代》2010年第3期。
⑥欧阳江河:《“凤凰”的意义重叠》,载《艺术时代》2010年第3期。
⑦吴晓东认为:“《凤凰》在这个意义上也构成了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某种超越。”见吴晓东:《“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评欧阳江河的〈凤凰〉》,《凤凰》单行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⑧吴晓东:《“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评欧阳江河的〈凤凰〉》,见《凤凰》单行本,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⑨根据欧阳江河的描述:“徐冰最初的方案做的是‘鹤’,这源于他一次漫步中在近距离看到的鹤,在离开地面起飞的那一瞬间的姿态对他造成的内心感动和视觉冲击。他其实是想把这一瞬间在他心理上造成的视觉和灵魂上的深深感动,转化为具体的作品。……但是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呢?因为这个作品最初的订购者是李兆基,作品本身是他为北京的财富中心这一特定建筑物的‘订货’。而鹤这个对象,在语义、象征和符号层面,与买家八十多岁年龄有着相冲突的暗示——‘驾鹤西去’含有关于死亡和归天的暗示,最后迫使徐冰放弃这一创作计划。凤凰一开始并不是他的创作构想,但这个作品与资本的关系一开始就被固定了。这个现象本身非常有意思:最后迫使艺术家改变作品创作构想的,不是艺术品的形状以及视觉的语义设计等因素,而是由于象征层面的因素造成的——所谓事先规定好的神学假定:‘驾鹤西去’。”见欧阳江河:《“凤凰”的重叠意义》,载《艺术时代》2010年第3期。
⑩在我收到的《凤凰》第四次修改版中,第13节有一句:“这奥义的大鸟,这云中君。”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波德莱尔著名的《信天翁》。正是波德莱尔在《1846年的沙龙》中提出了“现代生活的英雄”。但是在《今天》版本中,“云中君”被换成了“云计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