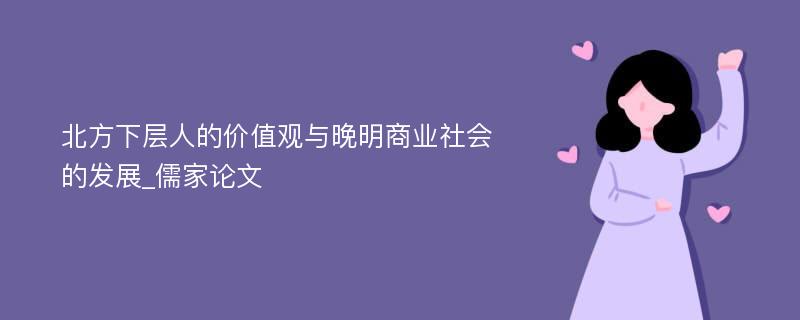
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层论文,价值观论文,民众论文,社会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1-0005-08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近来发表的关于17世纪中国宗教和家庭伦理的两篇文章包含一个共同的看法:16、17世纪中国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儒家观念体系有很大的错位和冲突(注:参见赵轶峰“儒家思想与十七世纪中国北方下层社会的家庭伦理实践”,《明史研究》第七辑;“17世纪前后中国北方宗教多元现象初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就当时发生的社会总体变动提出一个推论:这些变动的观念意识方面的主导的基础是当时普通民众的价值观而不是处于困境中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精英价值体系。从反面直接支持这个推论的历史事实是,明代中国社会的主要变动,包括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不是国家政策引导的结果而恰恰是伴随着明朝初年建立的土地、人口、赋税、商业制度和政策走向失效的过程而发生的,而儒家思想界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分化蜕变而再没有完成理学鼎盛时代那种程度的一致性。这个推论无疑带有韦伯思想的色彩,因为它的前提假设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观念体系对该社会的转变发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它又与另一种带有韦伯思想色彩的看法,即以所谓“新儒家”伦理来解释前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看法相冲突。后者当然以余英时教授和杜维明教授为倡导(注:参见杜维明,“Toward A Third Epoch of Confucian Humanism:A Background Understanding”,载于Irene Eber编Confucianism:The Dynamics of Tradition,New York:Macmillan,1986;并参见杜维明“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Daedalus,120∶2(Spring 1991),P.1-31。余英时教授的看法主要见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
韦伯认为“inner—worldly asceticism”(入世苦行)是调动人们从事积极的商业行为的必要因素。而这种伦理品质又是清教伦理中所独有的(注:韦伯关于儒教的系统观点,参看韦伯的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这是韦伯1920年发表的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中的一部分。这本书可以被看做是韦伯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的姐妹篇,参看Max Weber,“The Prefatory Note” in 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51。)。他认为清教徒为取悦于上帝而极其勤奋节俭地从事商业活动。余英时教授在批评韦伯时指出,中国新儒家伦理中也具有这类入世苦行的主要成分,两者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1](p67-69,74-84,136-166)。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种特殊的伦理成分肯定不足以解释诸如从前近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变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韦伯的新教伦理假说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他关于儒家伦理与现代社会的不协调性的看法,却大致不错。余英时教授在考察中国近世商业精神的时候提出的新儒家的入世苦行的事例相当多是非经济性质的和含义不明的,不足以调动明清鼓荡而起的商业行为浪潮。在余先生的论述中,王阳明和心学是新儒家积极作用的主要例证。但是王阳明在儒家内外都受到批评,嘉靖皇帝曾经一度明令禁止王学,顾炎武也对王学提出过严厉的批评[2]。心学在16、17世纪很有影响但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余先生和韦伯一样取了儒教中心的视角而忽略了下层社会宗教和伦理价值的特殊性。如果在17世纪的中国存在类似西方的清教伦理这样的东西,这也要在下层社会中寻找。
本文拟通过对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较东南落后的北方下层民众涉及商业行为的观念进行初步考察来说明:下层民众的伦理观念体系与近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之间并没有任何严重的障碍,而儒家思想与商业伦理之间反而存在严重的紧张。对于下层民众说来,卷入商业活动只是条件问题,而对于严肃的儒家人物则是自我变异的问题。韦伯主义的方式不可能回答传统中国商品经济没有自行转为近代形态的原因问题,也不能恰当地回答中国宗教文化伦理的特点问题,这主要不是因为它对儒家的误解,而是因为对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关系,乃至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误解。考察以北方为范围是因为北方在商业发展方面相对落后,而更为发达的东南地区的情况又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其实对东南地区的考察和对北方的考察所能得出的结论同理,此处特以北方为中心。
二、北方庶民的生财行为
16至17世纪间北方的商业发展程度仍不及江南,但是比较其他地区则更为活跃。张瀚曾经写了几篇文章描述明中叶以后北方的商业活动。他注意到,“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鲜矣。今辇毂之下,四方之人咸集焉。其在官者,国初以工役抵罪,编成班次,有五年、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二年、一年一班者……自后工少人多,渐加疏放,令其自为工作,至今隶于匠籍。若闾阎之间,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尤众。”[3](卷四)北京近郊的宛平县县令沈榜也注意到:“即使国门之外,画地而畦,围堑而庄,疑于农业矣,而所植非珍果奇花,则蓝蓼卉草。何者?彼一畦之入,货之固抵阡陌也。山壑之民,岩居谷汲,批裘舔犊,疑于业农矣,而所治非薪厂煤窑,则公侯厮养。何者?彼丝毫之利,岁计故致倍蓰也。”[4](卷一)沙河县:“人尚俭朴,士崇儒雅,市多逐末,农力粪田。”[5](卷一一七)傅衣凌先生在关于明清河南武安商人的研究中征引的许多文献中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如商业河南林县人民“稼穑兼陶窑”,“稼穑兼商贩”,河南武安“最多商贾,厢坊村墟,罔不居货”等(注:参见傅衣凌:“明清时期河南武安商人考略”,载《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8-205页。以上引文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河南·德府志”。)。
北方下层社会庶民面向市场的经济活动是在16、17世纪达到一个空前活跃的水平。《泰安州志》记载说,元末明初的时候,该县的人民“人情朴厚,俗有儒学”,“士尚诗书,民执常业”。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时候,当时的地方官任弘烈则说是“风移俗易,浸淫于贸易之场,竞争于锥刀之末,民且不自知其习于浮而风斯下也。以余耳目所闻睹,学士大夫循循笃行古风者什之二三……”。任弘烈显然是把这种变化看做传统价值的没落[6](卷一)。清朝初年兖州和青州农业商业化的情况显示出,普通农民在卷入商业活动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犹豫。兖州的滋阳县,自从顺治初年开始种植烟草,到雍正年间(1723—1735年)烟草种植已经普及到全县。商人频频来到这里收购,烟草牙人因而迅速增多[5](卷二三八)。
从17世纪的文学作品中看,经商是社会下层人,包括没有其他出路的生员谋生的重要手段。例如在《醒世姻缘传》中,狄希陈因为被妻子辱骂而离开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在兵部洼儿开个小当铺,赚的利钱以供日用”[7](第七十六回)。山东破落户宋明吾利用打官司断得的银钱到南京开杂货摊赚了钱,再回到山东“开了一座南京大店,赚得钱来,买房置地,好不有兴”[7](第六十三回)。这吸引了邻居富裕农民家的儿子张茂实,他“每日在那镇中闲坐,百物的行情都被看在眼内,所以也要做这一行生理;收拾了几百银子,独上南京,回来开张贸易……”[7](第六十三回)。这些描述给人一个清晰的印象,明朝后期的下层民众可以很容易地介入商业行为,没有任何观念上的障碍。在儒家的观念中,普通庶民的经商求利行为也要比儒生的同样的行为更自然合理。如清朝学者钱泳就说:“商贾宜于富,富则利息易生。僧道宜于贫,贫则淫恶少至。儒者宜不贫不富,不富则无以汨没性灵,不贫则可以专心学问。”[8](卷七)
三、庶民经商行为中的观念问题
虽然商品化似乎是晚明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但商业行为本身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由来已久。《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西汉时期的晁错已经看到:“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9](卷二四,上)。汉代已有河南中州“俗尚商贾,机巧成俗”的说法,并将其渊源追溯到周代[5](卷四三二)。山东兖州地方人民不鄙视商业的观念也可以追溯到汉代:“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衰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10](卷四)据此,则儒家的衰落和民风趋于利是相伴随着的。其实,一定数量的财富是生存的必要保障,私有制发生以后,对于财富的追求就成为普遍的价值倾向,引起道德问题的是对财富追求的程度和手段,即这种行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儒家伦理不以财富为出发点,但也不遏止它,而是推崇通过内心修养和服务于国家而光荣地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所以,16、17世纪中国下层社会普遍牟利倾向丝毫不是新奇的现象,而只是一个古老传统在社会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活跃。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说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伦理包含一种为了响应上帝赋予的天职(calling)而努力实践现世生活中的勤俭以求商业成功的精神。儒家本是入世的,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由于缺乏主张超越性拯救的统一宗教,都是强烈关注现世的。所以在入世取向这一点上,新教伦理和整个中国价值体系并非冲突,儒家思想与民间文化在这里也无根本的差别。差别在于:儒家的取向是通过个人道德完善和建功立业贡献于入世的道德完善;民间的取向则表现在更朴素的实用主义中。勤俭本身是中国文明开始时期就表现出来的特色,它的基础是民众普遍的低生活水准、频繁的灾害和政治动乱。这是一个简单的生活逻辑而无须宗教精神的推动。《管子》中就有“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的说法。世代习惯于节俭勤劳的农民无需任何其他的道德的或者宗教的激励来从事苦行式的积攒钱财的事情,问题是社会条件如何。
17世纪的小说《照世杯》描述了一个勤俭致富的故事:“有个姓穆的太公……原来义乡村在山凹底下,那些种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鸾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拾些残粪,这些粪到比金子还值钱。穆太公想出一个计较来道:‘我在城中走,只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我却如今想个制度出来,到强似做别样生意!’随即去叫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尽贴在这粪屋壁上……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太公从买粪坑之后,倒成了个富足的人家。他又省吃俭用,有一分积一分,自然日盛一日。”[11](“掘新坑悭鬼成财主”)穆太公的勤与俭对于中国下层民众说来,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故事的背景被放在湖州乌程,但这是全国普遍的情形。以山东为背景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中就讲到这种生意的利弊[7](第三十三回);明末官员李清处理过一个经营此道的生员董应迈的案子[12](P220-221);清初人钮琇也提到类似的事情[13](P232-233)。
按照韦伯的理论,明智的计算和理性化的簿记管理也是近代商业伦理的特征。但这些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由来已久的。战国时期孟尝君曾问门下食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责于薛者乎?”[14](卷一一)现在固然没有依据具体地判断当时的“计会”和复式会计是怎样的关系,但这里考察的是价值观念和经营观念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事实上,会计管理在明代已经达到很发达的程度。现存明朝政府的《万历会计录》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等反映了当时的水平。明中叶李梦阳为杞县人张廷恩所写的墓志铭中记述的情况颇类复式记账管理。铭云:“土俗租地亩钱百,张公则八十。已而曰:‘吾地亩租五十。’于是人争来租地,无间者。计其入反倍于他,由是富盛。”“其粜仓谷日入钱缗竟无弗明者。或问之。曰:‘凡仓谷入记之簿,予第令一仆主其出如簿数则已。又令一仆主入缗,缗头封识其姓名,有弗明责之渠也。”[15](卷四二,“明故例授宜武卫指挥张公墓碑”)
晚明北方下层民众的商业观念固然与近代商业社会的商业观念,或者和韦伯安排与新教伦理相对应的商业伦理有不同的色彩,但是我们看不出他们是不相容的观念体系。
四、儒家对商业行为的态度
儒家也鼓励人们忍耐贫苦的物质生活条件甚至认为这可以砥砺一个人的道德情操。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渊就因为能够平静对待贫苦的物质生活而得到孔子的赞赏。但儒家的节俭观受到儒家礼的观念的制约。当有人间到祭祀的羊可否省略的时候,孔子说:“尔爱其羊,吾爱其礼。”这里的价值中心是庙堂的尊严、地位显示、等级秩序等。这种节俭观念并没有能限制王室、贵族和官僚阶层的奢侈消费。在帝制中国的后期,奢侈的是缙绅阶层普遍的生活方式并且成为官僚腐败的一个基础。与此同时,儒家一般地对商业行为和商业持蔑视的看法。虽然一些士大夫卷入了商业活动,但这个时代承认商业行为合理性的儒家思想家主要只是承认这种行为对于社会说来是必要的成分,但总是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情况下才会亲身去从事,而不将之作为理想的人生目标。16、17世纪间士大夫卷入了商业活动的现象并不表明它们是为儒家伦理所推动的,它们更像是下层社会价值对士绅阶层影响的表现。下层知识分子因为生计问题和与庶民阶层接触密切,多能认同商业活动。
虽然儒家伦理和大众伦理有重叠的地方,明清时期的儒家经营对商业行为的态度还是和普通民众的不同。这首先是由于他们作为政治人对财富本身的戒备心理。晚明大学士沈鲤曾教导他的儿子说:“家下凡百俭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贵的气象,不惟俗样,且不可长久。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昃,一定之理。惟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虽处盛时,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张老先生一败涂地,只为其荣宠至极而不能自抑,反张气焰,以致有此。可为明鉴。我今虽作热官,自处常在冷处。必不肯多积财货,广置田宅,使身终之日留下争端,自取辱名。”[16](卷七)出身于纺织业家庭中的官僚张瀚认为经商是一种小聪明:“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怀巧捷给之夫,借资托力,以献谀而效奔走。燕姬赵女品丝竹,挈筝琴,长袂利屣,争妍而取容。彼且矜夸智能,足以自便,意笼宇宙之化工,计穷人物之变态,与时俯仰,举材货低昂,在我掌握中,持筹而算,百不失一,而不知其智能之小也。语云:‘大智闲闲,小智闻闻。’盖谓是耶?”[3](卷四)许多学者注意到《戒庵老人漫笔》中讲到的谈参(谭晓)善于经营节俭致富的事例,但很少人注意到,李翊所据邵北虞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要说明谈参的精明算计不过是小聪明,其富有及身而止,身后凄凉[17](卷四)。另一位晚明学者何良俊干脆认为财富是有害的,因为富裕人家的子弟比比弃学而从事商业(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中华书局,1959年,第313页。另清人钱泳说过:“银钱怪物,令人发白”;“富者持筹握算,心结身劳,是富而仍贫;贵者昏夜乞怜,奴颜婢膝,是贵而仍贱。如此而为富贵者,吾不愿也。”见《履园丛话》卷七,第178-179页。)。晚明官僚冯从吾“勤俭说”则举例说明:勤俭持家和认真簿记却不从事学术不仅不足以积累财富,而且是有害的[18](卷一四)。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政治手段来积累财富的行为主要地是由一些没有社会特权的普通人——商人进行的。儒家则一向支持“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抑”并不是“禁”,儒家思想家和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管理者都懂得商业是社会流通所必须的渠道,因而不能禁止。但是商业活动带来人口在地域间和职业间的流动,以及人心的浮动,增加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的困难,不符合儒家从稳定着眼的社会管理理念,必须给予控制。“抑商”政策显示出儒家从根本观念上与商品经济的矛盾。五代宋以来国家对商业的抑制相对减弱,儒家中也发生了一些重新估价商业活动的言论。但是从主流上说,儒家从来也没有放弃重农抑商的观念。中国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是在国家抑制减弱的前提下,而不是在国家支持提倡的推动下实现的。明朝初年,太祖下发了一个诏令,命令所有成年男子必须固守本业。任何人要离开家乡到外地必须告知邻里以防止出外经商。任何人要经商,包括那些已经得到官方执照的人在内,必须要拥有最少10贯铜钱或者钞票。本钱少于此数而经商者,要被发配到边远地方。10贯铜钱约值银10两,是个不小的数目。这样,小本经济的经营在14、15世纪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16到18世纪期间,情况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乡村的商业活动和乡村人民与地方、区域,乃至全国市场的联系发展到超过宋代和元代的程度。导致明朝中后期商业化发展的主要变化,如户口控制制度放松,白银取代政府发行的纸币成为主要流通货币等等,都不是在政府、士大夫,或者儒家思想家们的自觉倡导下发生的。它们首先是作为政府头痛的社会问题发生,在政府保持旧时状况的努力失败之后才得到政府的认可[19]。对于主流的儒家思想者说来,社会的商业化本身是儒家价值观念和社会稳定性式微的表征。而庶民们则没有许多顾忌,他们只是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谋求生存、富足,商业化的一般的而不是过度激烈的发展会带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机会。所以,庶民的价值、伦理、信念要比儒家的价值系统和商业化发展的关联更实际而紧密。
五、多样化与风气变动问题
韦伯关于中国宗教和商业伦理的分析和追随他的方法的关于中国的有关讨论几乎都是把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不变的或者是地域上说文化同质的对象。对时间定位的模糊和对历史变动的缺乏敏感实际上是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来分析历史问题时的缺点。社会学具有从地域具体性角度考察社会的方法工具,但是具体的研究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对地域差别给予关注却取决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内部区域差异的了解程度。韦伯眼中的中国是个远距离的而且间接得知的轮廓,被他当作一个文化宗教和社会单元的中国的内部区域差异是他的研究的盲点。我们前面的讨论虽然以16、17世纪中国北方为时间和地域上的范围,但也还由于论题角度含有针对性,所以没有突出历史变动和地域差异问题。现在来简单看一下这个方向会涉及程度如何的问题。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今山东列郡观之,乃不尽然。大较济南省会之地,民物繁聚。兖、东二郡,濒河招商,舟车辏集,民习奢华,其俗也文若胜质。青、登、莱三郡,冯负山海,民殖鱼盐以自利,道里僻阻,商旅不通,其俗也质若胜乎文。孔子所谓齐变至鲁,鲁变至道者,又不可执一以例。今之俗也,乃若六郡所同者,士大夫率多怀义质直,侃侃明达,如班固所谓好经术而矜功名,杜牧所谓多才力、重许可、能辛苦者,其风至今不衰。其小民力于耕桑,不贱商贾,丧葬有序,不泥风水。乡党岁时举社会,贫富相资,有蓝田乡约之遗风。此则山东风俗之近古者。”[20](“山东上”)山东一个布政司中,三个府文胜质,三个府质胜文,六郡又皆保留共同的前代遗风,各地有差别也有共性。历史上,至孔子的时代其风气就曾数次变化,不可“执一以例”。
以“文若胜质”的兖州一府而言,其于明代中期以后辖四州二十三县。其中府治嵫阳“俗温厚驯雅,华而不窕,有先贤圣之风,民好稼穑而不工生殖”。其东南的沂、费、峄、郯、滕、泗六县“民性朴质,无所纷华,以田畜自饶,颇有山泽之利”。沂州则“地多矿冶,揭竿鼓铸之奸时时啸聚”。府治西南的济宁、郓城、钜野、嘉祥、金乡、鱼台等地“俗稍华侈,士好文采,民逐末利”。由济宁而西南之曹州、单、城武、定陶“其俗阐缓和平,得刚柔之中,与豫境相类”。兖州西北方向的东平、东阿、平阴、阳谷、寿张,“其俗淳雅和易,文质得宜,土壤瘠薄,民务稼穑,不通商贾”[10](卷四)。其差别的基础在于地理条件、政治历史上的冲突治乱和经济交流之演进等。此为明代中期大致情况。复查其变迁,汉代地理志称其在姜齐时代尚经术,孔子时代好学尚礼义重廉耻,到汉代时候,“去圣久远”,则至于“俭啬爱财,趋商贾”。隋地理志云其人尚多好学,性质直怀义,但兖州近徐州,不若山东其他地方贱商贾、务稼穑、尊儒业[10](卷四)。至于明代情形则如上述,有“不工生殖”、“不通商贾”者,有好鼓铸而强悍的,有“民逐末利”的,差别极大。
如果以同样的方式来分别考察山东、河南、河北其他各府,看到的是类似的情况。其变动的不拘甚至有更频繁者。如《河南通志》所记河南各府、州、县人民对于商业的观念态度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并考其由来云:“班固谓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然则风俗者固山川地气使然,亦主治者之好尚有以转移之欤?”[21](卷二八)这里我们不能忘记,明代北方比较东南沿海地区在商业观念上是要保守得多,比较边缘地区却又还要灵动一些。所以,全国范围的差异又更是复杂得多的了。此外,关于明代后期中国北方民风趋于奢侈浪费的记载和关于勤俭节省的记载同样十分引人注目,两者的并存关系的基础更有待仔细的揣摩。那么,我们在前面几节的分析中所看到的明代中后期中国北方下层民众的宗教与商业伦理与近代商业化社会具有相容性的结论显然不能导致传统中国的价值体系为近代商业准备好了条件的进一步推论。这里的要点是用韦伯主义的方式来寻求传统中国的宗教和商业伦理与近代商业的关系是一个有意义但又很粗糙的方法。社会学和人类学之兴盛给予历史学极大的促进,但其毕竟有不能取代历史学注重时间、地点和具体情状的独特取向之价值处。
六、余议
中国社会的地域差异、下层社会的宗教多元化和伦理价值的多样化决定了中国的庶民们并不按照任何一个绝对的哲学或者宗教体系的规则行事。他们所遵循的是他们的生活经历给予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及与时代条件和历史传统相关的相互影响,后者即所谓风俗。这使中国的庶民们的行为缺乏一个宗教或者哲学指导下的人群的观念和行为的那种一致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庶民之社会行为没有纹理可循。中国商业伦理的基础既然是复杂的,它的变动也是复杂的。虽然儒家的思想观念和16世纪以来的社会商品化发展的关联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从儒家思想入手来解释这次商品化发展运动却会忽视更根本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和中国文明本身一样有古老的传统。但是过去的商人主要地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等级和专门职业。明后期以来的商业化的特征不在于商人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如何壮大,而在于商业活动成为四民大举卷入的活动,其中尤其是社会下层的工、农都在很大程度上卷入到商品经济中去。士大夫的经商虽然也有发生,但是比较起下层民众,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这个过程伴随着人口从强控制下的户籍类目向多种多样的以市场交换为方向的社会职业领域的流动。从社会身份控制角度说,这个变化是一个人的解放运动。明中叶以后中国商业社会的发展走的是一种独特的道路,考察下层社会的状况对理解这个过程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