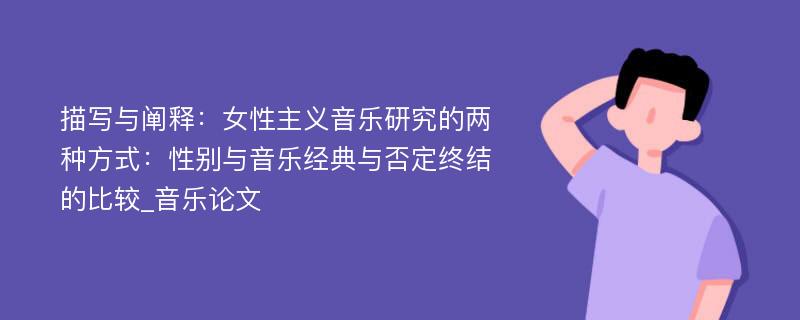
描述与阐释: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的两种途径——《社会性别与音乐经典》及《阴性终止》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阴性论文,音乐论文,途径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①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被引入音乐学领域,其初衷在于,“指出对女性音乐家在欧洲传统中地位的遗忘,使她们的作品得以出版、录制,并研究她们在音乐史上的地位”②。随着越来越多女性音乐家被发掘,音乐学者们发现在“遗忘”背后隐藏着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女性音乐家会被遗忘,以至于音乐的历史俨然成了“他的”历史(hisstory)?为什么女性在特定历史时期不被鼓励成为职业音乐家而往往仅能在家庭、沙龙等非正式场合从事音乐活动?为什么女性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无法享受与男性同等的音乐教育机会?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引导人们超越音乐本身,重新审视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观念,特别是其中的社会性别(gender)观念。 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性别”(sex)与“社会性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男、女性的生物特征,具有先天性;后者指特定文化环境对男、女性内涵的认定,它们规范着人们的社会行为。③比如,人们往往要求男性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要坚强而自信,要求女性应温柔、爱好整洁、能操持家务等。④任何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受这些观念影响,从而被塑造为符合社会所要求的样子。法国哲学家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常被引用的名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⑤ 在传统的父权制(patriarchy)社会中,男性被放置在优先地位。从受教育机会到职业选择,从收入分配到社会分工,女性处处受到压制。这正是女性作曲家被边缘化的社会根由。因此,一些学者不满足于仅收集、整理与女性作曲家相关的史料,还期望通过对作品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语境的解读、分析来批判父权制。其中,代表性学者有苏珊·麦克拉蕊(Susan McClary,1946-)⑥、玛西亚·希特伦(Marcia J.Citron,1945-)⑦、露丝·索莉(Ruth A.Solie,生年不详)⑧、苏珊娜·库西克(Suzanne Cusick,生年不详)⑨等。她们富于批判性的著述,使得女性主义音乐研究逐渐发展为批判音乐学(Critical Musicology)⑩的重要一支。 据《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介绍,女性主义音乐研究可分为两类:其一,受人类学影响(anthropology-influenced)的、关于音乐行为的研究;其二,针对音乐作品的分析式(analytic)或评论式(critical)研究。(11)前者偏重于以客观态度审视、描述特定语境中女性音乐家的行为及生活境遇,如创作、表演、职业选择、家庭生活等,带有社会学色彩,本文称之为描述型研究;后者偏重于阐释音乐形态中隐喻的社会性别观念,研究者积极提出对作品意义、价值的见解,不避讳、甚至鼓励作品解读的主观性,本文称之为阐释型研究。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述两类研究的差异性、各自价值及内在关联性,深化对女性主义音乐研究方法的理解,本文将选取两部风格迥异的著作,分别是美国莱斯大学音乐学系教授玛西亚·希特伦的《社会性别与音乐经典》(12)及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音乐学教授苏珊·麦克拉蕊的《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下称《阴性终止》)(13),就其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学术旨趣等方面做出比较和评述。之所以选择二者,一方面在于它们分属描述型研究和阐释型研究,为本文论点提供了良好例证;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女性主义音乐研究中皆属质量上乘之作,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社会性别与音乐经典》成书于1993年,偏重以社会学方法描述19世纪以来西方女性作曲家面对的种种社会限制,对其文化根源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藉此获得了国际妇女音乐联盟(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in Music)所设的宝莱·阿德曼奖(Pauline Alderman Prize)。英国音乐学家莉迪亚·戈尔(Lydia Goehr,1960-)曾指出:本书十分成功地呈现出女性音乐研究的最基本课题,其给出的答案也将具有持久的价值。(14)《阴性终止》则早已为我国学界所熟知,(15)成书于1991年,是最早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释音乐作品文化内涵的专著之一。直到今天,虽然人们对本书毁誉参半,却无法漠视其对英美音乐学研究中重形式分析、轻内涵解读的传统思路的犀利批判及在研究方法论上带来的新气象。美国学者克莱尔·迪泰尔斯(Claire Detels)曾说:“在她(麦克拉蕊)出版此书中各篇论文的五年来,文化批评和性别研究已从一个无人问津的领域变成了音乐学会议和刊物上常被提及的显学。”(16) 一、描述型研究个案评析 先来看描述型研究个案——《社会性别与音乐经典》。本书欲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在西方音乐文化中,女性作曲家的作品往往无法成为经典,常处于边缘地位?为了回答此问题,希特伦将注意力集中在19世纪,因为“该时段正是一系列习俗逐渐兴起和确立的日子,它们孕育了相互关联并在下一个世纪最终成为经典的曲目。”(17)在充分收集史料,了解当时主流社会性别观念、女性作曲家创作、生活状况及音乐评论、音乐出版业状况的基础上,作者主要从三方面展开叙述,力图重构其时的音乐生态景观。 1.音乐经典如何产生,由谁来认定? 希特伦指出:在人文艺术领域,经典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体现了某主流文化群体的价值系统,正是这个群体创造或维持着经典曲目库”(18)。换言之,经典是主流文化群体通过评价活动筛选出来的,与该群体的阶级、种族、性别、政治倾向等特征关系密切。主流群体的价值观具有权威性,渗透于社会生活诸方面,也渗透于经典形成的每一环节,从音乐创作、表演到接受、出版、评价、研究、教育环节,皆受其所控。具有影响力的表演者、团体选择上演什么,大众、出版商偏爱什么,评论家、音乐学者推崇什么,音乐教师以什么为教学内容,都有其背后的倾向性。他们的选择将使一部分作品得以突显,久而久之步入经典行列。那些被排除于经典范畴之外的作品只能暂处于边缘地位,等待着被发现。 在西方音乐文化中,所谓的主流文化群体即欧洲社会中上流阶层的白人,他们拥有一整套指引生活的价值观念,其中直接导致女性作曲家被边缘化的便是男尊女卑思想。希特伦指出,在19世纪,西方社会业已建立起来的父权制中充斥着一些蕴含不平等因素的二元论观念:首先,男性往往与文化性、精神性、理性相联系;女性则与自然性、身体性、非理性相联系。“在西方话语中,文化实际上被置放在自然的对立面。文化处于优势地位并与男性相关,自然则处于劣势地位并与女性相关。文化包含知识和人类所建立的社会结构,自然则暗示纯粹、未经开发的智力状态”(19)。由此,男性行为是文化层次的精神性劳作,如艺术创造,女性行为是自然层次的身体性劳作,如生育与家务。同时,女性的身体在相当一段时间中被认为是神秘且必须加以控制的。希特伦相信,这种男性控制欲根源于四方面,一是当时人们对女性生理结构不了解;二是人们相信女性无法如男性一般凭理性行事;三是男性对女性生育力的敬畏(即便是男性也由女性孕育);四是男性对女性性欲的恐惧(男性可能因此被耗尽)。(20) 另一对二元观念为:男性常与公共空间相联系;女性则与私人空间相联系。19世纪,欧洲人普遍认为两性分工应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与家庭可画等号。“这里包含了抚育子女、繁衍后代和自然性。由于家人是家的核心,妇女与私人空间有关。然而,她的家庭权威是有限的。她可能在孩子面前有权威性,却并非家庭的首脑。她从属于(男性)。这里暗示着某种被动而非主动的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丈夫因其处理家庭之外的事务而获得了权威性”(21)。女性即便要从事音乐活动,也常被限制在家庭音乐教育场合或沙龙中。 2.女性作曲家的“作者身份焦虑”(anxiety of authorship) 上述二元观念不仅为男性所推崇,也内化于每一位社会化了的女性意识中,成为一种自我限制,当她们期望以音乐创作为事业时,便会表现出矛盾心理。希特伦认为,19世纪的女性作曲家往往对自己的创作者身份缺乏信心,这被称为“作者身份焦虑”。她以门德尔松的姐姐范妮(Fanny Hensel,1805-1847)为例。范妮早年曾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酷爱创作,但当她考虑是否要以真名出版自己的作品时,却陷入了犹豫。1836年11月22日,在她给门德尔松的信中透露了这种心态:“关于出版的事情,我现在就像是一头站在两堆干草中间的驴。我必须承认对此事我持中立观点。一方面,汉塞尔(Wilhelm Hensel,1794-1861)(22)支持此事,另一方面,你反对。在其他事务上,我当然会完全遵从我丈夫的意愿,但唯独在这一点上,你的同意十分重要,没有你的同意我可能不会做任何此类事情。”(23)可见,范妮让自己依附于男性,失去了独立决断力。而门德尔松就此事给母亲致信道:“我想我毋需多言,如果她决定出版些什么,我会尽全力帮助她并消除这里产生的困难。但我不会去鼓励她出版作品……她作为一位女子并不适宜如此,而应照料她的家园……”(24)很明显,门德尔松所信奉的仍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 当一位女性真正走上职业化道路,她便更须面对作曲家和家庭主妇身份的矛盾,许多人不得不晚婚或放弃创作。希特伦援引了一些实例:如法国女作曲家、钢琴家查米娜德(Cecile Chaminade,1857-1944)为了专心创作,在44岁时才步入婚姻,嫁给了比她年长20岁的出版商卡本奈尔(Louis Carbonel,生卒年不详);英国女作曲家克拉克(Rebecca Clarke,1886-1979)在58岁时与钢琴家弗里斯金(James Friskin,1886-1979)结婚,后停止创作;美国女作曲家克劳福德(Ruth Crawford,1901-1953)在事业上升期与民族音乐学家西格(Charles Seeger,1886-1979)结婚,出于抚养子女或受丈夫影响等原因,她放弃了作曲事业,转向美国民间音乐研究(25)。照顾家庭与抚育孩子的压力使许多女性作曲家难以全身心投入创作。 3.男性接受者审视下的女性作曲家 除了从创作者角度剖析职业女性作曲家的限制因素,希特伦还从接受者角度展开论述。她认为,接受行为反映着特定语境中的群体评价标准,其实质即人们如何评论音乐。自1800年以来,正式书写的音乐评论在经典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影响并塑造着大众趣味。然而,“评论家群体几乎都由男性构成。女性的稀少意味着女性声音和女性观点的缺失……男性话语构成了职业音乐评论的基础”(26)。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评论家角色隐含着精神性、智慧和仲裁者的内涵:其认识论根基在于向他人传播知识。这让人们回溯至上帝的概念,上帝是最高权威的代表。然而,上帝是一位男性,由此,女性无法获得传播知识所必须的伦理根基……其结果便是鲜有女性评论家出现”(27)。 当男性评论家审视女性作曲家时,他们像一位“智慧却具有权威性的父亲”(wise yet authoritarian father),女性作曲家则被赋予“从属性质的、小女孩般的形象”(subservient,daughterly figure),她们往往与“天才”及“原创性”等美誉无缘,还可能获得让人无所适从的评价。希特伦列举了两则关于查米娜德的评论,其中一则说到,她的作品“强劲而富于男子气,或许太富于男子气了……对于我来说,我非常遗憾,找不到一丝女性本质中所具有的优雅和柔美”;另一则却说,她的音乐“如此具有女性化的优美和优雅,却令人惊讶的浅薄且缺少变化……所有的女性,当她们从事音乐创作时都是肤浅的”。(28)以上两则评论相互矛盾,使被评论者陷入左右为难的“必败”(no-win)窘境。一些女性作曲家为了避免不佳待遇,尝试采用男性名字出版作品,如美国作曲家布罗夫(Edith Borroff,1925- )曾说:“在我获得了作曲专业学位后,我发现我作品的表演和出版都与我的性别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有以我真名署名的作品都被拒绝了……相反,有两部以男性假名署名的作品却被接受了。”(29)这无疑是对男性主导的评论话语的讽刺。 从以上介绍可见,描述型研究较突出的特点在于:不关注音乐形式结构分析,不关注音乐形式中蕴含了怎样的内涵,更乐于叙述音乐之外的社会、文化生活细节和特征。在叙述过程中,描述型研究始终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为依托,重事实、讲依据,较好地避免了研究者的主观随意性(当然,所谓事实材料,既可以是史料,也可以是通过实地调查、统计而获得的现实材料,可根据研究对象而定)。如在回答“女性作曲家为何被边缘化”的问题时,希特伦细致描述了音乐世界中不同角色,包括女性创作者和男性接受者、表演者、评论者、研究者、出版者的价值观念、心理定势及互动行为,将彼此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自然而然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引发其思考。这种思路也具有鲜明的社会史研究色彩,扎实稳健、可信度高。 二、阐释型研究个案评析 与前者相比,麦克拉蕊《阴性终止》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不满足于音乐之外的社会史实叙述,欲揭示音乐形式之内蕴含的性别内涵。麦氏在全书开篇便系统介绍了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的核心课题:其一,研究不同作曲家如何刻画男、女性别特征;其二,研究音乐理论史上人们如何赋予终止式、和弦、调性等因素以性别内涵,如将强拍终止式、大三和弦、大调式视为阳性,将弱拍终止式、小三和弦、小调式视为阴性;其三,研究音乐过程与性别、性欲特征的联系,如将奏鸣曲式第一主题视为阳性,第二主题视为阴性,圆满的解决则是对阴性的抑制;其四,研究评论家对音乐风格的性别化比拟,如视肖邦为女性化的,视贝多芬为男性化的。其五,研究女性音乐家如何通过作品质疑男性主导的音乐传统。本文以为,这五方面不仅可视为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的核心课题,更可作为女性主义音乐阐释的具体方略。书中,麦克拉蕊正是运用着这些方略对文艺复兴以来一系列音乐作品的性别内涵进行深度阐释,包括蒙特威尔第的歌剧《奥菲欧》、比才的《卡门》、柴科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甚至流行歌手麦当娜的作品等。因篇幅所限,本文仅重温三例。 1.西方传统与当代音乐作品中的性别内涵 在“古典音乐的性政治”一章中,麦克拉蕊剖析了歌剧《卡门》各角色的性格命运及音乐特征,揭示出两对矛盾关系:其一,贞女与荡妇的冲突。剧中女配角米凯拉的音乐“简单、抒情、甜美……节奏天真不含肉体性”(30)。卡门的音乐则是具有异国色彩的哈巴奈拉舞曲,其摇摆的节奏和半音下行的旋律挑逗着霍塞和观众的欲望,也冲撞着追求严肃性的欧洲古典音乐传统。其二,“恶女”与父权制的冲突。所谓的恶女即卡门,其之所以恶,是社会性别观念认定为恶。霍塞则是父权制的代表,其音乐总体上循规蹈矩,“专注于崇高的情怀而不是身体”(31)。但在《花之歌》中,霍塞跨越了理性的边界,充分表达了对卡门的爱欲。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卡门不但拒绝了他,还利用了他。走投无路的霍塞刺死了卡门,这是他回归父权制行为模式的写照,似乎要以暴力重掌控制权。歌剧结束在象征阳性的大三和弦上,这意味着父权制的胜利,但并未终止在起始调上,又暗示着不完满,因为霍塞最终也毁灭了自己。 通过分析蒙特威尔第的牧歌《仙女的悲歌》(Lamento della Ninfa),麦氏引导读者关注西方音乐文化中塑造的疯女人形象,并对其文化意义做了剖析。此作品结构为三段式,两端由男生三重唱演唱,稳健而富于理性,中段的悲歌加入女高音声部,此段讲述一位被爱人遗弃的仙女在悲痛的回忆中陷入疯狂。麦氏认为:仙女富于情感性的声部虽构成中段的亮点,却总是“被男声三重唱小心中介:他们引进她、总是伴随着她直到结束,然后以简短的小结尾让作品安全关闭”,“他们为她的第一句话加上‘她说’……当仙女结巴时,他们完成音乐的句法单位,确保理性连贯不因她而损失……最后,他们以两个自满的C大调终止式带我们回到安全、规规矩矩的现实”。(32)麦氏有三点解读:其一,在欧洲文化传统中,往往将女性与疯癫、精神病联系起来,因为女人被认定为非理性的动物。其二,此作品中的男生三重唱既像疯女人形象的呈现者,又像听众的保护者,他们确立着父权秩序的框架,犹如“疯人院窗上装着的栅栏”,确保听众“安全观看她的痛苦……并获得美感享受”。(33)其三,疯女人代表着反抗理性社会的力量,但她实际上是男性的创造物,是男性自身矛盾的外在投射,因为男性也不时渴望摆脱理性的控制。 从美国现代作曲家范德费德(Janika Vandervelde,1955-)的钢琴三重奏《创世纪Ⅱ》中,麦氏又解读出两层深意。首先,作品表现了自然与人类文明的冲突。作品以类似分娩时胎儿心跳的固定音型起始,它由钢琴演奏,创造出循环往复的意象,隐喻大自然无始无终的更替。弦乐声部起初与固定音型和谐共处,随后第一次躁动起来,推向高潮,撞击着固定音型确立的秩序。这意味着人类不满于活在当下,开始了无止尽的求索。麦氏说:“17世纪由宗教改革、殖民地扩张、人文主义、哥白尼与伽利略的科学革命、笛卡尔哲学,以及许多其他因素促成的广泛危机,将文化的理想从稳定与平衡改成了对过度、个人主义的肯定。”(34)当固定音型再现时,已然支离破碎,然而,弦乐声部又一次展开了无情攻势,这一次夹杂着20世纪音乐语言,犹如当代文明对自然界的又一次冲击,固定音型被彻底瓦解,音乐达到第二次高潮。此后,躁动渐渐平息,音乐在寂静中结束,好似人类重返胚胎,一切如梦。上述分析透露出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忧虑,着实发人深省,但麦克拉蕊并未止步,将作品与性别问题联系起来。她相信,钢琴声部的固定音型营造出一种女性化的持续快感意象(image of pleasure),而弦乐声部的进取、强势和暴虐则营造出男性化的欲望意象(image of desire)。在男性欲望不断膨胀并最终走向毁灭后,一切又重归创世前的宁静。(35)这里隐含着以女性思维拯救男性欲望的内涵。 2.为赋新词强说愁? 麦克拉蕊的音乐阐释不乏精彩之处,她将音乐形式分析与社会、文化批评联系起来的思路,着实为读者提供了理解音乐的新途径,但有时也难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特别在分析纯音乐作品时更为明显。美国学者皮耶特·图恩(Pieter van den Toorn,生年不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细节:麦氏在“爬下豆梗走开”一章中对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阐释曾被其本人修订。此章节最早以论文形式发表(36),后在收入《阴性终止》时,作者删去了一些过激用语。在原版中有如下叙述:“贝多芬交响乐为风格史添加了两个维度:侵犯性的骨盆撞击(assaultive pelvic pounding)(如《第五交响曲》末乐章和《第九交响曲》‘消极’的第三乐章之外的其他乐章)和性暴力。《第九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再现部是音乐文献中最骇人的时刻,当精心准备的终止式受挫,被抑制的能量最终在无从发泄的强奸犯让人窒息的、凶残的狂怒(throttling,murderous rage of a rapist)中爆发。”(37)美国音乐学家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1945-)曾以“令人愤慨”(scandalous)来形容他对这段话的感受。(38)或许连麦克拉蕊自己都觉得这些用语十分不当,于是在修订版中删去了“侵犯性的骨盆撞击”、“性暴力”、“无从发泄的强奸犯让人窒息的、凶残的狂怒”等辞藻。(39)上例说明,阐释型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个性化的音乐理解方式,却也并非毫无底线的任意行为,一味求新求异、生拉硬扯而无视作曲家本意及作品背景的阐释是经不住推敲的。其实,麦氏也知晓,音乐艺术,特别是纯音乐的涵义往往没有唯一答案,女性主义的音乐解读也不应标签化。她曾说:“调性与奏鸣曲的典范之所以有效且强韧,部分原因来自它们的张力有多种解读”,奏鸣曲式中具有他者身份的第二主题、副调“不一定总被僵硬诠释为女性,它可以是身份的障碍或威胁,为了叙事关闭必须被清除或征服”。(40)也许,麦氏的某些极端言辞是一种刻意选择,她欲以明知故犯的论述策略唤起人们关注那久被忽略了的音乐中的性别隐喻。 三、殊途同归 上文重温了两本著作的主要观点,意在呈现其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然而,二者仍有四点不可忽视的共性。 其一,二者在主要运用某一研究方法时,均不约而同地结合了另一种方法,即在进行社会史描述时结合些许音乐阐释,或是在解读作品时关联历史材料。比如,希特伦专设一章对查米娜德《c小调钢琴奏鸣曲》(Op.21)第一乐章中的性别内涵做了分析。她认为,奏鸣曲式的第二主题一般被视为阴性主题,查米娜德却赋予该主题双重性格。起初,“它那‘安静’的呈现,抒情的特征,较柔和的力度(m)和较稀薄的织体似乎显露出女性特征。但是,持续的主调,其他声部进入后出现的有力的功能和声,及鲜明的赋格段又显露出男性特征。这种结构和性别特征上的模糊挑战着19世纪所理解的奏鸣曲式观念”(41)。希特伦为何要在自己偏于社会史风格的研究中带入阐释性因素?本文以为,这是其全书构思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全书各章的内容分别涉及了影响音乐创作、表演、接受过程的诸种性别因素,由此,在创作环节中,一位女性作曲家的反惯例意图似乎是不可忽视的,此意图在没有明确史料(如作曲家书信、创作笔记等)证明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作品阐释方式触及。而在麦氏的叙述中,经常会出现作品阐释与社会史描述自由切换的情况。如在对《卡门》的分析中,麦氏剖析了霍塞性格中的矛盾性——理性与感性、心智与肉体之冲突,随后话锋一转,便开始了社会史描述:“1870年代法国的许多领域爆发了这类无法解决的矛盾:帝国主义扩张的限度和反效果逐渐浮现,女性和劳工阶级都组织起来争取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这似乎在暗示个体矛盾与社会矛盾的联系。此后,话题回归,麦氏总结性地评价道:“《卡门》成功以最动人的方式戏剧化了上述每一种议题。”(42)这种自由切换在《阴性终止》中比比皆是,构成麦氏所说的“不正统的散文形式”,有时候多少让读者跟不上其思维节奏,但细细琢磨起来却回味无穷。 其二,二者皆相信音乐可表现社会历史信息。希特伦曾说:“音乐,如它的姊妹艺术一样,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语境。它以多种方式表现(express)着它产生于其中的文化的基本假设”,“各种重要的社会参数,如权力、阶级、性别皆铭刻于作品之中。”(43)麦氏则指出,老一辈音乐学者多关注音乐形态分析,甚少触碰音乐意义问题,此问题长期以来成为研究禁忌,如同蓝胡子公爵城堡中那扇不许被打开的第七扇门。而她偏要突破传统,自比蓝胡子公爵城堡中的朱迪斯,期待以女性主义批评作为打开禁忌之门的钥匙。为了让自己的研究获得扎实的理论基础,麦氏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处寻找理论资源:阿多诺把音乐视为“一种媒介,个人自由意志与社会循矩压力的中产阶级矛盾,在音乐中以越来越悲观的方式上演。他的解读剥去传统音乐学家珍惜的完全秩序与控制,不间断地专注于历史性的人类两难挣扎,而非着重于超越真理。在他笔下,德奥经典中被认定为非再现的器乐音乐,却成了整个文化最敏感的社会气压计……我若没研究过阿多诺,就不能进行本书呈现的任何工程”(44)。 其三,二者皆不遗余力地质疑男性话语霸权。前文对两本著作主要观点的概述已然说明了这一点,值得进一步提及的是希特伦对当前音乐史教学的批判。一方面,长期以来音乐史教材都采取了“伟大作曲家”、“伟大作品”的编纂模式。它不仅将某些作曲家、作品神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大作曲家多是男性。另一方面,音乐史教材的分期(如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等)多为男性视角下的产物。希特伦援引音乐史家琼·凯莉(Joan Kelly,1928-1982)的观点:文艺复兴虽被视为人文主义兴起的进步时期,对女性而言却未必如此,此时的女性多被限制在家庭中,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而希特伦本人则认为“古典主义”范畴也无法概括当时女性的音乐活动,“当时的女性积极创作利德歌曲。但把这种行为视为‘古典的’并硬以大约1820年作为一个人工切割的终点则有些不妥当,因为类似的创作行为至少继续了三十多年。”(45)当然,希特伦也看到上述现象有其客观原因,即历史上有关女性音乐家的记载、评论大大少于男性,她们多在私人空间活动,作品大多未被出版。如何才能在历史研究中增大她们的比重?希特伦认为,社会史研究将对此有助益。“社会史以特别群体的经验为研究起点。它关注各种阶层,而非仅仅是上流阶层,关注日常生活经验,而不仅仅是重大事件。对于女性而言,或许关注她们的生育经历,她们在家庭结构中的社会变动性,她们在经济结构中的参与性,她们的创造性活动,或是她们与宗教实践的关系……音乐史领域的女性研究将从这种方法中获益”(46)。为了实现这种研究,希特伦鼓励学者们从回忆录、日记、信件等中搜集材料,在散碎的历史信息中重构女性音乐家的生活及她们为反抗男性霸权所付出的艰辛。 其四,二者皆具有反主流、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意识。质疑主流观念,彰显被边缘化事物是后现代思想中一个侧面。主流意识形态往往被视为压迫者,非主流者则被鼓励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夺一席之地,甚至解构主流文化。希特伦和麦克拉蕊正是此种观念在音乐学领域的践行者。如麦氏不接受当时占据美国音乐学界主流地位的形式主义研究,积极探讨尚属禁忌课题的音乐意义问题;她致力于从女性视角理解传统经典作品,颠覆约定俗成的解读方式;她提倡加强对被边缘化的流行音乐的关注;她将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与作曲家的同性恋经历相联系等。希特伦则批判主流音乐史的编纂模式,提倡以女性音乐社会史研究为必要补充。以上观点皆在不知不觉中解构着音乐学研究的惯性思维。此外,二者还从后现代思想中获取了“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武器。反本质主义者否认永恒真理的存在,认为一切关于事物本质的叙述都是叙述者的主观构建,必然导致认识的片面性和知识霸权。在反思“是否存在女性独特的音乐风格”时,二人一致给出了否定答案。麦氏曾说:“尽管我们执迷于音乐风格的分类……去编纂何谓‘女性音乐’的独特风格,但是这种单一的东西并不存在,正如同没有普同的男性体验或本质一样。”(47)希特伦则说:“在音乐中,似乎没有本质主义所谓的女性风格……没有一种风格是由女性生物学固有特征所赋予的。我们难以相信每一位女性都以同一种风格创作……”(48)上述观点是合理的,正如我们不能简单接受社会关于男性和女性的刻板印象一样,也不应简单断言女性音乐风格有何固有不变的特征,真实情境中的每一位女性作曲家都是特殊的。法国哲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曾将女性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女权”、“女性”、“女人”三阶段。在女权阶段中,女性在政治、经济、职业等多领域追求与男性平等,具有精神解放的意义;在女性阶段,人们更强调性别差异,强调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体验,甚至导致“逆向性歧视”,即否定男性;在女人阶段,人们开始注重男、女性的互补与和谐关系。(49)上述转变实际是从激进转向平和,从抽象转向具体,从乌托邦转向现实的过程。在现实世界中,男女的先天差异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二者的社会分工,但每一位女性仍有选择的权力,并应当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如果她决定成为职业作曲家,那么,除了克服创作的艰辛,还不得不面对母亲与作曲家身份的矛盾。当然,她仍有可能二择其一,放弃成为母亲的权力。假若她选择了兼顾二者,便要付出超于常人的努力,也可能从中获得超于常人的收获,恰如希特伦提及的那位匿名创作者所言:作为一位母亲,我“必须持续地与外界发生关联,这似乎与每日创作的隔绝状态相悖。但是,积极地与外在生活近距离接触,增强了交流的渴望,更需要消除各种诱惑并变得更为直截了当。较少的工作时间意味着更清晰、更迅速的决断,更紧凑的工作和更有力的承诺,去除其他无意义的行为……抚育孩子与作曲颇为相像,奋斗、等待、观望、反应、寻找线索,以及许多精彩的时刻让这一切变得如此值得”。(50) 或许,女性主义音乐研究的归宿并不是仅仅重构历史或阐释作品中的性别内涵,而是在引发音乐世界中每一位男性和女性对两性权力关系的反思之后,启发他/她们找到适合于自我需要的、构建良性性别关系的行为方案。 ①“妇女研究”,又称为女性研究或妇女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从女性视角研究社会政治、媒体、历史等问题的学问。90年代以来,妇女研究逐渐发展为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着重探讨导致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机制。参见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②Stanley Sadie(editor).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ans.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2001.“Feminism”条目。也可参见宋方方《美国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学术历程》,《黄钟》2013年第1期。 ③佟新《社会性别研究导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④同注③,第26页。 ⑤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⑥苏珊·麦克拉蕊,现为美国凯斯西储大学音乐学教授,因其女性主义音乐学研究而闻名。著有《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Feminine Endings:Music,Gender,and Sexuality.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乔治·比才:卡门》(Georges Bizet:Carm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等专著。 ⑦玛西亚·希特伦,美国莱斯大学音乐学系教授、系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浪漫主义时期音乐、音乐与社会性别、勃拉姆斯等。著有《社会性别与音乐经典》(Gender and the Musical Canon.First Illinois paperback,2000),《当歌剧遇到电影》(When Opera Meets Fil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等多部著作。 ⑧露丝·索莉,美国史密斯学院音乐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19世纪音乐、音乐与社会性别等。编有论文集《音乐学与差异——音乐研究中的社会性别和性》(Musicology and Difference:Gender and Sexuality in Music Scholarship.The Regents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3)。 ⑨苏珊娜·库西克,美国纽约大学音乐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性别与音乐文化、音乐中的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音乐文化史等。代表作为《梅迪契宫廷中的弗兰切斯卡·卡契妮,音乐与权力的播散》(Francesca Caccini at the Medici Court,Music and the Circulation of Pow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 ⑩批判音乐学是20世纪70年代发端于英美音乐学术界的一股潮流,研究者以文化批评理论为基础探寻音乐作品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对英美实证主义音乐学的反拨。代表人物有苏珊·麦克拉蕊、劳伦斯·克拉默(Lawrence Kramer)、罗斯·R.萨博特尼克(Rose Rosengard Subotnik)等。 (11)Stanley Sadie(editor).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ans.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2001.“Feminism”条目。 (12)Citron,Marcia J.Gender and the Musical Canon.First Illinois Paperback,2000. (13)苏珊·麦克拉蕊著、张馨涛译《阴性终止——音乐学的女性主义批评》,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年版。 (14)Lydia Goehr.“Review,Gender and the Musical Canon by Marcia J.Citron".Music & Letters,Vol.75,No.4(Nov.,1994),p.616-618. (15)以下文献均或多或少地涉及麦克拉蕊著作的介绍与评述,并为本文所参考: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音乐艺术》2003年第3期;朱宏波《性别与才华——西方女性音乐家“失语”的历史考察》,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姚亚平《什么是音乐学分析:一种研究方法的探求》,《黄钟》2007年第4期;贾抒冰《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新音乐学”发展综论》,《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姚亚平《关于“分析”的若干话题分析》,《音乐研究》2010年第4期;宋方方《对美国20世纪末西方音乐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的审视》,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宋方方《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音乐分析范畴》,《交响》2011年第4期;孙露《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双重超越——对麦克莱瑞〈乔治·比才——卡门〉一书的解读》,《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姚亚平《错觉图——游走于形式与形式之外的凝思游戏》,《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宋方方《女性主义音乐批评的贡献与局限》,《人民音乐》2012年第8期;纪露《对“女权主义音乐批评”方法的解读和反思》,《人民音乐》2012年第11期;钟芳《阴性的声音与力量——试析中西文化语境中“社会性别”的音乐学表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王晶《文本分析与酷读——柴科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中“同性恋情结”的隐秘叙事》,《音乐探索》2014年第2期。 (16)Claire Detels.“Review.Feminine Endings:Music,Gender,and Sexuality by Susan McClary”.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50,No.4(Autumn,1992),p.338-340. (17)同注(12),第6页。 (18)同注(12),第20页。 (19)同注(12),第48页。 (20)同注(12),第50、51、53页。 (21)同注(12),第85页。 (22)威尔海姆·汉塞尔(Wilhelm Hensel,1794-1861),德国画家,范妮的丈夫。 (23)同注(12),第55页。 (24)同注(12),第110页。 (25)同注(12),第92页。 (26)同注(12),第181页。 (27)同注(12),第182页。 (28)同注(12),第186—187页。 (29)同注(12),第98页。 (30)同注(13),第118页。 (31)同注(13),第120页。 (32)同注(13),第164页。 (33)同注(13),第166页。 (34)同注(13),第207—209页。 (35)同注(13),第214、215、221页。 (36)McClary,Susan.“Getting Down Off the Beanstalk” Minnesota Composers Forum Newsletter(January 1987). (37)英文原文为:Beethoven's symphonies add two other dimensions to the history of style:assaultive pelvic pounding(for instance,in the last movement of the Fifth Symphony and in all but the “passive” third movement of the Ninth)and sexual violence.The point of recapitulation in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Ninth is one of the most horrifying moments in music,as the carefully prepared cadence is frustrated,damming up energy which finally explodes in the throttling,murderous rage of a rapist incapable of attaining release.转引自Toorn,Pieter van den.Music,Politics,and the Academ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9. (38)Richard Taruskin.“Material Gains:Assessing Susan McClary”.Music & Letters,Vol.90,No.3(Aug.,2009),p.453-467. (39)Toorn,Pieter van den.Music,Politics,and the Academ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29. (40)同注(13),第52页。 (41)同注(12),第152页。 (42)同注(13),第129页。 (43)同注(12),第120—121页。 (44)同注(12),第67页。 (45)同注(12),第213页。 (46)同注(12),第208页。 (47)同注(13),第221页。 (48)同注(12),第159页。 (49)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386页。 (50)同注(12),第90页。标签:音乐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音乐学专业论文; 社会性别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卡门论文; 第九交响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