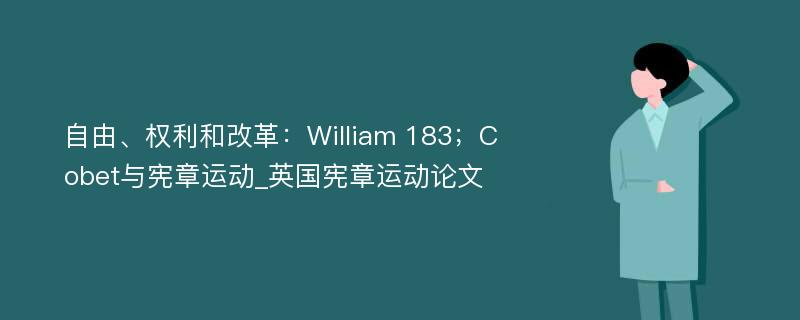
自由、权利和改革:威廉#183;科贝特与宪章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宪章论文,威廉论文,贝特论文,权利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运动是英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19世纪英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激进运动,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动员,波澜壮阔,持续十几年之久。这场的运动之所以被当时和后世的人称为宪章运动(The Chartism Movement)、运动的参加者之所以被称为宪章派(The Chartists)是因为他们以实现《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为奋斗目标,并以此为目标三次向议会请愿,要求批准《人民宪章》。《人民宪章》浓缩的六点原则是:(1)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2)每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3)实行平均的选区,每个选区选民数应该相等;(4)议员领取薪水;(5)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6)实现无记名投票,其中成年男子普选权是最核心的一条。六点原则是宪章运动的纲领,它体现出普通民众希望通过议会改革和普选权改变贵族和中产阶级垄断政治权力、控制议会并对人民大众实施压迫的状况。在“饥饿的四十年代”,贫苦大众始终寄希望通过向议会请愿实现《人民宪章》的政治解决方式来实现变革,解除苦难。但是,为什么当时民众运动会诉诸这样一种政治的解决方式?为什么他们提出的方案是以《人民宪章》的六点原则为核心的议会改革计划?英国学者加雷斯·斯坦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认为,宪章运动的思想主张起源于英格兰传统的、对腐败政治体制进行批判的激进主义,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早期的议会改革运动对宪章运动有深刻的影响,宪章派领袖继承了传统的激进主义主张,并将其运用于新的工业危机的环境之下。琼斯的观点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从社会主义运动或者民主运动的视角审视宪章运动,但是对英国传统激进政治文化和议会改革运动对宪章运动的影响却缺乏足够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一个微观视角出发,考察19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激进派威廉·科贝特的激进主义遗产在宪章运动中的传播,分析其激进主张和策略通过何种媒介传递给宪章派,这种激进主义如何对宪章运动产生影响,继而引导运动的发展方向,期望能抛砖引玉。
科贝特与宪章派
1835年6月20日,一位激进派议员逝世,这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关注,包括《泰晤士报》和《晨报》在内的三十多家报纸刊登了讣告或长篇纪念文章,在首都伦敦和其他一些激进派活跃的地区举行了大规模民众纪念集会,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给予他很高的赞誉:《泰晤士报》说:“无论如何,这个自学成才的农民在很多方面都比与他同时代的人更加杰出”①;《晨报》称他是“是英格兰造就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感觉敏锐观察准确,并且一直成功地在对他的读者施加影响”②;当时主要的激进派报纸更是赋予他各种美誉诸如“贫民的卫护者”③、“媒体之王,诚实和热诚的爱国者,劳工阶级勇敢而可靠的朋友,坚定而明智的政治家”④等;他的支持者甚至在热议应由公众捐资为他建造一座纪念碑。这位备受瞩目的人物就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激进派、民众激进运动的杰出宣传家威廉·科贝特。
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生于英格兰南部乡村。他本是一个保守派,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写作大量政治小册子为英国的立宪君主制辩护,因此受到当局的青睐,在陆军大臣温特姆的资助下创办《政治纪事》报。在19世纪初期,随着形势的变化科贝特转变成激进派,并成为议会改革运动的杰出宣传家。科贝特激进主义的核心是英国古老的权利观,也深受18世纪英国宪政主义激进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曾经是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所组成的议会下院曾是人民自由—主要是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忠实维护者;但是,到了科贝特生活的时代,传统的贵族大人物日渐堕落腐败,他们勾结金融投机家把持议会,将沉重的赋税和国债负担加诸于人民,总之议会被腐蚀了,议员被腐败的利益集团收买了,现存的议会下院已经不再能维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了,必须进行议会改革,将“真正”的人民代表送入议会,才能革除弊端,恢复美好的时代。科贝特不仅提出议会改革的主张,他还是19世纪上半叶议会改革运动最有影响的宣传鼓动家。在拿破仑战争后的紧张时期,科贝特提出动员普通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投入议会改革运动。在《告劳工大众书》中,他宣称劳工也被纳税(通过缴纳消费税的方式)因此有权参与政治事务,获得选举权,并且一些国民财富都源自于劳动。⑤在教育民众、启迪工人阶级政治觉悟方面,科贝特做出极大贡献。1816年他率先将《政治纪事报》降价,并出版售价仅2便士的《两便士报纸》(The Twopenny Trash),成功地逃避了政府的印花税压制,在劳工中广泛流传。科贝特的宣传活动极大地推动了1832年议会改革的实现,1833年科贝特当选为新议会的议员,与中产阶级工厂主约翰·菲尔丁一起代表新兴工业城镇奥德姆,并在那里两次当选。
科贝特的逝世在激进派中引起很大反响,他们纷纷撰文或举行集会,缅怀这位激进派先驱和用笔为勤劳阶级(the industrious class)的权利声辩、启迪民众觉悟的平民政治家。科贝特创办的报纸和小册子受到普遍的赞扬,这些宣传品传播了政治知识和权利观念,成功地教育了广大普通民众。科贝特的一些文章被认为是对启迪工人阶级的觉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关于税收、国债和腐败问题的论著,如《两便士报纸》⑥、《英语语法》、《穷人之友》、《新教改革史》、和《遗赠劳工》等。《布莱顿信使报》(The Brighton Herald)说“科贝特的一生都致力于与腐败的统治者做斗争,反对国家和教会的权力被滥用。他的《新教改革史》一书在英格兰造成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英语语法》也是被广泛阅读的书籍,有作家曾说那是科贝特先生教给人民他们自己的语言的一部书。”⑦曾受科贝特赞扬的激进派报纸《布莱顿爱国者和利维斯自由报》(Brighton Patriot and Lewes Free Press etc⑧)报道了一场在伦敦举办的纪念集会。会上倡议,由于科贝特生前一直致力于教育民众和改善劳工的生活状况,应该由公众捐资建造一座纪念碑以纪念这位伟大人物。⑨两个月后,这份报纸又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号召所有自由的、尚未被奴役的人们为修建科贝特纪念碑捐款。作者强调,科贝特的功绩在于他启迪民众意识到赋税致贫的现实和自己作为劳动者的正当权利:教会财产和十一税原本是人民不可剥夺的财产,但是后来被无耻地抢夺走;他还告诉人们赋税被从劳工的工资中拿走,国债同时增长,契约商人、投机家和犹太人从中获益致富,而劳工阶级变得贫穷和无家可归。因此,“让所有的人对这位‘穷人之父’致以敬意吧。让全世界知道英国人是如何懂得尊敬如科贝特那样维护他们权利的人;让每个人都来为修建科贝特纪念碑捐款吧”。⑩
菲尔丁与阿特伍德在议会递交宪章派的请愿时,激进议员托马斯·唐康比评论说:“那些最初被叫做激进派、随后被称为改革者的人,就是如今的宪章派”(11)。由于科贝特的激进主义对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派有极大的影响,当他们转变为宪章派之后,科贝特的遗产就传递给了宪章运动。导致宪章运动出现的直接原因是1832年后议会的压迫性立法,是贵族和中产阶级联合控制下的议会对普通民众实施的暴政。新议会控制言论和出版自由,除了继续维持《谷物法》之外,还在1834年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新的《济贫法》取消了院外救济的方式,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进入济贫院被统一管理,严酷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贫民仅存的受救济的权利,使其生活陷入绝对的困境。这些立法(尤其是新《济贫法》)侵犯了英格兰人一直珍视的自由和权利,由于制定立法的是议会下院,民众改变现状的斗争就理所当然地集中到进一步议会改革的问题上来,以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和议会改革为目标的民众激进政治运动—宪章运动由此出现。1837年“伦敦工人协会”(12)领导人洛维特在普雷斯的帮助下起草了《人民宪章》,并于1838年5月将文件公布于众,这标志着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兴起。
科贝特俱乐部与宪章运动
科贝特是宪章运动的先驱,尽管他曾对1832年议会改革寄予很大希望,认为改革将终止劣政,使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但是1832年后的议会令他失望。在1833至1835年间,科贝特在议会内发言多次,大多数关于税收、国债和《济贫法》问题。他特别激烈地反对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科贝特抗议说“依据英格兰传统法律,穷人有受救济的正当权利”,他警告议会穷人这项权利是从中世纪传下来的,一旦被议会法令剥夺,会迫使他们采用更激进的手段夺回法律和习惯曾经赋予他们的权利(13)。随着对议会失望情绪的加剧,从1834年开始科贝特重新联络院外激进运动,支持他们要求普选权的清愿。科贝特于1835年6月去世,他个人的奋斗终止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组成了科贝特俱乐部(The Cobbett Club),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了科贝特的激进主义。
科贝特俱乐部主要是一个中产阶级改革者的小团体,成员包括一些议会内激进派议员和院外科贝特的崇拜者,核心人物是科贝特在奥德姆选区的伙伴、中产阶级改革者约翰·菲尔丁。在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时期(1838年至1840年),由于菲尔丁在运动当中的巨大声望和影响力(14),科贝特俱乐部与宪章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使科贝特的遗产传递给宪章派领袖,对运动的路线产生一定影响。
约翰·菲尔丁生于兰开郡,父亲曾是一个布商和租地农场主,在工业革命当中靠勤劳发家致富,菲尔丁从小跟随父亲经营,一手发展起来“菲尔丁兄弟公司”。与大多数在工业革命中致富的第一代企业家一样,菲尔丁之父并不关心政治,但是他的儿子生长在法国革命和英国激进运动兴起的年代,受激进政治宣传的影响,很快像其父抱怨的那样转变成“一个十足的雅各宾派,就像在国内其他地方的那些一模一样”(15)。菲尔丁深受科贝特的影响,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经济萧条的时期,菲尔丁兄弟被迫降低雇工的工资,正是在这个时期科贝特的《告劳工大众书》出现了,它直接而清晰的指出当时问题的所在是劣政,变革的方法是议会改革。菲尔丁由此深受启发,从此开始订阅《政治纪事报》,随即菲尔丁兄弟决心要支持任何改革,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其他(16)。菲尔丁的激进主张与科贝特基本相同,他也反抗税收和国债对人民的压迫,反对谷物法和新济贫法等压迫性立法,要求议会改革和扩大人民代表权。1836年,在菲尔丁的主持下,激进派动员起来为科贝特建造纪念碑,尽管这项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募捐总数甚至没有达到100镑(其中包括菲尔丁的40镑和奥康内尔的10镑)(17),但是这一活动将科贝特的信徒们聚集在菲尔丁的周围。1837年3月,菲尔丁在伦敦举办集会纪念科贝特的生日,有153人参加了这一机会,宪章派的主要报纸之一、代表伦敦工人协会的《伦敦新闻和人民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者报》(The London Dispatch and People's Political and Social Reformer)报道了这个消息。1838年3月,同样性质的晚宴再次举行,而这一次集会者自称“科贝特俱乐部”。
怀着同样的不满情绪,科贝特、菲尔丁与宪章运动的发展结合了起来。在有生之年,科贝特与民众激进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他的报纸、小册子和演讲在劳工读者中流传很广,启迪了一代工人阶级激进派。死后他的遗产仍然对宪章运动产生影响,部分地通过科贝特俱乐部这个媒介发生作用。
在1838至1840年间科贝特俱乐部受到宪章派的欢迎和支持。科贝特俱乐部定期举办集会,在伦敦和其他激进派活跃的地区都有,最多时有几百人出席,当中包括众多宪章派的重要人物。《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和《宪章报》(The Charter)等宪章派的主要报纸都详细报道科贝特俱乐部的集会情况,从这些记录来看,科贝特俱乐部至少存在4年(1838-1842),它对一些宪章派领袖的观点有很大的影响。以1839年在伦敦举办的纪念科贝特生日的晚宴为例,这次晚会有150多人出席,宪章运动的领导层全国宪章代表大会(The National Convention)成员和著名宪章派活动家如奥布莱恩、约翰·克里伍、泰勒医生、韦德医生和曼彻斯特的理查森等都出席了会议,菲尔丁是纪念会主席并发表了长篇演说。菲尔丁首先赞扬了科贝特的品格和崇高原则,称科贝特一生始终都在关注英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劳动人民,并用他的笔维护他们的权利(18),因此,当前各个阶层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就将科贝特与激进派再次联系起来,并迫使他们继续从科贝特那里寻求支持。菲尔丁详细叙述了农业和工业的劳动人民的处境,抨击改革了的议会的劣政:首先是《谷物法》,它使得农业劳工和他们的家庭靠微薄的收入生活;其次是新《济贫法》,它将没有犯任何罪行仅仅是生活贫穷的人驱赶到济贫院,备受折磨而死。在这样制度下,农业劳工和手织工沦落到仅靠土豆和盐维持生活。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苦难?是税收的压迫,是游手好闲、奢侈浪费的土地贵族和金融投机家们控制议会,掌握制定法律和收税的权力,他们为了一己私利而将沉重的税收负担加诸勤劳阶级。那么应该如何解除苦难、回归幸福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菲尔丁既重复了科贝特的旧主张,如恢复《伊丽莎白济贫法》,恢复稳定货币和取消国债等,在新的形势下他也提出了新的计划,菲尔丁明确宣称,由于改革了的议会用《谷物法》、新《济贫法》等继续压迫人民,必须继续激进政治改革,实现普选权、年度议会和秘密投票。菲尔丁对时局的分析和诊断受到出席会议的宪章运动领袖们的一致欢呼喝彩。奥布莱恩说:“为劳工的权利干杯!如果这项权利得不到尊重,财产的权利不应该也不能够存在”(19),他称自己从未说过有财产的人应该失去产业,但是任何一个有产者都不应该用抢夺他人的方式使自己致富。(20)曼彻斯特的理查森说:“为不可动摇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或者恢复教会财产的本来用途干杯”(21),他宣称自己的观点是受到科贝特《新教改革史》一书的启发。
菲尔丁的演说和俱乐部集会吸引了很多宪章派,宪章派也利用自己的报纸宣传科贝特俱乐部。1838年,俱乐部向议会呈递请愿,要求实施普选权、年度议会、无记名投票、议员选举无财产资格限制和议员支薪,这些内容与《人民宪章》的六点原则是完全相同的,得到宪章派报纸的大力宣传。1839年,俱乐部又出版一份小册子《政治宣传册》,重申并详细阐述了这些主张。包括《北极星报》在内的大多数宪章派报纸都刊载了科贝特俱乐部的请愿活动(22)和出版物。宪章运动的杰出宣传家、出版商克里伍在他的报纸《克里伍的一便士报纸》(Cleave’s Penny Gazette of Variety)上评论道:“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这个小册子,在其中可以找到当今影响国内社会的所有主要的政治议题。我们可以确信,除非那些深刻理解科贝特先生作品的人,都不能提出这样明确而有洞察力的观点主张。我们相信不久将会看到这一杰出出版物的第2辑;我们建议所有真正希望理解影响当前公众问题的人都去阅读它”(23)。
但是,科贝特俱乐部与宪章派之间的亲密合作关系并没能持续很久,从1840年开始,俱乐部与宪章派的联系淡化,主要原因是双方在实现《人民宪章》和激进改革的方式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菲尔丁不仅认同科贝特关于赋税压迫和人民代表权的主张,而且坚持科贝特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由始至终都反对暴力”(24)。菲尔丁坚持人民必须使用科贝特曾建议的斗争方式—请愿,如果请愿被议会拒绝,人民应该再次提交请愿,并尽量用“得体的语言”(25)书写请愿书。菲尔丁也劝说全国宪章代表大会委员们保持镇定,坚持请愿的方式,但是他的听众尤其是那些饱受失业折磨,被新《济贫法》剥夺仅存的受救济权利的劳工,却无法像菲尔丁期待的那样冷静,他们要求尽快实现人民宪章,即使使用某种“最后措施”也罢。在1840年的纪念集会上,克里伍批评菲尔丁的要求“对工人阶级来说太过苛刻”(26),称纪念集会不能仅仅是吃吃喝喝和喊口号,应该利用他们所能利用的所有途径实现科贝特的伟大原则。他赞同菲尔丁的请愿的建议,但是认为议会根本不理人民的抱怨,无视人民的请愿,而他“准备去摧毁那些懦弱而腐败的立法者”。(27)从宪章运动的发展历程来看,运动的总体态势由始至终是和平的,从未出现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即使在形势最危险的1848年的第三次请愿时期也是如此。但在当时“最后措施”的威胁已经足以使温和的中产阶级改革派产生恐惧心理并与运动分道扬镳了。据甘米奇的《宪章运动史》记载,在1839年全国宪章代表大会的集会上,科贝特派主张集会只应当是一次请愿大会,全民请愿书呈递之后,他们的使命就该结束了。这一观点遭到与会大多数代表的反对,他们一致认为,人民群众期望得到更多的收获,倘若请愿书被拒绝,必须要采取某些最后措施。(28)甘米奇认为,在这次失败之后“科贝特派在全国宪章代表大会上就不能扮演任何重要角色了”(29)。随后科贝特派全部退出全国委员会,其中包括科贝特之子詹姆斯·保罗·科贝特(30)。后来菲尔丁也疏远了宪章运动,将他的精力转移到议会内的工厂改革法案,对院外激进运动失去了兴趣。结果,在1840年后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时期,科贝特俱乐部与宪章运动的联系很微弱,俱乐部不再能对宪章运动的方针施加影响。在1841和1842年间,宪章派的报纸停止报道科贝特俱乐部的纪念活动。材料显示,科贝特俱乐部至少存在到1842年,但是当年的纪念晚会只有50个人出席,会上爱尔兰的奥康内尔提议:“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联合是实现正义事业的唯一方式”(31)。
科贝特图书馆和宪章派
科贝特俱乐部与宪章运动的分道扬镳并不意味着科贝特对运动的影响就消失了。反之,科贝特的遗产通过另一种方式传递给宪章运动,即他的作品的传播。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科贝特的作品多次再版并在宪章运动中广泛流传,宪章派因阅读科贝特的著作而对他的激进主张和策略产生认同,由此对运动产生一种间接的影响。
科贝特被称为是普通民众的伟大教育家。他的一大贡献是首创了《两便士报纸》等廉价出版物,它们成功地向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传播了政治知识。在英国传统的等级制社会,居于社会上层的体面阶级牢牢掌控着教育体系,从而掌握知识、操纵舆论和控制社会。绝大多数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世代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更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政治觉悟。到18世纪中期,距离印刷术在欧洲出现已有300多年时间,仍有约一半的英格兰人不会写字。(32)但是,19世纪的激进运动首次动员起普通民众,向他们灌输政治知识并努力创造一种激进运动的“公共空间”(33)。在这方面科贝特是一个先行者。从1816年开始,科贝特转向直接针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宣传,他的《告劳工大众书》和《两便士报纸》销售量都达每周4万至5万份之多,比当时公开发行的任何一份报纸都要高,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激进运动当中只有潘恩的《人权》曾经创造过如此的高销量。科贝特的宣传不仅动员了劳工大众,还引导他们走上争取议会改革的道路。激进派班德福曾这样回忆道:1815年战争结束时,全国有许多动乱、人民的不满达到极点,国内的形式如布满干柴——
这时,科贝特的文章突然权威起来了……在所有这些工业区,以及许许多多苏格兰的工业城镇中,几乎每一座村舍炉边都在读这些文章。文章的影响很快就看出来了,科贝特给读者指出受苦的真实原因—劣政;指出适当的纠正方法—议会改革,骚乱很快就很少见了。(34)
在动员民众力量的同时,科贝特又不希望民众运动向过分激进的方向发展,他时时警惕出现暴力的苗头。在激进运动高涨的1817年,科贝特在《政治纪事报》上呼吁道:“(人民)因为改革问题已经被鼓动起来并情绪十分高涨,因此,我特别反对任何的联合会、协会、附属组织和通讯会等社团的出现”(35),因为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时常会出现群众情绪异常激动,导致发生暴力行为。终其一生,科贝特都主张通过合法的方式实现变革,反对任何暴力极端的手段,教育是他认同的实现社会变革的最佳方式。为此目的,科贝特不仅坚持《政治纪事报》的运作,写作大量政治小册子,还在1828年别出心裁地在《政治纪事报》上创办了一个《科贝特图书馆》(Cobbett Library)的专栏。科贝特说:“当人们问我年轻人该读些什么书的时候,我总是回答,‘请他们读所有我写的书吧’。我把这些书叫做我的图书馆”(36),“这些书证明我比任何一个大臣或者议员都更懂得国家的利益所在。整个国家都认可这些,并且除了那些靠税收生活和甘为政府奴隶的人之外,每个人都公开承认这一点”(37)。从内容来看,科贝特图书馆推荐的30几本书主要是教育和政治类的,包括科贝特影响最大的著作《英语语法》(38)和另外一些著名的政治宣传小册子如《穷人之友》、《纸币对金币》和《新教改革史》等。《科贝特图书馆》的形式和内容充分体现出科贝特注重教育、希望通过宣传普及政治知识来实现变革的愿望。在科贝特死后,他的子女继承了父亲的宣传事业。科贝特的两个儿子创办的报纸《战士和每周信使报》(The Champion and Weekly Herald)将《科贝特图书馆》栏目放在醒目的位置。1836年,他们将其父在《政治纪事报》和《豪猪作品集》上的政论文编辑成一部六卷本的集子,名为《科贝特政治作品选集》出版。此外,科贝特的女儿们成立一家出版公司,专门再版其父的作品,在她们的努力下,《英语语法》在1833、1835、1837、1838、1840、1842和1847年共7次再版;另一本广受欢迎的小册子《新教改革史》在1834、1840和1844年再版3次,其他政治、经济作品如《纸币对金币》、《13项讲道》、《该死的十一税》和《茅舍经济学》等也都被再版多次,这保证了科贝特的遗产能够继续对激进运动发生影响。
《科贝特图书馆》不仅向激进运动宣传了科贝特的著作,这种方式也启发了宪章派。宪章派报纸《北方自由者和战士报》(The Northern Liberator and Champion)一度将《科贝特图书馆》专栏移植到自己报纸上(39),运动最重要的报纸《北极星报》和《宪章报》都有《人民图书馆》(People’s Library)和《劳工图书馆》(Lahourer’s Library)专栏。1841年5月1日,《北极星报》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即发布《劳工图书馆》专栏。该栏目将由“爱国的作者们关于政府、普选权、移民、人口和政治经济的杰作组成”(40),列在第一位的一本就是科贝特的小册子《〈人民宪章〉选举权规定的穷人的权利:正义的普选权原则》,它是由宪章派将科贝特在《两便士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和他的《告劳工大众书》编纂一起而成,其中明确提出劳工的正当权利源自于他们劳动的原则。除科贝特的作品之外,“劳工图书馆”还包括奥康诺影响巨大的小册子《论土地问题》等,所有这些书都售价仅1到2便士,便于工人阶级读者阅读。不仅如此,宪章派将“劳工图书馆”看作是实现他们事业的重要途径:“宪章派们!无论何时,当你听到一个无知的蠢家伙或者一个掮客说你没有实现《人民宪章》的权利,你就把上述这些书中的观点当作你自己的观点告诉他们,你就可以永远地闭上他的嘴巴!”
另外一本在宪章派中影响巨大的科贝特的著作是《遗赠劳工》。1834年当改革了的议会通过《济贫法修正案》时,愤怒的科贝特决心给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写一部书,告诉他们自己的权利,指引他们反抗不正义的法案,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改革。他最终写成三本小册子:《遗赠教士》、《遗赠贵族》和《遗赠劳工》。这些小册子在1834年出版后还多次再版,其中《遗赠劳工》尤为重要,它在宪章运动中流传很广。在《遗赠劳工》一书中,科贝特称新济贫法是改革了的议会造出的可怕的新花样,侵犯了英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得到《伊丽莎白济贫法》确认的穷人受救济的正当权利,他要“努力阻止这种对权利的侵犯,使国家恢复到像我出生时的那种状态;努力阻止那些可怕的新花样”(41)。小册子包括给劳工的六封信,通过几个问题如“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什么有些人享有的占有土地上出产的权利比其他人要大?英格兰的贵族地主们对他们的土地有哪些权利?他们是如何拥有这些权利的?贵族地主对土地的权利是绝对的吗?贵族地主有权主宰他们的土地吗?或者说他们是否只享有依法支配的权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吗?”,告知劳工他们依据自然法则、上帝的法和文明社会的法律而拥有的享受自己辛勤劳动成果的正当权利,因此极大地鼓舞了劳动者反抗新《济贫法》、争取正当权利的斗争。《遗赠劳工》的售价仅1先令4便士,便于工人阶级读者得到,在宪章运动高涨的时期,它几乎成为宪章派的手册,和《北极星报》一起成为宪章派集会上必读的读物(42)。
科贝特的策略对宪章派中的“道义派”影响尤其大。道义派的领袖是洛维特(1800-1877),他原本是一个工匠,19世纪二十年既投身于激进运动,最初他的观点颇为激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洛维特身上的激进色彩淡化,他抛弃了欧文主义,开始相信教育才是促成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1836年6月,洛维特在伦敦创立伦敦工人协会,这个组织每月收取会费1先令,并限定只有“勤劳阶级中有良好道德的人”(43)才能加入。不仅如此,洛维特还创立了全国促进人民政治和社会进步协会,这个组织拥有一批会堂、学校和图书馆,把读书读报、讨论和接受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并相信这是促成政治和社会进步的可靠方式,参与其中的宪章派被称为是运动中的“道义派”。在道义派的报纸《宪章报》、《伦敦新闻和人民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者报》和《布莱顿爱国者报》上,书摘和读书评论都是这些报纸的主要内容,而科贝特的书是他们的最爱之一。道义派宪章主义者、无印花税出版事业的英雄克里伍(44)的报纸《克里伍的一便士杂文报》特别大量刊载科贝特的文章和书籍信息,节选了科贝特对劳工教育的诸多著作如《十三项讲道》、《英语语法》极其抨击十一税的文章(45)。
从宪章派报纸关注的科贝特作品的内容来看,绝大部分是关于税收、国债和人民代表权问题,以及一些批判谷物法、新济贫法、十一税的作品,从选题充分体现出宪章派认同赋税致贫的状况和议会改革的解救道路。例如,《宪章报》引用科贝特给制造业者的信,其中明确指出“税收和十一税是谷物法出现的原因。上层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家属都在从税收中渔利,通过官职、年金、奖赏和在陆军、海军和驻外使节任职等方式;至于十一税和其他教会开支,几乎是全部和直接地被上层地主支配或者受他们利益的影响;此外还有国债的压迫,有些贵族地主也是国债持有人,但大多数国债被30万个家族掌握着……必须要采取措施解除税收的重负,取消闲差、年金等以减少公共开支,削减海军和陆军开支,减少十一税和其他教会开支,解除国债和王室占有的土地。只要改革了的议会下院能采纳措施,苦难将会被解救,也不会伤害教会和宗教,贵族的特权和王室的特权、所有人的权利将得到保护并子子孙孙的传递下去。”(46)另一宪章派报纸《老伙伴》(The Odd Fellow)引用科贝特1815年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请愿,并评论说“我们恳请读者们注意,科贝特先生的请愿并不仅仅是废除《谷物法》,他还坚持应削减税收、和平时期的陆军和海军,以使公共开支降低到六百万英镑一年(不包括国债!),他也坚持要求改革议会的下院,这些是科贝特的真实愿望。”(47)此外,克里伍曾写作一篇文章题为“晚年的科贝特议员在原则上是一个宪章派吗?”,通过引用科贝特在1833年支持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言论,他给了这个问题肯定的答案(48)。
综上所述,威廉·科贝特的激进主张和策略对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宪章派和宪章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科贝特生前与民众激进运动关系密切,他的观点启迪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派。在去世后,他的激进主义遗产通过科贝特俱乐部和生前著作这两个媒介传递给宪章派,在宪章运动中被广泛传播和吸收,对运动的奋斗目标和路线产生重要影响。
宪章运动的主体是手工工人而不是工厂工人,这些人大多是前工业社会或者工业革命早期的工匠、店主及其他独立生产者,他们曾经有独立的地位,但遭受到税收、《谷物法》和新《济贫法》的压迫以及金融投机家的盘剥,逐渐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掀起激进运动反抗社会。他们普遍认同自己属于勤劳阶级,赞同科贝特对劣政的批评,认同他的分析:是那些土地贵族、特权者和投机家们操控议会,将沉重的税收加诸于勤劳阶级,导致了民众的贫困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于税收是由议会决定的,那么争取普选权、改革议会和实现真正的人民代表权就成了宪章派一直坚持的解救苦难的方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宪章运动这场19世纪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始终坚持政治斗争的路线,以争取普选权和议会改革为主要目标。但是在19世纪中期,辉格党政府采用严厉手段镇压宪章运动,政府逮捕、关押和流放运动的领袖,秘密破坏运动,并操纵公众舆论进行反宣传,这些沉重打击了宪章运动;此外,1832年后一批倡导改革的中产阶级激进派议员如菲尔丁、阿特伍德等进入议会,尽管人数较少但他们在议会内为积极为民众的权利声辩,并得到部分主张变革的托利党人的支持,促成工厂法等一系列改革法案的实现,因此逐渐获得群众的支持。在双重的压力下,宪章运动的群众基础逐渐流失,加上它不肯与中产阶级和工会运动合作,不能凝聚成足够的力量实现《人民宪章》,导致1848年后宪章运动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注释:
①Anonymity:“William Cobbett”,Times,Jun 20,1835.
②Anonymity:“Funeral of the Late Mr.Cobbett”,The Morning Chronicle,June 29,1835.
③Anonymity:“Posthumous Notice of Mr.Cobbett”,The Poor Man's Guardian,July 11,1835.
④Anonymity:“William Cobbett”,Brighton Patriot and Lewes Free Press etc,July 7,1835.
⑤(35)J.M.Cobbett and J.P.Cobbett(ed),Selections from Cobbett's Political Works,London:published by Anne Cobbett,vol.5,pp.1-17,p.155.
⑥Anonymity:“Death,Character,and Memoir of the Late William Cobbett”,The Poor Man's Guardian,June 27,1835.
⑦Anonymity:“The Late William Cobbett”,The Bristol Mercury, June 27,1835.
⑧科贝特曾在《政治纪事》报上写道:“不列颠爱国者报是我想向所有读者强烈推荐的一份读物”,该报参与了宪章运动,是道义派的支持者。
⑨Anonymity:“Cobbett Monument”,Brighton Patriot and Lewes Free Press etc,August 9,1836.
⑩Anonymity:“Cobbett Monument”,Brighton Patriot and Lewes Free Press etc,October 25,1836.
(11)1834年5月3日议会辩论(The National Petition-The Charter),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42/may/03/the-national-petition-the-charter,(Hansard 1803-2005,2012-5-8)。
(12)工人阶级要求议会改革的组织,成立于1836年。
(13)1834年6月16日议会辩论(Poor-laws'Amendment-committee),http://hansard.millbanksystems.com/commons/1834/jun/16/poor-laws-amendment-committee#S3V0024P0-18340616_HOC_15,(Hansard 1803-2005,2012-5-8)
(14)菲尔丁是一个富裕的工厂主,谷物法等对他的实际利益的影响并不很大,新的济贫法还能给他带来好处(可以压低雇工的工资,使工厂利润增加)。但是,出于对自由、权利原则的信仰和家长主义保护弱者的心态,菲尔丁毅然投身于民众激进运动,支持激进派普选权和议会改革的要求,这使他在宪章运动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15)S.A.Weaver,John Fielden and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radicalism,1832-1847,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3,p.38
(16)(25)Anonymity:“Oldham”,The Northern Star,March 14 1840.
(17)MSS.Cobbett(Papers of William Cobbett in Nuffield College Library),XXI/12.
(18)Anonymity:“Cobbett Dinner”,The Charter,March 17,1839.
(19)(20)(21)(24)(30)詹姆斯·保罗·科贝特称他之所以退出全国委员会,是因为奥康纳的具有暴力色彩的言论。双方在各自报纸上互相攻击,见Champion and Weekly Herald,March 17,1839;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March 9,1839.
(22)1838年科贝特俱乐部的请愿被议会拒绝,以后俱乐部每年递交请愿,但都被议会拒之门外。激进派报纸都刊载了请愿和被拒的消息。
(23)Cleave’s Penny Gazette of Variety,July 06,1839.
(26)(27)(36)W.Cobbett:“Cobbett Library”,Political Register,August15.1835.
(28)[英]R.G.甘米奇:《宪章运动史》,苏公隽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6页。
(29)(37)W.Cobbett:“Cobbett Library”,Political Register,September,27,1835.
(31)Anonymity:“Anniversary of the Late Mr.Cobbett”,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cial Advertiser,March 12,1842.
(32)David Vincent,Literacy and Popular Culture England 1750-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1.
(33)依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空间是公众表达、传播意见,实现监督和控制,由此对以国家权力为主题的公共权力形成影响和约束的媒介和场所,报纸和书籍传媒是它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34)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86页。
(38)《英语语法》一书出版于1818年,以对普通民众普及语法知识为目的,同时融入政治知识的宣传。
(39)见1840年的《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Liberator and Champion)。
(40)Anonymity:“The Labourer's Library,No.1.”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May 1,1841.
(41)Leonora Nattrass (eds),William Cobbett:Selected Writing,London,Picketing & Chatto,1998,vol,6,p.255.
(42)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August 7,1841.
(43)David Goodway,London Chartism,1838-184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22.
(44)克里伍(1794/5-1850)来自爱尔兰,青年时投身工人运动并较为激进,相信共和主义,同赫瑟林顿一起被看作是无印花出版事业的英雄。但是,同洛维特一样,他的激进色彩也逐渐淡化,并与洛维特的组织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克里伍与奥康诺仍保持联系,他是奥康诺领导的全国宪章协会的成员,还担任《北极星》报在伦敦的代理人。
(45)见Cleave's Penny Gazette of Variety,March 03,1838; May 05,1838; May 19,1838; May 26,1838; June 09,1838; July 21,1838; August 04,1838; August 11,1838; August 18,1838; September 08,1838; November 10,1838; February 09,1839; March 09,1839; March 21,1840.
(46)Anonymity:“Cobbett to the Manufacturer”,The Charter,April21,1839.
(47)The Odd Fellow,May 22,1841.
(48)J.Cleave:“Was the late Wm Cobbett,M.P.,in Principle,A Chartist?” Cleave's Penny Gazette of Variety and Amusement,November 28,1840.
